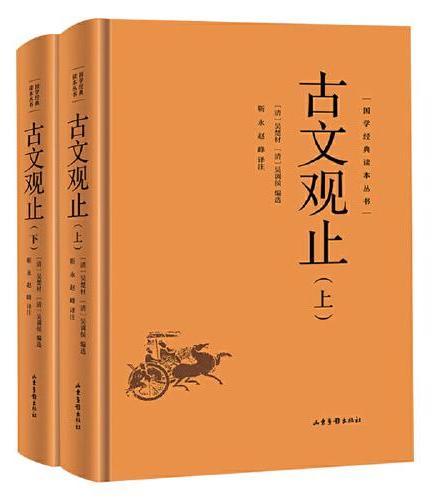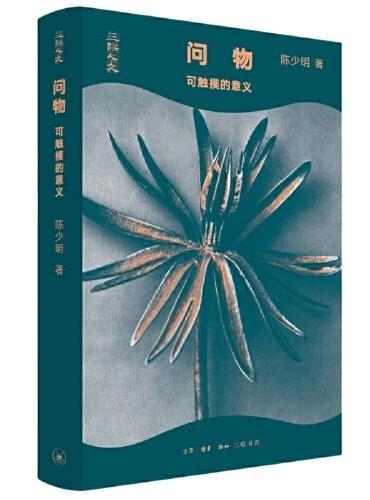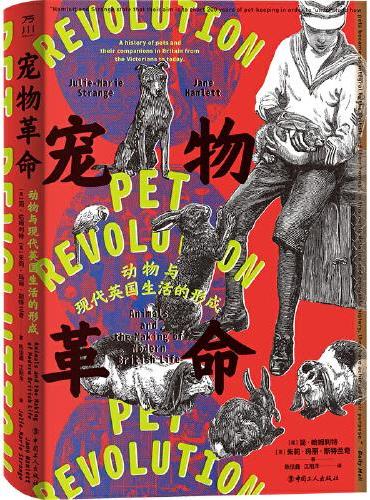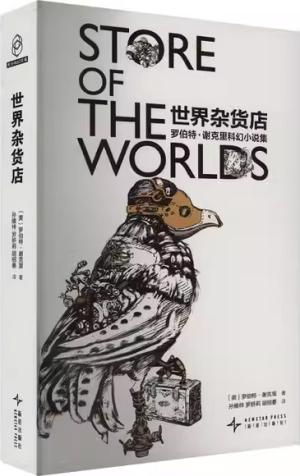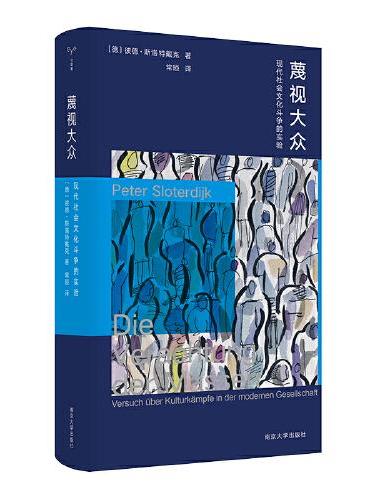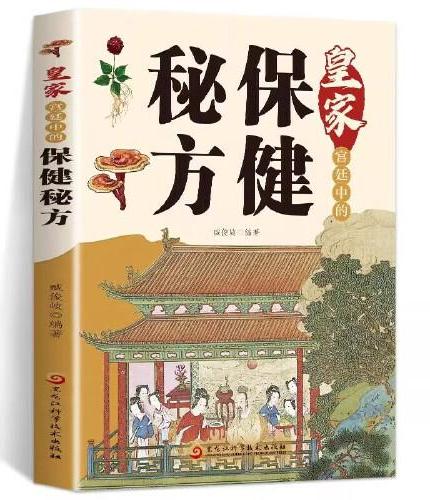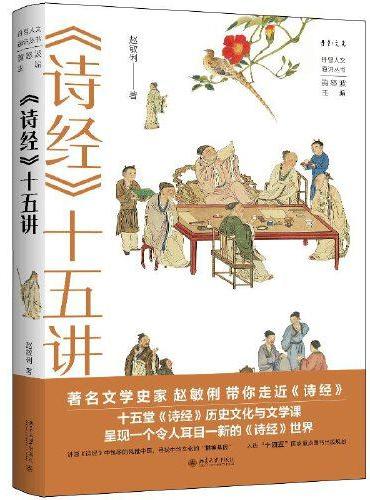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二十四节气生活美学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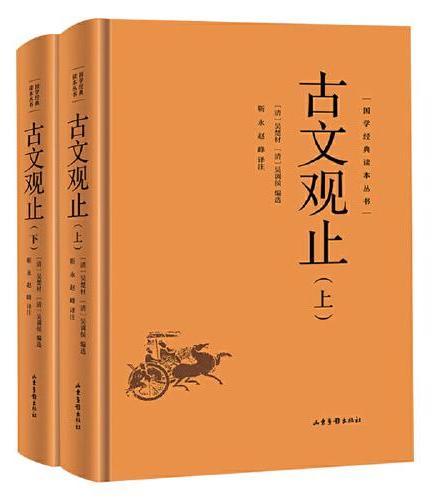
《
古文观止(上+下)(2册)高中生初中生阅读 国学经典丛书原文+注释+译文古诗词大全集名家精译青少年启蒙经典读本无障碍阅读精装中国古代著名文学书籍国学经典
》
售價:HK$
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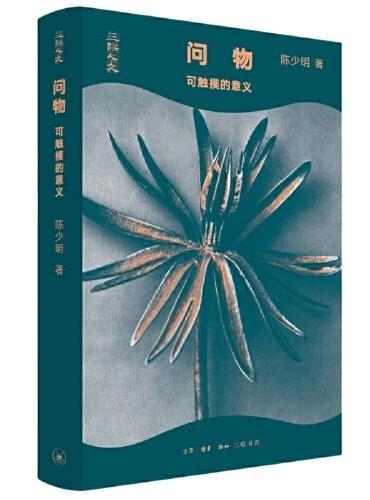
《
问物:可触摸的意义
》
售價:HK$
8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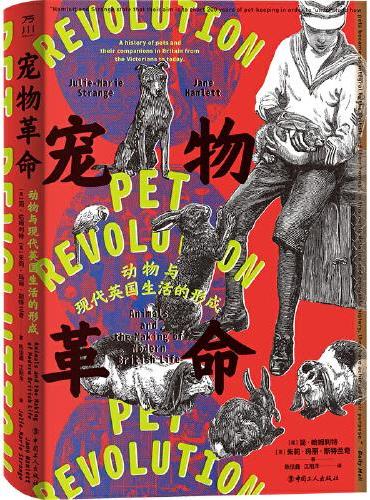
《
宠物革命:动物与现代英国生活的形成
》
售價:HK$
7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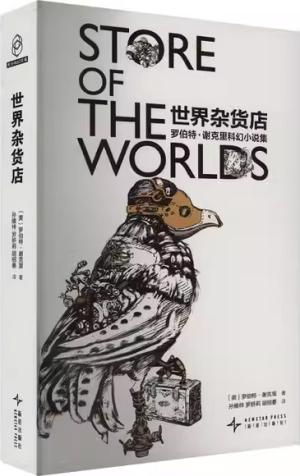
《
世界杂货店:罗伯特·谢克里科幻小说集(新版)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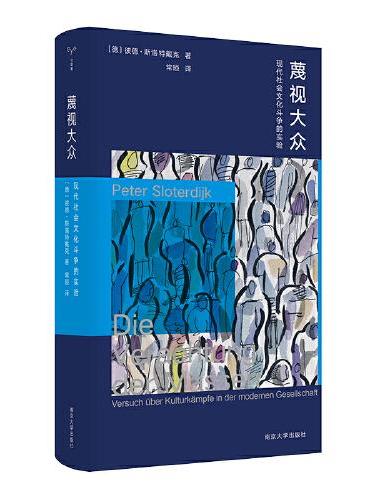
《
(棱镜精装人文译丛)蔑视大众:现代社会文化斗争的实验
》
售價:HK$
6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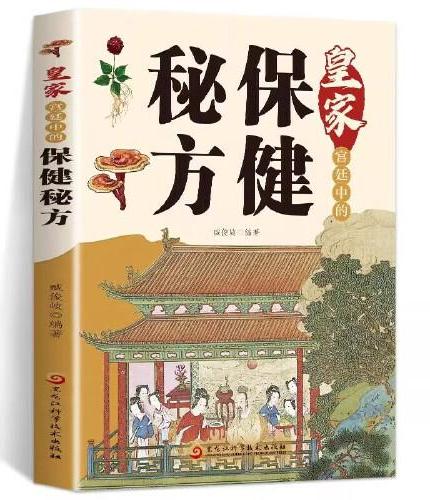
《
皇家宫廷中的保健秘方 中小学课外阅读
》
售價:HK$
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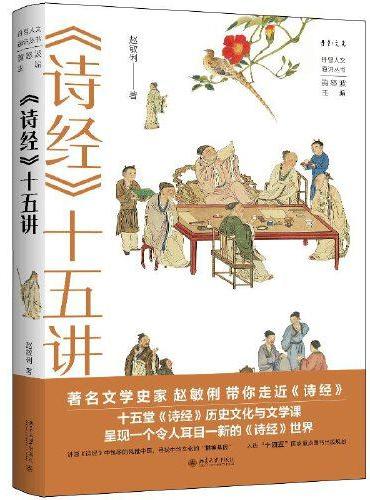
《
《诗经》十五讲 十五堂《诗经》历史文化与文学课 丹曾人文通识丛书
》
售價:HK$
86.9
|
| 內容簡介: |
|
本书是我国著名编辑出版家叶至善先生以编年体的形式,描写叶圣陶一生事迹的传记,本书为读者写出了叶圣陶这位睿智而智慧的老人不平凡的一生与中国命运紧密相连的经历,把近一个世纪波澜起伏的故事讲得栩栩如生,娓娓动听,特别是与叶圣陶相知相交的朱自清、郑振铎、茅盾、丰子恺、周作人、胡愈之、夏丏尊、俞平伯、冯雪峰、丁玲、老舍、巴金、冰心等20世纪中国文坛上的名人逸事生动有趣,让人看到一位大家的人生风采。本书的优点在于并不仅仅只是一个人物的传记,从书稿丰厚的史料和独具一格的顺序描写中,读者可以看到中国新文学史的发展及其重要事件,看到叶圣陶带动和影响了中国新文学创作的为人生和写实的风格;可以了解20世纪初叶及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基础教育的状况和教育工作者的探索,看到叶圣陶对新中国教育事业的规范和走上正轨的重要影响;可以追踪我国编辑出版业及前辈的探索和发展。因此可以说,这本传记也是我国的新文学史、教育史、出版史的一本侧记,对研究新文学史、教育改革和新闻出版发展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具有厚重的史料价值。此外,此书本次出版还插有约40幅珍贵的图片,这些图片是叶圣陶与家人与朋友的合影及书法作品等,特别是叶圣陶与20世纪著名作家如朱自清、郑振铎、茅盾、夏丏尊、俞平伯、冯雪峰、丁玲、老舍、巴金、冰心等的照片,让读者可以一睹名家的真颜,是不可多得的珍藏本。
|
| 關於作者: |
|
叶至善,叶圣陶长子,著名的少儿科普作家、优秀编辑、优秀出版工作者。1945年任开明书店编辑,编辑《开明少年》月刊和其他青少年读物。1952年编《中学生》月刊。1953年转入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成立,任首任社长兼总编辑。曾主持编辑《旅行家》和《我们爱科学》杂志。曾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名誉顾问等职务,获得中国福利会颁发的妇幼事业“樟树奖”,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颁发的老编辑“伯乐奖”。
|
| 內容試閱:
|
父亲长长的一生
《叶圣陶集》头一版共二十五卷,如今添上《传记和索引》一卷,成了二十六卷。主意是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的。他们说,如此规模的一部个人专集,该有一篇比较全面而且简要的作者传记,让读者阅读某一文篇的时候,能多少了解些作者在写作当时的生活、工作、感触、思绪,岂不是好?又说索引更不可少,某一文篇在哪一卷里,没有索引,叫读者往哪儿去找?**版的缺漏,如今知道了,就应该一一补上,这才是为读者负责。缪咏禾同志不惮其烦,已经把索引编得了,还不许我谢,说本是责任编辑的分内事。可是该我分内的传记才写到辛亥革命那一年,离完工还远着呐。
传记想尽可能配合前边的二十五卷往下写。有些人和事,在某篇中已经由作者交代明白,我就写得概括些,甚至只略提一下,请读者参看某些文篇就算了。有些人和事,作者未曾提起过,料想读者希望知道,恰好在我的记忆中还有印象,我就适当写上一些。或详或略,说说容易,实做起来分寸很难掌握。专为了练这一手,我两年多来写了不少篇回忆文字,长的五六千,短的两三百,*短的数各卷中的部分插页说明;看来成绩平平,进步不大。可是时不我待,传记等着发排,我只好再贾余勇,投入对我来说肯定是规模空前,而且必然绝后的一次大练笔了。
饭要一口一口吃。这篇传记还得分成好多段,一段一段地往下写。给插页写说明的时候,我绷着一副编者的面孔,实在太吃力。现在写传记,请允许我回到做儿子的位置上,把父亲唤作“父亲”,把父亲的朋友唤作“先生”,……所有的称谓都复了原,下笔的时候可以省却一些徒劳的思虑。篇名就用《父亲长长的一生》。父亲活到九十四岁,临终前,头脑尚不糊涂,这一生真活得够长的。
这七百来字,就算作序。
2003年一月五日
01
父亲的一生虽然那么长,但是传记还得从他出生写起,而且得把家门交代清楚。想起中学时代看过不少西欧的长篇小说,主角出场之前,作者不厌其烦,把他父系母系祖宗三代,一一交代明白,好像特意给当时新兴的遗传学研究提供实证似的。细细读来固然颇有趣味,过于啰唆也只得草草翻过。我如今做的,不也是这件营生吗?幸而我们这一支没留下可查的家谱,不必从尽人皆知的那位好龙的叶公写起;人口又不繁孳,也啰唆不到哪儿去,能写多少就写多少吧。
记得小时候听祖母讲过一回家史。她说:“你们叶家祖上才叫阔,齐门外头半条街都是你们叶家的。上代头开了爿生猪行,两百来斤重的肥猪,出出进进,哪一天不是好几十,你说罪过勿罪过。结果倒好,长毛来了,一把火烧个精光,齐门外成了一片白地,你们叶家本来也人丁兴旺,一下里都逃散了。回来的只有你阿爹和他堂弟两个,别的人都死在外头了,尸骨无存。”祖母说到叶家,头里总得加个“你们”,这是她母亲的口吻,这位朱老太太大概认为她女儿不太能干,甚至太不能干,先是舍不得女儿出嫁,等到年龄过了头,非出嫁不可了,做母亲的更放心不下,跟到了叶家来帮女儿——就是我的祖母——料理家务,直到八十六岁过世。那时我已经五岁,还记得穿上白布大褂,跟在也穿白布大褂的父亲后头,把老太太的灵榇送到朱家来接的船上。
祖母说的堂兄弟俩,哥哥就是我祖父。老人家名仲济,字仁伯,一直在大儒巷吴宅当账房先生,主要管收田租。父亲是甲午战争那一年——一八九四年十月廿八生的;祖父已四十七岁,都说是老来得子;祖母也年将三十,她是我祖父的第二个续弦。前头那两位,一位不知死于什么病,一位是难产,把肚子里的孩子一同带走了。因为有这么个不知是哥哥还是姐姐,我父亲排行第二,小名“二官”。后来他刻过一个小小的便章,阴文“叶二之章”四个篆字。生了我父亲之后,祖母又生了两个女儿。大的在十三岁上死于暴病,好端端的,忽然肚子痛得在床上打滚,没挨到天亮就断了气——这也是祖母告诉我的。因而我只有一位姑母。父亲在过世前五年写的《略述我的健康情况》,有一段列举年逾古稀的长辈,父系的母系的都说到了:寿*长的数我的祖母,九十六岁;居第二的是我祖母的母亲,八十六;我祖父和他的母亲并列第三,都是七十二。*后特地附一笔,提到自己的妹妹——我的姑母。父亲说:“她小我八岁,健康情况比我差,可是饮食起居还如常。”姑母一九八五年就亡故了,临终前,父亲让我陪着去医院探望,她面容非常消瘦,神志已经不清了。父亲那篇“略述”是一九八三年年底前写的。他说:父系母系中高寿的人数如此之多,可能是他们兄妹俩都年逾八十的因素之一。我看不仅“可能”,而且“必然”。所以我很不注意锻炼和保养,把宝全押在了这个不可捉摸的遗传因子上。
祖母讲家史,明明说我祖父有个堂弟,父亲这篇“略述”却半句也没提到,大概因为对祖父和父亲这一房来说,他的老叔和婶母已是旁系,他们俩都在六十前后过世了。这位老叔是教书先生,名朝缙,字绶卿。婶母不能生育,肚子里长了个瘤子,为了有人服侍,领养了一个女儿,我父亲才有了一位堂姐。在民国初年的日记上,还记着堂姐出嫁那天,由他跟着花轿送她去男家的情景。过了不久,老叔的东家迁居上海,也许做了官,也许为了经商,总算把老叔带了去。书用不着他教了,子弟们都进了洋学堂,专让他书写各方面的应酬信牍。把个病恹恹的老伴撇在苏州家里,叫他怎么能安得下心来。父亲在上海尚公学校的日子里,隔两三个星期去看老叔一趟。那东家很阔绰,底下人也不少,却从没有人打过招呼,倒出一盅茶来。叔侄俩谈些什么,还得找附近的茶馆或小酒店。父亲哪能不体会老叔心头所受到的压抑,他已经成了个书办,不再是什么西席了。东家的姓氏,父亲在日记上从没提过,我想不是偶然的。
对祖父的东家,父亲也没留下什么好印象。祖父在大儒巷吴宅当账房,到吴保初手里至少是第二代了。抠门是一般地主的共性。听人家说我父亲印章刻得不错,他拿了块石头来到账房里,对我祖父说:“烦令郎有空,随便刻个姓字章吧。”父亲初当小学教员,像孩子似的也盼着放暑假,好自由自在地读几本想读的书。没料到又让这位东家早给安排妥了,他对我祖父说:“令郎暑假里没有什么事,陪我那小的温温功课吧。趁中午前凉快,每天温两个钟头。闲着不也是闲着。”我祖父哪能不答应。吴宅的田产想来不少,每年秋收之前,我祖父得把收租的单据准备舒齐。我见过那玩意儿的复制件,记得叫“由单”,项目烦琐之极。佃户姓名,地块位置、大小和等级,必须填写清楚。然后按本年水旱丰歉,由官府核准的成数,算出每一块地该交纳多少稻谷,再按粮业同行公议的谷价,折合成银两,各一式三份。如此年复一年,我祖父的精神渐渐不济了,
吴保初似乎没想到给账房添人手。老人家只得把自己弄舒齐的一份带回家,让我父亲下了课替他誊写另外的两份。下乡收租倒不劳账房先生,自有村镇上一些叫作“催甲”的地头蛇包揽了,于是佃农又被加上了一层中间剥削。
那些年,四乡农民抗租的风潮已时有发生。有些地主变卖了祖产,成了新兴工商业的老板。吴保初另有一功,他擅长谋干,当上了锦州电报局局长,临动身前听说我父亲在小学里受到排挤,丢了饭碗,对我祖父说他先去锦州看看情形,好歹给弄个差使。我父亲很不愿意进电报这一行,又想借此出关去见见世面也不坏。正在犹豫,吴保初托便人带口信回来了,说关外冷得能冻掉鼻子,没长毛大氅狼皮褥子休想过冬,等明春再说吧。到得第二年春天,他调到了哈尔滨,那就更甭说了。谁知不然,他写信回来说不久就调回苏州,不知他使的什么神通,还真个回来了。于是宾客盈门,恳求援手提携的不断,我祖父就不去凑这个热闹了。
02
父亲早年出版的如《隔膜》《稻草人》等,封面上都印着“叶绍钧著”。“绍钧”是父亲的名,大概在出生时他老叔给取的,家里认真读过“子曰”的只有这位老人家。还有个字“秉臣”,可能十一岁上为报名应考童生,也是请他老叔给取的。旧社会里就有啰唆规矩。孩子出世了起个名,当然是必要的。男的将近成年,准备跨入社会了,必得起个“字”,也叫作“号”。长辈仍旧直呼其名,朋友之间非相互称号不可,直呼其名是很不礼貌的,更甭说对长辈了。而自己称名,则表示谦虚。号取多少个都成,可以自己取,可以请别人取,其实还包括众人硬给起的绰号,如“周扒皮”,如“孔乙己”。
有人说辛亥革命了,我父亲嫌“秉臣”太封建,自己改字“圣陶”。这是想当然,事实并非如此。证据之一,辛亥前一年,我父亲开始作日记,日记本封面就写的“圣陶日记”;证据之二,后来在报刊上发表的短文,还颇有一些署名“秉臣”的。“圣陶”这个号是草桥中学的沈老先生给取的。那一天同学们起哄,都开了自己的姓名请沈先生取号。老先生古书念得又多又熟,很愿意露一手似的,当场给我父亲写了“圣陶”两个字,后头用小字注明“圣人钧陶万物”。“圣陶”这个号,当时就在同学中叫开了。父亲说,他到老也没找着这句话的出处,只知道“陶”就是烧制瓦罐的黏土,把黏土团旋成坯的那个转盘,叫作“钧”。“圣陶”两字,无非是用“圣人之道”来陶冶自己、教化后进的意思。如此说来,给我父亲起名的老叔当时年纪还轻,塾师还没当够,还希望侄儿长大后继承自己的事业。沈老先生没给我父亲上过课,单凭“绍钧”这个名,批上了不着边际的赞语“圣陶”。父亲后来把许多心血花在教育事业上,我看并非由于受到了自己的名和号的激励。
父亲是两房合一子,全家长辈都把他看作掌上明珠,自幼受宠爱是必然的了,要是在如今,还不成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小皇帝?亏得我们家的经济情况一年紧似一年,祖父又很看不起那些不自振作的纨绔子弟。例子就在眼前:当时我们家租住在潘姓祠堂的后花园里,那潘家不就是这样败落的吗?要不然,怎么会把祖宗手里建造起来的家祠,卖豆腐似的分租给小户人家呢?那后花园,想来跟鲁迅先生笔下的百草园差不多少。我父亲也自小喜欢野花闲草,却从没写到过在那个荒园里度过的愉快自在的童年,我如今也没法凭空虚构。
如今兴的是望子成龙,儿女还没进幼儿园,做父母的就忙不迭教孩子识字认数。据父亲说,他进私塾前已认得三千来字,是我祖父亲手写了方块字,一个一个教他念的。我有点儿为祖母抱不平,怎么把她的功劳全给抹杀了呢?记得我牙牙学语的时候,祖母,还有太外祖母,常把我抱在膝盖上,按节拍摇着我,教我跟着念民歌和童谣。歌谣可不是单个的方块字,是字组成的词,是词连成的句子,活泼有趣、声调悠扬的句子,没有教训,念着不感到压力,我学了一支又一支,少说也有上百支。八十多年过去了,我还能完整地背诵出十几支来。其实父亲也不曾忘记他幼时从母亲和外祖母那儿,*早受到的语言教育和文学启蒙。在他编写的小学国语课本中,就有好几支经他加工的苏州童谣,有一回向中学生做广播演讲,还引用过一支《咿呀咿呀踏水车》,因为太长,记录上把后半截换成了删节号。我想有些报刊常命题征询知名人士:“对您一生*有影响的是哪一本书?”从没见过答案是“小学语文课本**册”的。父亲屡次谈自己的文学历程,都忘了提到自己的母亲,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二十世纪的**个春天,祖父把我父亲送进同巷的陆姓家塾附读。当时我父亲才六岁,只记得塾师姓黄,先教念《三字经》《千字文》。课堂是花园中的一座大厅,挂着块“报春草堂”四个字的匾。园里有亭有轩,种了几十棵梅树,还有李树杏树,想来跟《红楼梦》中贾府的家塾也差不多少。可惜才念了一年,陆家的各房闹分家,硬把一座大好宅院,分片卖了,家塾只好关门大吉。有一房迁到了萧家巷。父亲的日记中记着,他在中学时代常去萧家巷找陆家四兄弟闲聊,待他们一一成了家,也各奔东西,不知哪儿去了。一九五九年过苏州,父亲特地打听过,已经很少有人知道悬桥巷曾经有过这么一座清丽的花园了。
离开了报春草堂,父亲被送进了张元翀老师自设的书塾。有一件事非提前记下一笔不可:顾颉刚先生和我父亲在那儿开始成为同学,成为亲密交往八十年的老朋友。悬桥巷东西向,南边靠河;潘家祠堂对面有座小桥,过了桥右首边就是顾先生的家。一九**年我和妹妹弟弟陪父亲去过,仍旧叫作顾家花园。其实在顾先生出生以前,花园已经废了,租给了一家制线香的作坊。父亲说他下了学,跟随顾先生来这儿看水牛。香作里有头大水牛,老戴着眼罩,拉着石磙转圈子,把木屑香料碾成粉末。两人都不敢走近,至多蹬着小脚向它吆喝两声,或者拿根长竹竿在它屁股上点这么几下。大水牛并不理会,仍旧不紧不慢踱它的方步。七十多年过去了,香作早已不存在,老房子倒留着一些。看门的把我们领进顾先生旧时的书房,找了把椅子让父亲消停片刻。
03
张元翀老先生想来中过举,没这点儿名望,人家怎肯把子弟交给他教?又特严厉,顾颉刚先生说他“待童子若囚犯”,戒尺不离手。塾中的书房可不是如今的教室,一间大厅里七八个学生,年龄和程度都参差不齐,读的也不是一本书,这个念《论语》那个念《孟子》。老师只好一个个轮番教,给这个教几行,给那个教一段;先管识字断句,等学生背熟了,回过头来逐字逐句讲解。老师今天教的,学生第二天得照原样向老师还一遍;要是背不出答不上,就摊开手心挨戒尺吧。顾先生说他常常挂着眼泪回家,他父亲看他手掌肿得像半个馒头,连连说“怎么能这样呢”,第二年就不让他念书塾,留在家里自己教。我父亲倒从没尝过戒尺的滋味。同学中数他年纪*小,也许占了些便宜。而我祖父,自己也舍不得打的,怎能让娇儿受这样的苦楚;自己又教不了,只好做出规矩,要我父亲念熟了老师教的,方准许吃夜饭。
顾先生还说,当时和我父亲虽然同窗接席,却连谈话的机会也极少。小时候我听父亲说,只等老师出门拜客,同学们就闹翻了天,在书房隔壁的那张炕床上扮演《武松打虎》。甚至也敢把辫子上扯下来的长发连接成“电线”搞起了“秘密通信”。一九六五年动员老作家给孩子们写文学作品,父亲连续写了五篇,总名《一个少年的笔记》,想给高小学生自己寻找作文题材做些个榜样。在小标题《你们幸福了》那一篇中,这位少年记下了晚间乘凉,听老爷爷讲幼时念书塾的趣事。不用说,这位老爷爷就是我父亲,除了末尾上房顶一段,讲的是后来在小学里龚赓禹先生的故事,其余的全发生在张元翀老师设的书塾里。
在严师和慈父异曲同工的关怀下,父亲总算念完了当时士子必读的“四书”,还有《诗》《易》《左传》。在八九岁上老师说他可以开笔了,就是对圣人的训词有了些儿初步的理解,可以开始学做文章——代圣人立言了。出的题目《登高必自卑》,还关照他应当写到“为学”方面去。父亲依照他的吩咐写了八十多字,结尾是“登高尚尔,而况于学乎”。老师看得摇头晃脑的,提起朱笔,在“而”和“乎”字旁都加了双圈。想来父亲在当时是颇为得意的,回家给祖父看了,祖父一定像接到了儿子中举的报条一般高兴。一九四〇年年底前,父亲写《论写作教学》,用这件亲身经历开的头。我想读者定能理解,我父亲绝非夸耀自己自小聪慧,而是为了批判那束缚思想的应试教育,把它捡来做引子。
平心而论,张老先生可以算紧跟时代了。一九〇一年,清政府宣布废除八股,以策论取士;他出的确是策论题,可是指导学生走的仍是老路,也可见教学改革之难。废科举办学校的言论常见于报
刊,念了书塾不应试,叫孩子往何处去呢?我祖父一定被这个问题困扰过。乙巳年(一九〇五),秋闱照常举办,看来科举一时还废不了,祖父决定让父亲去试试,不在乎中不中,让他先历练历练,免得以后怯场。父亲借此撒娇要挟,说得让他带两个马铃瓜去,夜里好解渴。原来点名进场在半夜以后,等到天蒙蒙亮,才有人抬着白纸糊的大灯笼,在考棚的巷子里绕一周,考生们急忙抄下灯笼上的考题,各自回考棚对着蜡烛苦思冥想,只要凑成三百字以上的一篇文章,就可以交卷出场。祖父微笑着,答应并兑现了父亲的合理要求。由于此,过了整整十八年,父亲才有可能依据那一夜的见闻,写成了他那一万多字的短篇《马铃瓜》。
我把编在《叶圣陶集》第二卷中的《马铃瓜》翻出来重温了一遍,又触发了不少回忆。小说是随笔式的,有一段提到做舅父的三项义务。我岳父到绍兴府考举人,也是舅父送去的,据说那位舅父喝多了酒睡着了,竟耽误了他听点名入考场的时辰。到我小时候,教育制度已大大改变,当舅父就省事多了,只剩下外甥头一回剃发,还得请舅父抱着。小说中也有一些是我先前没注意到的:当时苏州已经有了中学校,大概是庚子之后教会办的,否则哪敢跟科举考试对着干,牌示学生如有改名冒试,查出立即除名。至于那位号称“天王”的衙内是否是被派来捣乱的,小说没加暗示。还有件事有点奇怪,小说有几处提到上回赶考怎样怎样,可是父亲明明对我说过,他只参加过这*后一次科举考试。虽说小说可以虚构,做这样的虚构有什么必要呢?是否为了暗示科举制度已气数将尽,到了回光返照的地步呢?谁都知道,杜绝夹带是历来任何考试的规矩,应试必须经过严格搜身,才能领考卷跨进贡院的高门槛。这一回“大放送”,什么书都可以带,从《五经备旨》到《应试指南》,都是石印小字本。还有那人手一本的《圣谕广训》,更非带不可了;老师一向不教,学生从未念过,可是应考必须恭默皇上的“圣谕”两三百字,跟卷子一并上交。阅卷的师爷照例不看。大家都知道不过虚应故事而已,就是“赵钱孙李”默上两遍也成;这一回可以公然抄录,岂不更加省心。父亲是当作笑话跟我讲的,小说只提到书名,没写上这一段说明。
果不其然,才过不久,清政府就颁发上谕:丙午年(一九〇六)罢科举,办学校;又传出小学毕业相当童生,中学毕业相当举人的话来;好像为了安定民心,却又遮掩不住无可奈何的心态。茶馆里渐渐传开,这一下动真格的了,苏州府属的长(长洲)元(元和)吴三县合在一起,一口气合办四十所小学,开春全部上课。我祖父想,既然念完四年就是个童生,让我父亲去试试吧。又听我父亲说,颉刚这孩子得到了他父亲的准许,已决定去考夏侯桥的那一所。我祖父思忖:顾老挑中的一定错不了,可是路实在远,上下午两个来回,少说也有八九里吧,叫个实足年龄才十一岁的孩子怎么受得了呢?祖父下了狠心,把家搬到了离夏侯桥才半里多路的濂溪坊。
公立小学开学那一天,顾先生早早地来到濂溪坊,跟我父亲俩手拉着手跨进夏侯桥小学的大门。教室是才刷新的大厅,明亮的玻璃窗上挂着五色纸环联成的彩带。课桌的桌面是可以掀起来的,坐的也是洋式的带矮靠背的椅子,都排得齐齐崭崭。墙上挂着乌油油的黑板,听说老师用的粉笔还是从日本带回来的,当时苏州还没有粉笔作坊。尤其那具精致的风琴,真叫人忍不住要伸个指头在哪个键上轻轻按它一下。甭忙,耽会儿就上音乐课了,课程表上写着呢。除了国文,还有算数、历史、地理、博物、音乐、美术、手工、体操。哪儿来的这许多名目?其实一点也不奇怪,都是老师从日本带回来的。
请别把这一班可敬的先驱者当成了掮客。经过庚子年一九〇〇义和团和八国联军,这一番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不相匹配的较量,更使他们看清楚,大好中华被列强瓜分的那一天已经不太远了。清政府镇压变法,不自振作,只得由他;办学校启发民智,激励知耻力行,总是利国利民的事。他们自愿去日本受短期的师资培训,主要学的是科目的设置和教学方法。苏州有了这样一班不求名利的实干家,才有了中国人自己办的**所作为样板的新式学校。
那些个小学的教员似乎个个是通才,什么课都能教,而且特别注重孩子的品德教育。我父亲那时身材矮小,正经跳绳踢毽子都不会,偏学会了爬竹竿。夏天院子里搭了凉棚,他顺着粗竹竿爬上房顶,坐在屋脊上逗底下的同学。正好龚赓禹老师进来,抬头看见学生上了房,连连说:“你好……好好地……快下……下来。”我父亲就双腿夹住竹竿溜到了地面上。龚老师瞧他没伤着什么,也没责备。我父亲到老也没忘记这位好老师。有一回上博物课,他挟了一棵蚕豆一棵油菜来到课堂,跟学生讲这是蝶形花冠,这是十字形花冠,还掰开花瓣,教学生识别雌蕊雄蕊。一朵花会有这许多讲究,我父亲从来没想到过。栽培花木,观察它们的生长,逐渐成了他毕生的爱好,在他的诗词、歌谣、散文,以及晚年写给俞平伯、贾祖璋等先生的信中,有不少有趣细致的记载。
音乐课也从没见过,老师一边教学生唱,一边还比画着教学生表演;有时让学生像兵士那样排着队,一边走一边唱行军歌。也非常注重体操,除了徒手操“立正”“开步走”,还有哑铃、棍棒等器械操。爱国主义教育从不间断,大都用老师们自己编写的教材。一九〇六年冬,为抗议美国政府驱逐华工,在历史课上,朱遂颍老师宣讲美国修建横贯东西海岸的大铁路,蒙骗了成千上万华工背井离乡,漂洋过海,生活困苦又受尽虐待,被称作“猪仔”;现在铁路修通了,却下令把一无所有的华工尽行驱逐。朱老师讲得声泪俱下,孩子们都感同身受,要求列队上街游行,高呼对美国政府抗议的口号,宣传抵制美国货,挨家挨户劝说莫用美孚油。那时苏州还没有电灯,晚上大多用煤油灯;而美孚牌煤油是美国货,这是谁都知道的。在苏州城里,反帝群众运动,可以说是从这一次开的头。
老师经常跟孩子们说,爱国要从热爱自己的乡土做起。沧浪亭西南角上有座五百名贤祠,既小又偏僻,似乎一向很少人知道。一九六二年年初,我跟父亲去苏州,说好久没去沧浪亭了,这一回发个心去看看吧。拣背静的地方走,无意中绕到了这座小祠堂前面。父亲有点儿累了,说进去歇歇脚吧。祠堂只像一条比较开阔的走廊,朝南的一边是门窗,五扇北墙上都横五竖四,齐齐崭崭嵌着二十块长方形的碑,不知是水磨青砖还是青石板,共一百块,每块碑上刻着五位名贤的半身像和传略。字实在太小,尤其是高处的,我踮起脚跟也很难看清楚。父亲说:“不用看了,打头的那位是吴泰伯,孔子的学生言游也在内。总之都是对苏州有过贡献的乡贤。我念小学的时候,章伯寅先生常带我们来这里讲墙上的名贤。特地指着顾亭林的像,要我们牢牢记住他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跟我们说:‘五百名贤还没满额,后边还留着地位等你们呢。’”果然后边四五块碑还空着。用心如此,真可以说良苦了。
我没见过章老先生,是从父亲在抗战期间写的《我们的骄傲》中认识他的。我知道这篇小说的主人公黄老师,原型就是章老先生。苏州沦陷后,汉奸维持会胁迫他出山,要他做教育界归顺敌人的带头羊。为保持民族气节,他孤身一人,历尽艰辛来到重庆。当年在夏侯桥的四个学生打听得他暂住川东师范,约定了日子一同去探望他慰问他。在小说中,“我”的原型不用说就是我父亲自己;戈君,是顾颉刚先生;孙君,是周勖成先生;邹君,是章元善先生。黄老师见是他们,说的**句话是:“啊,你们四位,准时刻来了。”守约遵时的好习惯,正是三十二年前,章老先生以身作则的教育成果。又说:“你们四位,往常也难得见面吧。”正是如此,除了周先生为了创办巴蜀学校,到重庆已多年,其余三位都是暂时歇脚的过客,不久就劳燕分飞了。多么难得的人生瞬间,四个幼年时代的同学,居然能围坐在老师膝前,细细地听他讲自己的生活故事,浸透着不屈的人格的故事。从父亲写给留守在上海的朋友的信中,可以查到这次可纪念的会面,是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七日。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