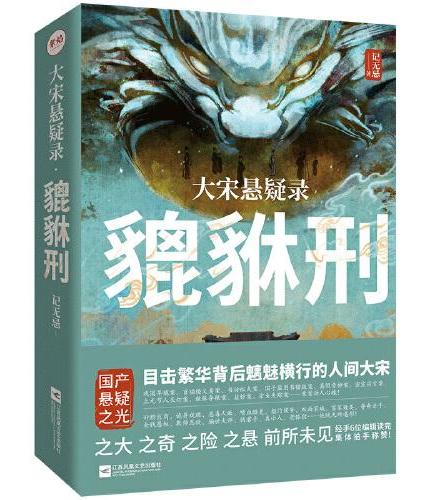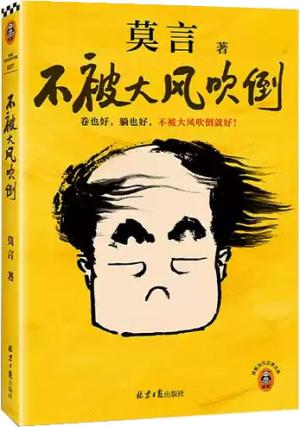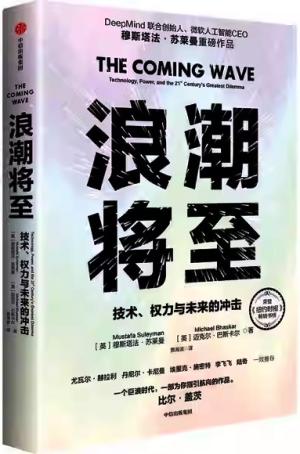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成吉思汗传:看历代帝王将相谋略 修炼安身成事之根本
》
售價:HK$
61.6

《
爱丁堡古罗马史-罗马城的起源和共和国的崛起
》
售價:HK$
76.8

《
自伤自恋的精神分析
》
售價:HK$
5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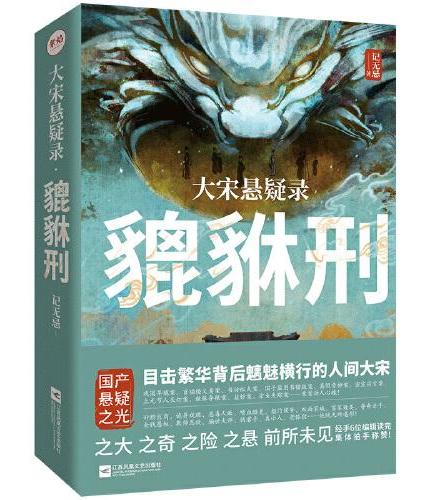
《
大宋悬疑录:貔貅刑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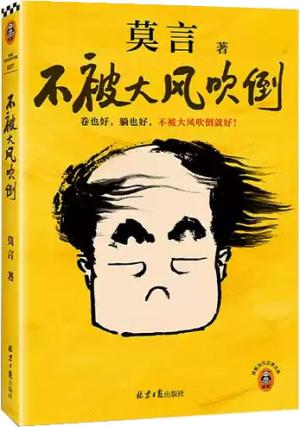
《
不被大风吹倒
》
售價:HK$
65.9

《
人生解忧:佛学入门四十讲
》
售價:HK$
107.8

《
东野圭吾:分身(东野圭吾无法再现的双女主之作 奇绝瑰丽、残忍又温情)
》
售價:HK$
6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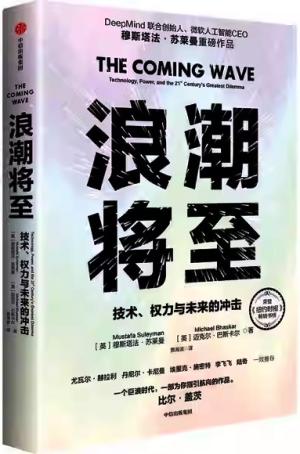
《
浪潮将至
》
售價:HK$
86.9
|
| 編輯推薦: |
教育部重点推荐的新课标同步课外阅读丛书:
中小学生必读丛书
教育部推荐书目
新课标同步课外阅读
全球百部英文小说第2名
影响村上春树*深的作品
一曲“爵士时代”的华丽悲歌
作家以凝炼而富有浓郁抒情气息的语言,不仅刻画出“爵士时代”一个“美国梦”从鼓乐喧天到梦碎人亡的悲哀,它也写了“人类*后的也是*伟大的梦想”的顽强生命力。
|
| 內容簡介: |
|
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空气里弥漫着欢歌与纵饮的气息。一个偶然的机会,穷职员尼克闯人了挥金如土的大富翁盖茨比隐秘的世界,惊讶地发现,他内心惟一的牵绊竟是河对岸那盏小小的绿灯——灯影婆娑中,住着他心爱的黛西。然而,冰冷的现实容不下飘渺的梦,到头来,盖茨比心中的女神只不过是凡尘俗世的物质女郎。当一切真相大白,盖茨比的悲剧人生亦如烟花般,璀璨只是一瞬,幻灭才是永恒。盖茨比是了不起的,他用生命谱写了一曲“爵士年代”的哀伤恋歌,却只有叙述者尼克一个人得已倾听。盖茨比的悲剧是“美国梦”破灭的典型代表。一阕华丽的“爵士时代”的挽歌,在菲茨杰拉德笔下,如诗如梦,在美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墨色浓重的印痕。
|
| 關於作者: |
|
菲茨杰拉德,美国杰出的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人间天堂》、《美与孽》、《了不起的盖茨比》及一百七十多部短篇小说。他凭借《了不起的盖茨比》奠定了在美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被誉为“爵士时代”的“桂冠诗人”、“编年史家”,是“迷惘一代”的重要作家。
|
| 目錄:
|
译者序
了不起的盖茨比
一颗像里茨饭店那么大的钻
五一节
重访巴比伦
|
| 內容試閱:
|
一
在我年少无知、不谙世事的时候,父亲便给了我一个忠告,这个忠告至今还萦绕在我的耳旁。
“每当你想要批评什么人的时候,”他对我说,“你一定要记住,并不是每个人都拥有你的那些优越条件。”
父亲没有再多说什么,但我们之间有一种强烈的默契,我明白他话中的弦外之音。因此,我养成了不随意评判他人的习惯,这个习惯致使许多秘密的心灵向我敞开。与此同时,这也导致一些无聊之徒和性情古怪之人与我纠缠不清。大学时代的我不幸被指责为政客,因为我总能觉察到很多行为不检点、来路不明的人的隐私和悲苦。然而,对人乱下断语是不可取的。直到现在,我仍然担心自己待人过于严苛,害怕自己忘掉父亲对我的谆谆教导:人的善恶感是与生俱来的,每个人的道德观念都有所差异。
在自我吹嘘了一通我的宽容性情之后,我还是必须得承认这种宽容是有限度的。人的品行有的基于坚硬的岩石,有的出于潮湿的泥沼,不过超过一定的限度,我就不在乎它的根源了。去年秋天我从东部回来的时候,真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穿上军装,在道德上永远保持立正的姿势;我再也没有兴致去探索那些悲惨的灵魂,让人对我推心置腹。只有盖茨比—这本书的男主人公—是一个例外。盖茨比身上分明代表了我所蔑视的一切。不过,如果说人的品格是由一连串美好的行为举止组成的,那么,盖茨比倒也不乏有他的光彩和伟大之处,不乏有一种对生活的高度感应能力和异乎寻常的乐观。
可以毫不谦虚地说,我们卡拉韦三代都是这个中西部城市里的名门望族。据家谱记载,我们还是苏格兰贵族布克里奇公爵的后裔。实际上,我们这一家系的缔造者是我的伯祖父,他在五十一岁时来到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他雇了一个人去替他打仗,自己却做起五金批发生意,这门生意现在传到我父亲手里经营。
可惜的是我从来没见过自己的伯祖父,不过家人都认为我长得像他—依据就是一直挂在我父亲办公室里的那幅颜色发黄的伯祖父画像。一九一五年我从耶鲁大学毕业,正好是我父亲从母校毕业的第二十五年。不久之后我参加了那场酷似公元一世纪初条顿民族大迁徙的世界大战。我是那么沉迷于那场反击战,以至于回到美国后我反而觉得无所事事。在我看来,中西部现在已经不再是世界的繁荣中心,倒像是这个世界上边远的贫瘠之地—因此我决定到东部去学做证券生意。我接触的那些人都在做证券生意,所以我认为这门生意再多养活一个单身汉应该没有问题的。我的姑舅叔婶们一起商量了这件事,那慎重的态度就像是为我挑选入学的私立高中一般,最后他们表情严肃又略带迟疑地说道:“唉,那就这样定了吧。”父亲答应资助我一年,几经耽搁之后,在我二十二岁的那年春天,我终于到了东部。那时我还以为自己要在这儿住一辈子呢。
第一件实际的事情,是寻找住房。那时正是温暖和煦的季节,我刚刚告别了有着宽阔草地和葱绿林木的乡村,因此当办公室里的一位年轻同事建议我和他到近郊一起租房时,我觉得这真是个好主意。他去租了房子,一间久经风吹雨淋的木板平房,月租金八十美元。就在这个节骨眼,公司派他去了华盛顿,结果我只能独自一人搬到那里去住。和我做伴的有一条狗,一辆旧道奇牌轿车和一位芬兰籍的女用人。她为我整理床铺,做早饭。有时她会一边忙碌,一边念叨着芬兰的谚语格言。
这样寂寞地待了一两日之后,一天早晨一个陌生的男子在路上拦住我。
“嘿,到西卵镇怎么走?”他询问道。
我告诉了他。当我再往前走的时候,我便不再寂寞了。他这一问让我成了一个向导,一个引路人,一个土著居民。他在无意之间给予我一种很亲密的信任感。
我就这样安顿下来。当阳光日渐和暖,树顶冒出嫩嫩的绿叶时,那熟悉的信念在我心中复生了:随着夏日的到来,生命又将重新开始。
且不说别的,有那么多的书要读,清新宜人的空气中也有那么多营养能汲取。我买了十几本有关银行业、信贷和投资证券的书,一本本烫金的书整齐地摆在书架上,就像造币厂新铸的钱币一样,随时准备揭示迈达斯、摩根和米赛纳斯的致富秘诀。除此之外,我还打算阅读一些其他方面的书籍。在大学的时候,我便喜欢舞文弄墨。有一年我给《耶鲁新闻》写过一系列表面上一本正经,实际上平淡无奇的社论—现在我准备重新成为所谓的“通才”,也就是那种最肤浅的专家。
我租的这所房子位于北美最离奇的一个村镇。这个村镇位于纽约市正东方向的一个细长而奇特的小岛上,除了大自然奇观之外,还有两个地方的形状异乎寻常。离城二十英里远的地方,有一对奇大无比的鸡蛋状的半岛,它们简直一模一样,中间隔着一条小湾,这条小湾一直伸进西半球那片恬静的咸水—长岛海峡那个巨大的潮湿的场院里。它们并非正椭圆形,而是像哥伦布故事里的鸡蛋一样,在着地的那头都被压成扁形了。它们在长相上的惊人相似会使翱翔天际的海鸥惊异不已。而对于没有翅膀的人类来说,一个更加有趣的现象是:这两个小岛除了形状、大小一样之外,其他方面都会让你觉得截然不同。
我住在西卵—比较不时髦的一个小岛,不过这只是两个小岛最表层的区别,并不足以表现它们之间那种稀奇古怪而对立的反差。我的房子挤在两座每季租金要一万二到一万五的大别墅之间。我右边的那一幢,有一座大理石堆砌的游泳池,以及面积四十多英亩的草坪和花园—这便是盖茨比的公馆。那时我还不认识盖茨比先生。相对而言,我自己的房子实在很难看,幸好它很小,不容易被人注意到,因此我才有机会欣赏一大片海景以及我邻居草坪的一部分,并以与百万富翁为邻而感到自豪—所有这一切只需每月支付八十美元。在小湾的对岸,东卵豪华住宅区里那片洁白的宫殿式的大厦光彩夺目,而那个夏天的故事正是从我开车去住在东卵的汤姆·布坎南夫妇家吃饭的那个晚上才真正开始的。黛西是我的远房表妹,而汤姆是我在大学里就认识的朋友。
大战刚结束的时候,我还在他们家住过两天。汤姆擅长各种运动,他是耶鲁大学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橄榄球运动员之一,可以说是闻名全国的。这人在二十一岁就已经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从那以后,他的一切不免有些走下坡路的味道了。他家里十分富有,在大学时他挥霍金钱的程度就已经遭人非议了。现在他离开芝加哥迁到东部,搬家的排场更是令人惊讶不已。举个例子来说,他从老家把打马球的马匹全部运了过来。在我这一辈人中竟然还有人阔绰成这样,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他们搬到东部的原因,我并不知道。他们总是不安定,先在法国待了一年,后来又东飘西走,然而所去的地方都有人打马球,而且大家都很有钱。“这次是定居了。”黛西在电话里说道。可是我并不相信,虽然我看不透黛西的心思,但我有一种预感,汤姆会这样一直飘荡下去,怅然若失地追忆昔日橄榄球赛场上的荡气回肠。
在一个暖风习习的夜晚,我开车到东卵去看望这两个我几乎一无所知的朋友。他们的房子面临海湾,是一座乔治王殖民时代式的大厦,红白二色,鲜明悦目,比我想象中还要奢华。葱翠的草坪从海滩一直延伸到大门,足足覆盖了四分之一英里的路面。房子正面还有一扇敞开的法式落地长窗,迎着午后的暖风,在夕阳的辉映中金光闪闪。
这幢豪华别墅的主人汤姆·布坎南身穿骑装,两腿叉开,正站在前门的阳台上。与大学时代相比,他的样子改变了不少。他现在已经三十多岁了,体格健壮,头发呈稻草色,嘴角略带狠相,眼神异常傲慢,给人一种盛气凌人的印象。他的双腿套在锃亮的皮靴里,鞋带绷得紧紧的。当他转动肩膀时,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大块肌肉在他那薄薄的上衣下面移动。这是一个强健有力的身躯—粗野霸道的身躯。他的嗓音又粗又大,这让他显得更加暴戾。他说话的时候经常带着一种教训人的口吻,即使对他喜欢的人也是如此,因此,在耶鲁的时候,不少人对他恨之入骨。
“我说,你别以为我的力气比你大,看起来更有男子汉气概,所以这些事情都是我说了算。”这是他惯有的口吻。我们两人属于同一个高年级学生联谊会,可是我们的关系并不密切,不过我总觉得他非常欣赏我,只是他用一种独特的蛮横和不屑的方式,来博得我的欣赏和喜欢。
在和煦的阳光下,我们愉快地聊了几分钟。“我这地方相当不错。”他说,双眼不停地飘来飘去。
他抓住我的一只胳臂,用力把我转过来,又伸出一只巨大的手掌,指点着前方的景色,就在他不经意的挥手之间,一座意大利式的凹形花园、半英亩浓郁的玫瑰花,还有一艘随着浪潮起伏的游艇掠过眼前。“这地方原本属于石油大王德梅因。”他又用力推我转回身来,客气地说,“我们到里面去吧。”我们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走进一间宽敞明亮的玫瑰色屋子,两头的落地长窗如两颗明亮的水晶镶嵌在这栋豪宅中。窗半开着,在外面嫩绿的草地的映衬下,显得晶莹夺目。
一阵轻风穿堂而过,洁白的窗帘飘向天花板上像婚礼蛋糕一样的装饰图案,然后又轻轻拂过绛色地毯,留下一阵阴影,仿佛风吹过海面。屋子里唯一静止的东西是一张笨重而庞大的长沙发椅,上面坐着两个年轻的女人,她们身穿白衣,衣裙随风飘荡,活像浮在地面上空的大气球。我站了好一会儿,倾听着窗帘刮动的嗖嗖声和墙上一幅挂像发出的嘎吱声。“砰”的一声,汤姆·布坎南关上了后面的落地窗,室内的余风这才渐渐平息下来,那两个年轻的女人慢慢地降落到地面。
我不认识两个女人之中比较年轻的那个。她一直平躺在长沙发的一头,身子一动不动,只有下巴稍微向上仰起,仿佛上面放着什么东西,生怕它掉下来似的。我以为她用眼角的余光看到了我,可是她一点儿表示也没有。我倒差一点儿就要张口向她道歉,我怕我进来的时候惊动了她。另外一位是黛西,她见我进来,身子微微向前倾,一脸真心诚意,然后她扑哧一笑,既滑稽又可爱。我便也跟着笑了,接着加快脚步走进客厅。
“天啊,我都快开心死了。”
她又笑了一次,好像说了一句十分俏皮的话,为此得意似的。然后她拉住我的手,仰起脸看着我,仿佛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其他人是她更乐意见到的了—那是她特有的一种表情。
她悄悄地对我说,那个一动不动的姑娘姓贝克。贝克小姐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露出似笑非笑、似说非说的表情,搞得我不知所措,她几乎看不出来地向我点了点头,接着又赶忙把头仰回去。
我回过头,我的表妹开始用她那低低的、令人激动不已的声音问我问题。这是一种让人不由自主侧耳倾听的声音,仿佛每句话都是由一串串抑扬顿挫的音符构成的绝唱。她的面庞忧郁而美丽,明眸皓齿,尤其动人的是她的声音,那是迷恋过她的男人都难以忘怀的:时而热情激昂,时而柔声细语—一声喃喃的“听着”暗示着接下来必然有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
我告诉她我到东部来的途中曾在芝加哥停留了一天,那里有好多朋友托我向她问好。
“他们全都想念我吗?”她欣喜若狂地高声问道。
“全城都充满了悲伤。所有的汽车都把左后轮漆上了黑漆当作花圈,城北湖边夜里的哀声不绝于耳。”
“这真是棒极了!汤姆,咱们回去吧,明天就走。”可随即她就转了话题,“你应当去看看宝宝。”
“我很想看看。”
“她现在已经睡着了。她三岁了,你还没见过她吧?”
“没。”
“去看看她吧。她是……”
汤姆·布坎南本来不安地在屋子里来回走动,此刻却忽然停了下来,把一只手搭在我肩上。
“最近在忙什么呢,尼克?”
“我现在在做证券生意。”
“哪家公司?”
我告诉了他公司的名称。
“我从来没听说过。”他断然说道。
这使我感到不开心。
“你会听到的,在东部待久了你自然就会知道。”
“放心吧,我肯定会在东部待下来的。”他先看看黛西,又看看我,仿佛在提防什么,“要是再搬到任何别的地方,那我就是一个天大的傻瓜。”
这时贝克小姐突然说了一句:“绝对如此!”我不由得吃了一惊:这是我进屋之后她说的第一句话。她打了个呵欠,随即迅速而灵巧地站了起来。
“我完全麻木了,”她抱怨道,“天啊,不知道我在那沙发上躺了多久了。”
“别看我,”黛西回嘴说,“我整个下午都在动员你去纽约。”
“不用了,谢谢,”贝克小姐拒绝了刚从厨房端来的鸡尾酒,“我在进行严格锻炼呢!”
男主人难以置信地瞪着她。
“是吗?”他一口把自己的酒喝了下去,“我真不懂你做得成什么事情。”
我看了看贝克小姐,不知她“做得成”的是什么事。不过我喜欢盯着她看。她的身材苗条,乳房小小的,像年轻的军校学员那样挺起胸膛,显得英俊挺拔。她用那双被光照得眯成一条缝的灰眼睛看着我,一张苍白、可爱、还略带不满的脸上流露出有礼貌的好奇心。我这才想起自己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她,或者是她的照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