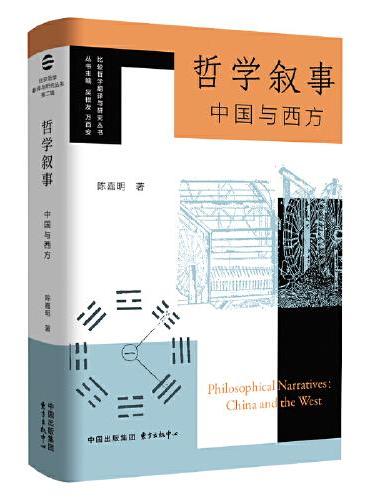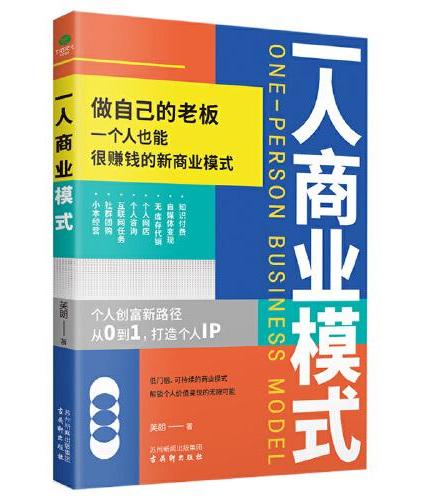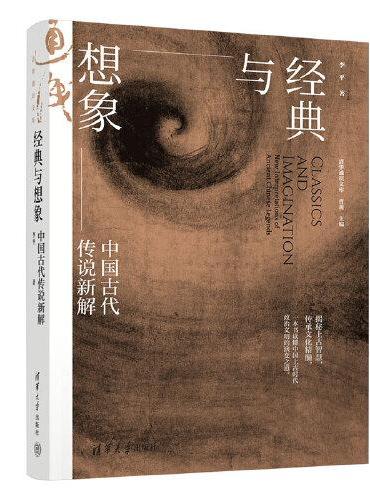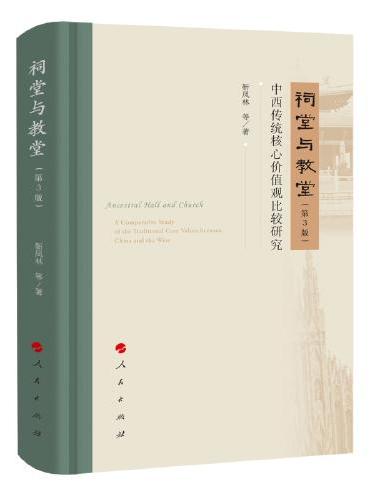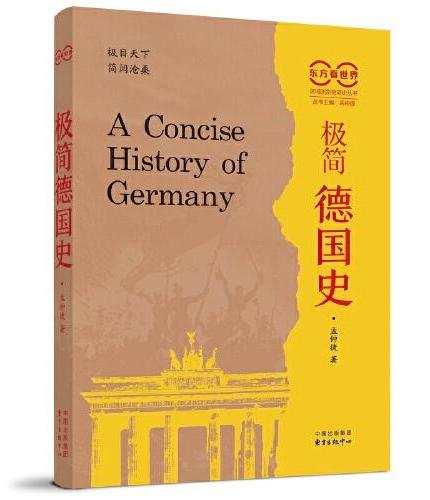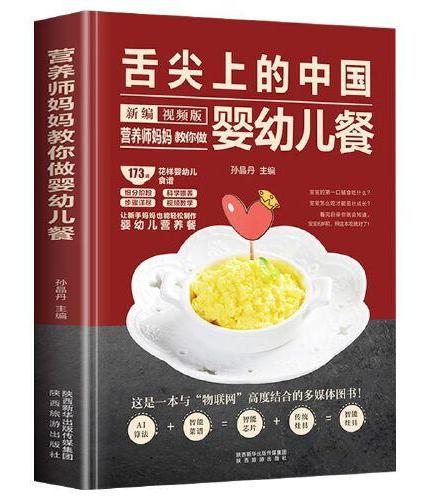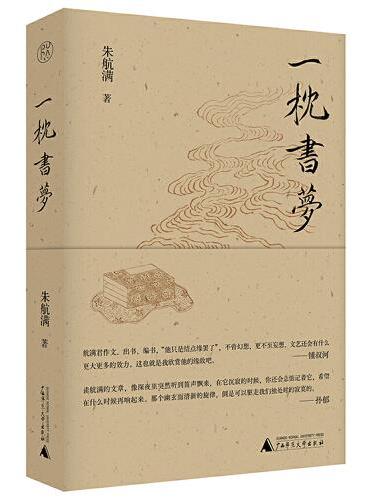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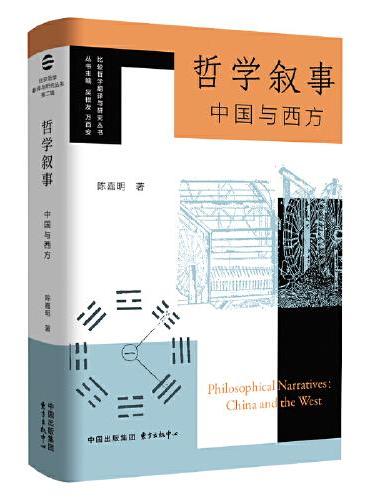
《
哲学叙事:中国与西方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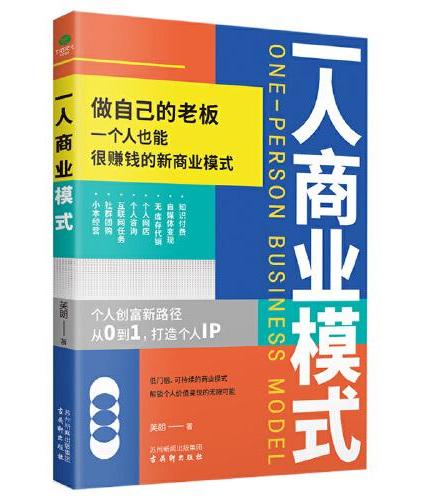
《
一人商业模式 创富新路径个人经济自由创业变现方法书
》
售價:HK$
5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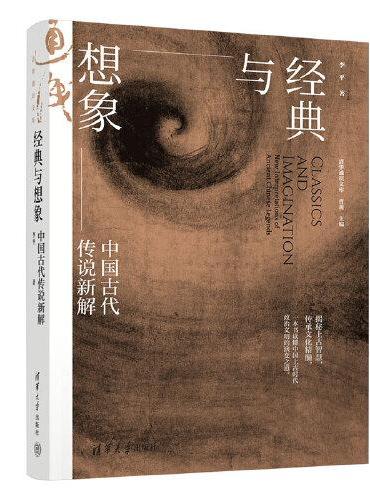
《
经典与想象:中国古代传说新解
》
售價:HK$
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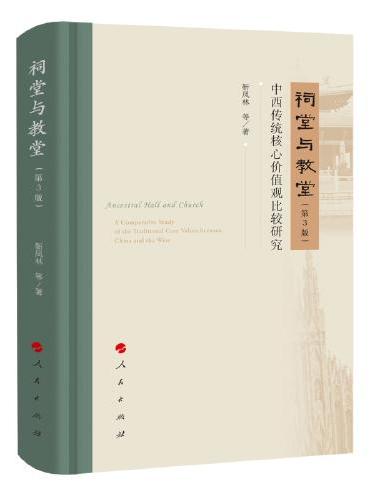
《
祠堂与教堂:中西传统核心价值观比较研究(第3版)
》
售價:HK$
11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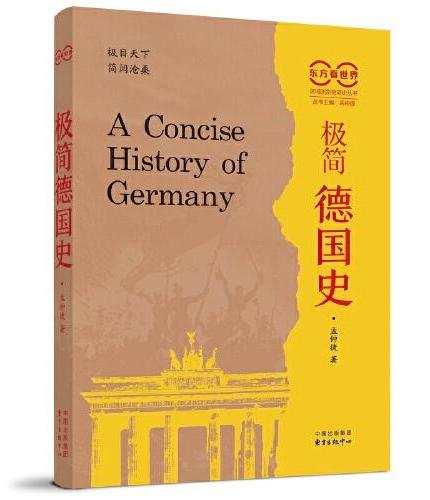
《
极简德国东方看世界·极简德国史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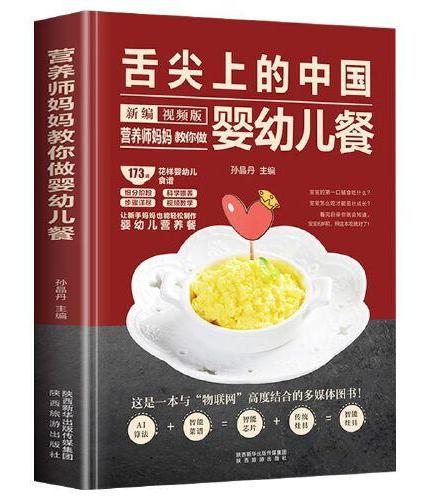
《
舌尖上的中国新编视频版营养师妈妈教你做婴幼儿餐
》
售價:HK$
63.8

《
Scratch创意编程进阶:多学科融合编程100例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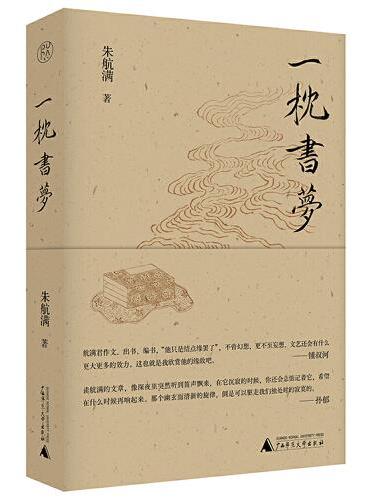
《
纯粹·一枕书梦
》
售價:HK$
79.2
|
| 編輯推薦: |
他,“现代主义文学之父”,“无家可归的异乡人”;犹太鬼才,情路坎坷;一生与两位女子订婚三次,都以解除婚约而告终;
她,记者、作家、译者,有夫之妇,卡夫卡深爱的女友,反法西斯斗士,二次大战中被捕,死于纳粹集中营。
*伟大的爱情书信,*热烈的灵魂绝唱;自我啃啮,自我平衡。
|
| 內容簡介: |
卡夫卡短暂的一生可谓情路坎坷,先后与两位女子订婚三次(其中与同一个人订婚两次),都以解除婚约而告终;同时,这位天赋异禀的作家又天生情种,在其创作高峰期先后与四位女子产生了爱情,密伦娜是其中形象最为鲜明,与作家最为志趣相投的一位,因而引发的情感波澜也最为热烈奔涌。二人相识于1919年,当时年届36岁的卡夫卡还寂寂无名,而密伦娜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位天才作家的惊世才华,主动提出将其作品由德文翻译成捷克文。卡夫卡几乎立刻就真挚而热烈地爱上了这位身处异地的有夫之妇,二人深陷情网,两地传书,往还不断。这段传奇的恋情在两人通信一年以后而告终,之后卡夫卡写下了不朽的名作《城堡》。
1939年春天,德国军队进驻布拉格不久,密伦娜将卡夫卡写给她的信托付给维利哈斯,随即被纳粹法西斯分子逮捕,投入集中营。而哈斯随后虽然经历了流亡,但把这批信件忠实地保存了下来。战后,哈斯接受卡夫卡终生挚友,同时也是其传记作者马克斯勃罗德委托,编辑出版了这本包含130余封信件的书信集,它们对后世了解作家卡夫卡的思想和创作历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参照。
|
| 關於作者: |
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奥地利德语小说家,犹太人。“现代主义文学之父”。生前比较寂寞,逝后才为世界所惊觉,从而赢得盛名。二十世纪各个写作流派纷纷追认其为先驱。
密伦娜·耶申斯卡(1896-1944),捷克记者、翻译家、作家,反法西斯斗士。卡夫卡深爱的女友。1939年遭德国纳粹囚禁于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并于1944年5月17日因一次被延误的肾脏手术而死于该地。
维利·哈斯,家住布拉格,与密伦娜及其捷克朋友圈交往多年,关系密切。
叶廷芳,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博导。1936年生于浙江省衢州市,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主要从事德语文学的研究,尤以卡夫卡、迪伦马特、布莱希特的研究见长。退休前历任文艺理论研究室副主任、中北欧文学研究室主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德语文学研究会会长(现名誉会长);先后获苏黎世大学“荣誉博士”、国际歌德学会“荣誉会员”;享国务院特殊津贴。著有《现代艺术的探险者》《卡夫卡及其他》等十余部;编著《论卡夫卡》《卡夫卡全集》等40余部以及译著《迪伦马特戏剧选》《卡夫卡文学书简》等数部。
黎奇,上世纪50年代中期出生于上海。70年代后期就读于复旦大学德语专业,后赴维也纳大学深造。毕业后先后在我国驻东、西德使馆工作多年,现在德国从事翻译和创作。
|
| 目錄:
|
译序写下的吻 叶廷芳
致密伦娜情书 卡夫卡
编后记 维利哈斯
原版后记 维利哈斯
附录一
密伦娜、施塔萨和波希米亚的生活
施塔萨弗莱施曼 文
黄曼龄 译
附录二
卡夫卡生平和作品中的爱情关系
叶廷芳 黎奇
|
| 內容試閱:
|
译 序
写下的吻
叶廷芳
不要以为,卡夫卡工作认真,在办公室的八小时“恪尽职守”;八小时以外又呕心沥血埋头写作,甚至不惜牺牲睡眠,于是大概就没有兴趣和精力贡献于情事了吧?非也!逻辑思维在这里不管用。不错,卡夫卡确实因紧张写作而导致咳血——当年的不治之症,以致英年早逝,且在短短的16年时间里(其中将近7年都是在病魔的折磨下度过的)留下342万字(汉语译文)的作品!尽管如此,他始终是个多情的种子!
年轻时他住在四层楼的家里,就常与楼下街对面的一个女子眉来眼去;1912年夏去德国旅游,很快和一家酒店的老板女儿打得火热;同年8月他经朋友马克斯勃罗德的介绍认识柏林姑娘菲利斯鲍威尔,并很快与之订婚。不久双方发生矛盾,女方托她的女友格蕾特布洛赫居中调解。第二年格蕾特产下一子,后来格蕾特坚称,此儿系卡夫卡所生(可惜此孩7岁即夭折了)!从认识菲利斯起的12年内,卡夫卡先后与4位女性产生了热烈的爱情,其中与两位(菲利斯鲍威尔和尤莉叶沃吕采克)订了三次婚,与一位(多拉狄曼特)同居半年多。唯一没有订婚也没有同居——至少没有正式同居——的是本书主人公密伦娜耶申斯卡。但唯独这位女性,卡夫卡倾注的情感最热烈,也最真挚。
就像俗话所说“英雄爱美人”那样,爱女人亦是作家的天性,这是公开的秘密。但这里我们感兴趣的倒不是卡夫卡多么爱女人,或他有多大的“艳福”,而是女人,或者说爱情在卡夫卡的创作中,乃至在推动卡夫卡登上现代文学创作顶峰的过程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君不见,卡夫卡的创作旺盛期是从1912年至1923年这12年,正是上述这四位女性一个一个接力赛似的陪伴着他,用他们的青春热情不断激荡着他的生命活力,频频刺激他的创作灵感。难怪不少研究者都提及:没有菲利斯就不一定会有《在流刑地》(一译《在流放地》)这一不朽杰作的问世;没有沃吕采克就不会有《致父亲》这一惊聋发聩的“醒世名言”的产生;尤其是,没有密伦娜则卡夫卡的最伟大代表作《城堡》就不会如此丰富和辉煌;没有多拉就没有卡夫卡告别人世时的幸福安魂曲。你看,她们不是贤内助,却胜似贤内助!
在与这四位女性的长期周旋中,就恋情的烈度而言,当首推密伦娜了!这是不难理解的:四人中若以年龄论,虽然密伦娜最大——25岁,但这对38岁的卡夫卡来说,算是相当年轻了!而密伦娜的优势,即文化水平和思想境界,则是其他几位无法比拟的:她当时是布拉格一家最大报纸的记者,且已是小有名气的作家。此外性格开朗、热情大方,且富有正义感和现代气息。不过这一切也许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在卡夫卡的重要性还没有得到普遍承认、正觉得知音难觅的时候,她就已经看到了卡夫卡作品的价值,主动写信向卡夫卡提出,要将他的德文小说《司炉》译成捷克文。这一信息马上将两位异性作家心灵中的“灵犀”点通了,在双方丰富的情感中埋下了爱的幼苗!这是1920年2月间的事。
从此,日益频繁的书信往来很快变成恋人之间的鸿雁传书,一位世纪性的世界顶级天才作家的情感库藏和智慧能量爆发出绚丽的焰火,它照耀着从捷克波希米亚至维也纳的道路,让这一对恋人实现第一次为期一周的相聚(6月29日-7月4日)。双方激越的情感经过拥抱和热吻获得开闸似的宣泄,但是否有床笫之欢,就不得而知了!因为这毕竟是在密伦娜家里,而密伦娜是有夫之妇啊。这就是为什么这趟充满诱惑的维也纳之旅,卡夫卡却显得那么犹犹豫豫,怀着那么多的“恐惧”。正像他在一封致密伦娜的信里所表达的:“写下的吻到达不了它们的目的地,而在中途即被幽灵们吸吮得一干二净。”原来这位在艺术观上如此现代的作家,伦理道德上却并未跟上。难怪他在一封信里甚至这样形容:见到她丈夫,自己就像一只耗子匆匆从堂前溜过去。这和当年歌德被他的红颜知己施泰因夫人邀入她的宫里居住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歌德的官位和声望比宫里的伯爵大人大得多呢!
不过,如果说维也纳之行留下什么遗憾,那么一个半月之后,即8月14-15日,两人在奥地利与捷克边境的小镇格蒙德的再聚当能得到弥补了,因为这是真正的私密式幽会。然而令人感到蹊跷的是:两人在这里只度过了一个夜晚!这一晚,依笔者之见,与其视之为两人爱情发展到顶点的里程碑,毋宁说是他们的良缘美梦走向坟墓的开始!不信你稍加细读就不难发现,卡夫卡情感的烈度自此开始降温了!四个月之后,即1921年1月,感情降到冰点,双方都宣布:从此不再写信和见面。两个敏感的灵魂经过长达一年、高潮半年的深度交融和波涌,终未能凝结成一个晶莹剔透的整体而重新散开、远去……
这一结局当然是读者所不愿看到的。卡夫卡给出的理由是:他发现密伦娜对其丈夫并没有恩断义绝。这似乎构不成理由:对于像密伦娜这样思想开放的现代女性,难道也要与其配偶达到仇人相见的地步才敢移情别恋?再说,爱情是最自私、最盲目的:它是不认理性的。在琢磨这个问题的时候,除了联系卡夫卡那特有的悖谬思维和行为方式,笔者也常常想到密伦娜的一位女友的女儿施塔萨弗莱施曼的一句话:“研究卡夫卡的权威们为什么不来读一读这封信呢?然而就在这封信中,密伦娜向他们解释了自己究竟为什么离开了卡夫卡。”所谓“这封信”指的是密伦娜致卡夫卡的挚友勃罗德的一封信,在那封信里,密伦娜向她所信赖的勃罗德说了心里话:“我怀着一种迫不及待的强烈愿望……即希望过一种有一个孩子的世俗生活。”这里道出了卡夫卡方面可能有的两个原因:一、卡夫卡不想要孩子;二、卡夫卡不能生孩子。后者是生理上的,也包括两种可能:他不能育子,或他存在性障碍。此外还有一种可能:卡夫卡对性行为的一种奇怪看法,即视之为“污秽不堪”,甚至咒之为“黑色魔法”。故在《城堡》中他让成排的妓女一个个走进“马厩”去过夜;在《乡村医生》中那位色迷迷走向医生侍女意欲调戏的马夫是从“猪圈”里出来的……以上诸种原因,很难断定是哪一种,但总的轮廓是清楚的:一个倾向理想,一个向往世俗。这既可通过卡夫卡有关言论加以佐证,也可通过密伦娜后来的行为来证实。卡夫卡在日记中不止一处有过自我争辩:他向往爱情、婚姻和一个有妻室的家庭,但这样却又会使自己陷入“小世界”,这岂不影响他的事业的完成!那么他的事业是什么呢——通过写作“把世界重新审察一遍”。
卡夫卡有一条箴言:人的内心中是不可能没有一颗坚不可摧的内核而生存的。“重新审查世界”可以说是他的“坚不可摧”的目标。所以在与密伦娜恋爱期间写的《城堡》第一稿的开头是这样写的:主人公“我”(不是K.)急急忙忙地恳求酒店侍女帮她的忙:他有一个十万火急的任务,一切无助于这一任务完成的事情她都要帮助他“加以无情的镇压!”显然,生儿育女是与他的这一使命相抵触的。密伦娜没过多久就与她的第一任丈夫离婚了,后来又嫁了两次,生育了孩子(参阅书后“附录一”)。
在这篇短序里用了这些篇幅来解释卡夫卡与密伦娜恋爱的结局,我想已经够了。其实我们更关注的当是他们恋爱的过程。人们常说:过程是最美丽的!确实,正是这一过程让我们看到了一位离我们不远的伟大作家那震撼人心的情感波涛,并为我们留下那大量的定格在纸上的焰火般的文字。它们不仅带给我们美好的文学欣赏价值和书信美学价值,而且让我们获得了重要的史料价值。就前者而言,它使我们惊异的是,一个先前已经先后与两位女子谈了多年恋爱、而且写了800多页情书的中年男子,在他接触第三位女子的时候,竟能掀起比以前更强烈、更壮观的感情风暴,写下更美丽、更动人的文字,而且是在病入膏肓的情况下,说明这位蕴有“坚不可摧的内核”的奇人——哦,一个犹太人的内在生命力多么强大!
许多读者阅读卡夫卡的作品时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觉:很难看出他的社会思想和政治倾向。但从他对密伦娜的爱可以使这个问题明朗起来。须知密伦娜不仅是个小有才华的青年记者和作家,而且是个思想激进的共产党人!她向往苏联,热情传播共产主义,虽然后来斯大林在1937年的大清洗使她感到失望,因而退了党(可以理解),但仍积极宣传激进思想,因而被法西斯政权投入监狱,并死于狱中。卡夫卡对这样一个“危险分子”爱得如此死去活来,没有一定的共同思想基础可能吗?难怪卡夫卡的一位共产党员朋友、诗人鲁道夫福克斯曾大声疾呼提醒大家:“可不要忘了:卡夫卡是有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的啊!”这一历史事实有助于我们理解: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什么共产主义思潮席卷了大半个知识界,而且包括了相当多的第一流精英人物如布莱希特、贝歇尔、阿拉贡、聂鲁达、马雅可夫斯基、毕加索、达利、鲁迅等等。现在有些人从当下的眼光出发,在评价这些人物时予以“扣分”,这就对历史不够尊重了。
阅读卡夫卡致密伦娜的这许多依然滚热的情书时,我们不由得对这些信件的接受者即密伦娜产生由衷的敬意:她在双方断绝来往以后,特别是在法西斯的追捕下,仍然想方设法保存着这些珍贵的资料,依然看重它们的无上价值。这是一位多么有见识、有良知、有风格的高尚女性!无独有偶,还有此前那位柏林姑娘菲利斯,她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见解虽然不如密伦娜,而且卡夫卡自己也承认:他伤害了她。但她亦看到了这位天才的价值而不顾个人恩怨,妥善地、完整地保存了卡夫卡五年内写给她的全部517封信件!
仅从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卡夫卡爱这两个人爱对了!她们的崇高风范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遗产。我们尊敬卡夫卡,也同样尊敬这两位欧洲女性,她们将与卡夫卡一样不朽!
本书的历史
我的这本回忆录初版于l 9 5 1年我原取名为《卡夫卡 我说》,出版社负责人改为《卡夫卡谈话录》。读者、报纸与广播电台的书评家以及职业文学批评家立即对我的文字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种兴趣在此后的岁月中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浓厚了。我的这本平淡无奇的书变成了被严肃评价的文学性研究资料。因此,在《卡夫卡谈话录》德文本出版后不久,很快就出了法文、意大利文、瑞典文、英文、南斯拉夫文、西班牙文译本,甚至出了日文译本。
于是我收到从世界各个角落寄来的大量书信,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始终一一作答。这样做并不困难,因为对那些难以回答的问题,我可以避而不答,但是,在与从世界各国到布拉格的卡夫卡崇拜者的越来越多的谈话中,这就不那么简单了。我常常只好保持缄默,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比我更熟悉卡夫卡的作品,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对他们来说,《诉讼》、《美国》和《城堡》不像对我那样只是书名;他们大多对这些书进行过真正的研究。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然而,对这些来自法国、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瑞典、意大利、日本和奥地利的来访者,我不能这样说。即使说了,他们也肯定不会正确地理解我。这一点在一位年轻的、富有才气的布拉格文学研究者克维塔·希尔斯洛娃博士身上得到了证实:我试着向她讲真话时,她脸上显出诧异的神情。克维塔·希尔斯洛娃博士就弗兰茨·卡夫卡这一文学现象写过一篇内容广泛的博士论文。她那撮圆的嘴巴和瞪得滚圆的黑眼睛无言地、然而却十分清楚地告诉我:“这可太荒唐了。"但对我来说,我对卡夫卡过世后出版的遗作其实只是通过道听途说而略知一二这一事实是完全自然的事,在我看来,这是任何人都非常容易理解的事。
我不能阅读弗兰茨·卡夫卡这位作家的长篇小说和日记。这并非因为他对我很生疏,而是因为他离我太近。青年时的困惑迷惘,随后几年的内外交困的处境,对幸福的种种设想的破灭,一切权利的突然被剥夺和由此而引起的日益加剧的内心的孤独和与外界的隔绝,充满忧伤、提心吊胆的忧郁日子,所有这些经历都使我紧紧地胶着在耐心地忍受命运的弗兰茨·卡夫卡博士身上。对我来说,他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文学现象。他对我来说意味着更多的东西。弗兰茨·卡夫卡博士至今还像多年以前一样,一直是我整个人的保护外壳。他是以他的善良、宽容、坦诚促进和保护我的自身在冷风凄雨中发展的人。他是认识和感情的基础,今天,在这个时代的阴森可怕的洪流中,我仍站在这坚实的基础上。
除了自己青年时代不可磨灭的经历的力量以外,对他的书籍进行解释的各种尝试能给我什么呢?只能是密封的感情与思想罐头。我所认识的活生生的弗兰茨·卡夫卡博士比他的书、比那些被他的朋友马克斯·勃罗德拯救出来免于毁灭的书伟大得多。我曾经拜访过、在布拉格陪伴他散步的弗兰茨·卡夫卡博士是如此伟大,如此坚固,致使我今天在人生道路上遇到任何坎坷挫折时,都能像抓住坚固的铁栏杆那样抓住他的影子。弗兰茨·卡夫卡的书对我意味着什么呢?
我住在布拉格民族街。我的小房间的笨重难看的暖气上放着橄榄绿手风琴,上面有一个石棉衬底的木制书架,卡夫卡的书就放在这个书架上。我有时取下这本书,有时取下那本书,读那么几句或者几页,但每次我的眼睛很快就感到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压力,血液在颈动脉里有力地跳动,我不得不把刚拿下的书迅速放回到书架上。读他的书是与往日留下的、珍藏在我心里的、依然非常清晰的印象和回忆相违背的,当时,我的心完全被弗兰茨.卡夫卡博士以及他对我说的话所占据、所迷醉,他的话给了我力量和勇气,使我敢于在批判性地评价和把握世界并进而评价和把握自我方面有意识地迈出突破性的第一步。
我不能阅读弗兰茨·卡夫卡的书,因为我担心,我阅读研究他去世后出版的文章,会减弱、淡化,甚至也许会完全消除他的人格留在我心中的魅力。我害怕失去继续活在我心中的“我的”卡夫卡博士的形象,直到现在,每当我感到在害怕与绝望的漩涡里快要沉没时,他的形象作为不可动摇的思想典范和生活榜样就给我新的力量,使我镇静。
我担心,阅读他的遗作会使我不祥地疏远我的卡夫卡博士,从而失去我青年时代令我十分陶醉的经历所具有的经常催人振奋的推动力。因为正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卡夫卡对我并不是抽象的、超人的文学现象。我的卡夫卡博士对我是一种深刻体验的,因而又完全是现实的私人宗教的偶像,这种私人宗教的影响却超出了纯粹个人的事务,它的精神使我得以对付某些荒唐的、笼罩着毁灭阴影的局面。
我所熟悉的《变形记》、《判决》、《乡村医生》、《在流放地》和《致.米伦娜》的作者对我来说是一位对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的坚定的伦理责任感的宣告者。他是布拉格工伤事故保险公司忙于公务的职员,但是,在他那看似平凡的公务生涯中,却闪耀着最伟大的犹太先知们对神和真理的包容大地的渴念的无望余火。
卡夫卡谈话录
1920年3月底的一天,我父亲在吃晚饭时要我第二天上午到他办公室去看他一次。
“我知道,你常常逃学,到市立图书馆去,”他说,“明天到我这儿来一趟。穿整齐像样点。我们去看个人。”
我问,我们一起到什么地方去。我觉得,我的好奇让他高兴,但他没有说到哪里去。“别问,”他说,“别好奇,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第二天快中午时,我来到劳工工伤保险公司四层楼我父亲的办公室。他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了我一番,打开写字台中间那个抽屉,拿出一个上面写着古斯塔夫几个美术字的绿色公文包,把它放在自己面前,然后又打量了我好一会儿。
“你干吗站着?”他停了一会儿说,“坐下。”我脸上紧张的神情使他狡黠地微微皱了皱眉头。“别害怕,我不会责骂你的,”他和蔼地说,“我要像朋友对朋友那样和你说话。你要忘记我是你的父亲,好好听我讲。你在写诗,对吧?”他看着我,好像要给我一张账单似的。
“你怎么知道的?”我结结巴巴地说,“你从哪儿听说的?”
“这很简单,”父亲说,“我们每月付一大笔电费。我研究了耗电量为何这么大的原因,于是发现你房间里的灯深夜还亮着。我想知道你都在干什么,就注意观察你。我发现你老是写呀画的,写了又撕,或者把它塞到钢琴下面。有一天你去上学时,我看了你的东西。”
“你发现什么了?”我咽下一口口水。
“没有什么,”父亲说,“我发现了一个黑皮笔记本,上面写着《经验集》。这个名字引起了我的兴趣。但当我发现这是你的日记时,我就把它放到了一边。我不想窥探你的灵魂。”
“可是你读了诗了。”
“是的,诗我读了。那些诗放在一个黑色公文包里,取名为《美好集》。好多地方我不懂。有些东西,我要称之为愚蠢。”
“你为什么读我的诗?”我已经十七岁,碰我的东西就是对我的大不敬。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