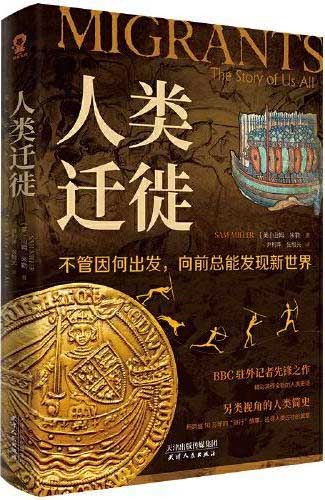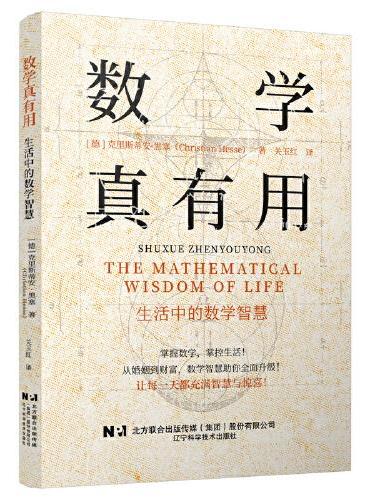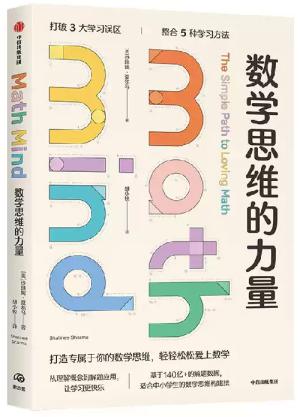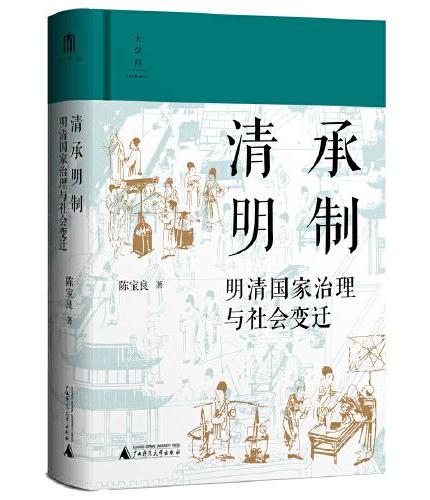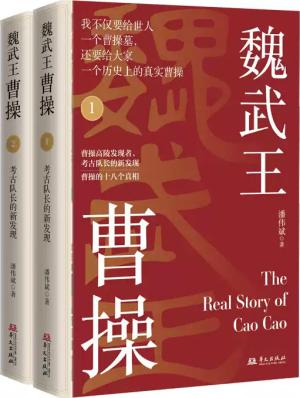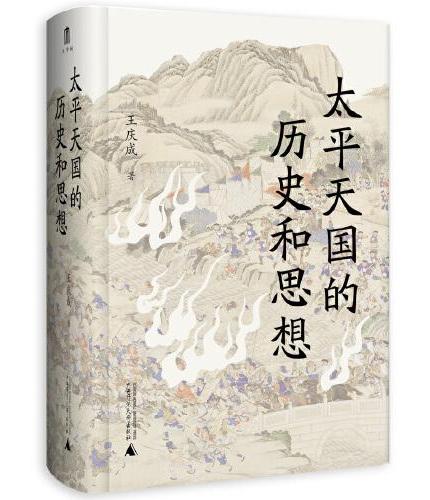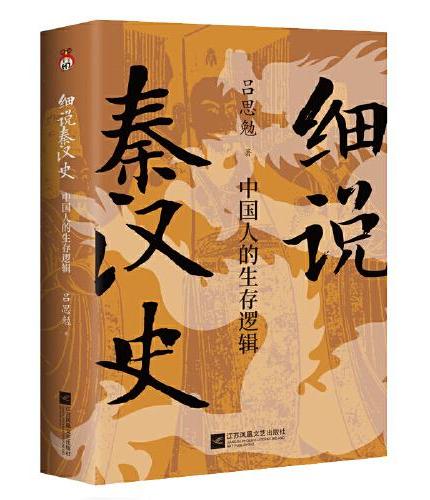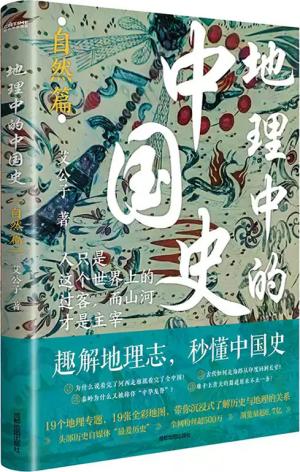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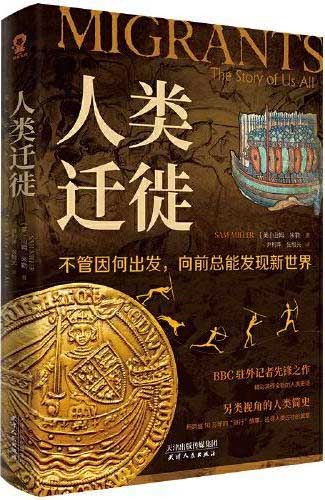
《
人类迁徙(BBC驻外记者先锋之作,另类视角的人类简史)
》
售價:HK$
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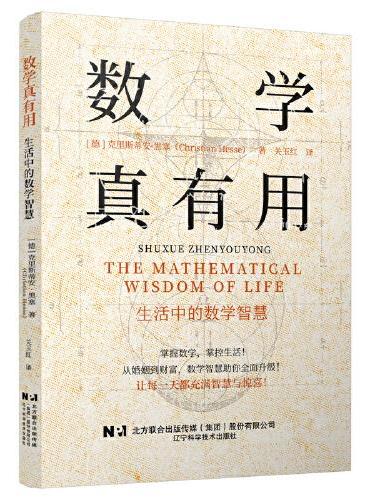
《
数学真有用:生活中的数学智慧
》
售價:HK$
5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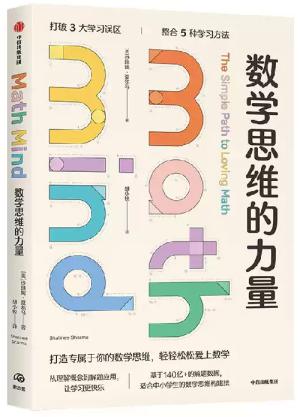
《
数学思维的力量
》
售價:HK$
7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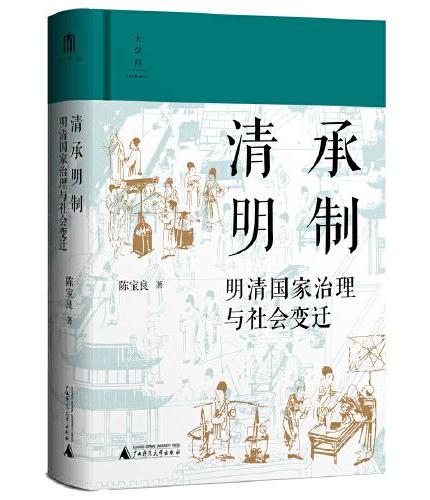
《
大学问·清承明制:明清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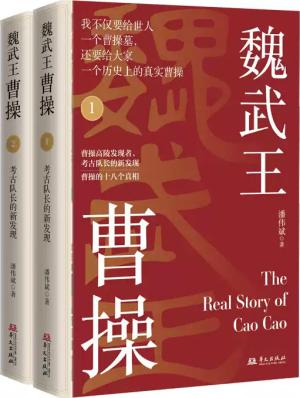
《
魏武王曹操(共两册)
》
售價:HK$
17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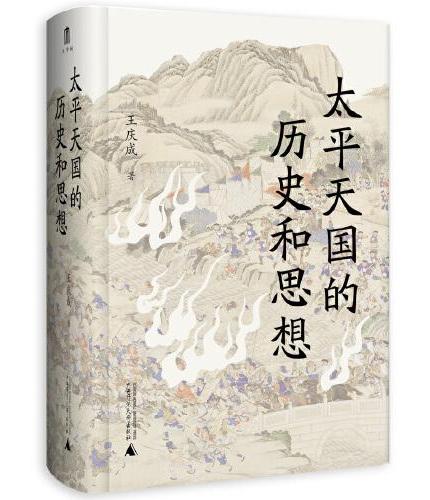
《
大学问·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一部研究太平天国的经典著作)
》
售價:HK$
14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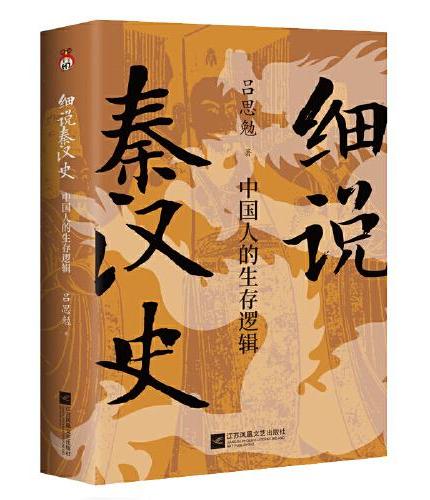
《
细说秦汉史:中国人的生存逻辑
》
售價:HK$
15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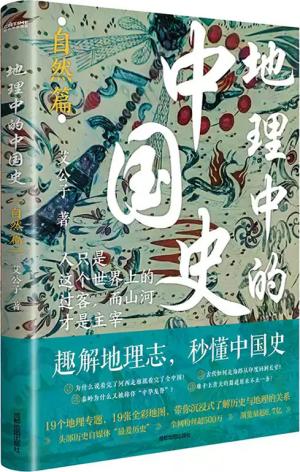
《
地理中的中国史(自然篇)
》
售價:HK$
64.9
|
| 編輯推薦: |
别和她说话,原名“暗示”
● 超现象级悬疑小说《别和她说话》(原名:《暗示》)*终话。史无前例“破胆+烧脑+虐心”式结局大揭秘!
● 这不是普通的杀人案件,并且超过一切侦探推理,它颠覆了你对犯罪和心理的概念:犯罪,可以不必亲自动手;真正的心理高手,几句话,几个动作,便能杀人于无形之间。这种神乎其技的超凡本领,远比变态连环杀手和高智商犯罪更让人恐惧,因为真正杀死你的,不是别人,正是你自己。意识一旦被操控,上帝也无法拯救。
● 超现象级悬疑惊悚小说 多家影视、图书公司争抢本书版权。
● 被网友誉为***烧脑本土悬疑小说,结局会因读者智商不同而完全改变。
● 紫金陈、周浩辉、蜘蛛、莲蓬 激赏推荐。
● 本书涉及:罪案学、心理学、伦理学、法学、医学、社会学、化学等二十余门专业。
|
| 內容簡介: |
超现象级悬疑小说《别和她说话》最终话
史无前例“破胆+烧脑+虐心”式结局大揭秘!
三十多年前的一桩惨案,让人亲眼目睹人性最极端的丑恶,几个当事人陷入绝望而崩溃,第一批X由此诞生。
几年前,一名年轻女孩被几个暴徒折磨致死,幸存者发生心理骤变,成长为新一代X。
A集团操控着X,杀人无数,罪恶滔天,却屹立不倒。神秘组织不畏艰险,前赴后继,与之对抗,却屡战屡败。
为了彻底打倒邪恶势力,她牺牲自己,终于创造出了最终极、最顶尖的心理高手。
就是我……
|
| 關於作者: |
遇瑾,原名张鑫,85后,年纪不大,却有着一段极富传奇色彩的经历(他在本书自序中对此有所提及,详见自序)。知识兴趣广泛,对物化、医学、心理学等领域均有涉猎,尤其是心理学,其专业程度令人赞叹。自幼热爱写作,十数年来笔耕不辍。其文笔精炼,叙事紧凑明快,逻辑极为严密。
本书原名《暗示》,在“天涯社区”等网站连载后,立即收获网友超人气盛赞,被誉为“史上最烧脑本土悬疑小说”,更是引发百余家影视公司争抢本书影视版权。
|
| 目錄:
|
第一章 无比诡异的梦境
我回想起前一晚似真似幻的梦境,记得很清楚:一个男人站在卫生间门口,先说自己是徐毅江,又说自己是马三军,而后说自己是陈玉龙,最后说自己就是——X。
第二章 变态的恋母情结
刘智普经常换女朋友,一个月内换了三次。院里最少有十几个女老师跟他有过交往经历,据说,其中有五个都怀过他的孩子,但他似乎从未想过结婚。
第三章 渴求无私的爱恋
他的目光中充满了对我的爱恋、依恋,还有种深深的怀念。他突然拉住我的手,颤抖着说了一句:叶老师,我不想离开你。当晚,我带他去了家里。
第四章 研究报告的秘密
我原本只是想让刘智普帮我寻找与M研究有关的线索,意外的是,他居然给我带了一份完整的《M成瘾性的实验研究报告》。那份神秘的研究报告,就这么浮出了水面。
第五章 记忆深处的错乱
我的两段记忆相互矛盾而又共存,其中一种显然是无意识对意识的欺骗。无意识过于活跃,这已经属于妄想的范畴了,很可能是精神分裂的前兆。
第六章 神秘人X的现身
他们把女生拽到楼下,一路拖到教室后面的荒土地里。他们扒光了她的衣服,老师过去拼命阻止。但我们都太文弱了,那女生最终还是遭到轮奸。
第七章 心理高手的交锋
两人合力把门踹开,被书房里的景象吓了一跳:刘向东双手支撑,跪卧在地上,血不停地从嘴角涌出,沾满了面部、衣物以及周围的地面。
第八章 内心深处的较量
哀号是如此真实,仿佛一个年轻女孩正坐在我右前方,遭受难忍的痛苦折磨。恍惚间,我看见右前方的沙发上躺着一个衣衫凌乱的女孩,她两臂满是横竖交错的割伤。
第九章 艰难的刺杀任务
据可靠消息说,纪委会在中旬有所行动,一旦行动开始,局面就没办法控制了。这次的任务,就是在月底前除掉他。还有,为了减少将来的麻烦,他的死必须是自杀。
第十章 完整的死亡名单
他们在拘禁过程中对我进行了各种虐待:辱骂殴打、断水断食、灌尿……但我总觉得这些并非全部——他们当时还做过什么更恶心狠毒的事,但我一时想不起来。
第十一章 叶秋薇的致命弱点
叶秋薇缓缓解开扣子,褪下衣裙,露出白皙的身体,静立在我眼前。我焦躁地咽了咽口水,用力敲击玻璃墙,不顾一切地想冲进墙内。
第十二章 深入骨髓的爱恋
他继续撕扯明溪的衣服,几秒就完全剥掉了明溪的上服。几个男人的哄笑声中,明溪发出沙哑而凄厉的哀号,如同尖锐的鸟鸣,在我耳中逐渐化作一种诡异的嘶鸣。
第十三章 没有胜者的角力
吴国鹏发现那些人的死亡方式只有两种,要么死于意外事故,要么就是自杀。同一起强奸案的十几名施暴者以类似的方式接连死去,而且死亡时间有序地从年初排到年末,世上绝不可能有如此的巧合。
第十四章 最后一次见面
她嘴角微扬,目光中却再次溢出哀伤,只是,我仍然没能意识到这种哀伤的来源。我走到门口,又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我惊喜地发现,她也在忍不住回头看我。我永远忘不了她那谜一样的双眼。
|
| 內容試閱:
|
一章 无比诡异的梦境
我回想起前一晚似真似幻的梦境,记得很清楚:一个男人站在卫生间门口,先说自己是徐毅江,又说自己是马三军,而后说自己是陈玉龙,最后说自己就是——X。
时间是2012年6月21号上午十点,与叶秋薇的第七次会面刚刚结束。我坐在车里,手捧死亡资料,依旧沉浸在叶秋薇那令人着迷又令人不寒而栗的精神世界里。
我突然产生了一种直觉,觉得从第一次会面开始,叶秋薇就在对我进行某种心理干预。那直觉强烈而真实,令我无法不信服。我屏住呼吸,开始下意识地回想与叶秋薇前六次会面过程中的种种细节。就在回忆与思索即将有所进展之时,那如海啸般席卷脑海的直觉却突然消退,瞬间无影无踪,只留下越发茫然的我。
我松了口气,看着车窗上斑驳的阳光,如梦初醒。
稍后,我定了定神,将死亡资料翻到第七页。第七个死者,就是叶秋薇提到的那个刘向东。关于他,资料里只有几句简短的描述:
刘向东,男,出生于1958年4月,生前为E制药公司科研中心主任,2009年11月6号,于家中自杀身亡。
我不禁皱了皱眉:为什么资料里没说他是如何自杀的呢?
人的心理变化微妙而迅速。我放下死亡资料,本想回去找老吴问问刘向东自杀的详情,刚打开车门,又突然下意识地收回了双脚,脑海中飞过这么一个念头:
老吴也未必知道,还是等到明天问叶秋薇吧。
刚离开精神病院,老婆就给我打来电话。
“一新,酒醒了没?什么时候回来?你要是不舒服,就休息到中午再上路,别让我操心。”
“哦。”我回忆了一下前一晚的事,大脑一片模糊,“我昨天晚上给你打电话了?”
“装,接着装。”老婆嗔怒道,“你昨天晚上拿着电话跟我说了一个多小时,我都快被你烦死了。我跟你说啊,就算这样,也不能证明你昨天晚上没有找小姐。”
我一边努力回想,一边随口问道:“那怎么证明啊?”
“今天晚上试试就知道了。”老婆笑道,“说真的,你要是不舒服就先别回来,中午退了房再走。还有啊,你抽空给付科长打个电话,人家昨天晚上好不容易才把你安顿好,你知不知道自己吐了人家一身?”
印象里,好像是我找代驾把付有光送回家的吧,怎么成了他安顿我了?我从前一晚的酒桌上开始回忆:我让付有光帮忙调查1727的登记信息,我趁他酒醉打听徐毅江的背景,最后我们称兄道弟,一起骂娘。他喝得烂醉,我打电话找代驾把他送回家——
想到这里,头部一阵刺痛,我忍不住叫出声来。
老婆吓了一跳:“一新?”
“没事儿。”我揉着脑袋说,“头有点疼。对了,我昨天晚上都跟你说什么了?”
“你真没事儿吧?”老婆关切地问了一句,随后笑了几声,说,“你每次醉了都这样,东拉西扯,胡说八道,说你多爱我,非我不娶什么的。我都快瞌睡死了,你就是不让挂电话。最后你来了一句,今天的太阳真毒啊,就再也没声了。”
今天的太阳真毒?我无奈地摇摇头,看来自己昨晚真是醉得不轻。
挂了电话,我赶紧翻了翻通话记录。前一晚十点,老婆给我打了一通五分钟的电话——这个电话我已经没有印象。十点十分,我拨出过一个陌生的固定电话,B市的区号。十点五十三分,我给老婆打了一通长达一小时的电话。十二点左右,付有光给我打过两次电话,但我没有接——我当时应该睡过去了。再往后,就是一点半左右,我给酒店登记信息倒卖者打的电话了。
我拨出那个B市区号的固定电话,对方是一家代驾服务公司。看来我的记忆没错,昨晚十点,确实是我找代驾送了付有光。这老小子,居然对我老婆说是他送的我——
等等,他为什么会跟我老婆通话呢?
我打电话给付有光,他接了电话:“醒了兄弟?昨天晚上的地方还可以吧?”
“啊?”我一愣,“昨晚是你给我找的地方?”
“不是我还是鬼啊?”他哈哈大笑,“兄弟啊,不能喝你就早说,下次咱就不喝了。你昨天晚上吐了我一身,还吐了人家代驾兄弟一身,要不是我多给了五十块钱,人家都不愿意干了。”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对不住啊哥,当时怎么回事,我全都不记得了。”
“我知道,你也不用在意。”他用力咳嗽了一声,说,“我比你好不到哪儿啊,快到家门口了遇上查酒驾,×他奶奶,局子肯定是不用进,就是罚了我五百块钱。”
我赶紧说:“就当是破财消灾吧,十月的人物你肯定能上。”
他哈哈大笑:“那还得靠老弟你了。对了,昨天晚上弟妹给你打了电话,你当时话也说不清,我就替你接了。说实话,我虽然没有亲眼见过弟妹,但光听说话,就觉得她不像会出轨的人。过日子还是多点信任吧,谁还没个歪心思?你昨天晚上还吵着叫我给你找姑娘呢。”
“嗨。”我尴尬地说,“我喝醉了就这熊样,可千万不敢跟你弟妹说。”
“哎,不说了。”付有光的语气平静下来,“你还是赶紧给弟妹打个电话吧,别让她操心了。”
我一边应着,一边继续回忆前一晚的事,突然想起了那个似真似幻的梦。
“哥。”我认真问道,“昨天晚上是你把我送到房间里的?”
“嗯。”付有光说,“你人生地不熟的,其他人送我也不放心。代驾把车开到酒店停车场就走了,我用自己的身份证给你开的房,又给你弄到房间里的。你一进屋又开始吐,还说冷,非得打开浴霸。我怕出啥事,一直到了快十一点,你说要给弟妹打个电话,电话接通了我才走。”
我问:“不会有其他人进我房间里吧?”
付有光一愣,随即说道:“不会吧,咋了老弟?你丢东西了?”
“啊。”我编了个理由,“丢了个工作本,也不是啥贵重东西。”
“要真有需要,我可以找人看看监控。”
我赶紧说:“那就麻烦哥哥了,那本笔记对我还挺重要的。”接着,我问了最后一个问题:“哥,昨天晚上你叫代驾是用我手机打的电话?”
“是。”付有光说,“我的手机当时没电了。”
我长舒了一口气。从付有光的语气、语速和逻辑性来看,他应该不是在骗我。那么,为什么他讲述的经过,和我记忆中的不一致呢?是我醉酒导致记忆混乱?还是有着某种更复杂的原因?又或者,我对于酒后的记忆,本来就是梦境的一部分?
脑袋又是一阵剧烈的刺痛。我眯着眼,捂住头,把车停在路边。当时是上午九点四十,阳光已经很亮。光线透过车窗斜射进来,我睁开眼,感觉一阵恍惚,再闭上眼,脑海中突然闪过几个真假难辨的记忆片段。
我想了起来:昨晚离开饭店时,我觉得头重脚轻,是付有光扶着我。我的手机响起,付有光接了电话,说,弟妹啊,我现在就把一新安顿好,你放心吧。
下一个片段:我看见一个精瘦的中年男人,他帮付有光把我扶到车的后座上。上车前,我大口地吐了起来,中年男人和付有光都是一阵叫唤。
第三个片段:我坐在马桶盖上,靠着水箱,仰起脖子,嘴里嚷嚷着,哥,你一定得给兄弟找个妞。付有光看着我,脸上带着复杂的笑容。
最后一个片段:我趴在洗漱台上疯狂呕吐,老婆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吐完之后,我打开所有浴霸,照了照镜子,抬头看了看天花板,被浴霸刺得睁不开眼,迷迷糊糊地来了一句,今天的太阳真毒啊。紧接着,我踉跄着走出卫生间,把手机扔到床上,自己也向床上倒去。倒下的一瞬间,我突然听见有人在身后跟我说话——
屋里当时确实有其他人!
想到这里,我不禁打了个寒战,头也再次刺痛起来。紧接着,我闻到一股隐约的腥味。我下了车,打开右后方的车门,在脚垫上看见一滩明显的呕吐物,坐垫上也沾了一些。如此说来,我前一晚确实是被代驾送到酒店的,为什么我之前一直认为是自己开车过去的呢?我前一晚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偷偷去了我的房间?
我给付有光发了一条短信:哥,请尽快帮我查一下酒店昨晚的监控。
几分钟后,我总算恢复了些许精神。按照叶秋薇提供的地址,我很快就找到一家名为“雨燕芳草屋”的店面。一进门,一个三十左右的女人就迎上来,热情地跟我问好,随后问我需要什么样的花草。
“玫瑰。”我不太确定地问,“女人都喜欢玫瑰吧?”
她用开玩笑的语气问:“送老婆还是送情人呀?”
我笑笑说,“老婆。”
“看年龄,你们结婚得有十年了吧?”她笑道,“我瞎猜的。”
“差不多十年了。”我环顾四周,“这么大一个店,你自己忙得过来么?”
“十年啊,那就不需要太热烈了。”她思量片刻,“十朵香槟玫瑰吧,配上相思梅,保证她喜欢,不过可不便宜。”
“二十朵吧。”我说,“我认识她已经有二十年了。”
“当然。”她笑笑,对着店铺深处喊了一句,“小刚,上楼取二十朵香槟,好好挑一挑。”
花草深处传出一声应和,五分钟后,一个体态略显臃肿的年轻男人举着花走来,胳膊上有几道明显的伤疤。两人熟练地包装花束。包装过程中,男人不时地瞥我一眼,神色有些异样。包好后,女人给我找了钱,男人把花递到我手上,犹豫片刻,问道:“你是不是——”
我好奇地看着他:“咱们认识?”
“哦——”他挠挠头,胳膊上的疤痕如蛇形蜿蜒,“没有没有,认错人了,你很像我以前的一个熟人。”
我闻着花笑笑:“我是大众脸,不奇怪。”
我捧着花往外走时,一个女孩推门而入,说道:“小燕姐,一朵康乃馨。”
我长舒了一口气。
半小时后,我带着花回到家里,老婆抱着我哭了很久,说我已经好几年没给她买过花了。我们二十年前相识,相恋也十年有余,期间一同体味过甜蜜,也承受过太多苦难,感情不可谓不深。然而,一旦生活开始顺风顺水,激情和誓言也就难免归于平淡。前些年,我一直渴望在其他女人身上重获激情,但最终没有付诸实践。我很庆幸自己的坚持,因为我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激情如同干柴烈火,欢快而短暂,亲情则是阳光,我们无法热烈地拥抱太阳,但可以享受永恒的温暖。
我原本打算去一趟S市,但回家不久,宿醉的疲倦就迅速袭来。我一直睡到傍晚,五点半的时候,老婆把我轻轻摇醒,说是付有光打来了电话。
我接了电话:“喂,哥。”
“兄弟。”付有光显得很轻松,“监控我都查过了,你放心吧,从昨天中午十二点到今天早上九点,你那房间除了咱俩,再没进过第三个人。”
我先是松了口气,随即产生了更大的疑惑:既然没有其他人进过房间,我倒到床上之前听到的说话声,又是怎么回事呢?
片刻后,我深吸了一口气:“哦,真是麻烦你了。”
“看你说的。”付有光嘿嘿一笑,“不过我问清洁工了,她说打扫的时候并没有看见你的工作本,我刚才帮着找了找也没有发现。”
“啊——”我赶紧说道,“那就别麻烦了,我凭着记忆再写一遍吧,你就别再为这事操心了。”
“毕竟是你在B市丢了东西,我这个做主人的不能没一点责任啊。”付有光不好意思地说,“我会让酒店的人多留意的,你那个本具体啥样?”
“哦,黑胶皮,挺破的,每一页都写满了字。”我随口编了几句,“真不用麻烦了。”
“嗯,嗯。”付有光说,“你不用操心了,听你声音还在睡吧,我就不打扰了,那个事还得你多费心啊。”
挂了电话,我揉揉脸,再度回想起前一晚似真似幻的梦境。我记得很清楚:一个男人站在卫生间门口,先说自己是徐毅江,又说自己是马三军,而后说自己是陈玉龙,最后说自己就是X。紧接着,我就回到了叶秋薇的病房,她诡异地笑着说:张老师,你跟我越来越像了。
这个梦究竟代表了什么呢?
晚饭过后,我打开录音笔,把第七次会面的谈话内容做了书面记录。我反复研读了叶秋薇三次释梦的过程,又从书柜底部翻出《梦的解析》,试图用精神分析的方式解读自己的梦境。
这个梦仓促而离奇。叶秋薇说过,越是奇怪的梦,说明潜意识的伪装越深。那么首先,一个男人站在卫生间门口,于我而言究竟有着什么象征意义呢?
第一个意象,就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暂且跳过这个意象。男人先后说自己是徐毅江、马三军、陈玉龙和X,又象征了什么呢?难道四个人是同一个人——这怎么可能?又或者,其中两个人是同一个人——我眉头一皱:X,会不会就是徐、马、陈其中一人呢?
我决定把自己的猜测记录下来,写到一半又停了笔,叹了口气:虽然这种猜测挺像回事,可说到底还是猜测罢了,不仅无凭无据,连个释梦的过程都没有。
我又想起最后一个意象:为什么在梦里,叶秋薇会说我跟她越来越像了呢?
这个倒是不难理解:我和叶秋薇虽然只认识了不到一周,但她的精神力量已经深刻地影响了我。我不仅提升了洞察力和分析能力,还不知不觉地开始学习和模仿她的思维方式。潜意识里,我早就知道自己跟她越来越像了吧。
抛开三个具体意象,梦中最奇怪的细节,就是陈玉龙这个名字的出现。我和他八年未见,别说联系了,连他的名字都很少想起。可以说,八年来,他的名字一直存在于我的潜意识深处。叶秋薇说“梦没有偶然”,那么,究竟是什么现实因素,导致他的名字“必然”地出现在了我的梦里呢?
我回想了一下前一天的经历:上午八点半到十点,我一直待在精神病院里,听叶秋薇讲述王伟的事,之后接受了心理评估。十点半到十二点,我在社里处理工作,还跟领导进行了一次不太愉快的谈话。下午两点,我去了一趟Z大,跟几名保安说过几句话。四点抵达省一监,见了付有光和陈富立。之后去立张村见了张瑞林和他的妻子云灿霞,晚上又回到B市跟付有光喝了酒。
如果梦真的不存在偶然,那么可以肯定:我前一天白天接触过的某个人,在我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对我进行了暗示,激活了我潜意识中关于陈玉龙的记忆。
这个人到底是谁?
我仰起身子,靠在椅背上,深吸了一口气,一种强烈的宿命感袭来:我突然觉得,自己和叶秋薇之间,早就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一周前决定去精神病院见她,绝非偶然。
奇怪的是,想到这里,我竟然一点都不觉得害怕。
我稍后继续思索。且不论是何人通过暗示让我想起了陈玉龙,我目前最应该考虑的问题是:这个人为什么要让我想起陈玉龙?
2009年2月7号,陈玉龙在B市××国贸1727房开了房间。而当晚,正是在这个房间里,张瑞林接受了X的突击训练,于翌日完成了对张瑞宝的暗示任务。
很显然,陈玉龙即便不是X本人,也一定跟X有着十分特殊的关系。难道那个人暗示我想起陈玉龙,是为了协助我的调查?
可是,如果这个人真的想帮我,为什么非要暗中相助呢?想到这里,我已经彻底糊涂了。
我打开电脑,对S市招牌里带“启航”二字的律师事务所进行了搜索,并将二十多家事务所的联系方式都做了记录,之后一一电话联系。幸运的是,刚联系到第七家,我就打听到了有价值的信息。
那是一家名为“光明启航”的事务所。核对了陈玉龙的身份信息后,负责人肯定地告诉我,我要找的陈玉龙确实在他的事务所里工作过,那是2004年年初到2005年夏天的事。2005年夏天,陈玉龙又跳槽去了一家“胡国栋律师事务所”。
我给胡国栋事务所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正是胡国栋本人。关于陈玉龙,他的印象很深。
“没错。”他回忆说,“挺勤快一个人,他在我这里一直干到07年。”
我问:“07年之后呢?”
胡国栋沉默片刻,缓缓说道:“07年6月,他输了一场几乎没可能输的官司,我就把他辞退了。你也知道,名声对一个律师公司来说有多重要……”
“他走了之后呢?”我追问道,“您知道他去哪儿了么?”
他说道:“这个我不清楚,不过请你稍等,我可以帮你问问。”十几秒后,他的声音再次响起:“还在么,张主编?”
“当然。”我赶紧问道,“怎么样?”
“是这样,我问了一下他以前的朋友。”胡国栋说,“她说,陈玉龙离开之后,好像是回了你们那里,开过一家法律咨询公司,后来没干下去,就去了你们本地的哪个企业当法律顾问了。嗯,就是这样。”
我心中一惊,听到“本地企业”,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E厂。
“具体是哪个企业,您知道么?”
“这个我问了,没人知道,我们所里的人,现在也都联系不上他了,不然我就直接帮你要到电话了。”
“那他开的那家咨询公司的信息您知道么?”我不肯放弃,“比如名字、地址之类的。”
胡国栋答应帮我问问,半分钟后又拿起电话说:“张主编,问到了,叫嘉龙,郭嘉的嘉,中国龙的龙,嘉龙法律咨询公司。好像是07年年底开的,08年上半年就停业了。”
我再次问道:“那您知道具体地址么?大概的位置、街道名称也行,能不能再帮我问问?停了这么长时间,肯定早就注销了,我是没法找的。”
“我问了,大家也不是很清楚。”他顿了顿说,“不过有个人听陈玉龙说起过,他的公司离家不远。如果你知道他们家原来的位置,可以去那附近问问。他在S市也没混出什么名堂,回去之后,搬家的可能性应该不是很大。当然,如果这几年房屋遇到了拆迁,那就真是不好找了,我也爱莫能助。”
我再三表示感谢。挂了电话,我开始回想陈玉龙以前的住处。2001年到2003年之间,我跟他关系很近,肯定是去过他家的,但想了许久,我也没能记起他家的位置。
回忆过程中,我也难免回想起自己那些年的经历:2000年,我刚刚大学毕业,旋即遭逢重大变故,险些被铺天的压力彻底击倒。我深入理解了各种社会规则,也见识了花样百出的卑鄙手段,更切身体会了人性的万千姿态。
我突然想起,那些年里,陈玉龙至少帮我打过十几次官司,协助我处理过许多法律事务。相关文件,我记得一直是存放在档案柜里的。那么,当年的文件里,是否会存有与陈玉龙个人有关的信息呢?
我连忙打开档案柜,把当年的文件资料一股脑搬了出来,我按照种类,将文件于书桌上分成四摞,之后便开始一一翻阅。在翻阅过程中,我逐渐注意到一件怪事:2002年7月23号之后的文件资料全都不见了。我把档案柜翻了个底朝天,也没能找到丢失的部分。
当然,这并非当时的重点,所以我只是疑虑片刻,就迅速回到了对陈玉龙个人信息的搜寻之中。找到快九点,我终于在2000年10月的一份判决通知书背面,发现了一行已经开始褪色的字:
陈律师,造纸厂家属院。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本地有过一家颇具规模的造纸厂。九十年代初,因为城市扩建,加之污染问题日益严重,造纸厂迁移至属县郊区。厂区拆除重建,职工家属院则留存至今,成为本地老人怀旧的去处之一。近几年,一直有造纸厂家属院拆迁的传闻,但因其住户过多,相关项目始终未能提上日程。
陈玉龙会不会还住在那里呢?
我收住思绪,看了一眼窗外的月色,决定去造纸厂家属院里转转。刚站起身,老婆就推门而入,做了个嘘的手势,随后关上门,低声说:“蛋蛋刚睡着。”又看了一眼打开的柜门和满桌的文件,疑惑地问:“你找什么呢?”
“哦,找点资料。”我手忙脚乱地整理着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