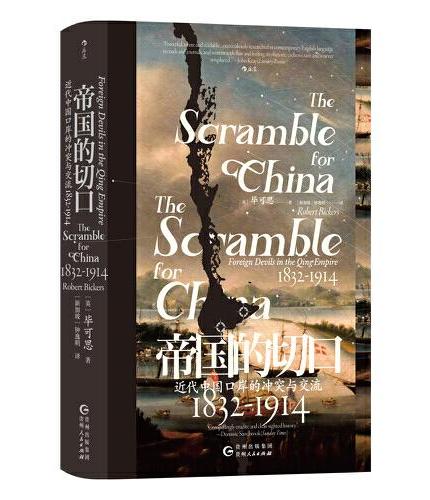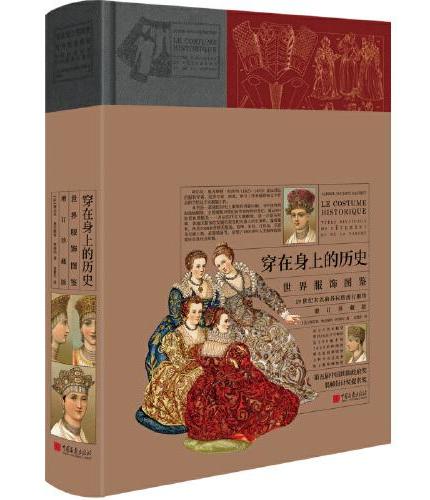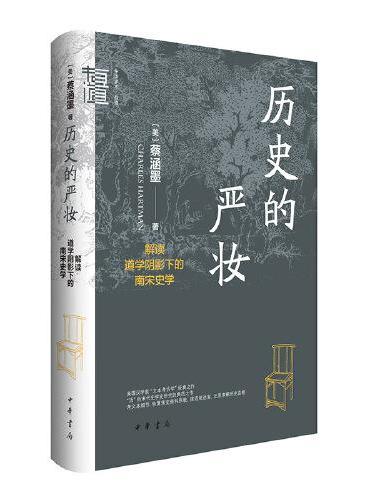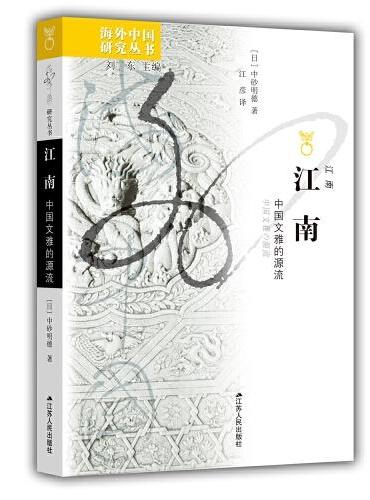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汗青堂丛书147·光明时代:中世纪新史
》
售價:HK$
85.1

《
能成事的团队
》
售價:HK$
111.9

《
现代无人机鉴赏(珍藏版)
》
售價:HK$
7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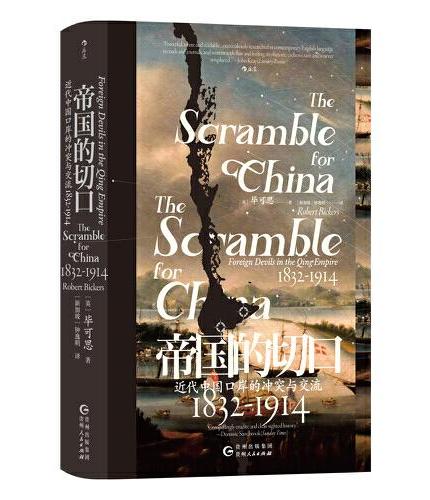
《
汗青堂丛书·晚清风云(4册套装):帝国的切口 清朝与中华传统文化 太平天国运动史 冲击与回应
》
售價:HK$
42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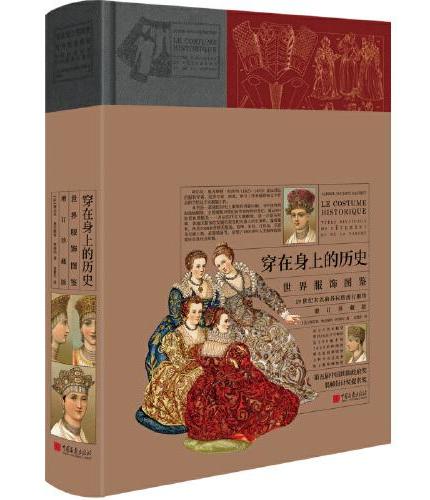
《
穿在身上的历史:世界服饰图鉴(增订珍藏版)
》
售價:HK$
55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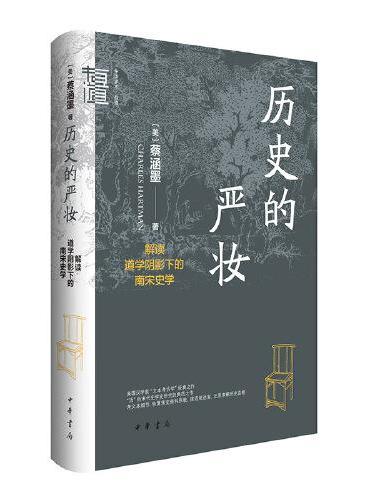
《
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中华学术·有道)
》
售價:HK$
10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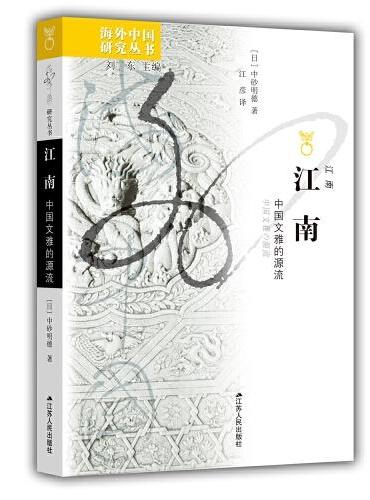
《
海外中国研究·江南:中国文雅的源流
》
售價:HK$
76.2

《
迟缓的巨人:“大而不能倒”的反思与人性化转向
》
售價:HK$
77.3
|
| 編輯推薦: |
不管是象牙塔里的原始人,还是社会下层无法摆脱依附命运与生活圈层的问题少女;无论是一往情深的男性友人,还是不顾一切只挂住孙儿的老人……每个人物都个性鲜明,一个个为不同的困苦挣扎的活生生的社会缩影,独立女性与爱情主题的着墨与社会问题并举,可能正是《银女》命名的某个原因吧……
“蔷薇泡沫”系列小说:《蔷薇泡沫》《那男孩》《心扉的信》《银女》《故园》《印度墨》
|
| 內容簡介: |
|
相识大学校园,有着美好的恋爱与浪漫的蜜月回忆,本应生活甜蜜、令人艳羡,却终究敌不过岁月的流逝。然而,生活总是那么具有戏剧性,刚准备正常生活,男主竟意外去世,女主瞬时做出一系列反常与笃定的举动,是什么力量让她苦苦忍受只为留下小山的遗腹子,又拯救私生子母亲——银女一家看似离奇又不现实的后续故事,因为一个“爱”字,使得最后的结局变得明媚,虽然仍有许多无奈与喟叹。世事无常,若能未卜先知,或许会是另外一个故事……
|
| 關於作者: |
亦舒,原名倪亦舒,1946年生于上海,祖籍浙江镇海,五岁时定居香港。她曾做过记者和编辑,后进入政府新闻处担任新闻官,也当过电视台编剧。现为专业作家,移居加拿大。亦舒兄长是香港作家倪匡。亦舒、倪匡、金庸并称“香港文坛三大奇迹”。
亦舒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与触觉,有擅于将平凡的字眼变成奇句的才华,她的写作正如她的人,麻利、泼辣,写作速度快,作品数量多,但即使换上十个笔名,读者也不难一下子从作品中把她辨认出来。
|
| 目錄:
|
(一)
我抬起头,季康缓缓走过来。无忧问:“你约他的?”
“他天天在这里午餐,这里近医院。”
她拾起手袋:“我回酒店,有什么事找我。”
我说:“耽会儿见。”无忧点点头,叫了街车走。
季康坐下来:“同他说了没有?”
“我是不会离婚的,季康。”
“我真不明白你。”他无奈地说。
我看着天空,也许我还有所留恋,我要等他先开口,待他亲口同我说,他要同我分手,届时我会走得心甘情愿。“人同人的关系千丝万缕,不是说走可走的。”
“很多女人都比你果断。”
“也许她们的男人已逼得她们走投无路。”我笑,“我不相信这世上有果断的女人。”“很多女人确实先提出分手要求。”季康说,“告诉我一个理由,我就不提此事。”
“我的公公婆婆。”我说。
季康叹口气:“我等你。”
“不必等了,像我这样没有味道的女人……三十岁已开始梳髻,整个人散发着消毒药水味……”我苦笑,“你是何苦呢?三年了,你早该成家立室,旁人看在眼里,又是我害的。”
“最近他对你如何?”
“好得很,动不动吃醋,这是他游戏的一部分。”
“你们没有同房吧?”
我站起来:“季康,朋友之间,说话要有个分寸。”
“我不是你的朋友,”他赌气地说,“谁有那么空闲,与异性做三年柏拉图好友?我从来没向你隐瞒过什么,我对你的企图谁不知道?”我的面孔激辣辣地红起来,烧了良久,我看着山外的雾,许久还没坐下来。
“我们走吧。”他看看表。“无迈——”
“不要再说了,季康,不要再等了。”我转过头。
季康笑出来:“这对白多像文艺小说,无迈,你是怎么搞的?”
“应该怎么样?”我质问,“三言两语跳到床上去,过后无痕无恨,这是现代男女的洒脱不是?让我活在旧小说里好了。”我有点愠意。
他把双手插在衣袋里:“也许我就是爱你这一点老派——差点儿没在襟前插支钢笔,或是在腋下别一条手绢。”
“我整个人是过时的,好了没有?”我无奈地说。
“连一张面孔都过时。现在流行粗眉大眼,四方脸蛋,你却仍然细眉画眼,我第一眼看到你,心想:这个人怎么做医生?人命关天哪。”
他笑。我也笑。
季康的声音轻起来:“于是我上了无形的钩,三年来成为林无迈女士的不贰之臣,人家的丈夫要提刀砍我呢。”
“后悔了?”后悔倒也好。
“还没有后悔。我有预感,他就要离开你。”
我们两个人都没吃中饭。
“你上哪儿去?”季康问。
“我去与无忧会合。”
我驾着车子上丽晶,甫停下车,就看见司机老张在那里探头探脑,心惊肉跳的样子,可真巧。
我喝道:“老张,过来!”
老张过来:“太太,我——”
“二小姐住在这里,你去告诉先生,我随时需要车子,叫他给我留点神。”
“这——”
“去啊,还站在这里?”我提高声音。“我一时间找不到先生。”我忍不住冷笑:“蛇有蛇路,鼠有鼠路,你怎么会找不到他?快去,别让我再见到你在这里出入。”
老张一直看着我身后,我警惕地转头。一个穿红的女人连忙转过身子,假装看喷水池。不知怎地,今日我特别大胆,盯牢她看。只见她理了极短的头发,像男孩子的西式头,独独在后颈留了一小撮长穗,又染成红棕色,看上去一阵妖气,鲜红色猄皮衣裤,显得盛臀蜂腰,配一双绣花高跟靴子,一百公尺外都错不过这个人。这便是我丈夫的情人崔露露。我看着自己身上的浅灰色套装与黑漆皮平跟鞋,非常自惭形秽。我深深叹口气。这时候崔露露也略略转侧面孔,像是要看我离开没有。浓妆的脸鲜艳欲滴,大眼黑白分明,下巴角上有几颗小痣,更衬得皮肤白得透明。我忽然想起无忧的问题:台湾女人有什么好?
我无奈地同老张说:“开车回家。”他只得开动车子走。我真不想让无忧看到这一切,回到那边又忍不住告诉父母,爸妈又忍不住担忧,我又得费一番唇舌解释。我往酒店大堂走,陈小山真不识相,香港数十间酒店,他偏偏要订这一间。我抬起头,正碰见他出来。他并没有看见我,照往日我会习惯地躲起来让他渡过这一关,但今日被他一番贼喊捉贼,忍不住要回报。
“陈小山。”他抬起头见是我,呆住了。我有点痛快。“真巧,”我说,“难怪我们有缘分可以做夫妻。”
他犹疑一刻,讪笑道:“我早该想到无忧住的是这间。”
“在门口我看见老张,我同他说:偷闲不要紧,怎么到这里来了?咖啡十五块一杯哩,近来谁给的小账,这么阔气?所以叫他回家去了。”
小山尴尬得不得了。但是他并没有离去。他面孔上有种“吵呀,跟我吵呀”的意思。“你的禁脔在外面等你。”
“你见过她?”小山有点意外。这是我与小山第一次提到“她”。
“多次,”我说,“有时在置地广场那两道自动电梯上交叉相遇,你与她下去,我正上楼。”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你。”小山讶异。
“当然,我穿得灰灰白白,与墙壁有保护色,你想想,你怎么会看得见我?”
“你为什么不同我吵?”
“没有力气。”我停一停,“而且,她的确是个美丽的女人。”
小山沉默一会儿,才说:“你比她美多了。”
我笑:“Give me a break.”“真的。”他说,“只是你太遥远……怎么搅的,无迈,怎么我们又开始谈话了?”
“人家在外头等你。”
“无迈,我不是要你为我放弃工作。我只有一个要求,请你为我告一年长假。”
“干什么?天天到丽晶来捉你?”我笑问。
“我们至少应该要一个孩子。”
“少肉麻了,记得今天晚上在海鲜舫。”
“无迈。”
“站好久了,她的腿不酸,我的腿可软了。”
“为什么老赶我走?”他握住我的手。玻璃门旁红光一闪,我知道是崔露露进来了。“快走,叫无忧看见,你我都有得烦。”我匆匆转头。小山叫道:“晚上有话同你说。”
我并没有找到无忧,她出去了。我自己在咖啡厅吃了简单的食物,打道回府。从头开始,小山想从头开始。太滑稽了,十五年已经过去,他居然想从头开始。怕是一时冲动。叫他天天下班待在家中?他会发神经。太迟了。
回到家我上床午睡,吩咐佣人不接电话。醒来无忧在书房等我。她微笑说:“你很难得有午睡的享受吧。”
我说:“唔,头痛,可见没这个福气。”
“陈小山来不来接我们?”
“他接崔露露还来不及呢。”
无忧说:“你们终于谈到她了?”声音中充满讶异。
“终于,是的,这两个字用得很好,我们终于摊牌了。多年来我逃避现实,否认有这个女人存在,现在……也不能免俗。”
(二)
第二天我回老宅子去看着工人拆水晶灯。这两盏灯足有一公尺直径,累累坠坠,走过时常碰到头顶,但小山喜欢,偏偏要挂在这么矮的天花板上,当年蜜月旅行时在威尼斯以老价钱买回来的。他是一个天真而冲动的人,到一处地方便得买纪念品,穿过的衣裳从不丢掉。
我就是他其中一件体面的旧衣裳。
一次把他的旧猄皮大衣扔掉,他铁青着脸跳得八丈高,拼老命责备我。骂我一点感情也没有,那件大衣是当年他穿了在宿舍门口等我的,下雨刮风都靠它。我根本不记得有那么回事,他起码有三十件类似的大衣。
我用手掩着脸,门铃响,我抬起头。难道还有管理费之类尚未付清?我去开门。门一打开,我看见一张美丽的面孔,它属于一个年轻的女孩,五官美带一种朦胧,紧绷的肌肤发出荧光,身材健壮,长而直的黑发垂在肩上,粗布裤,时髦的松身衬衫。
她面孔上没有一丝欢容,开门见山地说:“我找陈小山先生。”
我温和地问:“你是哪一位?”
“我找陈先生。”因为她出奇的美貌,如画中人一般的姣好,我静静地说:“陈小山
已经过世了。”
她的声音提高:“我两个月前才见过他。”
“他去世有七个多星期了,我是他的妻子,小姐贵姓?”我好脾气地问她。
她张大了嘴,如五雷轰顶般:“他——死了?”这么直截了当,我怔住,傻傻地看住她,这又是什么人?这么关心陈小山的死活?
她气急败坏问我:“你是他妻子?我能不能进来?”
“请进。”我打开大门。屋子里连椅子都没有。
“有什么事?我能帮你吗?”
“我的确认识陈先生,”她自口袋里取出张卡片,递给我,“这是他给我的。”我接过看一眼,的确是小山的卡片。她焦急地用舌头舔一舔嘴唇:“陈太太,我在第一夜总会做事,他认得我。”
第一夜总会,我暗自叹口气。陈小山陈小山,这个女孩顶多只有十八岁,你搞什么鬼。
“我需要钱!”她冲口而出。我看着这个足可以做我女儿的少女,不由得生出无限同情。这么美,这么原始,这么无知,靠着天生的本钱以为可以抓到钱,然而这是不够的。崔露露也需要钱,但是她不会这样狂叫出来。
我并没讪笑她,或是露出不屑。她实在太年轻无知。“钱?”我问。
“是的,陈小山先生说,我可以来找他。”她急急地说,“我多次打电话到公司去,都推说他这个人不在了,最后我找上门去,他们才把这个地址给我。”
如果不是今天拆吊灯,这间屋子早已人去楼空。
我想一想,记起来:“你是王小姐?”
“是,我姓王。”
我同她说:“王小姐,陈先生已经过世,他生前的应诺,我不能代他履行,希望你明白。”
“三千块,只要三千块。”她追上来,“陈太太,你一定有的。”
我不由得生起气来:“我为什么要给你钱?”
她呆在那里,说不出话来。
“你走吧,别在这里烦我。”我说。
她很倔强,涨红面孔,站了一会儿,终于转身离去。
我席地坐下,抽一支香烟。搬家是对的,否则不知有多少这样的纠葛要待我解决。陈小山,你真可恶!我懊恼得出血,若果他尚在人间的话,这一次真是忍无可忍。怎么
会去搭上可以做他女儿的问题女青年,还上门来勒取现金。
“太太,灯已拆好装妥箱子。”工人说。
“好,你们带回去寄出吧。”他们抬着箱子下楼,我尾随锁门。
人去楼空。
我转身刚欲离去,忽然有人叫我:“陈太太。”我吓一跳,一看,还是那个女孩子。
“你还不走!”我有点厌恶。
她并没有崩溃下来,年纪虽年轻,但经验是丰富的,她知道怎样使人心软。我是其中之一个。
“只要三千块,陈太太,这笔款子算得什么?你买一件衬衫也要三千块,而且我会还给你,我有这个能力,我在‘第一’一个晚上就赚过三千块。”
“你这样有办法,一定借得到,何必问我?”
“财务公司不相信我,高利贷集团不敢惹。”
我看着她:“你回第一夜总会好了。”
她愤怒地将宽衬衫拉向后,让我看:“这样子我怎么回去做?我能做的话还用瘪三似的向你借三千元去动手术?这孩子便是陈小山,你丈夫的!”
我目定口呆地退后三步,靠在墙壁上,如五雷轰顶。她的小腹隆起,任何人一眼看上去都会知道她已经有了身孕。
她掠一掠头发,颓丧地自手袋中取出香烟点上。我连忙掏出锁匙,再开了门,“进来。”我说。她随我进去,一脸的怨恨。她额角上细细的汗毛还没有退掉,眉梢眼角全是稚气,这么小的江湖女。我紧张地吞一口唾沫,“孩子是陈小山的?”我问。
“你管是谁的,反正我走投无路,才找上你这里来,谁知道他已经死了?谁会知道三千块钱都没处借?算了,我别处想办法去。”她的神情像一只被激怒的野猫。
我急说:“不!我有钱。”我虚弱地说:“我有钱。”
她看着我。我再问一次:“孩子真是陈小山的?”她点点头。
“有什么证明?”我颤抖着问。
“你可以去问我的妈妈生,我跟陈小山好了很久。”
“你的妈妈为什么不借钱给你?”我的声音更缥缈,我一直靠着墙壁站。
“我跟她斗气,她才不会借给我,她骂我是贱货。”
“没有其他可以帮助你的人?你的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没有朋友?”
“问那么多干什么?一有我就来还你,反正已经来到,我不想再走第二家,免得人家说我梅吉莉连三千块都弄不到!”我倒一杯水,喝一口,递给她。她仰头就喝得杯子见底。真干脆,完全豁出去的样子。
“你吃过饭没有?”我问。
“没有。”
“我们先去吃一点东西,慢慢谈。”我说。
“有什么好谈的?”
她摊开手,“钱呢?”
我只好打开皮夹子给她瞧,刚好里面有万来元现钞,我说:“吃完饭,全是你的。”
她警惕如一只野兽:“为什么全是我的?”
“想知道一些关于我丈夫生前的事。”我拉起她,“来,我想你的肚子也饿了,而且你上门来找陈小山,目的绝不止三千元。”
她随我下楼,我们到附近像样的法国饭店坐下。
“你几岁?”我问道。她看见食物就狼吞虎咽。
“你几岁?”我又问。
她抬起头来,漫不经意地瞪我一眼:“十七。”
十七,才十七。
“在夜总会做什么?”
“做什么?做经理!”她轰然笑起来,满嘴食物。
我无奈地说:“正经点。”
“做小姐。”她说。
“为什么不读书?”我又问。
“陈太太,你的口气同社会福利署的人一模一样。”
“十七岁可以在夜总会出入?不是要到二十一岁?”
“陈太太,有很多事你是不知道的。你没有必要知道哇。”从头到尾,她都是意气风发的,她狡狯,她懂得见风使舵,她气得激怒,但从头到尾,她没有一丝悲哀愁苦。
“你叫梅吉莉?”
“是。”她继续大吃大喝。
“你姓梅?你不是姓王吗?”
她不耐烦地说:“梅吉莉是我的艺名,就像人家做明星,有艺名一样,明白了吗?”“你的真名叫什么?”
“叫我吉莉得了,人人都那么叫。”
“你在夜总会做了多久?”
“客串了两年。”
“什么?”我睁大了眼睛。
吉莉惊异地看我,后来神色转为温柔:“陈太太!”梅吉莉拍拍我的手背:“你很有趣,你很久没有出来走走了。”她抹抹嘴,又伸出手。
我说:“吉莉,我有事要同你商量。”
“快快讲,我时间无多。”
“吃一块蛋糕好不好?这里的巧克力蛋糕做得很好。”我哄着她。她怀疑地看我一眼,点点头。
“吉莉,你喜欢钱——”
她笑:“谁不喜欢?说下去。”
我看着她像苹果似的脸颊,嘴唇还是半透明的,全身无处不透露着青春,这朵花还未尽放就要枯谢,她说得对,我对外头的世界一无所知,我一辈子住在象牙塔中。
“说呀,有什么话快说呀。”吉莉催我。
“我可以给你很多钱。”
“多成怎样?”她好奇但不尽信地问。
“多到你满意为止,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你是女医生是不是?”
“是。”看来她知道的也不少。“你说的话我可以相信?”
“当然可以。”
“什么条件?”
“把孩子养下来。”
“什么?”她怪叫起来。饭店里的客人向我们看来。
我坚决地说:“你听见我说什么,我要你把孩子生下来,不准拿掉。”
她骇笑:“我不懂你说什么,陈太太。”“
现在每月我供给你生活,孩子生下来之后,我再给你一笔整数。”
“为什么?”她张大嘴巴看着我。
我微笑:“我自己没有孩子,我喜欢孩子。”
“你发神经!”她指着我笑。
“或许我是发神经,但你想一想,梅吉莉,这件事对你有什么坏处,几个月之后,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小富婆,手上有一笔钱,可以做你要做的事情。”
我说:“你可以买一层房子结婚,你可以开一爿小小的时装店做生意,你甚至可以再读书。在这几个月内,衣食住行全包在我身上,不过几个月而已,你已经有孕,迹象那么明显,现在去做手术,会有生命危险,你想想清楚。”
她瞪着我。我已经决定了,在她告诉我,她有了孩子之后,我已经决定了。“你喜欢孩子,干嘛不到保良局去领养?”
我故作悠然:“我独独喜欢你这个孩子。”
她很聪明,立刻问:“因为这孩子是你丈夫的?”
“我怎么会知道这孩子是不是我丈夫的?”我也不那么好相与,“死无对证。”
“但是你知道有这种可能性。”她说。“否则我付那么多钱出来干什么?”
我反问,“正如你说,保良局有的是孩子。”
“我恨孩子!”她忽然说,“我不会生他下来。”
“我是妇科医生,你要相信我,我一看就知道,你有孕已经四个月,我个人就不会跟你做这个手术,你只能找到黄绿医生。”
她不出声。
我问:“现在你可以把真名字告诉我了吗?”
“我不会把孩子生下来,我不要孩子!”
“那最好,把孩子给我,我要,你可以一走了之,永远不回头,我也希望你不要回头,当一切没发生过,开始你的新生活。”
她呆视我。
“你不必今天答应我。”我打开手袋,取出一张钞票,“这先给你,你在什么地方住?”“喜相逢公寓。”她取过钞票。
“不能住那种地方,我替你去找一间正式的酒店。”
“你为什么对我好?”她忽然又问。
我看着她。过了很久我说:“如果我一早生孩子,我的女儿就有你这么大。”
她微笑。
我发觉她对我的敌意已消除一大半。
“乱讲,”梅吉莉上下打量我,“你顶多比我大三五岁。”我苦笑,来自她的赞美!陈小山,你在外头还作了什么孽?我送梅吉莉到大酒店,替她登记,向她拿身份证。她很乖,交上身份证。我一看那张身份证,感觉非常唏嘘,孩子要生孩子了。
上帝造物,怎地弄人,一个人真正心智成熟,非要到三十岁不可,但是女人到了三十多岁,已是超龄产妇。身份证上的姓名是:王银女。
我问她:“你父母呢?”
“什么父母?”她又倔强,“陈太太,如果你不停问问题,我们也不必谈了,我最受不了这些。”
“好,我不问。”我与她进酒店房间。
经过大堂的时候,我驻足。在这里,就是这里,我与陈小山说出最后几句话。现在一切都灰飞烟灭。
银女站在一旁等我。我恢复常态,按电梯。“陈太太,”她忽然说,“你长得那么美,陈先生还要出来玩。”
我惨笑。将她安顿好,我便离开。一切像个梦一样,我回到公寓,斟出白兰地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