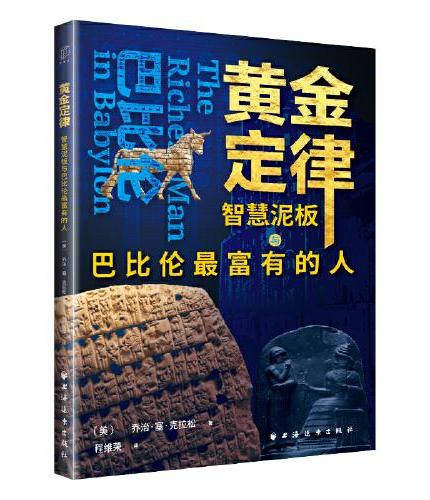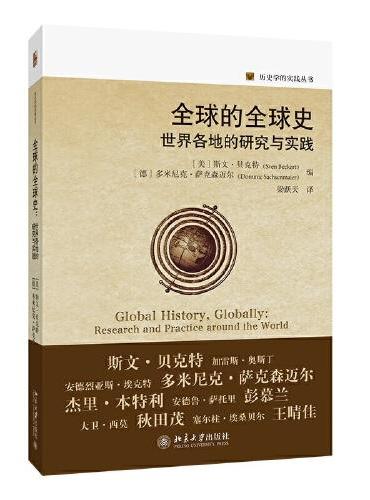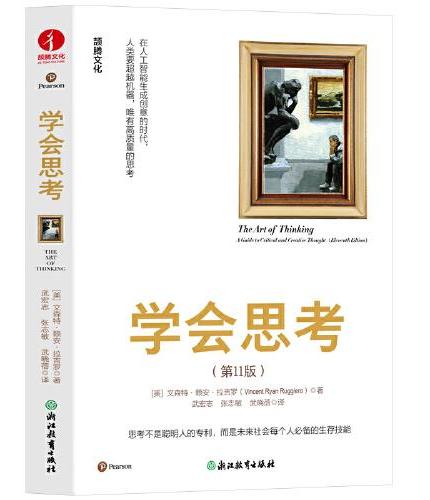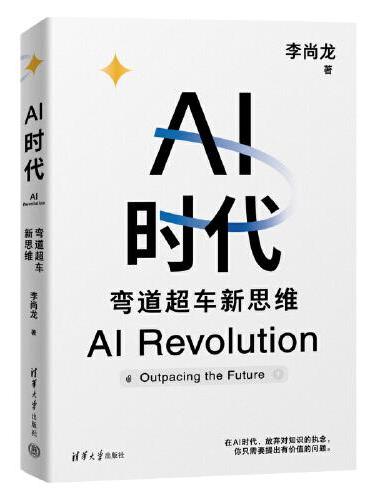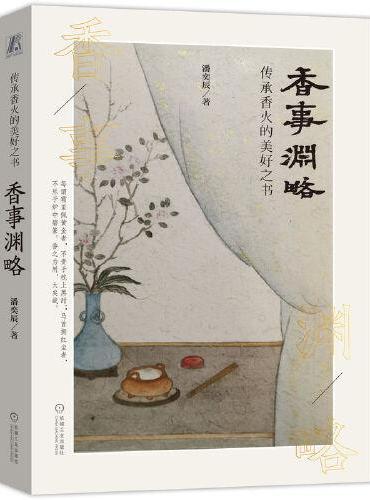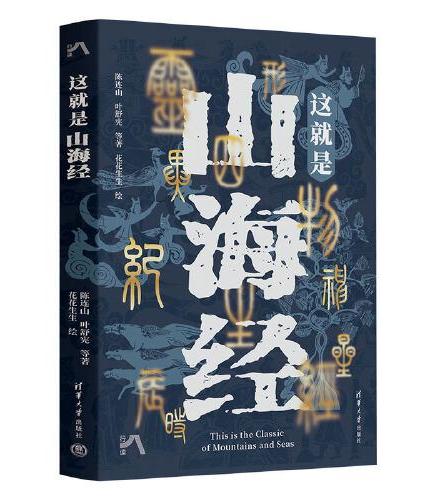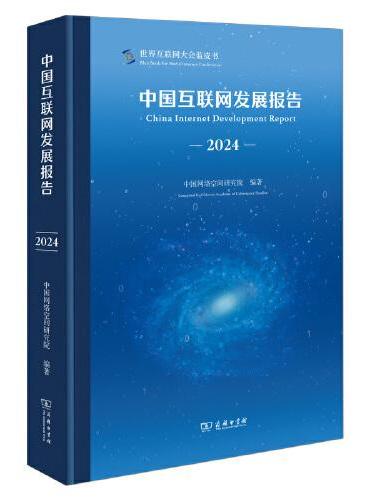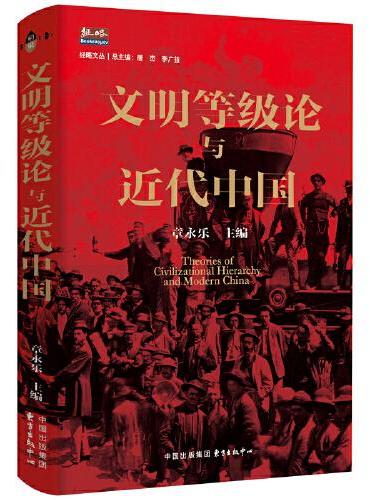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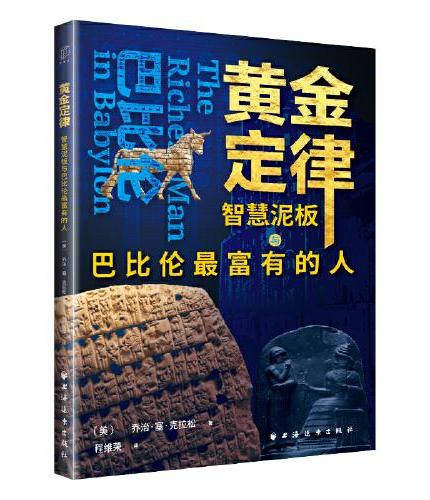
《
黄金定律:智慧泥板与巴比伦最富有的人(全球畅销书!来自古巴比伦的财富课,教你摆脱贫困,智慧管理财富,实现财富持续增长!)
》
售價:HK$
5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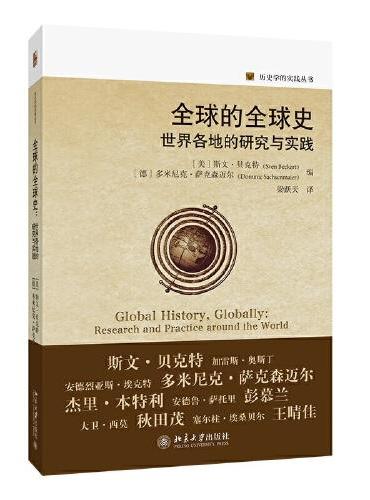
《
全球的全球史:世界各地的研究与实践 历史学的实践丛书
》
售價:HK$
8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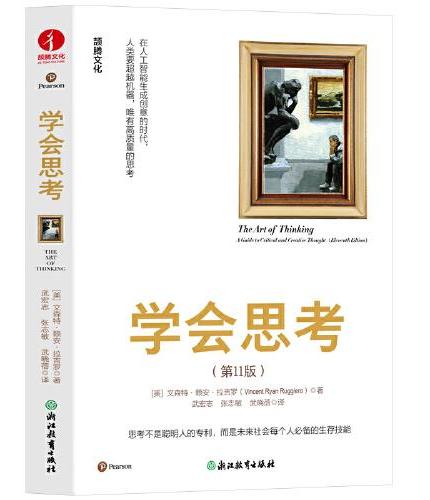
《
学会思考 批判性思维 思辨与立场 学会提问
》
售價:HK$
8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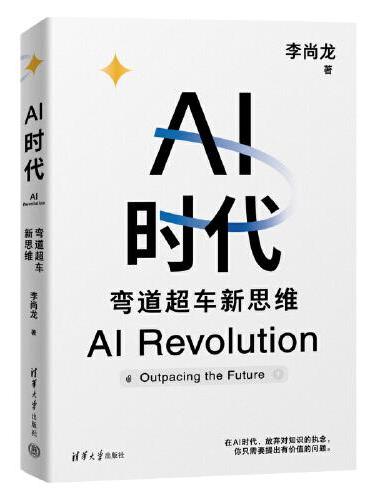
《
AI时代:弯道超车新思维
》
售價:HK$
7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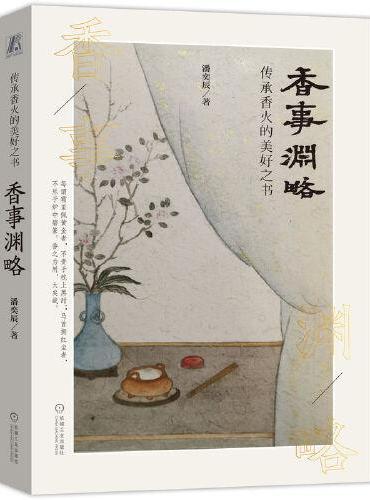
《
香事渊略
》
售價:HK$
10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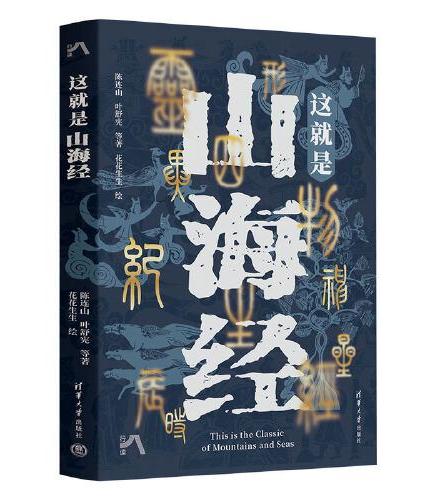
《
这就是山海经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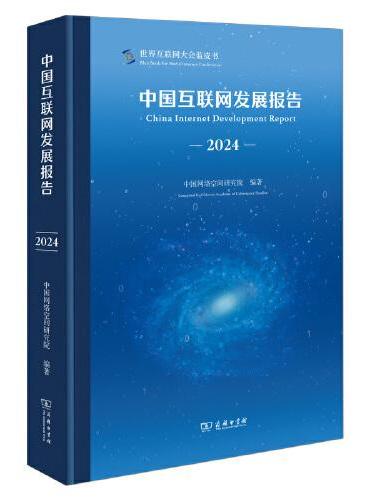
《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4)
》
售價:HK$
26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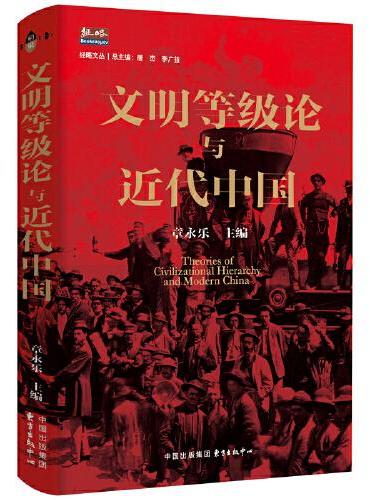
《
文明等级论与近代中国
》
售價:HK$
76.8
|
| 內容簡介: |
怂,还是不怂,这是一个问题。
他是郭德纲的朋友、师胜杰的干儿子、冯巩的属下、姜昆的忘年交。他来自相声圈,却与学术圈的贺卫方、文学圈的刘震云、艺术圈的栗宪庭亦师亦友。
在大多数人眼里,他已功成名就,但在现实生活中,他过得并不快乐。他念念不忘关于相声的一切,可他能站在台上说相声的时间越来越少;他是年轻人的励志偶像,却遍尝演员出走、剧场被封、演出被砸场的苦辛;走上舞台,他是让无数观众捧腹开怀的笑星,走下舞台,他是医院心理门诊的常客;他没有生活,只有工作,宁愿一个人在家看书,也不愿参加相声圈的任何活动;他本该轻松地当个娱乐明星,却自愿背上了过多的责任感与书生气而活得拧巴……
他的存在证明了一句话:唯有坚持梦想,才配得上自己的野心。
他是高晓攀,一个多面而纠结的高晓攀。他的人生就是永不停歇地吹牛逼,再马不停蹄地兑现那些吹过的牛逼。
|
| 關於作者: |
高晓攀 | 讲述
1985年8月2日出生,狮子座,保定人。自幼学习相声,19岁漂泊京城,组建“北京青年相声剧团”,旋即解散。此后,他刷过油漆,干过司仪,当过推销员,短暂“落草”德云社。 23岁,创建“嘻哈包袱铺”,红遍京城;28岁,摘得CCTV电视相声大赛职业组金奖;29岁,登上央视春晚舞台;30岁,“晓攀传媒”融资成功,成为相声界第一家进入资本市场的公司。
他是相声界的争议人物,有人骂他根本不会说相声,有人赞他是不可多得的相声奇才。他被众多粉丝誉为神话,也被不少同行视为瘟疫。他传闻不断,话题不断,掌声与流言齐飞,追捧与谣诼一体。
赵国君 | 撰文
1972年生,水瓶座,中国首席业余作家——业余时间写作的作家,新新中国第一代不明生活物。曾为税吏,后辞职北漂,职业即无业,生活即业余。业余做法律、话剧、媒体、当代艺术,不过找点儿人,说点儿话,思想啸聚,言语霹雳。吹过一些牛,骂过一些人,终成德艺双馨老愤青、感动中国思想钉子户。著有《与正义有关:中国律师纵横谈》、《我心自由:杜尚传》等,主编《读懂财富:茅于轼文集》、《法治必胜:江平文集》等。如今业余做互联网农业研究院。
|
| 目錄:
|
序一 迎风立于相声界 郭德纲 001
序二 看似疯癫,内涵无限 袁腾飞 004
序三 一棵迎风摇曳的小草 薛宝琨 007
序四 从男孩到男人 陶思璇 011
写在前面:这里的相声会好吗赵国君 017
我的自白:我对这个时代并无抱怨 021
第一章 我开始努力了
那一年,我十九 031
那一刻,我长大了 036
去你的,曲艺团 040
何以解忧,唯有单干 045
“我喜欢相声,但不喜欢相声这支队伍” 049
我的法国老炮 053
第二章 小小世界
嘻哈包袱铺成立了 059
先做增量,再做质量 063
喝喝啤酒,侃侃未来 067
黄鼠狼与蜘蛛精 072
我就这个逼样 078
只管搞笑,不计其他 081
这回真火了 085
什么是江湖 089
险遭灭顶之灾 093
这一夜,归我 097
干点儿正事 100
第三章 救,不救?
我得奖了 105
相声不是只会说段子 110
不做犯法事,哪怕见君王 115
从为人民币到为人民 123
我对你有点意见——致曲协 127
我对你有点意见——致老先生 139
我对你有点意见——致同人 145
有个姑娘叫“春晚” 150
当被黑已成习惯 154
我们愧对前辈,应该集体下跪 159
第四章 70 80 90
郭德纲:历史会记住他 175
姜昆:你不懂他 184
冯巩:不足为外人道的孤独 191
师胜杰:“最多给你40分,满分1000” 195
石富宽:“别总录像,跟个傻逼似的 ” 203
师爷冯宝华:一辈子老好人 208
师父冯春岭:“记住,死也要死在北京!” 214
先生马贵荣:我们欠她一份尊重 221
大师兄刘颖:“相声圈很虚伪,你要跳到圈外去活!” 226
第五章 像个孩子
人不犯二枉少年 234
要么最好,要么最坏 239
天生野种 247
那点儿喜好 252
我和小超的第一次 255
找回初心,才算长大 258
附录一 关于相声的一些常识 赵国君 263
附录二 在“认怂”与“不怂”之间——高晓攀对话赵国君 271
附录三 晓攀妙答粉丝提问 285
附录四 曾经的我是个笑话 高晓攀 289
后记一 我的病就是太有感觉 高晓攀 293
后记二 相声为什么不逗乐了 赵国君 297
|
| 內容試閱:
|
我的自白:我对这个时代并无抱怨
我叫高晓攀。拂晓的晓,攀登的攀,别人起床早餐,我起床爬山,纯劳累的命。对了,我属牛。
嘻哈包袱铺成立八年了,而我的故事却跟八十年一样长。不急,我慢慢讲给您听。
很多出版商跟我聊出版的事儿,言辞大多一致——传播正能量,成为畅销书。正能量,这个被人用滥的词,按我的理解就是和大人学着说谎。那可不行,征服人的永远是真诚,真诚就不能是好话一箩筐,不能说些连自己都不信的话,尤其那些煽情肉麻的心灵鸡汤对社会人心的迷惑腐蚀不可不察。
人活着,总该对社会尽些责任。尽管摸爬滚打之中,那么多装备精良的负能量向我袭来,但人生就是一场无休无止的战斗,明知死路一条,也要向死而生,活出个人样。人类是幽默而乐观的动物,我是其中光荣的一员。
我会依照自己的内心而活,无论怎样的血雨腥风都不能撼动我的灵魂。我总幻想自己对黑暗笼罩下的人类负有解救的责任,那是我的天命。
胡适先生四十才自述,我刚三十,远没到写自传的年龄。自述尚早,先自赎吧。
据说,第一流的人物会在有才能的人面前看见自己的才能。莫扎特年少多才,他的音乐那么青春、唠叨,兴高采烈又得意扬扬,在他面前我从自己身上只能看到平庸。相声界的老前辈“万人迷”李德钖能言善辩、俗不伤雅;“笑话大王”张寿臣词句干净、幽默有骨,“傲百氏、蔑王侯”。他们都是我学习的榜样。作为一个不谙世事的年轻人,我只想把相声说好,我想成为第一流的人物,而不是娱乐明星。
一个三十岁的年轻人可能没什么思想,但总还有些感悟与经验值得一说。成长是快乐恣意的,也是苦涩压抑的。一幕幕的回忆,常有开怀大笑,也有潸然泪下,不是我多脆弱,而是我发现自己竟犯过那么多无法弥补的错。如果再来一次,也许我还会犯错,但至少不会错得那么傻、那么丑。
诗人说:生命原是不断地受伤和复原,世界仍是一片温柔地等待着我们成熟的果园。但愿所有受过的伤都能复原,但愿所有犯过的错都能增进成熟,让我的生命温柔如初。
我想认清自己。夜深人静,打开大脑,借着手电筒的光看看自己到底是什么货色:十年学徒那叫一个励志,苦乐忧喜,光芒四射,对善良厚道那叫一个渴望;十年游历演出,江湖苦力,行业新兵,收获一堆误解和白眼,打掉牙和血吞;十年间也曾有过辉煌的时刻,顶着明星的光环招摇过市。我没受过什么学校教育(当然,只有中途辍学的人才会对学校记忆犹新),看的书杂七杂八、不合时宜。明枪暗箭让我变得皮实、早熟,更有各种半吊子的胡思乱想互相打架,我在人前怎么赔着笑脸、怎么抖擞精神也遮掩不住。
合上大脑,我明白了,我是出名了,被封为“最出名的不成功人士”。可成功是什么?人类都在急赤白脸、张牙舞爪地奔向成功这条不归路,浑不知死神正立在身后,望着那些千篇一律的背影哈哈大笑。
我对这个时代并无抱怨,因为时代从没有“正好”过,可从李白、苏东坡到曹雪芹,都活出了气度、神韵和伟大,我不能让时代的不堪为自己的没出息埋单。
有人说,有理想的人是痛苦的。不幸的是,我恰恰就是这样的人。尽管常常有心无力,尽管理想之船常常因碰触现实之礁而沉没,但我对这个时代还是有话要说。这些话有的成了我的相声作品,有的成了本书的文字。我不想支支吾吾,只想掏心掏肺,像一个不招人待见的“愤青”。其实,“愤青”于我,并非贬义,敏感于敏感的人、痛苦于痛苦的人,才会如此心态活泼、酣畅淋漓。愤怒不就是敏感心灵对粗粝现实的正当防卫吗?
在一个没有道德却大谈道德的神奇年代,我品尝着飞短流长之苦,不过,这样的黑色幽默也算是对我说相声的默契回报。人们总喜欢拿着道德的探照灯互相扫射。加缪说得对,痛苦和荒诞简直就是生活的春药,没这两样儿,怎么知道什么是快乐,什么是正经?钱锺书说得更好:人生的刺,就在这里,留恋着不肯离开的,偏是你最不留恋的。
连憨豆先生都抑郁了,据说周星驰也只善待自己。制造快乐的人被不快乐的魔鬼上了身,可中国梦还得做下去,我得努力快乐着。
塞林格说:一个不成熟的男人总是为了某种高尚的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的男人总是为了某种高尚的事业卑贱地活着。相声也好,小品也好,我对快乐负有高尚的责任,但我要声明,我的相声不是为了满足空虚无聊的上层阶级丰富而寂寞的生活,不是为了在同行相轻的争斗中胜者为王,我的相声要反映人的尊严在如今这个社会遭受了怎样的亵渎,我自己又如何在“为民请乐”的征途中狼奔豕突、守住底线。
谁说愤怒不是一种希望、幽默不是一种反抗呢?
我是欢乐英雄,我是天生野种,我的生命卑微而不卑贱,平凡而不平庸。所以,我要绝对告白,我要撕心裂肺,不,掏心掏肺。
江湖仗剑,白马秋风,我学艺至今二十余年,论演出也寒暑十载,虽不敢言老,却不便再卖萌装嫩。我见识浅陋,才华不够,但好歹也是一颗泥土沾身的鲜果。我不想成为罐头,不想德艺双馨,不想感动中国,人民艺术家那么多,还是让我先有点人样吧。
“我光着膀子,我迎着风雪,跑在那逃出医院的道路上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不,崔爷,我的病就是太有感觉!
总之,我与相声一见如故一心一意一炮而红一战到底一命呜呼,是的,终有一天一命呜呼。活着,不过是把死亡之前的这一段填满。就算佛陀也会随风而逝,他老人家临死之前,撩开衣服露出上身,让弟子看他的干瘪丑陋。肉身皮囊,终将化灭,留在我心里的是佛陀最终的教诲:万物终将消逝,兀自勤勉奋斗。
别怂!
那一刻,我长大了
福无双至,坏事却总是买一赠一。演砸的那天,因为拖欠600元房租,房东把我请出家门。
此时的我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只有眼泪才能稀释屈辱。我哭了。一个人沿着鸦儿胡同走到后海,坐在石凳上,一直流眼泪,流完了就发呆。何苦呢?我是家里的独子,本可回家找份安稳的工作,至少有房住,有饭吃。现在却孤身一人,第一次害怕黑夜,第一次感到无助与恐惧。那晚,我沿着四环游走,就那么走啊走,一直走到天亮。无处容身的我被这个城市的万家灯火淹没,悲从中来。
我感觉自己长大了,过去身边有父母可以帮忙解决问题,如今只有自己,只能自己面对,自己解决。
但我还是想家了,急切地想见到父母。回到保定老家,一看见我妈,眼泪立马掉了下来,我扑到妈妈怀里,哭了很久(最少两个小时),这是我迄今最后一次哭,仿佛把这辈子的眼泪都流尽了。哭累了,就睡着了,像小时候一样。迷迷糊糊中妈妈问我:“后悔吗?”我说:“不后悔!”就这样,我又回到了北京。
我坚信,谎言说多了,人们就会把谎言当成真相,我必须回到事故现场,用事实击碎谎言。那一刻,我暗暗告诫自己:别怂!
回到北京,我揣着妈妈给的600元钱,当务之急是解决住房问题。北京的出租屋分地上地下两种,价格不同。我当然租不起地上的,就在中国戏曲学院附近找了一间地下室,每月租金210元,没有窗子,因为有窗子的要360元。安顿下来后,看着四白落地的房间,我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要去哪儿。思索无绪,随口诵出:“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背完了才发现,励志名言都是书上的桥段,现实中根本没用。正所谓:“吃得苦中苦,还是平常人。”
没办法,只好继续漂泊。钻出地下室,我去了三路居旧货市场,花四十元买了一辆自行车,车子非常实用,安全到小偷都不会惦记,我就骑着它满北京城晃荡找工作。我去西单做导购,去798给艺术家刷漆,什么脏活累活都不计较,给钱就干。我还捡过废旧瓶子,有一天捡瓶子卖了七块六,来了份盖浇饭加鸡蛋汤,还剩不到一块钱,坐不起车,就走回了地下室。那也不觉得丢人,因为我在自食其力。
那时,身边的人多主持婚礼,一是来钱快,二是能迅速认识很多人。于是我就人模狗样地拍了张照片,去婚庆公司敲门应聘。由于年龄太小,怕他们不要新人,就愣说自己28了;没有经验,就声称自己主持过三十多场婚礼;不会说婚礼词,就上网吧逼着自己背。从南城到北城,从东城到西城,我几乎转遍了所有的婚庆公司。到现在很多人还奇怪——你一个外地孩子怎么对北京的街巷那么熟悉,其实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这样持续了五个月左右,终于等来了第一次主持婚礼的机会,虽说是个二婚,但这是我的处女秀。那是在娃哈哈大酒店一楼,我接过赚到的300元巨款,幸福得像花儿一样,终于可以阔绰地随便吃盖浇饭喝鸡蛋汤了。
很快,机会来了。北京曲艺团有演出,一个演员临时有事来不了,让我和尤宪超当替补。就这样,我第一次参加了北京曲艺团的演出。那时,北京市政府有个“星火工程”,就是送戏下乡,到北京最偏僻的区县去演出,很多青年演员都参与过。
此处先说几句我的搭档尤宪超。小超是我的表弟,长得膀大腰圆,体重一百公斤,身高一米九开外,别人是吃两口就饱了,他是饱了还得吃两口,并且会因饥饿而情绪失控,让你见识什么才叫愤怒。他打小学曲艺,当时担任“星火工程”演出队队长,这也是我们能有机会到曲艺团演出的原因。小超并不只是我的亲戚,还是我的死党,我俩是在交心见性之后才在一起合作的。
广茗阁风波过后,我被推到风口浪尖,小超也被人游说,要甩了我单干。当时他给我打了一个半小时的电话,说:“哥,你道个歉,这事儿不就完了吗?”我却一再说:“我没有错。如果错了,我会承认,可我没错,就不能认错。这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立场的问题。头上三尺有神明,老天爷睁眼看着呢。”就这样,小超选择留下来,一边上学一边和我演出。我很幸运遇到了这个好弟弟、好搭档。
第一次在北京曲艺团演出的节目是《打灯谜》,效果不错。为了能够留在团里演出,我俩努力当孙子——搬音响,拿道具,支话筒,各种琐事,都抢在前头。曲艺团觉得我俩演得还行,又能干活,演出费也便宜(当时一场一百),就一直用着我俩。
就这样,一个村落挨一个村落地演出,我俩负责开场,就是把观众聚拢过来。人多的时候几百人,人少的时候几条狗而已。山村僻静,偶尔能听到鸟叫,在这样的环境里说相声,不知是诗意,还是凄凉。
我俩每场都会换新节目,都会挖空心思创作、排演,有时候是正经演出,有时候只能做替补。无所谓,给我们演出机会就好。
话说一天凌晨五点多,小超狂敲我屋门:“快,快,演出去,夜里1点,团里来电话,谁也去不了,要求咱们这对老替补去救场。”我睡眼惺忪,惊问:“你怎么来了?”小超一脸气愤:“废话!打得通你电话,我至于来吗?”也是,地下室,人能钻进来,信号不能。
在北京曲艺团断断续续演了一年半,加上平时主持婚礼的收入,小日子过得还行。虽然演出费经常被克扣,虽然上的税都快赶上演出费了,虽然小超帮别人演出了N场没有得到一分钱只换来了一个二手包,但比起过去,日子过得真心不错。我从地下搬到了地上,虽然落下了风湿病,但能够说相声,我已经很满足了。
若说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调进北京曲艺团成为专职相声演员。那时曲艺团的团长崔老师找我谈话,答应把我和小超调进来,我俩甭提多高兴了,这么多年的漂泊终于有了归属感,这么多年的孙子没白当。
可一天过去了,没信。一月过去了,没信。半年都过去了,我终于忍不住去问团长。我赔着笑脸,团长却面沉似水,向我披露了一个重大“敌情”。原来,就在团长决定要办我俩进团的时候,有个叫“人民群众”的家伙跑来揭发,说我是相声界的害群之马,头号坏人,若我这个十恶不赦的人入了团,将长江倒流、泰山崩颓,曲艺团非垮不可!(多年来,我一直在反对者那里享受着巨大殊荣,他们这么高看我,让我自信,也令我练就一身不畏人言的本事。)就这样,我和小超进团的事被无限期搁置,而说这话的居然是小超至亲至近的人。这就是相声圈。
我们没有马上离开曲艺团,因为一离开收入就没了。我们选择沉默,继续当孙子,因为实在是谁也得罪不起。他们师出名门,有权有势,在野兽经常出没的丛林里能量非凡。
最后让我没忍住的是一场车祸。那次曲艺团演出,团里的车上坐满了人,我只能开自己的车去,顺便还捎上了几个演员。那天,下着小雨,我开着二手QQ汽车,跟着团里的车往前走,到路口赶上黄灯,团里的车一个急刹车,我追尾了。二手QQ的车鼻子完全瘪了进去,几近报废,好在车上的人没大事。为了不耽误演出,团里的车先行离开,说一会儿回来处理,由团里负责修。我一个人等着,等了好久,也没人过来,我被他们遗弃在了车祸现场。我问团里该怎么处理,他们说追尾我负全责,和曲艺团没有一毛钱关系,自己修。我说修理费5000块怎么办?他们说,你替团里开车拉人,那是你自愿的,冻豆腐,没法办。
5000块对我来说绝对是天文数字,我上哪儿去找这么多钱啊!就在这个时候,坏事又是买一赠一,坐在副驾驶的人找我要医药费,说责任在我。我真不明白自己错在哪儿,不明白老天爷为什么总是拿弱者开刀。当时的女友哭得不行,问我为什么这么受人欺负,我说:谁也不怪,就怪自己没本事!
就这样,我离开了北京曲艺团。
理想分两种,一种是自己的,一种是成人世界做好后派发给你的。
我的理想就是独自拼搏,自己选择。
在艺校的时候,我非常快乐,那是一种在应试教育下因犯禁而带来的快感。我们一群半大小子如同茂盛的小树四肢伸展,志在高空;而老师教给我们的基本技艺,却是拿着大剪刀,嘁哩喀喳地剪啊剪。原来,所谓园丁就是把小树成长的一切可能性全都剪掉。
我跟老师一板一眼地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的教导时时回响在耳畔。社会倡导苦中作乐,成人们暗示我不服从者不得食。可我却满心不解:为什么学习这件事这么苦逼、这么功利?如果学习不能让人快乐,不能带来追求真理的愉悦,那我宁可不学习。
于是,我拒绝按老师的方法学,捣乱、翘课,一会儿是整蛊少年,一会儿是检讨大王。老师摇头叹息,我却逍遥自在,体会着野蛮生长的快乐。
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日子很短。社会是个成长速成班,总要劫掠青春,消灭野种。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孩子也是。我年龄幼小,不明就里,对大人们的一惊一乍甚感困惑,在他们眼里我是个问题少年。
等上了大学,北漂打工,再也没有装嫩的理由,我必须长大,保持天真才是罪过。
幸福是什么?快乐在哪里?教育为什么那么面孔生硬、虚情假意?我不明白。
相声是古老的传承,也是大胆的创新,可为什么年轻人一创新,老先生们就害怕?
流言蜚语的目的是什么?是误解,是嫉妒,还是一种深深的自卑?
我还年轻,想法很简单——我渴望在一个自由多元的社会,按照自己的样子活着。我想,我的存在不会伤到任何人,因为我和你们一样对这个世界怀有美好的期待。
法国艺术家杜尚25岁的时候已经功成名就,但他决心退出艺术界,不再以艺术家的身份生活,尤其不加入任何艺术团体。杜尚认为,任何艺术团体在成立之初都信誓旦旦、野心勃勃,充满了前卫与先锋的念头,但时间一长,就会走向反面,成为压制新生、抵抗新潮的力量,人类在这方面没有长进,也看不到希望。我厮混的相声圈也有大量的团体请君入瓮。学校、曲艺团、协会是有形的组织;此外,无形的职业、事业与功名都引诱你投怀送抱。我虽不能免俗,但还是想保持距离,不被俗名所累。
青年剧团演砸了,没人要我,只得另起炉灶,我要用事实击碎谎言。几年之后,相声界对我的驱逐并未得逞,我三寸气在,活出了他们没有的模样。
大仲马说:人生是一串忧患的珠子串成的项链,有人却微笑着数完它。我,一直在微笑。
父母让我学相声是想让我有一个能安身立命的职业,如今,相声不仅是我的职业,还是我的理想。我知道做一个娱乐明星的好处,可我不想只得到眼前的好处,我还想说出相声的好处。
在没有忧愁时看到忧愁,在没有苦恼处感到苦恼,我情感丰沛,志气高扬,在经历了人间的种种可笑之后,我发誓要越过陷阱奔向理想。
“何以解忧?”我举头问天。
“唯有单干!”天空回答得响亮、干脆。
东城区有个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许多年轻演员都想到那儿去演出。年轻人嘛,机会不多,给点儿机会就灿烂。
“我也想去。”
“你去?谁去都行,就你不行!”
那位知名的相声演员判了我死刑。
可我还是去了,这得感谢孟凡贵先生。孟先生是俱乐部核心组成员,与主席李金斗先生的交谊非同一般,没有他的推荐,演出是不可能的。
我那叫一个激动啊!拿到节目单一看,是《夸住宅》,排在第一个。演出前,孟先生认为老段子第一个出场,效果不会太好,就把我调到了第二场。很简单的一次调场,却被一位老先生说成挑剔,说我挑场口演出。
十八九岁的我多希望遇见一些美好的东西啊。我承认自己还未得到过任何名利,但我觉得那位知名的老先生名利心也太重了些。我清楚地记得他在背后对我干的那些事:他拦着他的徒弟不让参加我的青年相声剧团;在琴书泰斗关学曾的葬礼上,他拉着曲艺团团长说“这个孩子不能进团”;他发狠死活不让我参加东城周末相声俱乐部的演出。每次见面我都客气地和他打招呼,他却对我赠以白眼,并在每个人面前抓住机会羞辱我。前辈本该春风化雨、大度为怀,可这一位却处处咄咄逼人,恨不得把我掐死。
我没有退缩,我要澄清谣言。如果离开,谎言就会变成侮辱我的现实,我并不准备上当。
此时,郭德纲正火,火了的郭德纲不只收获赞誉,也频遭非议,甚至威胁。面对这些风刀霜剑,郭先生咬着牙说:“如果不让我说相声,我就一头撞死在天桥乐门口!”这是用生命去捍卫相声。我能体会郭先生的难处,也就更有勇气正视圈里的流言蜚语。
对一个热爱相声的人来说,死在舞台上是件幸福的事。记得一次演出后,我躺在小梨园的舞台上,不愿离开。我抚摩着舞台,它平滑如水,又十分安静,我的心也安静了许多。我想,我一定要在舞台上留下属于我的故事。
马季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喜欢相声,但不喜欢相声这支队伍!”
我是相声界的小字辈,对相声队伍不敢说什么,但人情冷暖的事也算经历过一些,深知马先生话中的深意。相声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没有传承,很难发展,但所谓发展是要去除相声界的劣根性。老先生那一代也许习惯了“气人有、笑人无”,我们可不能这样,我们要习惯学习人家的优点。我们这一代说相声的就是要“体制内没位置,市场中找位置”。我不想卷入派系斗争,不想把有限的精力耗费在无聊的人际关系上,我要打造出属于自己的舞台。
活着,都是人在做,天在看。成长不就是一个试错并允许犯错的过程吗?老先生们的不宽容反倒成了助我长进的动力。我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就要去面对,哪怕我只是一只刚刚出洞的小老鼠。
小老鼠说:我要把老鼠夹子当成健身器。
我的法国老炮
生活不总是低谷,也有喜悦和高潮。
我意外地遇到了一位法国人,他带给我的记忆堪称美好,也影响了我的性格。
那时我刚大学毕业,找了一处房子,房东就是这位法国老外,中文名按音译叫冯嘉伟。我永远也忘不了第一次走进老冯屋里的情景。我被满屋子的书和电影光盘惊呆了,以前从未见过谁家有这么多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