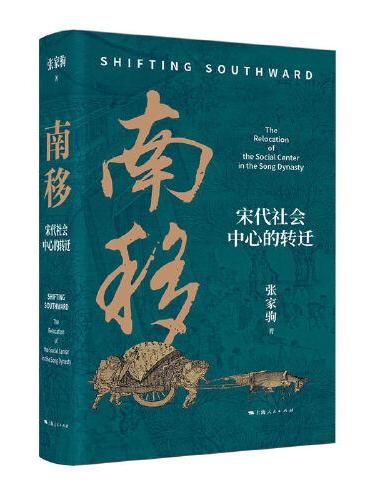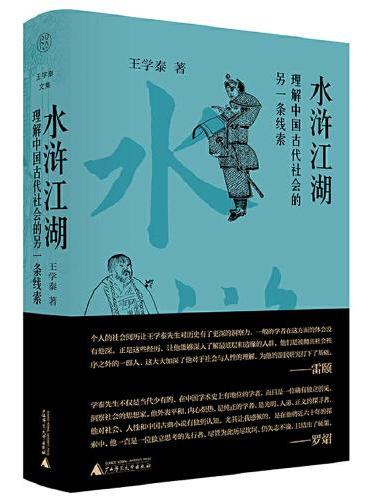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女人们的谈话(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提名、最佳改编剧本奖 原著!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简直是《使女的故事》现实版!”)
》
售價:HK$
61.6

《
忧郁的秩序:亚洲移民与边境管控的全球化(共域世界史)
》
售價:HK$
140.8

《
一周一堂经济学课: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
》
售價:HK$
107.8

《
慢性胃炎的中医研究 胃
》
售價:HK$
65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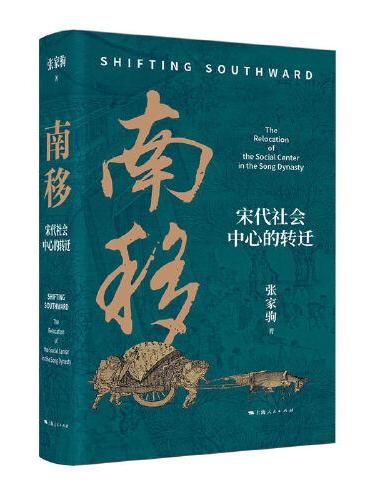
《
南移:宋代社会中心的转迁
》
售價:HK$
16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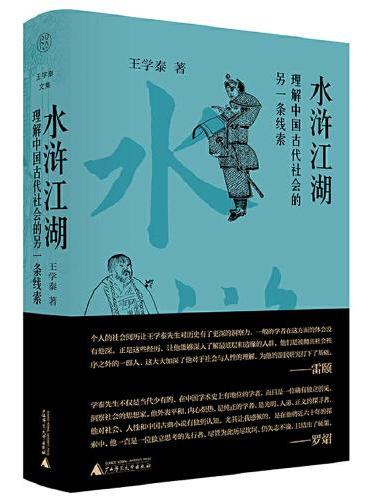
《
纯粹·水浒江湖: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另一条线索
》
售價:HK$
101.2

《
肌骨复健实践指南:运动损伤与慢性疼痛
》
售價:HK$
294.8

《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MySQL版)
》
售價:HK$
64.9
|
| 編輯推薦: |
|
这本《傅斯年诗经讲义稿》是傅斯年先生在1927年担任中山大学教授时,为学生讲授《诗经》所写的讲义。讲义涵盖了诗经研究史、诗经研究方法、诗经的地理、诗经的艺术性等多方面内容,显示出一个具有深厚国学积淀和系统西学思想素养的年轻学者的学术眼光。虽称讲义,其实名之“诗经通论”也不为过。其涉及《诗经》相关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放在今天的《诗经》研究著作中也并不过时,堪称《诗经》讲义类著作的经典。
|
| 內容簡介: |
|
《诗经讲义稿》是傅斯年先生在中山大学讲授《诗经》时的课堂讲义,也是近现代研究《诗经》的重要文献。在此书中,傅斯年发幽阐微,提出许多特异的见解,虽为学术著作,但并不深奥,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是国学爱好者与研究者常备的一部资料文献。
|
| 關於作者: |
|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生于山东聊城。中国近代文史语言学家、教育家,毕生提倡白话文学,宣扬新思潮。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英国有丁堡大学、伦敦大学、德国柏大学。回国后历任中山学国文系、历史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1928年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聘,筹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并出任所长。1949年随历史研究所迁往台北,并兼任台湾大学校长。著作有《诗经讲义稿》、《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性命古训辨证》、《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等。
|
| 目錄:
|
目录
叙语 1
泛论诗经学 3
一、西汉诗学 8
二、《毛诗》 9
三、宋代诗学 11
四、明季以来的诗学 13
五、我们怎样研究《诗经》 14
《周颂》 18
周颂说(附论鲁南两地与《诗》、《书》之来源) 18
《大雅》 46
一、雅之训恐已不能得其确义 46
二、《大雅》的时代 47
三、《大雅》之终始 49
四、《大雅》之类别 50
《小雅》 53
一、《小雅》、《大雅》何以异 53
二、《小雅》之词类 55
三、“雅者政也” 58
四、《雅》之文体 59
《鲁颂》、《商颂》述 60
一、《商颂》是宋诗 61
二、《商颂》所称下及宋襄公 63
三、《商颂》非考父作 67
《国风》 70
一、“国风”一词起来甚后 70
二、四方之音 71
三、“诸夏”和《国风》 75
四、起兴 76
《国风》分叙 78
一、《周南》、《召南》 78
二、邶鄘卫 81
三、王 86
四、郑 87
五、齐 88
六、魏 89
七、唐 90
八、秦 91
九、陈 92
十、桧 93
十一、曹 93
十二、豳 93
《诗》时代 95
周诗系统 96
非周诗 97
《诗》地理图 98
《诗》之影响 99
论所谓“讽” 101
《诗三百》之文辞 109
附录
文学革新申义 132
诗部类说 145
风 146
雅 153
颂 155
《诗经》中之“性”、“命”字 165
一、论《诗经》中本无“性”字 165
二、《诗经》中之“令”、“命”字 166
宋朱熹的《诗经集传》和《诗序辨》 174
|
| 內容試閱:
|
泛论诗经学
《诗经》是古代传流下来的一个绝好宝贝,他的文学的价值有些顶超越的质素。自晋人以来纯粹欣赏他的文辞的颇多,但由古到今,关于他的议论非常复杂,我们在自己动手研究他以前,且看二千多年中议论他的大体上有多少类,那些意见可以供我们自己研究时参考?
春秋时人对于诗的观念:“诗三百”中最后的诗所论事有到宋襄公者,在《商颂》;有到陈灵公者,在《陈风》;若“胡为乎株林从夏南”为后人之歌,则这篇诗尤后,几乎过了春秋中期,到后期啦。最早的诗不容易分别出,《周颂》中无韵者大约甚早,但《周颂》断不是全部分早,里边有“自彼成康奄有四方”的话。传说则时迈武桓赉诸篇都是武王克商后周文公作,(《国语》、《左传》)但这样传说,和奚斯作《鲁颂》,正考父作《商颂》,都靠不住;不过《雅》、《颂》中总有不少西周的东西,其中也许有几篇很早的罢了。风一种体裁是很难断定时代的,因为民间歌词可以流传很久,经好多变化,才著竹帛:譬如现在人所写下的歌谣,许多是很长久的物事,只是写下的事在后罢了。《豳风·七月》是一篇封建制度下农民的岁歌,这样传来传去的东西都是最难断定他的源流的。《风》中一切情诗,有些或可考时代者,无非在语言和称谓的分别之中,但语言之记录或经后人改写(如“吾车既工”之吾改为我,石鼓文可证,吾我两字大有别)。称谓之差别又没有别的同时书可以参映,而亚当夏娃以来的故事和情感,又不是分甚么周汉唐宋的,所以这些东西的时代岂不太难断定吗?不过《国风》中除《豳》、《南》以外所举人名都是春秋时人,大约总是春秋时诗最多,若列国之分,乃反用些殷代周初的名称,如邶鄘卫唐等名,则辞虽甚后,而各国风之自为其风必有甚早的历史了。约而言之,“诗三百”之时代一部分在西周之下半,一部分在春秋之初期中期,这话至少目前可以如此假定。那么,如果春秋时遗文尚多可见者,则这些事不难考定,可惜记春秋时书只有《国语》一部宝贝,而这个宝贝不幸又到汉末为人割裂成两部书,添了许多有意作伪的东西,以致我们现在不得随便使用。但我们现在若求知《诗》在春秋时的作用,还不能不靠这部书,只是在用他的材料时要留心罢了。我想,有这样一个标准可以供我们引《左传》、《国语》中论《诗》材料之用:凡《左传》、《国语》和毛义相合者,置之,怕得是他们中间有狼狈作用,是西汉末治古文学者所加所改的;凡《左传》、《国语》和毛义不合者便是很有价值的材料,因为这显然不是治古文学者所加,而是幸免于被人改削的旧材料。我们读古书之难,难在真假混着,真书中有假材料,例如《史记》;假书中有真材料,例如《周礼》;真书中有假面目,例如《左传》、《国语》;假书中有真面目,例如东晋伪《古文尚书》。正若世事之难,难在好人坏人非常难分,“泾以渭浊”,论世读书从此麻烦。言归正传,拿着《左传》、《国语》的材料求《诗》在春秋时之用,现在未作此工夫不能预断有几多结果,但凭一时记忆所及,《左传》中引《诗》之用已和《论语》中《诗》之用不两样了。一、《诗》是列国士大夫所习,以成辞令之有文;二、《诗》是所谓“君子”所修养,以为知人论世议政述风之资。
说到《诗》和孔丘的关系,第一便要问:“孔丘究竟删诗不?”说删《诗》最明白者是《史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袵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这话和《论语》本身显然不合。“诗三百”一辞,《论语》中数见,则此词在当时已经是现成名词了。如果删诗三千以为三百是孔子的事,孔子不便把这个名词用得这么现成。且看《论语》所引诗和今所见只有小异,不会当时有三千之多,遑有删诗之说,《论语》、《孟》、《荀》书中俱不见,若孔子删诗的话,郑卫桑间如何还能在其中?所以太史公此言,当是汉儒造作之论。现在把《论语》中论《诗》引《诗》的话抄在下面。
《学而》
1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为政》
2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3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4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5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6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泰伯》
7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8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9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子罕》
10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11“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先进》
12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子路》
13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卫灵公》
14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季氏》
15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诚不以富,亦祗以异”,其斯之谓与?(此处朱注所校定之错简)
16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
《阳货》
17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18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19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20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从此文我们可以归纳出下列几层意思:
一、以诗学为修养之用;
二、以诗学为言辞之用;
三、以诗学为从政之用,以诗学为识人论世之印证;
四、由诗引兴,别成会悟;
五、对诗有道德化的要求,故既曰“思无邪”,又曰“放郑声”;
六、孔子于乐颇有相当的制作,于诗虽曰郑声,郑声却在《三百篇》中。
以《诗三百》为修养,为辞令,是孔子对于《诗》的观念。大约孔子前若干年,《诗三百》已经从各方集合在一起,成当时一般的教育。孔子曾编过里面的《雅》、《颂》(不知专指乐或并指文,亦不知今见《雅》、《颂》之次序有无孔子动手处),却不曾达到《诗三百》中放郑声的要求。
一、西汉诗学
从孟子起,《诗经》超过了孔子的“小学教育”而入儒家的政治哲学。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简直是汉初年儒者的话了。孟子论《诗》甚泰甚侈,全不是学《诗》以为言,以为兴,又比附上些历史事件,并不合实在,如“戎狄是膺,荆舒是惩”附合到周公身上。这种风气战国汉初人极多,《三百篇》诗作者找出了好多人来,如周公、奚斯、正考父等,今可于《吕览》、《礼记》、《汉经说遗》文中求之。于是,一部绝美的文学书成了一部庞大的伦理学。汉初《诗》分三家,《鲁诗》自鲁申公,《齐诗》自齐辕固生,《韩诗》自燕太傅韩婴,而《鲁诗》、《齐诗》尤为显学。《鲁诗》要义有所谓四始者,太史公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又以《关雎》、《鹿鸣》都为刺诗,太史公曰:“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凌迟,《鹿鸣》刺焉。”其后竟以“三百篇”当谏书。这虽于解诗上甚荒谬,然可使《诗经》因此不佚。《齐诗》、《韩诗》在释经上恐没有大异于《鲁诗》处,三家之异当在引经文以释政治伦理。齐学宗旨本异鲁学,甚杂五行,故《齐诗》有五际之论。《韩诗》大约去泰去甚,而于经文颇有确见,如殷武之指宋襄公,即宋代人依《史记》从《韩诗》,以恢复之者。今以近人所辑齐鲁韩各家说看去,大约齐多侈言,韩能收敛,鲁介二者之间,然皆是与伏生《书》、公羊《春秋》相印证,以造成汉博士之政治哲学者。
二、《毛诗》
《毛诗》起于西汉晚年,通达于王莽,盛行于东汉,成就于郑笺;从此三家衰微,毛遂为诗学之专宗。毛之所以战胜三家者,原因甚多,不尽由于宫庭之偏好和政治之力量去培植他。第一,申公辕固生虽行品为开代宗师,然总是政治的哲学太重,解《诗》义未必尽惬人心,而三家博士随时抑扬,一切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必甚多,虽可动听一时,久远未免为人所厌。而《齐诗》杂五行,作侈论,恐怕有识解者更不信他。则汉末出了一个比较上算是去泰去甚的诗学,解《诗》义多,作空谈少,也许是一个“应运而生”者。第二,一套古文经出来,《周礼》左氏动荡一时,造来和他们互相发明的《毛诗》,更可借古文学一般的势力去伸张。凡为《左传》文词所动周官系统所吸者,不由不在诗学上信毛舍三家。第三,东汉大儒舍家学而就通学,三家之孤陋寡闻,更诚然敌不过刘子骏天才的制作,王莽百多个博士的搜罗;于是三家之分三家,不能归一处,便给东京通学一个爱好《毛诗》的机会。郑康成礼学压倒一时,于《诗》取毛,以他的礼学润色之,《毛诗》便借了郑氏之系统经学而造成根据,经魏晋六朝直到唐代,成了惟一的诗学了。
《毛诗》起源很不明显,子夏、荀卿之传授,全是假话。大约是武帝后一个治三家《诗》而未能显达者造作的,想闹着立学官(分家立博士,大开利禄之源,引起这些造作不少,尤其在书学中多)。其初没有人采他,刘子骏以多闻多见,多才多艺,想推翻十四博士的经学,遂把他拿来利用了。加上些和从《国语》中搜出来造作成的《左传》相印证的话,加上些和《诗》本文意思相近的话,以折三家,才成动人听闻的一家之学。试看《毛传》、《毛序》里边有些极不通极陋的话,如“不显显也”,“不时时也”之类,同时又有些甚清楚甚能见闻杂博的话,其非出于同在一等的人才之手可知。现在三家遗说不能存千百于十一。我们没法比较《毛诗》对于三家总改革了多少,然就所得见的传说论,《毛诗》有些地方去三家之泰甚,又有些地方,颇能就《诗》的本文作义,不若三家全凭臆造。所以《毛诗》在历史的意义上是作伪,在诗学的意义上是进步;《毛诗》虽出身不高,来路不明,然颇有自奋出来的点东西。
三、宋代诗学
经学到了六朝人的义疏,唐人的正义,实在比八股时代的高头讲章差不多了,实在不比明人大全之学高明了。自古学在北宋复兴后,人们很能放胆想去,一切传说中的不通,每不能逃过宋人的眼。欧阳永叔实是一个大发难端的人,他在史学、文学和经学上一面发达些很旧的观点,一面引进了很多新观点,摇动后人(别详)。他开始不信《诗序》。北宋末几朝已经很多人在那里论《诗序》的价值和诗义的折中了。但迂儒如程子反把《毛诗序》抬得更高,而王荆公谓诗人自己作叙。直到郑夹漈所叙之论得一圆满的否定,颠覆了自郑玄以来的传统。朱紫阳做了一部《诗集传》,更能发挥这个新义,拿着《诗经》的本文去解释新义,于是一切不通之美刺说扫地以尽,而《国风》之为风,因以大明。紫阳书实是一部集成书,韵取吴才老叶韵之说,叶韵自陈顾以来的眼光看去,实在是可笑了,但在古韵观念未出之前,这正是古韵观念一个胎形。训诂多采毛、郑兼及三家遗文,而又通于礼学(看王伯厚论他的话)。其以赋比兴三体散人虽系创见,却实不外《毛诗》独标兴体之义。紫阳被人骂最大者是由于这一部书,理学、汉学一齐攻之,然这部书却是文公在经学上最大一个贡献,拿着本文解诗义,一些陋说不能傅会,而文学的作用赤裸裸的重露出来。只可惜文公仍是道学,看出这些诗的作用来,却把这些情诗呼作淫奔,又只敢这样子对付所谓变风,不敢这样子对付大、小《雅》、《周南》、《召南》、《豳风》,走得最是的路,偏又不敢尽量的走去,这也是时代为之,不足大怪。现在我们就朱彝尊的《经义考》看去,已经可以觉得宋朝人经学思想之解放,眼光之明锐,自然一切妄论谬说层出不穷,然跳梁狐鸣,其中也有可以创业重统者(文公对于文学的观念每每非常透彻,如他论《楚辞》、陶诗、李、杜诗常有很精辟的话,不仅说《三百篇》有创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