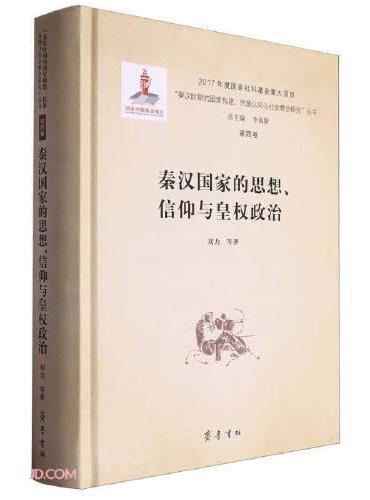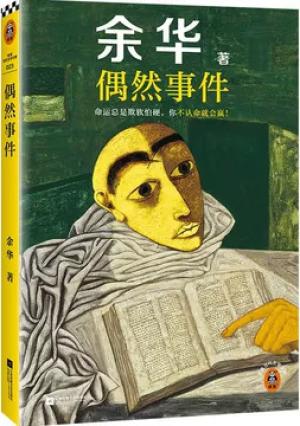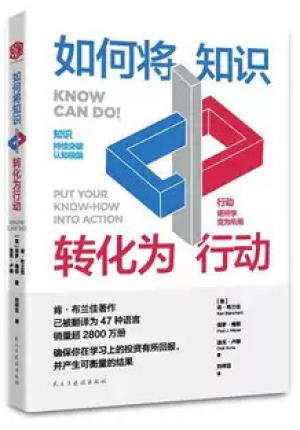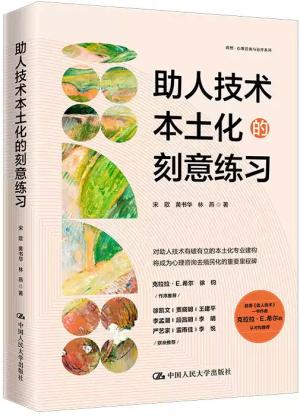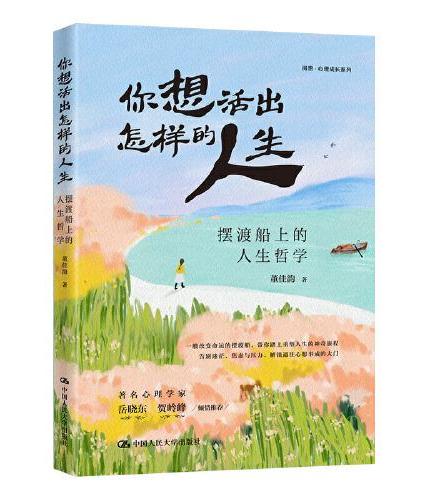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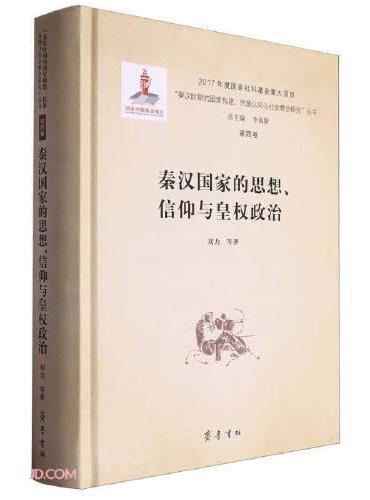
《
秦汉国家的思想、信仰与皇权政治
》
售價:HK$
215.6

《
反卷社会:打破优绩主义神话(一本直面焦虑与困境的生活哲学书!)
》
售價:HK$
8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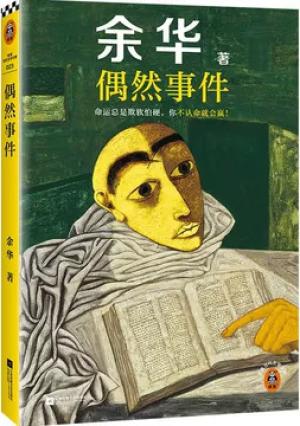
《
偶然事件(命运总是欺软怕硬,你不认命就会赢!)
》
售價:HK$
54.9

《
余下只有噪音:聆听20世纪(2025)
》
售價:HK$
20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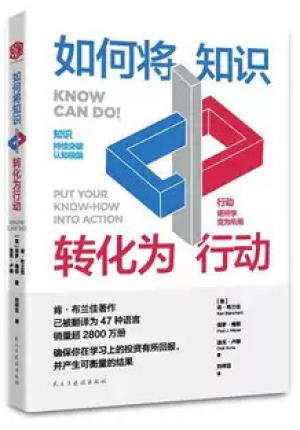
《
如何将知识转化为行动
》
售價:HK$
7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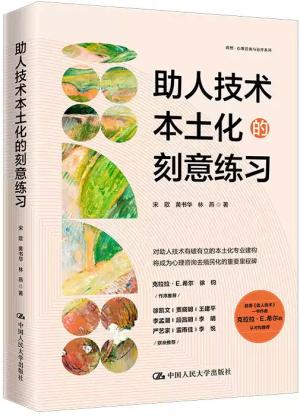
《
助人技术本土化的刻意练习
》
售價:HK$
87.9

《
中国城市科创金融指数·2024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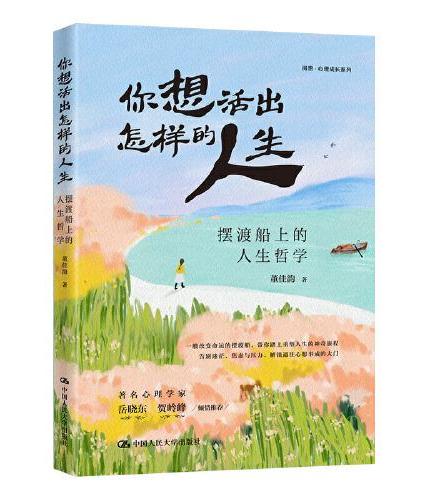
《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摆渡船上的人生哲学
》
售價:HK$
65.9
|
| 編輯推薦: |
|
“故乡在中国”丛书系目前国内首部整合、出版的,通过外国人的视角反映1926年至1937年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和以庐山为主的自然风光、中外交往的回忆录形式的纪实作品。对于丰富20世纪上半叶中外(美)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的研究史料,通过外国人的视角反映那一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和以庐山为主的自然风光,具有不可或缺的史料价值和重要的文化价值。
|
| 內容簡介: |
|
本书系“故乡在中国”丛书之一。全书共分三辑:赫特医生在庐山、九江、安庆等地的故事、赫特夫人在中国的日子、赫特夫人珍贵信件。对中华护理学会创始人赫特夫人及其丈夫芜湖弋矶山医院创始人赫特医生进行了珍贵史料的整理和补充,以特殊的视角丰满细腻地再现了上个世纪中国的社会经济、风俗文化、医疗卫生、饮食和自然风光。
|
| 關於作者: |
|
凯思林·C.格林、斯坦利·克劳福德都是中华护理学会创始人赫特夫人的后人,其中斯坦利·克劳福德在中国生活多年。
|
| 目錄:
|
译者序
前言
第一辑
赫特医生在庐山、九江、安庆等地的故事
埃杰顿·哈斯克尔·赫特医生继承父志3
九江特别验尸案16
舒欢的故事26
第二辑
赫特夫人在中国的日子
卡罗尔·伊内·马多克·赫特小传33
9月的芜湖41
1907年的蜜月58
蜜月中国行65
九十九人的村庄66
安庆67
夜遇江匪70
芜湖河州访旧友72
弋矶山附近的村庄73
捍卫自己的清白78
山东公会83
第三辑
赫特夫人的珍贵信件
小孤山87
景德镇93
霍格船长101
长江106
孤独112
|
| 內容試閱:
|
孤独
亲爱的卡罗尔:
正如你的孩子们所记得的那样,我一直感到很孤独。如今你父亲已经不能给我任何忠告、建议和限制,但我还是不得不做这些决定,不管人们对此如何判断,是褒奖还是谴责,是理解还是同情。我曾反复说过,如果在会议上能得到他的批评或勉励反而更好。
我现在说的这段逸事,只跟一个时间和一个地点有关,特别是当我非常怀念丈夫的陪伴和保护时。去年夏天巴德准备婚事时,我也参与了婚礼筹备计划,突然地,我很想逃离出教堂。
我一点也不害怕健康上的任何意外,产生这种想法可能是因为我问过诺伯里医生,我是否可以离开。内心里,我觉得在经历四十二年之后,已经到了忍耐一个人孤独做事的极限。我试图找出我的动机,几乎可以认定,被自我压制的、因为八个孩子成长和发展而产生的混乱和紧急状态,在四十二年后,似乎猛增而爆发了。
在婚姻中,无论是健康或疾病,富有或贫困,一个女人坚定而快乐地接受了她的丈夫。尽管考虑建立一个家庭的时候,我们总是忘记考虑所有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特别是在为了满足每个儿童多样化、个性化需要的时候。而且,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总是断言,丈夫和妻子将共同行动,却忘了若是剩下一个人独自行走时的凄凉。我内心承认,去年8月,在那种社交场合下,我的反抗被不断增长的孤独感所消融。今晚,不是借口,只是对我这种反抗的解释——当我被自己弄得烦恼不堪时,我就一直不停地写。
你父亲去世的几个小时后,医院的木匠就做好了棺材;裁缝又给它里里外外修整了一番;锡匠给棺材上配上了合适的锡金徽章,安上了金属把手。在美国,所有的筹备工作都会交给专业的服务机构,而在此,均由医院的成员们怀着爱与悲伤操办。许多朋友去山坡上,采集了野丁香和长茎紫罗兰,这些是仅能找到的葬礼用花。在这一天即将结束的时候,家里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有一百多个外国人和许多中国朋友参加。星条旗覆盖在灵柩上,由深爱着他的同仁们的肩膀担着棺材,去往三英里半之外的外国人墓地。
几周之后,芜湖众多的市民决定举办一个纯粹的本土追悼仪式。芜湖是一个内陆城市,有十二万人。商人、士绅、官员、行会、学校和教堂都参加了这一仪式,基督教、佛教、道教、儒教和穆斯林的教徒也都来参加了,因为对埃杰顿来说,他们都是一样的。
人们腾出了当地的剧院,那是镇上最大的礼堂。所有中方的各家组织都表达了他们对埃杰顿的敬意之情。追悼会持续了几个小时,大厅内悬挂了许多白色的挽联,上面写着对逝者的赞美之词。白色,是中国人表示悼念的颜色。追悼会音乐是由男子学校一个新成立的铜管乐队所演奏的,乐队使用了弦乐器、风琴和打击乐器,这些乐器对那时候的芜湖来说显得极为新鲜。乐队的指挥认真地指导孩子们演奏合适的音乐。他们不时地演奏出美丽而高雅的音乐,他们的新队服也令公众极为羡慕。
在中国传统观念里,男人和女人不能在公共场所同坐一席。礼堂长长的走廊留给了女人们,而男人们占据了整个大厅。
我发现要参与它很不容易。首先是因为它离我们的小山有几英里距离,而且除了骑马之外,步行的速度每小时只有三英里。中国人表示匆忙时常用“马上去”,人们常用这个词语。
由于相隔较远,参加追悼会就意味着要离开我的孩子们几个小时,三个月大的赫伯特正需要我。但是我必须认识到,我和到场的人们一样,是为了表达对埃杰顿毕生工作的敬意,我有义务这样做。我此刻应该打住话题,要提及我们教会的一位成员,我称呼他为X先生。
你父亲临终前,起病于星期日。之前的周五晚上,埃杰顿说:“有一些教会的事情,我必须要和X先生交谈。”因此,晚餐之后,他去了楼下。当回来时,天已经很晚了,他看上去很疲惫。在休息之前,我们只是简单地谈了几句话。埃杰顿说道:“这样令我感到很伤心,但我确信他的道德品行正在渐行渐远,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相信他了。”
这就是那天晚上他所说的一切。周六的工作耗去了他的时间,甚至是他的精力。周日,他患上了严重的斑疹伤寒。从那以后八天,到他离开人世,我们之间仅有过只言片语。但由于X先生是芜湖教会的领导,埃杰顿去世之后,在很多事情上,我不得不听从他的安排。当我意识到我必须在这种场合上出现时,我知道我将不得不接受X先生对我陪护的安排。
一两年之前,埃杰顿就拒绝乘坐轿子出行了,除非是出席官方正式场合。我们仍保留那时轿夫们使用的合身的棉服。那时,如果需要,看门老头儿会站在门口,同轿夫们打招呼,而他们也乐于回应,因为那意味着可以挣着现金。通常情况下,埃杰顿是骑着马或坐人力黄包车出去办事。
这天,X先生心不在焉地雇了一辆消毒不干净的轿子,轿夫相貌平凡,没有穿上平日里的棉服。我有点失望但没有吱声。也是因为相信X先生,所以我没有带仆人跟随,我通常会带的。
我们来到剧院,然后我去了阳台上留给我的地方。如果说我曾经渴望过礼貌而周到的陪同的话,就是那天了。
几个小时的紧张情绪让人难以承受。由于这些充满感激之情的人们是在悼念他们爱戴的人,因此那天我听到最多的词是“一个本地人”,意思是指那些落叶归根的人。他们没有忘记埃杰顿是出生在中国,所以人们把他视为当地人,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很长时间之后,追悼会结束。听着那些颂词,我深深地被打动了,我感觉自己已经很难控制情绪了。
我曾经被迫控制情绪,就在埃杰顿患病的第三天,偶然发生了一件事情。当时我正准备给王娜清理废纸篓以整理房间,在那里,护士安慰我说,埃杰顿的治疗有时还是有效的。她撕碎了一些手稿纸屑,把它扔在了纸篓里。我看到了上面的一句话:“斑疹伤寒,死亡的同义词。”
我愣在那里,医生们认为他已经治疗无望了吗?毕比医生告诉我,可能只有三周的生存期了。他鼓励我保持镇定。“死亡的同义词”使我感到深深的绝望。没有埃杰顿,我将如何面对生活?我又该如何面对那些已经长大了的孤儿们的需要?我的三个没有了父亲的孩子又该如何成长?我感到万分恐惧。忽然,我意识到我不能接受那样的现实。我必须鼓起勇气面对我的丈夫,在他人生的最后关头尽力。没有人知道希望与失望的交叉点在何处,我不会屈服的。仅此一次,如果我成功,将意味着两次生命:埃杰顿和赫伯特,因为赫伯特还依靠我生活。我站在那里,祈祷上帝给予我勇气。
我不得不继续倒完纸篓,时至今日,我没有告诉任何人,那个恐慌的时刻。而今在剧院里,我有着充分的毅力,并使我看上去很平静。追悼会结束后,人们向门口走去,我缓慢地移动着,在下楼时寻找着X先生,但没有找到。离地面几步时,我停住了,因为周围有数百人正涌向门外。这之后,我近乎惊慌失措,我该怎么办呢?我知道那些轿夫们想找个暗点儿的角落赌上一把,他们已等待多时了;我不能沿着街道走过去,然后招呼轿夫们回来;路上有很多陌生的面孔,但看上去一个都不认识;我们外宾团以为X先生会照顾我,都急匆匆赶回去继续他们的工作了。悲伤和孤独使我感到绝望。忽然从侧面大厅跑出一群人,我停下来,估计是有什么达官贵人来了吧!然后,我看到了李先生,大政治家李鸿章的儿子,也是李地主的兄弟。
很快,他明白了我的处境并嘱咐随从们挡住人群。他们中的一些人喊我的轿夫,抬来了我的坐轿。中国的礼节使他不能同我打招呼,我亦如此。他给坐轿让了路,并且让轿夫们斜着轿子两头的杆子,直到我坐稳,然后给轿夫们指了下方向。一丝慰藉和感激涌上心头,因为我感到了一种安全感。在剧院里经受数小时的煎熬之后重获轻松,我对此充满感激。现在,我只想安静地回到家里和孩子们待在一起。
在离开围墙般的城市之前,我们要穿过一英里多的狭小而拥挤的小街。轿椅前后长长的竹竿扛在轿夫肩上,经常会威胁到行人。随着我们前行,轿夫们吆喝着人们让开道路,行人们则紧贴着城墙或挤入路边的门廊。一个多小时之后,我就可以和孩子们待在家里了,这使我感到轻松一些。在这种令人尴尬的时候,除了羞怯和粗心之外,我不知道这一天中最难熬的时刻即将来临。过了一会儿,轿夫们停止前行,前面走着一支乐队,对那些男孩们来说,他们似乎正在为演奏成功而游行庆祝。在完成这一天艰巨的任务之后,他们穿着鲜艳的新队服正快乐地前进。我似乎已经忘记他们演奏的音乐很久了。
当听到这种热烈又令人激动的喧嚣时,所有的家庭都走出门廊观看。孩子们奏着刺耳的曲子,乐队弄得这里鸡犬不宁。随着乐队趾高气扬地前行,人们蜂拥而至,都赶来听这些新奇的音乐。我不便道出自己的反感,轿夫们跟着喧嚣的队伍前进着,直到我们成为其中的一员。轿夫们随音乐晃动着身子,而在那有弹性的竹竿上,我的轿椅也跟着有韵律地摇摆。我无法摆脱这种难堪、尴尬的窘境。这是我一生中,走过最可怕和最长的两英里路。随着我们前进,轿子上的竹竿就像乐队指挥手中的指挥棒一样,而这些人则是平生第一次听见这种奔放的铜管乐队演奏。
我们离开了城区,仍然有一英里的路才能转到男子学校。每个村子都有人欢呼雀跃跑来观看,还有不停吠叫的狗。在我的心底,厌恶他们所有人,如果他们认识轿子上的人的话。
人们对“规矩”(已接受的习惯)和对控制这个守旧国家习俗的反应,为何如此不同?如此这般失礼,让前行显得极不协调。对于一个寡妇来讲,当她说出失去了她生命中的伴侣时,她的行为究竟有何不妥?
“哎呀”,我听见有人叫喊道,“这些外国佬的行为多么可怕!她没有坐白色的丧轿,在这些震耳欲聋的噪声里,同大家一起游行。这些外地人破坏了这里所有的礼节。”
为避免触动他们所认为正确的这些事情,二十年来,埃杰顿都是小心翼翼地生活着。然而现在却发生了,这真叫人感到痛苦。最终,这些所有经历都结束了,刚开始,我看上去无法承受,而它就像噩梦一样在那天结束了。
倘若我厌倦孤独的人世,我是否该遭到谴责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