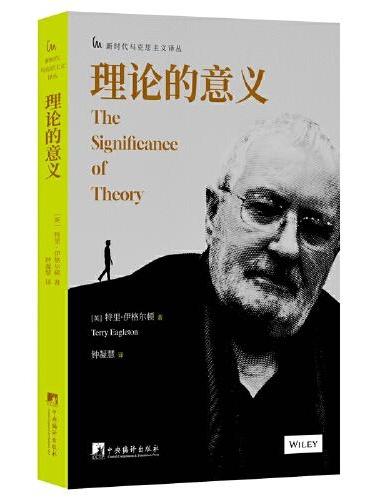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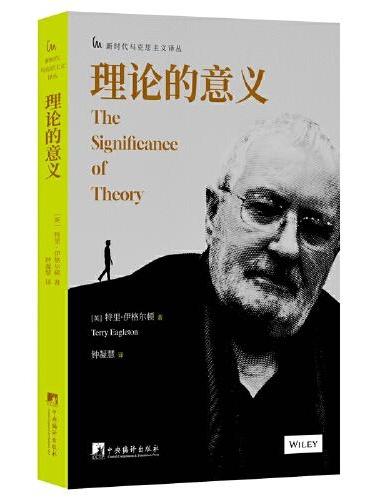
《
理论的意义
》
售價:HK$
74.8

《
悬壶杂记:医林旧事
》
售價:HK$
52.8

《
谁之罪?(汉译世界文学5)
》
售價:HK$
52.8

《
民国词社沤社研究
》
售價:HK$
140.8

《
帕纳索传来的消息(文艺复兴译丛)
》
售價:HK$
108.9

《
DK威士忌大百科
》
售價:HK$
294.8

《
小白学编织
》
售價:HK$
65.8

《
Android游戏开发从入门到精通 第2版 王玉芹
》
售價:HK$
108.9
|
| 內容簡介: |
|
沙叶新这本《阅世趣言》,绝不同于《警世危言》、《醒世诤言》,不那么严肃,不那么正经。没有官方话,没有大道理。有的只是趣人趣事,有的都是趣言趣语,还有不少幽默与讽刺,但都是善意的。读者不必认真领会,无须加强学习。宜置于枕边随读,伴你在笑意中入睡;亦不妨入厕时翻阅,使趣味驱散气味。读者可一试!
|
| 關於作者: |
|
沙叶新,1939年生,江苏南京人,回族,国家一级编剧。1957年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1963年7月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创作研究班,同年进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任编剧。1985年至1993年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1956年开始发表诗歌和小说。主要作品有多幕话剧《假如我是真的》、《陈毅市长》、《马克思“秘史”》、《寻找男子汉》、《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太阳雪人》、《东京的月亮》、《尊严》、《江青和她的丈夫们》、《幸遇先生蔡》、《邓丽君》、《自由女人》、《良心胡耀邦》等,独幕喜剧《一分钱》、《约会》、《〈风波亭〉的风波》、《论烟草之有用》等。另著有电影电视剧本、儿童剧本、短篇小说、政论、杂文及散文百余万字。近作有长篇小说《张大千》出版。
|
| 目錄:
|
随笔
沙叶新,何许人?
我的“饲养员”
沙叶新买菜记
父女情深
女大不中留
我和儿子下棋
心肝与宝贝
沙叶新翻脸不认人
始终不是我
我要严肃了
我又不严肃了
秀才遇见偷
戴了“帽子”之后
我穿时髦西装
我演《围城》曹元朗
我和英国女王握过手
让我们相吻吧
出售“鼻子”
抽象发言
上帝也有隐私
夜闯KTV
诸子语“怪力乱神”
深圳历险记
性笑话
喜欢你,才和你开玩笑
艺术家的笑话
我以笑声悼阿朱
我喜欢高晓声
我不敢写的文章
几位“腕儿”
活得有趣
我当嘉宾,鼓噪吹竽
从两则笑话看德国
“工程”现象
签名题词的喜剧
闲话秘书
请别误读,谢谢了!
假如都是徐虎
编辑们,别上课了!
观众们,别上当!
管好这张嘴
回归之后
点菜的洋相
有车阶级
小说
假如那天没下雨……
捡到的和失去的
饱学之士
告状
有奖阅读小说——《他和她》
为推销《马克吐温幽默演说集》所作的严肃的演说
憋不住了
水晶人
春宵一刻值千金
喜剧
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
假如我是真的
微博趣言
|
| 內容試閱:
|
沙叶新,何许人?
哦,你就是那个所谓的剧作家、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还莫名其妙地列入《世界名人录》的名人?报刊上常见到你的文章,舞台上常演出你的剧作,常有人请你开会,请你讲话,请你签名,请你题词,请你赴宴,请你合影,还请你出国。近几年,你真是春风得意,风头出足。有很多记者采访你,有不少文章吹捧你,说你从小是神童,长大是天才,写作如何之勤,知识如何之博,如今在政治上又是多么的爱党爱国,在艺术上又是多么的出类拔萃,还说你夫妻恩爱,家庭幸福,性格幽默,坚强正直,甚至连面色红润也提到了,只差没说你“质量可靠,负责三包”了。
而阁下你自己是怎么想的呢?你表面谦虚,心中暗喜,别人以为你对这些溢美之词不屑一顾,可有谁知道你对这类捧场文章还是感到惬意的。你呀,真不应该那么心安理得,其实你早已不是你自己了,你已经失去了一个真实的你。直到最近,你似乎才有所觉悟,你在答复一家报纸的提问时,不得不承认:“所谓名人都是社会形象,是社会根据各种需要在当今中国特别是根据某种政治需要人为地塑造出来的。只要你出一点名,你便不再完全是自己了。知名度越高,就越不是自己。”你还说过,有关你的报道,百分之五十是艺术夸张,百分之二十是凭空编造,只有百分之三十才是真实有据的,而这百分之三十也是只说好,不说坏。
你今年五十足岁,“五十而知天命”,但更应该知道自己,更应该有自知之明。那就让一个深明底细的我来评说一个被艺术夸张了的你,让一个不为人知的沙叶新来修正一下“社会形象”的沙叶新,不为尊者讳,不为亲者讳,更不为自己讳,如何?试试吧!
好,先说阁下的小时候,你不是什么神童,是顽童。顽皮,按你们南京方言来说,叫“厌”,把“顽皮得要死”,说成是“厌得伤心”。你可真是厌得伤心了!你小时候最喜欢装济公,头上戴着用绿荷叶卷成的圆锥形的帽子,耳朵上挂着红辣椒做成的耳坠,手拿破芭蕉扇,口唱“唵嘛呢叭咪吽”和尚念的经文。那时尚无“鞋儿破,帽儿破”的流行曲,否则你也一定会引吭高歌此曲,大显身手的。下大雨时,房檐水流如注,你和三四顽童竟然立于檐下,排成横列,伸长头颈,以颈就水,相互比赛,看谁坚持最久。而你在这类较量中,哪怕浑身湿透,冷得发抖,也要坚持到最后,击败所有对手。你就有那么一股呆劲,所以大家叫你呆子。你的乳名原来叫“六十子”,后来人们都叫你“六呆子”。
上学之后,你也并非天才。小学毕业时,班主任江浩老师叫你上黑板写你自己的名字。那时尚未实行简化字,你竟然将繁写的“葉”写错了,写成了“”——介乎“葉”和“業”之间的一个谁也不认识的错字。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你一直就是这么错下去的,整整错了六年,学习成绩可想而知!
到了初中,你也不是好学生。下午你常旷课,溜到新街口摊贩市场类似北京的天桥去听相声,看测字,旁观大人下棋,逛逛廉价书摊,接受典型的市井文化的熏陶。学习成绩呢?你至今还保留一本初中三年级的记分册,别不好意思,打开让大家看看,增加透明度嘛。哇!语文53分,数学43分,政治50分……你是怎么学的,这么多门功课不及格?!1953年你初中肄业,患了流行性乙型脑膜炎,没有考高中。病好后,重读初三,留级半年。
你小时候比较突出的倒是京剧。那时你爸爸开饭店,店名启乐园,在南京算是一家小有名气的清真饭店。离店门前不远,是著名的中央大舞台,全国一些著名的京剧演员常来此演出。你家则做这些演员的包饭生意,一些回族演员也常来店里用餐,这样你们全家看戏就方便多了。你当时常爬在台口,曾看过盖叫天的儿子张翼鹏的武生戏,看过现已在台湾退休的顾正秋的旦角戏。久而久之,你也学着唱了。后来你便拜你爸爸的老友梁大先生的儿子梁正平为师。梁老师是票友,工须生,他教你的第一出开蒙戏是《击鼓骂曹》,教你唱的第一个唱段是祢衡的“西皮快三眼”:“平生志气运未通,似蛟龙困在浅水中,有朝一日春雷动,得会风云上九重。”以后师傅说你嗓子“左”,太沙哑,便让你学麒派,于是你又学了《萧何月下追韩信》。你对麒派唱腔喜欢得如痴如狂,尽量想模仿得惟妙惟肖,那一段“二黄顶板”你唱得一波三折,声情并茂,倒也常得到大人们的称赞。记得你就读火瓦巷小学时,校长是戏迷,戏瘾一发作,便将你从课堂叫到他办公室,让你唱上一段。你摇头摆尾地唱,校长先生则闭着眼睛,手打节拍,像在品味一个名角的演唱。后来你这个连自己名字都写错的学生之所以能毕业,八成是校长喜欢听你唱京剧的缘故。1946年,蒋介石六十大寿,南京票友在新造的“介寿堂”举行祝寿演出。演出剧目之一是《汾河湾》,你演薛丁山,演出之前扮演薛仁贵和柳迎春的两位票友因排名先后而发生争执,以致不欢而散,戏未演成。幸亏如此,否则“文化大革命”中你便多了一条罪状。此事你在历次运动中交代过吗?显然没有。
1948年前后,南京一些票友成立“南京业余京剧研究社”。此研究社当时并未向国民党政府注册登记,也不知算不算非法组织。该社社址便设在你家饭店的二楼,你爸爸不收房租,而且免费供应茶水点心。票友们活动时,你也吊吊嗓子。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中国戏曲学校京剧科在南京招生,曾有票友建议你去报考,可你父母舍不得,“父母在,不远游”,因而作罢。否则你和浩亮同学,将走上另一条生活道路。也许在“文化大革命”中加入样板团,青云直上;也许因“破坏京剧革命”而惨遭迫害。世事难以逆料,人生有许多难解的谜,你今日之所以成为今日的你,其实是有许多偶然的甚至神秘的因素在起作用。
比如,要不是1953年夏天那只带病毒的蚊子叮了你一口,你就不会得流行性乙型脑膜炎,就不会耽误考高中,就不会在另一个班级留级读书,就不会遇到另一些你本来不可能遇到的老师和同学,就不会有你如今这样的生活历程……
高中,你仍然是在南京第五中学读的。你之所以喜爱上文学艺术并萌发写作的欲望,完全是受了语文教师武酉山先生和同学王立信的影响。武老师循循善诱,是他首先在你的心灵中注入了文学细胞。王同学是你们高中生里第一个发表作品的人。彼亦人也,尔亦人也,受其影响,你也因此拿起笔写起了小说,而且居然也发表了。你当初当然沾沾自喜,如今你才悔其少作,让你脸红,那确实是一篇极为幼稚的处女作。不过,若不是如此,若不是在你生活中出现了武老师和王同学这两个人,你以后也不会走向文学之路的。
在高中,你仍然不是循规蹈矩的好学生,你只是在读高一时还较用功,物理97分,立体几何100分。到了高二你就原形毕露,一头埋进古典诗词里,上代数看小说,上俄语背宋词,只有上语文课还算老老实实。作业,总是抄人家的;考试,倒不敢作弊,只是在考前突击一个月,将书本从头至尾看一遍,将习题从头至尾做一遍,考试时倒也能混个60分,这大概是你的小聪明。
高中毕业,考大学,可以填报十二个入学志愿。你不自量力,报考的都是名牌大学,北大、清华、复旦……结果呢?只录取了你填报的最后一个志愿——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其实这对你来说已经非常不错了。后来才知道,你是回族人,可以加分,在同等分数线上可以优先录取,否则你也早就名落孙山。你是沾了回族的光,是真主的保佑。
在大学,人大了一些,你总算懂得了用功,特别是对中国古典文学最用功。大学期间,你也发表小说,不多,只有两篇,在中文系里倒也引起轰动。但最轰动的还是以后在上海戏剧学院读研究生时所写的论文《审美的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和姚文元商榷》。当时姚文元是“大左派”,你跟他商榷,批评他,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文化大革命”中,姚文元更是青云直上,你的此项罪名也当然逐步升级,说你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那时真叫你冤难伸,口难辩。“四人帮”倒台之后,同样一件事,评价完全不一样了,你顿时成了早在
“文化大革命”前就反对“四人帮”的英雄。好在你倒没有头脑发热,只承认受过“四人帮”的迫害,没将自己打扮成反“四人帮”的英雄。还有一点,你心中一直有愧,也从未与人道及,那就是你那篇“和姚文元商榷”的文章发表在《文汇报》上没多久,你就怕了,认为自己错了。你写过信给《文汇报》的总编辑,认为自己在学术研究上缺乏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表示今后定要好好学习马列。由此可知,当时你其实并不认为真理在自己手里,也并未真正反过姚文元。
人们承认错误往往有三种情况:一是本来是对的,可后来却真心地认为错了。这种情况你有过,这已如前述。二是不知道对和错,脑子给搞乱了,但由于某个至高无上的权威说你错了,你也就认错了。这种情况你也有过,
如“文化大革命”初期,你反对造反,可毛主席说造反有理,你被搞糊涂了,只好承认自己无理了。三是明明自己是对的,可屈服于一时的政治压力,只得违心地认错,这是最不应该和最不可原谅的,可遗憾的是这种情况你也有过。“文化大革命”中,你写过一出戏,叫《边疆新苗》,文化部部长于会泳点你的名,上海市委文教书记徐景贤点你的名,说你违反“三突出”,违背“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还说“沙叶新审美的鼻子又伸向资产阶级那里去了”,于是上海的文化系统开批判大会,批判你。你心中不服,越想越没错,写了申辩稿,打算在批判你的大会上宣读。这当然是种顽抗态度,你是准备顽抗到底的。可后来你想到:第一,你斗不过他们。他们两位是中央委员,炙手可热,你是无名编剧,这样做无异于鸡蛋碰石头。第二,你也无法斗。因为在大会申辩之前,申辩稿必须在小组会上通过,当然这是绝对通不过的。第三,你怕株连,当时你妻子正在申请入党,你担心你的顽抗会影响对她入党的批准。第四,你最怕的则是他们会从此夺走你手中的笔,不再让你从事你最醉心的事业:戏剧创作。所以你低头了,屈服了,撕碎了已写就大半的申辩稿,重新写了一份检讨书。你在批判你的大会上自己谴责自己,自己批判自己。虽然你内心极为痛苦,可你不得不如此。这样你才能过关,才能免于更大的迫害。
“四人帮”倒台后,为此事又有不少人叫你去做报告,叫你讲讲你是如何在这件事上反对“四人帮”的。你其实心中有愧,你非常恨自己在当时没有顶住高压,说了假话,作了假检讨,所以你一次报告也未去做。你在这点上还算比较老实。大概也正因为如此,你从此以后再也不想说假话了,再也不愿做违心的事了;哪怕有再大的压力,再重的迫害,你也不打算屈服了。但愿你能够真的如此。
1989年6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