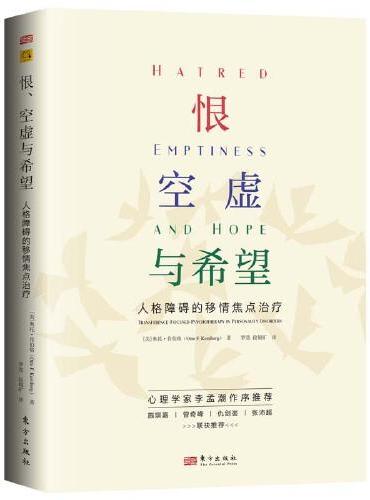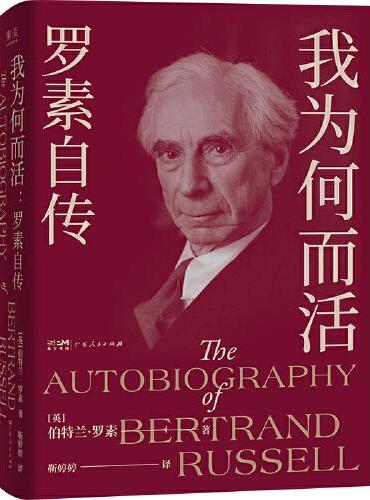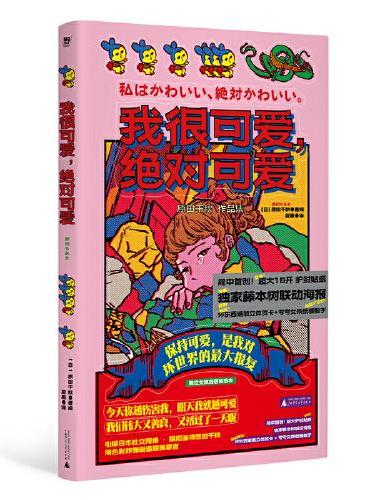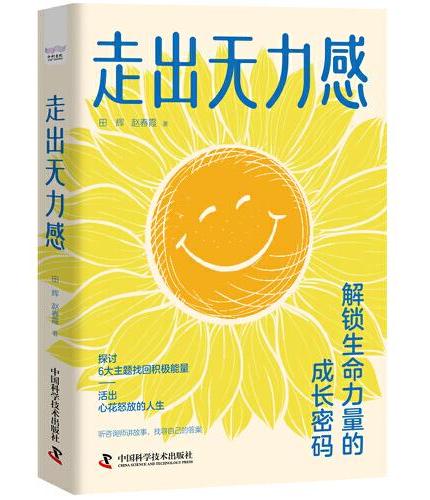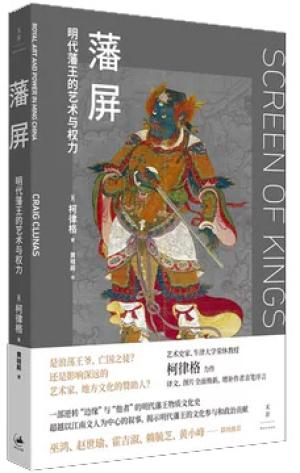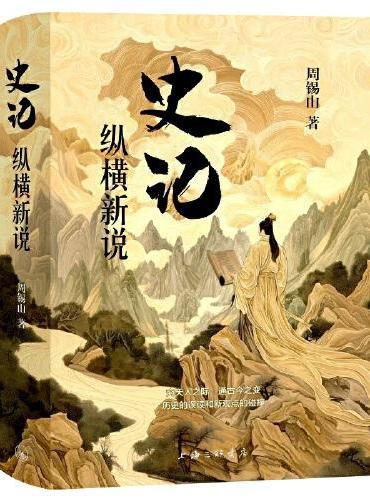新書推薦: 《
背影渐远犹低徊:清北民国大先生
》 售價:HK$
96.8
《
恨、空虚与希望:人格障碍的移情焦点治疗
》 售價:HK$
87.8
《
我为何而活:罗素自传
》 售價:HK$
85.8
《
我很可爱,绝对可爱
》 售價:HK$
107.8
《
溺爱之罪
》 售價:HK$
54.9
《
走出无力感 : 解锁生命力量的成长密码(跟随心理咨询师找回积极能量!)
》 售價:HK$
65.8
《
藩屏:明代藩王的艺术与权力(柯律格代表作,一部逆转“边缘”与“他者”的明代藩王物质文化史,填补研究空白)
》 售價:HK$
118.8
《
《史记》纵横新说
》 售價:HK$
65.8
編輯推薦:
黎戈有雅致且考究的趣味,因此她够看到事物最细微的部分,她的文字视角虽低,却讥诮别致,灵气逼人,深受读者喜爱与追捧,堪称新晋作家中最具才气与灵气的女子。翻开这本本精美有趣的小书,沉静动人的心灵私语、冲淡清和的生活体验、深情凌厉的阅读心得……一切都让你难以罢手。
內容簡介:
《各自爱》是作者的随笔精选集,收入"侘寂贴""白色俄罗斯""四季歌"三个小辑共六十六篇作品,其中"侘寂贴"收录了一些个人静心素文;"白色俄罗斯"谈了谈作者为什么深爱苏俄文学;"四季歌"写了作者平淡的日常生活,加了一些民俗饰纹,不为怀古,只为感念旧时那种与季候相依的温暖感觉。
關於作者:
黎戈,女,70后,原名许天乐,南京人。嗜好阅读,勤于动笔,作品刊于《人民文学》《今天》《鲤》等刊物,著有《一切因你而值得》(中国工人出版社),《私语书》(文化艺术出版社),《因自由而美丽》(新星出版社),《静默有时,倾诉有时》(台湾远流出版社)。
目錄
侘寂帖
內容試閱
茫然尘世的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