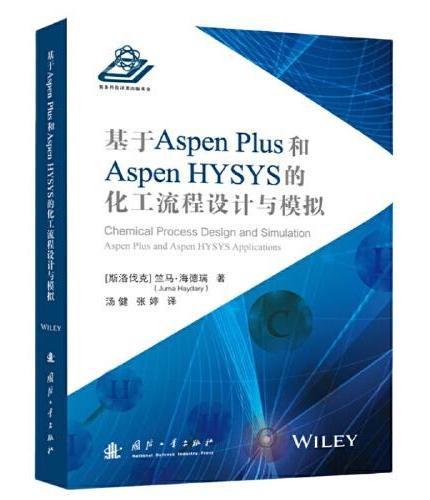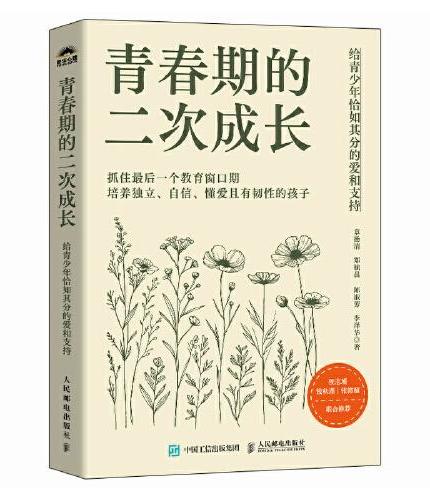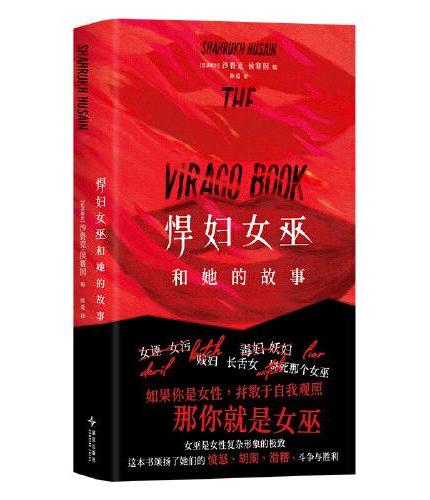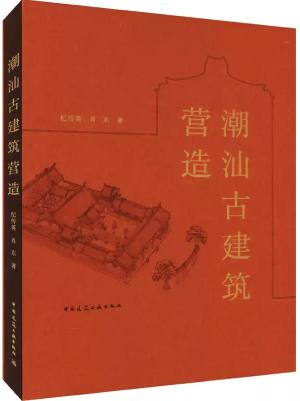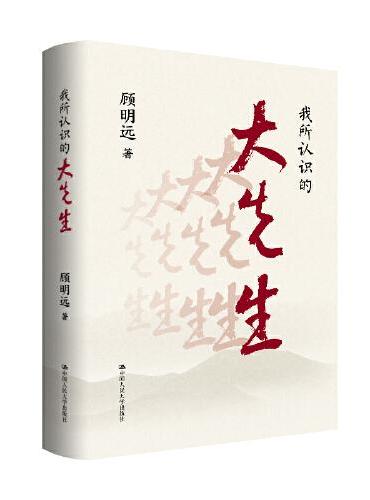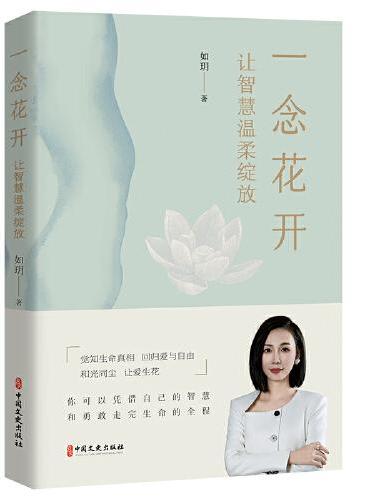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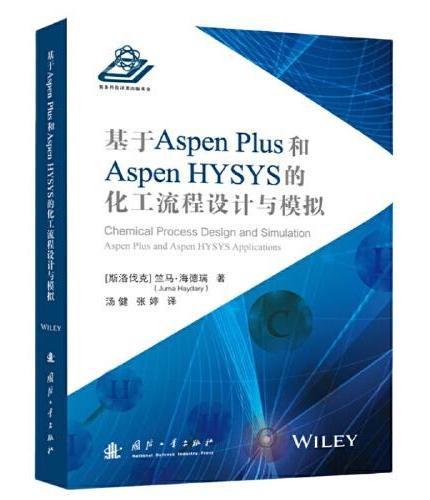
《
基于Aspen Plus 和 Aspen HYSYS的化工流程设计与模拟
》
售價:HK$
21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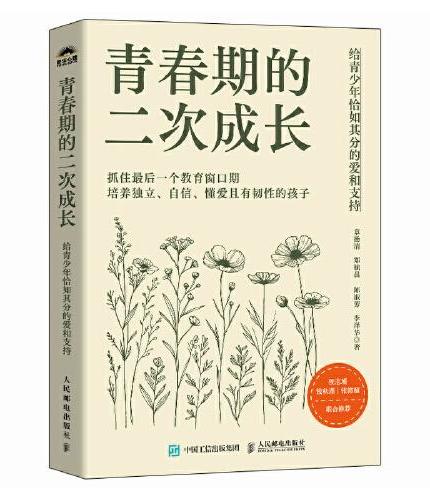
《
青春期的二次成长:给青少年恰如其分的爱和支持
》
售價:HK$
65.8

《
盐与唐帝国
》
售價:HK$
129.8

《
让花成花,让树成树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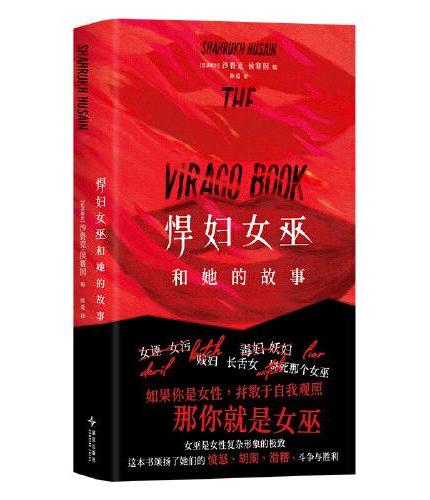
《
悍妇女巫和她的故事(第一本以女巫为主角的故事集!)
》
售價:HK$
7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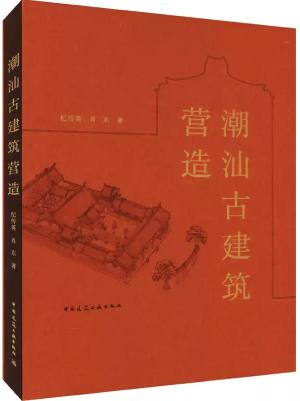
《
潮汕古建筑营造
》
售價:HK$
26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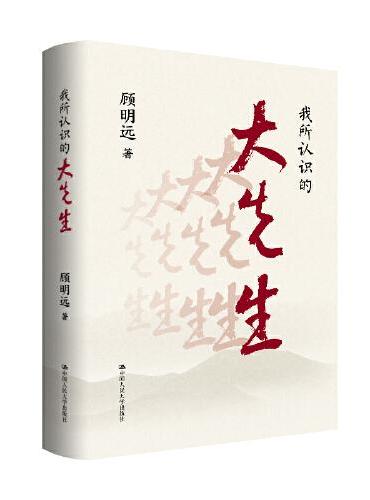
《
我所认识的大先生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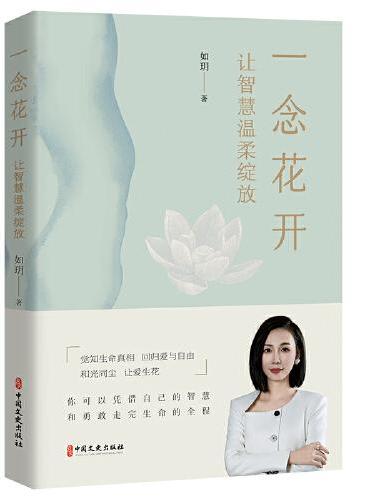
《
一念花开:让智慧温柔绽放
》
售價:HK$
57.2
|
| 內容簡介: |
|
《接头》是著名作家龙一最新长篇小说《潜伏》之后所写,龙一是中国本土最有特色的推理小说作家,通吃“地下斗争”和“职场规则”的高手。《接头》中讲述的潜伏任务别开生面,独树一帜,给人新的惊喜,又让人觉得险象环生。
|
| 關於作者: |
|
龙一, 著名当代作家,代表作《潜伏》。1961年出生于天津,祖籍河北省盐山县。生于饥荒之年,长于物质匮乏时期,故而好吃;长期研究中国古代生活史,慕古人之闲雅,于是好玩。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出身,写小说引读者开心为业。文学创作一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迷人草》《借枪》《深谋》《暗火》《代号》《暗探》《接头》,小说集《潜伏》《刺客》《藤花香》和小说专著《小说技术》等。小说《潜伏》和《借枪》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播出。现为天津市作家协会文学院作家,读书写作莳草玩物之余,尚有调和鼎鼐之好。
|
| 內容試閱:
|
1、上级领导对我说:中共党组织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群造反者,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有着正义的信念和真正的理想,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需要纯真的道德支持我们实现这个理想。
2、这件事开始于1939年冬天,我带着新代号和新任务回到日军包围下的天津英租界,但我最迫切的愿望却是想借此机会与谭美结婚。
进入租界之前,中共党组织对我提出了几点要求,那就是“受气不说,吃苦不叫,功则归人,过则归己”。我当时认为,这必定是因为我在香港做情报工作期间发的牢骚太多,提的要求太多,给领导添了太多的麻烦,让他们实在忍无可忍了。但《孙子兵法》说得好,“赏莫厚于间”,而我一向认为,孙子所说的这个“赏”绝不仅仅是金钱,其中也必定包括给间谍们发牢骚、说怪话、耍花招、提稀奇古怪要求的权力,否则,压在我们这些人心底的那团乱麻般难以承受的苦处和扭曲怎能释放得出来?
我在英租界威灵顿道租了间膳宿公寓安顿下来之后,便立刻着手联络谭美。我很快就28岁了,老大不小的,对情报员时常要经历的那套“假夫妻”的游戏已经深恶痛绝,早就该正经八百地安一份家了。然而,等谭美挺着远洋邮轮般硕大的肚子出现在接头的西餐馆时,我的心下立刻全凉了。
谭美却好像没把她的肚子当回事,一见面便开心地拍手叫道,这两年你跑哪去啦,害我整天替你担心,是不是娶妻生子过小日子去了,太太有我漂亮吗,孩子多大啦,他们跟你一起回来了吗?等哪天见见,我请他们吃饭,顺便认你的小孩作干儿子。她依旧是口无遮拦的脾气,一张嘴便像河堤决口,漂亮的小脸上五官乱飞。
我曾经热爱谭美身上的一切,只是,她的这个即将足月的肚子却像座大山一般把我们两个阻隔开来。我自认为是个风度优雅的绅士,特别是在女士面前,所以,像怀孕生子这类事,谭美自己不讲,我是绝对不能问的。为此我感觉很懊丧,只简单地讲了讲自己的近况,告诉她我还没结婚,但没提原本打算回来与她结婚的事;然后又问了问她领导的那个文明剧团的情况,约定了下次接头的方法,便故作依依不舍的样子送她离开。然而,等餐厅的门在谭美身后刚刚关上,我便在送餐小姐的惊叫声中,砸碎了餐桌上所有能砸碎的东西。
两年前分别时,我虽然与谭美并没有明确的婚姻之约,但我一直坚定地相信,只要我肯开口,她理应会兴高采烈地嫁给我。况且,这一次我费尽心智,好不容易“谢绝”了领导送我去延安休养的好意,拖着疲惫的身心坚持回天津工作,主要就是为了谭美。如今,心爱的女子已经嫁作他人妇,我即使是心中滴血也只能独自忍受——这就是做地下工作不得不承受的损失。于是我强迫自己平静下来,暗道,关大宁啊关大宁,别忘了你是一个有理想的革命者,要大度,大方,大气,拿得起放得下。只是,我依然无法摆脱锥心刺骨的心痛和猛然间像蝗虫一般拥入脑子里的各种狂乱的念头。滚开,我对这些“蝗虫”大叫一声,把街上的行人吓得纷纷闪避,但它们依然在我的脑子里乱撞不已。
与谭美建立联系之后,我又忙于联络另外一个情报员黄若愚,希望这个新挑战能冲淡我心中不幸的感觉。从组织上给我的材料来看,黄若愚这个情报员就像一颗时钟出了故障的定时炸弹,既危险又无用。这是因为,当年招募他的同志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无法向他表明自己中共的身份,便只好告诉他这是在替美利坚合众国工作,然而,长时间接触下来,黄若愚对此已经产生怀疑。另外,黄若愚只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天津站的档案资料员,因为“中统局”负责的是党务和思想工作,他那里并没有多少中共急需的军事情报,所以,上级党组织对他并不重视。
为此我不禁在心中暗叹,这次交给我的情报小组与我在香港掌握的巨大的情报网根本就没法相比,这只是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从这一点上看,便说明上级领导确实对我很担心,担心我在香港工作时积累下来的“疾病”随时都有可能让我垮掉,理应休息,然而,他们又不方便拒绝我回家娶妻生子的要求,所以才把我放进这个儿童游戏般的情报小组中。其实,我自己也很清楚,尽管我百般掩饰,但精明绝顶的上级领导绝不是等闲之辈,他们担心得一点也没错,这是因为,连我自己也担心我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因为一点小事而突然发病。只是,如果脱离了地下工作紧张的环境,精神一下子放松下来,我又怕自己会无所适从,变得百无一用。所以,还是边工作边治疗吧,我对自己说。
依照黄若愚的上一任联络员留下的方法,我先是用粉笔在通常的联络地点留下记号,但根本就没有得到回应;我又在英文版的《京津泰晤士报》上登了三天包含有暗语的求购旧乐器的启示,仍然没有回音。
上级领导此前交代得清清楚楚,说黄若愚每天都去中统局天津站迁入英租界后的掩护机关,也就是位于达文波道的新世界书店上班,没有离开本地。依照我的经验分析,情报员明明行动自由,却又不肯回应约定接头的信号,这便意味着他多半是打算脱钩不干了。但我可不能让黄若愚这么做,我手里现在总共只有两个情报员,谭美还挺着大肚子,若再放弃黄若愚,我便毫无理由继续工作,只能听从领导的安排前去休养。为此我耐着性子等了好几天,并且又在报纸上登了三天的“启示”,然后将这六份报纸打了一个包,径直邮寄到黄若愚租住的公寓。我相信他必定会吓一大跳,果然,黄若愚很快便在报纸上登出“回话”,约定见面。
他一开口便是带着浓重唐山口音和少许美国南方口音的英语,语速极快,怒冲冲地在发脾气: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你们不要再找我了;我不管你是替美国人还是英国人或者是俄国人干事,就算你是替共产党或汪精卫干事,也都跟我再没关系了,告诉你,今天我临出门时还左思右想,琢磨着要不要把你交给我们站长。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