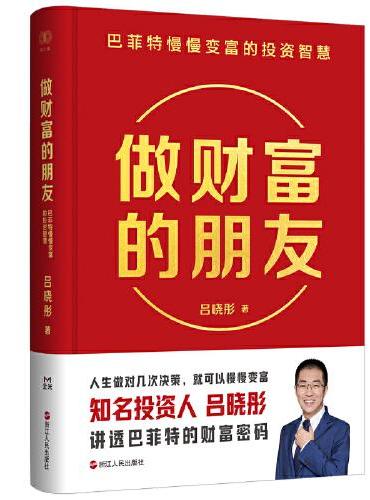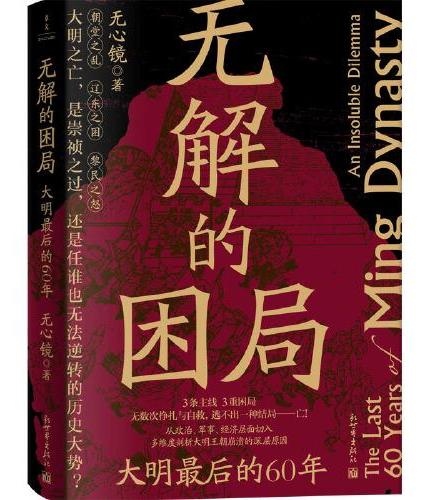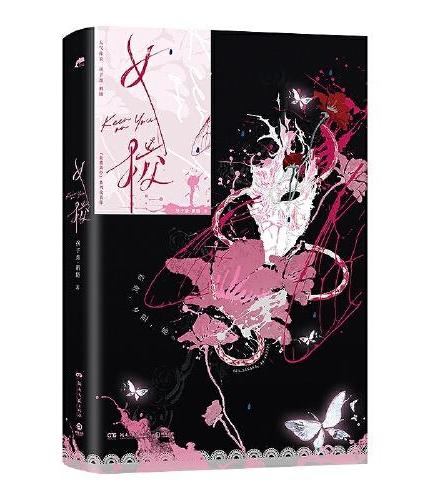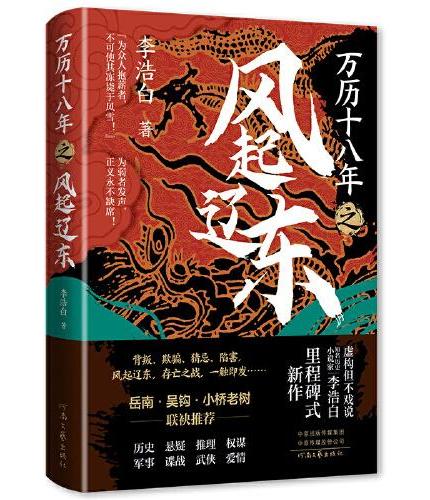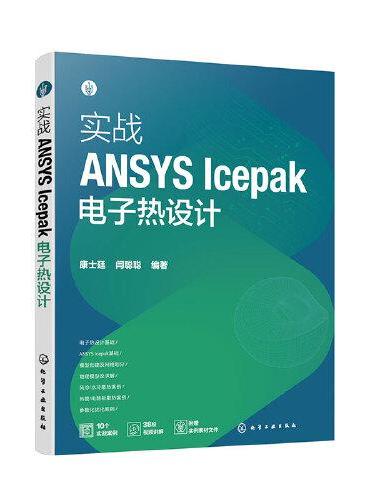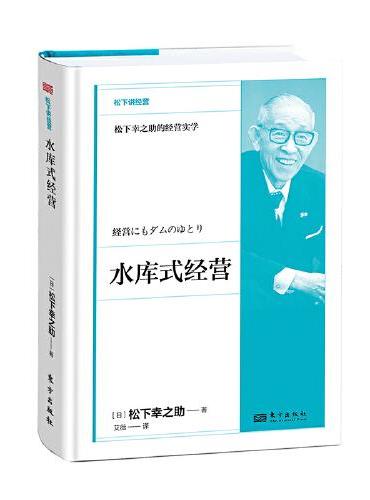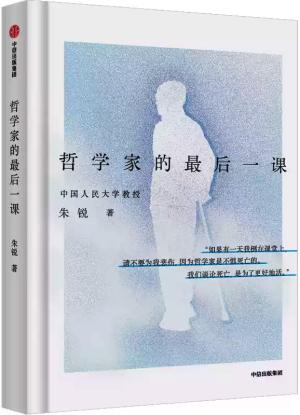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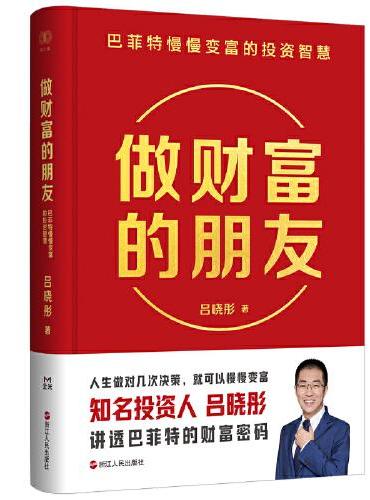
《
做财富的朋友:巴菲特慢慢变富的投资智慧
》
售價:HK$
82.5

《
一群数学家分蛋糕:提升逻辑力的100道谜题
》
售價:HK$
6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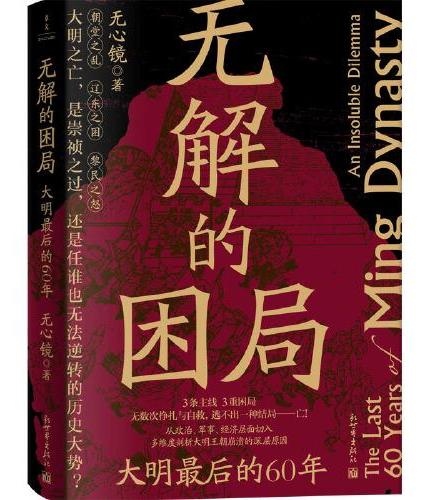
《
无解的困局:大明最后的60年
》
售價:HK$
6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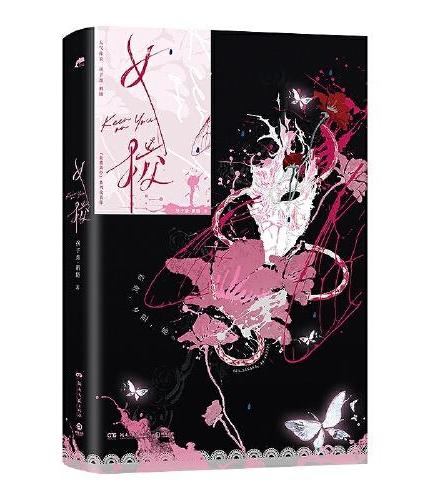
《
女校(人气作家孩子帮·鹅随“北番高中”系列代表作!)
》
售價:HK$
6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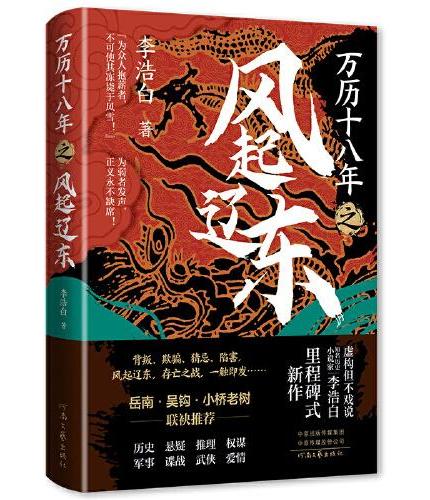
《
万历十八年之风起辽东
》
售價:HK$
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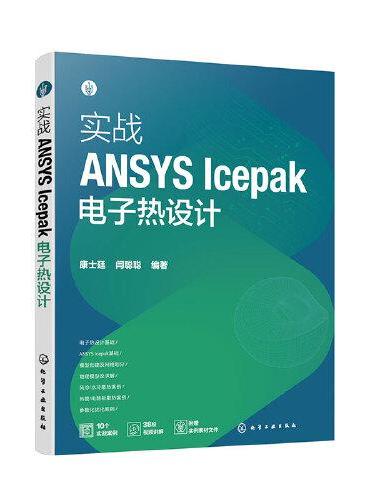
《
实战ANSYS Icepak电子热设计
》
售價:HK$
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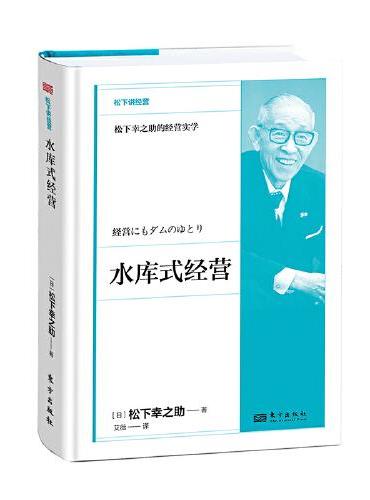
《
水库式经营
》
售價:HK$
6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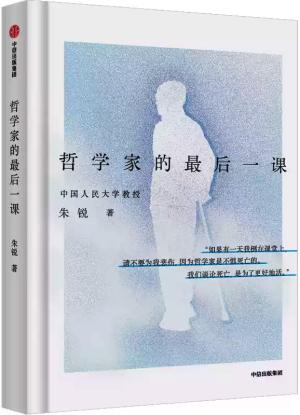
《
哲学家的最后一课
》
售價:HK$
57.8
|
| 編輯推薦: |
《祖父在父亲心中》收入作品:《一波三折》《祖父在父亲心中》《冬日苍茫》《落日》《桃花灿烂》《行云流水》
方方的小说贴近社会现实,描写从平民百姓到知识分子的生活故事,不回避痛苦,不夸张幸福,每一篇都直指人心,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深刻的社会认识价值。
方方的小说有智慧,不矫情。她敢于写出最无情、最悲惨的人物关系和人生境况,同时也写出最有力、最乐观的人生态度。这是方方的小说最令人感动的地方
|
| 內容簡介: |
“方方中篇小说系列”收入作品38篇,编为七卷:《风景》《祖父在父亲心中》《埋伏》《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万箭穿心》《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每卷以其中一篇命名),全面展现了方方中篇小说创作的成就。
方方是创作力最强的当代作家之一,也是中篇小说创作成就最高的作家之一。她的《万箭穿心》《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以及最新发表的《惟妙惟肖的爱情》等小说在读者中引起较大的共鸣和反响,方方在小说中对现实的深切关注、真实再现、深刻思考,使她和读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接近。特别是她的小说直面社会人生、言之有物,从不无病呻吟、矫揉造作,而且故事情节非常丰满,这在当下是非常可贵的。读者对这一点非常“领情”,因为他们从方方的小说里不光能看到别人的生活,也能看到自己,思考自己的人生。方方的小说具有长远的意义,并不追逐社会热点或思潮,不是“时效性”的,所以任何时候出版,都正当时。
从《白雾》《风景》到《祖父在父亲心中》《埋伏》《奔跑的火光》《行云流水》《万箭穿心》《声音低回》到最近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等等,方方打动人心的小说不胜枚举。她的小说有智慧,不矫情;她敢于写出最无情、最悲惨的人物关系和人生境况,同时也写出最有力、最乐观的人生态度。这是方方的小说最令人感动的地方。李宝莉过得惨不惨?惨透了,可是她是还有一股劲。现在说no zuo no die,她的惨很大程度上是她自己造成的。她心地善良性格暴躁,严重地伤害了别人还不自知,这可以说是一种愚昧。她以百倍的真心对待公婆和儿子,而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恨她到死,这又是何等悲哀!但是她失去一切以后,内心的善良到底没有泯灭,还是没有以恶待人。这就显示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人性力量。对于作者笔下的“狠”、人物的“惨”,读时又害怕,又期待,这又是艺术的力量。《声音低回》,写下层老百姓的生活,通过低能儿阿里一家来表现,充满温情和人性的美好,同时也批评了政府施政过程中对普通百姓的忽视。《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相信每一个来自农村贫困家庭,毕业后留在城市的大学生都会有强烈的阅读感受,它写出了这个群体的艰难处境,写出了小人物在权利、金钱、社会关系等等重压之下无可逃遁的命运,同时也反映出我们的教育对社会阶层固化的现实的无能为力。早前的《埋伏》,看似一个破案小说,却把人物的心理和生活的哲理不露痕迹地融在其中,令人感到趣味无穷。方方小说中有千变万化的故事、各种各样的人物,贴近现实、直指人心这个主旨是一以贯之的,她的小说打动人心,正在于此。
|
| 關於作者: |
|
方方,当代作家。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水在时间之下》《武昌城》,随笔集《到庐山看老别墅》《汉口的沧桑往事》,中短篇小说集《风景》《桃花灿烂》《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小说单行本《万箭穿心》《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等。现已出版小说、散文集约60部,多部小说被译为英、法、日、意、葡、韩等文字在国外出版。
|
| 目錄:
|
一波三折
祖父在父亲心中
冬日苍茫
浇日
桃桦灿烂
行云流水
|
| 內容試閱:
|
《祖父在父亲心中》节选:
他们在杀人的时候,是丝毫也没能想到这一滩乌红的血迹是怎样漾成一片巨大的阴影而笼罩在几代人的心头。
这片阴影有一天在父亲的心里突然变成一块巨石或说是一座山峰。父亲的呼吸因为它的缘故变得急促和沉重起来,并且渐渐地上气接不住下气。坐在父亲旁边的席先生说:“你父亲那时在发抖在发抖呐!”
父亲直面着疯狂的杀人场面。刺刀和鲜血在他的眼睛里闪来闪去。仿佛有人扯着他的耳朵死命地将一声声凄厉尖锐的呼号和哭泣强塞进去,还有杀人犯的笑声。大滴大滴的汗珠从父亲高高的额头上滚到他的面颊又滚下他泛黄的白衬衣上。父亲觉得晕眩无比,世界在他的那一刻变得鲜血淋淋,而他则是这个血淋淋世界上的一个成员。他的心抽搐着,恐惧感从心底漫向他的全身。
这是祖父死去三十五年后的一个日子。虽是初秋时分。但每一杈树枝都仍挑着夏日的盎盎生机,面对这浓郁的空间只能令人想到生的兴旺而很难去作死的玩味。而死的幽影却悄悄地潜入到父亲身边。
父亲的四周昏暗极了,许多张朦胧的脸环绕在他的周围。九月的热浪隔着门窗和厚厚的墙壁顽强地挤了进来。枣红色的窗帘从高高的窗户上垂下,散发着浓重的灰尘气味。很多人在狠狠地抽烟,青烟腾腾地缭绕在人们的头顶,空间为此而浓稠得仿佛可以捏揉。父亲便是坐在这窒闷而肮脏的环境之中。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日,武汉长江电影院放映内部影片《军阀》。父亲的单位发给了他一张票。并不爱看电影的父亲以为是政治任务而不敢不去。为此他看到了日本人是怎样地杀人。
刺刀和鲜血,铁骑和东洋语使父亲的记忆如一个鼓胀的汽球突然间地进裂了。密封在心灵深处的往事如血喷一样涌出,然后像千万条小虫缓缓爬入他体内的每一个部位。父亲痛苦难忍。他咧张着嘴,手指如鹰爪一般剧烈地抠着他坐下的木椅。他的两腿颤动得无法支撑他壮实的身躯。
父亲前面坐的是个女人,她是一个怯懦的女人,每逢有恐怖画面,她便轻叫一声且立即将头埋在手臂弯里。那女人是个高个子,她的头一直遮着父亲三分之一的画面。对于这种状况,父亲是向来不多说一句话的。他什么也不在乎地看剩下的三分之二。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使父亲将电影几乎一半的内容承受了下来,虽然他已痛苦万端了。当一个老苍苍的身影从父亲的视线里幻化为祖父的影子时,前面的女人尖叫了一声,然后迅疾地趴下,就在这一刹那,银幕在父亲面前豁然展开,而刺刀和它上面的滴滴鲜血亦猛然地伸到了父亲的鼻眼之下。很多的“啊”声蓦地轰响,而父亲那一刻却只“呵”了一声,仿佛轻微地叹了一口气。
这之后几秒种,他便扶着前排的椅背吃力地站立起来。席先生说:“他站了好几次才站起来,好像还站不稳,又定了定神才离开座位。我以为他上厕所呐。”
父亲的座位在电影院的楼上。楼上的过道是阶梯式的。父亲的双腿宛如灌了铅,每迈出一步几乎都要费尽全身的力气。父亲那天穿的是一双翻毛皮鞋,鞋很厚重。我至今仍奇怪父亲为什么在那样暑热未尽的季节里穿那样一双皮鞋。父亲喘息着走完一级级台阶。很短的一段路他却走了很久很久,仿佛比一个世纪更长。他走得那样艰难那样沉重。影院里所有人都注目着与父亲行进方向相反的地方,注目着杀人和被杀。只有父亲走了。谁也不曾介意步履维艰的他。黑茫茫中父亲在刺耳的惨烈的背景音乐伴奏下走得好孤独好寂寞。
已是黄昏时分。蓝光和紫光悄悄消散了,太阳剩余的色彩将西天染得如火如血。余晖开始变得黄晕晕的,把走廊的红漆木栏斜拉得长长,长长。厨房里油烟飘到窗外,母亲炒菜的“嚓嚓”声高一阵低一阵地响着。邻家自来水笼头哗啦啦急促地放着水。老远老远的地方传来一支口琴曲子。那是一支忧伤的知青怀念武汉的歌。我至今仍记得它的歌词和旋律。“武汉英雄的江城我们怀念你。”第一句就是这。口琴在渐渐黯淡下去的天空中如怨如诉,恍惚让人能看见曲子中飘零的黄叶和立于这无边落叶之下的伶仃之人。一个平凡的黄昏在这口琴中蓦地变得无比伤感起来。
那一刻我正躺在竹床上看莱蒙托夫的《诗人之死》。那是一九五五年我出生那年出版的译本,辗转几道借到我的手里。看《诗人之死》全然不是因为它是名诗,仅只为不知哪一位读者在那首诗的诗行里划下了许多红线。“一一他不能忍受这最后的痛苦了:熄灭了,像一把炬火,这稀有的天才,凋残了,那壮丽的花冠。”
邻居彭妈妈跌脚嘶声地呼喊我的名字,黄昏的情调一瞬间如浸入了鲜血,变得凄厉起来。 .
我冲下楼,惊恐着问:“是不是……是不是……”我想说是不是我爸爸被汽车撞了。因为父亲总是骑着他那辆破旧的自行车行进在窄狭的有许多汽车奔驶的工农兵路*上,我们经常为他的安全提心吊胆。
“快快快,在医院里。快去,快,在电影院,快,在医院里。”彭妈妈语无伦次。她那如歌吟般的南京话几乎变了调。
父亲出事了,这是一个基本弄清了的事实。厨房里正炒着的菜立刻糊了。糊味充溢得到处都是。母亲套她那条蓝绸长裤套了好几分钟。她仿佛没有了意识。她坐在邻居一个小青年的自行车后架上匆匆去了医院。而在那之前,母亲从没有胆量坐自行车后架,也从没坐过。
我赶到医院时,母亲早到了那里。她一个人静穆地坐在长椅上,那神情仿佛已经坐了一百年。她瞥了我一眼,淡淡地说:“你不要把辫子盘在头上,这不像个女孩子。”我的辫子盘了整整一个夏天,我常同母亲笑说我是藏族人,母亲多报以一笑。而在这一刻,却莫明地提出异议,我始终不明白这句话的来由。
我放下辫子,去往急救室。隔着玻璃门,我看见了我的父亲。
父亲仰躺在一张窄床上,他双目紧闭,棱角分明的嘴抿得紧紧,脸色一如他惯有的严肃。一个强壮如牛的男医生骑跪在他身上,他搓揉着父亲。我知道他这是在施行人工呼吸,但心里却觉得他似乎想杀死父亲。他摧残他折磨他凌辱他。父亲一动不动。我背过身子,贴墙而立,再也不敢看那屋子里的事情。很久很久以后,那强壮如牛的男医生搬进了我居住的宿舍区,此刻的他已变得苍老而臃肿。任凭他对我作出如何友善的微笑,我都对他视若仇人。我对自己说:不管怎样,父亲死在他的手上。
天黑得很厉害的时候,医生出来了。暗夜从走廊尽头的窗口递入一点星光和风,同时也将母亲嘤嘤的哭声送进夜空。医生说:“人完了。”他用三个字把父亲的一切都结束了且连同母亲的幸福。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