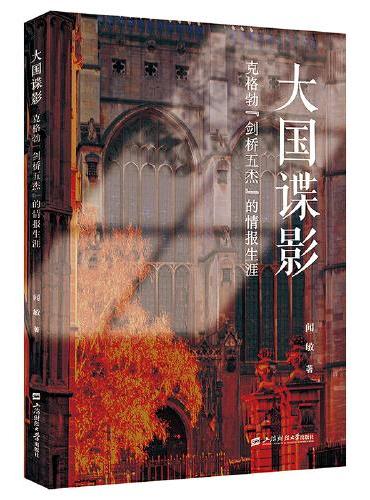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东方看世界·极简法国史
》
售價:HK$
74.8

《
动物与人体的比较解剖书
》
售價:HK$
98.8

《
步行景观:作为审美实践的行走(艺术与社会译丛)
》
售價:HK$
61.6

《
北朝隋唐史论集
》
售價:HK$
273.9

《
半小时漫画中国史(全5册)
》
售價:HK$
274.5

《
7步吃透商业提案写作
》
售價:HK$
6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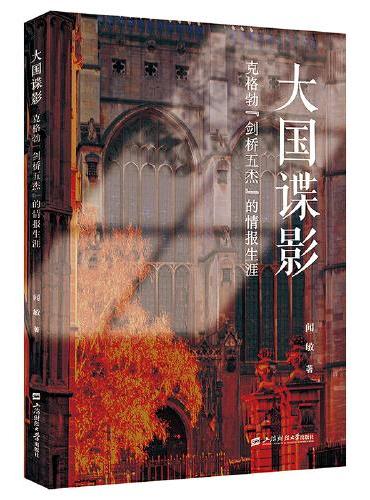
《
大国谍影
》
售價:HK$
96.8

《
制造消费者
》
售價:HK$
49.5
|
| 編輯推薦: |
|
近些年来,学者们愈发意识到,情感在我们实践理性中起到的作用,较我们过往认为的要大得多。克劳斯同意这一观点,但她也明白,这一洞见实则是一声呼喊,呼唤我们着手进行一项重要的研究,即理解激情是如何必然地指导我们的理性,以及“公民的激情”和“情感性无偏倚性”应当如何引导我们在道德和政治生活中进行判断、慎思和决策。她的这本著作携着丰富的想象、审慎的论证和独到的洞见发起了这一研究。
|
| 內容簡介: |
|
《公民的激情》考察了政治商议和个人慎思中,理性与激情的关系,认为理性无法独立负担起做出决定的重任,一旦排除激情,人类将无法做出决定。如何让激情合理地容身于公共行为之,是克劳斯在书中慎重考虑的问题,但并不是所有的激情在公共行为当中都经得起无偏倚性的考验。这些思考对于公民社会、对于每一个公民来说都极有裨益。
|
| 關於作者: |
|
莎伦R.克劳斯是布朗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就古典自由主义和当代自由主义论题撰写过多篇文章,论及休谟、孟德斯鸠、波伏娃,以及当代的正义理论,发表在《政治理论》、《政治评论》、《政治与性别》、《当代政治理论》等刊物上,并著有《荣誉与自由主义》、《主权之上的自由:重建自由的个体主义》等。
|
| 目錄:
|
致谢
导论:公民身份、判断与激情政治
第一章:罗尔斯与哈贝马斯理论中的正义与激情
第二章:理性主义的新近替代物
第三章:休谟:道德情感与关于判断的政治学
第四章:民主政治中的情感性判断
第五章:公共商议与无偏倚感
第六章:法律的情感性权威
结语:迈向一种新的激情政治
参考文献
索引
|
| 內容試閱:
|
导 论
公民身份、判断与激情政治
作为公民,我们如何在值得我们拥护的法律和那些我们应当拒斥或抵制的法律之间做出区分?民主的程序标准对此很有意义,但很明显,民主程序有时候也会误入歧途,导致一些危及公民自由权或妨害社会正义的法律。虽然司法审查原则赋予法院在评判立法成果方面以某种角色,但自由民主社会中的公民们在这方面也负有一份责任。无论如何,作为公民,我们与法律的关系不应当是一种盲目服从的关系,而是应当体现批判性的允诺和健全的判断。事实上,作为自由民主社会的公民,我们负有一种政治义务,去评判法律并抵制(或努力革新)那些确实侵犯自由或妨害正义的法律。我们如何进行这种评判呢?我们要运用何种心理与心智的官能呢?举例来说,现今的美国人正在就同性婚姻是否正义的问题进行公开商议。在就这类集政治、道德与法律问题于一体的议题进行商议时,我们要运用何种能力?特别要问的是,在这种商议之中,思考与感受、理智与激情、认知与情感如何结合在一起才算是恰当的?
对这个问题的一般反应是坚持认为,至少当事涉有关重要政治问题与基本正义问题的商议时,根本不存在理性与激情的恰当结合。换言之,获得有效商议的唯一方式,就是把激情从商议过程中完全剥离出来。忧虑在于,这些情感性的意识方式会模糊我们的理性,从而妨碍为健全的道德判断、公正的司法判决以及公平的政治商议所需的无偏倚性。这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主导性观点(固然并非唯一的观点)。同样,它也是当今政治理论中的主导性观点。本书要挑战这种看法。我们用以评估法律与公共政策的实践慎思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情感和欲望,而且对于使得公共决定具有正当性的那种不偏不倚的立场,这些激情能够以一种积极的方式起到促进作用。诚然,种种激情也可能妨碍无偏倚性,而且一旦如此,它们会给民主社会决策制定的正当性及其结果的正义与否带来一些问题。例如,残忍和偏执就绝不应当决定我们集体商议的走向。一种公民性(civility)精神,而非沙文主义或破坏性的盛怒,应当指导着这种商议。如同公民性一样,不偏不倚的理想对正当的商议和正义而言至为重要,它绝不应当被弃之一旁。然而,激情与无偏倚性之间发生冲突的现实可能性并未涵盖它们复杂关系的全部内容。本书提出一种对于情感性的、但却不偏不倚的判断的阐释,它在非严格的意义上受到休谟的道德情感理论的启发。同时,本书也就激情在道德判断与公共商议中可能恰当扮演的角色提供了一种系统的说明。
在阐述无偏倚性的情感之维的过程中,本书提出了一个困扰了整整一代规范性民主决策理论的问题。在当今政治理论中占支配地位的关于慎思与规范辩护的理性主义模型(如在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的作品中所刻画的那样)在动机问题上存在缺陷。根据这种观点,作为一种与情感相分离的官能的理性观念构成了无偏倚性的根基。但这种理性观念把慎思主体与人类行动的动力之源割裂开了,而这些源头恰恰见之于主体被要求与之疏离的情感性依恋关系与欲望之中。作为慎思者的自我与作为行动者的自我分裂开来了。不错,罗尔斯和哈贝马斯都在他们的正义理论中为情感留出了空间。具体说来,他们都认识到如下做法的重要性,即引入公民们的依恋关系和欲望,将其作为促进对规范辩护的理性程序及其结果的忠诚的手段,从而形成一种对正义的情感,以增强正义的稳定性。然而,两人的观点都试图把情感的作用限制在应用领域,而规范辩护本身则被设想为某种超越情感影响的理性的功能。结果,他们给我们呈现的是一种两阶段的模式:首先,理性告诉我们,就法律与公共政策而言,正义意味着什么、它提出了什么要求;然后,一俟这一规范性问题得以解决,我们就步入应用领域,此时我们可以开始思考,该如何把公民们社会化,使之习得那些支持已得到理性辩护之规范的情感倾向。由罗尔斯的原初状态和哈贝马斯的道德立场所塑造的判断形式暴露出了对情感的常见恐惧,亦即,我们的激情会责难关于正义问题的慎思所应当依赖的那种无偏倚性。因此,主导性的范式能够接受的是,情感关切帮助驱动正当的行动,而不是这类关切在对行动或指导行动之规范的辩护中出场。它们不愿把道德与政治规范的内容和权威同个体的心理状态联结起来。理性主义者视情感为无偏倚性的对立物,他们在某种与激情相扞格的理性中发现了规范性的根源。然而,把慎思与情感隔绝,就是将慎思与驱动行动的激情相分隔。
受到损害的也不仅仅是行动,由于试图过于充分地摆脱激情的影响,决策制定本身也受到妨碍。过去15年来,神经科学和神经心理学领域出现了一批革命性的新文献,它们对人在不动用情感的情况下从事实践推理的能力提出了质疑。这些研究涉及一些与情感相关的大脑区域受损的患者,它们表明,决策制定依赖于重要的情感体验,尤其是依恋、嫌恶和欲望。情感方面有障碍的患者或许完全能够进行逻辑分析,他们也常常能够就种种行动路线的成本与收益进行有效推理。这些研究表明,他们无法做好的事情是就行动路线做出决定。这些发现意味着,实践推理,亦即导向行为决定的慎思,必然包含着情感。情感在驱动行动和决定方面都发挥着作用,因此,与理性主义模式相关联的动机性缺陷所破坏的就不仅是(对决定的)服从,而且还有慎思过程本身。因此,这类新文献就对主导现今政治理论的有关慎思与规范辩护的理性主义范式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
近来,政治科学家们开始探究这些发现对于诸如政党认同、负面竞选、社会运动的形成,以及国际冲突调停等领域的政治行为的含义。他们全都强调的要点在于,我们对政治行为的分析视角应当反映如下事实:对于决策制定而言,情感与理性一样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情感乃是实践合理性(rationality)本身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什么与情感完全分离的实践理性能力。基于先前的学习和经验,通过提供一种对重要事项的意识,情感与其它东西一道为将来的决定设定基础。易言之,情感构成了关切的范围,而实践判断和慎思正是在其中得以发生的。经验性文献所表明的是,没有情感,我们无以对(政治或任何其它东西中的)实践目的进行有效慎思。这意味着,情感在关于正义的慎思中所发挥的作用,必定比政治理论中的主导性模式所承认的要更为重要。然而,经验文献所没有提供的则是对如下问题的一种规范性说明,即情感应当如何在实践慎思(如果其结论要符合正义的话)中起作用,尤其是情感如何能够服务于无偏倚性这一重要的民主理想。
道德哲学、政治理论与法学中的规范理论家们正日益认识到情感在判断与慎思中的重要性。这种认识标志着真正的进步,因为它扩展了判断与慎思在其中得以理解的概念框架,但它也带来了自身的一系列难题。虽然理性主义者们为动机性缺陷所困,但情感理论家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则遭到规范性缺陷的困扰。他们总是没能为对情感的正当容纳提供清晰的标准。毕竟,并非所有的情感都支持健全的判断或公平的公共商议。我们不妨看看沃尔泽就“我们对侵略的敌意”如何“恰与侵略本身一样为激昂的情绪所支配”这一问题所作的讨论。他认为,在这种敌意的背后并非一种超越情感的理性官能,而是一种溶入了情感的理性:
那种敌意的背后……是一幅像我们自己一样宁静而和平地生活于他们自己的处所、他们自己的家和祖国之中的人们的心理图像。他们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遭受攻击(这正是侵略的定义),他们的亲友、城镇和生活方式受到破坏性威胁,甚至遭到毁灭。可以肯定地说,不参照这一心理图景,我们对这一攻击的理性谴责是无从理解的。事实上,它衍生于那一图景;它依赖于我们与那些人在情感上的认同,他们是我们在家园中和平地与之生活的男男女女的被投射的形象。这类认同是亲和性激情的产物,它们型塑了我们对侵略的反应,其确切程度就如同对胜利与支配的激情型塑了侵略本身一样。
我们对好与坏、对与错的判断因此既是理智理解力的函数,在同样程度上也是情感的函数。然而,沃尔泽没有确定我们该如何在充满激情的判断与不健全的判断之间进行区分。可以肯定,有些亲和性的激情可能导向糟糕的判断和不正义的决定。我们需要知晓,情感应当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被纳入慎思过程;我们也需要明白,移情式的(或“亲和性的”)关切其影响应当达到何种程度;我们还需要一些标准或方式,以区分值得我们尊重的和不配我们尊重的情感。
另一个问题是,讨论情感的理论家们有时把情感性的判断当作无偏倚性的替代选项来为之申辩。1980年代浮出水面的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把判断植根于对特定他人的关切之中。它将无偏倚性与对普遍正义原则的理性尊重关联起来并予以回避。这一思路的一些更近的倡导者们有时则把以正义为取向的判断与以关怀为取向的判断视作互补的而非竞争性的。然而,与理性主义者们一样,她们把对正义的不偏不倚的慎思与一种超越情感的理性形式关联起来。在这方面,她们向主导性范式让步得太多。扬和纳斯鲍姆同样将情感性的判断形式奉为无偏倚性的替代选项。虽然她们的思路彼此之间明显不同(与关怀伦理学也不一样),但她们共同信奉某种关于无偏倚性理想的怀疑论,她们将这一理想与一种排他性的和不可靠的人类理性观念关联在一起。
不过,民主社会的公民们付不起放弃这一理想的代价。无偏倚性蕴含着一种慎思性的观点,它既非内含偏见,亦非支离破碎。它要求以特定的方式来考虑问题,该方式不由一个人的自我利益、狭隘的同情或特立独行的信念来决定,也不纯然服务于这些东西。它也是一种包容性的甚至是整全性的观点,把受所考虑的对象影响的所有人的相关看法纳入其中。考虑到我们的判断可以或多或少地摆脱偏见和具有包容性,无偏倚性也容有程度问题。我们很少有人在常规的基础上达到完全的无偏倚性,跨文化的无偏倚性尤为困难。但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在种种(不)完全的程度上运用无偏倚性则是一种熟知的经验。在这一过程中指导我们的那种令人向往的理想极富价值。与其它东西一道,无偏倚性帮助我们把我们的评价和决定与权力带来的特权隔离开来。没有某种程度的无偏倚性,公共决定就会缺少正当性,而正义也会被证明是不可捉摸的。这正是理性主义者们正确把握的见解:不偏不倚的判断是自由民主社会里正义的公共决策制订当中的一个关键条件。它保护公民们在事关正义的公共问题上免受赤裸裸的强力的侵害。
在个体道德判断的语境中,无偏倚性也很重要。一方面,它有助于社会协作,因为为了与他人协调我们的生活,我们必须能够超出我们自己私人观点的限制去思考问题。如果一个人的慎思性观点单单由自我利益所决定而没有任何对他人利益或观点的考虑,从长时段来看,他甚至连自己的目的都无法实现,遑论集体目的。无偏倚性有利于促进社会协作这一事实使之具有审慎的特征。无偏倚性也彰显了休谟所谓的“人性”之德,即一种对他人之困难与欢乐的反思性的敏感性,甚至也指一种对人的尊重,即认为他们在道德上很有价值。一如休谟所见,若无这一美德,一个人的人格品质就会显露出偏狭、粗野和无知,它绝对经不起自我省察。我们还可以在休谟之外进一步补充说,在判断中运用无偏倚性乃是一种把他人当作目的本身来对待的方式,而后者是一项能够通过道德情感的方式得到辩护的义务。一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一个人无需借助康德来支持平等尊重的责任,而这项责任令无偏倚性变得很重要。因此之故,虽然我们应该对排他性的、不牢靠的理性观念保持怀疑,我们却不应当拒斥无偏倚性。拒斥无偏倚性就会让种种情感性判断背负上一种规范性缺陷。简言之,我们的道德判断与民主商议理论已然处于两难之中:它们要么太过理性主义,以至于不能驱动行动与决定,要么就太过不加鉴别地植根于激情而无力承受规范性之重。本书旨在通过清晰阐述一种由情感所激发的无偏倚 性理念,从而也就是提出一种在动机与规范性方面都令人信服的对判断与慎思的说明,从而化解这一两难。
因此,本书处理的是困扰政治、道德与法律领域中的当代理论的一个盲点问题,但它同时也讨论当今美国公共生活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关于政治商议的通常看法设定了理性与激情之间的二分法,据此,一个人要么从“不偏不倚的理性”出发进行慎思,要么他的慎思就是由个人性的激情所驱动的。而我们以为,当激情驱动商议时,其结果只能被说成是卑劣的。然而,理性主义的那种弥漫于公共文化中的无偏倚性理想则纯然是田园诗。因此,如今美国的公共决策大多是通过基于利益的竞争所推动的,它是未经驯导的激情政治的别名,这就不足为怪了。但是,即便我们屈从于最低级的激情政治,我们那不可捉摸的理性观念仍旧吸引我们的心愿并告诉我们,由激情驱动的商议没有正当性且可能导致不正义。为不辜负这一不可能的商议理想而屡战屡败的一个结果,就是对政治的犬儒主义态度。人们广泛讨论的、现今美国政治参与的不足仅仅部分说来是过度的个人主义、没有公民美德、缺少社会资本的结果。这种疏离也反映出一种幻灭,它自然地导源于我们对理性与激情之间那种错误的二分法的念念不忘,导源于一种可以实现的无偏倚性理想的缺失。
更有甚者,普遍的公民政治疏离铲除了公共商议中真正的无偏倚性的可能性基础。理由在于,唯有当我们的商议过程体现了所有受影响者的正当关切,它才可能是完全不偏不倚的。但唯经他人告知,我们才能知晓他们的关切,而这恰恰要求为理性主义的观念所阻滞的那种对公共生活的积极参与。因此,美国政治需要一种理解公共商议的新方式,它既可以响应无偏倚性的高贵诉求,但又不贬低势必影响决策并激发行动的那些激情。我们必须拒斥在政治理论与美国公共生活中同时存在的理性与激情之间错误的二分法,因为这种二分法破坏了我们推进正义事业的能力。我们需要以一种对实践推理之整体性本质的更好理解将其取而代之,也就是将实践推理理解为一种综合了心灵的认知与情感状态、综合了理智与情感的能力。我们需要一些标准,它们可以激发深思熟虑的而又正当的决策制定,但同时又是实际可行的、在动机上令人信服的,从而是由情感所激发的。本书的目的就是要阐明实践判断在这方面的本质,并表明为何这种有关我们自己和我们能力的更具整体性的图景预示了一种更有生机、更为正义的民主政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