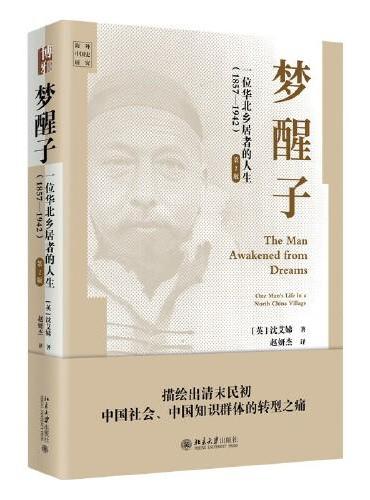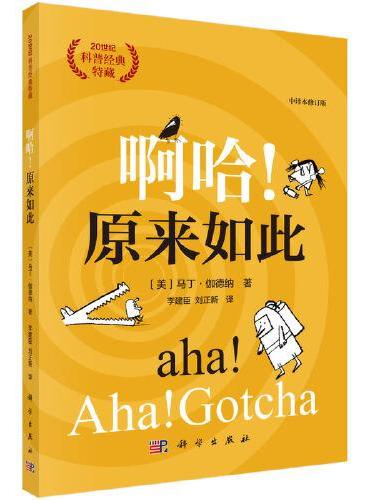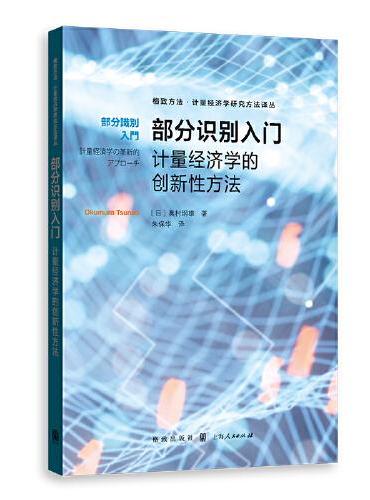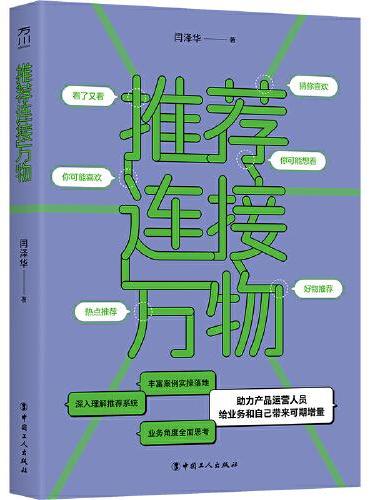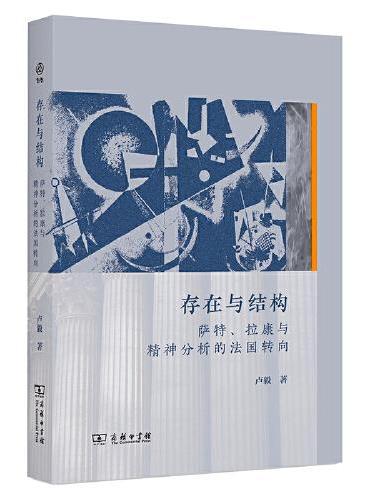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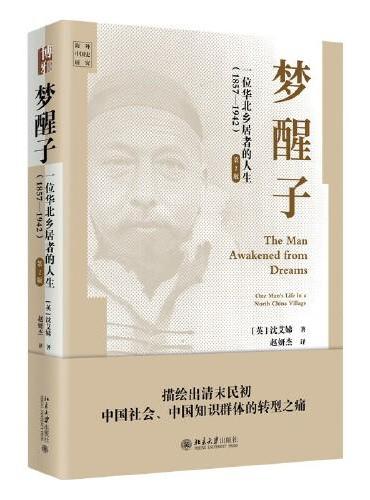
《
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第2版)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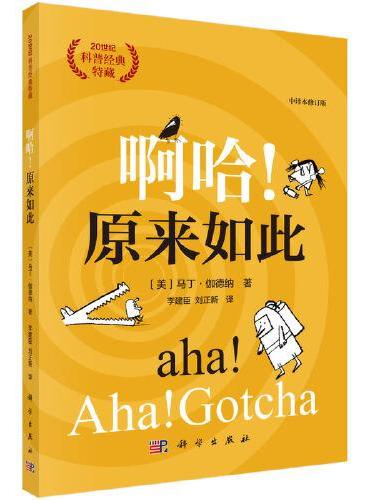
《
啊哈!原来如此(中译本修订版)
》
售價:HK$
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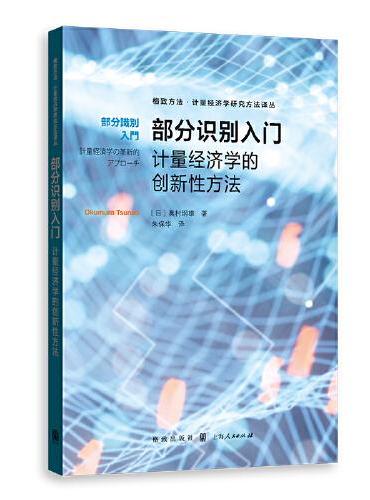
《
部分识别入门——计量经济学的创新性方法
》
售價:HK$
75.9

《
东野圭吾:变身(来一场真正的烧脑 如果移植了别人的脑子,那是否还是我自己)
》
售價:HK$
6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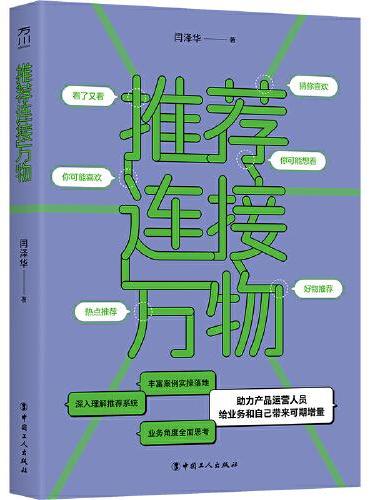
《
推荐连接万物
》
售價:HK$
63.8

《
严复与福泽谕吉启蒙思想比较(王中江著作系列)
》
售價:HK$
165.0

《
甘于平凡的勇气
》
售價:HK$
4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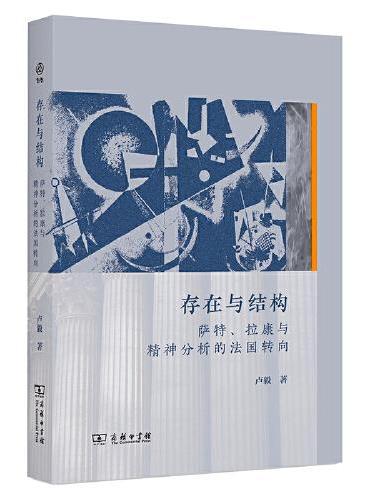
《
存在与结构:精神分析的法国转向——以拉康与萨特为中心
》
售價:HK$
52.8
|
| 編輯推薦: |
◎70后最火作家徐则臣最新散文自选集
◎小说家的散文——
最不虚妄的文字
最不做作的性情
最不雕琢的思想
最不掩饰的本色
◎“小说家的散文”丛书,打开另一扇窗,呈现小说家的本色。在散文里,小说家是藏不住的。他们把自己和盘托出,与最真实的灵魂照面。
|
| 內容簡介: |
|
《别用假嗓子说话》是青年作家徐则臣的最新散文自选集,共分3辑,既有对亲情乡情的描写,又有“在路上”渐行渐远的思考,以及对当下写作、读书的体悟。徐则臣的散文创作一直与小说并行,他在书中说:“有些情小说抒不好,有些理小说讲不清,有些话小说就是说不明白,但我又必须把它说出来——我就是一个用汉字来表达自我的人,不说话会憋死。所以,我坚持以小说家的身份顽固地写散文随笔。……写下它们让我心安。”
|
| 關於作者: |
|
徐则臣,作家,1978年生于江苏东海。著有长篇小说《耶路撒冷》《夜火车》《午夜之门》、小说集《跑步穿过中关村》《人间烟火》《居延》、随笔集《把大师挂在嘴上》《到世界去》等多部。曾获得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多种奖项。部分作品被译成德、韩、英、荷、日、意、俄、法、蒙等语。
|
| 目錄:
|
【辑一】这么早就开始回忆了
小博物馆之歌
世界和平与葫芦丝
我之所从来
放牛记
贵人
我的三十岁
进北大记
兄弟在我们北大的时候
—序《兄弟我当年在北大读书的时候》
生活在北京
中关村的麻辣烫
这么早就开始回忆了
一个知识分子的死
“春晚”与除夕夜
露天电影
出走、火车和到世界去
凤凰男
不想当大师的士兵不是好运动员
盐不荒心慌
没魂走不远
【辑二】我为什么喜欢凡·高
教堂
镇与小镇
哲学课
烟幕弹放多了
阿姆斯特丹和我们的历史
我为什么喜欢凡·高
上林赋
恍惚文登是故乡
从丹江口进入日常生活
汤阴行
鬼城记
在腊月里想起增城
【辑三】在北京想象中国
大师即传统
在北京想象中国
别用假嗓子说话
“不等人”的新人之书
《通往乌托邦的旅程》自序
《我看见的脸》自序
我所见闻的中国文学在英国
局限与创造
小说的边界与故事的黄昏
我的“外国文学”之路及相关问题
在世界文学的坐标中写作
J.贝恩勒夫与《恍惚》
与大卫·米切尔对话
|
| 內容試閱:
|
别用假嗓子说话
照有识之士的说法,风水轮流转,尴尬的70后终于在奔四的时候,被批评界认可为亚热门话题。当然,这些年来70后也从来没有被彻底遗忘过,一直靠边列席在关于50后、60后和80后的评说里:说到50后、60后,70后是一帮不长进的小东西,稀松平淡,没法跟前辈比;提到80后,70后成了没出息的哥哥姐姐,鸦雀无声,没一个能挺身冲进市场,争到一块蛋糕。跟50后、60后比质量,跟80后比销量,两套标准,这个判断固执地遵循一个奇怪的逻辑;懂文学的这么说,不懂文学的也这么说,鄙视70后成了最保险的文学结论之一,反正里外不讨喜。在我看来,做这样的反面典型挺好,我把稀松平淡视为深挖洞广积粮,把鸦雀无声理解为低调和淡定,我更喜欢看见一群正在劳作的沉默的脊梁。劳动者最光荣。的确,现在撅着屁股吃力不讨好地写中短篇的,绝大多数都是70后。身为编辑,有时候我会突发奇想,要是这群人集体抽风急功近利,中短篇小说罢写了,那么多文学杂志辽阔的版面该如何填满呢?这么一想,70后在当下文坛似乎也挺重要。不管是盼望着还是无望着,东风的确是来了,春天的脚步的确是近了,在盯50后、60后盯得审美疲劳之后,在看多了80后发现大家都长得差不多之后,70后的屁股被慢慢地挪到审判台的中间,可以开始了:坐好了,说你呢。
70后作家写得如何,我说了不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绝不相信延续在50后、60后身上蓬勃的文学才华,会在十年或者二十年后的一代人身上突然集体萎缩掉。也许70后已经做得很好,也许70后的路还很长,这要留待时间去定夺。摆在眼前的是,70后整体上宏大叙事野心的欠缺,在当下史诗成癖的文学语境里,是大大减了分的。我听到很多前辈为此忧心忡忡,语重心长地提醒:砖头,砖头。70后似乎迫切地需要“砖头”,拿不出来,只能和过去一样继续挨板砖,但这个谁也没法替他们急。
现在要做的是“就事论事”:70后是否成立,如何成立。
其实在使用“70后”这个词时,已经证明了这个概念的某种合理性。是“某种”——这只是权宜之计,因为它有巨大的不科学性。怎么能用一个狭隘的时间概念来涵盖和阐释作家与文学?文学是久远的事业,其通约的价值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我们才能在今天依然满怀激情地谈论唐诗三百、《荷马史诗》与《圣经》,依然可以夜以继日地欣赏曹雪芹、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非常对,千百年之后,没有人傻到会以十年甚或百年为单位,对作家与文学进行代际划分。但是,如果我们不急于观古今于须臾,不那么阔绰地看待文学史,而是将目光落实,尽力返回每一个作家和作品的诞生与成长现场,也许会别有洞天。历史往往如此,在一个波诡云谲的非常时代,它的历史容量将远高于平常;在每一个历史的节骨眼上,一天可以当成一年乃至半辈子来过。不存在均码的历史,也不存在等值的历史,否则,我们现在根本没机会看见时间和人类的起伏,上下五千年也将会是另外一个景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正视和重视个别时间段的差异,给予某些代际划分足够的合理性,也许对理解历史和我们自身的处境更具建设意义。对70后也如此,设身处地地将这一群体放进“代际”中来打量,同样会有别的一番发现。
我知道,大家已经习惯于使用70后概念的同时腹诽,认为根本没有必要把这代作家从当代文学的序列里单拎出来,因为70后文学的特质并不明显,也因为大家断定这一代的文学特质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明显。我不这么看,虽然就目前来看,的确不是很明显。
也许我们应该承认,时代在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这群人身上,留下了足以区分前后两代人的印记。如果60后作家的确能够被确认为“晚生”和“迟到”的一代,那70后作家更是迟至晚矣。1970年出生的作家,“文革”结束时也才六岁,刚刚开始有所记忆,而1976年以后出生的作家,根本连“文革”的边儿都没沾上,而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思潮”他们又没能赶上,平白错过了两个重大的历史和文学事件。和60后相比,70后一直被认为是没有“故事”和“历史”的一代。50后参与了建造也见证了毁灭;60后看见的只是废墟和阴影,但他们起码还有活生生的废墟和阴影可看,还有一个可以策动精神反叛的80年代,所以他们与生俱来就有颠覆和反叛的目标和冲动;70后什么都没见着,只能远远地想象,感不能同于身受,他们血液中缺少这样的基因。而80后,成长于改革开放的环境里,从小接受麦当劳、变形金刚和西方价值观的耳提面命,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里天然地有了全球化和地球村的影子,他们放松、从容、自我的世界与整个世界几乎可以画上等号,所以他们对这个时代和生活没有疑问,他们肆无忌惮,出入自由,他们可以真诚坦率地认同名利和商业时代。这也是他们比上几代作家更擅长与市场打交道的原因。与80后比,70后拘谨,忧郁,心事重重瞻前顾后,没法像他们那样放旷洒脱、坚决不“信”,放弃对主流价值观的追求,又不愿放弃对60后的“故事”和“历史”的遥望。他们希望自己也能“不信”,也能“怀疑”,也能“颠覆”和“解构”;而这“不信”和“怀疑”在60后那里恰恰意味着另一种“信”,“颠覆”和“解构”在60后那里也意味着另一种意义上的“建构”。也就是说,70后在骨子里还是希望像60后那样有所“本”,有所信仰,有所坚持和依傍,而这恰恰是他们与生俱来的缺失。所以,70后的焦虑在于,既不能像80后那样无所焦虑,又不能像60后那样深度焦虑;70后的焦虑在于他们的焦虑太过肤浅。这是一群犹疑和徘徊的人,这是一群两头不靠的人。他们生长在一个历史的节骨眼上。
这是一代人的胎记,抹不掉。它规定了他们在面对这个世界时,目光必然与60后和80后不同,这个世界在他们眼中映鉴出的必然也是与60后和80后不同的图景——代际意味的不仅仅是十年或者二十年的时间差,而是一辈子的看待世界的差异。上世纪70年代对70后来说,是一个无可替代也无法更改的十年,是宿命也是根源和出发地,更是独一无二的资源。如果一切皆可以入文学,如果一切皆有可能成就出好文学,那么,才华和勤奋之外,关键在于能否看清楚自己,能否坚守住自己,能否忠直有效地表达自己。
70后的要务也许正在于守住这个“不科学”的代际划分,70后就是70后,说70后看见的、听见的、想到的、焦虑的、希望的,别冒充别人,别用假嗓子说话。说自己想说的、能说的、应该说的、不得不说的,充分地、有效地说出来,提供一个人和一代人对世界的独特看法。这是70后的价值所在,也是文学的应有之义。
但在忠直有效的自我表达这一点上,毋庸讳言,我们做得并不好。这一代作家中有众多保有才华者,正沉迷于一些所谓的“通约”的、“少长咸宜”的文学款式,在从事一种跟自己无关、跟这一代人无关,甚至跟当下的这个世界无关的写作。这样的写作里没有“我”,没有“我”的切肤的情感、思想和艺术的参与。此类拼贴和组装他人经验、思想和艺术的作品,的确可以更有效地获取献花与掌声,但却与文学的真义、与一个人眼中的时代南辕北辙。我把这样的作品称为完美的赝品(如果足以完美的话),我把这样的写作称为假声写作。这种虚伪和无效的写作,长久以来,大概也是导致70后“面目模糊”,被集体无意识般地“列席”于各类评说的重要原因。
道路阻且长,谁也无法避免被与“某0后”打包混为一谈,但70后也许应该有自我提醒的自觉:你就是你,没事少往别人的队伍里混。没自己的声音可以慢慢找,别老用假嗓子说话,否则,要你干什么?这不是另立山头。自我区分不仅是自我确立的前提,也是历史本身使然。
我之所从来
2011年4月24日,在山东某地出差,因离家近,朋友顺道送我回了趟老家。家里正在翻盖房子,两层半的小楼已经完成了两层,钢筋水泥混凝土和红砖,脚手架,混乱得如同一场战争。因为楼顶刚浇注水泥,要多晾几天,工人们暂时都散了,父亲带我爬上空荡荡的毛坯房的二楼。房子算不上高,但视野开阔,半个村庄都在眼里,陡生了身轻如燕和豪迈之感。这两个感觉实在不搭界,但我踩着楼顶尚未抹平的水泥板,转着圈子把邻居们的院子看了一遍,生出的就是这感觉:想飞;钢筋水泥混凝土的楼顶很结实,有登高望远的豪迈。
这感觉从老屋里来。老屋在旁边,低矮的平房,红砖白瓦,为了给新房子腾地方,拆了一半,看上去悲伤破败,像一只折了翅膀的老母鸡。多少年来一家人就生活在老屋里,当然,那时候还不觉得它老,也不叫它老屋,我们在瓦房里出出进进,不认为它狭矮陈陋,我们过得喜气洋洋。那时候我小,对世界充满最朴素的好奇,坐在院子里仰脸望天,整个村庄的人声和狗吠都拥到一个院子里。我想站到高处,看一看别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看一看到了夏天的傍晚,他们是如何在院子里摆出一张桌子吃饭。但是院落低矮,除了爬到树顶,我只能坐井观天。我爬过很多树,可是村子里的树能有多高,到处又都是树,目光越过别人家的山墙就被枝叶挡住了,能见度太差。挂在树梢上整个人颤颤巍巍,感觉很不好,所以羡慕鸟,能飞上天,在某一个瞬间静止,一动不动。我想像一只鸟飞抵村庄上空,十万人家尽收眼底。后来看到电影和电视,知道了弄出浩大镜头的叫航拍,那时候我就希望像鸟一样航看我的村庄。因为我住在老屋里,在一个几千人的村庄,我们低矮,贴着地面生活,如同一枚棋子,被摁在了低海拔的角落里。当然,所有人都在自己低海拔的角落里。
只是我想看清楚,大家是如何生活在自己的角落里。所以我想飞。我喜欢想象一只鸟飞抵村庄上空,我更喜欢想象一个人一步一步走到高处,足够高,直到他把这个世界看清楚。所以我想登高望远。这些念头没有微言大义,也无寓意更非寓言,就是一个贫乏的孩子对世界最微小的好奇心。
此后的很多年,我离家念书、工作,寒暑两季放假回家或是小住,不是钻进书本里不出来,就是火烧屁股一般转个身就走。也是待在老屋里,但全然没有了少年时的天真,自以为知道外面的世界也无非如此,也不再会对邻居家的院子和饭桌感兴趣。就算坐飞机经过村庄上空,我也不过是从舷窗往下看看,在千篇一律的村镇中挑一个可能是我故乡的位置,哦,那是我家——我家离机场只有十多公里,小时候每见到飞机经过头顶都要大喊:飞机,停下。那只鸟从虚构中飞走了,回到家我几乎再想不起要登高望远。
但是现在,站在二楼粗糙的房坯上,我突然想起了那只鸟,想起了童年时我一个人的关键词:登高望远。现在,房子的确长高了;现在,房子长到二层,还要再长高半层。以我小时候的想象力,也许我曾经设想过有一天房子会做梦般地长高,但我肯定不会想到,真正站在长高了的房子上看村庄,究竟是什么感觉。
母亲一直不愿意盖新房子,老屋住着就很好,冬暖夏凉,主要是不必操心。嫁到我家三十多年里她参与盖了六次房子,搬家三年穷,何况造新家,穷怕了也累怕了。这几年但凡谁动议破旧立新,母亲都要历数六次里的穷困与操劳。在乡村,一穷二白的家境里屡建新居,和城里空着钱袋去买房的年轻人一样,都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母亲扳着指头说:你看,草房子盖了几间,瓦房盖了几间,半边草半边瓦的房子盖了几间……这样的房子我都经历过,只是每一间都是该款的绝唱,更穷困的生活我没过过。有一年给大爷爷单独盖一间屋,我也跟在父亲后头脱土坯,给房梁上的父亲扔稻草,我满头满身的汗,我懂得黄泥里掺上多少河水和稻糠壳抹墙才最牢靠。有一年,从院子里长老槐树和果树的草房子里彻底搬进白瓦房,就是现在的老屋,我只有四五岁,把自己的小零件蚂蚁搬家似的往新屋子里运,光脚踩到了一枚图钉,一扎到底。因为疼痛,记忆从那枚清醒的图钉开始,蔓延到整只脚,然后是白瓦房和草屋子,然后是新旧两个院子,然后是新旧两个院子所属的两个时代的生活——过去的世界通过一颗图钉闪亮地咬合在一起。那是我关于这个世界最初完整的记忆,从此,大规模的记忆才开始和我的生活同步进行。在遗落了图钉的新的白瓦房里,我们家一住二十多年,直到把白瓦的颜色住灰,把新房子住旧,成了老屋;直住到这些年有了一点点钱的邻居们都把小瓦房砸了,原地盖起了雄伟敞亮的大屋子。
祖父说:没法活了,人家都住在咱们头顶上,喘不过来气。盖不盖?
我说:盖。
祖父说:怎么盖?
我说:两层半。宜早不宜迟。
前后左右的邻居们,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我们家成了峡谷,头顶只有院子大的四方的天。年过九十的祖父要了一辈子强,现在低头抬头都憋得慌。那就盖新的。我负责说服父母。二十多年的老房子,够本了,再住下去就成了危房;还有三五十年要活,新房子早晚要盖,好日子早过一天算一天,为什么不从现在开始?就为了夏天凉快点儿,也得翻新的,否则邻居们都立秋了,咱们家还在三伏天里没出来。母亲还犹豫,我向她保证,这辈子她盖的最后一次房子,咱们全用好材料。
母亲说:就算用金銮殿的材料,不还是得我和你爸操持?
那天下午,我站在父母亲此生建造的最后一所房子的二楼上,在三十三岁这一年,终于在高处看遍了半个村庄,二十年的时光倏忽而逝。除了拿出一点钱,关于这座新房子我做的只是在电话里说了几次设想,嘱咐材料尽量用最好的;三个月之后回到家,我直接站到了二楼顶上。下一次再回来,我看见的将是一座祖父祖母和我父母这辈子住过的最完美的房子,他们把二楼朝阳的最大一个房间留给了我。搬家的时候我不会在,从老屋到新楼,我其实希望自己能像四五岁的时候一样,蚂蚁似的一趟趟搬运;就算出现第二枚图钉也未必不是好事,踩上去,疼痛将贯穿我一生。这可能也是我在自己的村庄里建造的最后一座房子。
我从二楼下来,给祖父祖母买了烟酒和点心,陪他们说话,和父母吃了顿晚饭,就拎着行李去了机场。从下车到离开,在家一共待了四个小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