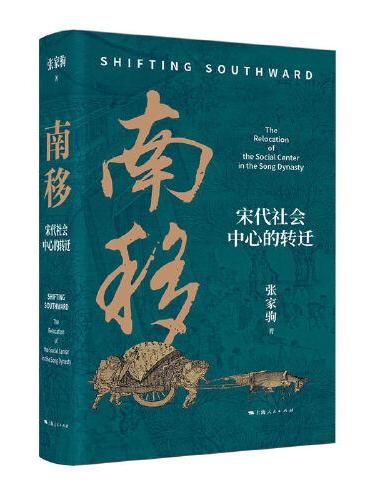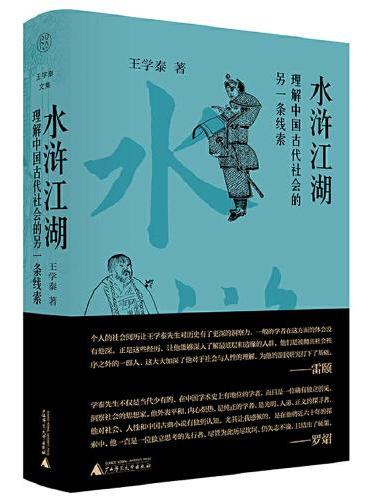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春秋大义:中国传统语境下的皇权与学术新版(小学《论语》,大学《春秋》代表中国精神的政治哲学至高圣典。得到近80万总订阅主理人熊逸代表作)
》
售價:HK$
96.8

《
女人们的谈话(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提名、最佳改编剧本奖 原著!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简直是《使女的故事》现实版!”)
》
售價:HK$
61.6

《
忧郁的秩序:亚洲移民与边境管控的全球化(共域世界史)
》
售價:HK$
140.8

《
一周一堂经济学课: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
》
售價:HK$
107.8

《
慢性胃炎的中医研究 胃
》
售價:HK$
65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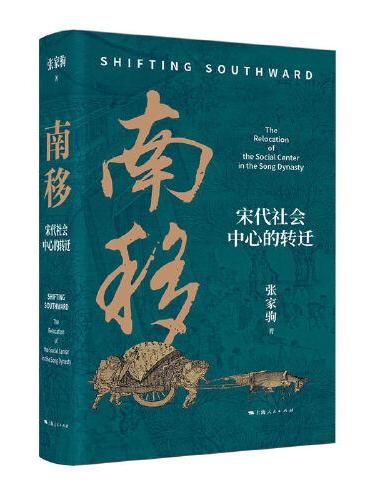
《
南移:宋代社会中心的转迁
》
售價:HK$
16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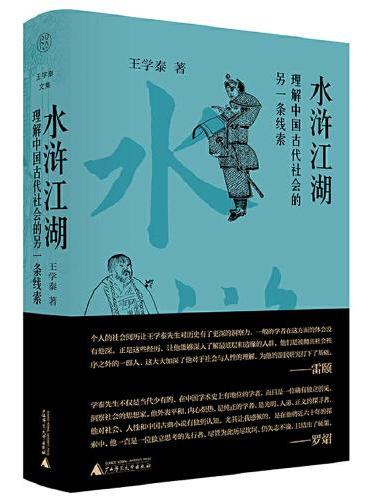
《
纯粹·水浒江湖: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另一条线索
》
售價:HK$
101.2

《
肌骨复健实践指南:运动损伤与慢性疼痛
》
售價:HK$
294.8
|
| 編輯推薦: |
|
《学游泳》是布克奖得主格雷厄姆斯威夫特历年来短篇小说合集。格雷厄姆是英国当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深受拉什迪、石黑一雄、约翰班维尔赞赏。《盗梦空间》《星际穿越》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自称受格雷厄姆斯威夫特影响最大,他是自己叙事艺术的导师。
|
| 內容簡介: |
|
《学游泳》以细润,深情,收放有度的文字,书写婚姻中无硝烟的战争,祖辈间的情感鸿沟,对真相的疑惧和战争留给人性的印痕。十一篇故事,都是对灵魂深度新的涉测。《学游泳》描绘平凡人内心世界的惊涛骇浪,揭示我们安之若素的生活背后的“真实生活”。翻开这些故事,如同突然拉开了一道通往地下室的门。
|
| 關於作者: |
格雷厄姆斯威夫特
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1949年生于伦敦。自幼热爱阅读,自学写作,发表过多部长短篇作品。1983年,小说《水之乡》为他赢得了布克奖提名,并摘得《卫报》小说奖。1996年,小说《杯酒留痕》力挫群雄,夺得当年的布克奖,从而奠定了他在英国文坛的重要地位。
|
| 目錄:
|
苏丹后宫
隧道
旅馆
霍夫梅尔羚羊
儿子
疑病症患者
加博尔
神表
克利夫埃奇
化学
学游泳
译后记
|
| 內容試閱:
|
旅馆
他们让我出院的那天,我逛了好长一会街。街上的行人看上去冷漠而伤感。我注意到每个人的脸上无不挂着劳累、恐惧和忧患的神情,而我似乎比他们优越,仿佛他们是区区侏儒,而我却挺拔魁梧,比他们看得更远。不过,这儿那儿偶尔也会冒出一些个子高大、目光锐利的人。这些人好像本事很大,好像随随便便就可以管人家,调遣人家,抚慰人家。
第二天,我如约回到了医院,去跟阿齐姆医生道别。他们放我出院的那天,阿齐姆医生被人请去出诊了。我对他说:“我想告诉您,我对您无微不至的关怀深表谢意,我对您和全体医务人员的工作钦佩之至。”他微微一笑,似乎非常高兴。我继续我的告别演说:“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我在哪儿犯了错。现在一切都一目了然了。你得做一个关爱他人的人,而不是一个被人关爱的人。就这么简单。” 然后我说:“我在这儿一直过得很愉快。”阿齐姆医生满面笑容。我离开时,他与我紧紧握手。那时我就知道,总有一天,我必须扮演一个像他那样慷慨好客、关爱他人的角色。
我母亲去世后不久,我就住了院,一住就是三个多月。警察把我抓了去,因为我在街上大嚷大叫,引得行人驻足围观。警察以为我喝醉了或者嗑了药。不过后来他们查明情况并非如此,就把我带到阿齐姆医生和他的同事们那儿。
说来也怪,当时我竟是被警察送到医院大门口的。怪就怪在给我所谓的“治疗”起先似乎与刑事审讯相差无几。我仿佛是个嫌疑犯。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为了避免麻烦,他们要我彻底坦白交待。医生们跟我玩起了小小的问答游戏(就像审问)。当我不能提供正确答案时,他们就会失望地长叹一声,给我拼命地注射镇静剂,然后等候下一轮提问。我不禁暗暗寻思,他们是否会在某个阶段采用更严酷、更狠毒的手段。
所以,当我说“实话相告,我曾经想害死我母亲”时,无论是他们还是我自己都如释重负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认为这并没有改变任何东西。我不过是说说而已。可是我的医生们似乎欣喜不已,开始替我忙开了。从那天起,我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信任我了,他们变得更友好了。而也是从那天起,我开始钦慕起他们。
只有一件事似乎令他们大失所望:当他们又追问“你为什么要害死她?难道你不爱她吗?”时,我无法给他们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是问题的第二部分使得我心烦意乱。一听到这个问题,我就情不自禁地生他们的气。我是非常爱母亲的,但是,我明白,假如我照实说,我肯定会越说越乱套。所以,我就干脆把往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得了:三年前,父亲撇下了母亲和我,我们娘儿俩就只好相依为命了。不过,我们的日子倒过得挺快活,我对父亲的去世甚至还暗暗窃喜呢(虽然我没有告诉他们这点)。等我稍微长大了点后,我就开始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觉得母亲想伤害我。我对她又怕又气。后来,这种感觉愈发强烈,我就巴望她早死。她倒真的死了。她是在大街上被一辆小汽车撞倒的。人家告诉我,那辆车行速极慢极慢,可她就给撞死了。我得赶到医院去辨认她。
接着,我的医生们又问道:“可是,假如你怕母亲,假如你怕她会伤害你,那么你干吗不离开她呢?”我没有回答。到了这个时候,我注射镇静剂了。
就这样,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们我到底为什么想要谋害母亲。不过,或许是我告诉他们的那点情况就够用了,因为,正如我所说的,我们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大大的改善。我们会常常谈论我的“问题”,好像我们是在议论一个局外人。我不再胡言乱语,不再大叫大嚷,不再因为去世的母亲而悲恸哭泣。我的责任医生阿齐姆告诉我,我的病情在逐步好转,我自己深有同感。
有一次,我对阿齐姆医生说:“我一直被禁闭在这儿——人们认为我精神失常——是由于我想谋害我母亲吗?是这么一回事吗?”
阿齐姆医生微微一笑,脸上的表情说明这种想法未免天真幼稚。“不是的。把你带到这儿来,并不是因为你想谋害你母亲,而是因为你对抱有这种意图感到内疚。”
我接过他的话头:“照您这么说,出路就在于心遂意顺喽?”
他又微微一笑。那是令人释然的一笑。
“没那么简单。人各有愿,人各有愿……”
随后的五六周时间——我至今依然认为这是我一生中最甜美的时光——我像任何大病初愈的人一样,开始了缓慢的疗养期,因为此时主疗程已结束。那时正值夏天,我久久地坐在医院的草坪上,观察其他病员,与阿齐姆医生交谈,思索那不可告人的心愿和负疚感。
我觉得世上没有一个人不抱有负疚感,而那负疚感永远是某种非分之福的标志。每个人的负疚感中,包孕着快乐;每张郁郁寡欢、自惭形秽的脸中,深藏着幸福。也许人们对此束手无策。然而,定会有人试图理解而不是责怪我们的负疚感,定会有地方供我们一吐隐藏心底的愿望,实现我们的非分梦想。总而言之,天底下总会有关爱。
就这样,我觉得这次住院真是三生有幸,为能结识阿齐姆医生和他的同事们感到非常自豪。我感到自己是一个体体面面、不胜荣幸的宾客——也许每个康复中的病人都有如此体会。所以也许就在那时,就在第一次跨出医院大门前,我的心中埋下了雄心壮志:终有一天,我要开一家旅馆。
可是千万别认为当初我跨出医院大门时,就已经胸有成竹——那时,我当然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一步步地努力,想法是慢慢成熟起来的。我用母亲遗留给我的钱买了一家小咖啡馆,苦心经营了多年——这家咖啡馆与无数其他的咖啡馆没什么不同。我很注重了解我的顾客,我要使他们感到他们可以向我畅所欲言,而我定会洗耳恭听。有些顾客对此十分赞赏,虽然也有些顾客不买我的账,后来再也没有回头光顾过。
也千万别认为在我出院那天与我的旅馆开张之日没有间隔多久,或认为在这期间我的人生也没有什么大的变故。我结婚了。我妻子帮我料理咖啡馆,她甚至把她的钱也投了进去。勿庸讳言,我们的婚姻不尽如人意,婚姻生活并不幸福。可我学会了对不幸采取一种客观稳妥的态度。我老婆——卡罗尔——常埋怨我,说我把她当孩子一样看待,说我对她摆出一副祖师爷的样子,说我总是居高临下地跟她讲话。可奇怪的是,我倒觉得情况恰恰相反。
我们离婚时,我就下定决心不再结婚了。我在环境优美的郊区买下一家新咖啡馆。咖啡馆上面有好几间房间,它们可用作客房。好长好长时间——直到它开始赢利——我几乎都是一个人单枪匹马上阵,真是辛苦得不得了。可我干得得心应手。我发现我有烹调、铺床、洗衣的天分。这一切是在与母亲相依为命的岁月中学会的。我认为我没有老婆并不感到孤独。在餐旅行业,你要招待客人,从来都不会感到孤独。过了些时日,我终于雇得起这一两个员工,这样我就可以逢单日抽出半天时间去给母亲上坟,去看望阿齐姆医生,但是获悉他因身体很差已退休,目前下落不明,让我深感悲伤。
多少岁月流逝而过。那是枯燥而繁忙的岁月。可我总是觉得我只是在等待,在等候时机。我要开一家旅馆的勃勃雄心正在成形。而且,我知道,总有一天,从我出院到拥有一家旅馆那长达三十多年的岁月会显得微不足道:那只不过是一种酝酿,只不过是两点间的一段旅程。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可知道——假如我还未把我的意思交待清楚——我心目中的旅馆并不仅仅追求一流的服务水准,并不仅仅提升一下大街上的咖啡馆和二流宾馆的层次。我是真心诚意这样想的。我对仅仅提供膳宿毫无兴致,尽管,天知道,我完全可以那样做。我想要的旅馆就像我以前入住过的医院,但不设医务部。我要开一家“开心”旅馆。
最后,经过等候、积蓄和搜寻,我终于找到了它。它坐落在河滨的一个西部乡村小镇,共有十二间卧房。原来的老板(他们都是当地人)似乎缺乏想象力,未能看到它隐藏的潜力。不出五年,我就把它改造成了一家憩息所。人们在夏冬两季来到此地。来干吗呢?我称之为“疗养探访”。许多客人都被这一用语所迷惑。我认为这家旅馆之所以红红火火,其中部分原因就在于它濒水临河。它面向河流,中间是一大片草坪,上面放着漆成白色的桌椅。置身于任何一个房间,你都能听到附近堰堤中的潺潺流水。人们喜欢与水亲近。这给他们一种心灵得到净化的感觉。
可是,在宜人的乡村小镇,有许许多多濒河的小旅馆。因此,仅仅这一切并不能解释为何我开的旅馆独具魅力。我依然认为它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魅力。我依然相信人们一跨进我的旅馆,马上就感觉到自己沐浴在关爱之中。不知为何,我知道在那“远方”,在他们原来的生活中,有各种各样他们所不愿承认和极力想逃避的事情——于心有愧的事情。而且,不知为何,他们也知道我知道这点,他们也知道我理解他们,知道我不会责备或非难他们。而且,与此同时,我还给他们一两周的逍遥解脱。当我与他们倾心交谈时——因为我总是千方百计地想使客人开口说话——他们有时会嘻嘻哈哈地笑谈某些事,而要是以前,我敢担保,他们谈起那些事来准会哭泣,或者压根儿就不敢声张。这种坦率而彻底宽容的气氛是治疗的一部分。
诚然,有些客人不想开口,对一切都守口如瓶。不过,有什么事都显露在脸上。在我的旅馆中,人们总是笑容满面,即使他们刚入住时脸上挂满了疲惫、缄默的表情。假如这一切还不足以佐证,那我只需开列一下回头客的尊姓大名(他们有时一年内要数度光顾),或者读几封客人写给我本人的信誓旦旦的信函。他们说他们在旅馆里过得何等的愉快。我不想隐瞒,这些人中,有许多都是有钱有势的头面人物,但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都感激我,都对我一片诚心,都赞赏我的工作。
我还要提一下那一类特殊的宾客。对他们我总是给予特别的照料和悉心的服务。对他们而言,我们旅馆俨然就是他们的罪过——还有他们的欢乐——的理想场所。我指的是那成双成对的男女——一对对情人们。他们一般不预订客房,或者就在到达前才预订,然后大笔一挥签名入住。签的名五花八门,什么史密斯夫妇、琼斯夫妇、基尔罗伊夫妇,等等。我从来不让他们感到丝毫的不受欢迎。恰恰相反,我以各种微妙的方式让他们明白:虽然我心知肚明,但我允许他们——甚至祈神保佑他们——耍一下小花招。所以,当我把他们引到他们房间时,仿佛在默默地说:“进去吧,祝愿你们心想事成,祝愿你们品尝到甜蜜的禁果。”我衷心希望他们在我的旅馆房间里,在堰水的潺潺声中,真正找到他们秘密的极乐。
我的其他客人——我指的是那些体体面面结了婚的或未婚的宾客——即使发现有这些偷鸡摸狗的男女混迹其中,也没有心绪烦乱。他们才不呢。他们要么假装没看见,要么眨眼而对——有时真的眨眼——仿佛从他人中间得到了乐趣,仿佛他们自己从隔壁房间里的勾当中得到了发泄,得到了解脱,而理由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于心有愧的。
你看,我的旅馆与众多的乡村旅馆不一样,丝毫不古板自大。在我的旅馆里,一切都包容得下,一切都获得宽恕。
这一切持续了许多年。我的客人们坐在餐厅里或遮阳伞下的白色桌子旁。他们望着河水起着涟漪向前流淌;他们聚餐豪饮;他们散步垂钓;他们到镇上觅购古董;他们春风满面,知道自己得到精心照料;他们给我来函,向我道谢,说他们以后会再度光临等等。
直到有一天,一对与众不同的男女登记入住,情况才有了变化。
他们并不是明显的与众不同:那男的四十多岁,那女孩子浓妆艳抹,年纪轻得多,大概才十几岁——他们入住包房的目的太昭然若揭了。可这一点也不是他们区别于其他男男女女的地方,因为其他男女来此的目的也无非如此。与初次踏进大厅的其他宾客相比,一下子吸引我的是他们的脸上布满了异常警惕、紧张、严肃的神情。我在心中默念道,这两张脸明天一定会漾出笑容。我把他们引到了十一号房间。
可是他们从来没有漾出笑容,他们的表情从来没有变得轻松起来。那是使我忧虑的第一件事。而且,他们故意避开其他客人,长时间地闭门不出,在人最少的时候才在最偏僻的桌子旁就餐,这一切反而使得他们的忧郁更加引人注目。
我想,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我怎么才能帮助他们呢?到了第三天早上,当他们正在一间几乎无人的餐厅吃早饭时,我的一个正在喝早咖啡的女服务员把我拉到吧台的一边,对我说:“仔细瞧那个女孩。”
这要小心谨慎地做才行,而且还得借助于吧台后面的镜子才瞧得清,可是我觉得从我自己的观察中已知道这女服务员到底是什么意思。因此,我耸了耸肩,轻声地对她说,话中分明含有一丝对她好奇心的责怪:“她极力摆出一副老成样,可实际年龄要小得多。”
我凝神注视着他们。我默默无语。女服务员见状说:“我以一赔十跟你打赌,那男的是女孩子的父亲。”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看不出来——或不相信她的话——要知道,我可是花了如此多的时间对客人察言观色;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向我的女服务员回敬了一句“胡说八道”;我不知道为什么从那一刻起我就开始感到在我自己的旅馆里处处埋伏着危险和不安。女服务员一般都是宽容他人、挺想得开的人——她们得保住自己的那份工作——可那个女服务员却带着责备的眼神看着我,好像我没有尽心尽职似的,好像假如我不采取点措施,她就会拿起法律武器似的。
而且,不仅是女服务员和我的其他职员,客人们也是如此。人们必定开始了飞流短长。他们用疑惑、探究的目光望着我,似乎他们也期望我采取果断措施。可是,我仍然看不出他们是父女。我眼中只有这对夫妇,他们在我那开心旅馆里显得那么孤凄而无法慰藉。我很想跟他们谈谈,很想引他们开口。然而,不知怎的,我没了平常的那份本领,而且我心里清楚,假如我真的友善地与他们交谈,我必定招众人之怨。我看着他们那毫无笑容的脸,而与此同时,我慢慢地发觉其他客人脸上的笑容也在渐渐地随之消失。
他们的笑容在渐渐地消失。仿佛受到了传染,笑容一下子变成了责难的目光。可是我还是不明就里。有一天早晨,罗素夫妇提着手提箱下楼来,要求退房结账(他们已多次光临我的旅馆,按订期还得再住四天)。我问他们为何提前离店,他们满脸怀疑地瞪着我。而罗素夫妇一走,仿佛是向别人发出了一个信号。有一大家子带着孩子走了;来这儿钓鱼的柯蒂斯少校走了。他们走时,嘴里还嘟哝着什么“太肮脏了”,“叫警察来”。还有一对夫妇扬言:“他们不走,我们走。”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我煞费苦心,尽力关爱的这帮人原来根本不需要关爱。他们来时一个个满脸愧疚,想在这儿图个良心的安耽,想舒展皱眉、绽开笑容,可他们其实根本没有亏心不安。他们不需要开心。他们光临此地只是想享受一下乡村的空气和美味佳肴。他们只想图个清静。是这些才使他们满面春风的。而混杂于其间的有几位露水鸳鸯——老板与秘书调情,丈夫背着妻子偷欢。我为他们尽心尽力,而如今他们却要弃我而去了。
一想到这儿,我就不再对十一号房间的那一对感到关切。我反而对他们生起气来。这下我终于明白了——实际上我一直心知肚明。十一号房间的那一对是父女关系。这是明摆着的。他们居然到我的旅馆里同床共寝,把我的客人——我的宝贝客人——统统赶跑了。我非得叫他们俩走人不可。
我手下的职员——其中有几个似乎也打算一走了之——看到我要动真格了,就围了过来。那是在那一对人住进我家旅馆的第五天早上。我身为负责人,不得不向他们开口摊牌了。女服务员已经告诉过我,每天早上他们下楼来吃早饭前(从来没有早于九点半),那个女孩子都要在楼梯底部过道的浴室里洗澡(唉,并不是所有房间都有专用浴室的),而这时那个男的就待在房间里。这真是面对他的最佳时机。
大约九点钟光景,女服务员告诉我浴室已经有人在用了。我不知道我到底该向他说些什么。我草草地准备了几种开场白,如“你们必须马上离店。我想你们知道为什么”或“你们必须马上离店。难道你们不明白你们在糟蹋我的生意吗?”可是,我觉得,说完这几句话后我该说些什么为好就浑沌一片了。我窝了一肚子火。我奔上楼,来到十一号房间。我本想大声地敲门,可情急之下就免去了礼节,径自推开了门。不用说,我当然期望见到那个男的。可是,那天早上他们改变了平时的洗澡惯例,因为映入我眼帘的是那个女孩子。他的女儿。她身着一件缀有粉红色小花的白睡袍坐在梳妆台前。她并没有浓妆艳抹;也许她此刻正准备上妆呢。她这一副架势,活像一个幼童坐在一架巨大的钢琴前,显得非常滑稽可笑。你可知道,她绝对不可能超过十五岁。有那么一瞬间,她肯定误以为我是她父亲,因为当她抬起头来时,我发现一朵乌云倏地掠过那张清朗平和的脸庞——刹那间,我仿佛看到她没有了在旅馆里常常挂在脸上的紧张神情。我默默无语,因为我无法言语。我仔细地端详着那张脸孔。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羞赧,如此惊惶的脸。然而,在那张脸的深处,在那万般无奈的脸的深处,我似乎看到了喜悦。它犹如一口黑咕隆咚的井底中闪烁的静水,它宛若一段久久掩藏于心田的美丽记忆。就那么一瞬间,我想我说不定会伸出双手,扼住那女孩的脖颈,把她活活掐死。一扇窗户敞开着,我可以听到堰水的潺潺声。
然后,我走下楼,来到办公室,关上门,泪水夺眶而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