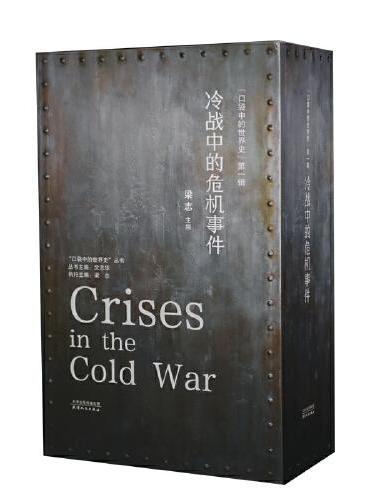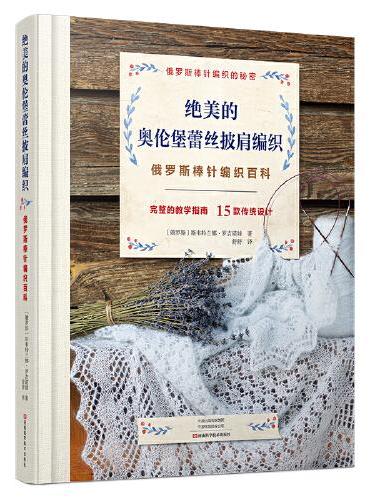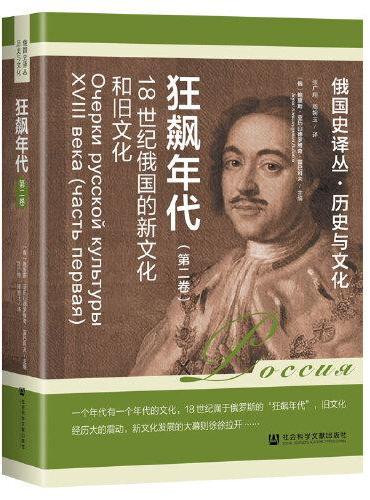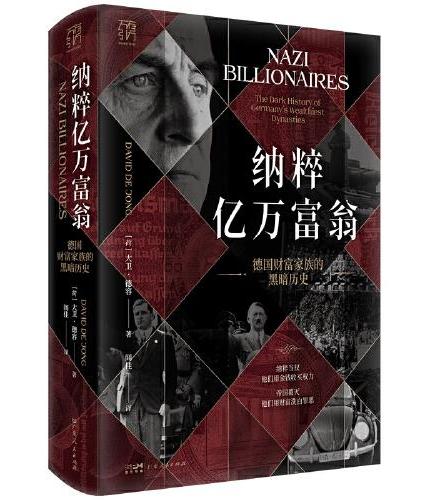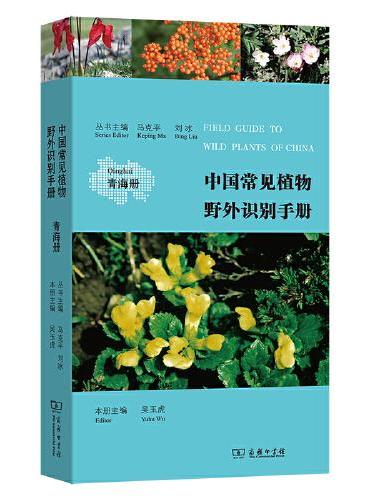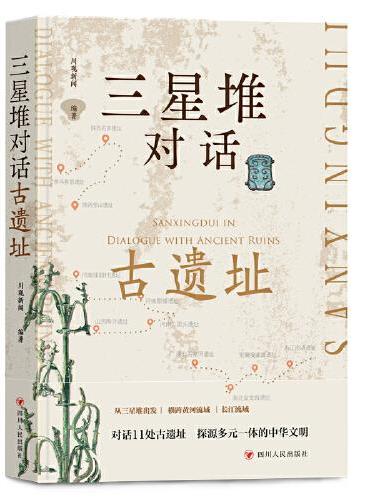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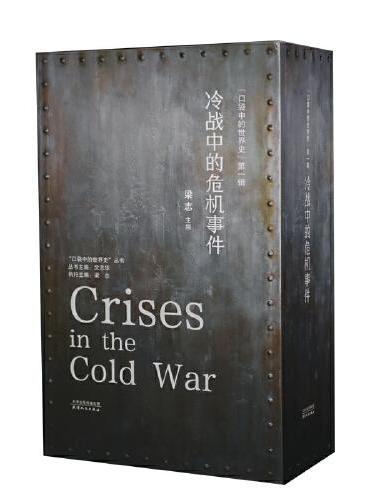
《
“口袋中的世界史”第一辑·冷战中的危机事件
》
售價:HK$
2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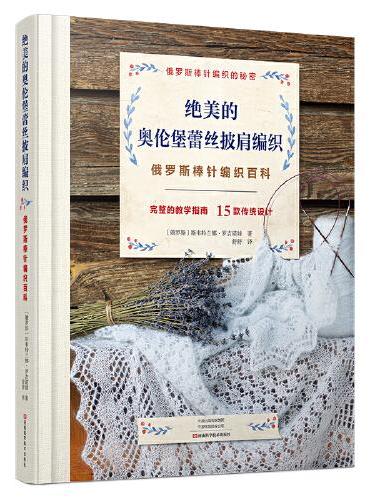
《
绝美的奥伦堡蕾丝披肩编织
》
售價:HK$
18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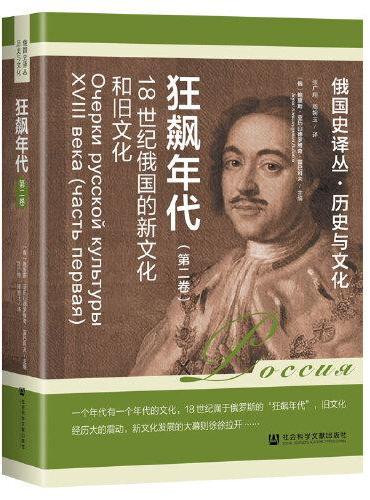
《
狂飙年代:18世纪俄国的新文化和旧文化(第二卷)
》
售價:HK$
17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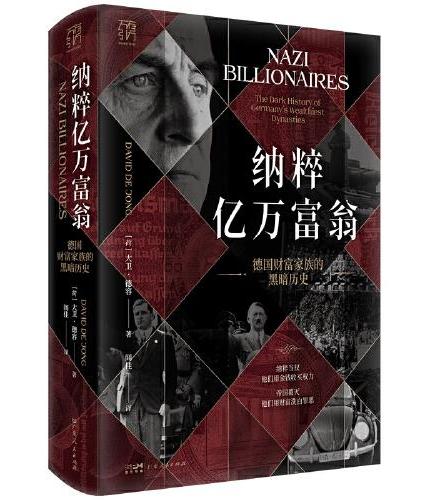
《
万有引力书系 纳粹亿万富翁 德国财富家族的黑暗历史
》
售價:HK$
1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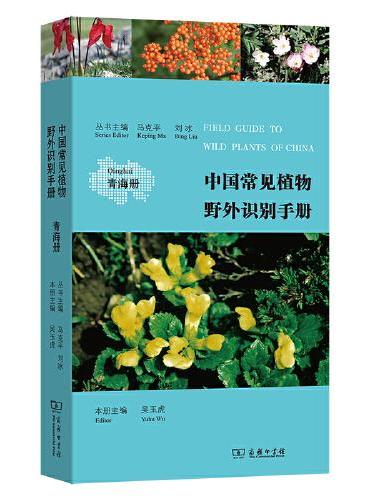
《
中国常见植物野外识别手册:青海册
》
售價:HK$
7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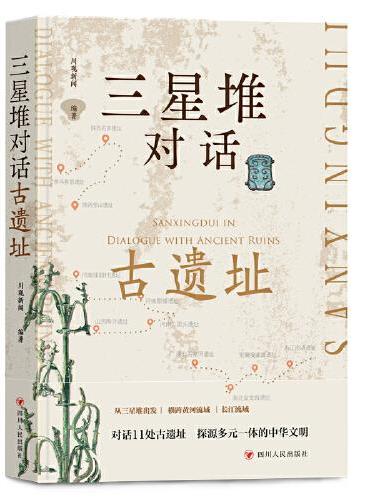
《
三星堆对话古遗址(从三星堆出发,横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对话11处古遗址,探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
售價:HK$
89.7

《
迷人的化学(迷人的科学丛书)
》
售價:HK$
147.2

《
宋代冠服图志(详尽展示宋代各类冠服 精美插图 考据严谨 细节丰富)
》
售價:HK$
87.4
|
| 編輯推薦: |
《时间的旅人》系台湾知名作家张曼娟2014年新作,着眼于“旅行”这个火热的话题,将这些年走过的许多国家和城市写进作品中,从小处着手,记录旅行中的见闻和感受。细腻的笔触,充满柔情,字字直抵人心。
这是一部充满人文关怀的作品,细细品读,你能感受到作者对每个地方每个人生阶段的一段情,收获对生活和生命的思考与感悟。那是曼娟老师经过时间洗礼所沉淀下来的成熟、从容与睿智,闪烁着熠熠光辉。
|
| 內容簡介: |
她到上海裁制衣装,寻回了丢失的童年碎片;
她到济南吃炒全鸡,吃到一整盘澎湃热切的人情;
她到樱花纷飞的日本,决意放慢脚步,慢得就像要在那里天长地久;
她到香港,化作一只鹰,展翅飞翔在海岸的城邦,成为美的发现者。
她去马告数神木,去日月潭骑脚踏车,去旧书店遇见转世的爱情,去童年时光跟洋娃娃诉说久远的心事……
她是张曼娟,一个永恒的旅人。这一次,她要陪你走过漫漫时光的千山万水,一边前行,一边回盼,在每一片回忆的风景里努力修补自己。
|
| 關於作者: |
|
张曼娟,台湾著名女作家,东吴大学文学博士,曾获教育部“文艺创作”小说第一名;中华文学散文奖第一名及中兴文艺奖章。1985年以《海水正蓝》点亮无数人心中湛蓝深邃的海洋。20余年间,出版多部小说、散文作品,创下耀眼的销售佳绩。2005年成立“张曼娟小学堂”,对语文教育和经典文学普及颇有贡献。多年以来,在她心中有一个“爱情私塾”,等待爱的,失去爱的,都在其中得到救赎。2014年,她带着“时间的旅人”来与你一起畅谈“远行”的快乐。代表作有《海水正蓝》《笑拈梅花》《此物最相思》《人间好时节》等。
|
| 目錄:
|
之一
到上海裁新衣去
到济南炒全鸡去
到日月潭骑车去
到白骨找温泉去
到樱国过生活去
到马告数神木去
到童年夹娃娃去
到旧书店转世去
到世博会排队去
到英伦当行人去
到黄浦江做梦去
到首尔庆中秋去
到神宫看迁徙去
到香港提灯笼去
之二
当两片海洋交汇
意念已经抵达
鹰的城邦
一歌一赋,春天脚步
此城·彼城
在沙漠种花
之三
给爸爸的情书
他们都说我像你
给妈妈的童话
六岁的大饥荒
|
| 內容試閱:
|
时间的旅人
通往未来的那条路
我走在那条路上,两旁樱花繁盛茂密地绽放着,因为承载了太多重量,树的枝丫微微倾垂,仿佛依恋着土地的温度。行走在土地上的我们,并不知道土地里的温度是怎样的,但,植物知道。
一棵树知道何时应该休眠,何时应该苏醒,何时应该奋力开花,何时应该结实累累……一棵树知道的,关于生命的规律,或许比我们更深刻。
树与时间订下了盟约,彼此都不违背,安静地信守。于是,在花开时,它不会得意忘形,狂妄自大;在落叶萧索时,它依然昂然伫立,不致消沉。不管荣茂或枯萎,都是时间的意志。
这是第二次,我走在那条路上。头一次是秋冬之际,领着我来的朋友说:“如果你不忌讳的话,我要带你去看个美丽的地方。”为了领略美丽,我是无所忌讳的,就这样,我们来到了谷中灵园。
灵园,是我们每个人最终的去处,是殊途同归的未来。因为太惧怕,我们不敢想象,甚至连靠近都以为不祥。
这些年来,与我的生命深深牵连的人,一个一个迈向了那个未来,我愈来愈不觉得恐惧,甚至有一点向往,我所爱的那些人,出发之后,去到了哪里?在做些什么呢?他们好像分别从我生命里取走了一小片,抵达远方,而我最后的出发与抵达,才能完整地拼凑我自己。
我与灵园初次见面,高大的树木满是枯索之气,许多壮丽的大型碑石指向天空,以一种艺术的方式,标示出逝者的人生索引,有些写得满满的,有些只是几行排句。我被它的规模与诗意震撼,死亡,可以这么庄严,这么瑰丽。
我站在巨型石碑前,努力辨识汉字,试图了解一个陌生人。
如果我们愿意多一点想象,想象未来墓志铭上会镌刻哪些字,或许,那些拼了命想争取的,突然都不重要了;在心里纠结许多年的怨愤不平,突然都一笑置之了。我常觉得我们的烦恼和焦躁,都是对未来缺乏想象的缘故。
选择了春天樱花盛放的季节,执意再一次造访,想看看传说中夹道怒放的樱花,该有多美。
“如果你们觉得忌讳,不用跟我一起去,但我是一定要去的。”我对同行的游伴说。
结果,没有一个人忌讳,大家都想看看开满樱花的灵园,是什么模样?我发现能成为旅伴的人,不管在什么样的旅途中,一起冒险、一起跋涉、一起欢笑,必然都有些类似的生命特质与情调。
对我来说,是旧地重游了,但是,依然被眼前的景象震慑。
那时已是落樱时节,一阵风过,小巧轻盈如指甲片的花瓣便细雪般地翩然飞舞,引起阵阵欢呼。我忍不住伸手去触摸,啊,是温暖柔软的樱花雪啊。我站立片刻,肩膀发际便留下一片片落瓣。“拂了一身还满”,李后主身上的是落梅不是落樱,但他是否也像我这样,有点小小的苦恼和疼惜,该把这些情意缠绵的落花怎么办呢?
许多落花被吹进一旁水槽里,前夜一场大雨,浸泡润湿着它们,阳光下闪动粉色光芒,宛如一个盛装粉晶和宝石的聚宝盆。是樱花前世的回忆吧,那些不肯忘记的回忆,都有着珠宝的贵重。
在灵园主要通路的樱花道上,有背着书包跑过的小孩,有拉着菜篮车的主妇,有骑着脚踏车的悠闲男子,有手牵手的年轻爱侣,穿越一个个安息之地,过着寻常的生活。也有像我们这样专程前来的旅人,在其间穿梭、跳跃、取景,拍完合照拍独照,将落樱缤纷的灵园当成游乐场,享受活着自在行走的乐趣。
我走在过去,走在现在,也走在未来的路上。
曾经以为旅行是一场空间的移动,渐渐地我明白,旅行也好,人生也好,其实都是时间的移动,我们只是时间的旅人,听凭时间的意志穿越。
这几年我一直在旅行,也常常重游旧地,与我做伴的都是比我年轻的朋友,有时我会回忆起某条街口的小店,或是某座公园里的喷水池,或是某个市集的开放时间,同行旅伴便很诧异地问:“你怎么知道?”不过是偶尔浮现的记忆啊。而在人生道途中,我有时也能准确指出某些事的发展,某些人的反应,某些心情的幽微与转折,身边的朋友很诧异地问:“你怎么知道?”不过是中年的历练与洞明啊。
中年以后,对我而言不是久别重逢,而是旧地重游。
值得庆幸的是,每一次的旧地重游,我总能保持着雀跃与好奇,充满热情地意欲探索更多的未知,旅行也好,人生也罢,总是有着许多未临之境,散发强烈诱惑。
我是一个禁不起诱惑的人,因此,2011年发生了一段小小的公职之旅。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进入公务员体系,却是因为香港,因为推广台湾文化,两项难以抗拒的诱因,我在香港工作了十个月。那当然是一段必须用特别色标记起来的日子,我陪伴着新闻局走进历史,见证了香港人的集体意识,在维多利亚港边的住处阳台上,看过两场华丽的烟花,也看过好多次的雾锁港岛。
我认为自己不是误闯丛林的小白兔,而是梦游仙境的爱丽丝,最终,找到了回家的路。
中年以后,我的步伐变慢了,喜欢散步更甚于赶路。想把经过生命的风景看得仔细些,把身边的美好多保留一些,却免不了忧伤的告别。
当我的忧伤太沉重,便让自己回到起点。
回到生命的起点,回到每场缘分的初相遇,太多的偶然与选择,有些因为时间的安排,有些则是我们自己的一念之间。
回到起点,有的不再是遗憾,而是感激。感激与我同行的人们,感激许多年来一直阅读着我的你。在时间的领地,我们彼此相伴,已经走了这么久,从来不孤单。
让我们也订下盟约,就像树与时间始终信守。
通往未来的那条路,不管是风和日丽,或是雨雪交加,都要怀抱信心向前走。
在沙漠种花
冬天里年迈的父母亲从台湾来,我陪着他们在楼下的商场散步,逛上一圈得走一个多小时,不必风吹日晒雨淋,也不必担心寒流的冷锋,他们在恒温、安全、舒适的环境中进行早起的晨运。而后又在有机超市购买蔬菜水果,回家料理。冬日的阳光是很和煦的,浑身酸痛的父亲常临窗而坐,晒足一两个小时的太阳,他的酸痛竟然不药而愈,身体硬朗了,心情也开朗了。
父亲和母亲常隔着一片海,望向港岛,我的办公大楼,看着日影退去,灯光燃亮,差不多是下班的时候了,于是,进厨房去准备晚餐。
有一天,海上起了点雾,我要出门上班时,父亲站在窗前望着我的办公大楼,对我说:“常常我在这里看你上班的地方,总觉得好像一个教堂,尤其是在黄昏或是起雾的时候。”我站在他身边,与他并肩,他一辈子都是个低阶公务员,劳碌地工作,任劳任怨又认命,一方面负担着养家的重担,一方面又把贡献国家社会的使命放在心上。“你啊,每天去上班都要有一种神圣的心情呀。”我的心里震动了一下,没表现出来,只是轻声回答:“我会的,请放心吧。”几天之后,遇见一个香港媒体,正好谈到我的办公大楼,说顶楼就是一间教堂呢,常有人在里面做礼拜。我的心又震动了一下,老人家原来是有点神通的。
在香港担任公职的时间虽然短暂,我却像个过动儿似的,规划着一项又一项文化推广活动,还把这些活动带进了大学与小学,就像个殷勤的农夫,埋着头种下一株又一株小树苗。
“你不觉得香港是个文化沙漠吗?”香港的媒体不只一次这样问我,我说我不觉得,因为我真的看见许多香港有心人,非常努力地开垦出一片又一片绿洲,他们的努力应该获得更多的鼓励与掌声,不该被忽视的。报上刊登了我的话语,却画了一幅图讥讽我,画中的我匍匐在一片沙漠上,却还掩耳盗铃地说,香港不是沙漠。
了解我的朋友为我感到不值与疼惜,我看着那幅画却很乐观地想,我是在沙漠种花的人呀,若不匍匐又怎能栽种?我依然坚持香港并不是文化沙漠,因我曾置身绿洲中,吹过清凉的风;因我曾在沙漠种花,带着满袖的花香离开。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