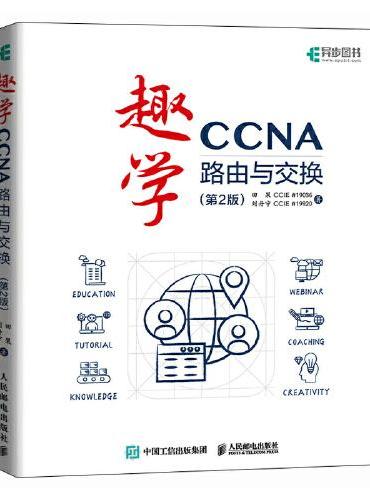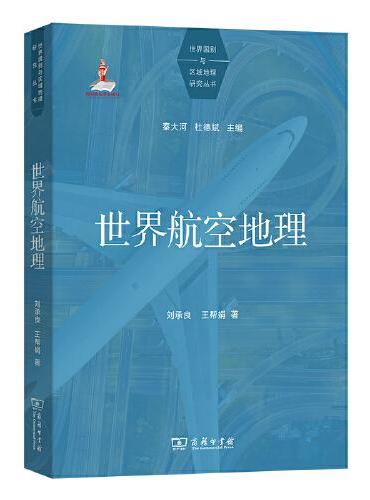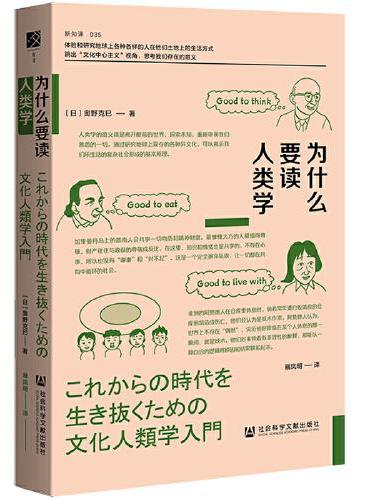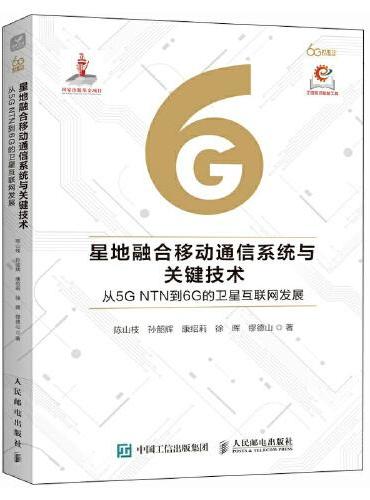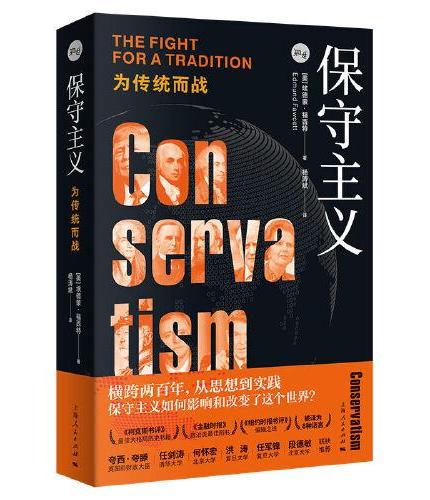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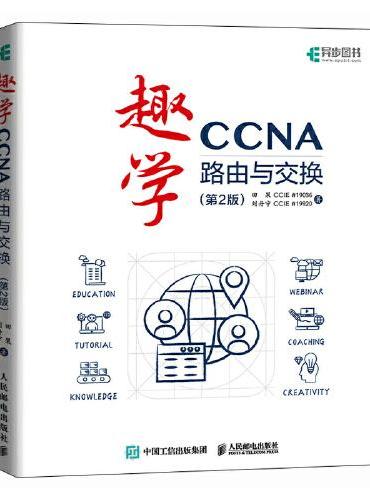
《
趣学CCNA——路由与交换(第2版)
》
售價:HK$
1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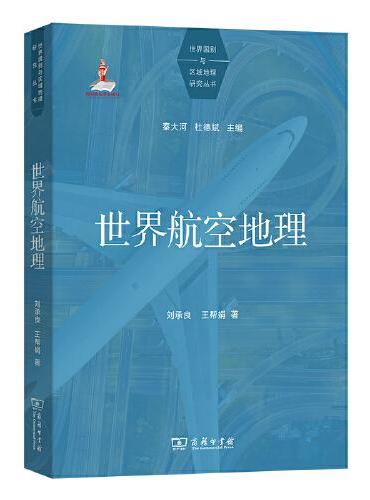
《
世界航空地理(世界国别与区域地理研究丛书)
》
售價:HK$
244.2

《
学术的中心:英法德美
》
售價:HK$
8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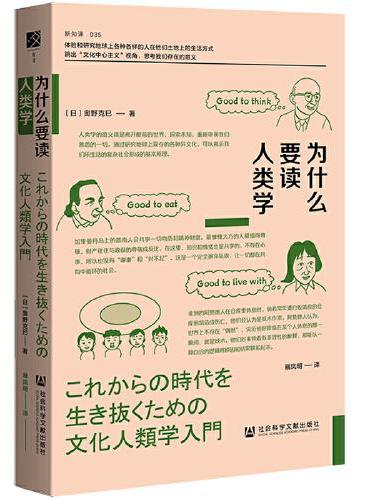
《
为什么要读人类学
》
售價:HK$
77.3

《
井邑无衣冠 : 地方视野下的唐代精英与社会
》
售價:HK$
9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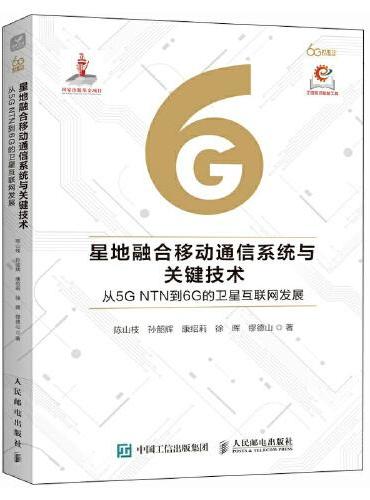
《
星地融合移动通信系统与关键技术从5G NTN到6G的卫星互联网发展
》
售價:HK$
212.6

《
妈妈,你好吗?(一封写给妈妈的“控诉”信,日本绘本奖作品)
》
售價:HK$
4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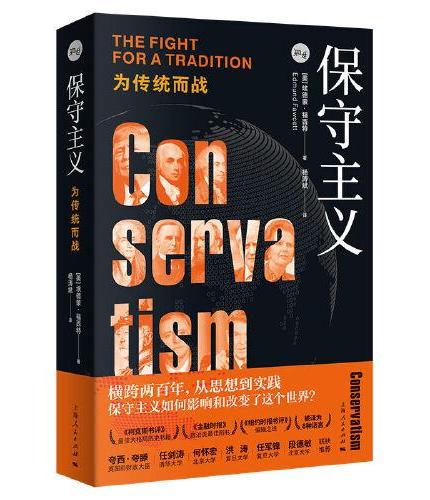
《
保守主义:为传统而战
》
售價:HK$
154.6
|
| 編輯推薦: |
《南方有令秧》是笛安创作的第一部古代背景的长篇小说,也是她的突破之作,在保有笛安一切写作优点的同时,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突破。与其他现代小说截然不同的是,笛安在故事中完整的还原了古人的价值观,创造出那些在我们完全陌生的价值观里树立自己的行为准则的人物们。因为尊重历史,通读历史书籍的笛安将人物的说话语句,甚至描写的一个人物衣着装饰都透过最具体的细节一点一滴的丰满于想象力的羽翼之上,正如笛安所说“所谓历史,既不是我们都念过的那些课本里冷冰冰的‘压迫与被压迫’,也不是随处可见的‘穿越戏’里那些完全用现代人的趣味解释甚至消费古人的桥段。”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部突破之作确是笛安写作生涯的里程碑式作品。
|
| 內容簡介: |
|
明朝万历年间,徽州商户人家的女儿令秧,在自己十六岁那一年嫁作休宁唐家的填房夫人,唐氏一族是徽州数一数二的富户,丈夫唐简虽比令秧大上几轮但中过进士,入过翰林院。然而在令秧成为唐家夫人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唐简便因意外离世。二十九年没有出过烈妇的唐氏一族,表面上为着光耀门楣,暗里觊觎朝廷旌表贞节烈妇的好处,像灾民求雨那样期盼令秧成为烈女,他们用尽各种手段诱导令秧殉夫,为了生存,还是天真少女的令秧踏上了艰难而又凶险的烈妇之路……
|
| 關於作者: |
|
笛安,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人气和实力并存的作家,《文艺风赏》杂志主编,著名作家李锐和蒋韵之女,新生代畅销新锐,她身上同时笼罩着市场和奖项的光环,一方面她以令其他同龄作家难以望其项背的销量,成功囊括了无数销售排行榜和商业销量榜单的显赫位置,同时,她又获得了包括苏童、刘恒、安波舜等等前辈作家、评论家的由衷褒奖,她的小说屡次登上殿堂级的文学杂志《收获》,成为全国媒体热捧的宠儿。她当之无愧是最被主流接受和推崇的80后作家,纯文学的代表人物。
|
| 目錄:
|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23
第三章 059
第四章 093
第五章 127
第六章 151
第七章 175
第八章 205
第九章 229
第十章 251
第十一章 281
第十二章 311
|
| 內容試閱:
|
第一章
01
明,万历十七年。多年以后的人们会说那是公元1589 年。只不过令秧自己,却是绝对没机会知道,她是1589 年的夏天出嫁的。不知道记忆有没有出错,似乎那年,芒种过了没几天,端午就到了。
她站在绣楼上,关上窗,窗外全是绿意,绿色本身散着好闻的气味。在这个绣楼上住了两年多,她关窗子的时候养成一个习惯,窗子上的镂空木雕是喜鹊报春,角落里有朵花因为遇着了窗棂,只刻了一半,她手指总会轻轻地在那半朵花上扫一扫,木工活儿做得不算精细,原本该有花蕊的,可是因为反正是半朵,做这窗户的工匠就连花蕊也省去了,就只有那三两瓣花瓣,她也不知为什么,就是看着它,觉得它可怜。她其实也没多少机会,能站在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好好看看她的绣楼,看看这粉壁,黛瓦,马头墙——不过她倒不觉得这有什么要紧,事实上她还庆幸,这两三年能住到绣楼上去,一年没几次出门的机会——因为她不大喜欢走路,小时候缠足那几年,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点岔子,她的右脚直到今天,站久了都会痛,而且那痛不是隐隐的酸疼,就像是有根骨头总是固执地刺着肉。按说不该的,眼看着都十六岁,别人家的女儿早就习惯了,那些大家都还没许人家,成天一起玩的日子里,她们都可以轻盈灵巧地追逐嬉戏,还放风筝——令秧觉得,既然跟人家不一样,总归是自己的错处。
她对着镜子散开了头发。两个属于姑娘的丫髻,一左一右,乖巧地耸在耳朵上方,可是日子久了,再乖巧也觉得呆板,即使她非常用心地在每个发髻边缘盘了细细的一圈麻花辫,也觉得自己怎么看怎么像只蛾子。她知道自己的头发很美,浓密,漆黑,像房檐上的冰凌突然就融化了,拢在手上厚实的一捧,从小,嫂子在帮她梳头的时候都会看似淡淡地说:“发丝硬,命也硬,嫁不到好人家。” 她也听得出那是嫉恨。
她耐心地将头发篦至蓬松,一股一股地,盘在头顶,小心地试图弄成花瓣的形状。想给自己梳个牡丹头——女人出嫁以后才可以梳这样的发髻,她就是想偷偷看看,这样的自己,究竟好不好看——看看就好,她悄悄在心里跟自己说。去年冬天,她的海棠表姐嫁人了,嫁给了她们共同的表哥,正月里,表哥带着海棠姐回来娘家,海棠姐的模样居然震住了她,她第一次看见海棠姐的头发全部盘在了头顶,洁白的脖颈露出来,整个人都修长了,头发梳成了一朵简单的花,就因为这花是头发缠出来的,有种说不出的妖娆。初为人妇的海棠姐穿着一件胭脂色的棉褙子,着石青色六个褶的马面裙,端坐在那儿,不像以前那么多话,一只手安然地搭在炕几上,笑起来的样子也变了,眼睛里有股水波一不留神就蔓延到了头上那朵牡丹花层层叠叠的花瓣里去。令秧想告诉她,她梳牡丹髻的样子真是好看,可是话到了嘴边,却成了:“海棠姐姐怎么胖了些?”
还好海棠姐一向心宽,不在乎她语气里的讽刺,只是慢慢待嘴里的糖莲子吞下去了,才笑道:“一入冬便会胖,我素来不都是这样么。”一句“素来这样”,又将令秧堵得接不上话。是的,海棠姐现在这样,曾经,少女的时候还是这样,一句简简单单,像是叹着气一样说出口的“素来”,告诉令秧,海棠已经是个有过去有历史的妇人,而令秧什么都不是。
所以令秧觉得,一定都是因为那个牡丹髻。
只不过,镜子里的那个自己,即使换了发式,看起来,也并没有如海棠姐那般,换了一个人。不过她来不及沮丧了,门外那道狭窄的木楼梯吱嘎作响,除了嫂子不可能是别人。她急慌慌地把差强人意的发髻拆开,罩上搭在床沿上的那件水田衣——那是嫂子拿零碎的布料拼着缝起来的,杂色斑斓,她不知道,其实这种每家女儿都有的水田衣穿在她身上,不知为何就更跳脱。门开了,她闻得出嫂子身上的味道。“还没梳洗?” 嫂子问。“好了,就差梳头。” 她一直都有点怕嫂子,也不是怕,说不清,总觉得嫂子站在她身边的时候,她们俩都成了摆错地方的家具——不能说不在自己家里,可总觉得有什么地方看着硌眼睛。嫂子淡淡地说:“记着帮我把剩下的那几个帐子补好,还有爹屋里那张罗汉床上用的单子也该……” 她答:“记着呢。” 嫂子皱了皱眉头——她不用看嫂子的脸,只消听着她的语气便知道她在皱眉头。“我还没说完呢。你记着什么了?” 她不吭声,重新把满头长发分成两半,开始盘左边,她知道,耐心些等这阵沉寂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果然,嫂子叹了口气:“等你嫁过去了,讲话难道也这么莽撞?你婆婆跟你说话,你也半中间打断说你记着了,人家只怕会笑话咱们的家教。” 天井里远远地传来一些此起彼伏的说话声,听上去像是佃户家的女人来了,嫂子急急地要去推门——她的一天比令秧的要忙太多了,临走,丢下一句:“要下雨了,天还是有点凉,再多穿一件。”
令秧的娘死得早,这些年来,嫂子就是家里挑大梁的女人。令秧有个年长自己十三岁的哥哥,算命的说,哥哥命硬,克兄弟姐妹——不知道准不准,不过在哥哥出生后的十多年里,娘又生过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都是在还没出周岁的时候就夭折了;还怀上过一个不知是男是女的胎儿,同样没留住——只有令秧安然懵懂地长大了,破了算命先生的咒。令秧是爹娘的宝贝,尤其是娘,看着令秧的时候总有种谢天谢地的感激。她给了令秧生命,可是令秧终结了她对生命的恐惧。病入膏肓的时候,娘甚至不再那么怕死。她只是平静地把令秧的小手放在嫂子手里,用力地对嫂子说:“照顾她,千万……” 嫂子知道这句话的轻重,恭顺地回答:“我知道。” ——嫂子不也一样没等婆婆说完话就答应了么?娘在那种时候,哪想得起来嘲笑嫂子的家教?嫂子就是喜欢把婆家描述得像阴曹地府一样,吓唬令秧——其实嫂子现在在家里管事儿,还不是说一不二——这个婆家还有个像令秧这样,有事没事会被她挤对两句的小姑子——能坏到哪里去了?
令秧也知道,一个姑娘家,总想象婆家是不害臊的。如果让任何人知道了这种想象,就更是该死了。可是除了这种想象,令秧实在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可以做。若是像海棠姐姐那样识得几个字,还能偷偷看点书,或许好些——有一年,表哥发了水痘,不能去族学里上学,家里只好请了先生来教——海棠姐姐早在刚出生的时候就得过水痘了,那时候他们都才六七岁,且表哥一个人总是哭闹着不肯念书,所以大人们就叫海棠姐姐去陪表哥玩,海棠就这样跟着表哥学了认字——表哥在家里一关就是半年,半年过去了,大人们也就默契地订下了他和海棠姐的婚事。
要是令秧很小的时候也出过水痘就好了。
要是令秧能和海棠姐姐一起嫁给表哥,就好了。
这件事只能放在自己那里,即使是对最能掏心窝子的姐妹,也不能说——令秧知道什么是自己可以盼望的,什么不行。所以,就是想想而已,没关系吧。令秧一边想着,一边帮嫂子做着针线——那些单纯属于缝补的粗活儿看不出什么分别,不过若是细致一些需要绣工的活计,就不同了,比如那件做给春妹,就是嫂子的大女儿的小襦裙。上头的花饰是令秧绣的——其实并没有多复杂,是用令秧的旧衣服改的,只不过,姜黄色的粗布裙摆上,令秧别出心裁地绣了两只小燕子,配着一点淡淡的,几乎像是水珠滴出来的柳叶。令秧绣的时候心里沉甸甸的,因为她怕若有一天,海棠姐姐看见了这两只呼之欲出的燕子,就看穿了她的心事——其实这种担心很是荒唐,她自己也知道。完工那天,嫂子只是略微吃惊地看着她:“真是长进了。” 随后又摇头道,“可是她小孩子家身子拔节那么快,不该穿这么精细。” 令秧一反常态地对嫂子认真地笑道:“就算我走了,也能给春妹绣衣裳,我做好了托人带回来给你。” 嫂子的食指用力戳了一下她的眉心:“少讲这些作怪的话。”
人们都说,令秧的亲事是桩好姻缘。既然都这么说,一定有些道理的,即便对方的年纪比令秧的爹小不了几岁,可好歹,是个什么老爷。令秧的夫君姓唐,名简,家在休宁,离令秧家不过二三十里。其实唐老爷家再往上数几代,跟令秧家一样,都是徽州的商户。不过唐家经营得高明些,虽然比不得那些巨贾,好歹也算是富户,还出了唐简这个自贡生一路中了进士的聪明孩子。殿试及三甲,入翰林院的那一年,唐简不过三十一岁,踌躇满志,男人在恰当的年纪得了意,无论如何都会有股倜傥——他并不知道那其实就是他一生里最后的好时光;他更加不知道,他此生最后一个女人将于十五年后来临——他只顾得上坚信自己前程似锦,不知道她那时正专心地注视着插在摇篮栏杆上的一只风车,她的窗外就是他们二人的故乡,绚烂的油菜花盛开到了天边去。
媒人自然说不清,为何唐简只在短短的四五年工夫里,就被削了官职,重新归了民籍;为何他在朝中的前途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断了,不过只曾在西北一个偏远荒凉的地方做了一阵子知县——哪能妄断朝中的事儿呢,问那么多干吗,是会惹祸上身的——起初,媒人就是用这样危言耸听的方式,把令秧她爹的疑问堵了回去。家乡的人们只知道,唐老爷自己的说法,是在西北上任的时候染了沉疴,无心仕途,所以回乡的——这自然是假话,但是无论如何,唐家是个出过翰林的人家。唐氏一族仍然是徽州数得着的商户,相形之下反倒是唐老爷这一支穷了些,可是守着祖宅祖产,耕读为本,没有任何不体面的地方。虽说是过去做妾,可是这是唐家夫人力主的,多年以来唐夫人只生过一个儿子,怕是比令秧还大两岁,却自幼体弱多病——为着添丁,唐老爷先后纳过两房侍妾,可是一个死于难产,脐带顺便勒死了胎儿;另一个,生过一个女儿之后就莫名其妙地疯了。提亲那年,令秧才十三岁,按理说年纪稍微小了些,可是八字难得地好,人长得也清丽,媒人几次三番地跟爹强调着,说唐家是难得的厚道人家,不会委屈令秧,还有个深明大义的夫人,夫人咳血已经有年头了,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所以,明摆着的,只要令秧能生下一个哥儿,扶正就是顺水推舟的事情。
令秧的爹说,得商议一下。媒人说,那是自然,只不过千万别商议太久。
其实,爹并没有和任何人商议,只是送走了媒人之后,交代哥哥说,他次日要带两个伙计到镇上和临近几个县里去收账,几天就回来,哥哥也不必跟着。哥哥奇怪地说还没到收账的日子呢,嫂子从旁边轻轻地给了个眼色。于是,爹就这样消失了几天,他只不过是在做决定的日子里,不想看见令秧。自从娘走了,爹越来越不知道怎么跟令秧相处。只是每年从外地经商回来,给令秧带一箱子他认为女孩子应该喜欢的玩意儿,说一句:“拿着玩儿吧。喜欢什么,告诉你哥哥,明年再给你买。”似乎是说了句让他无比为难的话。
那天晚上,十三岁的令秧静静地坐在狭窄的天井里,发现只要紧紧地抱住膝盖,收着肩膀,就可以像童年时候那样,把自己整个人藏在一根柱子后面。其实这个发现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无论她藏或不藏,也没有人来寻找她。哥哥和嫂子在厨房里聊得热闹,声音在夜色里,轻而易举就捅破了窗户纸。哥哥说:“我拿不准爹的意思是怎样,反正,我不同意。若是令秧去给人家做小妾,七月半的时候我可没脸去给娘烧香。” 嫂子叹着气:“这话好糊涂。你掂量一下,要是爹真的不同意,那他还出去收什么账,他是觉得这事情挺好的,只不过心疼令秧。” 哥哥道:“你也知道令秧委屈。一个翰林又怎么样了,我们不去高攀行不行?令秧怎么就不能像海棠那样配个年纪相当的,我们令秧哪里不配了?” 嫂子又叹了口气:“这话糊涂到什么地步了,谁说令秧不配,我还告诉你,假使海棠没许人家,保不齐舅舅他们也会愿意。你想想看,一个出了翰林的人家,风气习气都是错不了的,日后怎么就不能再出一个会读书能做官的呢?令秧若是生个有出息的哥儿,就算一时扶不了正,也终有母凭子贵的那天。我看令秧这孩子性子沉稳,不是载不住福气的样子。真像海棠一样,嫁去个家底殷实些的小门小户,倒是安稳,一辈子不也一看就看到头了?” 哥哥突然笑了,语气里有了种很奇怪的亲昵:“你是恨你自己这辈子一眼望到头了么?”嫂子笑着啐了哥哥一下:“好端端地在说你妹子的终身,怎么又扯上我了?你比我一个女人家还糊涂。” 哥哥似乎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反驳,只好说:“左一个糊涂,右一个糊涂,就你不糊涂。
令秧静静地听着,直到嫂子新生的小侄子突然啼哭起来,盖过了说话的声音。她能听见促织在叫,像是月光倾倒在石板地上的声音。她已经知道那就是她的未来了,尽管这些负责做决定的人还没有真的决定。三五天以后,爹就回来了。一家人静静地围着桌子吃晚饭。嫂子叫令秧多吃点,脸上带着种奇怪的殷勤。爹突然放下了筷子,跟嫂子说:“明天起,把绣楼上的房间打扫出来,让令秧搬上去吧。” 嫂子爽利地答应着。跟哥哥不动声色地对看了一眼。
没有一个人面对面地告诉过她这件事,但是每个人都知道,她已经知道了。
就这样过了三年。
都说令秧命好,可能是真的。因为就在正式答复了媒人之后,就传来唐家夫人病重的消息,没两个月就殁了。这种情形之下老爷自然是不好纳妾的,于是只能等等再说。又过了些日子,媒人再度眉飞色舞地登门,聒噪声在绣楼上能听得一清二楚。令秧从小妾变成了填房夫人。据说,是唐家老夫人,也就是唐简母亲的意思。
那天傍晚,她从嫂子手里接过新做的水田衣,她想跟嫂子说她不小心把梳子摔断了,得换把新的,又担心被数落莽撞。可是嫂子专注地看着她的脸,轻声却笃定地说:“给姑娘道喜了。”
可惜她完全不记得自己的婚礼是什么样的,因为她根本就没有参加,她是那个仪式上最重要的一件瓷器,被搀进来带出去,只看得见眼前那一片红色。所有的鼓乐,嘈杂,贺喜,嬉笑……都似乎与她无关,估计满月酒上的婴儿的处境跟她也差不多。她用力地盯着身上那件真红对襟大衫的衣袖,仔细研究着金线绲出来的边。民间女子,这辈子也只得这一次穿大红色的机会。不过也不可惜——她倒是真不怎么喜欢这颜色。她轻轻地捏紧了凤冠上垂下来的珠子,到后来所有的珠子都温热了,沾上了她的体温。她希望这盖头永远别掀开,她根本不想看见盖头外面发生的所有事。前一天,嫂子和海棠姐姐陪着她度过了绣楼上的最后一个夜晚,她们跟令秧嘱咐的那些话她现在一句也想不起来了。她只记得嫂子说,用不着怕,这家老爷应该是个很好的人——知书达理,也有情有义,婚礼推至三年后,完全是因为他觉得这样才算对得住亡妻——这么一个人是不会欺负令秧的。可是令秧没办法跟嫂子讲清楚,她的确是怕,可是她的怕还远远没到老爷是不是个好人那一层上。她知道自己是后悔了,后悔没有在最后的时刻告诉海棠姐姐,令秧是多么羡慕她。她想起九岁那年,舅舅带着他们几个孩子一起去逛正月十五的庙会,她站在吹糖人的摊子前面看得入了迷,一转脸,却发现海棠姐姐和表哥都不见了。他们明明知道长大了以后就可以做夫妻,为什么现在就那么急着把令秧丢下呢?昨晚她居然没有做梦,她以为娘会在这个重要的日子来梦里看她一眼,她以为她必然会在绣楼的最后一个夜里梦见些什么不寻常的东西——现在才知道,原来最大的,最长的梦就是此刻,就是眼下这张红盖头,她完全看不见,近在咫尺的那对喜烛已经烧残了,烛泪凝在自己脚下,堆成狰狞的花。
盖头掀起的那一瞬间,她闭上了眼睛。一句不可思议的话轻轻地,怯懦地冲口而出,听见自己声音的时候她被吓到了,可是已经来不及。她只能眼睁睁地,任由自己抬起脸,对着伫立在她眼前的那个男人说:“海棠姐姐和表哥在哪儿,我得去找他们。”
那个一脸苍老和倦怠的男人犹疑地看着她,突然笑了笑,问她:“你该不会是睡着了吧?” 他笑起来的样子很好看,清瘦的脸,微笑的时候绞出来的细纹让他显得更端正。他好像和爹一样,不知道该跟令秧说什么。他似乎只能耐心地说:“你今天累了。”
“你是老爷?” 令秧模糊地勇敢了起来,她知道自己可以迎着他的眼睛看过去。
他反问:“不然又能是谁呢?” 他把手轻轻地搭在了她的手背上,她有点打战,不过没有缩回去。
一直到死,他都记得,洞房花烛夜,所有的灯火都熄掉的时候,他和他的新娘宽衣解带,他并没有打算在这第一个夜晚做什么,他不想这么快地为难这孩子。黑暗中,他听到她在身边小心翼翼地问他:“老爷能给我讲讲,京城是什么样子么?”
02
唐简淡淡地笑笑,像是在叹息:“上京城是多少年前的事情,早就忘了。”
“老爷真的看见过皇上长什么样?” 他不知道,令秧暗暗地在被子底下拧了一把自己的胳膊,才被逼迫说出这句话来。她听见他说“忘了”,她以为他不愿意和她多说话,但是她还是想努力再试一次,这是有生以来第一回,令秧想跟身边的人要求些什么东西,想跟什么人真心地示好——尽管她依然不敢贴近他的身体。
“看见过。” 唐简伸展了一只手臂,想要把她圈进来——可是她完全不明白男人的胳膊为何突然间悬在了她的头顶。她的身体变得更加僵硬,直往回缩,唐简心里兀自尴尬了一会儿,还是把手臂收回去,心里微微地一颤——你可以抱怨一个女人不解风情,但是不能这样埋怨一个孩子。所以他说:“不过没看得太清楚,谁能抬着头看圣上呢?”
“你家里人叫你令秧?” 她听见男人问她。她忘记了他们身处一片漆黑之中。唐简听见她的发丝在枕上轻微地磨出一丝些微的,窸窸窣窣的声响,知道她是在点头。“睡吧。” 他在她的被面上拍了拍,“天一亮,还得去拜见娘。”
“老爷?” 她觉得自己的声音很陌生。
“嗯?” 回答过她之后,他听见她轻轻地朝着他挪动了一下身体,然后她的脸颊贴在了他露在被子外面的手臂上。她知道她可以这么做,他是夫君;可是她还是心惊肉跳,这毕竟是她有生以来做过的最大的错事。男人的呼吸渐渐均匀和悠长,睡着了吧,这让令秧如释重负。她将一只手轻轻地放在他的胳膊下面,犹豫了片刻,另一只手终于配合了过来,抱住了那只胳膊。她不知道她的姿势就像是把身体拉满了弓,尽力地去够一样遥远的东西。因为这个简陋的拥抱,她的额头和一部分的面颊就贴在了他的手臂上——自然,还隔着那层鼠灰色麻纱的中衣衣袖。她屏息,闭上眼睛。不知什么时候,也许就在他睡眼惺忪之时,依然会隔着那床缎面的被子,轻轻拍拍她——若不是他这个举动在先,令秧无论如何也不敢这样大胆。她希望自己快点睡着,仿佛睡着了,这一层肌肤之亲就暂时被她丢开,不再恐惧,可是能融进睡梦里,更加坐实了。嫂子告诉过她,洞房应该是什么样的,她知道好像不该是现在这样——可是,也好。
她是被天井或是火巷里传来的杂乱脚步声惊醒的,一瞬间不知道身在何处。夜色已经没那么厚重得不可商量,至少她仰着头看得出帐子顶上隐约的轮廓。有人叩着他们的房门,然后推门进来了。唐简欠起了身,朝着帐外道:“是不是老夫人又不好了?” 那个声音答:“回老爷的话,老夫人是又魇住了。喘不上气来,正打发人去叫大夫。老爷要不要过来瞧瞧。” 她怀里的那条胳膊抽离出去的时候,她藏在被褥之间,紧闭着眼睛,她听见唐简说:“不必叫醒夫人,我先去看看再说。” ——整间屋子沉寂了好一会儿,她才明白过来,原来“夫人”指的就是她。她犹疑地坐起来,帐子留出一道缝隙,男人起来匆忙披衣服的时候,点上的灯未来得及吹灭。帐子外面,潦草灯光下,这房间的样貌也看不出个究竟。“夫人。” 那是一个听起来甜美的年轻的女孩子的声音,“才四更天,别忙着起来。这个时候夜露是最重的,仔细受了寒。” 一个穿靛蓝色襦衫,系着水红色布裙的丫鬟垂手站在门旁边,朝着她探脑袋,“我叫云巧,以后专门服侍夫人——老爷到老夫人房里去跟大夫说话,我琢磨着,大喜的日子,夫人是头一天过来,说不定睡得轻,还真让我猜着了。夫人要喝茶么?” 她怔怔地看着口齿伶俐的云巧,只是用力摇摇头。随后就什么话也没了——云巧走过来拨了拨灯芯:“夫人还是再睡会儿吧,还早得很,我就住在楼下,夫人有事喊我就好。” ——她实在不好意思开口问,这丫鬟叫云什么,她没有记住这个名字——若真有事情,如何喊她。但是一句话不说也太不像话了,于是她只好问:“老夫人生的是什么病?”
云巧蜻蜓点水地笑笑——她长得不算好看,可是微笑起来的时候,眉眼间有种灵动藏着:“我只知道老夫人身子的确不好——半夜三更把大夫找来是家常便饭,好像好几个大夫也说不清是什么缘故,平日里也几乎不出屋子——别的就不大清楚了。”
事隔多年,她回想起那个夜晚,头一件记得的事情,便是自己的天真——伶俐如云巧,怎么可能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比云巧还小几岁的令秧,就不假思索地信了。终于再一次听见关门的声响,是唐简回来了。他重新躺回她身边的时候,她心里有那么一点点的欢喜。这点欢喜让她讲话的语气在转眼间就变得像个妇人,有种沉静像夜露一样滴落在她的喉咙里:“老夫人——是什么病?” 唐简回答得异常轻松:“疯病。好多年了。” “老爷的意思是——老夫人是疯子么?” 她在心里暗暗气恼着自己为何总是这么没有章法,唐简却还是那副不动声色的神情:“自从我父亲过世以后,她就开始病了,一开始还是清醒的时候多些,这一两年,清楚的时候就越来越少,特别是晚上,总不大安生。不过她是不会伤人的。最多胡言乱语地说些疯话而已。不过还是得有人看着她,不然……” 她静默着,等着他继续描述老夫人的病情——可是他却问她:“你怕了吗?” 寂静煎熬着,唐简似乎有无穷尽的耐心来等待她的沉默结束,她却如临大敌。她知道自己该说“不怕”,该说她日后也会尽心侍奉神智混乱的老夫人,还该说这些本来就是她分内的事情——但是她却隐约觉得,他未必高兴听到这些。
他突然转过了身子,面对着她,她的脊背贴着拔步床最里头那一侧的雕花,已经没有退路。他抱紧了她,他说你身子怎么这么凉。她紧紧地闭上眼睛。他的手掌落在哪里,哪里的肌肤就像遭了霜冻那样不再是她自己的。她知道她腰间的带子已经在他手上,她觉得此刻听见他温热的喘息声的,似乎并不是耳朵,而是她的脖颈——颈间的汗毛全部竖了起来,因着侵袭,灵敏得像松鼠。男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她的双臂掰开了。俯下头去亲吻她的胸口,她胸前那两粒新鲜的小小的浆果打着寒战,像是遇上了夜晚的林涛声。她知道自己不该挣扎,眼下的一切都是天经地义。她只能死死地攥紧了拳头,天和地都悠然寂静,顾不上管她。只有男人说:“把手放我脊背上。” 她听话地照做了,然后听见他在轻轻地笑:“我是说,抱着我。” 她恍然大悟,然后两人缠绕到了一起。男人讲话的语气其实依然温柔:“你不用怕。” 接着他略略直起身体,硕大的手掌有力地盖住她蜷曲的左腿膝盖——她没想到原来膝盖也是可以被握在手心里的,他把她的左腿往旁边一推,像是推倒多宝格上的一个物件儿,她的右腿也随着倒了下去,男人简短地说:“再张开些。”
表哥也会对海棠姐姐说一样的话吗?
疼痛开始是钝重的。然后像道闪电一样劈了过来,照得她脑袋里一片白惨惨的雪亮,还伴着轰隆一声闷响。她甚至没有办法继续让眼睛闭着——这件事也需要力气。她知道,那种疼带来的,就是从今往后怎么也甩不掉的脏。帐子上映着男人的半截影子,帐子凹凸不平,灯光随着坑坑洼洼,影子在挣扎,忽高忽低,像是就要沉下去。她就是他的坟,他的葬身之地。他的肌肤摸上去,总觉得指头能触到隐约埋在哪里的沙粒。他看上去比他的影子都要狼狈,脸上扭曲着,狰狞扑面而来。拿去了那些谦和跟威严,苍老纤毫毕现。她把目光挪开,看着他的胸膛,看着他胸膛跟腹部之间那道歪歪扭扭的线——此刻她才知道她的身体里有一片原野,可是她刚刚失去了它。他终于倒了下来,压在她身上。她费力地呼吸着,反倒觉得安心——因为噩梦快要结束的时候,不都是喘不上气么——喘不上气就好了,马上就可以醒过来。她知道自己在流血,这是嫂子教过的。另外一些嫂子没教过的事情她也懂了,为什么有些女人,在这件事发生过之后会去寻死。所谓“清白”,指的不全是明媒正娶,也不全是好名声。
他离开了她的身体,平躺在她旁边。她明明痛得像是被摔碎了,但是却奇怪地柔软了起来。她侧过身子贴在他怀中,根本没有那么难。羞耻之后,别无选择,只能让依恋自然而然地发生。她的手指轻轻梳了梳他鬓边的头发。男人说:“我会待你好。” 然后又突兀地,冷冷地跟了一句,“你不用害怕老夫人,她是个苦命的人。”
云巧的声音传进了帐子里:“老爷,夫人,热水已经备好了。我来伺候夫人擦洗身子。”
血迹仓皇地画在她的腿上,小腹上也有零星的红点。血痕的间隙里,还有一种陌生的液体斑斑点点地横尸遍野。令秧嫌恶地把脸扭到一边,她算是见识过了男人饕餮一般的欲望和衰败,男人也见识过了她牲畜一般的羞耻和无助,于是他们就成了夫妻,于是天亮了。
在唐家的第一个清早,是云巧伺候她梳头。“你会不会盘牡丹髻?”她问,怔怔地注视着镜子切割出来的,云巧没有头和肩膀的身体。“会。” 云巧口齿清晰爽利,“不过我倒觉得,夫人的脸型,梳梅花髻更好看。” “梅花头——我不会,你帮我?” 令秧扬起下巴注视着云巧,眼睛里是种羞涩的清澈。云巧略显惊愕地看着她:“夫人是在打趣了。只管吩咐就好,哪里还有什么帮不帮的话呢?” 令秧欠起身子,将身子底下的束腰八脚圆凳挪得更靠近镜子些,重新坐回去的时候,那一阵痛又在身体里撕扯着。她皱了皱眉头,倒抽了一口冷气。“你刚才给我涂的那种药,真的管用?” 她不知道此刻的自己又是一副小女孩的神情,充满了信任。云巧站在身后,拢住她厚重的长发,轻声道:“听说管用。” 令秧垂下眼睑,拨弄着梳妆台上的一支嵌珠花的簪子,听到云巧说:“太太把那个玳瑁匣子里的发簪递给我一下吧,我若自己拿的话,刚编好的就又散了。” 令秧叹了口气:“云巧,你——你跟老爷的第一个晚上,是谁把这个药膏给你的?”
她觉得,那是她成为女人之后,无师自通地学会的第一件事——至于这件“事” 究竟是什么,她说不明白。
云巧默不作声,隔了好一会儿,才说:“是老夫人。”
“你在这儿多久了?” 令秧莫名觉得松了口气。
“有八年了。” 云巧从她手里接过了递上来的发簪,“是来这儿的第三年头上,开始服侍老爷的。不过,夫人放心,我会尽心侍奉老爷和夫人,不敢有什么不合规矩的念想儿。”
“老夫人为什么不让老爷娶你呢?
”没想到云巧笑了:“看来他们说得没错,夫人果真还是个小孩子呀。”
“那云巧,你会梳多少种发髻?” 她有点沮丧,即使经过了洞房花烛,依然会被别人当成是个小孩子。
云巧的眼睛斜斜地盯着窗棂片刻:“十几种怕是有的。”
“你答应我,天天给我梳头?” 令秧看着她的眼睛。
“自然啊,夫人这又是在说哪里的话。
没过多久,休宁县的人们都在传,唐家老爷新娶的十六岁的夫人,进门不到一个月,就做主将一个丫鬟开了脸,正式收在房中成为老爷的侍妾。府里人都唤作“巧姨娘”。乡党之间,略微有些头脸的男人都打趣着唐简的艳福。到了冬天,又传来了巧姨娘怀孕的消息——这下所有的打趣都变成了由衷的羡慕。自然,人们也好奇这位唐夫人是真贤良,还是缺心眼儿。谁也不知道,那其实是令秧嫁进唐家以后最快乐的一段日子——因为她总算是有了一个朋友。云巧帮她梳各种各样她梳不来的发式,给她讲府里上上下下那些事情——有众人都知道的,自然也有些不好让人知道的。云巧是个讲话很有趣的人,很简单的一件事,被云巧一说,不知道为何令秧就听得入了迷——这世上,甚至算上娘在世的时候,都没有人愿意花这么多的时间跟令秧说话。还有就是,云巧还可以代替她,去跟老爷做那件令秧自己非常害怕的事情。令秧知道,自己好像是举手之劳,就改变了云巧的命运——成为一个对别人来说举足轻重的人,令秧从来没尝过这么好的滋味。她小心翼翼地将手掌放在云巧的肚皮上,一遍又一遍地问号出喜脉的大夫:“到底什么时候,云巧的肚子才会变大?”
唐家宅子里,从管家夫妇,到各房丫鬟以及跑腿小厮,再到劈柴挑水的粗使丫头婆子——虽说加起来统共不过三四十个人,倒是都觉得,这个新来的夫人很是特别。甚少能在天井,或是后面的小园子里看见她,多半时候,她都喜欢倚着楼上的栏杆,托着腮,朝着天空看好久——本来空无一物,也不知道在看什么,猝不及防地嫣然一笑,像是在心里自己给自己说了个笑话。这种做派,哪里像一个“夫人”。眼见着老爷十日里有六七日都睡在巧姨娘的房里,第二天一大早还照样欢天喜地,有说有笑的模样真看不出是装的。老爷的一双儿女——哥儿和三姑娘,见着她了自然要问安,照礼数称她“夫人”,她倒是羞红了脸,恨不能往老爷身后躲。老爷似乎也拿她没什么办法,就比方说,她和老爷一同吃晚饭,那天厨子炖了一瓦罐鸡汤,里面有正当时令的笋干和菌,瓦罐不大,她和老爷一人盛上一碗之后,还剩下一点点,一转眼工夫她那份见了底,她就那样直愣愣地冲老爷笑道:“老爷听说过汤底是最鲜的吧?” 老爷点头,她说:“那老爷就让给我,如何呢?” 谁都看得出,老爷有点蒙,但是老爷眉眼间那股笑意也是很久未曾见过的了。或许老爷也跟下人一样,有时候不知该如何对待她——相形之下,倒是老爷和巧姨娘说话的时候,你来我往,有商有量,看着更像是寻常夫妻——叫旁人看在眼里也松一口气。在唐家待了快二十年的厨娘有些失落地说:“若是搁在老夫人身子还康健的时候,哪容得下家里有这么个行状不得体的夫人?” ——虽如此说,不过人们倒是都有数,她不会存心跟任何人过不去,也因此,唐家宅子里当差的各位,也都打心底愿意称呼一声“夫人”。于是,在唐家,令秧反倒能够心安理得地做一个被宽容的孩子。
若是搁在老夫人身子还康健的时候——在唐家,这话时常听到,但其实,哪里有几个人真的见过康健的老夫人,最多只见过疯癫不发作时候的老夫人罢了。老夫人不发病的时候,一切都好,无非就是沉默寡言,且对周遭的人和事漠不关心而已。为家里大事下决断的时候,也是有的。发病的时候,虽说判若两人,也不过就是个寻常的疯子,有两三个婆子看着便好,灌几天药,人就会在某个清晨突然正常起来,安之若素地梳洗,进食,精神好的时候还会条理清晰地责骂丫鬟——全然不记得发病时候的种种形状。令秧自然是见过,老夫人说着话,突然间一口气接不上来,眼睛翻上去,脸涨成猪肝色,平日里照顾她的人自会熟练地冲上来,将一块布塞进她嘴里,抬回房中去——接下来的几天,宅子里最深那一进,总会传出些莫名其妙的喧嚣声,令秧听到过很多回:有时候是笑声,并不是人们通常描述的那种疯子瘆人的惨笑,病中的老夫人笑得由衷地开心,元气十足,远远地听着,真以为房里发生着什么极为有趣的事情;有时候是某种尖利的声响——断断续续,虽然凄厉,但是听惯了,即使是深夜里传出来,就当是宅子里养着什么奇怪的鸟,也不觉得害怕。令秧从没对任何人说过,她其实更喜欢犯病时候的老夫人——因为在疯子的笑声和呼啸声里,她才能觉出一种滋生自血肉之躯的悲喜——老夫人清醒的时候,就跟塑像差不多吧,总是不好接近的。
没有人解释得通,为什么在老夫人发病的时候,令秧还总是愿意去老夫人房里待一会儿。这种时候,人们会用绫子缚住老夫人的双手双脚,将她捆绑在床上——因为她曾经拿着一把剪刀把自己的胸口戳出两个血洞。被缚在一堆绫子中央的老夫人,衣冠不整,披头散发,脸上却是真有一种自得其乐的神情,虽说神情麻木眼神涣散,喉咙里发着悲声,但令秧总会觉得,此时的老夫人更像一尊凡人难以理解的神祇,全然不在乎被五花大绑的冒犯。令秧托着腮坐在这样的老夫人旁边,相信自己总有一天是能够和此时的老夫人对话的。府里的人们自然是觉得,就算这位新夫人有些缺心眼儿,可是能做到在这种时候来陪伴着老夫人,也实属不易——换了谁不是硬着头皮进来呢,此情此景,目睹了难免伤心。也因此,就当是新夫人孝心难得吧。不然还能如何解释这件事呢?
直到唐简死的那天,令秧都相信,疯病中的老夫人,一定是想要告诉人们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