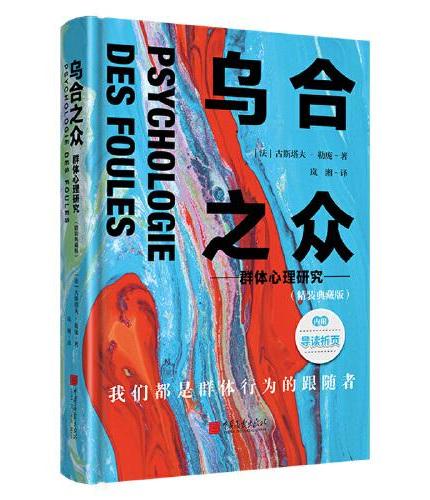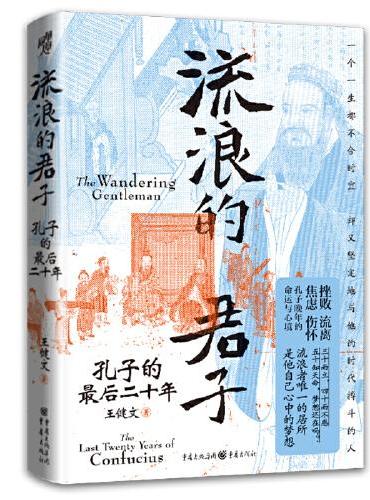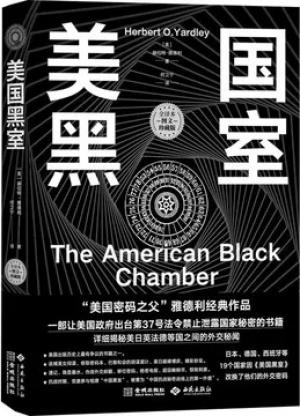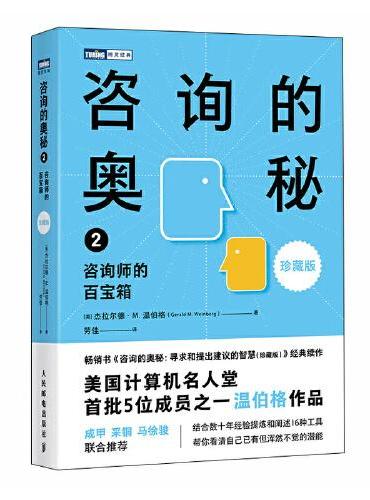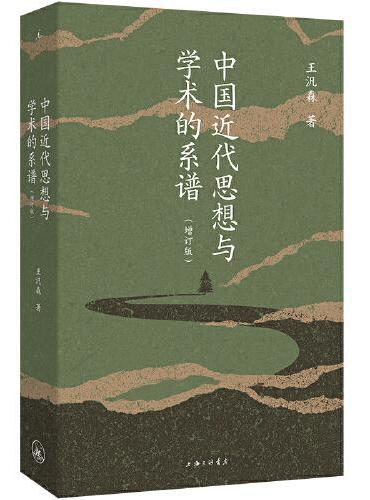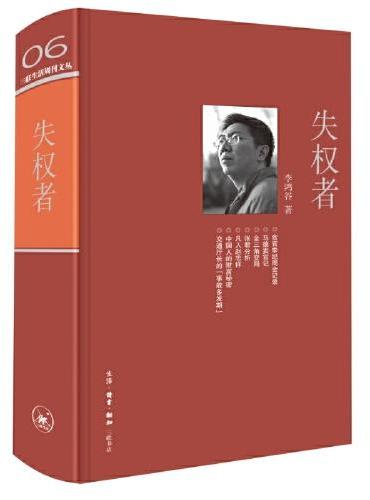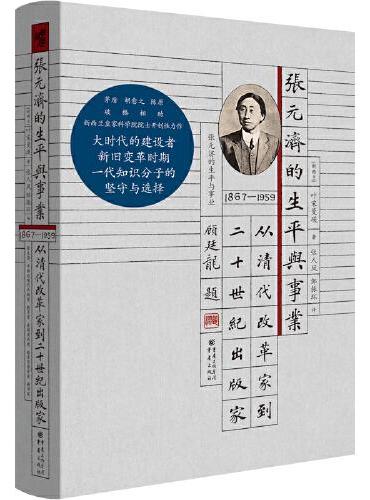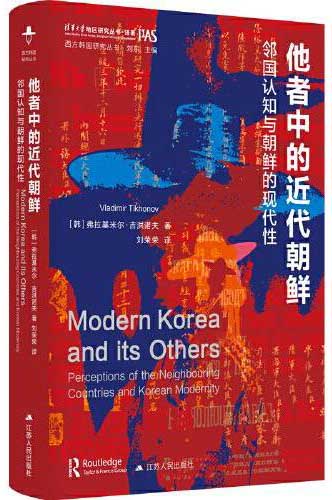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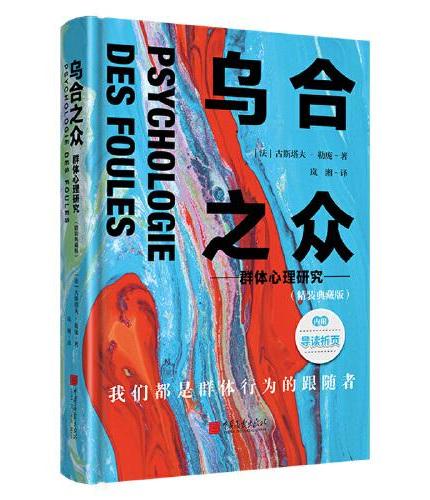
《
乌合之众:群体心理研究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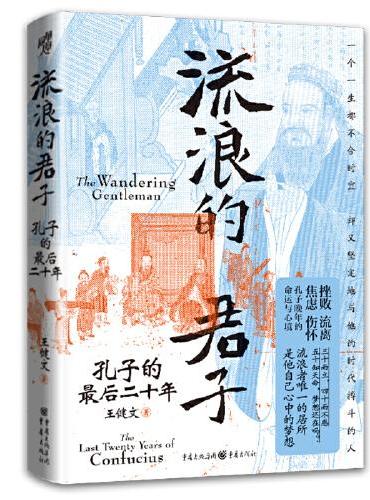
《
流浪的君子:孔子的最后二十年 王健文
》
售價:HK$
5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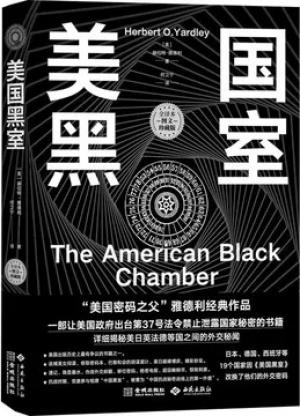
《
美国黑室(全译本 图文珍藏版)
》
售價:HK$
7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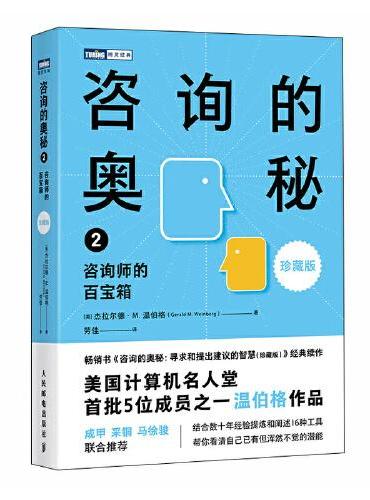
《
咨询的奥秘2:咨询师的百宝箱(珍藏版)
》
售價:HK$
7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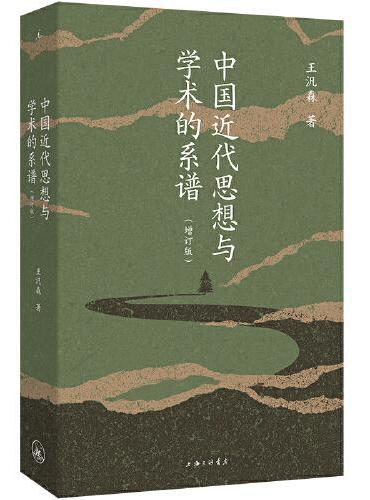
《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增订版)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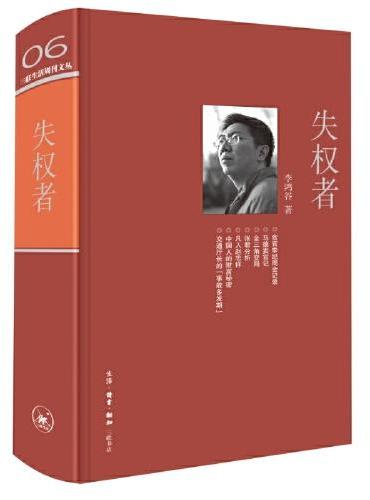
《
失权者(三联生活周刊文丛)
》
售價:HK$
7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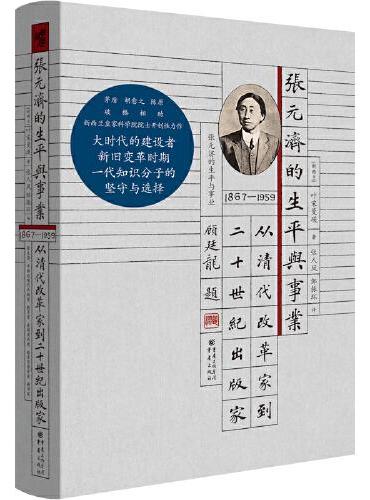
《
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从清代改革家到二十世纪出版家
》
售價:HK$
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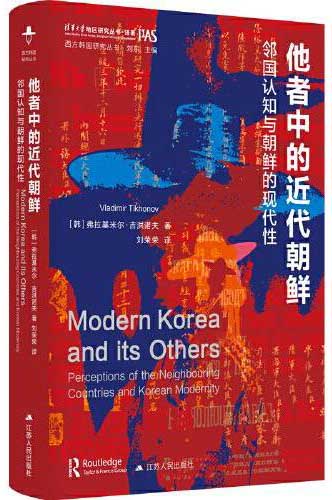
《
他者中的近代朝鲜(西方韩国研究丛书)
》
售價:HK$
85.8
|
| 編輯推薦: |
纯爱经典痞子蔡爱情回归
那一年,网络还没有现在如此发达;那一年,才开始有win98;那一年,博客、微博不知是何物,大家也不知道电子书。就是在那一年,她——轻舞飞扬、它——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他——痞子蔡,第一次通过网络,在BBS上与我们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作为网路文学第一人,蔡智恒(那时候大家很少称呼该名),他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曾红透网络世界,掀起全球华文地区的“痞子蔡”热潮。
十五年了,蔡氏爱情一如既往带给我们温暖和感动!
蔡氏爱情的永恒魅力
在人们心底,永远流淌着纯真爱情的诗篇,只是忙于生活的人们没有察觉或者尚未发现或者渐渐被生活的厚重所遮盖。它给人的感觉就像一缕清风、一股甘泉、一支恋曲,相比目前流行的“恋思癖“,它给人的阅读体验是清新飘逸的、举重若轻的。在“宅男”“宅女”尚不流行的当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让万千少男少女相信了网络恋爱的神奇,更让《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成为到目前为止,国内最经典的纯爱小说和诠释纯爱小说的典范。
美好的纯爱小说就像舒伯特的《小夜曲》,古典忧伤而又浪漫四溢,蔡氏爱情便如此。他的爱情小说总是通过调动人类的所有感情来打动读者,用
|
| 內容簡介: |
关于爱情这东西,我并不懂,所以我无意告诉读者,
什么是“对”的爱情、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合理”的、
什么是“不变”的、什么是“永远”的、什么是“没有亏欠”的……
我只是觉得,不晓得爱情是什么东西的人,
反而能够真正享受爱情的单纯与美好。
|
| 關於作者: |
BBS的ID为jht,网络上的昵称是痞子蔡。
1969年出生于台湾嘉义县,成功大学水利工程博士。
1998年于BBS发表第一部小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掀起全球华文地区的痞子蔡热潮。
自此以后,左脑创作小说、右脑书写学术论文,独树一格。
现任教于立德管理学院。
|
| 目錄:
|
003.第一支烟
当这些字都成灰烬,我便在你胸口了
008.第二支烟
海蚌未经沙的刺痛
就不能温润出美丽的珍珠
于是我让思念
不断刺痛我的心
只为了,给亲爱的你
所有美丽的珍珠
013.第三支烟
我想你,已经到泛滥的极限
即使在你身边,我依然想着你
搁浅的鲸豚想游回大海,我想你
那么亲爱的你,你想什么?
021.第四支烟
不论我在哪里
都只离你一个转身的距离
我一直都在
在你身前
在你影里
在楼台上,静静等你
042.第五支烟
我无法在夜里入睡
因为思念一直来敲门
我起身为你祈祷
用最虔诚的文
亲爱的你,我若是天使
我只守护,你所有的幸福
071.第六支烟
你柔软似水
可我的心
却因你带来的波浪,深深震荡着
于是我想你的心,是坚定的
只为了你的柔软,跳动
跳动中抖落的字句,洒在白纸上
红的字,蓝的字,然后黑的字
于是白纸,像是一群乌鸦,在没有月亮的夜里飞行
107.第七支烟
我像是咖啡豆,随时有粉身的准备
亲爱的你,请将我磨碎
我满溢的泪,会蒸馏出滚烫的水
再将我的思念溶解,化为少许糖味
盛装一杯咖啡
陪你度过,每个不眠的夜
146.第八支烟
我愿是一颗,相思树上的红豆
请你在树下,轻轻摇曳
我会小心翼翼,鲜红地,落在你手里
亲爱的你
即使将我沉淀十年,收在抽屉
想念的心,也许会暗淡
但我永不褪去,红色的外衣
184.第九支烟
请告诉我,怎样才能不折翼的飞翔
直奔你的方向
我已失去平衡的能力,困在这里
所有的心智,挣扎着呼吸
眼泪仿佛酝酿抗拒
缺口来时就会决堤
亲爱的你,我是多么思念着你
224.第十支烟
我对你的思念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
可是,不假
并以任何一种方式,源远流长
亲爱的你
无论多么艰难的现在,终是记忆和过去
我会一直等待
为你
267.后记
|
| 內容試閱:
|
Contents
“台北火车站。”
左脚刚跨入出租车开了四分之一的门,右脚还没来得及甩掉沾上鞋底的湿泥,我便丢下这一句。
“回娘家吗?”
司机随口问了一句,然后笑了起来。
我也笑了起来。
虽然是大年初二,但我却是单身一人,只有简单的背包。
还有,我是男的。
即使雨下得很大,仍然只能改变我的发型,而不是性别。
我不是高桥留美子笔下的乱马,所以不会因为淋到冷水而变成女生。
“今天真冷。”
“嗯。”
“淋湿了吧?车后有面纸,请用。”
“谢谢。”
“赶着坐火车?”
“嗯。”
“回家吗?”
“不。找朋友。”
“一定是很重要的朋友。”
“嗯。”
下了雨的台北,陌生得令人害怕。
看来我虽然在这座城市工作了半年,却从来没有认真生活过。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无法融入这城市的血液。
台北的脉动也许左右着我的喜怒哀乐,却始终得不到我的灵魂。
我像是吴宫中的西施,身体陪伴着夫差,但心里还是想着范蠡。
隔着车窗,行人像一尾尾游过的鱼,只有动作,没有声音。
好安静啊,仿佛所有的声音都被困在黑洞里。
我知道黑洞能困住所有的物质和能量,甚至是光。
但声音能从黑洞里逃脱吗?高中时有同学问过物理老师这个问题。
“声音?你听过有人在黑洞中叫救命的吗?”
老师说完后陶醉于自己的幽默感中,放声大笑。
也许我现在的脑袋就像黑洞,困住了很多声音,这些声音到处流窜。
包括我的,荃的,还有明菁的。
“165元,新年快乐。”
“哦?谢谢。新年快乐。”
回过神,付了车钱。
抓起背包,关上车门,像神风特攻队冲向航空母舰般,我冲进车站。
排队买票的人群,把时空带到1949年的上海码头,我在电影上看过。
那是国民党要撤退到台湾时的景象。
我不想浪费时间,到自动售票机买了张月台票,挤进月台。
我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有方向。
往南。
第一支烟
当这些字都成灰烬,我便在你胸口了
月台上的人虽然比车站大厅的人少,不过因为空间小,所以更显拥挤。
车站大厅的人通常焦急,月台上的人则只是等待。
而我呢?
我是焦急地等待。
爱因斯坦说得没错,时间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等待的时间总像是失眠的黑夜一样,无助而漫长。
而该死的火车竟跟台北市的公交车一样,你愈急着等待,车子愈晚来。
“下雨时,不要只注意我脸上的水滴,要看到我不变的笑容。”
突然想到荃曾经讲过的话,我的心情顿时轻松了不少。
那天下着大雨,她没带雨具跑来找我,湿淋淋地说了这句话。
“帮个忙,我会担心你的。”
“没。我只是忘了带伞,不是故意的。”
“你吃饭时会忘了拿筷子吗?”
“那不一样的。”荃想了一下,拨了拨湿透的头发:
“筷子是为了吃饭而存在,但雨伞却不是为了见你一面而存在。”
荃是这样的,她总是令我担心,我却无法说服她不令我担心。
相对于明菁,荃显得天真,但是她们都是善良的人。
善良则是相对于我而言。
“为什么你总是走在我左手边呢?”
“左边靠近马路,比较危险。”
明菁停下脚步,把我拉近她,笑着说:
“你知道吗?你真的是个善良的人。”
“会吗?还好吧。”
“虽然大部分的人都很善良,但你比他们更善良。”
我一直很想告诉明菁,被一个善良的人称赞善良是件尴尬的事。
就像颜回被孔子称赞博学般地尴尬。
我慢慢将脑袋里的声音释放出来,这样我才能思考。
这并不容易,所有的声音不仅零散而杂乱,而且好像被打碎后再融合。
我得试着在爆炸后的现场,拼凑出每具完整的尸体。
然后我开始意识到我是否正在做一件疯狂的事。
是疯狂吧,我想。
从今天早上打开香烟盒想拿烟出来抽时就开始了。
搞不好从突然想抽烟这件事开始,就已经算是疯狂。
因为我戒烟半年了。
有一次柏森问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事是什么?
我想了半天,只能想出钥匙忘了带,所以从10楼阳台翻进窗户开门的事。
“这叫找死,不是疯狂。”
“熬了两天夜准备期末考,考完后马上去捐血。算吗?”
“仍然是找死。”
“骑脚踏车时放开双手,然后做出自由式和蛙式的游泳动作呢?”
“那还是叫找死!”
后来我常用同样问题问身旁的同事或朋友,他们的答案就精彩多了。
当然也有一面跑马拉松一面抽烟这种找死的答案。
有人甚至告诉我,总统大选时投票给陈水扁是最疯狂的事。
他是公司里一位快退休的工程师,20年忠贞的国民党员。
他的思想偏右,立场偏右,连穿四角内裤时也是把命根子摆右边。
“那为什么你要投给陈水扁呢?”
“如果当你年老时,发现自己从没做过疯狂的事,你不会觉得遗憾吗?”
我也许还不算老,但我已经开始觉得遗憾了。
记得有次柏森在耍白烂,他说:
“你没有过去,因为你的过去根本不曾发生;
你也没有未来,因为你的未来已经过去了。
你不可能变老,因为你从未年轻过;
你也不可能年轻,因为你已经老了。”
他说得没错,在某种意义上,我的确就是这么活着。
“你不会死亡,因为你没有生活过。”
那么我究竟是什么?柏森并没有回答我。
像一株檞寄生吧,明菁曾经这么形容我。
终于有火车进站了,是班橘色的莒光号。
我往车尾走去,那是乘客较少的地方。
而且如果火车在平交道发生车祸,车头前几节车厢通常会有事。
因为没看到火车经过才会闯平交道,于是很容易跟火车头亲密接触。
更不用说抛锚在铁轨上的车辆被火车迎头撞上的事故了。
只可惜,乘客太多了,任何一节车厢都是。
我不忍心跟一群抱着小孩又大包小包的妇女抢着上车。
叹了口气,背上背包,退开三步,安静等待。
火车汽笛声响起,我成了最后一节车厢最后上车的乘客。
我站在车门最下面的阶梯,双手抓住车门内的铁杆,很像滑雪姿势。
砰的一声巨响,火车起动了。
我回过头看一下月台,还有一些上不了车的人和送行的人。
这很容易区别,送行的人会挥舞着右手告别;
上不了车的人动作比较简单,只是竖起右手中指。
念小学时每次坐车出去玩,老师都会叮咛:
“不要将头手伸出窗外。”
我还记得有个顽皮的同学就问:“为什么呢?”
老师说:“这样路旁的电线杆会断掉好几根啊!”
他说完后大笑好几声,好像动物园中突然发情的台湾弥猴。
很奇怪,我通常碰到幽默感不怎么高明的老师。
那时就开始担心长大后的个性,会不会因为被这种老师教导而扭曲。
火车开始左右摇晃,于是我跟着前后摆动。
如果头和手都不能伸出窗外,那么脚呢?
我突然有股冲动,于是将左脚举起,伸出车外,然后放开左手。
很像在表演滑水特技吧。
柏森,可惜你不能看到。这样可以算疯狂吗?
再把右手放开如何?柏森一定又会说那叫找死。
所谓的疯狂,是不是就是比冲动多一点,比找死少一点呢?
收回左脚,改换右脚。交换了几次,开始觉得无聊。
而且一个五六岁拉着妈妈衣角的小男孩,一直疑惑地看着我。
我可不想做他的坏榜样。
荃常说我有时看起来坏坏的,她会有点怕。
明菁也说我不够沉稳,要试着看起来庄重一点。
她们都希望不要因为我的外在形象,而让别人对我产生误解。
我总觉得背负着某些东西在过日子,那些东西很沉很重。
最沉的,大概是一种叫作期望的东西。通常是别人给的。
然后是道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