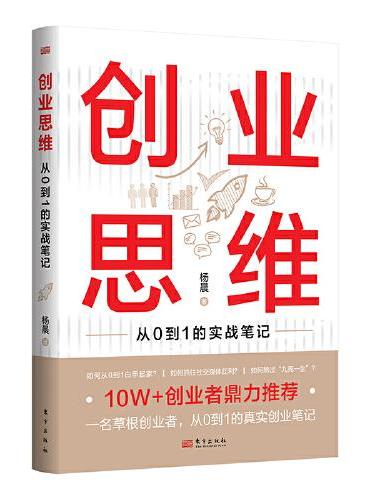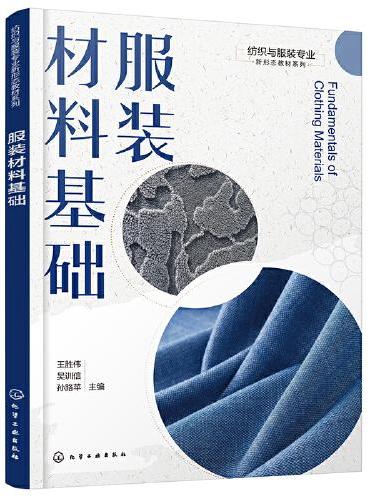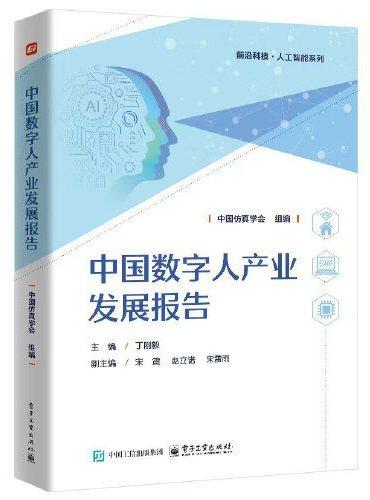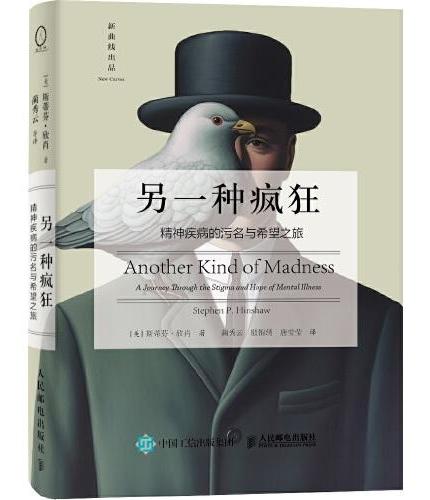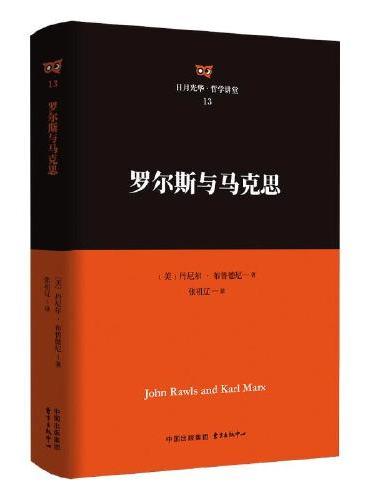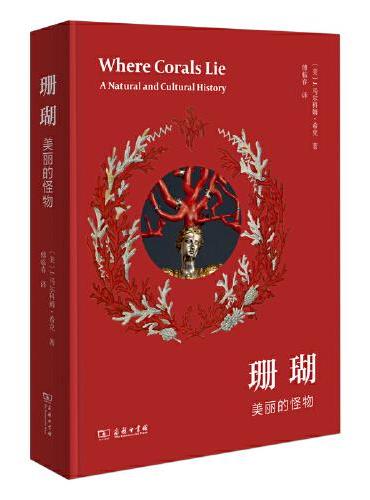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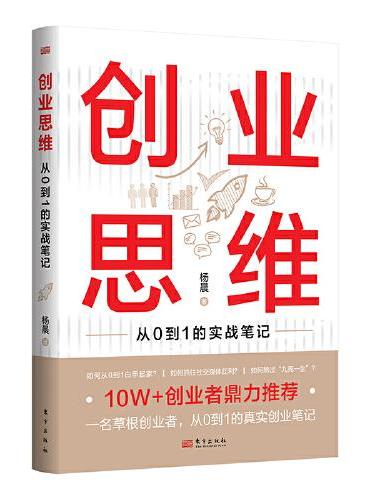
《
创业思维:从0到1的实战笔记
》
售價:HK$
76.8

《
家庭财富管理指南
》
售價:HK$
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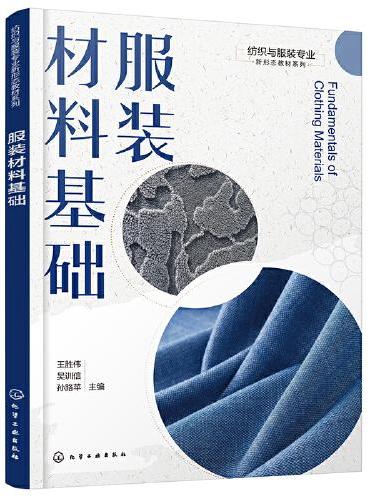
《
服装材料基础
》
售價:HK$
63.8

《
国家名片C919(跟踪十余年,采访百余人,全景式呈现中国大飞机C919,让读者领略到中国航空科技的最新成就)
》
售價:HK$
14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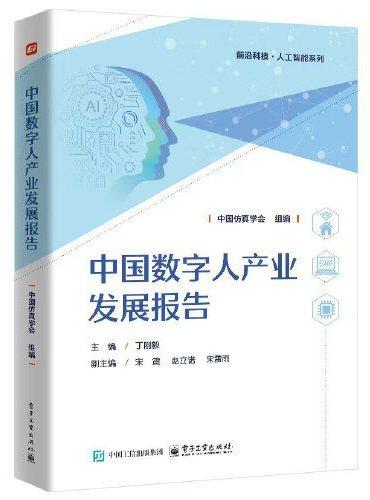
《
中国数字人产业发展报告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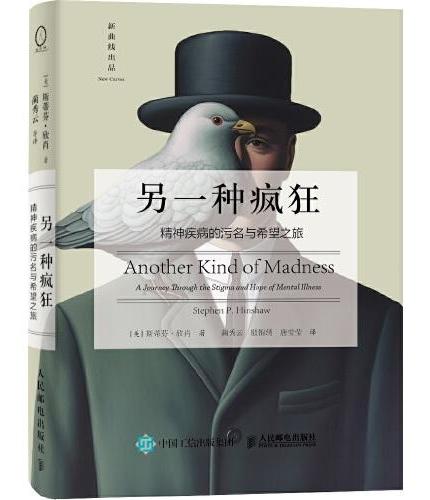
《
另一种疯狂:精神疾病的污名与希望之旅(APS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斯蒂芬·欣肖教授倾其一生撰写;2018年美国图书节最佳图书奖)
》
售價:HK$
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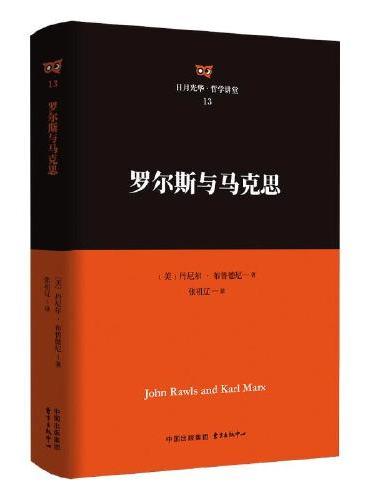
《
罗尔斯与马克思
》
售價:HK$
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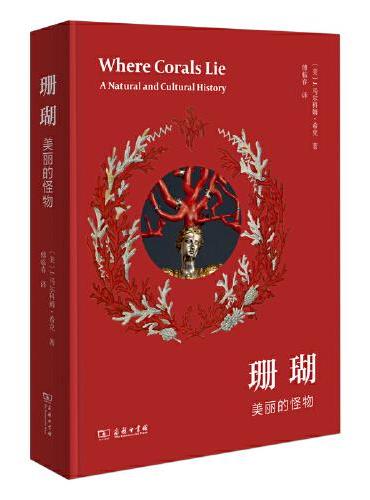
《
珊瑚:美丽的怪物
》
售價:HK$
126.5
|
| 編輯推薦: |
★活在一个不负责任的时代,我们该如何经历并反对这个时代?
★《战后欧洲史》之外,托尼朱特最富盛名的两部著作之一。
★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托尼朱特,以三位重负责任的知识分子,触及了我们时代思想和道德的困境。
★“被遗弃的先知”莱昂布鲁姆、“不情愿的道德主义者”阿尔贝加缪、“局外的当局者”雷蒙阿隆 ,三位深度介入政治的法国知识分子,如何以道德责任挑战黑暗时代?
他们的生活和著述都与这个不负责任的时代格格不入。他们毕其一生,经常感受到这个国家所要求的政治与思想相一致的压力,却甘愿在政界、公众、左翼同僚或知识分子同侪中充当不受欢迎的人,这是一种稀罕而耐人寻味的个性。仅此,他们的事迹就值得一书。
——托尼朱特
|
| 內容簡介: |
《责任的重负》是托尼朱特最富盛名的两部著作之一。
在这本书中,他选取了阿尔贝加缪、莱昂布鲁姆、雷蒙阿隆这三位法兰西精神最优秀的代表人物,还原他们生活的年代,考察他们的言行与历史纵横嬗变之间的联系,讨论知识分子与思想史的诸多重要议题。
托尼朱特认为,评价知识分子的核心词应是“责任”。这三位道路迥异却共同拥有“勇气与正直”这种道德人格的知识分子,在投入公共生活之后,将个人利益置于公共责任之下,以独立的良知发言,以一致的言行影响现实政治、纠正时代谬误,并不惜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才有所谓“责任的重负”。
他们活在一个不负责任的时代,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经历过,并反对这个不负责任的时代”。
可以说,他们不单代表了现代法国的思想和政治文化中独特的、令人憬悟的一种声音,还代表了现代社会和思想中许多最优秀、最持久的价值——过去是,如今也是。
|
| 關於作者: |
托尼朱特(Tony Judt)
◎全球百大思想家
◎奥威尔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21世纪初最顶尖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
著名历史学家,以其对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的深入研究而闻名于世。1948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先后执教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纽约大学。
1995年,创办雷马克研究所,专事欧洲问题研究;
1996年,当选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
2007年,当选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
2008年,入选美国《外交政策》评选的“全球百大思想家”;
2009年,以其卓越的“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获得奥威尔终生成就奖。
托尼朱特长期为《新共和》《纽约时报》《纽约时报书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等欧美主流媒体撰稿,并以尖锐的自由主义批评文风成为备受尊重的知识分子,拥有“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之美誉。
其主要著作有《战后欧洲史》《沉疴遍地》《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思虑二十世纪》等。其中,《战后欧洲史》被誉为“关于战后欧洲历史的最佳著作”“短时间内无法超越的伟大著作”。
译者简介
章乐天 独立记者、独立书评人和专栏作家。译作另有《开端》《思虑中国》《加缪和萨特》等。
|
| 目錄:
|
前言
导论 巴黎之误
第一章 被遗弃的先知——莱昂布鲁姆和妥协的代价
第二章 不情愿的道德主义者——阿尔贝加缪和暧昧的难堪
第三章 局外的当局者——雷蒙阿隆和理性的报应
进一步阅读
六十年后,一个更重的赌注(译后记)
人名索引
|
| 內容試閱:
|
导论 巴黎之误
纸面所书的历史同亲历的历史不同,理当如此。对于亲历历史的感觉,历史中人所知比我们更多,但是,他们大部分人以当时所处的位置,并不适宜理解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及其缘由。不管我们能给昔日之事做的解释如何不完美,都得仰仗后见之明的便利,哪怕这种后见之明对我们完成对历史的同情之理解而言,本身就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昔日之事的形貌取决于一个适时适地采取的视角;而所有这些形貌又都是局部真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取得了更长久的可信力。
我们本能地知道这一点,因为这最好地描述了我们自己多样化的生活面貌。但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他人,而且,他们对我们生活的解释也只是局部貌似真实的时候,我们就得承认,对错杂交叠的个人历史有无穷多可能的解释。出于社会和心理上的便利,我们对个人生活——我们自己以及朋友、同事和熟人的生活——会持有一个得到公认的一致理解。但是,这一最低限度的认同一致之所以能够保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多数情况下我们没有合适的理由去深究我们安到自己或他人头上的叙事。除非遇到非常的危机,否则我们不会自找麻烦,试图去质疑现在的我们和过去的我们之间的关系;况且,大多数人醒着的时候也很少会去推究我们的历史之本质与含义,视其为盖棺论定的东西更方便,也更安全。而且,即便我们真的心血来潮,一个劲儿地追问我们过去啥样现在啥样我们何以变成这样,把自己细细研究一遍得出结论后下一步又该如何动作,我们与多数他人之间的关系仍将维持原状,他们还是过自己的日子,基本上不会被这种自恋兮兮的玄想所搅扰。
然而,适用于个人的情况并不适用于民族。一段共同历史被赋予的含义,它对当下国内国际的关系的影响,有关古往今来各种集体行为和集体决策的独立而又相互排斥的说法所占据的道德与意识形态地位,在世界各民族各国家中引起了至为激烈的争论;历史也几乎总是处于争议中心,哪怕表面上争的是现在或未来,其实争的也是历史。在许多地方,国家实体之存在很大程度上就倚仗着这类争吵;没有一个得到批准或一致承认的集体历史版本能通过争吵而图绘出来,因为,正是分歧本身构成了这一共同体的基本认同。
这是个独特的现代问题。在更古老时代的帝国、政权和共同体中,正常情况下,政治权威不会有多个发源地,关于谁能掌权、凭什么掌权的认识也不会有分歧。作为既存合法性的来源之一,“历史”是唯一的——由是观之,我们现在所说的“历史”则根本不是历史。大部分曾在这颗行星上生活过的人都没有主动去接触过他们的历史。关于自己缘何成为现在的样子,他们的认识都狭隘而实用,与他们的统治者讲的故事——一个他们最多只能模糊了解的故事——密不可分。只要权力和权威仍然垄断于一个家族、集团、阶级或宗教团体之手,对现世的不满乃至对未来的期许就仍将受制于有关集体历史的一种叙述,这种叙述纵使有时被人恨之入骨,却不会受到决定性的动摇。
一如我们现在所知,革命性的剧变产生了政治,也改变了所有这一切。脱胎于革命的一套新秩序,就像被推翻的旧人旧秩序一样,其提出的主张和承诺也需要公信力和合法性,为此,新主子对自己即将君临的这个社会和国家的历史肯定也得有自己的一套叙述。而且,既然对这一叙述而言,首要的是证明唯一能导致这种改朝换代的事态恶化和发展过程是正当的,所以,它不但要宣说自己的政治主张,还得彻底剥夺旧秩序政治主张的合法性。由此,现代政治权力高度仰赖于关于历史的宣说;结果,历史成了政治。
通常情况下,这种嬗变很自然地会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挂起钩来,而与大革命本身联系更为紧密。因为不仅法国革命者们自己明白,他们的所作所为从根本上而言是断章取义的,就连他们的后继者和敌人也沿循这一本能,把大革命本身视为适合进行历史论争的首要阵地。谁能“控制”对法国大革命的阐释权,谁就能控制法国,或至少能在大革命后的法国抢占有利位置,主导关于政治合法性的论争。不单对马克思及其继承人,而且对托克维尔的自由派一系以及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及其反革命儿女而言,对1789年巴士底狱“陷落”以来的10年法国史的理解,具有和政治理论与实践同等重要的地位。同时,不仅限于法国——此后两个世纪里,对法国大革命的“恰当”解读在许多情况下给世界各地的激进和反动思想制定了意识形态纲领。
但是,大革命是在法国爆发的;政治和公共生活实践铸成的最持久、最具分裂性的后果都落在了革命发源地,并非全系偶然。法国是欧洲最古老的单一民族国家。因此,18世纪末的革命者们手头已有一大把历史可以做文章。从那时起,大革命的诸多事件及其在国内造成的后果就提供了一块独一无二的沃土,那里结出了异议、争斗和分裂之果,而在这块土地上,在这个地理、制度和语言上的身份早已得到确认并固定下来的民族之中发生的战争,使得这种种争端更加尖锐,更加你死我活。
与她的欧洲邻居们相比,法兰西太不一样了。在德国或意大利,那些导致国内冲突和政治动乱的分裂敌对并未让民族国家早早降临,也没有呈现出倒退回早期国家的症状。自然,对本民族集体历史应居何许位置,当如何解释,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也有很多争论,有些和法国的还很相似。然而,这些争论常常与“德国人”或“意大利人”内部的历史无关,其涉及的是对局部的、地方性的历史的不同理解,直到很晚,这些局部历史才被纳入作为一个单一民族的德国或意大利的历史(有时这非常可惜)。1939年、1919年或1878年前的东欧和东南欧地区的国家历史,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常常只是一个“虚拟的”存在。人们争论历史,争的与其说是政治,还不如说是神话传说,尽管仍得为此头破血流。
所以说,法国与众不同。种种迹象表明,法国应是唯一一个涌现了一大批讨论其“记忆地”的学术出版物的国家——这些“记忆地”集体体现着这个国家对自己传统的理解。更具象征意义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如果说四卷中等篇幅的作品就足够容纳“共和国史”和“民族史”的话,要编一部“法国史”没有洋洋三大卷是拿不下来的,其中最大的一部分用来写“冲突与分裂”。给欧洲其他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共同历史记忆建一座学术纪念碑,都不需要建成如此规模,人们也很难理解,这部书何以必须有6000页那么厚,更无法相信法国人竟不得不以如此浩繁卷帙去解释那让国民们彼此相敌的昔日。 一边是法兰西表面上的大一统,另一边是四分五裂的现代法国无休止的激烈争吵,两者之间存在的紧张,乃是这个国家及其历史中最突出的特征。
20世纪涣散飘摇的法国有三大病症被谈论得最多:政治上的左右两派争个没完没了;维希政权及其对民族道德境况的恶劣影响延续了数十年之久;政治制度的持续不稳重现了19世纪的情形,正如19世纪也重现了18世纪十年大革命的政治和制度斗争,并为其画上了句号。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阿尔及利亚战争的40年间,法国经历了四个不同的政权,从议会共和制到老人独裁政治的多种不同的政治体制;在其中第三个政权——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存续的短短14年中,政府平均每半年更迭一次。
观察家和历史学家把这三个症状统称为“法兰西病症”,它们直接来源于对法国共同历史——特别是法国大革命的遗产——的相互冲突的解释。“左派”和“右派”这两个术语的付诸使用源于革命联合开始因意识形态一分为二之时;两大派系围绕应从大革命以及当时人们狂热的拥护或反对中汲取什么教训各做各的阐释,进而相互对立。典型的如法国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之争,双方都寸步不让地要求继承“未完成的”资产阶级大革命的遗产和衣钵;所以并不意外,当贝当政权标榜“民族革命”的时候,其属民一开始所能达成的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就是希望消除大革命及其遗产。至于法国无法建立一个稳定的、得到普遍接受的议会系统或总统制,与法国社会的性质也没有多大关系——它在很长时期内因其自足的、保守的稳定性而独树一帜。法国人在如何管理社会的问题上始终无法取得一致,是因为从1789年到第三共和国崛起的一个世纪里,法国人一直不信任各种宪法模式和政治权力形式。
20世纪前三分之二的时间里的许多观察家认为,左右之争及相关的政局不稳,是法国面临的最重要、最紧迫的难题,因为这些问题深深植根于各种政治记忆之争,植根于有关“真实的”法兰西历史道路的各种叙述之争。当然,争论的参与者本人不觉得问题是由动荡或冲突引起的,而都认为是对方固执己见、拒绝遵循自己的世界观所致。意识形态之争在参与者们眼里显然是第一要着,其他事情顶多偶尔地、短时间地关心一下。这种态度在今天看来荒诞不经,是很久以前才有的咄咄怪事。但是就在数十年前,法国公共空间还充塞着教条语言,耽于争吵,吵到酣处几乎能不顾一切。意识形态右翼要到坠入维希深渊而名誉扫地时才走出这一误区,而左派则一直保持到70年代。
不过,研究法国晚近历史已有其他途径,不那么强烈地依赖大革命视角和语汇了。在1940年、1944—1946年以及1958年发生了三次转折的传统的制度编年史学,无力回应这一问难:这种史学方法低估了社会变迁、经济变迁的趋势与时机的意义。另一条叙述路径则强调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社会明显的连续性以及与此相伴的经济停滞。法国人自己首先就明白,国家仍然是一个人口增长率罕见低下的农村和农业社会,极度需要连续性,拒绝各种形式的变革——这些变革正在同一时期内改变其邻国的面貌。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当下威胁面前保护过去的做法对这个民族很有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兰西民族的这种威胁感进一步增强,从而进入长达20年怀旧伤逝性的拒绝之中。两次大战之间的大萧条令其他欧陆国家遭遇了经济崩溃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剧变,法国却得以幸免。但从另一角度看,全民转向隐晦不明的旧制度,憎厌现代化和改革,却促成了维希政权的降生,因为后者许诺说要迎回一套前现代价值观及制度,这让政治阶级(political class)及选民本能地感到宽心。而且,尽管政治首脑们无知依旧,但新一代官员和管理者们都已认识到,并不是战后的第四共和本身,而是新的国际形势和机遇在50年代中期过后把法国推进了一场迅猛的经济、人口和社会变革之中。
关于1930—1970年历史的另一种说法认为法国陷进了一场三边斗争之中:一个怯懦的、不敢冒险的社会,一个颟顸无能而又离心离德的政治阶级,以及一小撮为国家的停滞乃至倒退而满心沮丧的公仆、学者和商人。按照这种观点,1936年成立的人民阵线,不管泛着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色泽,它首先是向着国家经济体制和政府系统的全面检修迈出的迟疑不决的第一步。这一行动在30年代厝火积薪的政治氛围下铁定败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重拾变革的反倒是维希“实验”的一些年轻参与者。以“民族革命”和废除议会对行政决策的压制为旗号,他们全面检查了地方和中央政府机器的各个零部件——他们努力的结晶未获认可,尽管法国的现代化政府部门终于在下一个十年中建立了起来。只是到了1958年第五共和问世以后,社会变革、行政革新和政治制度才算齐头并进——即便如此,也还是对第五共和创建者的本愿偶有违逆——法国得以克服其“病症”,体验“正常”的经济和政治生活。
但是,在span style="font-fa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