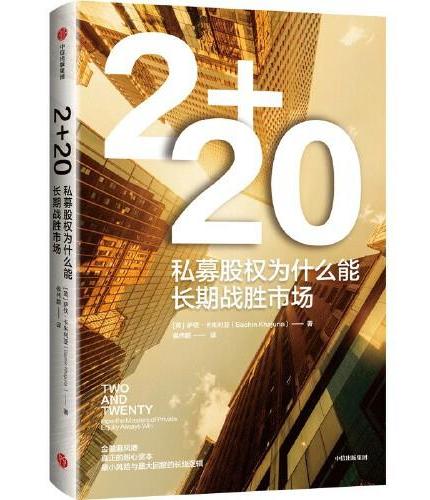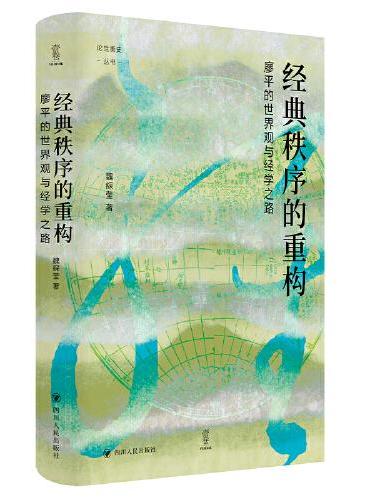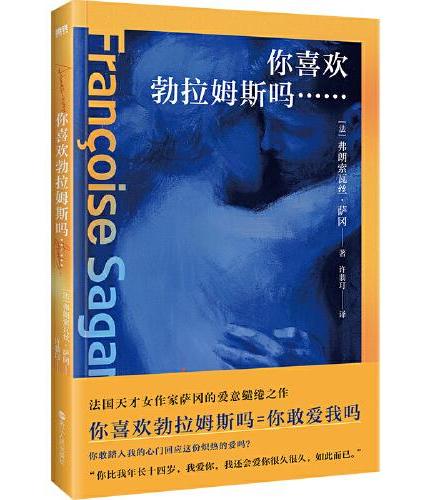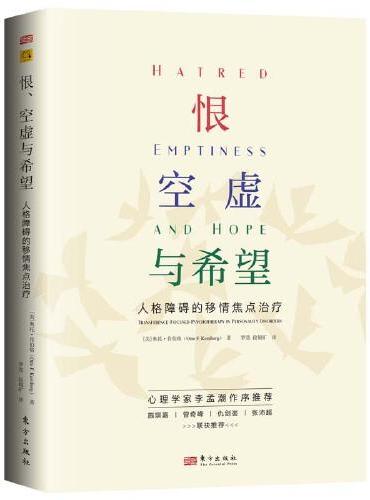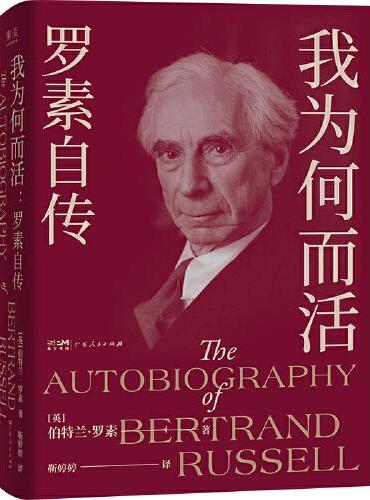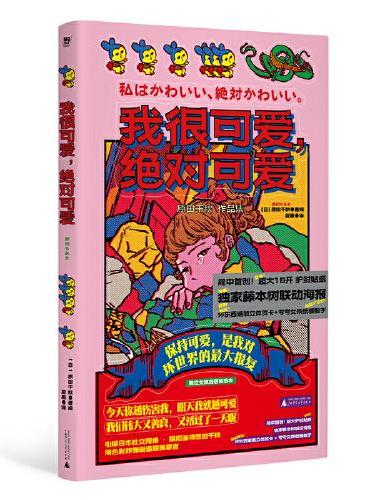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太极拳套路完全图解 陈氏56式 杨氏24式和普及48式 精编口袋版
》
售價:HK$
3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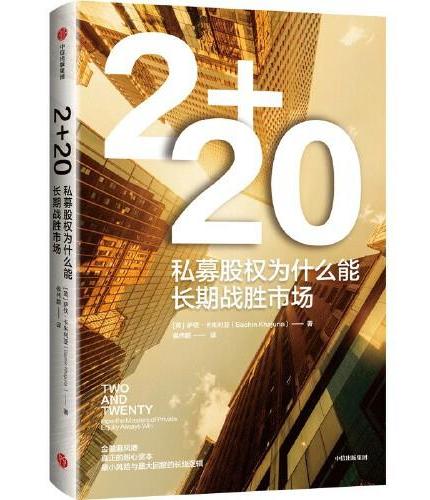
《
2+20:私募股权为什么能长期战胜市场
》
售價:HK$
8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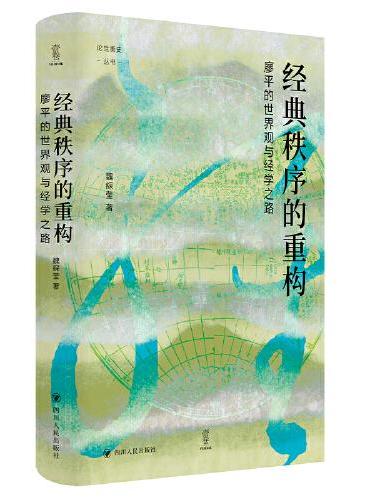
《
经典秩序的重构:廖平的世界观与经学之路(探究廖平经学思想,以新视角理解中国传统学术在西学冲击下的转型)
》
售價:HK$
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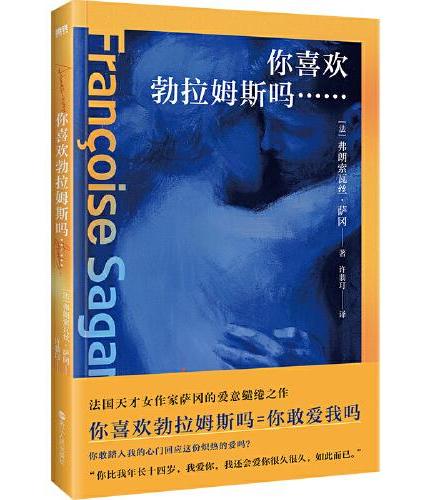
《
你喜欢勃拉姆斯吗……
》
售價:HK$
52.8

《
背影渐远犹低徊:清北民国大先生
》
售價:HK$
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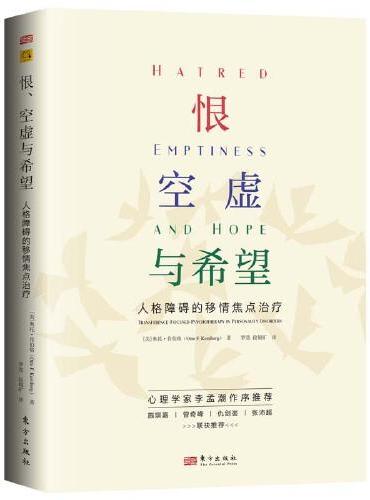
《
恨、空虚与希望:人格障碍的移情焦点治疗
》
售價:HK$
8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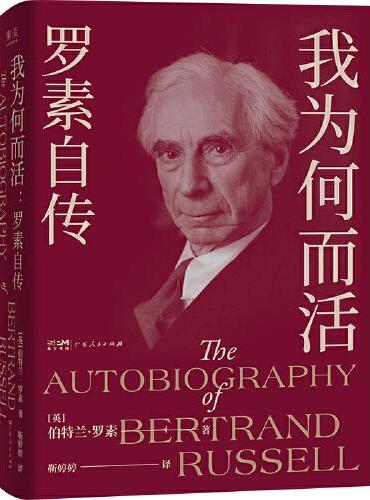
《
我为何而活:罗素自传
》
售價:HK$
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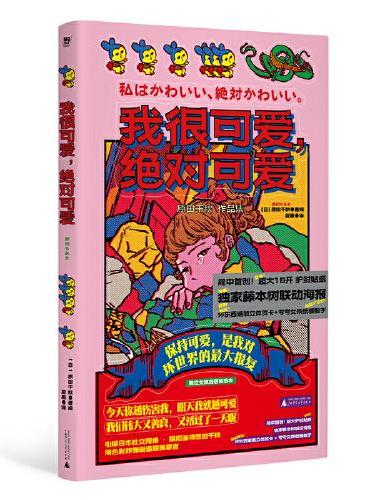
《
我很可爱,绝对可爱
》
售價:HK$
107.8
|
| 內容簡介: |
汤一介、乐黛云夫妇是北大未名湖畔的学界双璧,汤一介先生传承中国学脉,执掌《儒藏》编修,乐黛云先生则是中国比较文学的拓荒者。1952年秋,汤一介父亲、时任燕京大学副校长的汤用彤被分配住至燕南园58号。后来,汤一介与乐黛云一家又在这里历经了悲苦与喜乐。
耄耋之年的汤一介与妻子乐黛云,及其长大成人的女儿汤丹、儿子汤双用心回忆自1952年搬入燕南园58号以来,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和酸甜苦辣咸的五味杂陈,结成回忆家国往事的散文集《燕南园往事》。
87岁高龄的汤一介先生回忆了青年时期随父亲汤用彤读书、治学,回忆了母亲张敬平相夫教子、在战争年代守护家庭,回忆了与冯友兰、季羡林等北大学者相交的事迹。83岁高龄的乐黛云先生回忆了公公汤用彤的治学谨严、宽容温厚和“文革”时期的处变不惊,回忆了与王瑶、马寅初、朱家玉、裴家麟等北大师友同窗的交往岁月,回忆了政治风浪中儿女求学之路的噩梦。汤丹和汤双也回忆了幼年时期在燕南园的幸福时光和遭遇特殊时期所经历的大起大落。
2014年9月9日晚,国学泰斗汤一介仙逝,学术界又痛失一位大师。2014年10月出版的《燕南园往事》,成了汤一介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也是汤一介、乐黛云夫妇与一双儿女合著的唯一一本家庭回忆录。文字平实厚重、真挚深情,配以66张珍贵历史照片,深厚的亲情和时代烙印下的忧伤溢于言表,令人动容。即便是家庭生活中的日常琐事,言语间,其人生态度和哲学思想也尽现其中。
|
| 關於作者: |
汤一介:
一九二七年生于天津,一九五一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自一九五六年起一直任教于北京大学,从事中国哲学、中西哲学比较的教学与研究。一九九〇年获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并在海外多所大学任客座教授。生前曾任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主任、中华孔子学会会长。著有《郭象与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佛教与中国文化》、《瞩望新轴时代》等。
于2014年9月9日晚去世,享年87岁。汤先生一生恪守家训:“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 堪称思想文化的“守夜人”。
乐黛云:
一九三一年出生于贵阳,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现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法合办《跨文化对话》集刊主编。一九九〇年获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二〇〇六年获日本关西大学荣誉博士学位。著有《比较文学原理》、《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跨文化之桥》、《中国知识分子的形与神》、《跟踪比较文学学科的复兴》,主编有《世界诗学大辞典》(主编之一)、《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十四卷、《中学西渐丛书》八卷。
汤丹:
汤一介、乐黛云之女。十六岁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八年之中下过田、做过饭、管过账。返京之后考取北京大学分校图书馆学系,一九八二年毕业。其后在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获得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现为高级软件工程师,任职于跨国公司埃森哲(Accenture)。
汤双:
汤一介、乐黛云之子。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后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理论物理研究所(现称杨振宁理论物理研究所)获得物理性博士学位。曾任马里兰大学、俄勒冈州立大学博士后。现为美国Veson Nautical公司软件工程师。
|
| 目錄:
|
【目录】
前言
燕南园童年往事
在燕南园随父亲读书
燕南园五十八号的小喽啰对阵五十七号的大学者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我心中的汤用彤先生
父亲的矛盾心态
记我的母亲
当我幼年时
寻找溪水的源头
燕南园家中的老保姆
北京大学有三个“宝”
香山红叶山庄小住纪实
我在燕南园时期最难忘的一个人
马寅初校长住在燕南园六十三号
随秦元勋先生读书记
姐弟情深
燕南园的常客朱家玉
汤双在燕南园的大朋友施于力
发生在燕南园的人生变奏
在儿子八个月的时候
我的同窗好友裴家麟
“文革”时的中学生活
“井冈山”上小喽啰
燕南园的噩梦
从燕南园到黑龙江
我在八连的故事
鲤鱼洲干校的快乐时光
北大空前绝后的草棚大学
噩梦中的噩梦:儿女求学之路
同行在燕园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
|
| 內容試閱:
|
【试读章节】
燕南园童年往事
我们家
自从北大由沙滩迁入燕园,我们家就住在燕南园东南角的五十八号。我们的西邻是冯友兰先生家,北面对着周培源先生家,东北角则是冯定先生家的院子。
我们家是那种中西合璧的房子。前后有两个很大的院子。大门朝北。两扇大门上各嵌着一个铁环。门上书有一联黑字红底,因为年代久远,颜色有些暗淡,显得古色古香。一边书的是“园林无俗韵”,另一边书“山水有清音”。字体工整,苍劲,不知是否出自名家之手。门口有两个石礅儿和一道挺高的门槛儿。门上面是灰色圆瓦铺成的飞檐。大门东边有一棵紫藤萝,开花时节,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甜香,一串串紫色的藤萝花儿挂在飞檐上,非常好看。汤丹小时候常常坐在一根离地不高的藤条上,手里拿着一本小人书荡来荡去。藤萝的另一头沿着门边的十字形空花墙(我们称之为空空墙)一直伸展到墙外的大树上。花墙大概有两米高吧,中间有十字形的墙洞,很容易便可攀上墙头。坐在墙头上,晃着两条腿,吃着伸手可得的藤萝花蕊儿,优哉游哉。
走进大门的右手边是一个月亮门。月亮门里是一个小跨院。院儿里有两棵大柏树,北边是保姆们用的厕所和煤屋,东边则是一间储藏室。由于我们家有自己的暖气锅炉和大灶,要用很多煤,两棵大柏树就像长在煤堆里。煤屋里堆满木柴和废弃的家具,是捉迷藏的好去处。储藏室里有两口大缸,奶奶每年都用它们腌雪里蕻。腌好的雪里蕻放上点肉末儿和辣椒一炒,是爷爷最爱吃的一道菜。
腌雪里蕻是我们家的一个大工程。季节一到,奶奶总是让做饭的保姆去订购,再由合作社用车送来一大堆。家里的全部“闲人”,奶奶、姑奶奶、几个保姆和工友齐上阵,择掉黄叶子,清洗干净,再挂在一条绳子上沥水,然后一层层放到缸里,洒上大盐粒,再用大石头一压,便大功告成啦。奶奶会时常看看腌的雪里蕻会不会起“噗”(长一层白膜),汤丹时常也装模作样地跑去看。由于缸很高,踮着脚尖都看不到里面,每次都要用力一撑,撑在缸沿儿上观察,做饭的保姆就吓唬说谁谁家的孩子掉进缸里淹死了云云,汤丹当然不信啦。终于有一天一头栽进缸里,把脑门磕了一个大青包。
正是这间储藏室在“文革”中一度成为汤丹的栖身之地。爸爸成了“黑帮”之后,我们被勒令腾房子,汤丹便和被查封的书一起搬进了这个房间。房间里顶天立地地堆满了各种“毒草”,在两个书架之间架上一块床板,汤丹便睡在“毒草”丛中,博览群书。那时候不过十二三岁,有些书根本看不懂,但就此养成了读书的习惯。那是一段非常难忘的日子,虽然爸爸妈妈都进了劳改队,外界压力很大,但生活是充实的,还有几分快乐。
小跨院南边是进厨房的门。厨房门前是一个挺大的水泥台子,有两尺来高吧。春天的时候,奶奶会把藏了一冬的豆子拿出来晾,红红绿绿地铺了一地。夏天是晒箱子,秋天是雪里蕻,冬天则是冬储大白菜,一年四季都不闲着。快入冬的时候,做饭的保姆会到“河那边”去买白薯(未名湖北面有一个粮食站,不知道为什么家里人都称它为“河那边”)。买回来就堆在水泥台的一角,从那时候起,厨房的烤箱里时常会散发出烤白薯的香味儿,而我们对烤白薯的热爱也是从那个时候培养起来的。
过了月亮门小院往南一点儿是锅炉房,我们称之为地窨子。从地面到锅炉间要下十几级台阶,里面黑乎乎的,一个不太亮的灯泡悬在头顶,由于光线不好,那个灯泡就像悬在半空中一样,颇有点儿神秘之感。一旦我们在家里为非作歹,“关地窨子”便是最严重的警告。地窨子是烧锅炉的刘大爷的地盘儿。刘大爷长得黑黑瘦瘦,掌管着燕南园很多家的锅炉。每当我们在地窨子门口儿探头探脑的时候,刘大爷总是不客气地大喊“去去去,这不是小孩儿玩儿的地方”!“文革”开始后,各家的锅炉都停烧了,刘大爷无事可干,只好回乡。临走前,也许是为了弄一笔养老费吧,他挨家挨户去“算剥削账”。可能他知道我们家不是特别富,说了几句,就放了我们一马,也没真的拿钱。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
地窨子对我们有着特殊的吸引力,趁刘大爷不在,我们会偷偷溜进去,搬出一堆瓶瓶罐罐和大包小包的化学药品(这些东西都是叔叔汤一玄玩过剩下的),开始 “科学实验”。那时最常和我们一起进行这种冒险活动的,是周培源先生的两个外孙。我们当然搞不清那些白的、黄的粉末和晶体是什么东西,但是发现如果把白色的粉末加水再和蓝色的晶体混合,瓶子里就会发出阵阵恶臭,冒出缕缕青烟,要是再能从飘荡的青烟中钻出一个巨人,满足我们的三个愿望,那该多好啊!所幸那些化学药品都不会爆炸,不然还不知道会是哪一家的公子眇一目呢。
地窨子侧面是一间用人房和一间洗衣房。洗衣房里有两个大水池,足有一米高,通常用来洗衣服,但我们却用来大战三百回合,一人占领一个水池,打得不亦乐乎,搞得满地都是水。
逢到春节,奶奶总是要做很多水磨年糕。开始时用一个大盆泡江米,然后用一个小磨磨江米面。小磨上有一个眼儿,一勺一勺喂进去,转动小磨,带水的江米面便沿着小磨边的槽流进一个布袋里。洗衣房的水池里便渐渐地堆起这样的布袋,一袋压一袋,上面再压上小磨盘,过年的时候就可以吃上各式年糕了。那个时候没有塑料袋,洗衣房的另一个水池里是用布袋装的炸萝卜丝丸子。那种炸萝卜丝丸子凉了非常好吃,后来我们曾经试着做过好几次,再也找不到那个味道了。记得有一次奶奶让做饭的林阿姨拿一袋萝卜丝丸子送给隔壁家的冯奶奶,汤丹便等在厨房里看林阿姨是否会从冯奶奶家带回什么好吃的,结果冯奶奶回赠的居然也是萝卜丝丸子,真是令人大失所望。
用人房一度住着小高叔叔。他是我们家另一个保姆道兰阿姨的丈夫。小高叔叔是与燕南园一墙之隔的小理发店的理发师,常到家里来给爷爷理发,还会变戏法儿。听说小高叔叔的技术特别好,后来进了中南海,专门为大首长们理发,还曾给朱德将军理过发。虽然小高叔叔和道兰阿姨在“文革”前就离开了我们家,但是在“文革”最困难的日子里,他们还常来看望奶奶。
在我们家被赶出燕南园之前,汤丹是这间用人房的最后一个居民。由于那间放书的储藏室后来也被收走了,那些书连同汤丹一起就搬进了这间用人房。这间房比储藏室小很多,由于书太多没地方放,只好全部放进一个个木制的书箱里,摞在地上好几层,上面搭一块床板,汤丹便高卧在一大堆“毒草”上。为了找想看的书,常常得倒腾那些书箱,似乎变得力大无穷。在“文革”中汤丹认识了一些北大的大学生(也都是红卫兵),他们有时会到这儿坐坐,借几本“毒草”回去“批判”。他们开玩笑地称这块地盘是“资产阶级窝儿”。
大门的左手边,是一大片草坪和一个花坛。早先的花匠是洪大爷,他的样子看起来有点吓人,驼背,还瞎了一只眼睛,说起话来声音沙哑。除了我们家,他还兼管冯友兰先生家和褚圣麟先生家的花园。洪大爷好像很偏爱芍药,沿着墙根种了许多。天暖和的时候,他常常拖着一根胶皮管浇花、浇草地,我们就跟在他周围玩水,尤其是我,对那根胶皮管情有独钟,常用一个手指堵住管子头,把水滋得到处都是。洪大爷不像烧锅炉的刘大爷,他虽然沉默寡言,但从来不因为我们在那儿调皮捣蛋而轰我们走。秋天,他会把落叶扫到一起,堆成一大堆烧掉。每到这个时候,我们总会围着火堆打转,火实在是太好玩了,如果捡一些松枝扔进火堆,火就会突然变大,洪大爷就赶紧用他的大扫帚把四处乱飞的火星扑灭。我们也经常捡一大堆瓜子碴(枫树子)塞到火堆下面烤,烤熟的瓜子碴吃起来很香,不过不能吃太多。我就曾经因为吃了太多的瓜子碴而中毒上医院。洪大爷离去得很突然,谁都不知道他是为什么走的。接替他的是贾大爷,但我们都不喜欢他。他不但不让我们玩水、玩火,草地和花也管得不如洪大爷。那个花坛就是在贾大爷的时代消失的。
我们家的院子以房子为界,分成前院和后院。前院里有一棵很大的白果(银杏)树,树下有一个长椅。天气好的时候,奶奶、姑奶奶和保姆们会坐在树下晒太阳,织点毛线活儿、聊聊天儿,别家的保姆时常也会参加进来。有时候我们也跟着在那儿晒太阳,由此也听了一耳朵的张家长李家短,诸如某家的阿姨曾经是妓女、某家的太太如何抠门之类。每到白果收获的季节,成熟了的白果会掉满一地。随着白果皮的腐烂,周围会变得恶臭难挡。我们时常想,《西游记》里的“稀柿胡同”大概也不过如此。去掉腐皮清洗干净之后的白果可一点也不臭,白白胖胖的,拿到大灶上用个盒子一扣,等听见“咚”的一响,就可以吃了。
比白果更有吸引力的是毛桃。后院里有两棵毛桃树,每年能结很多果。毛桃虽然不好吃,但却是我们的生财之道。因为毛桃核可以入药,海淀土产收购站便收购毛桃核。毛桃成熟后,会裂开一道小口,使点劲儿就能掰开,花不了太多工夫就能收获一小袋毛桃核。冰棍钱、酸枣面钱就全有啦。毛桃树胶更是个好东西,搞一小团粘在竹竿上,什么样的蜻蜓、知了(鸣蝉)都能拿下。毛桃树胶只有在树的天然裂缝里才有一点,物以稀为贵,所以还能用它同别的小孩换我们想要的其他小零碎。
前院里还有一棵龙爪槐,夏天会有很多“吊死鬼”(一种浅绿色的肉虫)拖着丝挂在树梢上。我们常常把它们摘下来,捏着上面的一根丝,拿去吓唬人。“吊死鬼”的另一个用处是可以喂鸡,拿一个玻璃瓶,把“吊死鬼”一只只装到里面,拿去给家里的几只老母鸡吃,也算没白吃它们下的蛋。我从小就不怕虫子,这一定是得自妈妈的遗传基因(爸爸对虫子怕得要命)。她小时候就曾经将一条用水彩画得花里胡哨的大肉虫放在铅笔盒里,把老师吓得嗞哇乱叫。我也干过类似的事,带了大批的蚂蚱、蛐蛐去幼儿园,为的是让用积木搭成的“动物园”里能有些活的“动物”。结果被罚放学不许回家,坐在那里反省,直到家里大人来领,才被释放。
房子正门前的马尾松是现在五十八号院里剩下的唯一一棵老树,它还活着,但下端的枝丫全被砍掉了,像大病后被截了肢的老人,一副风烛残年的样子。四十多年前它是院子里最茂盛的树,低处的树枝几乎触到地面,我们可以沿着树枝一直爬到树梢。汤丹还敢坐在顶端的一根树枝上,上下忽悠着玩,吓得管她的保姆杨大大直叫:“小姑奶奶,快下来……”汤丹从小就喜欢登高爬低,以冒险为乐事。爬树、上房、在墙头上奔跑,都是家常便饭。最刺激的一幕,发生在一九六四年我们去青岛度假的时候,那是北大组织的暑期活动。刚到旅馆,大家都在一间屋子里等着分房间。汤丹上完厕所要出来时,厕所的门却怎么也打不开了。大家正在外面想方设法试图打开那个门,汤丹却等得不耐烦,居然从厕所的窗户钻了出去,试图沿着不到半尺宽的水泥边沿走过来。当时把在场的人都吓坏了,也没人敢出声阻止,生怕她一分心反而掉下去。那可是在六层楼上!一旦掉下去,肯定是没命了。大家就这样提心吊胆地看她演“杂技”,还好,总算有惊无险地走过来,从我们这边的窗户钻了进来。这惊心动魄的十几秒,现在想起来还让人心有余悸。
说起青岛之行,还有一件趣事。在去青岛的火车上,我们正好和著名物理学家黄崑先生一家坐在一起。那时我还在上幼儿园,觉得世界上很多现象难以理解,现有大教授坐在对面,正好可以请教。于是向黄先生提了一个问题:人站在地球上,而地球是在转的,如果说白天人是头朝上的,那么到了晚上,地球转了半圈,人岂不是头朝下了吗?由于这个问题牵扯到相对参照系,大物理学家着实费了一番唇舌来解释,还在纸上画图认认真真地讲解。后来,黄先生又问我长大了想做什么,我说想像他那样,当个科学家。不料黄先生却十分严肃地把我教训了一顿,说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应该从小立志当工人或者农民。搞得我非常不好意思。也是在那次旅行中我认识了黄先生的两位公子。由于黄夫人来自英国,他们的两个孩子长得完全一副洋人模样,黄头发、蓝眼睛,在学校的外号就是“大黄毛”和“小黄毛”。我后来也到他们家里去玩过,再后来还和“小黄毛”成了冬天在未名湖冰场打冰球的伙伴。他们住在北大的一栋公寓楼里,室内陈设极为简朴,很难想象这里住的是从英国归来的大教授。尤其与燕南园中的那些教授之家相比,更有天壤之别。曾经有人传说黄先生把工资的三分之二都交了党费,我相信这多半是真的。
接着说我们的庭院。在前院和后院之间有一条小路,小路的一侧有两棵巨大的海棠树,春天开花的时候几乎可以用遮天蔽日来形容了,但结的果却又小又涩。小路的另一侧有一棵枣树和一棵白果树,和前院的那棵白果树不同,它从来不结白果。据保姆杨大大说,因为这棵树是棵“男树”。
后院里有两棵白丁香和一棵紫丁香,每到春天满院都是浓郁的花香。院里还有枫树、梨树、李子树、毛桃树、桑树、樱桃树和一大架葡萄。另外还有一棵小树,树干上枝枝丫丫,我和汤丹一个记得是花椒树,一个认为是山楂树。总之,它从来没结过任何果实,那时就说不清它是什么,现在就更无从考证了。
说来奇怪,我们家的果树大部分都不结果子。记得有一年,梨树上结了一个梨,全家人都跑出来看。可惜好景不长,不久它就掉到地上,最终没能成熟。倒是樱桃树每年都能结些樱桃,这种樱桃和现在市面上卖的不太一样,个子比较小,鲜红鲜红、亮晶晶的,又酸又甜非常好吃。那时候也不怎么讲究卫生,经常把樱桃从树上摘下来,洗都不洗就往嘴里放。夏天,樱桃树还会招来一种叫“红辣椒”的小蜻蜓,身体是鲜红色的,翅膀略带一点金色,几十只落在树上,很是壮观。这种蜻蜓比较傻,甚至不用桃胶,只要小心翼翼走过去,用手快速捏住翅膀,就可以捉到一只。现在也搞不清为什么小时候对捉蜻蜓有那么大兴趣,不光我们,园里别的小孩也常来和我们一起捉。
大桑树是我们家另一棵每年都能结果的树。桑树下端的树干光溜溜的,很难攀上去,好在它离房子很近,就在爷爷卧室的窗户边上,汤丹就先登上爷爷的书桌,然后从窗户钻出去爬到树枝上坐下来大嚼桑葚,每次都要吃到满嘴黑紫方肯罢休。不过,上去容易下来难,要从树枝上下到窗台上相当困难,好几次都是靠爷爷的秘书林叔叔用梯子把汤丹弄下来的。这时候奶奶就会笑话她“小耗子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吱啦吱啦叫奶奶”。后来汤丹发现从房顶上可以轻易地爬到桑树上去,而且高处的桑葚更大更好,于是就采取了新的路线。当然,上房顶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需要先上花墙,翻过一个用人用的小厕所的屋顶,再从我们家和冯友兰先生家的隔墙上面走过去,最后翻上正房的顶。而且房顶的坡度很大,在上面行走得有相当的本事。在登高爬低方面,我们俩的天赋差别很大,汤丹从小就能“飞檐走壁”,而我对这类事总是敬而远之。结果是汤丹能吃到很多大桑葚,我只能望桑葚兴叹,后来干脆采取阿Q精神,宣布根本就不爱吃桑葚。
爷爷的房间的窗下有很多丛被称为“七仙女”的粉色蔷薇,开起来,十分繁茂艳丽。窗外是很大一片空地。空地上种着一大片草莓。黄昏时分,妈妈常带着我们,用长胶皮管给草莓和葡萄浇水。这是我最爱干的活儿,经常拿起胶皮管四处乱滋,尤其喜欢用四处飞溅的水吓得堂妹又哭又喊。有一次,真把她的裙子全淋湿了。她的尖叫把我婶婶和奶奶都惊动了,全跑了出来!妈妈气得揍了我一巴掌。回想起来,这是平生唯一的一次挨打。
除了西边有月亮门的那堵墙外, 天井的北面是一间很大的客厅,爷爷将它隔为两间,里间较小,用作餐室;外间较大,是爷爷的书房和客厅。这里四壁都是装满古书的玻璃橱柜。爷爷常在这里读书和接待一些来访的客人。天井的南侧是两间向阳的大屋子,一间是爷爷和奶奶的卧室,另一间是叔叔一个人的房间,堆满了冰球杆、手风琴、录音机、电唱机等时髦玩意儿。后来有了我们,这间大屋子就让给了我们和保姆,叔叔则搬到天井东侧的一间屋子。
冬天的时候,在天井中捉麻雀也是一件十分有趣的活动,不过得有耐心。拿一节劈柴支住煤筛子的一边,劈柴上拴一根绳子拉到屋里,在筛子下面和外面都撒上一些米,就可以坐等麻雀来自投罗网了。麻雀吃了筛子外面的米,尝到甜头,就会去吃筛子下面的米,这时候把绳子猛地一拉,麻雀就被扣在筛子里面了。最难的是怎么把麻雀弄出来,通常得请叔叔汤一玄出马。他会用一根筷子伸进筛子眼,先将麻雀压住,再掀开筛子把麻雀拿出来。绝对属于高难度动作。
曾经有一段时间,汤丹还在天井里养了一对荷兰猪(一种鼬鼠)和两只大白兔。有一年冬天,隔壁冯家在他们家的天井里晒大白菜(我们两家的天井只有一墙之隔),两只兔子可能是闻到了白菜味,居然在地上掏了一个洞,钻到墙那边,把冯家的白菜吃了个乱七八糟。弄得我们家非常狼狈,不知如何是好。
汤丹小时候做事经常心不在焉。有一次黄昏时分她嘴里含着块糖在天井里玩儿,一不小心嘴里的糖掉了出去,她随手在地上一摸,捡起糖又塞回嘴里。后来保姆喊她进屋吃饭,她还自言自语道“吃饭了,糖就不要了吧”,随口把糖吐到地上。岂料吐出来的竟是一颗黑乎乎的东西,原来她塞回嘴里的不是糖而是一枚兔子屎!很长一段时间这事儿一直在家里传为笑谈。
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兔子们的末日也来临了。由于实在没有东西给它们吃,家里做了一个现在看来十分残忍而在当时却非常自然的决定:把它们杀了吃肉!决定虽然做了,可没有人真能下手杀兔子。最后找来妈妈的一个朋友,叫施于力,这是个什么都敢干的人,他两下就摔死了兔子,然后剥皮、送到厨房里去做红烧兔肉。为这事,汤丹很长一段时间对他都耿耿于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