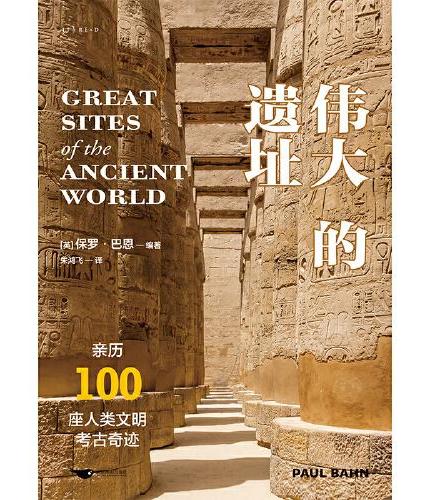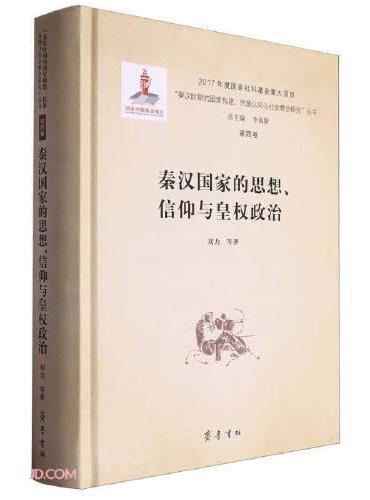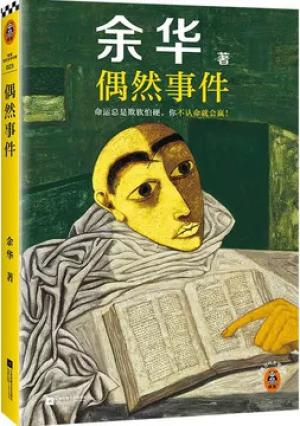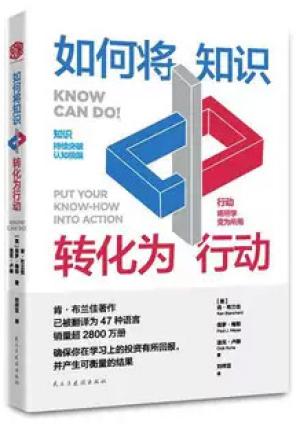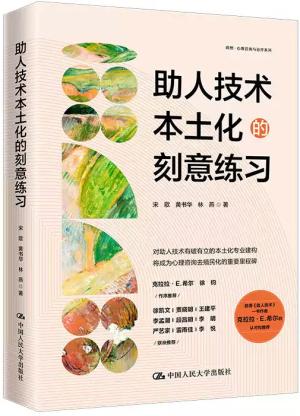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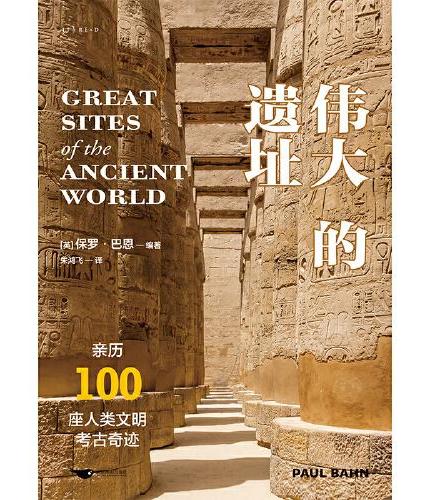
《
伟大的遗址(亲历100座人类文明考古奇迹)
》
售價:HK$
20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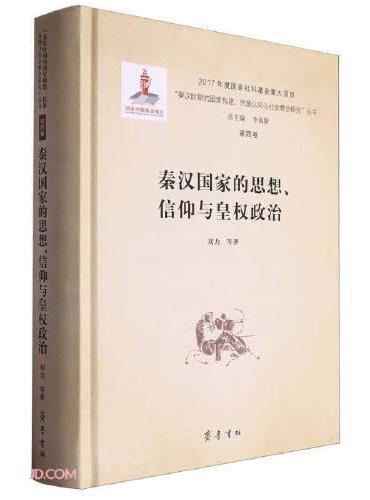
《
秦汉国家的思想、信仰与皇权政治
》
售價:HK$
215.6

《
反卷社会:打破优绩主义神话(一本直面焦虑与困境的生活哲学书!)
》
售價:HK$
8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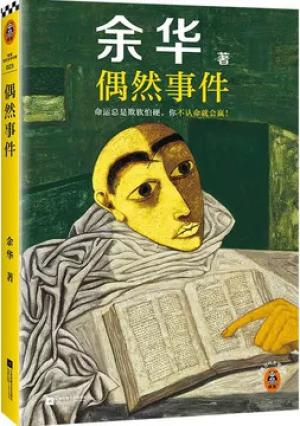
《
偶然事件(命运总是欺软怕硬,你不认命就会赢!)
》
售價:HK$
54.9

《
余下只有噪音:聆听20世纪(2025)
》
售價:HK$
20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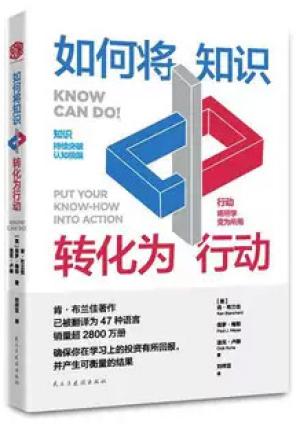
《
如何将知识转化为行动
》
售價:HK$
7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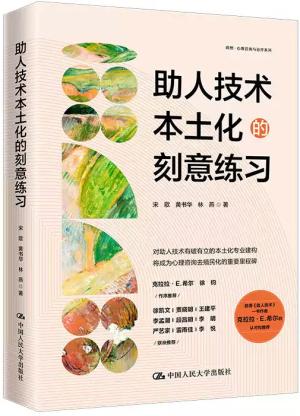
《
助人技术本土化的刻意练习
》
售價:HK$
87.9

《
中国城市科创金融指数·2024
》
售價:HK$
107.8
|
| 編輯推薦: |
小说《生命》是一曲感天动地的生命之歌。叙述者“我”通过在病床上的回忆、渴望和倾听,严肃而冷静地讲述了他那与死亡赛跑的生命。小说以非凡的叙事技巧,将与疾病、器官移植、恐惧和寂寞交织在一起的生命展现为主人公对爱与死、责任与幸福有保留的、近乎带有讽刺意味的自我反思,深邃而不善感。整个表现感人至深,启人深思并充满生存智慧,使读者掩卷之后会对生命中的许多东西产生不同凡响的思考。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
|
| 內容簡介: |
大卫·瓦格纳曾因肝病接受了肝移植手术,他以此为主题创作了自传体小说《生命》。
作者从自身的经历和感受出发,讲述了一个接受肝移植手术的病人前前后后的生活与心路历程。主人公在病房中经历着各种生死事件,同时也思考着自己的生存与死亡。病房就像主人公身上的导管一样,是一个接口,连接着生存与死亡,身边不断有病友进进出出……主人公最终成功移植了肝脏,在康复期间,他又无数次的想起捐献者,想到两个生命彼此依存而获得生命的延续,想到生命的种种色彩……最终,主人公选择拥抱生命,在生与死的竞争中获得了胜利,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获得了一次新生。
《生命》是一部难得的真诚的作品,大卫·瓦格纳写的就是自己的切身体会,他把自己怎样被病痛折磨,又怎样一步步战胜了死亡的一点一滴都记录下来。主人公以强大的毅力抵抗住了病痛,在生与死之间,带着希望,带着对生命的热爱,将冷静的目光投向了生命的深处。
|
| 關於作者: |
|
大卫·瓦格纳,德国作家,1971年出生于莱茵河畔的小镇安德纳赫,现居柏林。大学时代在波恩、巴黎和柏林攻读比较文学和艺术史。曾居留罗马、巴塞罗那和墨西哥城。作品有长篇小说《我的夜蓝色的裤子》《四个苹果》,短篇小说集《都缺什么》,散文集《孩子说》《柏林有什么颜色》《墙公园》。他曾因肝病接受了肝移植手术,以此为主题创作的自传体小说《生命》2013年获莱比锡书展大奖,入围2014年度“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
|
| 目錄:
|
目录
血
当孩子们睡了
一个新的生命开始
疲倦的长颈鹿
雪
结语
|
| 內容試閱:
|
血
午夜之后我回到家。孩子在她母亲那儿,女朋友没在,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在冰箱里,找到了一瓶打开过的苹果糊,拿勺子舀着,一边翻着还摊在厨房桌子上的报纸,我读着有关蚊子的文章和它们在雨中为什么不会被落下的雨滴打死的问题。我还没弄明白它们究竟是如何逃生的,我的嗓子痒了。我呛着了?被苹果糊呛的?
我起身,走进浴室,照着镜子,没看到什么特别的,什么都还那样,也许有点儿苍白。这会儿我已经在浴室了,想就刷牙吧,反正一会就要睡觉了——可就在这一刻,我觉得我要呕吐。我转过身,弯腰趴向浴缸,已经一口喷出来了。当我睁开眼睛,我被浴缸里的这许多血惊呆了。它慢慢地流向下出水口。
我明白,这意味着什么。B先生,我的医生,我十二岁起就是他看的,几年来经常警告我的。我知道,这是食道静脉曲张,我食道中的静脉爆裂了,我明白,现在我正在内出血,我不能晕过去,我必须给急救医生打电话。尽管如此,我在考虑,我考虑得很慢,叫一辆出租车去医院,但最后我还是决定叫急救医生来。在镜子里我看到,我变得更苍白了,去找电话,在书房的书桌上找到了。还真有本事,竟然拨错了紧急电话,我拨了110,听到一个声音在说:叫救护车您得拨1-1-2。我挂下了,问自己,这是不是一个信号。我最好还是待在家里?叫一辆救护车去也许有点夸张?我等了一分钟,电话还在手里,然后告诉自己,我最好别在这儿出血死了,下个星期,还是在复活节假中,孩子就要回来了。于是我又拨号,小心翼翼地,这两个键紧挨着,1-1-2。一个亲切的声音回应,告诉我,我得打开房间门,开着,——不过,我还是决定,重新穿好鞋、外套,去外边迎一下医生。我知道,在这儿他没法为我做什么,我必须去医院。
我在楼梯上迎面碰上了急救医生和两个救护车助手,打了招呼,说:就是我,我必须去医院。我马上注意到,他们把我当成了装病的人,他们没有看到浴缸里的血。在救护车上,我坐在担架椅上,朝后坐着,医生不知道拿我怎么办,他看着我的急救和器官捐助证。我说,我得去菲尔绍院区,夏洛蒂医院的菲尔绍院区,我报告着我的自身免疫性肝炎,肝硬化,食管静脉曲张,还有我肝门脉高压等等,说着说着,我感觉到嗓子口又有什么东西了。手刚到嘴边,血已经猛地喷出来了,溅满了半个车。一幅泼墨影片景象,几乎让我发笑,只可惜这会儿不是人工的溅血。那个急救医生,惊呆了,我的血顺着他的两个眼镜片流下来。他给我按上针头,给我输盐水,车终于开了。稍过了一会儿,我看到街边树的摇曳,还有顶上的星星——我很吃惊,为什么这个急救车怎么就没有车顶呢——,我又要吐了。我躺着,一半吐进了透明塑料袋里,大部分流到外边,溢到地上了,我知道,这血若不马上止住,我就会死的。
病史:胃肠道出血史。已知静脉曲张病史
药物治疗:100毫克静脉注射丙泊酚
发现:在食道下部三分之一处可见四处直径大于5毫米静脉束。(静脉曲张突出管腔直径50%,相互接触,Ⅲ度)。在贲门以下胃小弯一半处浅表静脉呈鲜红色。活动性出血。胃部有凝血块,评估不足。
治疗:在距牙齿34厘米至39厘米一段橡皮圈结扎6处,内镜治疗下止血。
1
我醒来,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一根管子插在我鼻子里,新鲜清凉的空气,山风,还带着些异样的味,沁我心肺。一条半结冰的林间小溪在高高的松柏间穿行,结了白霜的草在太阳下闪着光——我显然在画着一幅年历画。我听见呻吟和杂音,听到点滴和沙沙的声音,还感觉到一只手在我的左上臂,抓住我,拽得很紧——然后又松开。这不是手,我一会儿就注意到了,这是一个带绷带的自动血压器,每过一刻钟就量一次,记录它,然后又到睡眠状态。听上去,像人吹充气垫。在这个充气垫上我漂向海洋。
2
他们站在岸边向我招手。他们在等着我,他们都到了,我的妈妈,我的外婆,吕贝卡,亚历山大,我的外公穿着制服,我的曾祖父母,第一眼我没认出他们,因为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他们来了,来欢迎我,他们站在沙滩上向我招手,对,真的,我听到他们呼唤我:欢迎,你总算到了——可一个大浪袭来,没有把我推到沙滩上,像我期待的那样,呵,不,一股暗流又把我拉回到海里,更远了,很快,岸在我的眼里消失了。
3
我睁开黏着的眼睛,眼前一片模糊。一个房间满是彩色斑点——这倒使我想起,可能是我没有戴上眼镜。不知道会放在哪儿。尽管如此,我还是可以看出点东西,我只要稍稍眯上眼睛:窗户在右边,门在左边,门是开的。很多器具围在我身边,电线,三个还是四个显示屏,我听到嘀一声。指挥中心?我喜欢我的宇宙飞船,我这么轻盈,没有重量,我能飞。
4
城市上空很亮,我飘动着,往下看。我看着,又重新想起来了,我什么也没忘。这医院的平顶,这白色的鹅卵石,那运河,那发电厂,站台,这一切,我都可以看到,我躺着,我在这城市上空飞着——几分钟后,几个小时后,或是几天后我才会回来,回到我的皮囊里,回到这张床上。
5
呵,怎么,我没躺在坟墓里,我没躺进土里。天亮了,然后又黑了。我躺在医院的一张床上,在一张有轮子的床上,我会被推出去。如果我转一下头,我会看到天空。今天它是白色的,前面垂着光秃秃的桦树枝。窗户是斜开的,清冷的空气新鲜甘甜,我听到了鸟儿,它们叽叽喳喳,意味深长。一道阳光透过云层射过来,照到另一边,红砖墙的后面,海的另一边,有一个坟墓,我曾到过那儿。
6
有人洗我的背,刷我的牙。我什么都不用做,只要躺着,我甚至不用吃饭,一个护士给我带来宇航员营养,流质餐,凡身体需要的,里面什么都有了。
宇航员饮料是香蕉味的。现在我知道了,我完全明白了,这个房间真是我的宇航船,我是在飞向火星。至少到火星。即使是轨道再便捷,也要花一年的时间,或更长。我适应了,我待下来。
7
我的眼镜又在了。我戴上它,看看周围,又把它拿下来。我想,这一切我不需要看得那么清楚。
8
我问起B。听到了,他不在,他休假。一个肠胃专家走进房间,叙述着是如何把静脉出血止住的。是用内窥镜的方法把它给制服的,也就是说,用一根软管推进我出血的食道,在这根软管里,装有一个仪器,通过它,把一个橡胶夹子夹在爆了的静脉上,这样,静脉曲张出血被控制住。我很幸运,这项技术出现的时间还没多久。就在二十年前,面对这样的出血,人们没法做什么。我失去了几升血,我的血红蛋白值不好,还有肝的数值,也因为出了那么多血,导致了蛋白丢失而更加糟糕。但,我活着。
一个新的生命开始
两点刚过电话来了。我吃过午饭,坐在我办公室里,一个声音说,瓦先生,我们有适合您的捐献器官了。我等待着这个电话,我一直害怕这个电话。孩子没来,周末才该再来,我已吃过饭,不必饿着进医院,而且别的没什么打算。太阳照着,我想,嗨,我多想再呆会儿,或许几年。可还是说:可以。之后那声音回答,他们现在就派救护车来。
四分钟后我站在楼下房前等着。有空的停车位,城市空着,柏林放暑假,很热。我看着花盆,里面花开着,看着铺石路,看着步行路板之间的脏物,看着马路对面咖啡屋前的桌子。大约一个小时前,我觉得,好像过去了好多年,我在那里刚吃过饭,服务员招呼着,我们相互认识。
我身边放着一只棕色旅行包,我随便扔进了几件东西,不是所有东西都在门边准备好了——尽管我知道,电话随时都会来,可没想到是此刻。或许我根本就没愿意这么想,屋里穿的鞋,我现在想到了,总之是被我忘了。当女理疗师三天后逼我第一次重新站起来的时候——站起来是最重要的,女医生说——, 我脚上戴着橡皮手套,很怪异的样子。我觉得可笑,可是笑起来就疼。
我记得,我另外一次准备得还更不充分。我从一块步行路板挪到另一块,我走来走去,不得不,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想起,我的电话已经响过一次了,在一个结冰地滑的冬夜,凌晨四点,孩子在隔壁房子里睡着。还没有完全醒来,拿起话筒,听到一个声音,说了我刚才听到的同一句话:瓦先生,我们有了适合您的捐献器官了。我即刻回答,根本不需要思考:不,最好不。最好不,我想,因为,否则我会吵醒孩子,而且,我怎么向他解释我要进医院,在深夜里?我原本可以把隔壁女邻居或孩子的母亲叫来的。
第二天上午我打电话到器官移植中心,问,我是否做梦接到了电话。我不知道是不是做梦听到了,或者,我想说服自己,已经不知道了。相信我只是做梦听到了这个电话,我觉得是个好的理由,因为我当然知道,我应该答应才是。什么时候,有人要帮助延长我自己的寿命呢?我了解到,我的电话的确响过。我说“不”之后,另外一个在等待的病人高兴了。
我后来打电话告诉了B我都拒绝了什么。我没听到指责,但他建议我以后不要再拒绝了。我决定在等待名单上呆着,已经等待的时间不会作废。
四五个月之后静脉破裂。
[……]
94
我看到光,很多光,一盏大灯。我飘在城市上空,这座城叫什么来着?我甚至有翅膀,看呢,我是一只鸟,是一只自由国度的鸭子,我游着,飞着,潜水,对不起,我的名字是唐老鸭。
109
一只乌鸦落到了支撑那只干瘪风向袋的棍子上,风向袋让我想起一位长发修女的帽子。现在的修女还戴帽子吗?尽管这曾是护士们的圣像,她们现今不再戴帽子了。我突然想起薄伽丘《十日谈》里的木刻画,正是因为这些大多色情的木刻画,我很早就对此书着迷,我时不时地翻着看,书就在我父亲房间,书架最下边。插图里几个修女是裸体的,其中一位头上戴着情人的裤子,而不是帽子。风吹动了布做的袋子,它动了一下,应该是阵风,之后又耷拉下去。
雪
273
突然没有菜单了。这些打孔卡,这些文物,这电子处理数据的小黑板,至今为止,我每天都要在上面画叉,点爱吃的菜,现在取消了——奇迹出现。现在来了一个护理员,带了一个电子的定菜器,进房间问我们想吃什么。有点儿没劲儿,他得带着它进每个房间,读着同样的东西。我已经开始想念那些卡了。
274
一个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女人一声不吭走进屋里,开始拖地,她的拖把撞击着每个桌腿椅子腿。我疼,这些桌椅腿,这些凳子,纸篓,他们就是我的同志。而这个女人把它们这样推来推去。
她又向门的方向拖,马上就要离开这个房间了,我说了声:谢谢。她抬头看我,好像这会儿才注意到我,看着我,向后捋了一下盖在脸上的发绺,轻轻清了下嗓子,嘴角向上咧了一下,这看起来像是个微笑了,轻声说了声:不客气。
275
我的邻床卡尔-汉茨,要出院了,他原来是民主德国海军驱逐舰上的厨师,他有一个生活至理名言留给我:每一天都是新的,现在即永远,每道菜只会吃一次,没有错过的机会会回来。
我会努力,不忘记它。
276
医院星期天的下午。我累了,从浴室回来,我累了,在走廊散步,我累了,向外眺望,我累了,来回翻动的书页,我几乎没读到什么。又是我们俩躺在席梦思上。你一直都在,当我睡下,当我起床,当我又躺下,在床上翻来覆去。我在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动作,都感觉到你,我们一起躺在这个筏上,我们一起漂洋过海。
277
而所有这些记忆碎片,这些怀疑,这些尴尬,这小小的医院愉悦,也许只要这样记录下来,就将是感谢信的一种。
对,重生,我将藉此新的生命重新开始。那个总在这儿来回嚷嚷的清洁工是对的,我不能只是躺着,我得做些什么,应该去拿活页本或者笔记簿,钢笔我已经有了,很好写的。我应该掏出钢笔,拧开笔帽,就这样开始,我已经想好了第一个句子,可以就是这样:午夜刚过,我来了——床头柜上的手机振动,开始在平滑的桌面上移动,我伸过手去,拿住它,按接听,开始没听到什么,过一会,一个声音,说:爸爸?你很快就能回家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