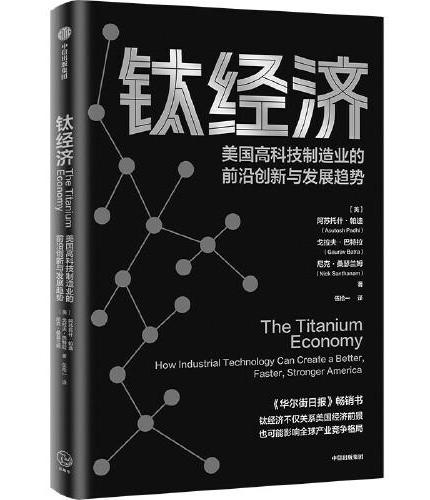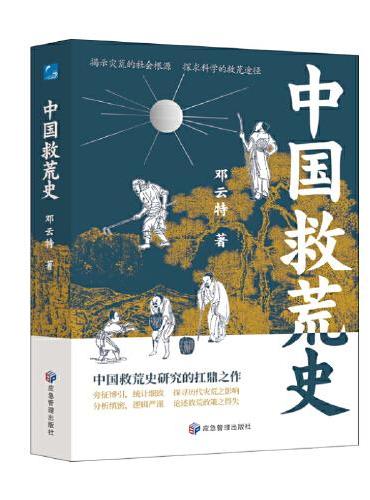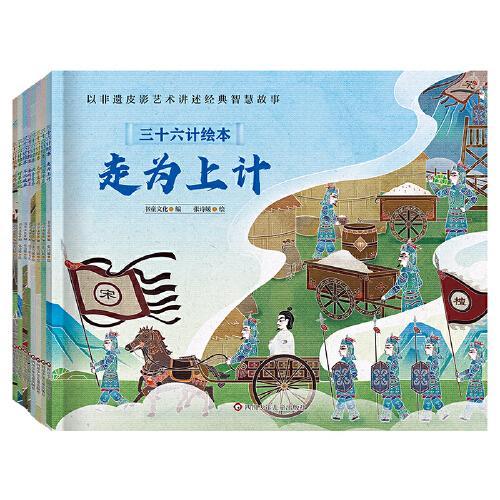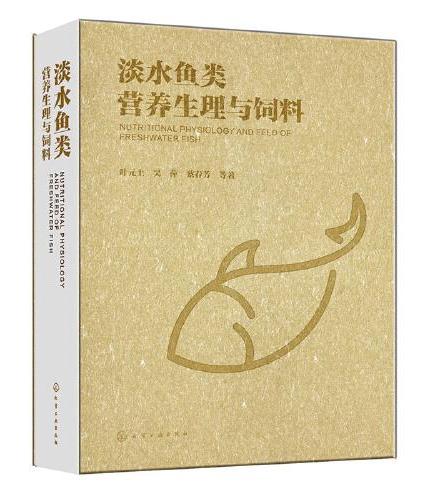新書推薦:

《
现代化的迷途
》
售價:HK$
9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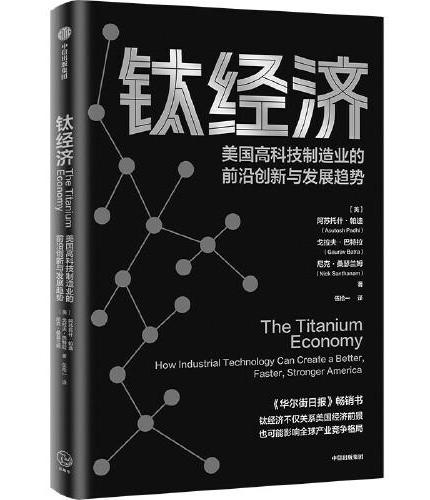
《
钛经济
》
售價:HK$
77.3

《
甲骨文丛书·无垠之海:世界大洋人类史(全2册)
》
售價:HK$
32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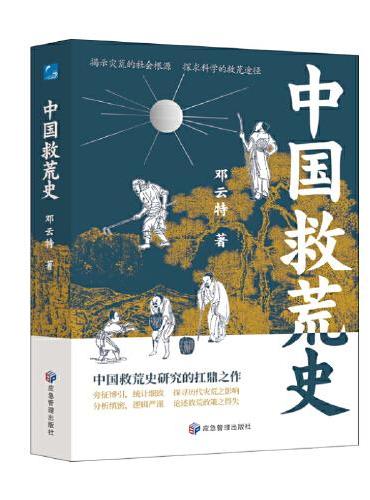
《
中国救荒史
》
售價:HK$
10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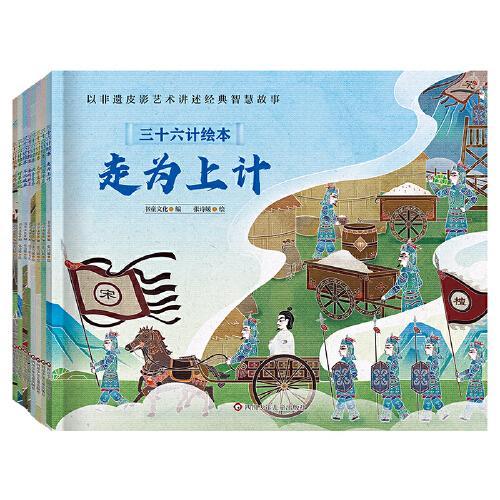
《
三十六计绘本(共8册)走为上计+欲擒故纵+以逸待劳+无中生有+金蝉脱壳+浑水摸鱼+打草惊蛇+顺手牵羊 简装
》
售價:HK$
177.4

《
茶之书(日本美学大师冈仓天心传世经典 诗意盎然地展现东方的智慧和美学 收录《卖茶翁茶器图》《茶具十二先生图》《煎茶图式》《历代名瓷图谱》等86幅精美茶室器物图)
》
售價:HK$
65.0

《
云冈:人和石窟的1500年
》
售價:HK$
7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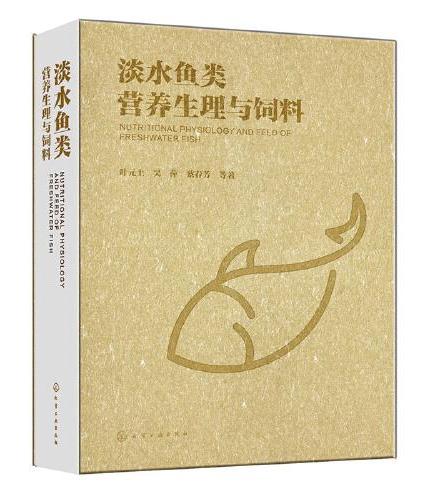
《
淡水鱼类营养生理与饲料
》
售價:HK$
333.8
|
| 內容簡介: |
|
作为盛开的新特色系列,本系列共计12本,本书是该系列第3本。本系列作品均来自90后获奖者的最新作品,他们用丰富细腻的情感和超强的文字,勾勒出了最独特的青春风貌和青春生活,是可读性非常强的作文学习辅导和课外阅读书籍。
|
| 關於作者: |
|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文学》杂志主编。现居北京,湖南湘乡人。
|
| 目錄:
|
专题种子
【飞絮】漂浮 侯佩儒 美好的女孩们,陪我长大,终究离开
【落土】听他说,生活的味道 舒锦润 粗糙生活打磨出岁月皱纹,尘埃落定
【晶沁】不醉的人 杨典运 螳螂姑娘,犀牛叔叔,相交的平行线
【寻光】FAITH 黎江萍 爱乐既信仰,永不回头的钢琴路
新作家新力量
理发师 莫诺 人世百态,纠葛,迷失
今晚,我们不说话 莫诺 孤独的姐姐,暖流般的弟弟,融化沉重
成长吧少年
维特少年 辛晓阳 生活磨砺也给予信念,逐渐坚定的少年
二十岁的我,六十岁的你 忘小川 信,致父亲,含蓄的爱
致二十岁的情书 忘小川 淡淡的惆怅,观自己,期望
诗歌镜头
是谁删除了你的坏消息 严彬 La Notte
文本创世纪
远山的钟声 孟祥磊 追,远方的钟声,追到虚无,停步似近
蛋 陶浪 追蛋的是我,偷蛋的还是我,我是谁
萌星球志语
宠物 曲玮玮 宠物,脆弱与责任,逐渐学会的坚韧
南方的天空是你的脸 容嘉奇 加菲还是波斯,这是一个问题
校园青春如迷
青春咏叹词 周宏翔 归人,离人,谁是谁的过客
我们其实并没有故事 苏陌年 青葱的故事,只要发生在心底就够了
最好的爱 赵丹盈 隧道,泪,误会与信任
专栏
品
追寻宁静之旅 王鑫煜 宁静,书法
张爱玲的纸笔传奇 木目 你看,张看,一粒瓜子壳
你好,没有色彩的多崎作 王君心 《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
跑着迎接你 王君心 《穿越时空的少女》
行
生活的分寸感 周苏婕 巴厘岛,西藏,鼓浪屿,植物般生长
给远方写信,寄给下一座城市 李娜 孤旅,梦,人人都在途中
校园文学巡礼——湘潭大学
差不得先生 黄如婕 半分半秒都差不得的“心”
致铭生 黄如婕 当你老了,两鬓斑白……
我所相依的岁月 何雅静 灿烂洗礼,生命,究竟
成都行记 李林芳 我们都是这个城市的过客
致我已经逝去的猪头肉 叶德霂 就算fresh bird变成old youtiao,最爱猪头肉
绮想他人生
竹骨梦凉 林丽茹 竹骨,九命猫,魂魄为谁而灭
离踪 林为攀 喜乐小学怪谈,胆小孩子
|
| 內容試閱:
|
漂浮
文侯佩儒
1
“程静以。”
妈妈握住我的右手极缓慢且微小地移动,我的手毫不适应地攥着的铅笔缓慢地在桌子上铺着的白纸上沙沙地写出了三个字。妈妈漆黑的长直发柔顺地从她的肩头滑落到我的头上、脸边,很痒的触感,我便摇头晃脑地想躲开。而她却只顾专心教我写这三个字,她轻轻地笑着,告诉我这是我的名字。
窗外的阳光很好,刚好透过窗玻璃落在这纸上。纸上的三个字就莫名地印在了我年少的脑海里,哦,这是我的名字。方才躁动的想出去玩的心突然沉静下来,很专注地看着那三个字。妈妈捏了捏我的小脸,故作一脸嫌弃地说:“写得真不好看。”然后转身走进书房翻出了爸爸的蓝墨水瓶和钢笔。爸爸倚在书房门口挑眉对妈妈笑道:“你这课程教得真快,只一上午就直接跳到三年级的钢笔字了。”妈妈就用好看的杏眼瞪着他,不说话,瞪得爸爸耸耸肩拿起一本极厚的书随手翻看起来才作罢。
她把钢笔拿给我看,说这是我以后要经常用到的书写工具。我却好奇地拧开了蓝墨水瓶的瓶盖,顺便探一下头看妈妈用充满蓝墨水的钢笔写出来的字,是娟秀的连笔字。她见我好奇便得意起来,说她还会写楷体呢。于是她又唰唰地写了很多蝇头小楷。可让我发愣的其实是字的颜色,很干净的蓝色让人心里觉得安静。我左手握住拧开瓶盖的蓝墨水瓶,右手将瓶盖放在桌子上,问妈妈是不是用这里面的液体写的字,她点点头。我兴奋地笑起来,将左手的墨水瓶举高,妈妈不懂我是什么意思,或许以为我想扔掉这瓶子听玻璃瓶碎掉的声音,也或许以为我兴致很高觉得这是什么饮料想喝掉。她很紧张地拉住我,说:“这是墨水,写字用的,不好玩的。”我笑弯了眼睛,奶声奶气地看着她说:“让我玩一下嘛。”直到我后来长大,她才告诉我她当时一下子就被我这样的表情和声音融化了。
她放开了手仍是小心地看着我,我干脆利落地将墨水瓶一下子倾倒过来,将蓝墨水一股脑倒在了好几张白纸上。她后悔得肠子都青了,气急地把还剩一半墨水的墨水瓶抢了回来。她正要去拿抹布,却被我拉住了衣角,我睁大眼睛小心翼翼地问她不喜欢吗。我想她一定欲哭无泪,揉揉我的头发说让爸爸来陪我玩会儿。说罢,她就扯着嗓子把爸爸从房间里召唤了出来。她指了指桌子上的一摊蓝墨水给爸爸看,爸爸笑起来也开始捏我的脸,我噘着小嘴看着他们两个,不满地说:“其实大部分墨水都被白纸吸进去了。”之后还命令他们不要擦这里,等到下午再说。他们依然不理解,我转身打开了电视,刚刚好在播动画片,里面的大魔王叉着腰喊道:“哈哈哈,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类!”
虽然他们觉得我很胡闹,但我津津有味地看动画片时也认真地守护着那些纸和墨水。年幼的我一定在窃喜,觉得自己多像动画片里那些维护世界和平的正义之士啊。直到墨水完全干了,我才喊出了爸妈,从那些纸上没有墨水浸湿的一角开始仔细地将纸张一层层分开。然后用透明胶把每一张纸的边缘粘贴在一起,贴成了好大一张纸。我费力地向着阳光举起那张纸,很大片很大片的纯蓝,也有几张纸边角没有被染上蓝色,贴在一起后是突兀的白色。我逆着光站在他们面前,让他们好好看这张大纸与窗外的天空做对比。
外边的天空也是大片澄澈的蓝色,上面有几小朵像棉花糖似的云朵飘浮着。像极了我手里举着的这张大纸。我得意地欣赏着他们表情的变化,过了好久我爸才意味深长地瞥了我妈一眼,说:“看来咱们家以后要出个搞文艺创作的人了。”妈妈就一直笑,将我抱起来,说:“真好,静以真聪明。”不过到了长大以后我也不懂这到底和我聪明有什么关系,总之我记得自己让他们吃了一惊。
我以为,那片我从小就觉得像打翻了蓝墨水瓶似的天空会就这样一直保持最初的干净蓝,就像我的故事也会一直美好下去一样。
2
妈妈教我用铅笔写名字的作用很快就显露出来。幼儿园里所有小朋友都不会写字,只是看看书、讲讲故事、做做游戏作为启蒙教育,所以上了小学一年级很多孩子都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有的孩子看着父母将自己的名字写在纸上后仔细地临摹下来;有的孩子小手攥着衣角不好意思地告诉老师自己不会写名字,老师就问他叫什么名字,然后帮他把名字写在课本的扉页上;只有一小部分孩子,会握着铅笔仔细地写出自己的名字,尽管写得很慢。
我属于那一小部分人,可作为一年级新生对学校的忐忑还没有被这微小的自信心冲淡多少,我就很意外地发现我右边的女孩子也会写自己的名字,而且似乎比我写得还要快。我偷偷看了一眼她的名字,“余越”。但两个字我都不认识,于是又开始沮丧起来。
她好像很大方的样子,我悄悄地注意到她把多余的铅笔、橡皮借给了旁边同学,看她教好奇的人怎么念她的名字,看她微笑、大笑甚至自来熟地对着别人做鬼脸。
她突然转过头跟我打招呼说:“你好!”我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吓得往后一缩,差点从小板凳上掉下去。她咧开嘴笑,头发编成复杂的小辫子一晃一晃的。她说,“你真是害羞的小孩子。”我还不太懂“害羞”是什么意思,只是下意识地红了脸,结结巴巴地说:“你好,我叫程静以。”她稚气地重复了一遍我的名字,说:“真好听。”我的脸便红得更甚了。
从小我就是个小路痴,长大了是大路痴。余越说:“你真文静,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了。”她表情灵动,我刚点点头她又追问起我家住在哪里。我皱起眉头,冥想了一阵子后,用手指向一个模糊的方向,说:“我家在那边。”她也学我的样子皱起眉头说:“那是太阳升起的地方。”
刚刚入秋的天气还不是很凉,她露在短袖外的胳膊很纤细,让我想到一小节莲藕。到了小学放学已不比幼儿园由父母接送,我们排着队伍整齐地走出校园。队首是余越,她举着小黄旗,我站在她身后紧跟着她的步伐。小黄旗上写着校名与班级,秋风将小黄旗吹动得像一片小小的麦浪在翻滚。她威风凛凛地站在麦田旁收敛了笑容很严肃地领着我们向前走。我盯着她的复杂辫子和她背着的米奇小书包,用食指轻轻戳了戳书包上米奇的大耳朵。
树上的叶子都渐渐泛黄转红,路上偶尔可以踩到几片叶子,她佯装了许久的严肃这才败下阵来,跑几步就停下捡起地上的枯叶。我担心地拍拍她,说:“这还是在放学的队伍里呢。”她听后谨慎地看了看身后,露出笑脸说:“这队伍已经只剩下了我们两个人,其他小朋友都走了。”我急忙看路边,生怕自己已经走过了家。她偏着头看我,问我是想去她家玩吗。我的幼小心灵在小小纠结,还没来得及拒绝或同意,她又亲昵地跑到我左边,左手举旗右手挽住我的胳膊,说,“那一起走吧。”
我凝重的表情到了她家门前才消散,我说了句“等我一下”,然后转身向她家旁边的楼上跑,跑到三楼后站定敲敲门,将书包递给开门的妈妈,告诉她我想和我的小朋友玩一会儿,她家就在楼下。妈妈点了头,我这才又跑了下去,站在我家楼下那棵法国梧桐树下指着三楼对余越说:“这就是我家。”她喜笑颜开,我们两家相隔不到五米,觉得彼此像是自己得到的意外的礼物。
她带我走进那扇暗红色的铁门,是独家小院。院子里靠墙种下了好几棵树。枝繁叶茂,绿得直逼人眼,淡淡的香气环绕在周围。她见我移不开目光,就告诉我:“这是香樟树,5月会开花,那时会更香的。”她也看着那些香樟树,眼神竟温柔起来,像是目光所及之处都坠落入一片星湖。
这是我一直忘不掉的她最深沉的眼神,哪怕后来看到过更多更深沉的眼神。
我们友情发展得迅猛的时候,几乎每天都腻在一起。在家门口拉上几个不太熟的小朋友一起玩耍,或者只有我们两个坐在我家的天台上远眺城市的尽头,尽管一直找不到城市的边缘。
那些香樟树在我们相遇的夏末初秋还茂密得不像话,似乎想违背自然界的规律。后来春天的温和苏醒了,它们却开始飘飘洒洒地落叶。我不知道这是因为什么,但在春雨淅淅沥沥落在青石板上打出很轻的声响时看到那些仍绿的落叶,这是我人生里第一次无端地感到忧愁起来。好像人会突然间消失不见,就这样离开,再也不见了。
后来就这样慢慢地成长,记忆里余越大多时候是极聪明的。
阳光很亮眼的下午我依照习惯去找唯一的朋友,跑到她家的铁门前看到旁边墙壁上有一幅白色粉笔画出来的画,画得很重,像我平时写字的力道。也许她画画一直不太好,画面上只有一个简陋的大房子,房子上写着“中国银行”,下面门口画着一个小女孩,扎着两个辫子,头顶上是“越越”二字。我便极快地懂得她去了银行,便又转身跑回家里,对我们的心有灵犀感到窃喜。
对于骄傲有了感知是二年级那一年,我们成了新生里第一批少先队员。我们面容肃穆地站在升旗台前听大队委员宣读一些很容易激起年少的我们豪情的句子,身旁一对一的是高年级的学生。一声令下,庄严宣誓,身旁的大哥哥、大姐姐接过我们手中被熨平折好的红领巾,动作不太娴熟地为我们系上。当四五年后我作为高年级学生为新生系上红领巾时,我才明白他们的手法为什么不娴熟,所幸我还系得相当好。仪式结束后,余越也一脸兴奋不停抚摸着自己胸前的红领巾,我仿佛也听得很清楚胸腔里心脏的跳动,“咚、咚、咚”,浑身像流满了沸腾的血液。老师宣布解散,我们迎着干燥的风如同两只刚找到路的迷途的鸟,张着双臂跑向操场,她的小白色皮鞋踏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天空很蓝,时光还很静好。
我们慢慢地成长,所以必定会遇到学生命途里惧怕的分数。一起坐在我家天台上吹风原本只是一种消遣,随着年龄的增长却开始变成迷失的地方。年幼的我们喜欢坐在上面看着远方的夕阳染红了西边的一大片天空,纯蓝变成玫瑰红,厚厚的云彩堆积成火烧云,好像一不留神天使就会右手旋转着一朵娇艳欲滴的玫瑰花降临在面前,挽住我们的手,微笑着喊我们公主。而三年级之后她在那里流了很多泪,抽噎地回头看我,说:“又考砸了,数学应用题错了一堆,才考了六十多分。”高楼的凉风吹来拭干了她脸颊上的眼泪,我远远站在她身后看夕阳脆弱的光线打在她身上,周身的光芒比不上她滚滚落下的泪珠反射的光亮,可再也不像想象里会飞出来的天使了,天使不会哭泣。我恐高,所以总是不敢像她一样走过去坐在天台的边缘晃动双腿,但她的难过还是催动我走到很靠近她的地方轻轻说了一句奇怪的话,我说:“成绩就像跳跳球,摔得越惨就会跳得越高。”其实我也并不确定她下一次会不会考好,但下意识就这样安慰起来。浓郁的悲伤气氛里我抬起头看正上方的天空,纯蓝色已经被稀释了,好像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天空就在渐渐地发白,就像老照片总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泛黄起来。
再往后的时光,关于她的片段突然被剪开来。她走了,搬到了一个远离我的城市。她在我们一起走过四年后的夏天里依然笑着看着我,一如四年前坐在一年级的教室里。也不知道是从何时起我们都开始不爱笑了,她每次悲伤之后好像都把消极情绪转移给了我似的。她还是会勉强笑出小酒窝,我就看着她也笑起来。但心却都开始沉下去,我们都深知不快乐却还是要笑。那时候的我们开始日渐成熟,比同龄人更懂得悲伤的重量。在那天的暴雨里她背对着我锁上了她家暗红色的铁门,雨水落在香樟树叶上啪啪作响,她的声音没有了平日里的甜美,说她要搬家了。她看着那些香樟树垂下了眼帘,说或许再也不回来了。我就呆呆地看着她锁门的背影,暴雨哗哗落下,打在我裸露在短袖外的皮肤上,有点儿冷。
于是她真的离开了。
我吸了几口稀薄的凉空气,仰起头看到天空的颜色又变淡了。
3
初一的寒假夜里我听到轻微的声响,似是我骨节拔高的声音。然而声音越发大了起来,是铁门晃动的声音。“是她回来了吗?是她回来了吧。”身体里的每个细胞都吵闹起来,我推开玻璃窗往那边看,一个人影在晃动却看不真切。
我急忙穿了件大衣跑下去,夜风很冷。地面有积雪隐约反射出浅淡的银光,我不小心脚滑了一下,但还是很快稳住了。记忆里就想起还小的时候她有一天向我家跑要找我玩,我在窗边看着她,吊兰叶子垂下去被清风吹动晃动起来。她也抬起头看我,却踩到沙子上滑倒了,将膝盖擦破得很严重,被涂上了紫药水后的一个学期都是我搀扶她去上学。想到她那时还故作不疼的笑,我鼻子有点儿酸,咧咧嘴学她笑,哈出的哈气很快融入了夜色里。
不是她。
我盯着那个人的身影判断了很久,失望地回头要走。夜风吹着跑到我的怀里与我拥在一起,好冷的夜。抬起头只有一轮不圆的月亮,星星都隐匿在夜空深处。身后试探的声音很清晰,又不太现实,那个人推开了铁门,吱吱呀呀,她问我:“你是程静以?”我顿住了,这个声音我没听过。
“我是卫水淼。”她搓了搓冻红的手,因为寒冷而声音颤抖,“和余越是朋友。”我错愕地看着她,胸腔里的热血突然喷涌。我想问余越去哪里了,还会不会回来,过得还好吗,为什么要离开。所有话都堵在喉咙里,泪光点亮了眼睛,就定定地看着她。她不好意思地清了清嗓子,微胖的身体不住地颤抖。我突然笑了,对她说明天天亮会来找她。
搬家公司的大卡车将家具搬运到那扇铁门前,香樟树无精打采的,像见了外人提不起兴致。卫水淼坐在香樟树下讲了关于余越在那个城市的事情,最后她告诉我余越留在了那个遥远的城市,而她家买下了这里。那些话后来我都记不住了,香樟树叶被风吹过的沙沙声和我一直的沉默替代了那些记忆。
余越离开之后我没有再遇到过像她一样温暖爱笑的女孩。卫水淼也很爱笑,我甚至有时候会突然觉得她就是余越。于是我们就不可阻挡地待在了一起。卫水淼喜欢画画,而且画得很好。在某个秋季她跳跃着踩碎路边的枯叶,听叶片破碎时咔嚓咔嚓的声响。她挥舞着双手,微胖的身体看起来储藏了很多能量与想法,她没有转过身看我,只是面向前路大声地喊:“静以,我一定要成为最好的服装设计师。”我跑到她身边,看到她的眼神在发亮。那一刻,她也在发光。
我记得她唯一没有在我面前的笑那次。我们坐在初春的小河边。流水潺潺,还能听到婉转的鸟叫,我突然感觉苍凉,没有说话。她脱掉鞋袜将脚伸进河水里不停地摇晃,河水就被激荡出来,春天的气氛还不是很浓。我也学着她的样子将脚小心地放进河水中,凉意一下子传到心里,我突然被吓得一激灵。中考在即,她的成绩一直不好,现在的她极像当时因为数学考砸了在天台上哭的余越,爱笑却收敛了笑,无助茫然。这些年来我越发不会安慰人了,所以连成绩像跳跳球的那个比喻也再也没有拿出来过。我很安静地陪她坐着,听她说话再随声附和。很浓的离别感莫名地出现,春雨适时地落了下来,落在河水里又溅出来。
我坐在中考考场里的时候,卫水淼已经离开去了中专。
那个独家小院再次易主,接手的是一个世俗的白领。卫水淼陪了我两年半,她没有让我看她离开,我们都怕会掉眼泪。那个白领砍掉了香樟树又铺上了水泥。甚至翻新了铁门。这里多年来环绕的淡淡香气终于变成了钢筋水泥的冷漠气息。
她们都走了。
天空的颜色变成惨白,我已经找不到了小时候用蓝墨水画成的那幅画了。
4
中考顺利,我收到了一中的录取通知书。
星光很黯淡,窗外突然刮起了大风,猛烈地拍击着窗玻璃。沙尘被卷起,这些年来这座小城的环境也被严重破坏了,我很少再见到蔚蓝的天空了。
妈妈说觉得我长大了。我点点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转身走上了天台。风很大,把我的衣袖吹得鼓了起来。初中的毕业典礼结束后我带走了一个紫色的心形气球,还捡了一朵在送行会上不小心掉落在地上的塑料花。人流拥着离开,它们静静地躺在地上。我以为它们足够让我一直记得一段时光,到了现在气球已经缩小成最初的样子,上面还沾着一层薄灰,干瘪得像我如今已经不太多的情感。
我终于一个人坐在天台上吹风,很远的地方灯火闪耀。隐约幻化成一片蓝天,上面流云行走。我一直在看,看久了才发现所看景象已经变得很不一样了。她们都像那些流云,不打招呼地出现在我的生命里,用纯白色点缀过我的蔚蓝世界又飘逸地离开了。天空渐渐稀释了那种蓝,而流云也不见了。
我闭上眼睛开始流泪,思念像巨大的藤蔓肆意地疯长。
再见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