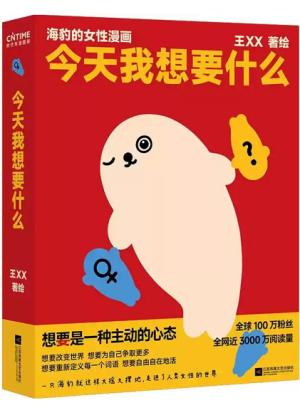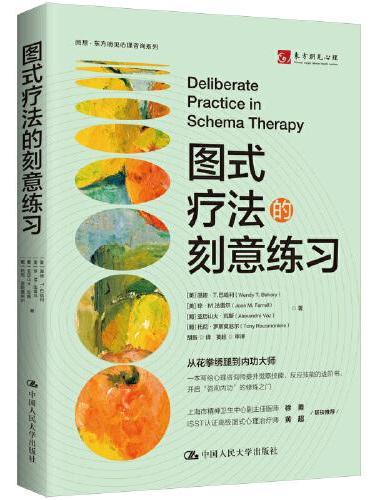新書推薦:

《
诡舍(夜来风雨声悬疑幻想震撼之作)
》
售價:HK$
54.8

《
讲给青少年的人工智能
》
售價:HK$
52.8

《
海外中国研究·宋代文人的精神生活(经典收藏版)--重构宋代文人的精神内核
》
售價:HK$
107.8

《
埃勒里·奎因悲剧四部曲
》
售價:HK$
30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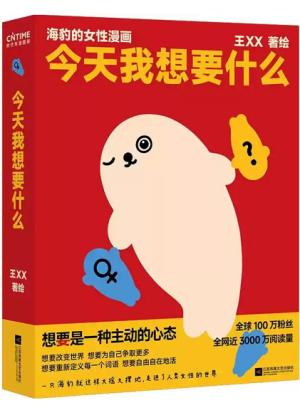
《
今天我想要什么:海豹的女性漫画
》
售價:HK$
74.8

《
日常的金字塔:写诗入门十一阶
》
售價:HK$
74.8

《
税的荒唐与智慧:历史上的税收故事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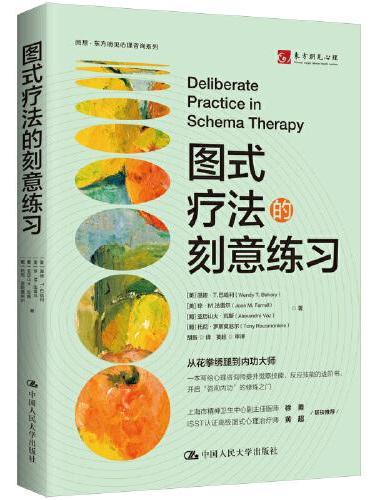
《
图式疗法的刻意练习
》
售價:HK$
87.9
|
| 編輯推薦: |
周其仁《城乡中国》与费孝通《乡土中国》一脉相承。
《城乡中国》是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关于中国城镇化这一焦点问题的鼎力之作。
在《城乡中国》一书中,作者用经济学视角解析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厘清迷雾预见中国城乡发展的大趋势。
他借城乡之分野,把脉中国经济,用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解读中国的过去和未来。
《城乡中国》用清晰的逻辑、简洁的语言、浅显的实证、趣味的叙述,把复杂的经济现象和本质深入浅出地分享给大众。
陈锡文、文贯中、李培林、李铁等各路专家学者强力推荐!
|
| 內容簡介: |
《城乡中国》内容介绍:中国虽然大,可以说只有两块地方:一是城市,一是乡村。中国的人口十几亿,也可以说只有两部分人:一部分叫城里人,另外一部分叫乡下人。城乡中国深刻的分野,促使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就写出他著名的《乡土中国》。
今天,虽然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可是城乡之间依然有着巨大的差距,甚至鸿沟越来越大,导致中国发展中的大多数重点难点,都在农村,都在城乡之间。周其仁教授在《城乡中国》中指出,没有农村、农业和农民状况的根本改善,国民经济是搞不起来的。因此,近年来关于城镇化的讨论始终不绝于耳,成为政府、大众、舆论、专家学者热议的焦点问题。
5年来,周其仁教授及其同人陆续以实地调研的形式,深入调查了中国很多地方城乡的情况,在《城乡中国》一书中,将城乡之间这些差异形成的原因、后果以及可能的解决办法娓娓道来,试图增加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认识,找出沸沸扬扬的城镇化改革的症结,消除城乡之间的巨大分隔。也期望让更多的读者通过《城乡中国》了解和思考今日的中国和未来的发展,找到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契机和触发点。
|
| 關於作者: |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经济人物之一。
早年在黑龙江下乡,其中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半。
1978年从农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工作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在杜润生先生指导下从事农村改革发展的调查研究。
1989年5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访问学习。1991年秋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96年春季起,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为国家发展研究院)任教,并应邀为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和长江商学院等院校开设课程。
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等等。自1996年以来,相继开设了有关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
著作有《改革的逻辑》、《竞争与繁荣》、《货币的教训》、《中国做对了什么》、《病有所医当问谁》、《世事胜棋局》、《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挑灯看剑》、《产权与制度变迁》等。
|
| 目錄:
|
|第六部分|寻找突破口|
“政社合一”的长尾巴 3
也谈“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 8
政产不分,遗祸无穷 13
农村确权要到户 18
拖延改革,永无宁日 22
为什么宅基地流转后来居上? 28
分宅基地的游戏 33
“房地分离”是奇迹 38
超强的土地需要 43
|第七部分|治标分歧路|
土地用途管制的起源 51
土地用途管制的后果 56
制度成本,兹事体大 61
逼出来的“增减挂钩” 66
挂钩主体是怎样产生的? 71
政府主导的增减挂钩 76
郫县的佐证 81
土地收益分配与权利的制度安排 86
|第八部分|“挂钩”三岔口|
走出“半拉子”改革工程的第一步 93
市场版的“挂钩”(上) 97
市场版的“挂钩”(下) 102
“土地交易所”破土而出 107
土地的市场流转不可阻挡 112
从产权的角度看土地流转 117
国土部怎么成了“供地部”? 122
行政之手不高明 127
土地配置,何难之有? 132
分权、分责、分利 138
|第九部分|思维的辨析|
辨“土地供求无弹性” 145
辨“给农民权利会损害农民利益” 150
辨“土地涨价要归公” 155
辨“建筑不自由” 160
辨“土地配置靠规划,不靠市场” 166
规划出错催生市场 173
管制不当激活黑市 178
法外行为一分为三 183
“非法”帽子满天飞 187
同地同权的宪法依据 193
农地农房入市,会天下大乱吗? 198
农房入市早就发生了 203
收权容易还权难 208
改革要改也要革 213
房转地转,帮衬人转 218
|第十部分|形势比人强|
打开城乡间的市场之门 225
以城带乡“新土改” 230
缘起上海的“三个集中” 235
“地票”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 240
凤凰社区飞凤凰 249
土地入市的路线图 255
转让权的政治经济学 260
跋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 267
|
| 內容試閱:
|
凤凰社区飞凤凰
2013年12月20日,深圳市拍卖了一幅土地。不少媒体报道,“深圳打开利益死结”,“新土改破冰,首宗农地入市”,“小产权落地”,标题醒目又养眼,令人目不暇接。很正常,倘若没有新鲜刺激的内容,早在1987年就拍下第一锤的深圳,土地拍卖怕是上不了新闻头条的。
当天,我和两位同学就在现场。我们是专程前往观摩这场颇有标志意义的土地交易的。说新闻“标题党”抓眼球但不准确,似乎不困难。但轮到要我们自己来刻画这场土地拍卖的特别之处,却也不容易。该拍卖土地1 .46万平米,成交价1.16亿人民币,地价款“70%归深圳市政府”、“30%外加建成后物业的20%,归深圳保安区街道的凤凰社区”。问一句吧:如果所拍之地是国有土地,收益何容凤凰社区分享?如果不是国有土地,又何以堂堂皇皇合法地公开拍卖?
不怕见笑,能把问题问到这个“水准”,是我们二十来位北大国发院的老师同学,在深圳土地问题上调查了一年之久的“成果”!话说2012年年初,深圳方面召开过一个土地制度改革的研讨会,请来专家很少,但主办方介绍情况详尽,又不公开报道,摆明要认真探查解决实际问题之道。会后东道主问我有没有兴趣做深入调研,其时我们的成都研究已近尾声,遂回应回去问问各位同好。
怎么可能没兴趣?深圳首开国有土地市场公开交易之先河,名满天下。更重要的是,这个城市率先——迄今为止也是惟一——完成全部土地国有化,后续究竟如何,不来此深入一下,总有缺憾。过去对深圳的调查,企业、产业和创新的题目碰过不少,偏偏土地方面的,还一个都没有。现有机会上门,积极响应者众,大家一拍即合,2012年的寒假和暑假就全都泡在深圳了。上课时回校区,做的则是案头工作。一年多的时间,访谈记录外加收集到的文档、照片,收获之丰,远超预期。东道主后来有没有觉得“请神容易送神难”,我辈当不知道(一笑)。我们自己收获满满,怕要消化多年,方知养怡之福。调研成果,来来回回改出一份综合报告发表(“城市更新的市场之门——深圳经验”,刊《国际经济评论》2014年第3期),有心的读者或可找来作为参考。
感受深的,是城市土地全盘国有化引发的麻烦无穷。对那段宪法公案,本书做过梳理(见“‘城市土地国有化’的由来”,以及“全盘土地国有的第一步”) 。不过再次细读1982宪法,在“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的表述之后,还有一句,“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也许可以这样解读:属于国家所有的,仅“城市的城区土地”而已,因为宪法还很明确规定,“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集体所有。“城市”涵盖城区与郊区,既然后者土地法定为集体所有,那么全部城市范围内之土地,在逻辑上不可能都属于国家所有。
事实上,《1982宪法》颁布后,并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包括直辖市、省会城市、地级市或县级市,真的实施了全部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理由有二:一是现在的城市,市域范围一般都划得很大,既有城区也有郊区和农村——以至于出现了一个老外不易听懂的术语(“某某市的城镇化率”)——没必要把全部农村土地划归国家所有。二是“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虽有了宪法根据,但把世世代代农民的土地划入国有,要履行征地手续,要支付补偿,还要安置原来土地的主人,不是说国有就国有那么简单。
深圳却是唯一的例外。作为毗邻香港的特区城市,深圳增长迅猛。尤其邓公南巡之后,中国的市场化开放度急速上升,深圳的城建呈现比近代上海更猛烈的扩张势头。这个新兴城市平均每年新增建成区的面积,相当于东部沿海地带一个中等县级市的市区面积。原来不过广东省一个县的幅员,即使全部建成城区也难满足需要。深圳大量新增城市建设用地的要求,不能不受到土地管制政策逐年收紧的掣肘。1992年,深圳市出台《关于深圳经济特区农村城市化的暂行规定》,对原特区关内的农村土地实行“统征”,即把那里的全部农村土地转为城市国有土地。2004年,深圳市又在特区关外实施“统转”,即把全部关外农民转为城镇居民,以此实现全域土地的国有化。从细节上打量,2004年的“统转”沿用了1992年“统征”时的土地补偿标准。问题是12年来深圳地价早已翻番。结果,“统转”广受抵制,出现了关外地区“违建”和“抢建”高潮。据2010年深圳完成的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问题违法建筑信息普查资料,全市违法建筑35.7万栋,建筑面积3.92亿平方米,用地面积131平方公里。 如此规模的“法外土地”与“违建”,颇为罕见。更为严峻的现实,是生活在“违法建筑”里的外来人口,差不多占到深圳总人口的一半。与一个“正规深圳”并列的,还有一个由原村民、“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继受单位”(“统转”之后,理论上不再存在集体经济组织)、以及生活在违建里的庞大外来人口组成的“非正规深圳”。这里,名义上城乡已完成一元化,但又隐隐生成了一个“法内”与“法外”交织的新二元世界。
焦点在“违建”。以“正规深圳”的眼光看,只要土地不合法,上盖的建筑当然就不可能合法。但恰恰是数万栋深圳建筑物下之下的土地,历史遗留的权属纷争一直紧紧地纠缠着当下的活人。访谈多了,我们发现那叫“一块土地,各自表述”: “正规深圳”认为“应转未转”,“非正规深圳”则认为“应补未补”!闹来闹去,政府宣示“全部关外土地属于国有”,原村民及其“集体经济继受单位”却争分夺秒起楼、建房——我们课题组的张惠强给这类行为命名,叫“种房保地”!从旁观察,还是老乡实际,要土地干嘛,还不是加盖了物业才能有收益?你说是你的地,那我盖我的房,横竖建了楼、收到租,土地国有化不国有化的,有什么关系嘛?
政府当然拆违。不过当我们拜访了深圳拆违大队之后,才明白那可是一件知易行难的工作。别的不提,执行成本之高昂就令人望而生畏——反正有过花费200万元拆除一栋建造费1200万元建筑的记录,还没算“保持高压态势”的常备行政经费。本国国情,“条条”执法向来离不开“块块”之配合,而深圳关外最基层的“块块”,恰恰就是“集体经济继存单位”!几次集中拆违之后,违建高峰总算被遏制,但行家估计,“违建”的存量与增量,还是与“正建”旗鼓相当。
困局难破,我们的思考也渐入迷茫。过去也有类似的经验:对一个问题完全无知的时候,调查进展快,想法与招数来得更快。可是等到对问题有个七七八八的认知后,却发现研究再难推进,因为真正的难题常常一时无解。几番研讨,我们横下一条心,反正就是不抖机灵。无解就无解,也别冒充我们就比当地人高明。80年代早期第一次会杨小凯就在深圳,他当时的话语我现在还记得清——“来闯深圳的,没有等闲之辈,所以这里人的平均素质远比内地城市的为高”。深圳人没辙的难题,我们才来看了几天就“有解”了?当如此“经济的”经济学者,没什么意思吧。
沉下去,发现“解的元素”就在难题里。本来啊,难题让人难受,当事人总要寻求减轻之道。外来人灵机一动就能有的点子,人家就没有?还是早有人想到过,只是手脚受限做不成?这样想下去,调研工作柳暗花明又一邨,新发现接踵而至。凡可记下的,都记录在我们那份发表的报告里了。印象最深的是深圳的城市更新:无论法外土地和违建多么插花交错,他们设计了一套对路的更新政策化解过去遗留下来的麻烦。细节这里展不开,研究报告里都写了,反正基本思路,就是如果讲理太费劲,那就不妨试一试“讲数”——“法外土地加违建”缴付多大一个代价,政府就让人家分享合法开发的收益。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尽最大努力将多数人的经济活动纳入合法框架。
面上推开,选先易后难的路线。2013年1月,深圳市政府下达关于优化空间资源促进产业升级的文件,率先“解放”工业用地。按此政策设计,原村民及其经济实际控制的工业用地,愿意拿出来以国有土地拍卖的,收益可与政府分成。于是,我们才有机会看到本文开头的故事。准确描述并不容易——此次拍出的那宗土地,在法律上属于国有,但原村民及其集体有权却有权分享30%土地收益,外加持有20%开发出来的物业。戏中有戏,凤凰社区还拿自己应得之地价款,购入开发方(深圳方格精密器件有限公司)的部分股权。经此,模糊不清的原住民地权,就转为清晰的物业所有权与公司股权。深圳关外的凤凰社区,果然飞出一只金凤凰。
为什么宅基地流转后来居上?
农地承包留下的那条集体制尾巴,一时半会儿蜕不干净。这是农地转让拖泥带水、发展不足的一个体制原因。但另外一类农村土地——宅基地的流转,近年以来却有后来居上之势。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在《城乡中国(上)》的“‘还权赋能’,意义不凡”一文里,我向读者交代过自己开始接触农地转非农用途现象的经过。那是200 年春夏之际,我在成都看邛崃市羊安镇仁和社区时入的门。那里通过平整农地,把缓坡治平,重新安排地里的路、渠、沟、坎,增加实际可耕地面积,再把结余出来的土地指标卖给城市充当“占补平衡”,为建新农村筹得部分资金。在同一经济逻辑下,“农地整治”又扩展为“村庄整治”,农村宅基地由此列入可转让范畴。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新现象。过去多年在杜老(杜润生)帐下从事农村调查,关注的焦点是农地,因为粮食、农产品以及农民的收入,皆出于农地,所以政策与制度变迁的重点也在农地。当然我到农村去调查,也是见过宅基地的。更不要说,自己下乡十年,住在完达山自建的窝棚里,严格说也占过一幅宅基地。不过没有问题引领,理解不到的也就感觉不到,大体对宅基地很熟视无睹就是了。
在邛崃受到可观察现象的刺激,脑子开始转,也开始关心其他地方有无同类事情。是年 月,《南方周末》发表的两篇出色的报道让我如获至宝。
一篇是记者肖华的作品,题目就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农宅入市,为谁开闸?》。也许是编辑加上的提要,则更为传神:“广东一脚踏入土地制度变革的最后一块禁区,这个省的农民有望能买卖、抵押他们建在宅基地上的房子。”
另外一篇是记者王小乔写下的北京故事。她的题目是《“小产权房”:生命中不能承受之便宜》——你看了就不可能放过不读的。该文的提要也过瘾:“被高房价催生的‘小产权房’同时迎来了发展高潮和清查风暴,被‘小产权房’改变了的村庄和追逐着‘小产权房’来到乡村的城里人该何去何从?”这似乎印证了我早就讲过的预言——这个时代出大记者的机会,比出大经济学家的机会大多了。
不约而同,一南一北的两大都市,在城乡接合部都发生了农宅流转,加上我自己在成都三圈城邛崃的观察,该不会事出偶然吧?没把握,于是决定从京郊着手探查。办法也现成,就是拜王小乔为师,请她到我们师生组成的研讨会上讲情况,提问题,理思路。大体有了一张“地图”后,就在京城四环到六环内外,一个一个跑带有农宅入市现象的村镇。我自己的记录是,前后跑了 个“小产权楼盘”(包括王小乔专题报道过的太玉园),还访问了刘守英写过的“建在集体土地上的城市”——郑各庄,并由前北京农工部领导老赵亲自当向导,几次三番到因“小产权”官司闻名京师的“画家村”宋庄问东问西。
这些实例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涉及农民宅基地的转让。问题也来了:宅基地不就是农宅下面的那块土地吗?农民生活在农宅里,为转让宅基地,常常不惜拆了农宅易地再建——早期邛崃的村庄整治,干脆就被当地老乡叫成“拆院并院”——为什么要如此折腾?农宅拆旧建新,里外总要花上一笔投资,究竟谁来出钱?倘若拆了旧房又建不起新房,农民岂不是要流离失所,那又岂不是要在太平世界活活酿成民变?
要解答这一连串麻烦问题,怕只有从最初级的开始。刚刚讲过的,宅基地无非就是农宅下面的那块地。不过,这只是宅基地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呢?免不了要问宅基地的权属,也就是它究竟属于谁所有。答案是中国农村的宅基地属于农村集体公有。再问:为什么宅基地也要归集体所有,以及它是怎样归属于集体所有的呢?
宅基地本来是生活资料,按标准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必须实行公有制的应该限于生产资料。所以,20 世纪50 年代农村的集体化高潮,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归集体公有的是耕地、耕畜、生产设施和大型农具,一般并不包括农民家居的房屋连同其下的宅基地。那还是农民的私有财产,正如家具、锅灶、衣物等生活资料一样。公社化之后的“大跃进”,也确有地方把老百姓家含铁的物件统统缴来搞土法炼钢的,不过那与公有化纲领没有直接关系。拆农房的极端行为也是有的,不过拆了也就拆了,并没有宣布宅基地归公。
等到发现“大跃进”损害了生产力,中央开始纠正“左”的错误,开始调整农村政策,重新规范人民公社的生产关系,于是才有了1 962 年的《人民公社 60 条》,全称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该文件是党的文件,不是法律,不过人民公社化从来也没有一部法律,重新规范公社的管理,也不需要一部法律。
正是这份政策文件第一次明确规定:“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第21 条)所以严格地讲,宅基地归集体所有,是人民公社化三年之后才实行的。读者不要奇怪那不是一份“反‘左’”的文件吗?怎么反着反着,顺手把宅基地这土改以来一直明明白白归农民私有的财产,一句话就划归公有了呢?我的感受是,那个年代的左、右以及打引号之“左”,连同“反左”、“反右”或“反‘左’”,从来就是一笔糊涂账,根本就不是任何讲形式逻辑的人所驾驭得了的。
反正说不清左右,农村宅基地从此就“归生产队所有”,且“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了。从此,社员——其实农村所有居民天生都是社员——到了成家立业的当口,凡要宅基地盖房子的,一律有权找生产队解决,因为除了按“习惯法”可以继承上一代的农宅连同宅基地,谁也买不到、租不到宅基地,因此再没有制度通道能解决随人口增加的宅基地需求。从此,获取宅基地就成为集体成员一项与生俱来的权利。
比照一下,以前宅基地问题是每个农家的私人事务,他们可以从私有的农地里决定拿出多大一块来盖房,由此增加的宅基地,当然要以减少农地的其他收益为条件。他们也可以买得、租得宅基地,那又要受到家庭收入、开支的实际约束。但宅基地公有化之后,这却成为集体“成员权”的一个内容,反正生产队有义务为每个成员解决对宅基地的不断增长的需求。虽然还受限制,不过那已经不是各家农户拥有的土地和收入,而是生产队拥有的土地总量,以及对内怎样分配宅基地的问题。
当生产队平等地为每个合乎一定条件的成员——如本队已成年、要成家、无第二处住宅的——都分配一定数量宅基地的时候,新制度的优越性是毋庸置疑的,至少贫困农户再也不至于因为穷而无立锥之地了。这也许是宅基地集体化建立得那么容易的原因。问题是,新制度的分配准则从此要受新逻辑的约束,特别要经受永无止境的“人丁滋生、土地减少”压力的考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