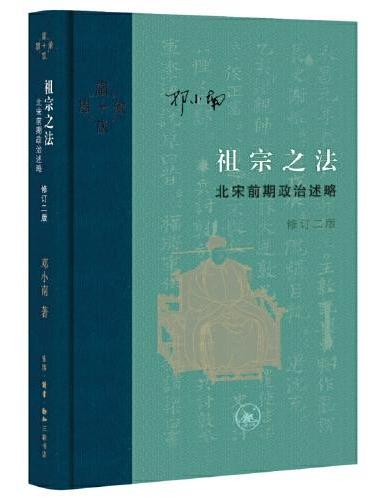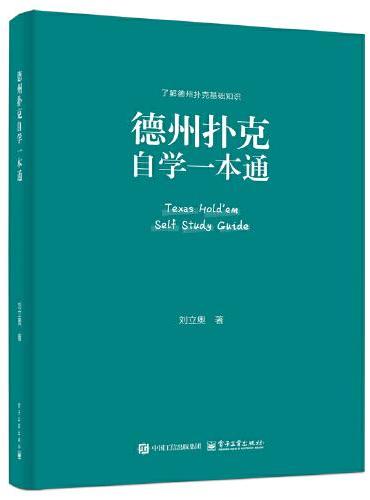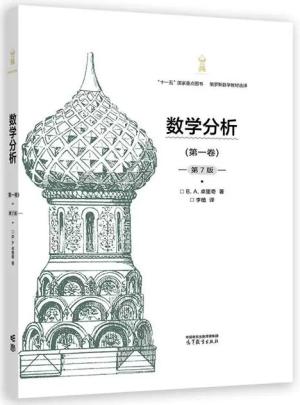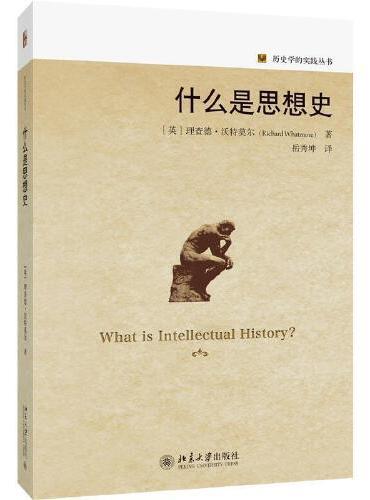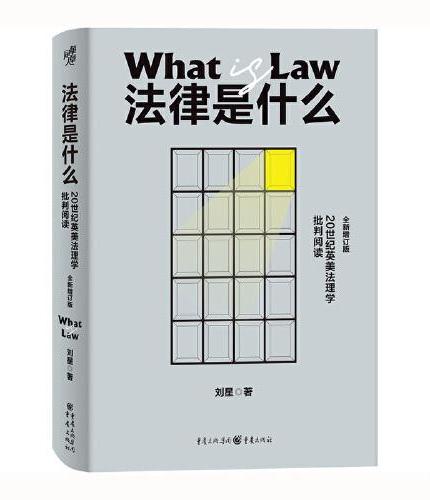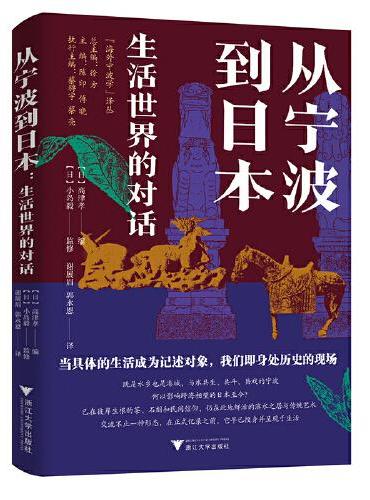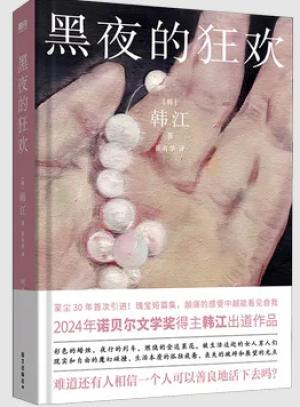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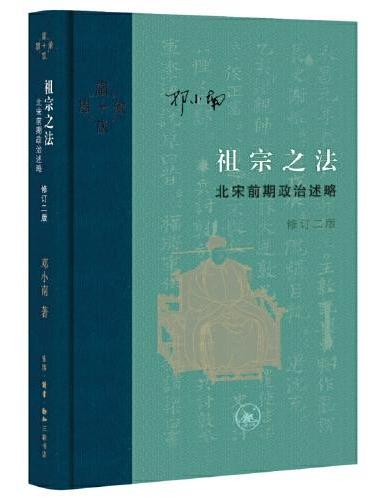
《
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修订二版)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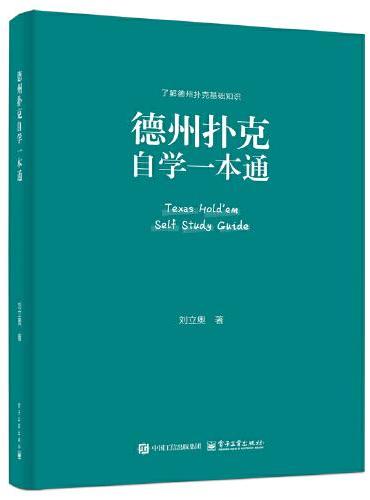
《
德州扑克自学一本通
》
售價:HK$
5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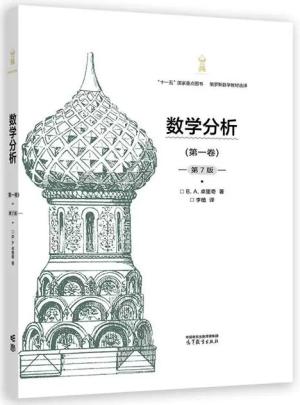
《
数学分析(第一卷)(第7版)(精装典藏版)
》
售價:HK$
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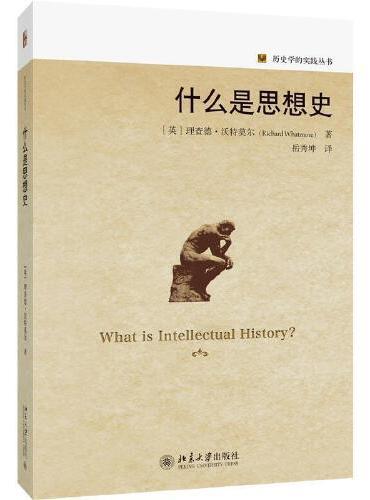
《
什么是思想史 历史学的实践丛书
》
售價:HK$
6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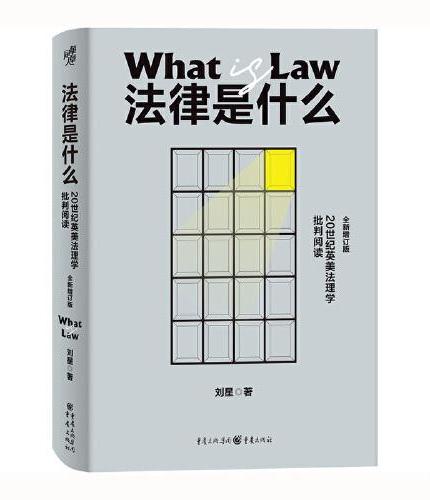
《
法律是什么:20世纪英美法理学批判阅读(全新增订版)
》
售價:HK$
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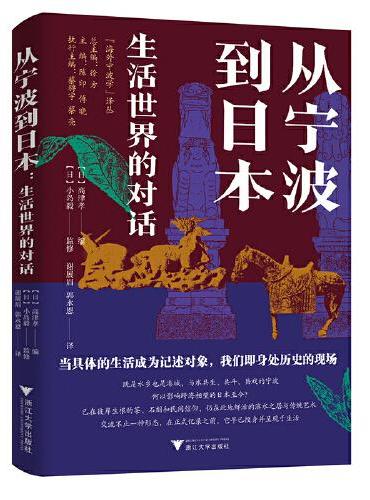
《
从宁波到日本:生活世界的对话
》
售價:HK$
74.8

《
怪谈:一本详知日本怪谈文学发展脉络史!
》
售價:HK$
5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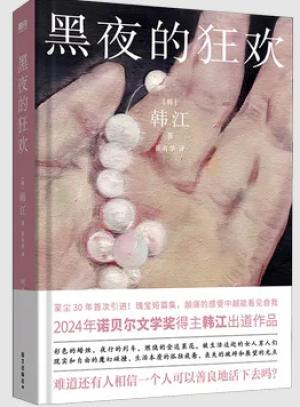
《
韩江黑夜的狂欢: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韩江出道作品
》
售價:HK$
63.8
|
| 編輯推薦: |
所谓“退步”,语涉双关,可理解为对百年中国人文艺术领域种种“进步观”的省思和追询。作者的文字观察敏锐,细节刻画尤其生动。书评人黄集伟说:“陈丹青虽是个画家,但很多散文家写不出他一样的文字。另外,读者们虽不是他本人,但这个海龟派笔下文化与语境的‘隔膜’与‘无助’,乃至‘欲拒还迎’的心态每个人都不难感同身受。”
《退步集》作者归国五年来的部分文字,话题涉及绘画、影像、城市、教育、自云“退步”,语涉双关,始末不可理解为对百年中国人文艺术领域种种“进步观”的省思和追询。
|
| 內容簡介: |
《退步集》是陈丹青归国五年来部分文字的结集,三十余篇文章,话题兼及绘画、影像、城市、教育诸方面,自云“退步”,语涉双关,也可理解为对百年中国人文艺术领域种种“进步观”的省思和追问。
也许归功于长年的绘画训练,陈丹青的文字观察敏锐,细节刻画尤其生动,时有连珠妙语。书评人黄集伟说:“陈丹青虽是个画家,但很多散文家写不出他那样的文字。另外,读者们虽不是他本人,但这个海龟派笔下文化与语境的‘隔膜’与‘无助’,乃至‘欲拒还迎’的心态每个人都不难感同身受。”
在《退步集》中,有相当多的篇幅是陈丹青对当今城市建设的痛陈,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将城市原有的文化生态和历史记忆无情地摧毁引起艺术家陈丹青肝肠寸断地“叫嚣”:“江南水乡已经没有了。”“今天新上海的改造,很遗憾,其整体的规划与设计在理念上是失败的,是以大面积放弃上海的居住传统为代价,全盘移植香港东南亚中产阶级的居住模式。在旧上海,‘法国’与‘上海’相处无间,在今天的新上海,既看不到‘法国’,也看不清‘上海’,‘东方的巴黎’已经自我肢解了。”“我深知这叫嚣无非是失败的哀鸣,其声调,有甚于真的失败。”
所谓“退步”,语涉双关,可理解为对百年中国人文艺术领域种种“进步观”的省思和追询。作者的文字观察敏锐,细节刻画尤其生动。书评人黄集伟说:“陈丹青虽是个画家,但很多散文家写不出他一样的文字。另外,读者们虽不是他本人,但这个海龟派笔下文化与语境的‘隔膜’与‘无助’,乃至‘欲拒还迎’的心态每个人都不难感同身受。
·痛击教育制度针砭学界时弊
·陈丹青:中国最敢言的知识分子之一
·2005年卓越网文化风云榜年度图书
·2005年《新周刊》新锐榜年度图书
|
| 關於作者: |
|
陈丹青,1953年生与上海,1970年至1978年辗转赣南与苏北农村插队落户,其间自习绘画。1978年以同等学历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1980年毕业留校,1982年赴纽约定居,自由职业画家。2000年回国,现定居北京。早年作《西藏组画》,近十年作并置系列及书籍景物系列。业余写作,2000年出版文集《纽约琐记》,2002年出版《陈丹青音乐笔记》,2003年出版杂文集《多余的素材》。
|
| 目錄:
|
“且说说我自己”
绘画
中国人为什么画油画?
常识与记忆
山高水张
批评与权力
骄傲与劫难
向上海美专致敬
油画与图像
绘画、图像与学术行政化
访谈
人样的,太人样的!
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
无知与有知
消费不是奢侈
媒体、大众与神话
城市
城市建设与历史记忆
建筑设计与行政文化
“有史以来”
我们应该向那位大清国老兵丁好好学习
心理景观、建筑景观与行政景观
古镇:衰败与沦亡
评议
众生相与人物画
国画革命的隔代国画
世界的重叠
地方与画家
伟大的残骸
影像
影像与中国
摄影的严肃,严肃的摄影
艺术作为摄影
摄影在中国
教育
我们上百年文化命运天灾人祸的总报应
天性和才能是挡不住的
关于绘画专业的“前瞻性”意见
无用的禀赋
调皮与聪明
事相、事实与理论
辞职报告
|
| 內容試閱:
|
【“且说说我自己”】
这不是“我自己”起的题目——事情是这样子:《收获》杂志明年改版(真抱歉,我从未读过们获们,编辑说是要开辟作家或艺术家谈论“自己”的专栏,在电话里几番情词恳切向我要稿子,终于推托不过,我说,非要写,出个题目,发几句问吧,于是电传传过来,给了这题目。
我不愿谈论我自己。我的家不挂自己的照片、自己的画一不为什么,也没想过为什么。平时偶尔发表文字,编辑索要照片,我也不寄。不知起于何时,中国的书刊作兴发表一张以至一张以上的作者照片(十九彩色,彩色照片真难看)。我不明白:为什么要麻烦读者看自己?你怎么知道读者愿意看见你?
可是好几位编辑语重心长劝过来:“随俗吧!这是读者的愿望。”
谁是读者?他们在哪里?就算真有读者坐在我跟前,我也不知如何“说说我自己”一人只要是坐下写文章,即便写的是天上的月亮,地上的蒿草,其实都在“谈自己”,而我是读到文章里出现太多的“我”字,便起反感,因我向来怕见进门坐下滔滔不绝大谈自己的人。
今岁我回国存身,不走了。人一旦成了所谓远来的和尚,归国的游子,即便仍是黄脸一张,“读者”总不免过来瞧一眼一采访,座谈,约稿,热乎乎地,都是抬举,都该解作善意。好吧,豁出去,我就三陪小姐似的陪一阵,陪过一阵,总会四散的吧,然而难办的是临了还要提供自己的照片拿去印,怎么办呢,挨得过初一挨不过十五,我终于屈服,就范,随了几回“俗”。新近接受ELLE杂志(即叫作《世界服装之苑》)的采访,就给要去几张与家人一起的照片,因编辑说是要给读者“亲切感”。事先征求女儿意思,不料她就高兴叫道:YES!同学们可以在ELLE上看见我!——她倒预先知道谁是她的“读者”了,而且中文版ELLE拿到美国去,怕是比法文原版还吃香。
自己拍照自己看,没什么。谁手边没有自己的相片呢,可是一朝发表流市,譬如在ELLE连篇累犊的朱唇、香肩、玉臂、秀腿之间忽然撞见“我自己”,我登时变成身份不明的“读者——昨天,11月号ELLE上了市,封面是美国影星“甜宝贝儿”布兰妮,侧身斜瞧着,一对丰乳在滑亮的铜版纸上几乎跌出来。打开,翻下去,心惊肉跳,闯了祸似的:“我自己!”
在“我”与“自己”的画作之问,感触怎样呢?9月,我的个展在北京展过,10月即开始了从湖北发端的巡回。在武昌那个空阔陌生的展厅,我又目睹一百六十多幅大大小小自己的画从货柜里一件件取出:有点亲腻,有点烦。二十年来年年办展,自己的画,自己早已看熟、看厌,每当这样的打点布置自己的展览,我多少像是置身事外,并茫然惊异于自己的冷漠。这茫然的惊异,外人不易觉察,我心里是知道的,此刻无妨说出来:那其实出于一种难以弃绝的自顾与依恋,仍算是轻微的热度吧。
但这都是后台的“内心活动”,纸面上的“文宇处理”。人在现场,“我”与“自己”往往还是不知如何坦然相处,犹如当年初出道。
只要有观众,我向来羞于走进张挂自己作品的展厅中去一不为什么,也不知为什么。多年前读到一篇关十马奈的回忆文字:他也竟羞于走近沙龙里自己的画幅跟前去,朋友拉他,他回执拒绝,停在远处。我知道,我岂能自比马奈,但是人同此心。幼年在体育场看见球手投中,满场叫好,那球手却总是埋首疾步跑开包毫不理会周围的响动,而那神色又分明听见并知道周围的响动的。胡兰成对此自有他的说法,他似乎格外倾心十他的说法,他说:古人箭中靶心的一刻,每在心里叫声“惭愧厂’为什么呢?因为此时是“在众人里看见了自己”。
放学了,一群小孩于,欢天喜地连打带闹,这时最怕爹娘冷个防窜出来,连名带姓叫回家。
贡布里希说:“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是吗?好像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每在大画家的回顾展厅里徘徊不去,我常会想起那位罗马总督手指耶稣说的话:“瞧一这一个一人。”是啊,我常想,真有所谓“艺术史”么?没有这单个单个的“人”,艺术史是什么?
在作品上签署姓名的传统是十分晚近的故事,相传始于乔多。乔多的时代,相当于我们的元末吧?中国艺术家的署名史,似乎要久远得多了。但我们可知道兵马涌的作者是谁?敦煌的作者又是谁?
“艺术家”一词是翻译过来的。在敦煌与兵马涌的时代,那些伟大的作品并不被看作是艺术,“艺术”一词,也是翻译过来的。
纪德(抑或是福楼拜?)说:“呈现艺术,隐退艺术家。”
签名只是签名。如今满世界的油画行货张张都签名,在中国,许多作者用的是拼音字母,斜体,飘逸,粗看以为是英文,是法文,其中最快的快手,一天能刷几十张。真的,在行货上,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
我长久迷们于委拉斯开兹的滋力。在他的画中,只见艺术,不见艺术家。
小时候翻墙越界,手腕于给大人捉牢了,拽到办公室,桌子一拍:讲!此刻,我若犯事败露扣在局子里,我将被迫“说说我自己”,正式的说法,即“坦白交代”一我愿坦白,我自认很坦白,只怕我说出的话,编辑、读者不要听。
编辑在电传里问:什么因素、什么时刻使你萌生了、确认了要当一名“艺术家”的想法?
我不知道,也不记得。至今我羡慕能够留起络腮胡子的人,我真想知道是什么因素、在什么时刻,他们的胡子开始“萌生”,并“确认”为络腮胡子,而我却没有。
编辑又问:面对现在艺术学院最年轻的艺术学生,如果他不知道您,会如何?
在今年出席的几次座谈会上,“最年轻的学生”递给我的字条会这样的提问:“请谈谈您的初恋,还有中年的欲望。”底下加个小括弧,歪歪斜斜写着:“一定要回答呀!”我“会如何”呢?我说,在我的青少年时代,男生女生根本不讲话。至于中年的欲望,请诸位等到中年再问吧。
编辑还问:听说两次您的流泪,一次是在伦勃朗画前,一次是在学生面前。
胡说!我从未在“伦勃朗”或“学生”面前流过泪。在别的时刻或场合,我确曾纵容过自己的眼泪,有时,那简直是欢欣的经验,但除非“刑具伺候”,我绝不招供详细,直到我愿意将之转化为别的叙述方式。罗兰?巴特在他追念亡母的著作《明室》中,母亲以及母亲的照片是贯穿全书的话题,可是在书中的大量照片里既没有他的母亲,也没有他自己。他坦白,但什么也没交代。他说:
“我要发表心灵,而不公开隐私。”
年轻的达利初访毕加索:“先生,我今晨抵达巴黎,没去卢浮宫,先来看您!”
毕加索应声答道:“你做得对!”
艺术家自当如是看自己。凡?高同志要算是倒霉的,但他在给亲兄弟的信中说:“有一天,全世界会用不同的发音念我的名字。”
这算是“隐私”还是“心灵”?20世纪初,据说散在巴黎蒙马特高地的“盲流画家”中有位老兄每天早起将脑袋伸出阁楼大窗对着大街吼叫着:我是天丁,我是天才!
看来我不配是个艺术家,不因谦虚,或因我是中国人。少年时,我在穷山沟里好像曾经躲进被窝偷偷默念过“我是天才”之类谚语,因是过期太久的陈年“隐私”,可以“发表”,聊供读者笑一笑。当代中国艺术家总算敢于公开求声名,放狂话,逞急旷达,旷达而遑急,似也渐与西方人连同一气。我就不止一次在国中关于艺术的文字中读到引自安迪?沃霍的话:
“每人出名五分钟。”
二十多年前,我时或被人告知我已出了名。近年回转来,小小美术圈的同行居然依旧记得“陈丹青”。只是这点若有若无的小名声,与“我自己”有什么关系?是什么关系?每见围上来要求签名的“最年轻的艺术学生”,我总是感到委屈而失措:替他们委屈,替他们失措。我签,但即便是伦勃朗或毕加索此刻坐在正对面,我一定不会走上去要求签个名。我会目不转睛看他们,假如能够,我愿为他们捶背,洗脚,倒尿壶。齐白石说他甘愿给青藤八大磨墨理纸当走狗,绝对真心话。
编辑的电传还说:即使现在,也有人不断在对《西藏组画》做解读。不见得吧,要真是那样,我该怎样解读这“不断的解读”?那是我的“声名”还是“我自己”?关于那些画,倒是四川美院一位学生说得最痛快。他生长在拉萨,与我老交情,看到后来一拨拨画家跑去画西藏,他脱口而出:打倒陈丹青!
上个礼拜我遇见了陈丹青,真的!还是在湖北,讲座过后,同学们又挤过来要签名。忽然人丛里钻出一位能说会道的小姑娘,江西人,属羊,与我闺女一般大——大家哄笑了:原来这姑娘与我同名又同姓一名叫“丹青”的同志我知道好几位,同名同姓,现前面见,却是第一回——我们彼此瞪着,傻笑,不知如何是好。她要是个男子,与我同龄,我就可以模仿安迪?沃霍聪明而善良的恶作剧,聘请这位陈丹青为我抛头露面开讲座。不是吗?在众人的朗声哄笑中,我俩终于并排站站好:这回是我要求与“陈丹青”合个影。
临了,陈丹青同志一定要我为她写句话,我就写:
丹青:你怎么也叫陈丹青?接着签了我的名。
但随即我就后悔了:凭什么人家不能也叫陈丹青?我该这样写:
丹青:我也名叫陈丹青。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