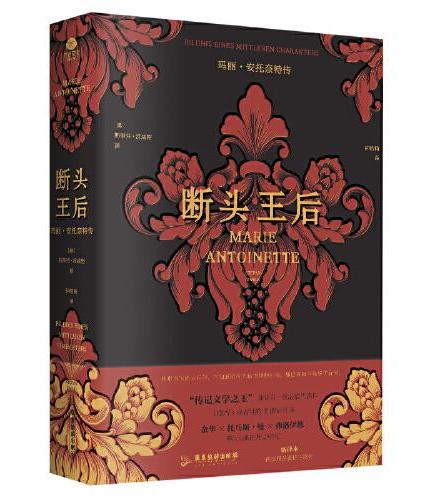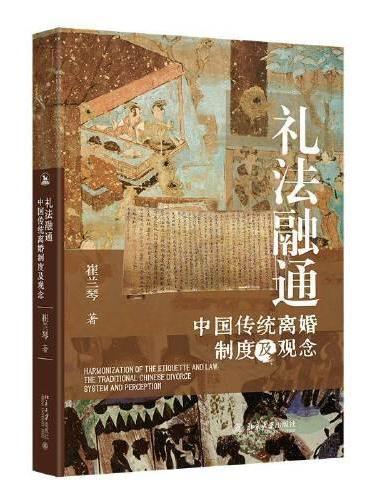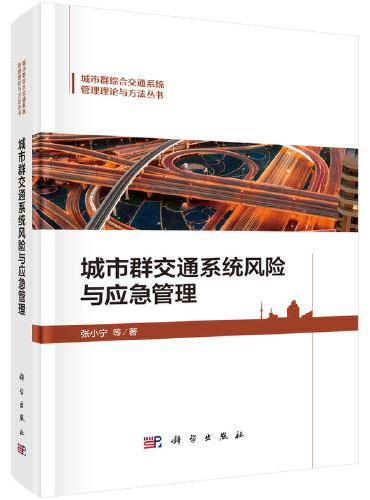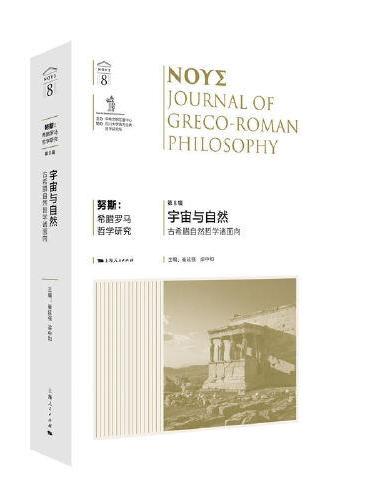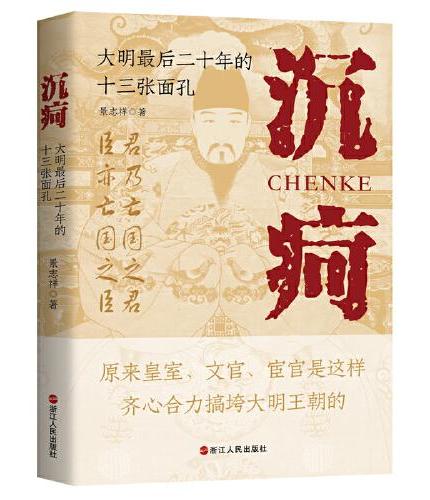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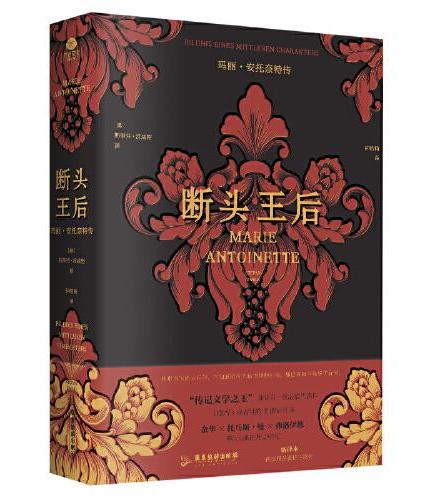
《
断头王后:玛丽·安托奈特传(裸脊锁线版,德语直译新译本,内文附多张传主彩插)
》
售價:HK$
61.6

《
东南亚华人宗祠建筑艺术研究
》
售價:HK$
97.9

《
甲骨文字综理表
》
售價:HK$
21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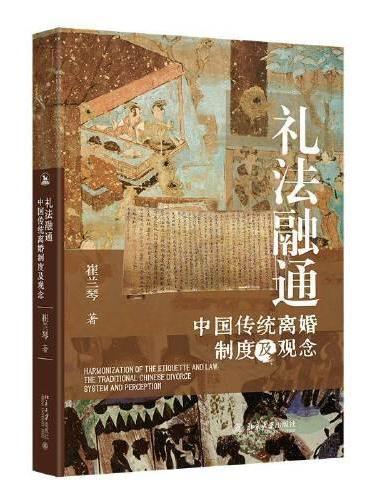
《
礼法融通:中国传统离婚制度及观念
》
售價:HK$
8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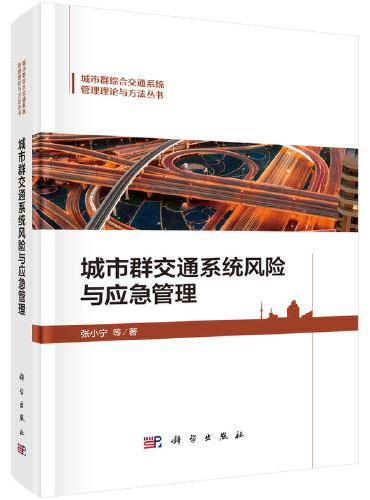
《
城市群交通系统风险与应急管理
》
售價:HK$
204.6

《
华南主要观赏树木图鉴
》
售價:HK$
17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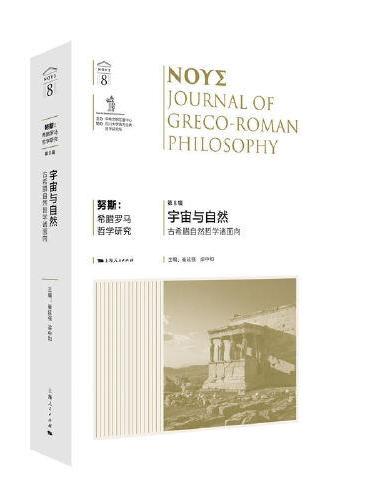
《
努斯:希腊罗马哲学研究(第8辑)--宇宙与自然:古希腊自然哲学诸面向
》
售價:HK$
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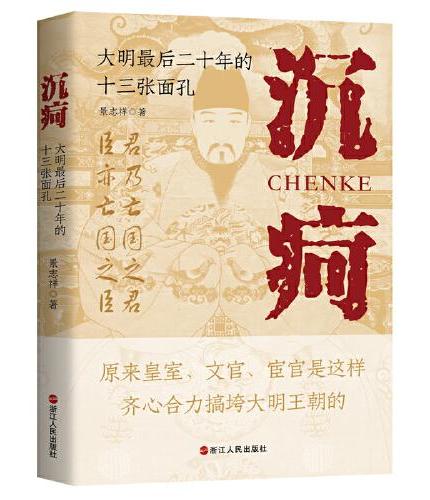
《
沉疴:大明最后二十年的十三张面孔
》
售價:HK$
52.8
|
| 內容簡介: |
|
《火烧经》及《吃饭》作者新作,章小东在《文景》杂志及《南方周末》的“私信”专栏作品集合。《尺素集》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是一封信,写给她文学上的先辈、老友,或是虽不得见面却神交已久的故人。《尺素集》还原那些文学史上赫赫有名人物背后的真实,完成个体化的生命记实;其中既有不为人知的文坛秘闻,也有作者独到的观察见解。
|
| 關於作者: |
|
章小东,现代文学大师靳以之女。出身名门,本应成为闺阁中的上海小姐;命途多舛,最终为吃饭远渡异乡。在美国端过盘子,打过零工,却依然守着自己的文学故乡。当年许多老一辈的文学巨匠都是她家的座上宾,到了异乡以后,更有国内外的文化名人叩响她的家门。虽然她已经不再迷信“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却依旧笔耕不辍,将自己的半生漂泊写成《火烧经》《吃饭》两部书稿,惊艳文坛,成为“最老练的小说新手” 。
|
| 目錄:
|
自序
墙(致巴金)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致张充和)
“鹿园”的守望者(致聂华苓)
迷雾当中的红楼一梦(致端木蕻良)
予唯不食嗟来之食(致莫言)
今夜的更声打着了多少行人? (致辛笛)
洋场恶少(致施蛰存)
从“礼物”到“遗物”(致朱安)
含英咀华(致王元化)
锲而不舍 久必有成(致李俍民)
你是《收获》的主编(致父亲)
私奔(致母亲)
假如(致孙寒冰)
一条河(致萧红)
江南才子(致黄源)
阳台上的张看(致张爱玲)
多变(致柯灵)
红色知识分子(致罗竹风)
一座山(致高行健)
死了没有遗憾 活着也很高兴(致夏志清)
人生有如大海行船(致孔罗荪)
|
| 內容試閱:
|
予唯不食嗟来之食
莫言先生:
你好。想起来这些天你家的电话一定打到“爆”,又因为自己的电邮地址不会出现在你的名单上,弄不好直接进了垃圾邮件,于是便用这种现代人早已抛弃的老古董的方式——写信。
打开电脑搜索你的名字,跳跃出来的都是有关诺贝尔奖的消息,而我的脑海里却重叠隐现了十二年前的景象。那时候的你,当然还不是诺贝尔奖的得主。你和所有到我家里来的作家朋友一样,随随便便地坐在我家的餐桌旁边喝茶、吃饭。我忘记了有没有喝酒,我想在这个异乡异地,我拿不出“红高粱”,你说有一顿中国饭就很好。记得那是本世纪第一个阳春似锦的三月,可是在美国的东部,仍旧还有些乍暖还寒的感觉。我生怕你不习惯,把房间里暖气开到很热。你热了,但是仍旧包裹着那件笔挺的西装,显然有些拘谨。事实上比你还要拘谨的应该是我,因为在当时我只读过了你的一部长篇和一个短篇。后来的一些作品对我来讲有些生涩,读起来很吃力,所以都没有读到最后。那个短篇的名字我已经忘记,内容却十分清晰,讲的是一个“你”在回乡的野地里,捡到了一个被人丢弃的女婴,没有办法处置,那种无奈、碰壁,特别是尴尬,让我忘记了这是一个讽刺故事,在哭笑不得当中平白无故地生出来许多同情。这就是一个作家最成功的本事,可以从纸上伸出两只手,把读者带进自己的世界,和你一起感受人生的甜酸苦辣。
我在这里要特别提起的还是在当时我唯一阅读过的你的那部长篇,这就是《红高粱》。阅读《红高粱》是因为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电影刚刚出笼,热门得一塌糊涂,我买不到电影票,只好到单位图书馆借来你的小说。
虽然是图书馆的书籍,却是崭新的,大概都去看电影了,冷落了真正的原版。还记得我是在上班的时间,偷偷打开了这本《红高粱》,躲在办公室的角落里开始阅读,不料立刻就被吸引了。我一页一页地阅读过去,忘记了窗外的太阳早已跌落到了大海的另外一边,眼睛里仍旧被一片鲜红映照。那里面浓厚的血腥搅拌着醇醉的酒香,被土地淫荡得神魂荡飏。
这以后我便拒绝观看电影《红高粱》,我以为你的小说老早就转化成了电影,一幕幕地印刻在我的脑子里,这是比电影更加精彩的电影。那里面有得是影像、色彩、声音,甚至都可以闻到其中的味道。这味道里面除了鲜血、老酒、人体以外,还有的就是土地。这是一片原始的土地,养育了一群原始的纯种的中国人。
我有些糊涂了,为什么合上小说仍旧逃脱不了小说里面的场景?是因为那里面的人?人的本能?本能的野性?对了,就是这个野性,长期以来一向被我拒绝的野性,此时此刻让我感受到了生命和生命的力度。我的心跳了,并且激动不已。高行健曾经履历千辛万苦寻找他心目中的灵山,即一种野性和原始,而这野性和原始正是组成你的《红高粱》的灵魂。
可是那天,当你坐在我家的餐桌旁边的时候,我实在没有办法把你和我心目当中那片野性的原始的红高粱连接在一起。我不会心跳,更不要说激动不已了。当时我们还住在校园里,红砖的小楼外面是一片平整的草地,你坐在那里,两只不大的眼睛透过落地玻璃门,久久地注视着户外的景象。终于你站起身来,打开玻璃门,踱入我的院子里。外面有些阴冷,我抓起你的外套跟了出来。我看到你西装革履皮鞋锃亮,笔笔挺地站立在院子当中,两只脚一踏上泥土地,就好像接上了地气,立刻活泛起来。你对着土地说:“多好啊!”
你又对着我说:“多好啊!挖开来,可以种植很多东西。”
“不好的呢,我挖过了,种了一点小葱和大蒜,结果长得稀稀拉拉的,就好像是个瘌痢头。”我指了指自己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开发出来的一片小地,说。
你走过去看了看,说:“你这哪里是挖地啊,仅仅刮破了一点点地皮,真是浪费了呢!”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浪费了土地还是浪费了我的力气,不容我多想你伸出手来,认真地对我说:“拿把铁锹来,我来帮你挖,只要给我两天时间,我就可以把你这片土地统统开发出来!”
我吓了一跳,刚刚你还在我的饭厅里惋惜,说是这次出国三个多月,让你少写了一部长篇,可是现在一看到土地,你就忘记了一切,恨不得甩开膀子在我的院子里开荒种地,我似乎又看到了那片种满了红高粱的土地,感觉到了土地的力量。
你在说到土地的时候是认真的,你说:“现在正是开荒的好季节,冬天的积雪把土地滋润得松软,一锹挖下去足有半尺多深,播上种子,松松土、施施肥、拔拔草……到了秋天,这里就是一片丰收的景象了。”
你还说:“土地是通人性的,只要尽力地对待它,它就会尽情地回报……”你不断地对我讲述土地,就好像是一个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土地的老农民。
事实上你就是一个农民,一个农民的儿子。十一二岁的时候辍学回乡,开始了你的农民生活。以后因为喜欢读书,用借的、用换的,换苦力的等方式,读遍了自己和邻近村落的所有书籍,变成当地最有学问的人。你告诉我,你有一个哥哥?还是表哥?到上海的一所师范大学读书,羡慕之余,你便阅读了他带回来的所有课本。随着你知识的眼睛渐渐睁大,你便越来越向往外面的生活。终于在二十一岁以后,你离开了当时你以为是枯燥无聊的土地。然而土地并没有离开你,当你一旦离开了那片土地,那片生你养你的土地,立刻长出无数的魔爪,日日夜夜缠绕着骚扰着你。生活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之间的你,内心深处却仍旧在遥远的土地上耕耘。土地是孤独的,你来了,带着你的真诚和纯朴,尽情地劳作。而土地则面对着你,舒坦地把自己展开,给你讲述最古老的故事,让你寻找到其中最隐蔽的私密。
你站在我的院子里,一遍又一遍地给我讲述土地,那陌生的乡语仿佛要把脚底下这片睡梦中的土地唤醒。你忘记了时间和空间,甚至忘记了你这次访问的目的,是要为史瓦兹摩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的学生演讲。年轻的大学生总归是最为单纯的,他们并没有想到你将来会是诺奖得主,也不会因此而感到你更加伟大,他们只是单纯地喜欢你的作品,喜欢你这个人,他们把你紧紧围绕在中间,问你一些质朴的问题。一个女孩子口无遮拦问你: “你怎么会这么残酷,把活剥人的头皮,生割人的鸡巴,描写得如此淋漓尽致?”
你毫不忌讳地回答:“实际上我是一个很胆小的人,连只鸡也不敢杀的呢!”
大家都笑起来了,一个男孩子问你:“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会写小说的?”
你不假思索地回答:“在我阅读了福克纳的小说以后,我发现:原来小说可以这样来讲故事的呀?!这样的故事我有一肚子,于是我就把肚子里的故事倒出来了。”
大家又笑了,一下子和你亲近起来。后来几个学生留学北京读中文,竟然摸到你的府上,你和你的家人就好像对待自己远归的孩子,亲亲热热地围坐在一起,大吃了一顿自制的饺子。那些学生兴奋之极,除了是因为吃到了你家的饺子,更因为你家的饺子非常好吃又好看。这些幸运的学生现在早已毕业,他们当时一定不知道吃饺子是你家最隆重的庆典方式,在你获得诺奖的第二天,你就说:你准备晚上和家人好好吃一顿饺子。
我仿佛又看到了站在我家院子里的你,不对,是站在红高粱当中的你,你一个人站在你的土地上,若有所思地和你的土地对话。我的思绪发生错乱,好像看到福克纳站到了面前。你走过了一条和这位先行的诺奖得主如此相似的道路,同样是乡下的牧羊人,你阅读了哥哥的大学课本,他跟着邻居假装“读”哈佛;你没有经历过抗日战争,他没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冲锋陷阵,可是你们都可以把战争带来的痛苦描写得身临其境过一样。特别是你们的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视土地为生命——为生命全部的意义。
你很聪明,一下子抓住了福克纳的脚后跟。但是,当你跟随着这位先行者好不容易爬到了山峰顶端的时候,却发现山外还有山;就好像你以为你诺奖的奖金足以让你在那个你临时歇歇脚的大城市购买一幢大房子,结果只是一间空中楼阁。
此时,打开电脑,立刻跳出你的许多消息,不知是真是假。假如是真的,我很欣赏你家人的一句话:“予唯不食嗟来之食……”
我想这是大家都懂的。
小东
2012 年10 月写于美国圣地亚哥太平洋花园公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