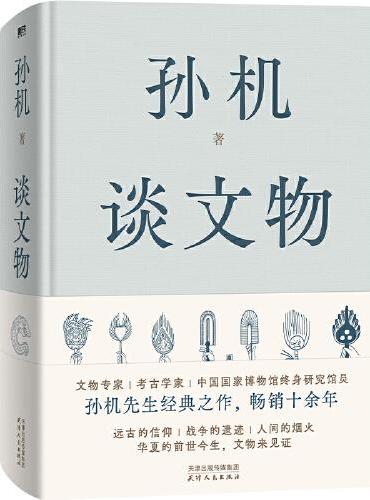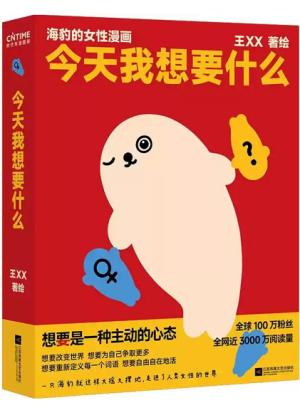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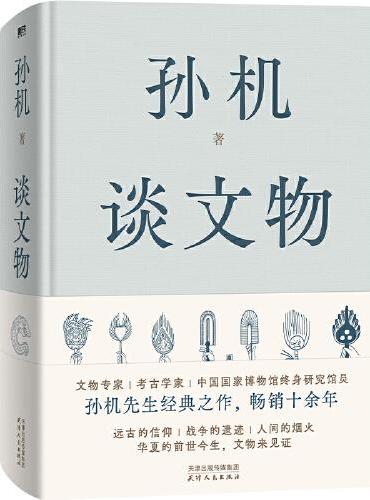
《
孙机谈文物
》
售價:HK$
118.8

《
诡舍(夜来风雨声悬疑幻想震撼之作)
》
售價:HK$
54.8

《
讲给青少年的人工智能
》
售價:HK$
52.8

《
海外中国研究·宋代文人的精神生活(经典收藏版)--重构宋代文人的精神内核
》
售價:HK$
107.8

《
埃勒里·奎因悲剧四部曲
》
售價:HK$
30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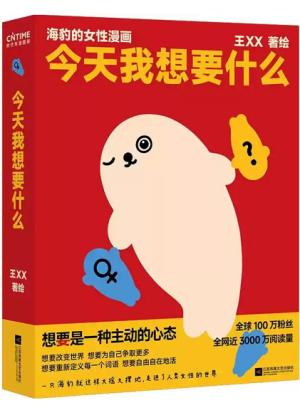
《
今天我想要什么:海豹的女性漫画
》
售價:HK$
74.8

《
日常的金字塔:写诗入门十一阶
》
售價:HK$
74.8

《
税的荒唐与智慧:历史上的税收故事
》
售價:HK$
107.8
|
| 編輯推薦: |
《北京晚报》《世界日报》《立报》《新蜀报》《华商报》……
——从事报业六十余载;
创办《光明报》《光明日报》《民族画报》《人民政协报》……
——他的事业至今传承;
冒险报道“七君子”案,深陷国民党集中营两年多……
——他的风骨令人叹服。
同行眼中,他是优秀新闻学家,著名办报人;
同事眼中,他是著名民主人士,爱国一赤子;
儿女眼中,他更是最亲最爱的父亲。
女儿萨沄亲笔撰述,
群言出版社隆重推出,
真实还原历史动荡中的爱国知识分子本色。
|
| 內容簡介: |
|
萨空了1907—1988 ,原名萨音泰,笔名了了、艾秋飙,是20世纪我国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新闻出版家、报刊主编、新闻学家,也是出色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1927年开始在北京从事新闻工作,曾供职于北京《北京晚报》《世界日报》、上海《立报》、新疆《新疆日报》、重庆《新蜀报》《华商报》等报社。抗战时期,与梁漱溟在香港创办民盟机关报《光明报》;建国后,筹建《光明日报》《民族画报》和《人民政协报》。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十分重视少数民族的文化建设,是新中国民族文化工作的开拓者。同时他也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曾任第四届、五届民盟中央副主席。
|
| 關於作者: |
|
萨沄,又名萨苦茶,出生于1928年,是萨空了长女。多年从事新闻编辑工作,曾在国际新闻局和外文出版社任翻译;在《内蒙古日报》、《健康报》和《大众健康》等报刊任记者、编辑、高级编辑和主编。
|
| 目錄:
|
【目录】
前言
序
第一章 雏凤清声 蒙古族青年
一个蒙古后裔的故事
初涉社会
第二章 东奔西走 著名办报人
登上新闻大舞台
创办香港《立报》始末
为了建设新新疆
重庆一年
第三章 身陷囹圄 民主宣传人
香港沦陷前后
艰难世事(上)
艰难世事(下)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
工作大忙人
为争取人民民主奔忙
迎接新生活
与救国会的渊源
新中国民族文化工作的开拓者
一次不寻常的赴港演出
第五章 历尽劫波后
赤子情怀存
在劫难中
故地留痕
建国后在民盟工作
在政协机关工作
第六章 桑榆夕阳红
斯人终逝去
在医院中
晚年
附录:
萨空了同志生平
萨空了年表
后记
重版随想
跋
|
| 內容試閱:
|
第一章 雏凤清声 蒙古族青年
一个蒙古后裔的家事
1907年3月26日,在四川成都.虽是乍暖还寒的节气,却逢阳光明媚,给万物带来无限温暖与生机。就是这—天,在离都督衙府不远的一座深宅大院里,诞生了一个男孩。这是都督府正黄旗蒙古笔帖士石麟第二位填房桂氏生下的第三个男孩。他就是我的父亲萨空了。
这年石麟已三十一岁。他的祖上世居扎库木地方,郎姓。自从清初随军入关以后一直都居住在北京。他的父亲荣惠、祖父特克什布、曾祖广宁,几代都为巩固中国的领土、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立过汗马功劳,曾受到清帝的嘉奖。他自己十四岁从正途经考入仕,当了个候补笔帖士。因为他的聪慧好学,光绪帝还特嘉奖他的母亲教育有方,加封为二品夫人。可是当他的父亲去世以后,由于只知读书不会理家和惧内,常受妻家骚扰又无法解脱,他只好央人换了一个外差,举家搬到成都,在川督赵尔丰手下当笔帖士,求个安静。但是,在清朝正趋于败落的光绪末年,国事不宁童哪里有安乐之地?一向寡言少语,性格内向的他,更是郁郎不欢。
新生的儿子给地增添了几分喜悦,冲刷了他不久前因伤逝二子留在心上的阴影,他给新生的儿子取名萨因泰蒙语译音,意思是有福气的人,并吩咐家人称他为老二。此后,桂氏又接连生了两个儿子。到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石麟千家返回北京时,他已是五个孩子的父亲,除了原配生的女儿外,还有四个儿子。
回到北京,家产已被亲戚分占。石麟家属于被推翻的清朝蒙古族小官,正是当时被唾弃的社会阶层。他既不敢与人争要家产,又无法再求职谋生,只好靠变卖藏品衣物度日,躲在家里课子读书,《四书》、《五经》、史文、诗书画,尽己所能讲授给儿子。在贫病交加中,他四十五岁就去世了。
我知道上述故事时已十六岁,在重庆。那是1945年,父亲刚从国民党集中营释放出来不久.有一天他带我去看望女友——后来成为我第一位继母的方菁。他们在闲谈各自的家事时,我在旁边听到的。那时,我家已经历过重大变故。自1935年,我家离开北京到上海,由于抗日战争的影响和父亲工作的变动,以后就不断迁移,从上海到香港、到新疆、到重庆,又到香港,再到桂林,又到重庆。在这段艰难坎坷的生活历程中,先是父母离了婚,继而父亲被国民党逮捕。
以前,我对父亲家的事知道得极少。我母亲金秉英娘家是基督徒。母亲只和自己娘家人往来,不大看得起父亲家的人。加上我七岁时全家就离开北平,所以几乎对奶奶、姑姑,叔叔全无印象。我真正知道家事是在解放以后重返北平故里时。
1949年,北平解放后,父亲从香港到北平,我和妹妹萨石 原名萨苦荼也从解放区进入北京,这时,才和亲属们团聚。
这一天,我见到了我的姑姑、叔叔、婶婶和堂弟妹们。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我们走进三叔家院子时,亲人们都从堂屋迎了出来。进入堂屋,只见北面墙上挂着祖父母的大幅照片。我们向祖父母行了礼,我仰头仔细打量,照片上的奶奶显得比爷爷老,四为爷爷去世时是中年,而奶奶去世时已是老年了,我一眼就能看出,父亲的嘴像爷爷,眼睛像奶奶,姑姑完全像爷爷,三叔是眼睛像爷爷,嘴像奶奶。几十年过去了,虽然照片已在“文化大革命”中丢失,但至今我仍记得那两张照片,记得爷爷紧紧闭着的嘴,想象出他的顽固执拗;记得奶奶那炯炯有神的眼睛,想象出她那精明能干。
那是很快乐的一天,见到那么多亲人。我的三婶特别会照顾人,亲切热情而且无微不至。三叔是真正地爱我们,就是不会表达。他拿出许多小物件,使劲地想找一些东西是我们喜欢的,让我和妹妹带走。姑姑则更不善言辞,只是含笑站在一边看着我们。这样的情景以后就不多见了.因为父亲工作忙,几乎再无时间到亲戚家叙家常。
五十年代初,北京市扩建,近城的坟地需迁移。我家的祖坟就在红庙附近。三叔找爸爸问怎么办?爸爸说,平了算了。三叔不肯。最后还是他去迁了坟。后来听三叔说,原先只知道祖坟很大,看坟人在此赖以种庄稼为生,过去还常送些玉米、豆子给他们,这次挖坟才知道,这里竟埋着好几代人。他只是大致收殓了遗骨,重新埋葬了。三叔还带回一个包袱,里面包着从墓地挖出的陪葬品。正好那天我在三叔家玩,我略略看了一下那打开的包袱皮,有扳指、簪子、戒指、挂件等等。因为年代久远又埋在土里不见天日,已失去光泽。三婶忙让包起来,说:怪瘆人的,别看了。
三叔是个感情不外露的人。迁坟以后,坟场上还留着几棵古柏,他过一段时间就要去看看那树,却什么也不说。后来.我家坟地的旧址上建立了劳动干部学校。学校校名一改再改,而那古柏至今仍矗立在后门外。据说已成为受保护的古树。
由于解放后人们都怕说自己的出身不好,父亲从没向我们说过祖先的情况。只是在他被任命为国家民委副主任时,说了句“我爷爷在清朝当过理藩院侍郎,就相当于现在的民委副主任吧?”大家听了只觉得有意思,谁也没理会这事。后来,有一个星期日,我去三叔家,看见三婶收拾柜子,拿出许多废字纸,打算卖给收破烂的,我信手翻翻,看见有清朝的文书.就和三叔翻阅起来。三叔说这都是给我曾祖父荣惠的。我们当时还算了算,他很长寿,给皇帝干了五十年。回家后我曾向父亲说起这事,父亲只是淡淡地说:你管那些闲事于什么!从此,我不再提这事,也不想这事,看到的东西也渐渐淡忘了。现在回忆起来,仿佛有称他蒙古学士的,有褒扬他当钦差清廉的,还有批准把侧室扶正的。主要因为那时我很年轻,文言文看不懂,自然就记不住了。直到最近,我想起这件事,去翻阅了中华书局1977年版的《清史稿》,找到荣惠的名字,原来他还当过兵部和礼部左侍郎。
“文比大革命”以后,年老的姑姑仿佛知道自己来日无多,总爱向我们说说她童年的往事。但由于她读书不多,只能东拉西扯地说故事.不能有条不紊地讲历史,我们也只是随便听昕,从没问个究竟。姑姑比爸爸大一轮十二岁,她和爸爸不是一个母亲所生。她的母亲是爷爷的原配,也是蒙古族。由于她生下来不久母亲就病逝,她连母亲的名字也不知道了。后来爷爷娶了填房,但不久又病逝。因此人们认为爷爷克妻,在娶我奶奶时,就从后门而入,以免惊动神灵,免祛奶奶遭灾难。姑姑说,在娶我奶奶的那天,人们都忙着办喜事,没人管她那时姑姑大约五六岁,是我的曾祖父抱着她在堂屋里来回遛。曾祖父十分怜爱她,还带地到东北当差。曾祖父是在东北病逝的。灵柩从东北运回北京时,家人在慈云寺跪迎。据《天咫偶闻》载:“相传慈云寺为某邸家庙。”和我家有什么关系就不得知了。姑姑又说,那时家里是殷实的,曾祖父去世后,由于爷爷为人清高,家事统由奶奶掌管,家产外流到奶奶娘家。待到祖母醒悟过来.—切已无可挽回,从此家道败落。姑姑是不原谅奶奶的兄弟们的,不愿和他们往来。
姑姑命运多蹇,不仅幼年失母,长大结婚,丈夫又是纨拷子弟,不久家产败尽,丈夫一病而亡。姑姑只好靠做手工度日。她从没生育过,没有儿女。解散后,我们重返北京,父亲说接她到我们家,她执意不肯。后来是我和堂妹硬把她接了过来。从此,她就一直在我家照料家务。那时,我们家有一位保姆,还有一位公务员,姑姑总争着干事,不肯闲着。父亲多次和她说,你是我姐姐,年纪大了,谁也不会嫌弃你。姑姑总是默默地低头听着,过后还照原先一样。有一次姑姑不声不响地把父亲的一条毛裤拆了,要重新织。继母发现后说,不用她干,姑姑说,毛裤破了,我不能让他那么忙的人,穿一条破裤子。继母说,你眼睛不好,不是掉针就是打错。两人争了起来,姑姑哭了。后来,父亲对姑姑说,万事要能忍。咱们萨家的人,—个比—个倔,我学了一辈子,才学会忍,你就不能忍?!父亲就是这样—下个人,对谁越亲,对谁要求得越严。姑姑当然懂得父亲的难处。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送到“五七”干校,生活十分艰难,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姑姑常为此而悲泣,恨自己年纪太大了,否则不管到什么艰苦的地方,她都愿去照颐自己的弟弟。“文化大革命”后,父亲从干校回家,健康大不如前。姑姑关心他,又不会表达。只能默默地弄点他爱吃的零食,什么玫瑰枣,煮花生啦。每当晚上父亲一个人在客厅看书或工作时,她就悄悄送过去。她看到父亲头发渐渐花白,听人说吃核桃好,就每天给他剥七个核桃,而且一直坚持下来。姑姑的爱是藏在心里的,她不会表露,也不想表露,因为她从不想求回报。有一个冬天,我回家过春节,姑姑找东西,我在旁边和她说话,看见箱子里有一个木制小手饰盒。我随手打开,里面有一张男人的半身照片,穿戴是民国初年的样子。我问姑姑是谁?她说是你姑爹。我故意逗她,说:“哈,您把姑爹藏在这儿?从不让我们看。”姑姑笑了。因为姑爹不争气,家里人部看不起他,姑姑也从不提他。但是,她的心里,无疑仍有着他的位置,没准儿,仍然爱着他,思念着他。1979年,姑姑是在她八十一岁时去世的。她摔了一跤,就起不来了。她可能是不愿拖累别人,她是那么好强,连被子都不愿让别人帮忙洗,怎么肯让别人服侍?她就不吃东西,谁劝也没用。临死的前一天,我在天津工作的妹妹萨石突然感到非回家看看姑姑不可,匆匆忙忙赶了回来。姑姑看见她,显出来高兴。晚上萨石喂姑姑吃鸡蛋挂面,姑姑竟然吃了。不料,就在这个晚上姑姑去世了。萨石说,因为她和姑姑感情好,也许是预感吧,让她赶回来,为姑姑送了终。
我当时在内蒙古工作,知道姑姑有病,我写信问严重不,我要不要回去?父亲回信说,先不用。没想到竞未见到姑姑最后一面。其实,在她去世前两年,每年我回家过春节离去时,她总是哭,说怕见不着了。她可能感到自己年老体弱,支持不了多久了。姑姑去世后,我回到家里,丧事已办完。父亲见我,嗔怪地说,现在回来有什么用。他是重视亲情的,怪我回来晚了,父亲拿给我一个姑姑做手工用的银顶针,这是我曾在信中提出来要做纪念的姑姑的遗物。顶针由于使用年代已久,有的小孔已经磨平。这是姑姑一生辛苦的见证。我不仅自己保存它,还要留给我的子孙,让他们永志不忘这位心地善良,坚韧勤劳的老人。
我到八宝山向姑姑的骨灰痛哭告别。当晚,我仍住在姑姑住房的外间。夜里,忽然听到一阵滚动的声音,窗子也在震响。我想,也许姑姑来看我了。我并不害怕,我们彼此关心,真诚相待,她若有灵,也会保佑我的。
我的三叔本是个小职员。解放初期,自己弄了个小作坊,磨镜头。夫妻两人干,请过一个亲戚帮忙。社会主义改造时,神差鬼使,他没加入合作社,却把作坊和一家大厂合并了,因此就成了一个只有三干元资本的小资本家。戴着这顶帽子加入了光学仪器厂当技术员。他懂英、法、德、日文,给工厂翻译点资料。“文化大革命”中,我三叔家被抄,还扫地出门,住进小杂院的一间小房里。“文革”后发回抄家的东西,其中有家谱。这是奶奶留下来的东西。由于抗战时期,我们家、四叔家都离开丁北京,奶奶是跟着三叔一起生活的,奶奶去世后,祖上留下来的东西也就留在三叔家了。父亲从没过问这些事四叔一家后来失去音讯,估计已不在世了。直到这时,我才第一次看见家谱,是蒙、汉文各一份。谱里卷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八世祖伊里布曾孙世珍元孙连翰。世珍和连翰两个名字是用红笔写的。我们推测,这是制谱人,用红笔写是因为当年他们仍活着。谱上首位名叫福满,名旁有一行小字,写着:世居扎库木地方。扎库木在哪儿?我不知道,由于父亲一直说我们是内蒙古翁牛特旗人,我猜想,可能在现在的赤峰一带。算起来到我父亲这一代已是第十一代子孙了。伊里布和我太祖特克什布是堂兄弟。他们这一支人到底在那里?就无从知道了。
1984年,我三叔患重病。去世前几天,我去看他。他对我说:“告诉你爸爸,孩子不懂事,别生气。我已写信说他了。我说,哥哥对我的恩情,我一辈子都报答不完。他们不应因为满足不了自己的要求而责怪你爸爸。”三叔又让三婶把诰封拿出来,让我带回去给我爸爸。还说,是不久前刚退回来的抄家拿去的东西。三婶从柜子里拿出来,共十卷。以前,我们从没听人讲过浩封的事,连父亲也不知道有这东西。
诰封是清朝皇帝对五品以上官员本身及其妻室、父母、祖先授予荣誉和封赐的文书。过去,我只是在电影里看见过宣读诰封的场面,以为它不过是一方锦片。真的诰封全不是那么回事。它横长约八尺以上,竖长九寸,各年代的规格不尽相同。这是完整的一块长锦缎,头尾织有双龙纹和奉天诰命宇样,中间用黑、红、黄、白、金黄五色分段织出云头花纹,在它上面用黑、白色,或绿、蓝、黑、白、红色笔,书写满、汉两种文字的皇帝的命令,并盖有皇帝玺。诰封用白纸黄绫边装裱,尽头的一段则用金黄底,蓝、绿、白色织成如意花纹的锦缎装裱,卷起来看,是一个色彩斑谰的锦卷。
从这几卷诰封中,我才第一次知道,原来我们是正黄旗蒙古人。这真让我吃惊。因为过去.我一直对旗人没好印象。虽然什么叫旗人,我根本不知道,真可谓一窍不通。但是,由于人们都这么说,清朝时,旗人欺压老百姓,坐享皇饷,好吃懒做等等,我一直是鄙视旗人的。自己也是旗人?—时真接受不了。为了弄清究竟,我就找书来看。现在我终于找到了答案,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作为蒙古放人,既没什么光荣,也没什么可耻。这不过反映了历史生活中的一段事实。
八旗制度是清代满族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太祖努尔哈赤初建黄、白、红、蓝四旗,后增建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共为八旗,满族成员分属各旗,旗归参领、佐领领导,平时生产,战时从征。太宗皇太极时,又将降伏的蒙古人和汉人分别编为“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这种组织兼有军事、行政、生产三方面的职能,适应当时满族社会经济基础的需要,对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入关后,清廷曾利用八旗制度来控制人民,生产意义缩小,作为军事组织和行政组织的职能仍存在。旗人和民人的不同之处是旗人享有多少不等的粮饷,在入学出仕方面有一定特殊待遇。这些当然会激起一般民人的愤愤不平。特别是对汉民族,本来,在他们看来,汉族统治少数民族是天经地义.被异族统治则是痛心疾首的事,再加上旗人享有特权,就更不满了。清朝灭亡后,民族关系翻了个个儿。一些人弄不清究竟,就统统鄙视旗人,少数民族又遭到歧视。在这种情况下,旗人和他们的后代.悄悄地销声匿迹。只是在解放以后,民族隔阂和民族歧视才渐渐消除。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人后来都承认了自己的祖先是少数民族,是旗人。
从这几个诰封可以窥见我的祖先生平的一斑。如:乾隆五十年给我五世祖广宁的一段文字:“……尔正黄旗蒙古佐领加一级广宁,职司军旅,材裕韬钤迪果毅于戎行,……兹以覃恩,特授尔武翼大夫,锡之诰命……”又如;“尔绰克图,乃正黄旗蒙古佐领加一级广宁之祖父,性资醇茂,行谊恪纯,启门祚之繁昌,簪衍庆廓韬钤之绪业……兹以覃恩赠尔为武翼大夫……三世声华,实人伦之盛事,五章服采,洵天室之隆恩……”再如嘉庆十四年给我太祖特克什布之妻的诰封中有这样一段:“尔理藩院主事加二级特克什布之妻觉罗氏,素谙内则,作配名门,训典明允,协珩璜之度,礼仪纯备,克彰苹彩之风,兹以覃恩封尔为宜人……”从文字看来,我的祖上是行伍出身,立过军功,属名门望族。
据我的堂弟萨备说,他家曾存有皇上赐的两副围棋子,一副是紫晶的,一副是玛瑙的,“文化大革命”被抄,不知去向。总之,这—切都是我们祖先留传下来的,关于他们生平的记录,但是,除了华丽的词藻,炫耀的传说,所表达某种虚荣的东西以外,没有什么实在的,有血有肉的故事可供纪念。这对于我们,作为后代的人,留下的实在太少了。
父亲去世后,我整理他遗留下来的文稿.见到一份他写于1960年的自传草稿,其中谈到自己的家事时,这样写道:“我的父亲,是精通汉学和藏语的蒙古人。生平嗜文物书画,爱游历,淡泊名利,消极厌世。辛亥革命后,蒙古族受歧视,长期不能就业,靠出卖藏品及衣物度日,时有断炊之虞,更增了他悲观的思想,1920年,他四十五岁就病死了。”
我从这短短的文字描绘中,感受到祖父作为—个蒙古族没落世家子弟的悲怆情怀。后来,当我翻阅一本名为《话说峨眉山》的书时,这种感觉尤深。这本书中有一段说,上峨眉山在过了纯阳殴,就是慧灯寺遗址,在这儿可以仰望金顶,可以看到峨眉山的全景。往前走是万定桥,再往前就能看到一股清泉从大石隙中涌出,这就是闻名遐尔的所谓神水。这水质地清冽,含有多种矿物质。古代来这里游历的文人墨客很多,多有题刻。其中有“水啸山空”的宇样。读到这里,我联想起父亲从前向我说过的往事。
原来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