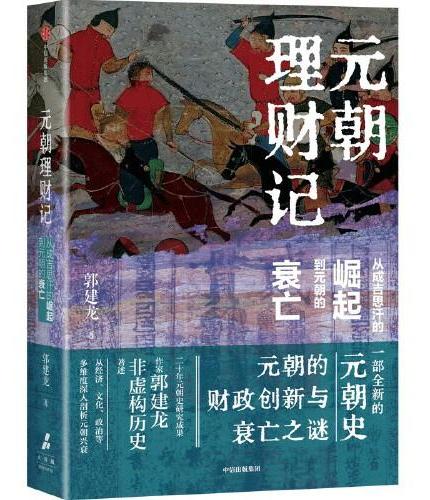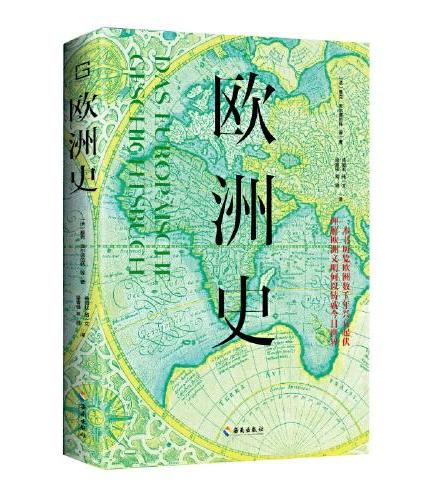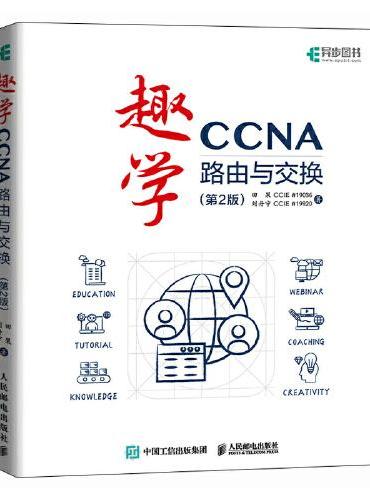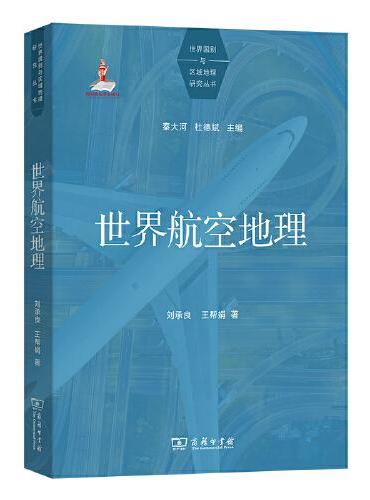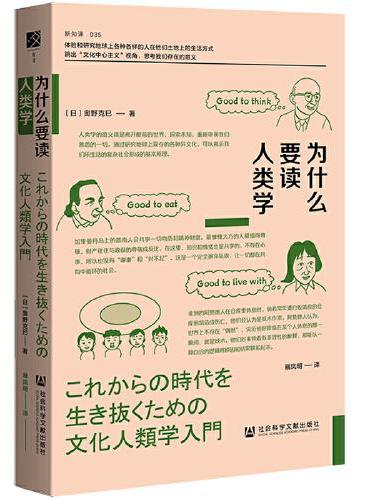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以经治国与汉代社会
》
售價:HK$
98.6

《
我真正想要什么?:智慧瑜伽答问/正念系列
》
售價:HK$
5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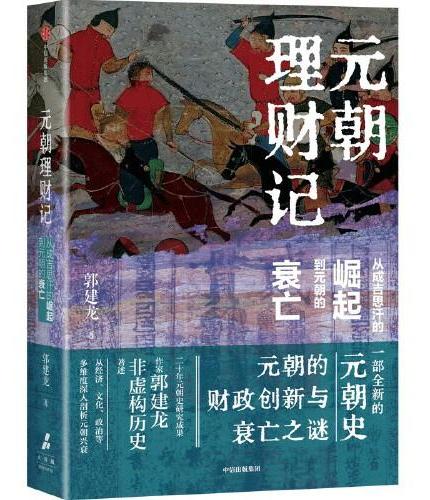
《
元朝理财记 从成吉思汗的崛起到元朝的衰亡
》
售價:HK$
9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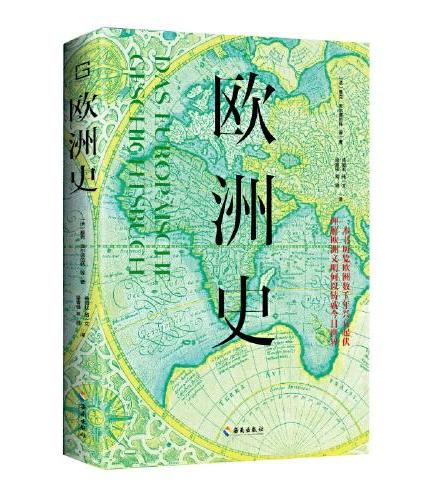
《
欧洲史:一本书历览欧洲数千年兴衰起伏,理解欧洲文明何以铸就今日世界
》
售價:HK$
33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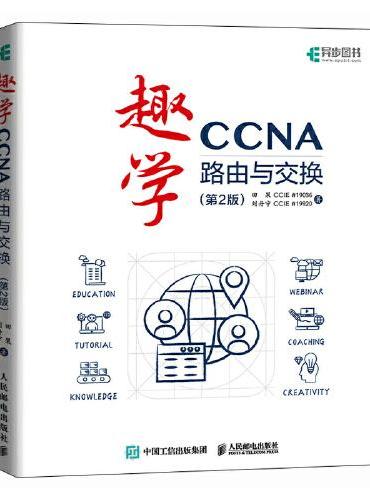
《
趣学CCNA——路由与交换(第2版)
》
售價:HK$
1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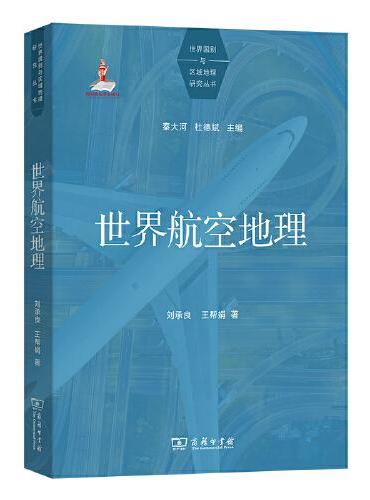
《
世界航空地理(世界国别与区域地理研究丛书)
》
售價:HK$
244.2

《
学术的中心:英法德美
》
售價:HK$
8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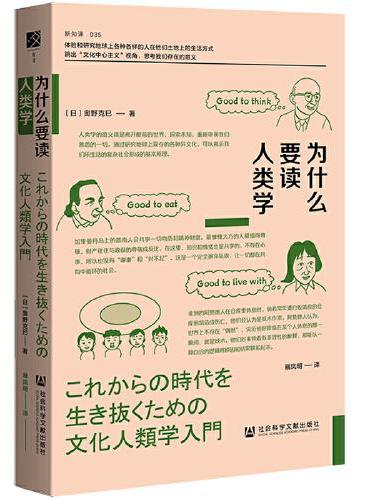
《
为什么要读人类学
》
售價:HK$
77.3
|
| 編輯推薦: |
余光中最经典、最权威作品,套装全8册、大陆首发
“阴阳一割,昏晓两分,抒情与评论不再收在一起。”《分水岭上》是余光中先生的第一本评论文集。
余光中先生的这本评论文集,虽为特殊场合而执笔,却十分认真写成。二十年后,作品仍然不失讽时的价值,显然经得起时光的浪淘,没有被文学史淘走。
|
| 內容簡介: |
书以《分水岭上》为名,表示在那之前,作者的文集常将抒情文与议论文合在一起,但从此泾渭分明,就要个别出书了。这本评论集,评析内容包含新诗、古典诗、英美诗、白话文、小说、综论等,虽为特殊场合而执笔,却十分认真写成。
检讨白话文西化的三篇文章,是有感于当日中文的时弊,不吐不快而一吐再吐的杞忧。二十年后,此弊变本加厉,变成了积弊,足见这些文章仍不失讽时的价值,值得仓颉的子孙参考。
|
| 關於作者: |
余光中 当代著名的散文家、诗人。一九二八年生于福建永春,因孺慕母乡常州,神游古典,亦自命江南人。又曾谓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
一生从事诗、散文、评论、翻译,自称为写作的四度空间。被誉为当代中国散文八大家之一。
|
| 目錄:
|
新 诗
徐志摩诗小论
用伤口唱歌的诗人
——从《午夜削梨》看洛夫诗风之变
青青桂冠
——香港第七届青年文学奖诗组评判的感想
谈新诗的三个问题
古典诗
连环妙计
——略论中国古典诗的时空结构
星垂月涌之夜
重登鹳雀楼
三登鹳雀楼
英美诗
另一首致萧乾的诗
马蹄鸿爪雪中寻
苦涩的穷乡诗人
——R.S.托马斯诗简述
白话文
论中文之西化
早期作家笔下的西化中文
从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
小 说
断雁南飞迷指爪
——从张爱玲到红卫兵带来的噩讯
红旗下的耳语
——评析金兆的小说
从逃避到肯定
——《毕业典礼》的赏析
综 论
分水岭上
选 灾
给抓到小辫子
横岭侧峰面面观
——论作品中词性之变换
诗的三种读者
亦秀亦豪的健笔
——我看张晓风的散文
缪思的左右手
——诗和散文的比较
后 记
|
| 內容試閱:
|
《分水岭上》是我中年的评论杂集,里面的二十四篇文章都在1977年至1981年间写成;1981年4月由纯文学出版社初版,后来曾经三版,但是纯文学歇业后,迄未再印。二十多年后改由九歌接手重印,我这做母亲的总算把流落江湖的浪子又召回了一位。他如《焚鹤人》、《青青边愁》、《在冷战的年代》等等,也将一一召回。
书以《分水岭上》为名,表示在那之前,我的文集常将抒情文与议论文合在一起,但从此泾渭分明,就要各别出书了。在那以后我又出版了五本评论文集,其中的文章有的是自己要写的,不吐不快,有的是应邀而写的,包括编者邀稿,会议命题,或是作者索序。回顾这本《分水岭上》,也有这种现象。例如检讨白话文西化的三篇文章,就是有感于当日中文的时弊,不吐不快,而一吐再吐的杞忧。二十年后,此弊变本加厉,变成了积弊,足见这些文章仍然不失讽时的价值,值得仓颉的子孙参考。另一方面,像《亦秀亦豪的健笔》一篇,原为张晓风女士的新书《你还没有爱过》作序,这些年来竟成了学者与记者经常引述的“定论”,足见吾言不虚。这本文集九歌最近重印,作者在感言中竟说,重读我的旧序,仍然十分感动。作品要传后,评论同样也要经得起时光的浪淘。她的书,我的序,显然都没有被文学史淘走。这是多么可贵的缘分。
九歌将我的浪子一一接回家来,固然非常温馨,但是相应地我也要重校旧籍。目前我正在自校五百多页的《梵高传》,不由对吾妻我存叹说:“我就像一个古老的帝国,终将被众多的殖民地拖垮。”
为了抢救帝国,我存常在灯下戴起老花眼镜为我分担校对之劳。这本《分水岭上》有一半是她校的,另有一小半是维梁夜宿我家所接力。容我在此谢谢他们。
余光中 2009年5月14日于左岸
谈新诗的三个问题
从五四到现在,中国的新诗已经有六十年的历史,迄今名诗人已经很多,而大诗人仍然渺渺,论者每以新诗“成绩欠佳”来责备诗人。六十岁在人,已是花甲之年,但在文学史上,却不能算长。唐开国百年,才出现李、杜、王、孟、高、岑等大家:杜甫和高适、岑参、储光羲等同登慈恩寺塔的那一年,唐朝立国已有一百三十四年了。欧阳修开始写诗的时候,宋朝已有七十年的历史;等到王安石、苏轼出现,那就更晚。六十年来,我们的国势不比唐宋,诗的成就怎能直追前贤?
有人会说,尽管如此,为什么小说的成绩要比诗好?我想这有几个原因。第一,小说的传统比诗浅,对后继者的压力和束缚也比诗小:相比之下,新诗对旧诗更是“突变”。第二,旧小说用白话文已成传统,新小说发轫之初,在语言上只是“渐变”。新诗用白话文,在语言上和旧诗不能衔接,在格律上要挣脱旧诗,又要引进外国形式,一时难以调整。第三,在古代,写诗是读书人必具的修养,进可以应科举,退可以怡性情、酬知己;但在那时,写小说和写戏曲一样,都是儒者闭门自娱的小道,不登大雅之堂,而小说作者也多是失意的文人。但是到了现代,小说取得了正宗的文学地位,稿费又高,市场又大,不但成为报刊争取的对象,更有征文重奖加以鼓励,即使电影电视,也不能完全取代它的地位。
中国的新诗发展至今,出现了不少问题,致使论者与作者辩论不休,争而不决。这中间,有的是纯文学的问题,有的还涉及政治意识,更形复杂。以下且就三个最迫切的问题,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是大众化的问题。论者往往指责新诗,说它孤芳自赏,不够大众化,长此以往,中华恐成无诗之国。其实六十年来的新诗固然不够大众化,但是黄遵宪、苏曼殊以来的旧诗又何曾大众化呢。有五百年来第一人之誉的陈散原,似乎也没有多少读者。真正称得上大众化的,还是唐诗宋词之类。老实不客气地说一句,政治进入民主,教育兼重文理,传播工具商业化之后,儒家的诗教,蔡元培的美育等等已经不能维持——真正大众化的诗,既非李杜,也非徐志摩,更非陈散原,而是流行歌。此所以大陆三十年来的“诗教”,抵不住邓丽君的一匣录音带。
大诗人也不见得就能大众化。以李白而言,“床前明月光”固然人人会背,但是《襄阳歌》、《梁甫吟》之类又有多少解人?杜甫的《春望》、《登岳阳楼》等固然脍炙人口,但是《壮游》、《遣怀》一类较长较深的作品,也不见得怎么大众化。苏轼的名句,像“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像“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都已变做成语,流行自不待说,但是像“不减钟张君自足,下方罗赵我亦优”之类的作品,又有几人能懂?同样地,诗经的句子很多已成后世的成语,楚辞则绝少此种现象。
一般人口中的大众化,往往只指空间的普及,而不包括时间的持久。其实真正的大众化应该兼顾两者,不但普及,还要持久。畅销书往往一时普及,但十年百年之后,便已湮没无闻,那样的大众化是靠不住的。例如王渔洋在清初,诗名满天下,曾在大名湖赋《秋柳》诗,和者数百人,但三百年后,谁也不记得那首诗了。反之,李贺生前虽少知音,但迄今千余年,他的作品仍持久不衰,甚至知音日众。又如梵高,生前只有三五知己,画都卖不出去,身后却家喻户晓,名重艺坛。诗之大众化,有时隔世始显:杜甫号称诗圣,但今传唐人所选唐诗九种,只有一种载录杜诗。直要等到北宋中叶,杜诗才“大众化”起来。
大陆的文艺最爱讲大众化,但是江青揠苗助长的那些“小靳庄”诗歌,现在恐怕已随她的样板戏销声匿迹了吧。我认为让所谓无产阶级也来写诗作文,本无害处,但要自发自然,像“帝力于我何有哉!”那样的民歌才算天真可爱,否则即使是农民写的,却一味忆苦思甜,颂德歌功,岂不成了新式的“应制诗”?所以那些诗,只能当做政教合一的工具,写字造句的练习,不能美其名曰文艺。那样的东西只能当做“政治运动的消耗品”,用完便丢,绝不耐久。那样的大众化,只有大众,没有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