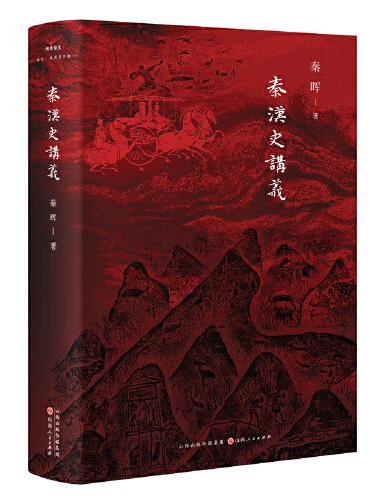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新民说·逝去的盛景:宋朝商业文明的兴盛与落幕(上下册)
》
售價:HK$
173.8

《
我从何来:自我的心理学探问
》
售價:HK$
119.9

《
失败:1891—1900 清王朝的变革、战争与排外
》
售價:HK$
85.8

《
送你一匹马(“我不求深刻,只求简单。”看三毛如何拒绝内耗,为自己而活)
》
售價:HK$
6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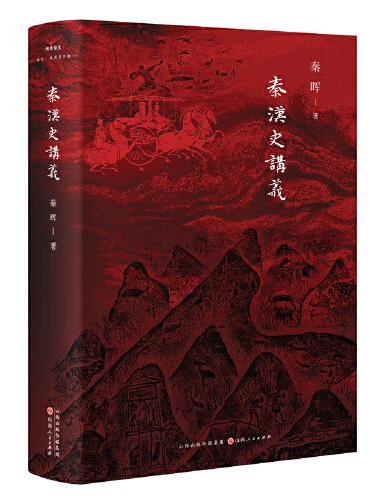
《
秦汉史讲义
》
售價:HK$
151.8

《
万千心理·我的精神分析之道:复杂的俄狄浦斯及其他议题
》
售價:HK$
104.5

《
荷马:伊利亚特(英文)-西方人文经典影印21
》
售價:HK$
107.8

《
我的心理医生是只猫
》
售價:HK$
49.5
|
| 編輯推薦: |
|
理性细致的分析。作者的研究角度与国内许多专家不同,使人精神为之一振。语言细腻生动,然而仍然需要极大的耐心去看,属于散文式的叙述。 基于作者个人的观点感受而写成,但仍然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与其说是书中具体的观点影响我们,但不如说是提供给我们一种新的看待古典文学的途径,而这种难得的创新正是我们中国学术界所缺乏的。
|
| 內容簡介: |
|
宇文所安最富盛名、最“成功”的代表作,是其尝试把英语“散文”essay和中国式的感兴进行混合而造成的结果。初版于1986年。作者从汗牛充栋的古典文献中拣选了十数篇诗文,出其不意地将它们勾连在一起,通过精彩的阅读、想象、分析与考证,为我们突显了一个中国古典文学的经典意象和根本性的母题:追忆。
|
| 關於作者: |
宇文所安:为唐诗而生的美国人
宇文所安,美国著名汉学家。1946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他从小就对诗歌感兴趣,在巴尔的摩市立图书馆,宇文所安第一次接触到中文诗,并迅速与其相恋,至今犹然。
宇文所安认为,文学传统就好像神话里的宝盒:你把其中宝藏给予越多的人,你就会同时拥有更多别人的宝藏。但是,假如你想把这个宝盒锁起来,说“是我一个人的!”那么,它就只是一个空盒。
|
| 目錄:
|
三联版前言
作者的话
导论:诱惑及其来源
1 黍稷和石碑:回忆者与被回忆者
2 骨骸
3 繁盛与衰落:必然性的机械运转
4 断片
5 回忆的引诱
6 复现:闲情记趣
7 绣户:回忆与艺术
8 为了被回忆
译后记
|
| 內容試閱:
|
1 黍稷和石碑:回忆者与被回忆者
有这样一种关系,一种能动的关系,在其中,未臻完善是这种关系继续存在的必要条件。完善只是在理论上存在,如果能够实现,“摹仿”就不再是摹仿,而成了它所要摹仿的东西。同样,如果把要抹去的东西彻底抹掉,那么,我们也就不可能知道曾经有过抹掉这样的行为。既然我们知道有过抹拭的事发生,那么,我们也就知道,一定有某种东西曾经存在过;我们一定可以看到未能抹尽的痕迹:在自然界或是书页上的、被弄污弄糊的、残缺不全的痕迹。丧失的东西、不复存在的东西和被丢弃的东西,它们就像是拖把,在历史的书页上用力擦拭。因为我们渴望要“存在”——在有形的物体内,在著作里,在作品中——我们绝不可能无动于衷地把经过抹拭的地方简单地看作一片空白。
大自然不断地把我们从地球上抹去。人们以及他们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流逝沉入地下,又被掩上黄土。大自然的万古常新同人类个体陨灭枯烂之间的对比,已是老生常谈,这是一个只能引起人人都有的情感的陈旧话题。然而,凡是老生常谈,其间总隐藏着某种人们共同关心的东西;我们所以轻蔑地把这种反应称为“老生常谈”,是因为我们憎恨人人都会对个人的毁灭作出同样的反应,抱有同样的情感。老生常谈也是一种抹拭,是普遍对个别的抹拭,我们对它报之以一种出于恐惧的蔑视,这种恐惧是一种预感,预感到还存在有另一种陨灭:人的身份名望的陨灭。
对老生常谈,特别是我们现在讲到的这个老生常谈,应当作进一步的挖掘,它涉及到某种失去的、过去曾是独特的东西,某种被无名的大自然埋没的东西。它不只是代表它自己,它代表的是所有的老生常谈——有个性的东西变得越来越不清楚,最后消失在无数反复出现的、无名无姓的东西之中。
从土台上或许还看得出宫殿废墟的大体模样,在布满龟纹的石块上或许还勉强能辨认出上面的碑文。时间湮没了许多东西,磨蚀掉细节,改变了事物的面貌。除了那些知道该如何去找寻它们的人之外,对其他人来说,“以前的东西”变得看不见了。正是那种按照某种一定方式来看待世界的意向,承担着我们同过去的联系的全部分量。
这里有一幅赫伯特·W.格里森Herbert W.Gleason,1855-1937年拍的照片,题目是“五月花,朴利茅斯;l903年”——拍的是盛开在岩石间的花朵。英国清教徒l620年首次去美洲时所乘的“五月花号船”就是以这些花朵命名的,这些花名又凭借这艘船名而闻名于世,这样一来,人的带有作者特点的作品要消失在延续不变的大自然中的说法,倒要受到挑战了。不过,真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幅照片的日期。今天的五月花同1903年的五月花根本没有什么不同,假如我能在朴利茅斯找到他拍照的具体地点,在一年的同样季节和一天的同样时间里,我也能拍出一张即使不是一模一样,至少也很难把它同格里森的那张区别开来的照片。假如这幅照片当时只署题为“五月花”,假如它只是一本旧植物学课本中的一幅插图,那么,我会无动于衷。然而,由于署上了“1903年”,这幅照片就有了它特殊的美和特殊的价值;我在它里面就能找到旧时的照片常常给人带来的那种独特色调和使人感伤的雅趣。而那幅没有标明时间的照片,则难以产生情趣,它只会让我明白,即使我想要回忆,对它我也几乎谈不上有什么可以回忆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