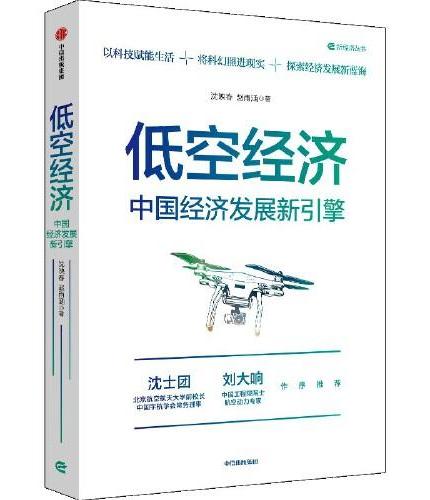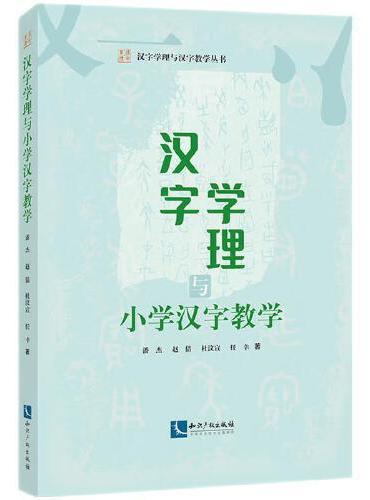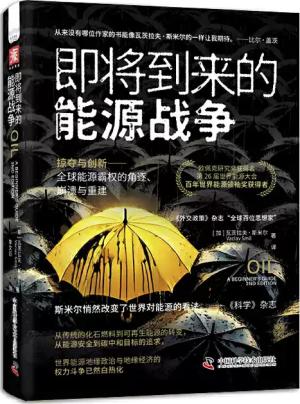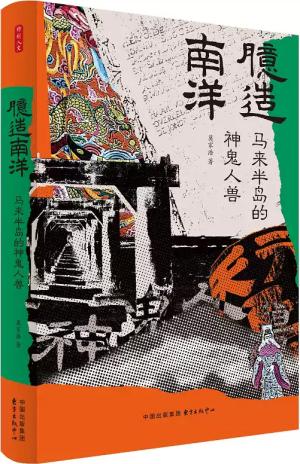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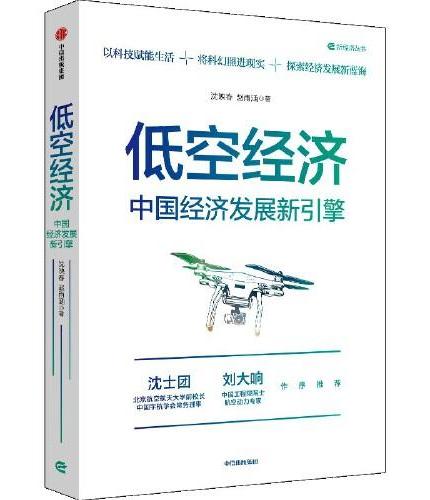
《
低空经济:中国经济发展新引擎
》
售價:HK$
8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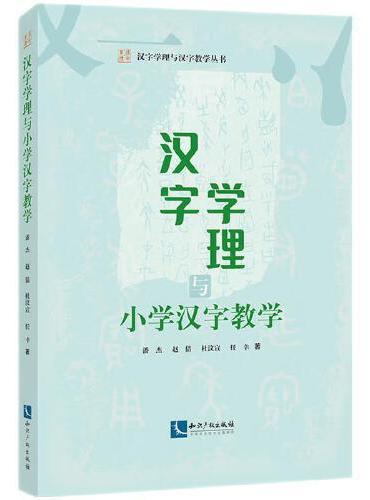
《
汉字学理与小学汉字教学
》
售價:HK$
8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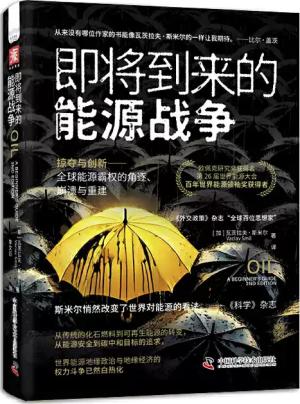
《
即将到来的能源战争
》
售價:HK$
8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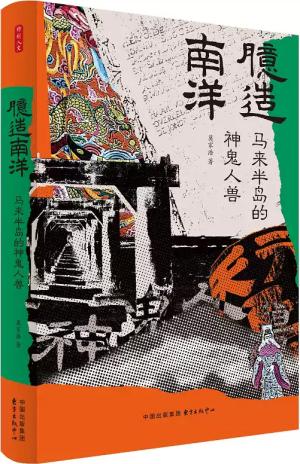
《
时刻人文·臆造南洋:马来半岛的神鬼人兽
》
售價:HK$
65.0

《
心智、现代性与疯癫:文化对人类经验的影响
》
售價:HK$
188.2

《
周秦之变的社会政治起源:从天子诸侯制国家到君主官僚制国家(历史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论丛)
》
售價:HK$
188.2

《
时刻人文·信用的承诺与风险:一个被遗忘的犹太金融传说与欧洲商业社会的形成
》
售價:HK$
103.0

《
同与不同:50个中国孤独症孩子的故事
》
售價:HK$
66.1
|
| 編輯推薦: |
变走一架钢琴、弄没一头大象、让一架波音747消失,都是雕虫小技。
达伦布朗可以把中产阶级白领变成银行劫匪、可以改变中式信徒的信仰、可以预测乐透奖号码。
全球最神秘、最危险的意识控制大师——达伦布朗,教给你过目不忘的本领,透露给你意识控制和心灵魔术的核心秘密。
|
| 內容簡介: |
本书共六章。从心灵魔术最基本的唤醒、纸牌游戏,到催眠暗示、意识控制。详细阐述了关于心灵魔术的学习办法和科学分析。
达伦布朗的语言诙谐、俏皮。在轻松的语言环境下交给读者一些简单却极具心理欺骗性的魔术,同时他阐明自己所有的魔术都是有科学依据的,与那些神秘主义替代性疗法有着本质的不同。
|
| 關於作者: |
|
达伦布朗Derren Brown, 1971年2月27日在克罗伊登(英国东南部)出生,他毕业于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 ),原专业是法律和德语,后来因为对幻觉艺术深感兴趣而进入了魔术行业,如今是英国的心理学研究者和魔术师。他是全球最神秘、最危险的意识控制大师。
|
| 目錄:
|
平装版序言 1
序言 3
第一部 觉醒
觉醒 3
真相和谎言 12
第二部 魔术
硬币魔术 19
纸牌魔术 24
感知就是一切 28
带有心理暗示的魔术 36
第三部 记忆
出发点 53
锁链记忆法 58
位置记忆法 69
挂钩记忆法 79
记忆人名 100
复习的重要性 104
第四部 催眠和暗示
简史 112
什么是催眠? 117
貌似独特的催眠现象 125
如何进行催眠 135
神经语言程序学 152
个人改变的工具 163
第五部 潜意识沟通
学会读人 193
辨认谎言及其他泄密信号 195
第六部 反科学、伪科学和错误思维
思维陷阱 217
科学和文化相对主义 225
对超自然现象和伪科学的信仰 233
替代疗法 251
灵媒、通灵师和江湖术士 268
最后的思考 303
粉丝来信 307
致谢 317
深度阅读推荐资料及本书援引文献 319
其他援引文献 338
索引 340
|
| 內容試閱:
|
献给妈妈、爸爸和弟弟。
平装版序言
多谢惠顾这本书的官方平装版。也许,你像我一样更偏爱口袋大小、携带方便、适合带在身上走来走去的书,而不是庞大笨重的精装版,对精装版情有独钟的,是些附庸风雅、拥有华丽书房、财产多而性生活少的人。选择了这个平装版,你就会毫不费力地契合自己一直努力塑造的穷困潦倒却风流倜傥的落拓才子形象,所以我感觉你极有可能购买这个更年轻、更性感的版本。而且我可以向你保证,精装版里的每一个字平装版里面都有。所有的句子都按照原来的顺序放在那里,书后的索引也完全依字母顺序排得清清楚楚。
不过,这个版本也悄悄做了一点修改:对热情来信并指出精装本错误的读者,我一直心怀感激,很高兴他们指出了所谓错误。这些信件绝大多数来自没受过太多教育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读不懂本书第六部讲到的反直觉概率问题,对于蒙提霍尔问题①的正确答案,他们表示费解。有的来信更加有趣:一个小伙子提醒我说,购买彩票的人们选择数字序列“1,2,3,4,5,6”的概率其实高得不合比例,它甚至可能是最常被选的一个数列。我在本书中明确说过,这一数字序列在彩票中获奖的概率与其他任何随机组合的六个数字一样高,并提出谁也不会选择这个等差数列,因为它看起来一点机会也没有。现在我发现我的猜测大错特错。很有可能,有一群像我一样常为概率知识而自鸣得意的人,在所有博彩游戏中都选择同样的数字,然后告诉别人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验证概率论。
自精装版问世以来,市面涌现出许多无神论方面的图书:毫无疑问理查德道金斯营造的那个广阔平台提升了大众的觉悟水平,这也是他的目的所在。毫不奇怪,一种叫做“无神论原教旨主义”的逆流也随之初露端倪。显然,任何一种原教旨主义都会变成丑陋的东西。鉴于本书讲的是我个人的无神论,我觉得可以趁机重申一下:对某事产生疑问,不会自动升华为信仰或哲学,带来麻烦的,是常常缀在其后的“主义”。无论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在辩论失利时都有可能变得同样傲慢无知、气急败坏,都有可能使用尖刻而不留情面的语句来试图提高自己的气势。这种说法虽不客气,但却中肯,那就是:不相信上帝,与不相信尼斯湖怪兽、不相信海神波塞冬或任何与自己生活相距甚远的东西的想法一样,没什么大不了的,并不因此就会变成“不相信主义”。除此以外,所有辩论都只是我们选择表达方式的问题。
我觉得我说得够多了:希望大家享受这本轻松愉快的小书,如果你发现了什么错误,一定要写成邮件、打印出来、叠好,然后塞进自己屁眼儿里。
序言
去年某个春日,我忽然想去水族馆探访一下女王陛下的鱼。水族馆位于略微令人失望的“伦敦眼”下面,距离我们的节目制作公司不远。那时,我刚在家里装了一个鱼缸,正准备买些鱼虾蟹蚌来充实它。当然,除非我想攻击潜水艇或者变成詹姆斯梅森 ,那些触须悠长、肢体繁复又阴冷滑溜的生物实在不适合放在家里。探访一个拥有许多巨型章鱼(我注意到,微软的文档处理软件不仅认为章鱼octopus的复数octopodes属于拼写错误,还建议我们改为octopi。我们这些喜欢骚扰别人的人都明白,其实微软建议的拼写才是错误的)的场所,那些动物隔着加固型玻璃阴森森地瞪着我们,它们的视线因折射而发生奇怪的扭曲,想到这些我立刻兴奋到难以言表。后来我发现,水族馆的第12区因无脊椎动物太少而无比枯燥,那天下午最大的亮点就是我隔着鲨鱼池的窗子,看到一位将身体挤扁在玻璃上的痴肥女士。
在数量庞大、形状雷同的海鱼观赏之旅中,我竭力阅读每个鱼缸旁边的小铭牌,它们告诉我和其他饶有兴趣的游客鱼缸里正在潜水、游泳或者翻着白肚皮浮在水面的鱼儿的名字、摄食习性和最爱的音乐类型。在这座半地下的网格状迷宫游览到一半时,我那理性的大脑忽然发觉一个奇怪的现象。我发现不同鱼类动物的描述下面,都有种奇怪的译文,我推测是铭牌内容的布莱叶盲文版。刚看到这个你会觉得很自然,但很快我就禁不住寻思:每年到底有多少盲人造访伦敦水族馆?我不想让自己听起来冷漠无情,但我觉得这个数字应该是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
我很希望得到盲人朋友的反馈,帮我解决从那以后一直滋扰我的几个问题。第一,你如何知道那些布莱叶盲文的铭牌在什么地方?在电梯之类的设备中寻找铭牌应该比较容易,但在陌生的环境呢?如果一个盲人独自去火车站的卫生间,他怎样才能找到那种不太常见的洗手液或马桶按钮上的布莱叶盲文?这听起来真是种不太愉悦甚至不太卫生的探索,尤其是在迪克特大道火车站一带寻找卫生间。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显而易见,如果一位盲人终于找到了水族馆里的盲文铭牌,又有什么意义呢?除了“触摸池”里刺鳐偶尔扫过的胸鳍,对于有严重视觉缺陷的人士来说,伦敦水族馆绝不是一个有趣的地方。我意识到,那些盲文铭牌——如果盲人们能找到的话,最大的作用不过是给盲人游客那个下午的行程提供了一个鱼类的名单。鱼类名单。
离开水族馆时,我先是在出口的麦当劳迷了路,然后又对前方乌贼馆内的表演大失所望,终于离开时,一个年轻人拦住了我。他跟我打了招呼,问了几个和我职业有关的问题。我们聊了会儿,接下来他问我有没有一本现成的书可以告诉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尤其是我用来娱乐大众并有效提高部分观众性欲的各种技巧。截止目前,无数人向我提出过这样的问题。部分提问比较礼貌,显示了良好的教养,但太多时候,提问者粗蛮无礼,那冰冷的眼神让我直想殴打他们的子女。他们问,关于我这个收入不菲、获奖无数、令人心醉神迷、给观众带来无数欢乐的魔术表演工作,是否有一本书可以将秘诀全盘托出?这样他们就可以将上述问题的答案直接捧在手里——极少数读者需要捧在脚上。我试着把与我工作有关的主要兴趣领域都写个概览,像顽皮的孩子一样将它们绑在一起,变成一种貌似图书的卫生而简单的形式,读者们就可以轻松携带,且不影响他们玩轮滑或打网球。
多年来,在许多不可避免的社交活动中,比如我像所有普通人一样离开公寓到街道对过买面包或牛奶时,我遇到过许多人。通过倾听,我知道,他们中的一部分聪明而机智,我很愿意带着他们到我家看看,但其他人似乎就需要一些专业的护理。很多人都对我的职业持有一种明智的怀疑主义和一点娱乐精神;但其他人经常阅读《每日邮报》 ,与至少三只猫一起生活,同时认为《特丽莎》 属于严肃新闻节目。当然,第二群人自然而然地包括那些永远怒气冲天、喜欢给报纸和电视节目写抗议信的人,他们的怒火常常惊得我目瞪口呆。我的震惊,不仅因为怒火本身,更因为这样一种事实:电台或电视台竟然不断鼓励这群人拨打热线电话并对非常复杂的话题发表意见,他们的声音甚至还被当作民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缺乏理性却情绪强烈的声音(这里尤指带有宗教色彩的声音,因某些原因,它们在我们的社会总是得到特别的优待)无非是一些偏见而已,跟你我或其他任何人对自己不理解的领域的看法——比如我对曲棍球、诺尔埃德蒙兹 或箍桶技术的看法——一样,都是没 有说服力的。
因此,鉴于我节目的观众数量庞大且层次多样,我决定将这本书定位为一个外行对与头脑有关的事物的兴趣,理想受众是智慧型的读者。书中涉及的课题,有些我兴趣十足,有些我觉得略显枯燥:我只是将出现在我这颗硕大且长满胡须的头脑中并与那些课题有关的想法,坦白地写出来。这本书涵盖的内容非常多样,有些话题略带学术色彩。有人曾建议我就大脑相关事物写一本“轻松”又引人入胜的入门读物,我拒绝了——那样的书当然会比较易读,写起来也快得多,但无疑将导致大众对这个领域的误解。我更愿意写一本客观全面又带点怀疑精神的书,而怀疑精神在我看来至关重要。
我真的希望,看了这本书以后,你们能在本书提到的一两个领域内深入研究。如果没有这样的读后效果,它至少可以作为价廉物美的澡盆玩具,送给你最不喜欢的那个孩子。如果它能给你带来一些实用信息,或者作为你进一步探索的有用跳板,我会非常开心。我最不愿意见到的,就是你读完却感觉只看到了一份鱼类名单。
觉醒
《圣经》不是历史。
接受并习惯这个事实,对我来说非常艰难,因为我曾经对上帝、耶稣、撒旦之类的深信不疑。笃信这些东西并与持相同信仰的人每周聚会一次的好处就是,你从来没有机会仔细审视它们并对自己的信仰进行反思。而我一直认为,反思自己的信仰,会让它们更加坚不可摧。
如果将我现在的公众形象和我少年期间的模样做个对照,许多人会难以适应。现在的我通常以“英俊而神秘”(《疯魔文学增刊》)、“绝不是一个自鸣得意的傻瓜”(《曼彻斯特论坛晚报》)的风格印在分辨率极高的海报上,并被许多人贴在装修优雅的客厅或旅行车的车体。而我十八九岁时却是截然不同的一个人:精力充沛却又严肃得不可思议,认为世界上最荣耀的事情莫过于说服那些耐心至极的朋友皈依神圣庄严的宗教世界。如果你想狠狠呕吐一次的话,请想象这样的场景:一个自封的牧师,鼓励我们在五旬节展现用多种语言讲话的才能 ,而且只要一开始讲话就不能停止,因为一旦我们因自觉愚蠢而闭嘴的话,就证明魔鬼控制了我们。再吐一次,请想象,我对一个非基督徒朋友说我会为他祈祷,浑然不觉这种姿态有多么的居高临下。如果别人对我这样说的话,我也会非常高兴,并为自己的直言不讳和严格教养而深感自豪。这种不愉快的局势,就是压抑的童年再加上几年封闭式宗教教育的结果。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兴起的所谓“新纪元运动” 的潮流,在我那狂热而虔诚的牧师朋友及其同类看来,简直令人厌恶。他们警告说,撒旦亲自出马,激发了大众对水晶球和通灵疗愈的兴趣,这些巫术的出现也造成了克罗伊登那些另类书店的繁荣。我深感赞同,认为塔罗牌之类的事物都危险至极。如果你觉得这种想法幼稚可笑,请考虑一下现代教堂的作法——它们大都不会把魔鬼当作真实可见的实体,而是认为它们隐匿在学生宿舍、重金属音乐唱片商店等罪恶场所。那个朋友的部分工作内容——别忘了他是个“牧师”——就是告诉承蒙他们庇护的天真无辜的普通人,让他们相信魔鬼之类的东西全然属实,信徒们会因恐惧而对宗教产生更多的依赖,尽管这种信仰里小小的甜蜜已被哗众取宠的热望所压倒。
但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件小事,却成了我个人生活中的一场大马士革 般的体验。那时候我住在布里斯托大学的学生宿舍“威尔斯楼”,其建筑格局是几座典雅楼房围成一个方形的天井,让人恍然觉得仿佛到了牛津大学的四方院(与各处的天井一样,草坪禁止行人穿越踩踏。青草,只要长成四方形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座宿舍楼的投资人威尔斯先生是二十年代的烟草业巨头,为了弥补爱子没有考上牛津大学、只能在布里斯托大学屈就的遗憾,特意捐赠了这座建筑并造出一座四方院,好让儿子拥有与牛津大学相似的环境。(深受父母溺爱之苦的同学们请注意了,你们其实非常幸运,至少令尊没有专门为你在大学里盖一座楼)。这么说吧,我走出当时那个我称为“汽车风景号”的宿舍,去食堂里吃一顿略晚的早餐。路过走廊时,我发现一张海报(如果英国遗产中心已考虑在这里挂一个纪念铭牌的话,具体的位置是A座宿舍楼)。海报黄色的背景上印着一只巨大的黑眼睛,宣告当晚将举办一场催眠术的讲座和表演,地点是学生会的埃文乔治大厅。我之前从未参加过类似的活动,而且它听起来比我每晚的常规日程要有趣得多:一般来说,我的夜晚通常是一边喝水果茶一边努力研究kafkan和不太常用的kafkaesque这两个单词之间的区别,然后回到宿舍享受一场温柔的手淫。
通灵师马丁泰勒那天做完正式的催眠表演后,还在一个学生的家里举办了讨论会,催眠了几名易受暗示的学生。我记得很清楚,作为回报,这些学生可以享受免费的康沃尔郡菜肉烤饼,以及一晚的免费住宿。那位催眠师绝不是拉斯普廷 那种人;相反,他是个开朗活泼的金发小伙儿,且对催眠术的原理毫不隐瞒。那天深夜和朋友尼克吉拉姆-史密斯返回宿舍以后,我说将来我要当催眠师。
“我也要当。”他说。
“不,我是认真的。”我强调说。
我收集了所有能够找到的与催眠有关的书,开始自学。每天都有同学主动来做小白鼠,供我催眠。后来其他大专院校的学生也来了,这种人我发现更容易被催眠。中学时代让我自惭形秽的棒球队员,成了我新晋技能的理想实验对象,而控制这些人的感觉也让我心醉神迷。我开始在大学附近做小规模的催眠表演,有时还会在酒吧里对朋友实施催眠术,让他们在只喝水没喝酒的情况下酩酊大醉。
那时,我好几年没有定期去教堂了,但内心仍然信奉宗教。笃信基督教的朋友说我对人实施催眠是展示魔鬼的力量,我惊讶万分。在一次表演中,我看到基督教联合会的一名会员站在观众席的后面,用多种语言大声讲话,我猜测,他是在驱赶舞台上正在作恶的魔鬼。还有一次,圣诞节前的一个星期天,我刚走进学生教堂,就听到后排传来疑问:“他来这里干什么?”真不错。
我陷入了迷惑。如果上帝创造了我们,那么人类大脑也许是造物的最佳作品(只比亚马逊网站和菲利普塞默霍夫曼略逊一筹)。我深深知道,关于催眠术的运作机制,我比这些人了解得更多。但是,我不能因为某几个人令我不悦的行为,而对他们信奉的宗教产生偏见,于是我耸耸肩,将这些事情置之脑后。事实上,那时我根本不知道催眠术会把我的人生带到哪里。我曾受雇在一个男性聚会上表演催眠,但我明白在女同性恋脱衣舞后为成年男性上台演出,并不是我的职业方向。之后一天下午,我在城中的二手书店里无所事事地闲逛,忽然邂逅了马克威尔逊的《魔术完全教程》,一本引人注目、令我惊喜的大部头。光亮挺括的封面上,高帽白手套的魔术师向我承诺,一定要把江湖老千所需的全部技巧都教给我。关于魔术背后的秘密,我一直充满兴趣。但以前从未有人将它们白纸黑字写下、装订成册并送到我的眼前,哈哈,我立即开始自学魔术,静心研究那些秘而不宣的诀窍和花招,想看看能否只靠翻书自学变成成功的魔术师。
我对魔术的迷恋慢慢加深,从饶有兴趣到如痴如醉到变成离婚的理由,潜滋暗长的,还有对超自然世界中那些诡计和骗术的无法避免的痴迷。揭露魔法骗术的历史,几乎与魔法骗术的历史一样悠久,将来也会一直与哗众取宠、愈演愈烈却大行其道的通灵师和神秘主义者如影随形,而绝望的民众也会让打假人士愈加痛苦和厌烦,因为他们懒于自救、一心贪求捷径,甚至拒绝面对他们的“拯救者”谎话连篇而且一直操纵盘剥他们的事实。这种现象加上我长期以来对心理暗示和催眠技术的热爱,立刻激起了我对以下问题的兴趣:为什么我们会相信超自然的东西?我们是怎样被“新纪元”花样百出的伎俩说服的呢?那个时候,“新纪元运动”在白人中产阶级中大行其道,追随者似乎为自己极为主流的白种人和中产阶级身份颇感羞愧。显而易见,担心被“魔鬼附身”只是因恐惧而产生的无稽之谈。我觉得,超自然的世界,其实是因压抑无望却又希望对生活产生确定感而导致的由自我欺骗、安慰剂效应、自我暗示以及江湖骗术和精巧盘剥组成的混合体。魔鬼是否存在的问题根本不用讨论。
由于对幻觉艺术的热爱,我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错觉世界。而且,正是我对传统魔术的兴趣和求知欲,让我有能力探索神秘主义到底如何运作。有些人一看到魔力和灵异世界的东西就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支持,却根本没有准备在信任之前考察一下是否可信;另一些人(比如我,从小就喜欢把玩具拆开研究内部结构)则想要看清这些东西到底由什么构成。
我的熟人中颇有一些笃信超自然现象的人,他们最令我震惊的是那种明显的循环信念系统。其特征是,如果一个人对事物甲深信不疑,所有与这种信念冲突的证据都被他们选择性忽略,而所有支持这种信念的证据都被他们接受且放大。比如,一个灵愈师朋友曾告诉我,她在前几天的聚会上治好了某个朋友的烫伤。那天一个热水壶在他面前忽然爆炸,烫伤了他的胳膊。她对这件事的表述很有意思:她将自己的双手放在他的胳膊上,坚持了一会儿,他的疼痛和水泡就迅速消失了。鉴于我和那位疗愈师有几个共同的朋友,我就联系了另一个也在聚会现场的朋友,问他这件事是否属实。他听了以后哈哈大笑。千真万确,那位疗愈师确实曾把双手放在伤者的胳膊上,但却忽略了之前大家用冰雪绑在他胳膊上冷敷一个多小时的事实。我的疗愈师朋友并不是有意对我进行误导,她只是过滤掉了冷敷这件事,她觉得那无关紧要。而且,这件事还让她对自己的神力更加深信不疑,成为她助长自己信念的养料。
这种事见得越多我就越担忧,因为我发现,作为一个基督教徒,我的信仰和神秘主义落入了相同的陷阱。难道我不也是沉溺于相同的循环信念吗?那些实现了的祈祷我牢牢铭记,而没有得到上帝呼应的就故意忘掉,甚至认为上帝将会以其他不太明显的方式来回应。那么我的信仰与灵愈师朋友的怪异信念又有什么不同呢?除了她的信念比较非主流因而更易遭人嘲笑以外。对于自我安慰式的胡扯,我们是否都暗自感觉不安?显而易见,我取笑神秘主义却又身为基督徒,真是伪善而无法自圆其说。
我又询问了多个教育程度较高的基督徒,因为我愿意听到更加完备的回答。一个人可能真心地信仰任何事物:超自然能力、基督教,或者正如伯特兰罗素的经典说法(当然是充满嘲讽的),相信有个茶壶正围绕地球运行 。我完全可以用百分之百的虔诚来相信以上所有东西。但我的虔诚并不能证明它们因此就是真的。事实上,如果我说因为我相信一件事所以这件事就是真的,对于真正的理性而言,简直就是一种侮辱。的确,如果我们坚信有一种我们可以信任的宇宙秩序,坚定到可以容忍所有的公众质疑,我们应该能找到除了不切实际的虔诚以外的切实根基。一些我们不相信的证据恰好是正确的。在当今社会,我们都同意人有时会犯错,而且一段时间内坚信的以后可能证明是个错误。我们内心对于某件事物的虔诚程度,与外在世界中该事物的真实性并没有必然联系。比如,我们对一幅画或一首歌的鉴赏,甚至爱上什么样的人,都是非常主观的事。但是涉及整个宇宙以什么样的方式运转、甚至人们是否可以因意见不同而发动一场战争——比如“我们如此坚信一件事所以别人必须与我们一致,不然就得去死”,显然需要更高水平的论证,而不仅仅满足于“我真的真的感觉这是正确的”这种低层次。
为了避免当局者迷,我决定向外在世界寻找证据。事实上,对基督教发出质问非常简单,尽管其他教徒和牧师都不鼓励教徒们这样做。
基督教不仅不鼓励信徒们对自己信仰发出质疑和挑战,甚至,借用理查德道金斯机智的说法,当宗教来到屋子里以后,所有的理性质询都必须“毕恭毕敬蹑手蹑脚地离开”。内部人士的质疑会带来危险,外部质疑又显得非常无礼而武断。这个社会允许我们对政治或伦理问题进行质疑,并期待人们厘清自己的信念,或至少对任何重要话题都寻找足够重要的资源和证据来进行论证,但一旦涉及神是否存在以及他如何影响人类行为这个宏大的话题,所有理性的讨论在听到“我相信”之后就必须闭嘴。宗教有时候会带来非常可怕的结果,比如近年来东西方都发生过的宗教暴力活动。尽管如此,最好不要质疑宗教这个危险的理念却早已在人类伦理中牢牢扎根,并对《圣经》形成之初的几个世纪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当然,许多温和的教徒对于此类暴行总是敬而远之,假装《圣经》里对奇特及暴力行为的清晰号召从不存在,相反只挑选那些“美好的内容”。但是,他们仍然因不敢就信仰问题展开理性思辨而深感愧疚,因为这种做法极有可能让他们看到,那本神圣经典之中其实包含着导致宗教原教旨主义的丑陋东西。
对于我自己和以前的基督教朋友来说,一切的关键在于耶稣基督是否真的死后复生。如果他真像《圣经》说的那样从死亡中复活,那么宗教说的就是真的,无论人们对于基督教徒及其行为的看法是什么。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么一切都是胡说八道,基督教本身也就是一场骗局。
一切都以那个问题为核心,而且举证责任当然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