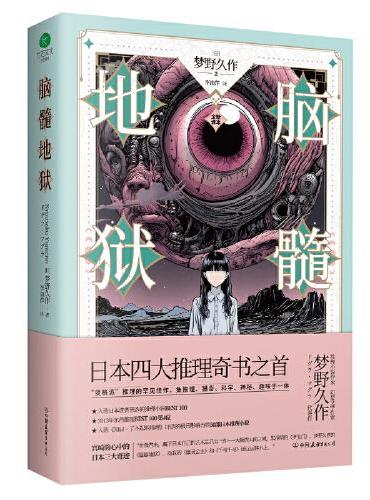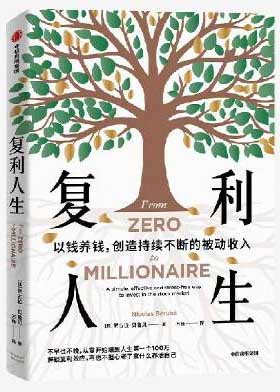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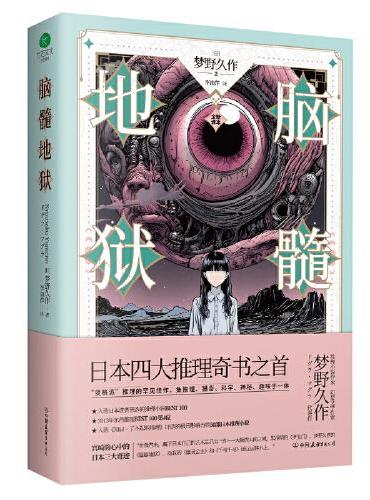
《
脑髓地狱(裸脊锁线版,全新译本)日本推理小说四大奇书之首
》
售價:HK$
6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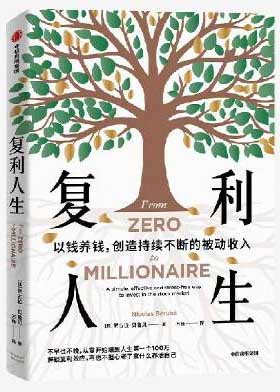
《
复利人生
》
售價:HK$
75.9

《
想通了:清醒的人先享受自由
》
售價:HK$
60.5

《
功能训练处方:肌骨损伤与疼痛的全周期管理
》
售價:HK$
140.8

《
软体机器人技术
》
售價:HK$
97.9

《
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
》
售價:HK$
74.8

《
奴隶船:海上奴隶贸易400年
》
售價:HK$
75.9

《
纸上博物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诞生(破译古老文明的密码,法国伽利玛原版引进,150+资料图片)
》
售價:HK$
85.8
|
| 編輯推薦: |
1 最净化心灵、解放思想的精神之作,让你永远远离忧心如焚的日子
2 教育部新课标重点推荐书目!
3 被美国国会评选为“塑造读者人生的25部经典之一”!
4 畅销百年的传世经典!美国自然文学的典范!当代美国读者最多的散文经典!
|
| 內容簡介: |
|
《瓦尔登湖》是美国环境运动的思想先驱梭罗的代表作。它是一本自然随笔集,真实记录了梭罗隐居瓦尔登湖湖畔两年零两个月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和所感,详细描述了他感知自然、领悟生命、重塑自我的心灵历程。书一问世,好评如潮,畅销至今,被公认为美国文学最优秀的经典作品之一,并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评为塑造读者人生的25部经典之一。曾深深影响托尔斯泰、圣雄甘地、罗曼 罗兰、马丁 路德 金、海明威、亨利 米勒、海子等人。
|
| 關於作者: |
|
梭罗1817-1862,19世纪中期美国文坛巨匠,超经验主义哲学先驱。1845年春,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梭罗因对工业文明、喧嚣社会破坏人类生存环境、侵蚀人类肉体与灵魂满怀忧虑,选择隐居于康科德城的瓦尔登湖边,体验过一种与世隔绝、自耕自食的生活。在隐居期间,他深入探索大自然,积极寻求生命之美和自然之光,并写下著名的《瓦尔登湖》一书。
|
| 目錄:
|
关于经济
补充诗篇
我居于何处,又因何而生
阅 读
声 音
远离喧嚣
访 客
种 豆
村 子
湖
贝克田庄
更高的法则
禽兽为邻
室内取暖
旧居民:冬天的访客
冬天的禽兽
冬天的湖
春 天
结束语
|
| 內容試閱:
|
我居于何处,又因何而生
到达人生的某一阶段,人们就会想找个合适的地方安家,于是,我把方圆一二十英里之内的地方全部考察了一遍。想象中,我陆陆续续买下了那一带的所有田地,我必须买下它们,何况我对其市场价格了如指掌。
我走到每一块田地里,跟主人谈论种植或品尝地里的野果,然后让他随便出个价钱,就以这个价钱,甚至更高的价钱, 把田地买下来,然后再抵押给他——我买下了一切,只是没有立契约——而是把他的谈话当做契约。我天生喜爱交谈,看上去我耕耘的是田地,但从某种程度上说,我耕耘的却是他的心田。我在想象中充分享受了交谈的乐趣后,便离开了,让他继续拥有自己的田地。这段经历,会让我的朋友误以为我是一个地产中介。事实上,我在任何地方的一次逗留,都有可能变成长时间的居住,而我周围的风景也能因此大放异彩。所谓的家,不过是一个坐的地方,这个座位在乡下是最理想的。
我发现,很多能够建造房屋的地方,都很难在短时间里被休整好,有些人认为这些地方离乡镇太远了,而我却认为是乡镇离这些地方太远。于是,我跟说,就住在这里算了,我便真的住下了,可能是一个小时、一个夏天,亦或是整个冬季,看时间悄然流逝,掠过严寒的冬季,迎来暖暖的春天——当这个地方的未来主人想要在这里建屋造房时,会发现早有人在这里居住过了。
我用一下午的时间把田地化为果园、牧场或者林地,然后选定了留在门前的某棵漂亮的橡树或松树,同时为砍掉的树木找到了最好的归宿。然后,我就放任土地不管了,让它休养生息,因为越是富裕的人,越是能放置很多东西不用。
我的想象太漫无边际了,我甚至认为有几位主人会拒绝将田地卖给我—— 这倒正合我意——我从未因为购置田地这样的事情伤过手指头。我在现实中的唯一一次置业经历,差一点成功,当时我决定购买霍乐威尔,而且已经为种植买好了种子,为制造运货的手推车选好了木料,但就在我与田地的主人签订合同的前一刻,他的妻子(每个男人都有一个这样的妻子)突然改变了主意,她要继续持有自己的田地。为此,他们愿意给我10 美元,作为解约的违约金。
说实话,我当时只有10 美分,假设我在拥有这10 美分的同时,又有了一块田地和10 美元,这对我的数学知识可是莫大的考验。最后,我把那块田地和那10 美元都退还给了他们,因为我已经很成功了,确切地说,是我的慷慨让我以买进的价格又卖给了他们,又因为他们也贫穷,我又施舍给他们10 美元,但我的10 美分和种子以及制造手推车的材料,我都留下了。因此,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富裕的人,任何事都无损于我的贫困,甚至,我还额外获得了那里的风景,以后,即便不用手推车,我也能将其收获全部载走。关于风景——
我如帝王般审视一切,
无上的权威无人相抗。
我见过这样一位诗人,他在尽享田园风光中的精华部分之后,悄然离去,而愚钝的农夫们却以为他只是摘走几枚野果。很多年以后,茫然无知的农夫们仍然不知道,自己的田园早已被诗人写进了诗歌,而且用一道看不见的篱笆围了起来,自己并挤出了全部牛乳,拿走了所有奶油,只给农夫留下了脱脂的奶水。
在我看来,霍乐威尔田园最大的魅力在于,它是那么隐蔽,两英里之外才有村落,最近的邻居也在半英里之外,与公路之间隔着一大块田地。它坐落在河流沿岸,据其主人说,正因为这条河形成的雾,才使他的田地在春天免受霜冻,我对此却并不在意。田园里的农舍都显得破旧不堪,再加上七零八落的篱笆墙,就像与现代居民之间隔着多少个年代。那里种着一些苹果树,但上面长满了苔藓, 树身早已空了,很明显,兔子曾一度光顾,据此可以想象,我的邻居是什么样的人。最重要的是,我对这个地方有一段美好的回忆,很多年前,我就曾沿着小河溯流而上,看到几处屋檐掩映在茂密的红色枫叶林中,几声狗叫声传入我的耳朵。
我迫切想要买下它,在原来的主人把那些岩石搬走、把那些空洞的苹果树砍倒、把那些新生的赤杨树苗铲除之前,简单说,我想要趁它还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之前买下它。为了享有上述好处,我决定让它保持原貌。把世界放在我的肩膀上吧,就像阿特拉斯所做的那样——我从未听说他因此得到酬劳——我之所以这样做,没有任何目的或者推托之词,我只想尽快付清钱然后拥有这片园子,以防止他人对它造成伤害。我确信,只要我放任它自生自灭,它就会释放出我所渴求的丰硕果实。事实上的结果,我在上文中已经叙述过了。
迄今为止,我始终种着一块菜地,而我为所谓的大面积耕种事业,仅仅准备好了种子。在大多数人眼里,经过越长时间改良的种子就越好,我相信时间能够区分出好坏,但我现在就要播种,我相信我不会太失望。但我想告诉我的同胞们的是(只此一次,以后永不再提):你们应该尽可能摆脱束缚,自由生活,因为痴迷于一片园林,无异于桎梏于一座监牢。
我的启蒙者,是老卡托的《乡村书》,可惜的是,这本书唯一的译本,却把原著翻译得面目全非,书中曾说:“如果你想买下一片田园,与其如此,不如多在头脑中想想,千万不要贪婪地买下来,也不要因懒惰而不去照看它,千万不要以为绕着田园转一圈就行了。如果这片田园很好,你去的次数越多,收获的喜悦就越多。”我想,我不会因贪婪而买下它,但我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不其烦地去看护它,如果我死后能埋葬在那里,那么我生命的尽头也算享尽了愉悦。
我现在要写的,是诸如此类试验中的一个,我想要详细叙述这次经历,为了书写方便,我暂且把这两年的生活压缩成一年叙述。我早就说过,我不想写那种令人沮丧的诗篇,而只想像一只栖息在树上的公鸡一样,在清晨啼鸣报晓,希望借此唤醒我那熟睡中的邻居。
我首次住在森林里的那一天,就是白天和晚上都在那里度过的那一天,正好是独立日,即7 月4 日,那一年是1845 年。当时,我的小屋还没有完全建好, 还不足以抵挡冬日的严寒,只能暂时遮蔽一下风雨。小屋还没有砌烟囱,墙壁使用的都是破旧的木板,每一块木板之间的缝隙很宽,而且没有粉刷灰泥,一到晚上就无比凉快。小屋使用的柱子,是我刚刚砍伐的笔直的小树做成的,门框和窗户框也是最近才刨平,这让小屋看上去很整洁,通风情况也很好。到了清晨,我能感觉到木料里蕴含的露水,这难免让我幻想着中午会从里面流出甜滋滋的树胶来。在这个小屋里,我沉浸在清晨的情调中,这让我想起很多年前曾去过的、一个坐落在山顶上的房屋。那个小屋没有涂灰泥,空气很好,很适合旅行的男神仙歇脚,而女神如果来到这里则会裙裾飞扬。拂过我屋脊的阵阵清风,犹如掠过那个山顶小屋的风,送来时断时续的曲调,仿佛是来自人间仙境的天籁之音。清晨的风从不停止,造化的诗篇从未中断,只是能够听到的耳朵太少了。世人认为, 奥林匹斯山坐落于大地之外,从无例外。
如果小船不算住所的话,我之前所拥有的唯一一座房屋就是一顶帐篷。每年夏季,我偶尔会带着它去郊游,如今,它已经被卷好放进了我的阁楼。至于我的小船,在倒过几次手之后,我也不知道它如今的下落。现在,我拥有了更好的庇身之所,看来我离定居生活又近了一步。我的小屋虽然简陋,但于我,却像是一个晶体,我置身其中,也沾染上了这种色彩,就像绘画中的一幅素描。我不必跑到屋外呼吸新鲜空气,因为屋里的空气也一样新鲜。坐在门里和坐在门外没什么差别,即便是倾盆大雨的天气也是如此。
《哈里梵萨》中写道:“没有鸟雀居住的房屋,就像没有放调味料的烧肉。”厌我的住所却不是这样,因为鸟雀就是我的近邻,不过,我并没有把某只鸟儿关在鸟笼里,而是把自己关在了它们身边的一只笼子里。对于那些经常飞到花园和果园来的鸟儿,我们自然很熟悉,而对于那些颇具野性、歌声也更为优美的鸟儿, 我则更愿意主动接近它们,它们很少通宵达旦地为谁歌唱,它们是:画眉、猩红丽唐纳雀、野麻雀、北美夜莺以及别的鸣禽。
在康科德镇和林肯乡之间那片蜿蜒的森林中间,有一个小小的湖泊,我的住所就坐落离湖不远的地方。这里距离北边的康科德一英里半,距离著名的康科德战场两英里。与森林的地面相比,我的小屋所在地的地势较低,这就导致我周围的一切都被森林掩盖住了,除了半英里之外的湖的彼岸——那是专属于我的地平线。我搬到这里的第一个星期,无论什么时候向湖面望去,都觉得小湖是高居于山坡上的一汪龙潭,湖底比其他湖泊的湖面还要高。当太阳升起时,小湖换掉了夜晚的雾衣,平如镜面的湖面上泛起粼粼微波,而雾呢?则像一个幽灵从四面八方撤退到了森林深处,又像是某个隐蔽的宗教集会散场之后,教徒们四散而去。树梢上、山崖上都挂满了露珠,直到第二天还不肯消退。
八月来了,当轻柔的风和绵绵的雨停下脚步的时候,这方小小的湖泊就成了我最难能可贵的邻居,水面平静了,空气也平静了,乌云仍然悬在空中,午后过半便有了黄昏的氛围,周围回荡着画眉的歌声,处处可闻。此时是湖面最为平静的时候,湖上透明的空气在乌云的映衬下,显得格外轻淡,湖面上形成的倒影, 宛如地面上的另一个天空。附近的一个山顶刚刚被砍掉树木,站在那里向南望去, 可以看见湖对面的一处优美风景,湖岸所在处,正是这绵延不断的景色的凹陷处, 与倾斜而下的山坡形成鲜明对比,宛如一道溪流从山坡上直流而下,奔入湖中, 但事实上那里却没有溪流。
我身处附近的矮小山峰,极尽所能地向远处更高的山峰望去,蔚蓝色的小山映入眼帘。我踮起脚尖,看见遥远的西北方那些湛蓝色的山脉,那种蓝色是如此纯净,无疑是来自天堂的染料厂。此外,我还看见了小镇的一角。但是,如果我转身再看,尽管站在高处,视线也会被郁郁葱葱的丛林挡住,什么也看不见。附近有几处活水真好,正是水的浮力,让大地得以游走。作为活水之一的水井,即便是再小,也有其特殊的魅力,当你望向井底的时候,会发现大地并不是连续的, 而是由一个个单独的小岛组成,这是水井至关重要的作用,远远超过其冷藏黄油的作用。
如果是洪水频发的季节,站在山顶,当我的目光越过小湖,向萨德伯利牧场望去的时候,可能是出现了海市蜃楼的幻觉,我感觉牧场似乎上升了很多,像落入盆地中的一枚天然硬币,湖底以外的大地,像是被隔绝出来的一层表皮,漂浮在一片横亘的水面上。但此时,我猛然惊醒,记起我居住的地方本是一块干燥的陆地。
在我的屋外,能够看到的风景范围有限,但我却不觉得它狭小,也不觉得压抑,因为这足够我的想象力驰骋了。对面是一处高原,上面长满了矮橡树,向西无止境地延伸出去,一直通向许多年前鞑靼活跃的荒原,这是所有游牧民族广阔的活动天地。当牛羊需要更大的新牧场时,达摩达拉说:“除享受广阔的视界外, 再没有什么能让人如此快乐了。”
时间和地点都发生了改变,而我生活的地方却是宇宙中永远不变的角落,更接近于我所向往的时代。我的住处是如此遥远,就像天文学家每晚借助于望远镜看到的星空。我们总是沉湎于幻想,希望在宇宙的一角,有一块充满快乐的乐土, 它有一万里那么远,甚至比仙后座还要远,纤尘不染,远离喧嚣和繁杂。我发现, 我的住处正是这样的一个处所,它永远那么清新,是宇宙中没有被污染的一部分。如果说居住在昴宿星团、毕星团、天鹰座或牵牛座附近更有价值的话,那我真的愿意到那些地方去,不过,至少我居住的地方像那些星宿一样遥远,我所散发出的柔和的光线,洒向我最近的邻居,在没有月亮的夜晚他们才能够看到。这就是我的住所,造物主创造的一部分——
世上曾有一位牧羊人,
他的思想如高山般伟大,
时时给予他营养的羊群,
散布在高山之上。
如果羊群不断攀爬,直到爬上比他的思想更高的高山,那么牧羊人会过什么样的生活呢?
每一个清晨都是对我愉悦的召唤,让我像它那样简单地生活,或者说让我像大自然那样纯洁地生活。如同忠诚的希腊人那般,我心怀敬意地膜拜黎明女神。我每天早早起床,用湖水沐浴,就像宗教行为那样严格遵守,这是我做的最有价值的行为。据说,成汤王的浴盆上刻的铭文意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我深知其中之意。清晨重现了英雄时代,天色尚早,我打开门和窗户,安静地坐在屋中,这时,一只小飞虫来拜访我,所到之处,留下似有若无的嘤嘤嗡嗡声, 我不免为之动容,就像听到了献给英雄的号角声。它边在空中飞舞,边唱着挽歌, 那是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歌声中充满着愤怒和流浪,颇有宇宙本身的感觉,宣告着宇宙的生生不息和无限活力,这是一种永恒的告示。
清晨,是醒来的时刻,是一天当中最让人怀念的时刻,我们混沌的感官会清醒过来,至少在一个小时之内,不会再度陷入昏昏欲睡。但是,如果唤醒我们的不是本能,而是仆人的胳膊生硬的推搡,这样的日子有什么意思呢?如果唤醒我们的不是内心新生的力量,而是那没有神圣的音乐伴奏,没有芬芳的香气跟随, 嘈杂刺耳的工厂汽笛声,那么即便我们醒了,生命也不会变得更加崇高,即使是生活在白天,也毫无希望可言。因为,黑夜也会结出丰硕的果实,其作用与白天一般无二。每天总有一段无比神圣的时间,比人们往常浪费掉的更早、更富光彩, 如果有人对此表示怀疑,那么他的生命已经陷入了绝望,他正在向黑暗沉沦。在休息一晚上之后,人的感官,乃至人的灵魂,会重新获得力量,而其禀赋也会开始尝试他所能达到的生活高度。
我敢说,所有值得纪念的事情,都发生在清晨。《吠陀经》中记载:“一切慧性,皆于清晨苏醒。”诗歌、艺术以及人类历史上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事情,都发生在清晨。所有的诗人和英雄都是黎明之神的宠儿,比如门农,是在太阳升起之际将悦耳的琴声洒向人间。对于那些灵敏活跃、精力充沛的人来说,白天始终充满了清晨的气息,他们是追随太阳的人,不会在意时钟是否奏鸣,人们会持什么态度或者做什么事。对我来说,只要清醒便是清晨。重新塑造精神,就是为了抛弃沉睡的恶习。如果人们没有昏昏沉沉过日子,何以将自己的生活述说得如此可怜?他们并非不精明,倘若不是被昏睡俘虏,他们大可有一番作为。数百万人的清醒只能从事体力劳动,一百万人中,只有一个人的清醒能够从事脑力劳动, 一亿人中,只有一个人的清醒能够诗意而神圣地生活。有什么样的清醒就有什么样的生活。我从未遇到彻底清醒的人,又怎么可能看到他呢?
我们必须重新觉醒,而且要时刻保持清醒,但不是用生拉硬扯的方式,而是要满怀对清晨的向往,如此一来,即便我们陷入沉睡,也不会被清晨的光辉抛弃。与人类付出努力以提高自己生命质量的行为相比,没有比这更让人振奋的事情了。深谙绘画技巧、雕刻技能,固然能创作出几个精美的作品,但更为卓越的才能, 则是描摹或雕刻出某种气息或介质,以便让我们进行精神实践,能够真正地有所作为。世界上最高境界的艺术,就是那些能够影响事物本质的艺术。每个人都试图让自己做的每件事,甚至是每个细节都富有价值,好值得我们花费生命中最宝贵的时间去做。倘若我们抛弃或厌烦了平日里的卑微见识,那么神自会给我们启示,告诉我们如何去做。
我来到丛林中生活,是因为我想看清楚生活的本质,并验证自己是否领悟到了生活给予我的启示,以免到临死前才发现,原来我从未真正生活过。生活是如此美妙,我不想把生命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不到迫不得已时,我也不愿意修行隐居。我要深深扎根于生活之中,吸收生命的精髓,以便像斯巴达人那样坚毅刚强,好彻底刨除生命中非本质的所有东西,大刀阔斧地开辟出一小块土地, 把生命安置在这里,使其只剩下最基本的需求。如果生命注定是卑微的,那么将其卑微之处公之于众;如果生命原本就是崇高的,那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证明, 让它显现在我下次的远游中。我认为,大多数人在尚未认清自己的生活是属于上帝还是魔鬼之前,就草率地认为自己的人生主要目标是“彰显主的荣耀,享受神的赐予”。
可是,我们依然像蚂蚁那样卑贱地生活着。根据神话记载,我们变成人类已经很久了,最初的人类就像俾格米人那样,和庞大的仙鹤打仗,这样的说法真是错上加错,致使我们的美德变得微不足道,本可避免的灾难接踵而至,我们的生命也消耗于鸡零狗碎。对于一个诚实忠厚的人来说,十个手指头就可以计算了, 实在不行再加上十个脚趾头。简单啊,真是简单!要我说,不要让你的事情超过两三件,一百件、一千件,甚至一万件你是计算不过来的,半打足够你计算了, 把账目记在拇指指甲上即可。文明生活宛如波涛汹涌的海洋,一个人要经历怎样的惊涛骇浪、流沙洗礼以及一千零一种考验,才能安全抵达生活的港湾,而不至于沉入海底,这样的人,绝对称得上是一位伟大的计算家。简单啊,真是简单!
何必一日三餐,一餐足矣;何必上百道菜,五道绰绰有余,其他也可按此比例缩减。我们的生活,就像由很多小国构成的德意志联邦,永远变动的边界,即便是德国人也搞不清楚。这个国家有所谓的内政改革,但实际上只是表面文章。这个国家的机构是如此庞大臃肿,以至于因挥霍无度、奢侈浪费毁于一旦。它不懂计算,鼠目寸光,正如世界上的上百万户人家。想要医治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居民,最好的办法是厉行节俭,让人们的生活像斯巴达人那样简朴,让人们的追求提高。人们现在的生活太过放纵了,他们毫不怀疑商业活动、冰块出口、电报的重要性,反而对人们应该生活得像猩猩还是像人拿不定主意。
假如我们不是昼夜不停地工作,不搬来枕木,不锻造铁轨,而只是致力于改善自己简朴的生活,那么还有人去修铁路吗?如果不修铁路,我们又该怎样准时到达天堂?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忙于家务,谁又需要铁路呢?事实上,不是我们利用了铁路,而是铁路利用了我们,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那铁轨下的一根根枕木是什么?那是人,是一个个爱尔兰人或美国人。他们身下拥着黄沙,身上压着铁轨,陷入沉睡,火车就从他们身上驶过。几年之后,他们会被新的枕木替换掉, 而火车却始终在奔驰。如果一些人因乘坐火车而获得了快乐,那么相应的就有一些人因遭受碾压而承受痛苦。当他们因碾压上一根出轨的枕木,而不得不停车的时候,车厢里传来了阵阵责怪之声,似乎这是不该发生的事。于是,他们每隔五英里安插一帮人,以便让枕木维持沉睡状态,规规矩矩地躺着,这说明,这些枕木随时可能苏醒。
我们为什么要急匆匆地生活?为什么要浪费生命?俗话说:及时缝一针,以后能省九针。所以人们现在忙于缝一千针,以便省去之后的九千针。人们终日里碌碌无为,连脑袋都得了跳舞病,无法停下来思考。如果教堂着了火,当我拉响教堂的钟报警时,还没等钟摆回到原处,康科德的人们就会火速赶到现场——不管是男人、女人,还是孩子,而他们早上还在强调多么繁忙——不过他们大多不是来救火的,而是来看别人怎样救火的,看到火差不多快灭了,可能也会伸出援手。
在午餐后休息的人,才刚打了半个小时的盹儿,就警醒地抬头问身边的人: “发生了什么新闻?”他要求别人每隔半小时叫醒他一次,好像别人都是为他站岗的士兵,而他这样做的目的显而易见。为了感谢别人叫醒他,他会把自己做的梦讲给别人听。睡过整整一夜之后,新闻便像早饭一样必不可少了,“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新闻?”——他一边吃早饭,一边看报纸,得知一个人在瓦奇多河上被挖去了双眼,而对于自己也处在黑暗世界却茫然不知,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眼睛也不健全。
对我来说,邮局没有那么重要,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事需要通过邮局传递, 确切地说,就算是不需要花费邮费的信,到现在为止我也只收到过一两封。一便士投递制度的目的,是想让你用一便士换取某人的思想,但实际上你换到的却只是接近于玩笑的东西。我确信,我从未在报纸上获得有价值的新闻。我们读到某人被抢劫、某人被谋杀、某栋房子被烧、某只船沉入海底、某只船爆炸、某只母牛被火车撞死、某只疯狗死了、某年冬天蚂蚱成灾——再不需要别的了,这就足够了。如果我们掌握了它的规律,为什么还要在意那上百万的例证呢?在哲学家眼里,所有新闻都是谣言,而编辑和读者都是喝着茶嚼舌根的老太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