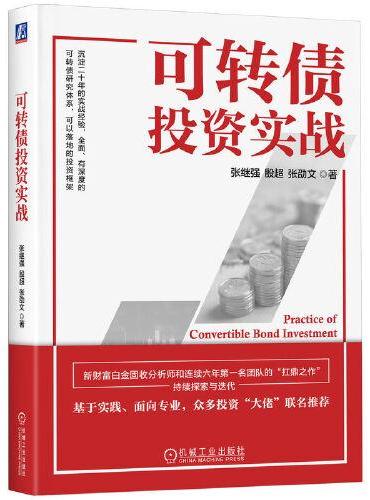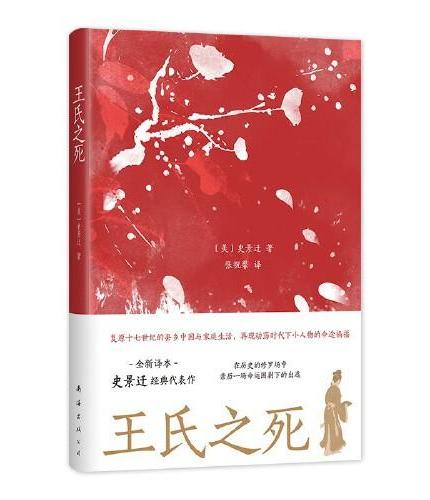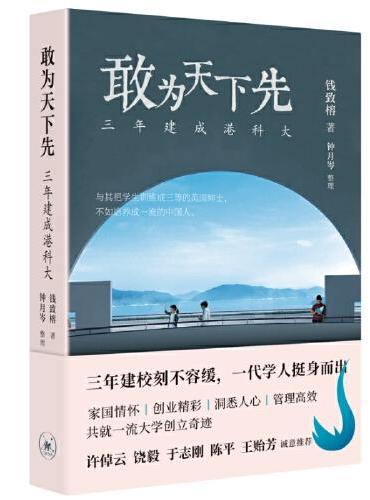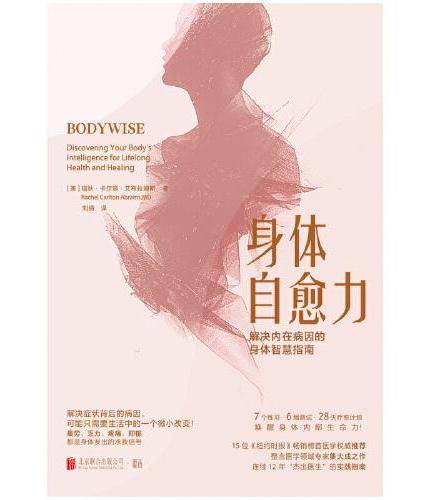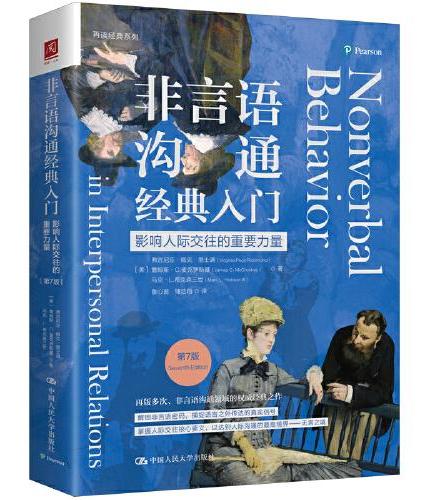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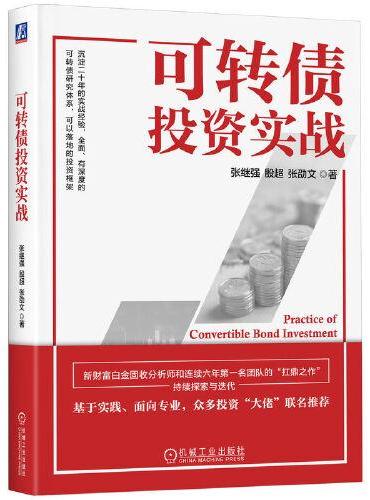
《
可转债投资实战
》
售價:HK$
10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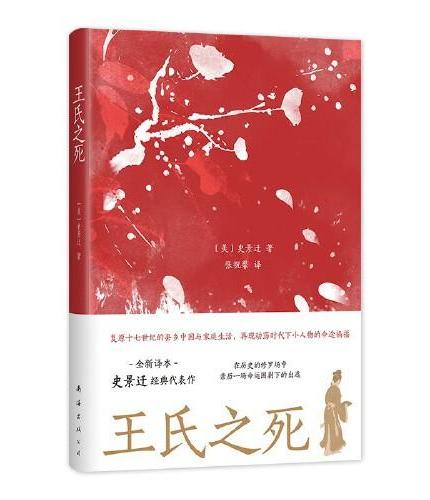
《
王氏之死(新版,史景迁成名作)
》
售價:HK$
5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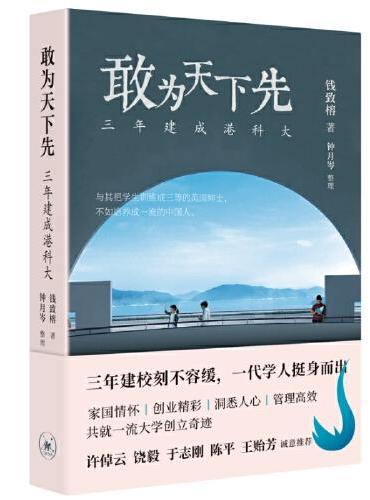
《
敢为天下先:三年建成港科大
》
售價:HK$
79.4

《
长高食谱 让孩子长高个的饮食方案 0-15周岁儿童调理脾胃食谱书籍宝宝辅食书 让孩子爱吃饭 6-9-12岁儿童营养健康食谱书大全 助力孩子身体棒胃口好长得高
》
售價:HK$
4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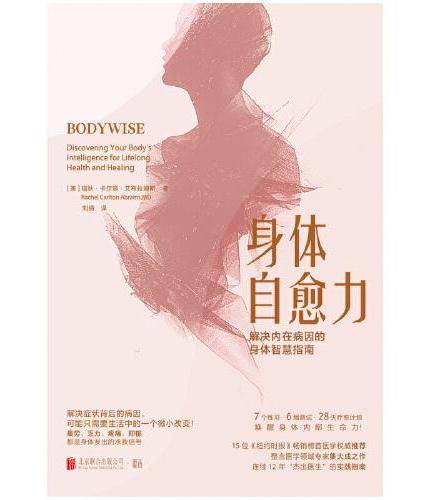
《
身体自愈力:解决内在病因的身体智慧指南
》
售價:HK$
1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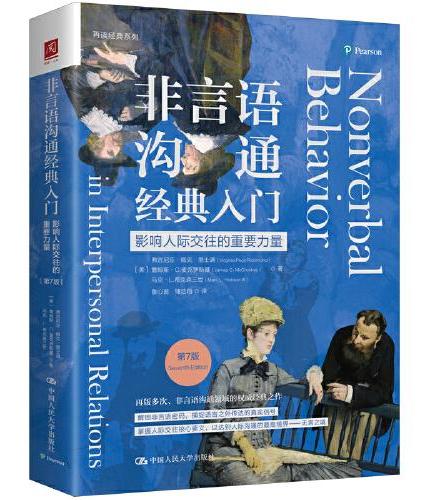
《
非言语沟通经典入门:影响人际交往的重要力量(第7版)
》
售價:HK$
126.4

《
山西寺观艺术壁画精编卷
》
售價:HK$
1725.0

《
中国摄影 中式摄影的独特魅力
》
售價:HK$
1127.0
|
| 編輯推薦: |
|
《魔山》以其波澜壮阔的场景,磅礴的气势,细腻的心理分析,精辟的哲理,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风云变幻的社会现实,不愧是一部划时代的交响乐性质的杰作。它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在现代德国小说中是无与伦比的。
|
| 內容簡介: |
|
《魔山》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 曼的代表作。小说以一个疗养院为中心,描写了欧洲许多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人物,其中有普鲁士军官、俄国贵妇人、荷兰殖民者、天主教徒……他们都是社会的寄生虫。整个疗养院弥漫着病态的、垂死的气氛,象征着资本主义文明的没落。作品通过人物之间的思想冲突,揭示出颓废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血缘关系。
|
| 關於作者: |
|
托马斯·曼1875—1955,20世纪德语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出生于德国吕贝克城。1901年凭借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而轰动欧洲文坛,成为德语文学继歌德、席勒以来又一高峰时期的领军人物。出版于1924年的《魔山》及其后期代表作《浮士德博士》被认为是托马斯?曼最成功的三部小说。 1929年获颁诺贝尔文学奖。
|
| 目錄:
|
第一章
到达
三十四号房间
第二章
关于洗礼盆和双重性格的祖父
在蒂恩纳佩尔家以及卡斯托普的
品德
第三章
神秘的面纱
早餐
取笑 旅行用品 欢乐受挫
魔鬼
心理的磨炼
多余的话
当然,是一个女人!
阿尔宾先生
魔鬼提出不光彩的建议
第四章
必要的采购
关于时间的附记
他练习法语
政治上可疑
希佩
分析
怀疑和揣测
餐桌上的谈话
疑虑重重:关于两个祖父和黄昏的
舟游
温度表
第五章
一成不变的汤
顿悟
自由
水银之奇想
百科全书
人文学科
探索
死亡之舞
沃普尔吉斯之夜
第六章
改变
新来的那个人
关于上帝之城以及恶魔的释放
愤怒以及更糟糕的事
进攻与击退
精神磨炼
雪
勇敢的战士
第七章
穿过时间的海洋
皮佩尔科尔恩先生
二十一点
皮佩尔科尔恩先生 续
皮佩尔科尔恩 续完
不近人情
悦耳的小调
疑云重重
狂热的激情
晴天霹雳
|
| 內容試閱:
|
第一章
到达
那是盛夏,一位朴实的青年从家乡汉堡出发,到格劳宾登州的达沃斯高地旅行,打算作一个为期三周的访问。从汉堡到达沃斯是一段漫长的旅程,跟这短暂的逗留相比,确实显得太长。这一路不知要经过几个国家,翻过几座山岭,从德国南边的平原,一直往下延伸,到康士坦茨湖的湖岸,还要穿过翻腾的海浪,还有那些我们曾以为深不见底的沼泽地。
这本是一条宽阔而笔直的道路,到这里却中断了,时不时的要停下来,或是绕道前行。到了瑞士境内的罗尔沙赫,倒是又可以乘坐火车,却也只能到兰德夸特,这是阿尔卑斯山旁的一个小火车站,人们只能在这里换乘火车。风吹着,在一段冗长无聊的等待之后,你才能登上一列狭小的火车;而当火车虽小但异常有力的发动机启动之后,这段旅程最让人心惊胆战的部分才刚开始。火车沿着陡峭的山坡一路往上攀去,似乎永远不想停歇。兰德夸特火车站地势不高,但铁轨奋力前行,却一路朝着阿尔卑斯荒原上的石子路绵延而去。
青年的名字是汉斯 卡斯托普,他独自坐在铺着灰色小坐垫的车厢里,还带了一个鳄鱼皮手提包,这是他叔叔和养父蒂恩纳佩尔参议员——这里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他的名字——送的礼物。他还带了他的行李毯,还有挂在钩子上的过冬外套。车窗已经拉下来,这个午后渐渐显出寒意,这位娇生惯养的青年把那件时髦的丝质的夏季外套领子竖起来。在他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本叫《远洋客轮》的杂志;旅程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把这本杂志来回翻阅了数遍,现在却无心再看,它静静躺在那里。火车引擎喘着粗气,轰隆隆地往前行驶,书的封面沾了不少灰尘。
这个年轻人少不更事,两天的旅程把他与之前的世界完全隔离了。所有所谓的责任、志趣、纷扰、前途等,都被他置之脑后。这样的感觉,比他坐着马车,前往火车站的时候更为强烈。在他自己与那片纯粹的土地之间盘旋的空间里,存在着我们通常认为时间的力量。和时间的作用一样,空间每时每刻都能引起他内心的变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空间起到的作用更大。它和时间一样,也会让人忘记某些事情,但我们只有脱离了周围环境的控制,回到无拘无束的原始状态才能忘记那些事情。没错,它甚至会让书呆子或市侩庸人转眼间变成流氓。有人说,时间是一条忘川,但是到别处去换换空气也像是在忘川里饮一瓢水,尽管作用没那么彻底,却让人忘得更快。
汉斯 卡斯托普现在正是这种感觉。对他来说,这次旅行他并没有那么认真,他本身也没有太过看重,甚至,他还想尽快草草略过,虽然这是一次不得不动身的旅途,他只想怎么开始便怎么结束。他打算在他不得不暂住的地方安排一下生活。就在昨天,他还一直回忆着发生的种种,一面想着刚刚过去的考试,另一面又想着马上去“通德尔 维尔姆斯”公司工作的事。这是一家监管造船、机械制造以及冶炼的公司。他似乎对什么事情都很不耐烦似的,所以对于未来的三个星期,他压根没有在意,但现在,他好像必须要对目前所处的环境全神贯注一样,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火车把他带到了一个全新的他从未涉足过的地方,他知道,这里的生活条件不如往常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艰苦的。但他却变得兴奋起来,甚至有些许忐忑。家乡以及以前的生活被他全部抛开,并且落在他脚底下几百米深的地方,不仅如此,他甚至还在往上前行。他在过去以及不可知的未来之间犹疑不定,他自问未来的路应该怎么去走。这对他来说也许不够明智,自打出生之后,他就只生活在海拔几英里的地方,而今突然来到这荒无人烟的高地,而且这一路无论哪个地方一两天都不能停留一下。他忽而希望旅程已经结束,这样他可以像在别处一样开始他的生活,不用再回想这整个旅程坐着火车不停地爬在山路上的荒唐情景。他望向窗外,火车沿着又窄又弯的轨道前进,他看到前面的几节车厢,还有机车费力吐出的灰色和黑色以及绿色的烟,烟雾往旁边弥漫开来。水流在右边的深谷里呼啸,左边的巨岩间却是耸入云霄的暗黑色枞树。火车穿梭在一个又一个黑不见底的隧道里,出了洞口,迎面便是宽广的峡谷;峡谷两面是错落的村庄。接着峡谷又不见了,出现的是狭小的山谷,在山谷的裂口和裂缝处还能看到皑皑白雪。火车有时候在寒碜的小火车站或是一些大的火车站停下来,然后朝着相反的方向驶去,让人一下子分不清东南西北。这些高耸入云的山峰在眼前慢慢展开,变幻莫测,景色壮丽,一幕幕壮丽的景色,令人肃然起敬。山上的小道相继出现,然后又渐渐从眼前消失。汉斯 卡斯托普想,草木繁盛的地带应该已经过去了,可能再也看不到莺啼燕语;这甚至让他感到生命是那么的贫乏,他感到一阵轻微的眩晕和恶心,他不由得用手盖住了眼睛,过了几秒才恢复过来。他感觉到火车不再往上爬,已经过了山谷的顶峰。这个时候,火车正沿着山脚下的平原平稳前行。
此时已近八点钟,但天色尚未暗下来。远处还可以看到一川湖水。湖水是灰色的,湖岸是暗黑色的枞树,枞树往上延伸,一直到周围的高地上。越高的地方植物越是稀疏,最后只剩下光秃秃的隐匿在山雾中的岩石。火车在一个小车站停了下来,汉斯 卡斯托普听到有人喊道:“达沃斯到了。”这段旅程即将结束。忽然,他耳边响起了他表哥约阿希姆 齐姆森的声音,是亲切的汉堡口音。他说:“嘿,你到了!现在可以出来啦!”突然听到旁边传来熟悉的汉堡口音。他往外一看,正是表哥本人,他站在下面的月台上,穿了一件棕色的外套,没戴帽子,看起来比以前更加壮实。他笑了,又说道:“快出来,别磨蹭啦!”
“可是我还没到呢!”汉斯 卡斯托普惊慌地说道,仍旧坐着不动。
“噢,不,你已经到了。正是这个村子。这儿离疗养院很近,我已经叫了一辆车。把你的东西给我吧。”
于是汉斯 卡斯托普在一阵到达与重逢的欢笑声,迷惑不解以及激动中,把他的手提包和外套以及一个装着手杖和雨伞的行李包交给他,最后把那本《远洋轮船》也递了出去。然后他沿着狭窄的通道走出去,跳到月台上,向他的表哥问候。他们在重逢时的问候并没有十分热烈,那些性格沉稳的人往往保有这样的习惯。说来奇怪,这对表兄从不称呼彼此的名字,只为了不使内心真情流露。而且,因为他们也不叫对方的姓,互相之间只用“你”来称呼,这已经成了两人不变的习惯。
当他们急匆匆不无尴尬地握手时,一个身穿号衣头戴一顶编织帽的人站在旁边看着。年轻的齐姆森方方正正地站着,脚跟并在一起。这时候旁边的那个人走过来,跟汉斯 卡斯托普要他的行李票;他是山庄国际疗养院的门房,当这两位绅士直接驱车前去用晚餐的时候,他愿意为这位在车站下车的客人取那只大大的行李箱。那个人走起来一瘸一拐,非常显眼,汉斯 卡斯托普问他表兄的第一句话便是:“他是退伍军人吗?怎么瘸得这么严重?”
“退伍军人!当然不是!”约阿希姆语气有些刻薄,“他膝盖有问题,或者说,以前害过病,膝盖骨被切去了。”
汉斯 卡斯托普在脑中迅速地想了一下:“原来如此。”他说,一边走一边回头朝那人很快地瞥了一眼,“不过你还是无法让我相信,你还是以前那个样子!因为,你看起来像刚参加完军事训练回来一样!”他斜眼看了一眼表兄。
约阿希姆的个头比他高,肩膀比他宽,看起来年轻力壮,似乎生来就适合当一位军人。他皮肤黝黑,在这个金发碧眼的种族里,他这副模样并不常见。他的肤色原本就是黝黑的,晒过之后几乎变成了古铜色。他的眼睛又大又黑,嘴唇也很漂亮,上唇蓄着一抹又细又黑的胡须,要不是长了一对招风耳,他完全称得上是美男子。这一度成为他生活中唯一遗憾的事情。不过现在他又有其他烦心事了。汉斯 卡斯托普继续说:
“你要跟我一起回家乡去吧?我看没理由不回去。”
“跟你回家?”表兄用那双大眼睛直直地盯着他。这双眼睛一向很温柔,但这五个月来,却显出有些倦怠甚至忧伤的神色,“什么时候?”
“怎么了,三周后吧。”
“哦,对,你已经想好要回家了。”约阿希姆回答,“哎,等等,你这才刚到呢。三个星期对我们这里的人来说可不算什么。不过对你这个来这儿探访且打算待三周的人来说,三个星期够多了。你得先适应这里的水土,这并不容易,你以后会知道的。不过,对我们来说,气候不算是唯一奇怪的,你会看到很多想都没想过的事情的,慢慢看吧。至于我,并没有你想得那么顺利,你说‘三个星期后就回家’,这只是乡下人的想法。没错,我是黑,这大部分是因为雪光反射的结果。这没什么,贝伦斯也经常这么说;上次大家定期检查身体时,他说我还得在这里待上半年,毫无疑问。”
“半年?你疯了吗?”汉斯 卡斯托普叫道。在这个破旧的像草棚一样的车站前面,有条石子路,他们爬上石子路空地上停着的一辆黄色篷车。当两匹棕色的马儿起步的时候,汉斯 卡斯托普坐在硬垫子上愤愤地责怪起来:“半年啊!你已经在山上待了半年了!谁有这么多时间。”
“哦,时间——”约阿希姆说着频频点头,对表弟那副义愤填膺的样子不以为然。
“这儿的人根本没把时间当回事。你应该不会相信。对他们来说,三周就好比一天。你早晚会知道这些的。”他说着,又加了一句,“人的想法都会变的。”
汉斯 卡斯托普一路都在认真地看着他。
“不过我看你身体恢复得挺不错的。”他摇头晃脑地说。
“你真的这么想的吗?”约阿希姆回答,“我想我是恢复得差不多了。”他在垫子上坐直了身子,接着又放松下来,“没错,我好多了。”他解释道,“但还没有完全恢复。左肺叶还有罗音,现在听起来有些粗,但也不是很严重;但是下肺叶的罗音就非常粗,第二肋间还有些杂音。”
“你都懂这么多了。”汉斯 卡斯托普说。
“知道的还真不少啊!天晓得,也就是生病之后才慢慢知道的。”约阿希姆回答,“不过我还有痰。”他说着耸了耸肩,既有些漠不关心,又有些激动,这副神情与生病的他有些不搭调。他从外套侧面的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给旁边的表弟看,刚掏出一半又马上塞了回去。
这是一只拱形且扁平的蓝色小玻璃瓶,扣着一只金属制的瓶盖:“这儿的很多人都有一只这样的瓶子。”他说着把它胡乱塞了回去,“我甚至还给它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他们老是拿这个来开玩笑。你在看风景吗?”
汉斯 卡斯托普确实在看风景:“太美了!”他说。
“你是这么想的吗?”约阿希姆问道。
他们已经在那条崎岖不平、沿着山谷方向的山路上驱车赶了好一阵子了,这条路与火车轨道平行。接着马车向左边拐,穿过一条小道和一条水路,然后在马路上奔驰,这条马路一直往上延伸到树木繁茂的山坡上。现在,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有些突起的草原,草原的西南方向矗立着一座长长的建筑物,圆顶,数不清的长廊,远远看去像海绵一般,满是小孔。暮色很快降临了,建筑物的灯逐渐亮起。天色渐暗,方才染红了天空的最后一抹红霞也已慢慢退出天际,周围陷入一片朦胧又安静的氛围中,夜晚就要降临。人口稠密,绵延不绝的山谷已到处是万家灯火,不仅是中间的部分,山谷的山腰上和两旁到处是房屋。特别是右边,那里的房屋都是呈梯田式排布的。左边的几条小径一直往上延伸,一直到斜坡上的草地上,然后消失在松林处的暮霭中。山谷在入口处渐渐变得狭窄,远处的山在它面前显得一阵凄清的灰蓝色。一阵风吹来,使人感到夜晚的凉意。
“不,坦白说,这儿也并没有那么让人敬畏。”汉斯 卡斯托普说。“冰川、雪山还有高山在哪儿呢?在我看来,这些山不算很高。”
“不,它们高着呢!”约阿希姆说,“到处都可以看到参天大树,这些树轮廓清晰。枞树停止了生长,其他的也不生长了,只能看到光秃秃的岩石。在上面那座施瓦茨山的右边,有一座尖尖的高峰,那就是冰川。你能看到蓝色的那一片吗?虽然不算很大,不过毕竟是冰川,名字叫‘斯卡莱塔’。峡谷中间是‘皮茨 米歇尔’和亭珍峰。你在这儿可以看到。那里一年到头都是积雪。”
“永远积着雪。”汉斯 卡斯托普说。
“只要你想,它永远积着雪。是啊,那些地方都很高,不过我们所处的地方本身也非常高,海拔已经到一千六百米了,所以那些山峰看起来才不那么高。”
“没错,爬得可真高啊!我可以告诉你,我担心会死掉。一千六百米。我估测了一下,大概有五千英尺高。我长这么大还没爬过这么高的地方。”汉斯 卡斯托普尝试性地深深呼吸了一下这块陌生地方的空气。空气很新鲜,仅此而已。它没有香气,没有尘土,没有潮气。他轻而易举吸了进去,并不觉得惬意。
“空气很新鲜。”出于礼貌,他评价了一句。
“没错,这里的空气很出名。不过这地方今晚看着不如往日。有时候比这美多了,特别是下雪的时候。不过你看多了也会厌烦。你能想到的,这里的人都已经腻了。”约阿希姆说,他的嘴角扭曲,表情有些让人厌恶,不像之前的耸肩,看起来有些焦躁,和他的风格极为不搭。
“你说话的方式有些奇怪。”汉斯 卡斯托普说。
“是吗?”约阿希姆若有所思,把脸转向他的表弟……
“啊,不是,我不是说你奇怪。我只是刚才那一瞬间有这种感觉。”汉斯 卡斯托普急着表明意思。不过他指的是“我们山上这些人”,这些字眼儿表兄已经用了好几次,他听起来有些不顺耳,有些反感。
“我们疗养院地势比你看到的那个村子还要高。”约阿希姆继续道,“海拔比它高了五十米,在旅行简介里说的是一百米,不过事实上只有五十米。最高的疗养院是茨阿尔卑。你在这儿看不到。冬天的时候,他们要用雪橇把尸体运下山去,因为路都被阻断了。”
“尸体?噢,我明白了,想想那副情景!”汉斯 卡斯托普说。他突然忍不住哈哈大笑,笑得很大声,无法自持,身体都笑得抖了起来,那张被风吹得冻僵的脸也扭曲了,甚至有些疼痛:“噢,用雪橇!你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居然如此麻木!这五个月你确实变得愤世嫉俗了。”
“根本没有。”约阿希姆说着又耸了耸肩,“为什么不可以呢?对尸体来说本来也没什么区别,不是吗?不过兴许我们在这里确实变得愤世嫉俗了。贝伦斯一直就是个愤世嫉俗的人。但不管怎样,他不是普通人,以前曾是学生会会员,又是一名优秀的医师。你会喜欢他的。那位叫克罗科夫斯基的是他的助手,非常聪慧。那本宣传册里还特别提到了他的贡献。他能为病人作精神分析。”
“他能干什么?精神分析!真叫人恶心!”汉斯 卡斯托普大声说道;此时他的神经振奋起来,无法自持。精神分析真的让他笑了出来,笑得如此厉害,甚至眼泪都出来了,沿着脸颊流下来;他用手蒙住脸,双手也被带着抖个不停。约阿希姆也大笑着。这对他来说是好事;两人情绪高涨地从马车上爬出来,这个时候马车已经缓缓登上了陡峭的迂回曲折的车道,把他们带到了山庄国际疗养院的门前。
三十四号房间
他们从右边的门房进去,门房坐落在疗养院大门和玄关之间。一位有着法国味道的服务生向他们走过来,他原本正坐在电话旁看报;身上穿着和车站遇见的那个人一样的灰色号衣。他带他们走过灯火通明的大厅,大厅的左边是会客室。经过会客室的时候汉斯 卡斯托普往里面看了几眼,但是那里空无一人。他问客人都在哪里,他的表兄答道:“他们都在修养治疗,我今晚要不是出去接你,一般都会在晚饭后去阳台待着。”
汉斯 卡斯托普差点又要笑出来:“什么!你晚上居然都在阳台上躺着,躺在这么潮湿的地方吗?”他问道,声音都在发抖。
“对,这是规定。从八点至十点。不过现在先去看看你房间吧,洗洗手。”
他们走进法国人开的一部电梯里,电梯升上去的时候,汉斯 卡斯托普在擦他的眼睛。
“我笑得没力气了。”他说着吸了一口气。
“你跟我讲了这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精神分析那事是记得最清楚的。我想我这旅途的劳累也缓解了不少。脚有些冷,你的冷吗?我的脸又很热,不太舒服。我们要吃饭了吗?我有点饿了,这山上的饭应该还不错吧?”
他们踩着的狭窄的走道是用椰子皮编成的地毯,他们安静地往前走,走廊顶上白色玻璃灯罩里的电灯照下来,墙上反射出乳白色的光。
他们看到一个戴着白帽子的女护士,架着一副眼镜,一根带子系到耳后。她看起来像一个新教徒。可以说,她对自己的工作并没那么用心,有些焦躁不安,懒懒散散的。他们在走廊里走的时候,汉斯 卡斯托普看到她在两间用白漆标了号的门中间放了几个很大的圆圆的短颈球形容器。他有些好奇这些是什么东西,只是当时忘了问。
“你住这儿。”约阿希姆说,“我住你右边那间,你左边那间住一对俄罗斯夫妇,他们有些吵闹,很讨人厌,但是也没办法。嘿,你觉得怎样?”
房间有两道门,一道在外面,一道在里面,中间有挂衣钩。约阿希姆打开屋顶上的灯,闪烁的灯光让房间顿时有了生气。屋里摆着一些实用的白色家具,墙纸也是白色的,可以刷洗。地上铺了干净的油毯,窗上挂着时髦的亚麻刺绣窗帘。门还开着,从屋里可以看到山谷里的灯,甚至还听到远处传来的舞曲。好心的约阿希姆还在橱柜上的一只花瓶里插上了花,其中有风信子和欧式蓍草。这些都是他亲自在山坡上采的。
“你想得真周到。”汉斯 卡斯托普说,“房间真漂亮!我可以在这里好好待上几个星期了。”
“前天这屋子死了一个美国女人。”约阿希姆说,“贝伦斯说过,你来之前她就得直接搬出去,这样你才有房间住。她的未婚夫和她在一起,是一个英国海军军官,但他不太安分,老是跑到走廊里去哭,像个孩子似的。还往脸上涂抹冷霜,胡子本来就刮得很干净,全被眼泪摧残了。前一晚美国女人狂吐了两次血,然后就没声息了。但是他们昨天早上才把她抬走,所以之后他们当然用福尔马林把房间通通消毒了一遍,用这东西来消毒很有用。”
汉斯 卡斯托普并没有认真听,有些心烦意乱。他挽起袖子站到一只大洗手盆前,水龙头在电灯照射下闪着白光,他回头,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冷冰冰的床以及床上干净的床单。
“烟熏消毒,哈?真是厉害。”他讽刺地说,洗完了手,等手风干。“当然,用甲醛的话什么细菌都能杀死,不管它多厉害。不过太臭了。当然啦,良好的卫生是最基本的。”他说话的时候还带着比他表兄更重的汉堡口音,表兄在上学的时候已经戒掉了乡音。汉斯 卡斯托普滔滔不绝地继续道:“不过我想说什么来着,也许那个海军军官用的是安全剃刀,这种刀比那种锋利的刀片更容易刮伤脸。总之,这是我的经验,这两样我都是轮流用。还有,盐水自然会伤到光滑的皮肤,怪不得他要用冷霜。这一点对我来讲倒不足为奇……”他还在喋喋不休,说他箱子里带了两百支马利亚 曼契尼牌香烟,海关的官员非常客气,家乡的很多人让他向表哥问好等。“这里有暖气吗?”他突然问道,伸手去碰暖气片。
“没有,房间一直这么凉。”约阿希姆说,“到了八月份通暖气的时候,跟现在就大不一样啦。”
“八月,八月!”汉斯 卡斯托普说,“可是我觉得冷!冷得不行;我是说我的身体,因为脸滚烫滚烫的。你摸摸看!”
这种让别人摸摸脸的请求,跟这个男人的性格完全不搭调,他自己说出来后也觉得挺不自在。约阿希姆没理他,只说道:
“这边的空气就是这样,根本不算什么;贝伦斯自己也是整天脸红得发紫。有的人还没习惯罢了。走吧,不然我们就没东西吃了。”
在外面他们又看到那个护士,她在后面用她的近视眼好奇地盯着他们。到了一楼,汉斯 卡斯托普突然站住,他听到走廊不远的拐角处传来一阵恐怖的声音。声音不大,却令人毛骨悚然。汉斯 卡斯托普的脸都绿了,瞪大眼睛瞅着他的表哥。很明显,这是咳嗽声,一个男人在咳嗽;但却不同于汉斯 卡斯托普以往听到的咳嗽声,相比之下,以往的那些声音是健康而富有生命力的。而这是一种近似奄奄一息的咳嗽声,它突然发作,像某种有机的黏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