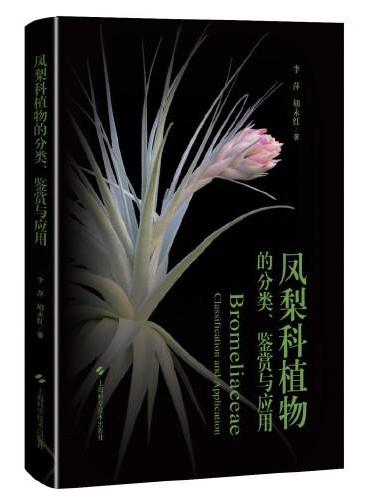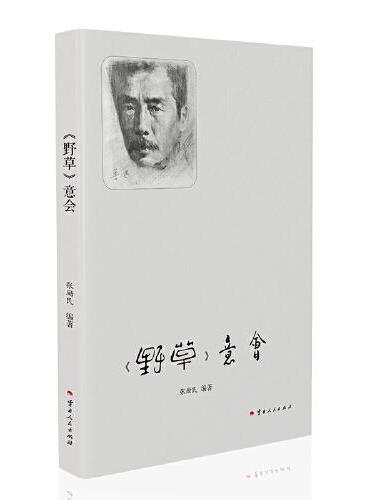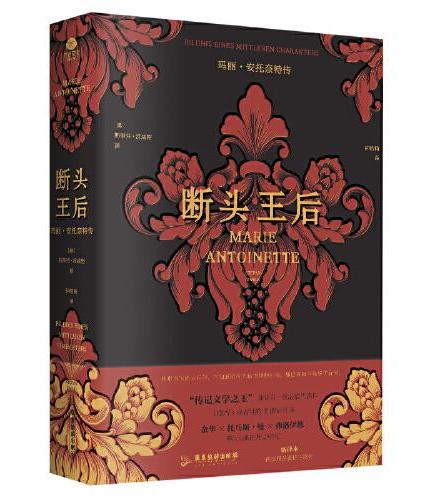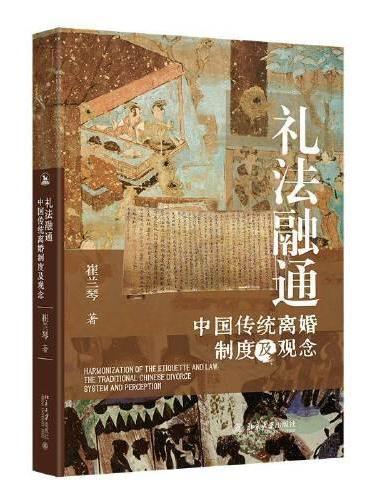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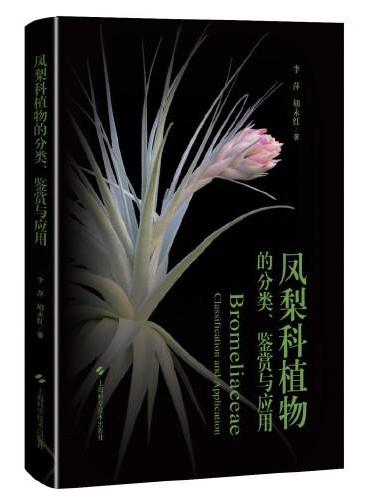
《
凤梨科植物的分类、鉴赏与应用
》
售價:HK$
49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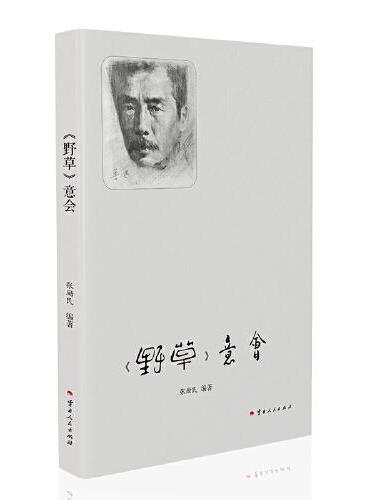
《
《野草》意会
》
售價:HK$
107.8

《
格外的活法
》
售價:HK$
86.9

《
大陆银行(全两册)(上海市档案馆藏近代中国金融变迁档案史料续编(机构卷))
》
售價:HK$
62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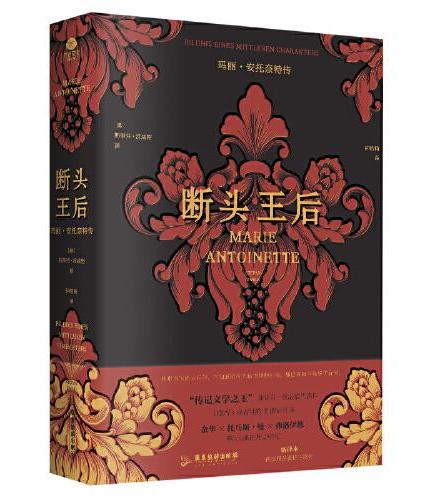
《
断头王后:玛丽·安托奈特传(裸脊锁线版,德语直译新译本,内文附多张传主彩插)
》
售價:HK$
61.6

《
东南亚华人宗祠建筑艺术研究
》
售價:HK$
97.9

《
甲骨文字综理表
》
售價:HK$
21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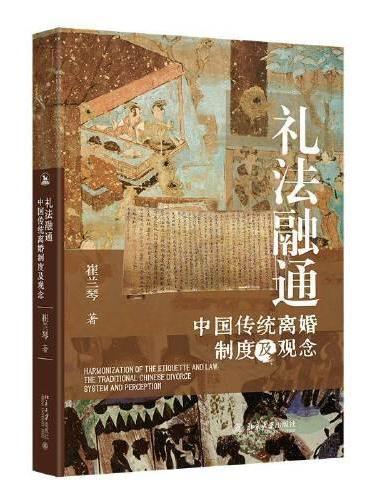
《
礼法融通:中国传统离婚制度及观念
》
售價:HK$
86.9
|
| 編輯推薦: |
1.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经典之作。1985 至1987 年,以马原、刘索拉、徐星、残雪、余华、苏童等人作品为代表的先锋小说,将中文小说的形式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更以其开创性和独特的语言风格,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无法回避的经典,并且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王朔、王小波等人的写作,本书为徐星唯一一部长篇小说。
2.本书先后被翻译成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等多种语言,并多次再版,其中法语版获法国梅迪希斯奖提名,中文版被《南方周末》评为2004年度十大好书。
3.中文版《在路上》。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在路上”式的小说,不仅因为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一次又一次的旅途中,更重要的是小说所表达的精神世界,以及作者本人的生活态度,书中人物充溢着逝去时代的灵光,颓废、伤感,又不失温情,是过去的写照,也预示了我们如今一脉相承的现实处境。
|
| 內容簡介: |
你到了这块大陆灯红酒绿的尽头,在这么一个醉醺醺的黄昏里,你心里充满了寂寥,你不能再前往,你以为总会有无限的什么,会鼓舞着你去刨根问底、鼓舞着你心底里残存的对神秘的一丝渴望。现在你知道一切都是可知的,剩下的就是这些,用不着你费尽心思,剩下的就是这些,这些都属于你……
这是一个路上的小说,我热爱出门上路,直到今天,我已经渐渐衰老,但我仍热爱上路,每次上路以前,我仍会像一个孩子一样,期待着路上的新鲜感和奇遇。
——徐星
《剩下的都属于你》是徐星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中文世界里少见的一部具有批判精神和思想深度的“流浪汉小说”。
小说描写了两个没有工作的青年,先是从北京骑自行车南下,遇到了村支书、落魄导演和“多情的婊子”,后来又走到西藏,走到国外,一路上经历了各种荒诞、可笑、温情、无奈的故事。小说取材于作者的真实经历,反映了当年千奇百怪的现实社会,也预示了如今已然来到的、“什么也没剩下”的生活。
|
| 關於作者: |
|
徐星,1956年生于北京。1977年当兵,开始写作。1981年复员,半年后到全聚德烤鸭店工作。就是在这半年中,他创作了小说《无主题变奏》。1985年,处女作小说《无主题变奏》由《人民文学》杂志刊发,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由传统转入现代的标志性作品之一。1989年,赴德国西柏林艺术大学讲学。1992年,赴德国海德堡大学读博士学位,后放弃。1994年回国。1995年,徐星被法国《观察家》评选为全世界240位杰出小说家之一。2003年在法国出版长篇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后多次再版并被翻译成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等多种语言,同年获法国文化部授予的“文化艺术骑士勋章”。导演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五加五》和《罪行摘要》。
|
| 內容試閱:
|
再版说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我的长篇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这个小说的成书时间比较早,读者可以从故事里交代的地铁票价推算出来早到什么程度,在我的故事里地铁车票尚三毛钱一张,当时北京的地铁只有唯一的一条线路,即现在被延长了的、被称为一号线、从国贸到八宝山的线路。2004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时候,本来想校订一下,因为忙于别的事情无暇顾及,就那样拿给出版社了。
现在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惠及再版,尽管为五脏庙的供奉仍忙碌终日,但我野心勃勃,还是觉得应该重新校订一下以后再版,为此拖了很长时间没有交稿,现在离合同约定的交稿时间越来越近,我一遍又一遍地重看这个小说,发现了很多幼稚,很多表述上的问题,很多意识上的不及意,它就像一个学步的孩子,但事过多年,孩子已经长大成人,美丑是它自己的造化,想想其实也没有必要再给他做一番涂脂抹粉的整形了,不如利用这个再版的机会跟大家谈谈我的文学构成。
我出生于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受过高等教育,祖父来自内蒙古喀喇沁旗,在民国时期的蒙藏学校(现在的民族大学前身)读书,现在的民族大学仍存有他当年带领一些学生参加学运的记录,父亲在一个民国时期的园林专科学校完成了园林学的专业教育,母亲出生于一个辽宁小镇上的基督教牧师家庭,在教会学校完成了产科接生专业的学习。父亲年轻时应该是个典型的文学青年,我刚刚记事的时候,家里有很多文学书籍,他给了我很多文学教育,要求我随着年龄的增长,背诵大量由浅入深的古代诗词,小的时候,我在同龄的孩子们当中很以这个为荣,至今,仍有很多诗词印象深刻,我顺口就可以完整背出来。父母也没有忽视对我的外国文学教育,小时候母亲给我订阅了《小朋友》彩色画刊,尽管中苏关系已经交恶,但画刊里仍有很多前东欧国家的儿童故事,画刊里系着红领巾,穿着金色小皮鞋,在一面巨大的红旗下行少先队礼的金发碧眼的小姑娘,和插图版通俗本少儿读物古希腊罗马神话故事里的人物形象,在我童年的小脑瓜里编织了很多文学幻想。童年的生活虽然算不上多优越,但也衣食无忧,我成年以后回想,理解了当时父母所承受的压力,他们在那么大的压力下,仍让我享受到了他们提供的力所能及的幸福,他们不仅尊重我的文学梦想,父亲甚至还为我请了老师,斥巨资买了八十键的德国手风琴,和同院子里五十多个孩子比较起来,我读到很多的课外书,那时母亲对我做错事的惩罚就是“今天你不能看书”或者“你不做好功课,今天就别看书”。
大概是在我能勉强读懂《水浒传》的年纪吧,“文革”来了,在“文革”的环境里,学校里什么都不学,就学会了“批判”这个那个的,和如何用漫画手法丑化刘少奇,以及一些“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诸如此类的一堆儿歌。父亲再也无暇顾及我了,记忆中他不经常在家,凡是他在家的时间就是伏在桌子上写东西,可惜不是文学,是写给机关里的有关部门的交代和给各种人的信,那些信分别是给很多很多年前打过交道,可能还有他少年时期的玩伴儿的,为了证明某个人在某个时间说了某话,或者证明某件事情的发生经过。他写的时候表情悲痛,目光凝重,有时眼含热泪,我记忆深刻,写完封好,由我做小邮差,投递到大街上的邮筒里,因为寄的次数太多,我很烦,有几次我把不贴邮票的信件扔进邮筒,拿卖邮票的钱买了糖吃。父亲,在您生前我没来得及向您坦承,愿您在天之灵原谅我,值得庆幸的是,在天上,您再也不用写那么多毫无用处让您痛苦不堪的文字了。
一九六七冬天,我十一岁的时候,父母被下放到了不同的地方,我随母亲下放到了甘肃省庆阳县。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加上两天一夜的卡车山路才到达目的地,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民间,民生的贫穷破败凋敝荒凉,文革派性中人们的粗俗野蛮尽入我童年的眼底,在心中引起了巨大的波澜,我产生了一些对这个世界初步的怀疑,也许幼稚,但成人的世界从此不再神秘。
半年以后母亲为了能让我受到稍好的教育,把我送回北京,这时哥哥姐姐也已经去了不同的地方插队,家里的房子已经被一对进驻到母亲原单位的“工宣队”领导夫妻住进,他们对我很友好,女工宣队员已经怀孕,由她们安排,在北京一个我完全不熟悉的环境中一间14平米的小房子里, 我安顿下来了。
我开始了一个人在北京的独立生活,那时我十二岁,相对于后来而言,我的美好童年生活结束了。在全国人民只能读毛和马列著作的严厉的禁令下,当然也无书可读,我曾亲眼看见一个姑娘手里拿着一本《安娜卡列尼娜》在火车上看,被车上的一个戴着红袖章的军人叫到餐车上,她被叫去的一段时间里,她母亲紧张得哭了,过一会儿姑娘沮丧地回来,手里的书没了。在那样的气氛下,火车上众目睽睽读这样的书,用现在的话来说,姑娘确实有点装,但是姑娘长得很漂亮,军人借反对资产阶级腐朽没落之名,把姑娘单独叫走,也许更装。
我的学生证比别的孩子多出了一页纸,蜡版油印的,学校盖着章,证明我的父母在外地,每年可以凭着这一页小纸片两次买火车票去探亲。那时所有的人出门都需要介绍信,到北京来要凭“县团级”以上的证明才可以买到火车票,我的学生证在同龄的孩子们中间居然意味着一种小小的特权,一年两次的出门上路,让我在同龄的孩子们当中显得见多识广,也显得比同龄的孩子们成熟。从此我迷上了出门上路, 在路上遇到了大量穷于奔命的知识青年,他们经历了家庭的变故,政治风云的诡诈,理想主义的破灭,颓废虚无,酗酒打架偷偷地乱交,在完全封闭的社会环境里鼓吹着“人家外国”,议论着一堆外国文化名人的名字,向往着“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些颓废虚无深刻地影响了我,我觉得他们的行为举止有一种潇洒,引起了我的好奇,也引起了一种我内心深处向往的神秘,我追随他们、模仿他们,从他们那儿我得到了一些以前没有的知识,和悄悄流传的以前从未读到过的文学名著,甚至很多极为内部的书籍,比如德热拉斯的《新阶级》等,现在我家里仍藏有一本当年印刷的、印数极为有限的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现在它已经变成了时髦的话题,我早在四十多年前已经读完,也许因为没有完全理解,当年它并未像“震撼”了现在的许多人一样的震撼我。
路上的生活让我着迷,我在极大程度上得到了在学校里得不到的好奇心满足,我开始逃离学校,借口看望父母,去一个人的“旅行”,出门儿后当然马上就会变成实质上的流浪。我跑了很多地方,学会了逃票,当时知识青年的术语叫扒车,当然也学会了讨饭,有时一人有时跟一些比我的大的知识青年们一起混迹人间。
另外非常值得说说一个没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几乎无法想象的细节,当时整个的社会生活都弥漫在斗争当中,在广播里,在遍布全国各地的大喇叭里,孙敬修爷爷般的、我们美好的汉语,从来没有被那么穷凶极恶声嘶力竭令人产生恐怖感地表达过,我可以想见假如突然公开地出现了一个温柔的声音,发出这个声音的他或她很可能第二天就会因为“资产阶级思想”倒霉。不知道为什么,列车上的播音员好像置身这个世界之外,她总是以一种温柔的女性化的声音报站,今天我给自己解析,也许出于少年人朦蒙眬胧的性意识,这类的声音也迷住了我,也让我经常产生出上路的冲动。
为了就近入学,我的学校也转到那里, 刚开始的时候母亲向所在单位的军代表请假回来了一次,安顿了我的生活。她去了学校见了老师,求我当时居处附近的一家小饭馆提供帮助,她每月寄粮票和钱给那家小饭馆,我每天三次去那家小饭馆吃饭, 也许是因为少年人长身体的缘故,似乎从来就没有吃饱过,饭馆里的一个老阿姨开始时还帮我规划,后来发现我喜欢跟表现不好的年轻服务员(都是知识青年)一起混,她不再管我了。我很快就会把母亲寄来的伙食费花光,而且磨着饭馆的阿姨给我变成现金很快胡乱花光,然后就是挨饿的日子,那些饥饿的记忆至今仍旧锐利。然后,在十五到十六岁之间,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单相思初恋,这场无结果的恋爱破坏了我的全部生活,它的影响直至如今仍未消去,在我记录个人生活的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里,有全部的记述。就这样,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五年这七年当中,我以一种畸形的方式度过了少年生活,完成了青春期,
后来经历了插队,当兵,一九八一年我从部队复原,被复转军人安置办公室分配到了北京全聚德烤鸭店工作。在这之前已经被分配过一次,报到时得到的暗示,好像是要去北京郊区的劳改农场做狱警,我想来想去这份工作实在不适于我,于是谢绝了,以后的半年时间内复转军人安置办没有再理我,大概是有点对不服从分配的惩罚的意味,那时我已经二十五岁,经过近两年农村插队和近四年的当兵生活,多少算是已经有了些人生的历练。
等着被重新分配的这半年时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多难以想象的巨变,每天早晨七点钟开始的、相当于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各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广播,通过半导体收音机和偶见的文革残留下来的高音喇叭做着权威新闻发布,那时民间尚罕有电视,那时中国唯一的电视台叫做北京电视台,即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全中国只有一个阶层—高层,才可以享用。所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几乎就是唯一获取有声新闻的途径,现在的人们几乎难以想象,每天早上七点钟以后的“全国各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以后,在这个黄金时段,会由一个铿锵有力的男播音员,向全中国播送一个小说—刘心武先生的《班主任》。
在这之前,我从未注意过官方的文学刊物,对我来说,那不是文学。为了配合当时的政治需要,我所见的文学,手法上仍在沿用文革,作家们都在积极投入一场诉苦大会式的哭诉,文学表达上仍然没有可能摆脱所谓“反面人物”或“正面人物”,换句话说,你不能写一个看不出是“好人”、“坏人”或者“主题不积极向上”的小说。如同《班主任》里给过去是黄色小说的《牛虻》重新定位一样,当时整个社会的传播手段极为贫乏,人们通常会从文学作品里嗅出政局的变化,我可以不过分地说:在那种情况下,文学从来没有在中国社会里产生过那么强大的作用,这些都可以从再版的“文革”前的小说集《重放的鲜花》以及白桦的《苦恋》,刘宾雁的《人妖之间》等文学作品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力得到佐证。
以我通过上述经历完成的文学观和文学表达来看,我不太喜欢这类的文学,对我来说民间更接近于文学本质的、西单民主墙上的文学作品倒是被禁止被打击的。
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八一年,我写了我的处女作《无主题变奏》,在当时已经公开发表了作品的张辛欣的帮助下在一些艺术院校的朋友手里、主要是在中央戏剧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传看,我记得当时辛欣第一次看了以后非常紧张,对我说:“你写这样的东西,当心点儿,可别出事儿!”当时正在“严打”,有些人为了举行家庭舞会就付出了坐牢的代价,在街上跟女孩儿搭讪就有可能会因流氓罪而被判刑劳教,朋友们的担心当然不无道理。
随着逐步渐进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九八五年,我觉得可以在官方的刊物上试试发表我的小说,于是投给了《人民文学》,在编辑朱伟和主编王蒙的支持鼓励下,我修改了这个小说,在七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得以发表。
发表以后得到的最严厉的指责是“颠倒主流价值观”和“反英雄”“长江黄河流淌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英雄的血……”等等,不过当年的大形势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起初我稍有些担忧,但后来并没有人身安全之忧。
就这样,我从一个全聚德烤鸭店的清洁工,变成了一个作家。
一九八六年我跟一个朋友骑车做横贯北南中国的旅行,回来后,就开始筹备写这部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我的本意是要写一部路上小说,八九年初写完,在四月号的春风文艺社的《中外文学》上发表出来,很快就被当时影响力、发行力巨大的中国作协《小说选刊》选载,据说在当年的某个时候,很多学生手里都有这个小说,直至清场。
让我略有得意的是,当年这部小说令人吃惊在于,它的内容对后来中国社会的变化,以及后来中国发生的很多事情,都做出了准确的预测,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的确是一部先锋文学作品,可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当时它没有发出它应该有的文学意义上的影响力。
后来我去国多年,无从发表文学作品,在国外因为工作生活紧张,我也只是当做消遣偶尔继续写一点儿,当做这部小说的第二部第三部,到九一年,我算写完了这部小说,因为没有出版的压力,写得很随意,权当生活记录来写了,写完在全部文本尚
没有中文版的情况下,很快就出版了法语版和意大利语版。始料不及的是,它在欧洲读者中反响强烈,在法国和意大利出版了第二版之后,在德国出版的最初几个月里,就被德国最大的出版社Fisher第二次买了版权,出版了第二版。
现在广西师大出版社决定出版这个中文版,我重读时,毕竟时过境迁,有些汗颜,有些难堪,本来想校订一下,但是下笔时觉得困难重重,我是把年轻时的感知换成现在的呢,还是再次夸大年轻时的感知?想来想去改写自己的小说是个不太好的事情,所以最后还是决定一字不动,交给读者。拉拉杂杂写下这个说明,算作给读者一个交代吧。
这是一个路上的小说,我热爱出门上路,直到今天,我已经渐渐衰老,但我仍热爱上路,上路以前,我仍会像一个孩子一样,期待着路上的新鲜感和奇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