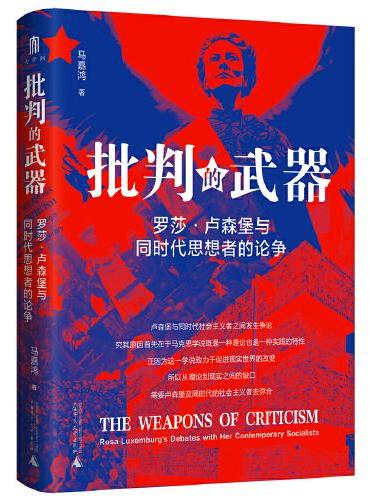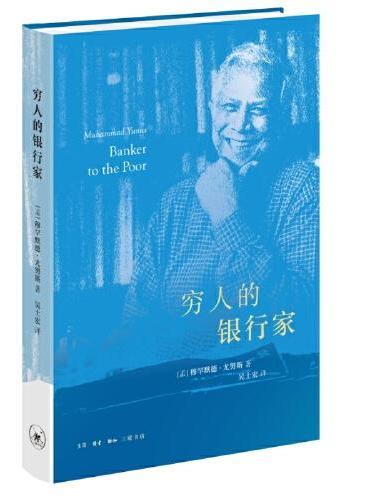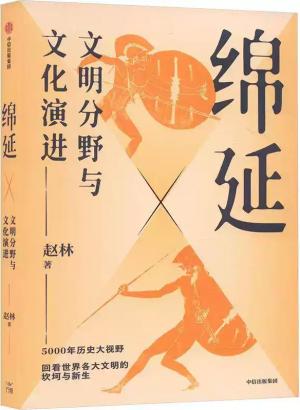新書推薦:

《
迟缓的巨人:“大而不能倒”的反思与人性化转向
》
售價:HK$
77.3

《
我们去往何方:身体、身份和个人价值
》
售價:HK$
6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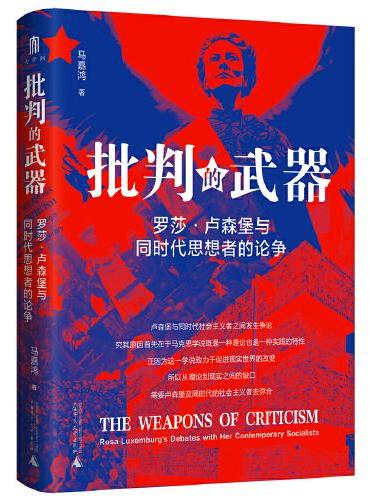
《
大学问·批判的武器:罗莎·卢森堡与同时代思想者的论争
》
售價:HK$
98.6

《
低薪困境:剖析日本经济低迷的根本原因
》
售價:HK$
6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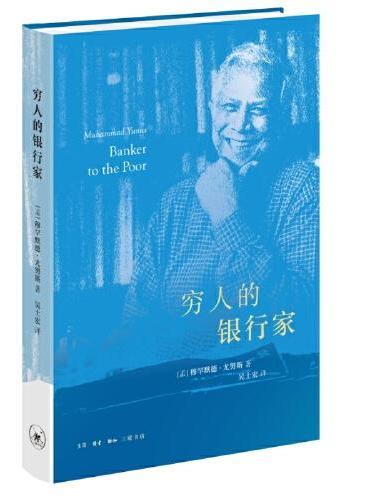
《
穷人的银行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自传)
》
售價:HK$
7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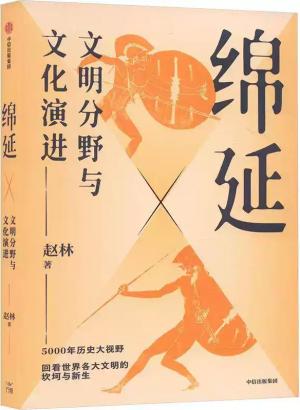
《
绵延:文明分野与文化演进
》
售價:HK$
66.1

《
三神之战:罗马,波斯与阿拉伯帝国的崛起
》
售價:HK$
80.6

《
法国通史(全六卷)
》
售價:HK$
985.6
|
| 編輯推薦: |
美国最重要的战地记者、普利策得主代表作
《时代周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年度好书
美国国家图书奖年度最佳非虚构作品
最直接、残酷的战争场面,最动人、温情的感人细节
即使在最绝望的城市,我们也要跑步
呼吸,生活,积极乐观地面对所发生的一切
|
| 內容簡介: |
|
本书是根据作者自己1998年起在阿富汗及伊拉克的采访观察写成,作者舍去了政治局势分析与褒贬功过,而是专注于还原战争中的一个个“人”,从士兵到平民,从高层军官到普通老百姓,他们在战争中的切身感受、所思所想,他们的生存处境。全书充满了众多真切而生动的感人细节。
|
| 關於作者: |
|
戴斯特·费尔金斯 被美国新闻界誉为“这个世代最重要的战地记者”,自1998年起持续报导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事,曾担任《洛杉矶时报》新德里分社的社长;2007—2008年担任哈佛大学卡尔人权政策中心研究员,2010年加入《纽约时报》,持续在阿富汗及伊拉克等地进行采访报导,2012年加入《纽约客》。2009年凭借阿富汗及巴基斯坦的美军战地报导获普利策奖2010年 因揭发阿富汗战争内幕,获得乔治·波尔克奖两度获得美国国家杂志奖(20092011)及美国海外新闻协会奖
|
| 目錄:
|
引子 地狱钟声
第一部分
阿富汗 喀布尔 1998年9月
1 “只有这个”
2 不祥之兆
3 “詹格”
第二部分
伊拉克 巴格达 2003年3月
4 希望与忧愁之地
5 “我爱你”
6 一去不复返
7 半空中的手
8 一种疾病
9 内部人士
10 自杀
11 皮尔兰
12 消失的世界
13 “说说而已”
14 马赫迪
15 普洛透斯
16 适得其反的革命
17 迷宫
18 “毁了我们”
19 老板
20 转变
21 逝者
尾声 莱卡
致谢
|
| 內容試閱:
|
一切都是从一张脸开始。一张黑色的脸,被薄薄的灰尘覆盖着,嘴唇微微张开,没有血色。他可能是北非的阿拉伯人,脑袋四周都是碎瓦片。这是海军陆战队在费卢杰南部一座清真寺尖塔内发现的,他的头被摆在螺旋楼梯的最上面一格。士兵拍了张照,夜色给这张脸染上了一层黑蓝色。尖塔是游击队的主要据点,他们在里面射击、盯梢、传递信息。海军陆战队刚到时,要经过允许才能在清真寺里拍照,不过几个小时后就没人理睬这规定了。
我们知道很多游击队员死了,但我们没见过。费卢杰的战役进行了一星期,勇士连中已有四分之一的士兵受伤或阵亡:罗姆洛、尼克、内森、朗尼;布莱德利·帕克,19岁,家在西弗吉尼亚;杰克的脸被炸伤,不过幸存下来。当然,这只是一小部分伤亡者。我们依然在向前推进:我们在街上飞跑,被子弹打中,穿越火线。他们朝我们射击——海军陆战队、阿什利还有我。现在我们到了费卢杰的边缘,街道通向一片巨大的平原,那里长着星星点点的矮灌木,堆满了垃圾……像是电影中的场景。忽然之间,费卢杰到此为止了。叛乱分子去了哪里?他们死了,被埋在瓦片下。他们被埋葬,然后分解,尘归尘,土归土。“被2000磅的炸弹炸了以后还剩什么?”一个美国军官曾这样问我,他并不想炫耀什么,因为这是他的士兵所受的遭遇。“阿富汗,误伤,五人阵亡。我们把骨灰装在一个三明治袋子里。”他说。
但是,我们依然对为何尸体的数量这么少感到好奇。长官在无线电里报告,几百死者,几千死者,但我们没看见那么多尸体。你以为我们会看见一条手臂,一个脑袋,好像在巴格达汽车爆炸现场那样。我想过一些原因:穆斯林很快就把尸体埋葬了,这是出于宗教原因;叛乱分子绝不会把死者丢下,是第二种原因。为何总是看不见他们?他们有秘密出城的通道吗?怎么可能?
那张脸。当时我们站在费卢杰边缘一栋房子的屋顶上,看着从城市南部延伸出去的那一望无际的平原。一等兵亚历克斯·萨克斯比(Alex Saxby)走过来给阿什利看照片,他举起一个小小的傻瓜相机给我们看,他知道我们需要叛乱分子死伤的照片。“我有两个战友死了。”他说。亚历克斯的眼镜碎了,他用几块创可贴粘起来,他似乎只剩下这张照片了。“今天是我的生日。”他说。
我记得,海军陆战队是几天前杀死这个叛乱分子的。当时,我们来到一个不设防的区域,有点像是费卢杰中央公园,地上到处是垃圾,街的另一边有一排建筑物,里面全是坏人——至少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应该很了解。他们出动了无人驾驶的扫描鹰直升机在空中拍照,飞机像巨大的苍蝇那样嗡嗡叫着。他们派来坦克,不是把房子炸平,就是在墙上炸出大窟窿,这样我们才能在街上畅行无阻。他们炸毁尖塔,两枚大炮弹,在尖塔上凿出两个大洞,然后安静了。海军陆战队是后来才上楼的,他们沿着螺旋楼梯爬上去,发现了这个家伙,他被埋在废墟里。萨克斯比拍了一张照。一张黑蓝色的脸。
战斗结束了,有事做了。阿什利要给报社发一张死人照片,所以他请奥莫亨德罗派几个人陪我们去。他们现在喜欢我们了,因为我们和他们一同历经生死,目睹他们战友的惨死,他们想帮助我们。我们沿着几天前来时的路走了回去。那时,我们几乎没怎么注意废墟,因为实在太多,一堆堆白色的石块,扯断的电线和散架的汽车,一些汽车还在冒烟。这是被毁弃的世界,它和我们来时大不一样,那时,费卢杰看上去是一座普通的城市。海军陆战队炸毁了一切:每栋房子,每辆车——包括没人的车,每个人——包括躲在阴影中的人。现在,如同一场狂欢刚刚结束,城市又安静了。没人多说什么,有很多天我连我自己的脚步声都听得到,只有在那时,我才感觉有什么事不对劲了。
我们到了尖塔门前,阿什利要进去。当他要拍照时他什么也不怕,他会为了拍照去任何地方,死也在所不惜,几天前他在机关枪子弹中飞跑时我躲在一堵墙壁下面。我不太想跟他进尖塔,毕竟只是照片而已,死人对我没什么用处,我想走了,但我还是跟在他后面。阿什利和我正要踏进门时,两个海军陆战队员出现在我们前面。“我们先走。”他们说。第一个人伸出手挡住我们,我们没看清他的脸。他们上了楼,阿什利拿着相机跟在他们后面,我跟在阿什利后面。
楼梯螺旋向上,很窄,只有一个人那么宽,在我们脚下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它好像是一只几百尺高的鹦鹉螺,不是很稳。楼梯很暗,不过借着被子弹打出的孔,有光束从下面射上来。我放慢了脚步,楼梯上传来一声巨大的射击声,我看不清楚,第二个海军陆战队员摔下来,他摔在阿什利身上,阿什利摔在我身上。温热的液体洒在我脸上,我们滚到走廊里。
第一个陆战队员走到楼梯四分之三的地方时遭到攻击,射击声从楼梯更高处传来,很响,紧接着一声尖叫,瞬时安静了。发动攻击的人在尖塔里面,他一直坐在楼梯顶部。
“米勒!”士兵大叫道。
“米勒!”
没有回应。
我想象着楼梯上的米勒,他的脚被卡住,没能像我们一样滚下来,因为某种理由而没有说话。
阿什利坐在尖塔入口处的门廊上,背朝里,脸朝外,他的头盔歪了,使他看起来很脆弱。他耸着肩喃喃自语:“是我的错。”他的脸上、衣服上和照相机镜头上都粘着血和白色的人肉,“是我的错。”
“米勒!”海军陆战队员又叫起来。
援兵来了,当时很乱,但他们排着队有序地跑上尖塔,就好像一个机关枪阵势。他们都很年轻,神情坚定,跑上弯弯曲曲的楼梯。上面传来更多枪响和尖叫,我分不清是谁开的枪,谁在尖叫。第一个陆战队员空手出来了,他活着,但没有救出他的战友。“操!”他叫道。
他是迈克尔·戈金(Michael Goggin),19岁,爱尔兰人,家在马萨诸塞州韦茅斯(Weymouth),口音很重。他的脸被尘土覆盖——就像照片中那样的尘土,看上去像个鬼魂。“我够不到他。”他说。
戈金和其他人一次又一次跑上楼,每次都带来越来越大的枪声、越来越多的尘土和越来越响的叫骂。我在想多少人会为挽救米勒而死,而米勒是为一张照片而死。叛乱分子不会把死者扔下,海军陆战队员也不会。米勒被卡在楼梯上,有一个叛乱分子就在上面,那是一个绝佳的防守位置。你也能从海军陆战队员的眼中看出这一点,他们的眼睛里都像要喷出火来。也许整个排都会死,我想。
“米勒!”
没有回应。
“米勒!”
那天指挥行动的是山姆·威廉姆斯(Sam Williams)军士长,他26岁,家在密歇根北部。他指了指尖塔顶部,示意士兵开火。子弹和手榴弹同时响起。砰砰砰砰,响得令人难以忍受。
如果米勒还活着呢?我想。当时枪战如此激烈,子弹、弹片和瓦片四处飞散。有两个陆战队员受伤了,一个是德马库斯·布朗,他22岁,家在弗吉尼亚州马丁斯维尔(Martinsville)。德马库斯和战友扫射尖塔,忽然他扔下枪,捂住右脸:“我被打中了。”他的眼中充满惊恐,好像就快死了。但是伤口很小,他又那么年轻,他看上去就像那些在操场上玩耍的小孩,每次都会受伤。他非常害怕。德马库斯于四天后阵亡。
交火停止了,枪在冒烟,又有两个陆战队员爬了上去,尖塔快倒了。砖头和石块一块块掉下来,尖塔摇摇欲坠。尖塔旁边的房子里飞出子弹,叛乱分子发现我们了。
阿什利还坐在门廊上,歪戴着头盔,喃喃自语:“是我的错……”他看上去像一个小孩。
米勒出现了,两个陆战队员把他拉了出来,其中一个是戈金,他被烟呛到了,一边把米勒背出来,一边在拼命咳嗽。米勒的头先露出来,他的脸成了一个V字形,像鱼肉一样裂成两半,两半都在微微地抖动。
“他还没死吧,他还没死吧?”阿什利说。
“他死了。”我说。
就在那一瞬间,我感觉到了。你走进这些地方,并没那么可怕,绝没有人们传闻中那么危险。低下头,把枪端在前面,每次出来时都毫发无伤,你的脸还是那样年轻,神情是那样轻松。记者总是在讲别人的故事。在伊拉克的一所医院里,一个女人拥抱着她刚刚失明的儿子,一滴眼泪滚到她的脸颊。她的脸颊很干,眼泪流得很慢,好像你凝神注视一会儿,眼泪就横穿了整片沙漠。你的摄影师需要给死人拍照,你和海军陆战队员就去了,忽然,一切离得那么近。你脸上沾满了温热的液体,你如此惧怕的死亡,在微笑着注视你,好像它早已知晓谜底。这是你的错。
一辆老式运兵车开来搬运米勒的尸体,车停下时有几粒子弹滚了出来。车要直接开往医院,就好像米勒还有生还的可能似的。士兵把米勒搬上轮床,放平他的手和头。
掩护撤退的任务落到山姆身上,阿什利终于站起来,我们走进尖塔边的清真寺主楼。到处都是枪声,叛乱分子越来越近了。一个士兵拿着一支枪看了阿什利一眼,我想他也许是觉得最好不要把枪交给阿什利,于是才把这支M-16步枪塞给我,枪管很热,很黏。海军陆战队员也不会把他们的枪丢下。上高中时,我用朋友的枪打死过一只鸭子,是坐在他父母的汽车里朝外瞄准的。鸭子在水塘里绕了几圈就死了。“笨蛋,拿着这个。”我并没有听到他说这句话,外面太吵了。
山姆举起三个手指开始倒数,三、二、一。我们跑出门,跑上街,我背着沾有米勒鲜血的枪。我们东面的几挺机关枪开火了。双腿是那么沉重,又是那么轻盈,我们好像一起飞了起来。子弹擦过我们耳边,打中墙壁。“我想死。”我听到阿什利说,“我希望他们打中我。”我们跳过最后一棵倒在地上的树,转进一条小巷,我们安全了。
“我知道你们在想是你们害死了米勒。”回到房子里,山姆这样说道。他叼着烟,背靠二楼的一堵墙坐着。他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充满智慧的老人,脸上却没有一丝岁月的痕迹,而我们反倒成了小孩。“这是战争。”他慢慢地说,语气就像岁月老人,“战争就是这样的。”
艾克特中尉走进来,他没和我们一起去。
“我们要为这些负责。”阿什利对艾克特说,我跟着他这么说道。
“是的,是你们的错。”他回答。
后来一架喷气式飞机投下两颗500磅的炸弹,看上去是在示威:两颗炸弹对付一个杀手。第二天,海军陆战队又回去了,去检查所有人是否都死了,这次他们没带我们。他们找到两具尸体。有时我会想象那个活着的叛乱分子和那个我们想为之拍照的叛乱分子。那个活着的,他在楼上干什么?在安抚他的同伴吗?在为他哭泣吗?他们是一起从沙特阿拉伯来这里为吉哈德而战的吗?是坐着同一辆破旧的汽车到达叙利亚边境的吗?或者那个活着的只是奉上级的命令来取回尸体,而米勒上楼妨碍了他?
威廉·米勒,一等兵,22岁,家在得克萨斯州皮尔兰,这个名字让我想到珍珠(Pearl),或项链。遗像中的米勒有一张瘦长而孩子气的军校学生的脸,神情无忧无虑。我在阿什利的照片集里翻到另外一张,是在费卢杰市中心的大清真寺拍的。美军为攻下这座清真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照片中米勒和他的战友正在休息,当时很安静,他们排成一行,不远处窗户里射进来的光照亮了他们的脸。米勒的仰起的脸向右歪着,他睡着了。
几个月后在北卡罗莱纳州的一个体育馆举行纪念悼念活动时,我看见了米勒的父母苏茜(Susie)和刘易斯Lewis。米勒的枪、头盔、靴子和名牌以墓碑的形状被摆放在地上,其他阵亡士兵的遗物也被这样摆成墓碑形,地板上的众多墓碑形成一个大大V字。比利的纪念碑在右边倒数第四个。
我不知我是否可以面对米勒一家人,但我想对他们说点什么。他们无疑读过了事后回顾报道,里面详细描述了那天发生的事。“第一排奉命陪同两位记者前往清真寺,为尖塔内的身亡敌军拍照。”
我犹豫地走向米勒夫妇,他们看见了我,我带着笔记本。我想他们会说些充满绝望的话压迫我的神经,或者忽然朝我扑来。我在佛罗里达棕榈湾时,一个被害者的父亲在医院的大厅里朝我扑来。“你这混账!”他对我说。我什么都没问,也没有杀死他女儿。
仪式结束后,我们站在体育场中间,刘易斯对我说:“非常感谢你。如果不是你,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儿子是怎么死的。”
我想告诉米勒夫妇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没看后续报道吗?我看着他们的眼睛,他们的眼神疲惫,几乎是精疲力竭。我小时候有个朋友叫帕特·加洛威(Pat Galloway),后来开枪自杀了,他父母的眼神也是这样精疲力尽——哭泣耗尽了他们的体力。他死后,加洛威一家把他的高中毕业照片放在起居室的壁炉架上,我想米勒家的壁炉架上也会有一张米勒的照片。
我向他们问起皮尔兰。
“梨子(pear)-园(land),”刘易斯说,“梨子园,顾名思义,我们的梨很有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