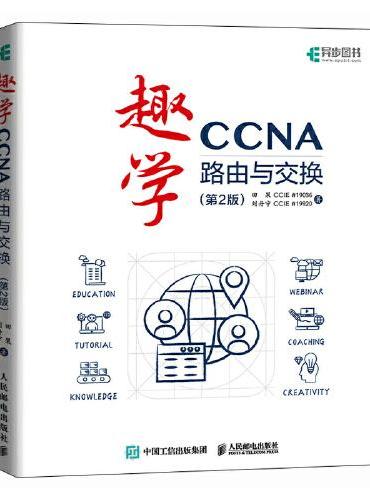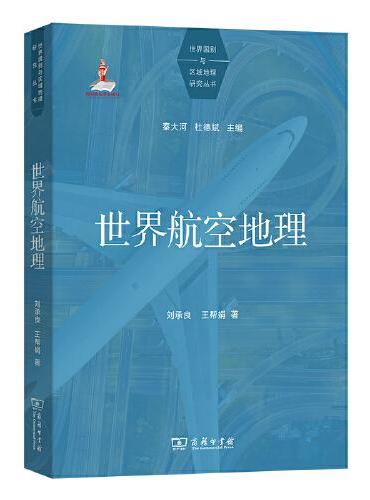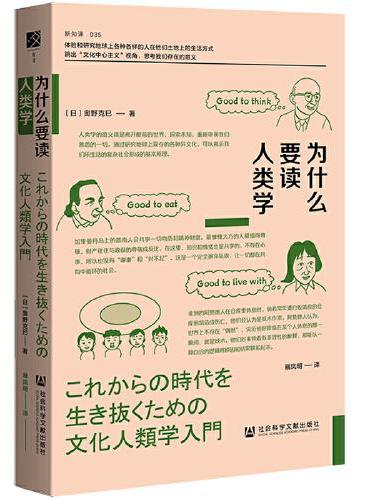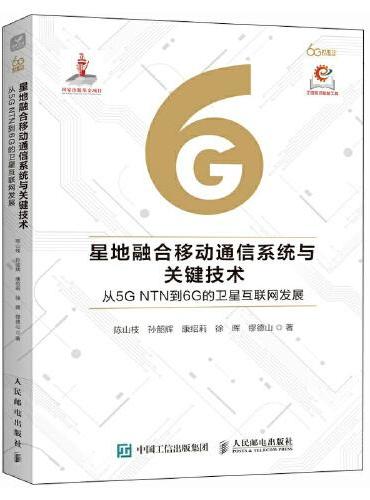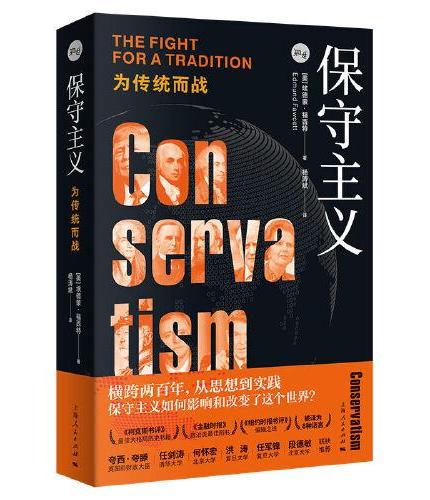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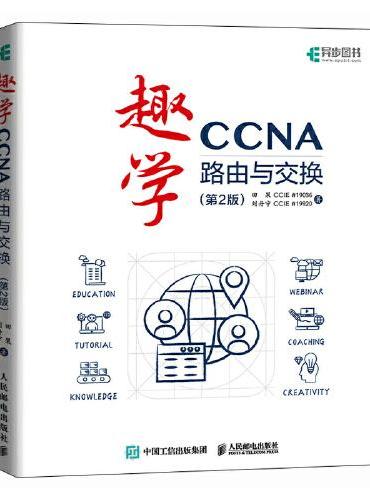
《
趣学CCNA——路由与交换(第2版)
》
售價:HK$
1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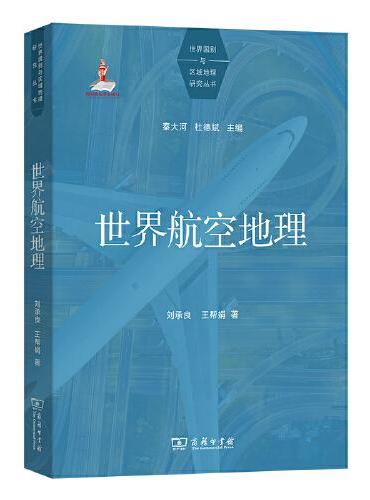
《
世界航空地理(世界国别与区域地理研究丛书)
》
售價:HK$
244.2

《
学术的中心:英法德美
》
售價:HK$
8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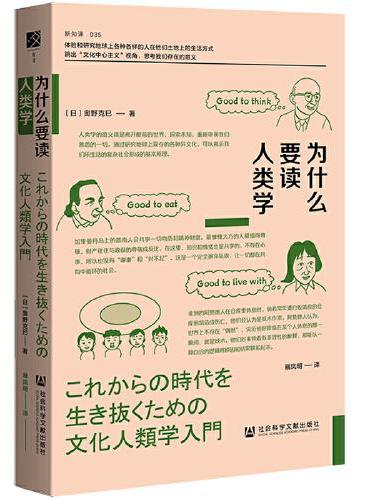
《
为什么要读人类学
》
售價:HK$
77.3

《
井邑无衣冠 : 地方视野下的唐代精英与社会
》
售價:HK$
9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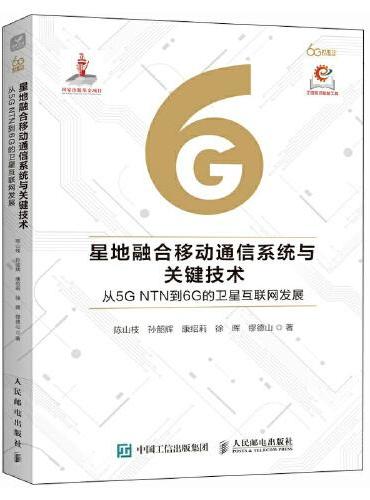
《
星地融合移动通信系统与关键技术从5G NTN到6G的卫星互联网发展
》
售價:HK$
212.6

《
妈妈,你好吗?(一封写给妈妈的“控诉”信,日本绘本奖作品)
》
售價:HK$
4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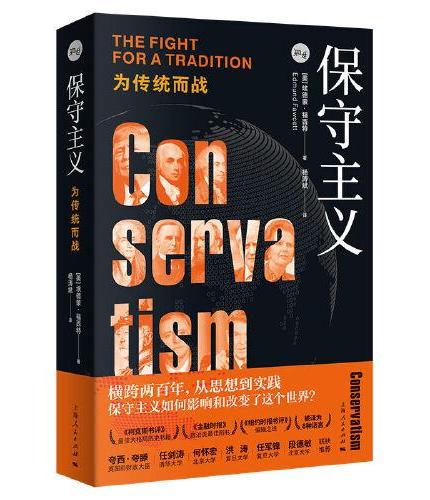
《
保守主义:为传统而战
》
售價:HK$
154.6
|
| 編輯推薦: |
阵容最强大的实力作者集体亮相,最权威的新概念作文精华,不仅是一本作文“圣经”,更是一代人的心路历程。
1.震撼的文字视觉,激荡的文字体验,书写出荏苒年华中的青春文字。
2. 集结历届新概念获奖者,延续永不停息的思索与创作!
3. 本书内容优良,插图精美,版式活泼,全力为青春读者专属打造。
|
| 內容簡介: |
|
本书共分六辑,每个章节主题独立,构思新颖。本书作品依然体现新概念作文参赛者不同凡响的创作水准,高手云集,形式多样,内容健康阳光、积极向上,是为千万份新概念稿件的甄选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
|
| 目錄:
|
"凤孤飞直到四季静默无声
凤孤飞 梦田
新的旧情人 占晖
分手 向夏
直到四季静默无声 潘云贵
小城爱霞美镇少年溺水事件
小城爱 李晁
小孩因此沉默了十年 普鲁士蓝
霞美镇少年溺水事件 黄可
随安火锅少年
随安 张其鑫
越狱 卢鹤来
蓝色蝴蝶发卡 晏耀飞
火锅少年 王天宁
五日咖啡
五日 夏克勋
恍如隔世 弋止
虚宴 简唯
咖啡 李梦芸
迦南地守 夜
迦南地 陈娇
房子飘在水面上 三梧
守 夜 韩倩雯
梦非梦北京三人行
梦非梦 陈娇
三份零工 棉兰
我脚掌遗落的地方 丁威
下落不明 谢宝光
北京三人行 雪轩
旧城夜语黒玫瑰的秘密 \n
旧城夜语 陈仕杰
镜子的背面 丁威
黒玫瑰的秘密 暮寒\n
这该死的时间共轭
这该死的时间 杨杨楠
当局者,迷 宋南楠
共轭 邬龙飞"
|
| 內容試閱:
|
霞美镇少年溺水事件
一
客车在离二叔家大约四十米的加油站停下来加油的时候,我下车徒步走了过去。漫天都是橙红色的火烧云,风拂过我的脸黏黏的,那些云却一动不动,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咸湿的海腥味,我背着硕大的登山包,走在这条只有单车道的水泥路上,呼吸时仿佛能察觉漂浮在空气里的细小尘埃,干燥而且夹着辛辣的味道。
我走到二叔家门口的时候,那辆客车加好了油轰隆隆地从我身后开了过去,水泥路是笔直的,我看着它上了坡片刻后消失在坡后边了,海边小镇的傍晚安静极了,路上没有闲散的人,房子也是稀稀疏疏地建着,能看见房子后边大片的田地,来的路上我看到那些正由青变黄的水稻一片一片地蔓延着,甚为壮观,约摸下个月就是割稻子的时候了,这几日天气逐渐变得燥热难忍,身上的衬衣在车上吸了汗水变得酸臭,我看了一眼余晖下的稻田,带着猩红色,安谧而壮阔,相当好看。
走进二叔家的院子,我看见了站在玻璃药柜后边的二叔,长条椅子上还坐着几个中年男女。二叔看见我对着屋子里提高嗓门说道,蔡婷!寒阳到了,把菜炒了。我叫道,二叔。他点点头,对着站在柜台边等他拿药的病人说,这是我侄子,刚刚高考完,马上就要上大学了,来我这里住几天。那拿药的人哦哦几声点头,大学生啊,真好。我进了屋穿过当诊所用的前厅,二叔家的这栋楼是狭长的,后半边是厨房和餐厅,脱掉鞋上了二楼,二楼还有个客厅,往里走是书房,我把登山包放在会客厅的沙发上,取出毛巾进房间的浴室洗了脸,把水放掉的时候我听见了声响,回过头看见二婶也进房间里来了,这么远的路很累了吧,晚饭做好了可以下楼吃了。我应了声,二婶继续说,二楼楼梯那边的房间就给你睡,我下午打扫干净了。我说好,二婶笑了笑说,昱倩待会儿就回来了,我们先下楼去吧,吃饱了再说。
我把拿在手里的毛巾挂到了墙上,下楼去了。
碗里的饭吃到一半的时候,昱倩才骑着自行车回来,从餐厅我坐的地方望出去刚好可以看见庭院,天色暗下来了。昱倩跑进餐厅里,哥哥你来啦!哎呀我饿死了!二婶把饭盛好递给她的时候,二叔正好忙完了前厅里的事情也走了进来。
二婶张罗了一桌子的海鲜,吃得我满嘴鱼腥味,餐厅里的灯光有些暗淡,二叔二婶断断续续和我交谈着。二叔说,你们学校有医学院么?我愣了一下,点了点头,他继续说,当初怎么不报医学呢……二婶笑着道,那是你的想法,人家寒阳有自己的打算,别老看见孩子就叫人家学医,过几年还不一定不让你女儿学这行呢。昱倩扒拉了几口饭,插嘴道,我才不当医生呢!一点意思都没有。二婶听完开心地对二叔道,瞧见了吧,你女儿。二叔也笑了,道,这可不好说。
墙上的挂扇来回摆头,然而吃完晚饭的时候,我的后背还是湿透了。我刚要端碗起身,二叔突然说道,我待会带你和昱倩去海边吹风。透过厅堂我看了一眼外边的庭院,暮色四合,天早就黑了。
坐在摩托车上,风呼呼地从我的耳边吹过去,头发都在空气里翻飞,这个夜晚本该有微弱的月光的,然而此时只有漫天的乌云。车轮下的水泥路弯弯曲曲地在大片大片的海场固沙林中延伸,那些高大的固沙植物落下的叶子满路都是,摩托车坐了这么久,路上一个人都没有,昱倩似乎很开心,正在哼着我听不清楚的歌。
穿过了林子,路边开始出现稀稀疏疏的楼房,亮着灯,却仍旧显得有些孤零零的。我闻到了愈发浓烈的腥味,二叔突然说道,前边是鲍鱼养殖场。言罢,我们往左一拐,进了一条长满杂草的小路。车灯在前面晃动着,二叔说,到了。摩托车便停了下来。我从座位上下来,脚下是柔软的沙子,四下里漆黑一片,风很大,前面似乎有海浪翻涌的声音。
昱倩往前走去,我跟上了。二叔站在摩托车边上抽烟,回过头时我在黑暗中看见了那个红色的亮点飘忽不定,我不知道为什么二叔今晚要带我来海边,昱倩正朝着大海的方向大声地喊叫着,我走在沙滩上,有沙子跑到我的鞋子里去了。二叔抽完第二根烟的时候,我和昱倩往回走到摩托车边上,二叔道,我们去个伯伯家里。
那是一栋瓦房,有个大而整齐的庭院,我们进去的时候,一对中年夫妇正在庭院里坐在讲话,看见二叔都站了起来,那个伯伯说,嘉义你今晚怎么有时间来我这里。二叔道,带我侄子和昱倩去海边吹了吹风顺道过来坐回儿,这个是我侄子,寒阳。那个中年妇女进屋搬了几张椅子出来,招呼我们坐下,昱倩却没有坐下,跟二叔嘀咕了几句,回过头来对我说,哥哥我带你去看小鲍鱼!二叔接下话音说,就在后边,你们自己去吧。那个中年妇女给了昱倩一把大手电,我跟着昱倩从院子围墙里侧的一个小门出去了,听见了水声哗哗地响着,昱倩把手电递给我,兀自走在前边,我胡乱照了照,明白过来这是个养殖场,田字格一样的布局,这么说来每个水池里都养着鲍鱼苗,我把手电望水里一照,水底除了一堆正方形的水泥片什么都没有,我问昱倩,鲍鱼在哪里?昱倩走在前面说,我带你去鲍鱼最多的那个池子!我跟着她小心翼翼地走着,绕来绕去终于到了一个最里面的小池边上,昱倩回过头来拿过我手里的手电,说,哥哥你把那个水泥砖拿起来。哪个?随便一个。我蹲在水池边,把手伸进水里捞起了一块在其他水池里看到的一样的正方形水泥片。
昱倩接过我手里的水泥片,小心地翻了过来,借着手电筒的光我看见了那上面密密麻麻的小东西,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没有想到鲍鱼小时候是这个样子,一个个和我的拇指头一般大,正像蜗牛一样在砖面上滑动着,我想不明白,这些鲍鱼壳怎么才能长成餐桌上看见的样子。昱倩开心地说,多吧,这里面每个池子里的砖上都这样养着小鲍鱼哦。
我和昱倩回到庭院里,二叔看着我说,看到鲍鱼苗了么?我点了点头。那可是一池一池的宝贝啊,二叔说道。我说,长得和餐桌上的真不一样。一边坐到凳子上去了,昱倩在庭院里走来走去坐不住,我掏出手机随便开了个网页。
二叔和那个伯伯喝茶的时候谈话断断续续,我坐着一言不发,零零星星地听着。
二叔说,陈德厚好像去跟沈利坐了一个晚上,不过……沈利还是不打算退出。
伯伯抽着烟,良久才答道,要是这次沈利选上了,恐怕陈德厚不会轻易放过他的。
二叔答,要是真让沈利给选上了,陈德厚又能有什么办法,人家是一票一票选出来的。
伯伯接下话音,是一票一票买出来的。接着便是长久的沉默,我不断地更新手里的网页,听不明白这话里究竟是什么意思。
二叔来霞美镇当医生已经十年了,十年的时间里她娶了这里的女孩当妻子,生下了女儿,盖起了两栋楼,来回奔波在医院和自家诊所之间,只有在年假时才匆匆忙忙地回到爷爷那里一趟,住上一晚,翌日天未亮连奶奶准备的早餐都来不及吃就又匆匆忙忙地离开,赶回到霞美镇,因为有很多的病人在等着他回来开药单打点滴,这个海边小镇的海风四季一样猛烈,二叔似乎已经在这里扎下了根,爷爷说二叔当年学医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料到这小子就这样算是送给人家了。
在外人看来,医生是个赚钱的好职业,但是在爷爷奶奶看来,自己的儿子连回家都变得奢侈,他们觉得当年给了二叔一个现在看上去光鲜亮丽的生活,但是实际上忙得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总是后悔不已。这两年二叔和霞美镇当地的几个人合伙搞副业,建了个鲍鱼养殖场,二叔只是提供资金,没有亲自下过海,现今又建鱼池养鲍鱼苗,看上去正在大把地赚钱,但是爷爷奶奶总是在台风到来的前几个晚上睡不着觉,担心一阵大风轻而易举地毁掉整个养殖场,几年来的投入瞬间化为乌有。
这个晚上从海边回来的路上,我坐在摩托车上抬起头望天,看见了乌云都散去了,漫天久违的星辰,那是我很久以来没有见过的壮丽景象,深邃辽阔,带给我一阵莫名的眩晕。路上依旧没有行人,连那些稀疏房屋的灯都灭掉了,漆黑一片的夜晚里只有摩托车灯投射在路上,空气里的海腥味似乎消失不见了,虫鸣不绝,凉意中我知道夜已经深了。
二
我醒来的时候天大亮了,房间里亮堂堂的。头发都纠结在一起黏糊糊的,海风里似乎有什么东西把它们变得非常油腻,我觉得有些烦躁。打开手机的时候看见了好多未接来电,看着似乎又都无关紧要,便起身去浴室里刷完牙洗完脸下楼去。这会儿,昱倩已经去补习了。我一个人在餐厅里吃着早餐,看着前厅里来往的人,二叔去上班了,二婶和那个药师正在忙进忙出,好些人在打点滴,还有那些买药的人似乎没完没了,我吃完早餐后去前厅坐了一会儿却发现自己完全帮不上忙,庭院南边的棚子下里有几个人坐着聊天,我看了看那些陌生脸庞,转身上楼去了。
二叔的房子是三层楼,第四层只有一半用玻璃搭建的单独房间,余下的一半留作阳台,种了些许花草还放了石桌石凳,不过看来这里疏于打理,花草萎蔫,反倒是那些不知道怎么长出来的杂草占据了大部分的地方,石凳上放着几个塑料盆子,我把它们拿到地上去,吹掉上面的尘土便在石凳上坐了下来。
从我坐的地方透过栏杆往右手侧望下去,是块不大的地,看上去像是打好了地基,长满了茂盛的杂草,再过去一点的地方是块水泥地,地上湿漉漉的,都是从渔网里流淌出来的海水,上边搭了黑色的塑料纸当做棚子,许多中年妇女正坐在棚子下面挖蚵,戴着挽袖和口罩,我远远望过去看不清她们手里的那把工具是什么,似乎正在忙着撬开一个个海蚵的壳,把新鲜的蚵扔进盆子里,二婶曾经跟我说过这是一项非常有技巧性的工作,这些熟练的妇女们撬一天手都不酸,而且收入可观。
近海的小镇都有这样的场景,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讨生活本来就不是一件易事,来的路上我看见了堆积得像山一般的蚵壳,白花花地散发着腥味,其实没有细想,这或许暗示着这样的小镇千百年来的生存延续之路。
二叔的这栋楼在马路边上,站在这个阳台的栏杆边上往西北方向看过去,就是我昨天下车的加油站,在早晨的光芒里,红色的顶棚显得生龙活虎,而马路那一侧和二叔家正对面的是一栋二层的楼房,庭院里收拾得很整齐,一角里还有辆黑灰色的老式自行车。目光越过这栋楼,后边便是大片的稻田,连绵一片的金黄色和青黄色相互交错,相当壮观。稻田的中间还有个水塘,面积不小,远远望去水面平静,正倒映着边上那棵大树的影子,那棵树扭曲着树干,叶子不多。
呆在阳台相当凉快,日光被四楼的玻璃房挡在了那一侧,投下的影子随着太阳升高变得越来越短,我坐在石凳上,还在阴影中。我把几本书带上来,正无所事事地翻着,却透过栏杆看见二婶披着那件长袖的白衬衫骑着女式摩托车朝着加油站方向去了,片刻就消失在房屋之后,我知道二婶出诊去了。
对我而言,出诊这个词并不是我一开始能理解的,在我的概念里,这个词必须和大山里的行走医生才有关系,像霞美镇这样靠海发家的富裕村镇是不会需要医生去出诊的,然而事实上,相反的是二婶和二叔下班之后,似乎更多的时候都会背着一个绿色的药箱在巷道里村路上来回出现。
二婶回来得晚,午餐做得迟了。昱倩在楼上开电脑玩小游戏,一边吃着大大小小的饼干糖果,我躺在沙发上看书,这时候已经是将近下午一点钟光景,肚子开始觉得饿了,便在茶几上的糖饼盒找了包水果糖随便吃了起来。
吃过午饭之后,我又上了二楼,昱倩进房间去写功课,我无聊地刷着网页。两点钟过后二叔下班回来了,他上楼来坐在沙发上自己泡起茶来,满头大汗地问我,这几天都干什么了?我摇摇头说什么都没做,就是看看书而已。他刚想接下去说什么,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他接起来道,德厚啊,你好!然后嗯嗯啊啊一通便挂断了,对我说,有客人要来。我点点头便继续刷网页去了。
站在书房窗边,太阳毒辣辣地投进屋里,望下楼去就是庭院,停着两辆自行车。空气里有股烧焦的气味,夹杂在海风里飘过,让我有点反胃。吃过午饭的时候我接到高中班主任的电话,他告诉我学校通知领取档案,要我转告给同学,我这才想起我答应了同学过几天去聚会的事情,我早就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翻看了下日历,这么说我再过几天就得赶回去。
去客厅倒开水的时候,看见客人已经来了。想必就是刚才给二叔打电话的陈德厚,昨晚我就听过这个名字,和想象中有些不同的是,原本我以为会是个发福的中年男子,没想到坐在我面前的竟然是高高瘦瘦的,看上去年纪也没有很大的男子,倒是完全看不出官相。昨晚吃夜宵的时候我问二叔他和鱼池那个伯伯的谈话,才得知二叔所在的这个村叫美南村,过几天要选村主任了,陈德厚和沈利是两个候选人。二叔似乎没有多大的兴趣,他把户口迁到这边之后,也获得这里的选举权,只是按照二叔说来,每次村选举总是麻烦不断,今年恐怕也是如此。我没有细细追问是什么麻烦,倒是觉得与我无关。
二叔跟陈德厚介绍了我,我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转过身要进书房的时候我看见了茶几边的地上放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子,口子系着,迷迷糊糊显露出里面的东西是有棱有角的。怪不得鱼池那个伯伯昨晚说是一票一票买出来的,看来今天陈德厚是有目的而来的。
我站在书架前,看着上面那一排排药学和医学的书本杂志,书架边就是房门,客厅里二叔和陈德厚的谈话声正悠悠地传进来,我随便取下一本书便靠在书架上听了起来,我觉得二叔说话是嗓音有些许不同,甚至有点阴阳怪调的意味。
陈德厚说,大后天就要选了。
二叔说,你啊,都当得这么习惯了,现在还会紧张啊?
陈德厚说,哈哈,我都想退居二线了,就想再做一届。
二叔说,这一届还是你做。
陈德厚说,哎哎你不知道啊,沈利的势头很猛。
二叔说,再猛也是新人。
陈德厚说,后生可畏啊,我听说他砸了不少下去。
二叔说,你难道还没有信心么?
陈德厚说,这可真说不准!本来以为就我一个人选这个,结果半路杀出来一个沈利说他也要选,我就觉得不能掉以轻心。
二叔说,沈利和我同岁。
陈德厚说,是啊,你看看,小了我六岁啊。正年轻!
二叔说,年轻是好事,我说……你该做的工作都做了吧。
陈德厚笑了,说,是啊,都做了,这点我没敢耽搁。
二叔说,那你怕什么,再几天就选了。放心吧。
陈德厚说,哎哎,你不是和沈利是同学么?
二叔说,是啊,是同学。
陈德厚说,我就直说吧,我想啊……你能不能做个中间人。
二叔说,我嘴笨,说不好。
陈德厚说,哪里哪里,像我这种粗人都敢说,你一个知识分子怎么会说不好。
二叔说,真说不好。唉唉。
陈德厚又笑了,哈哈,你看你这么谦虚。
我听见打火机嚓的声响。
二叔沉默了一小会,接着说,我觉得啊,你去找沈利说比较好。
陈德厚说,事实上我去说过了。
二叔说,说过了?沈利什么态度?
陈德厚许久之后才说道,他就说没有打算退出。又是一阵良久的沉默,我把手里的书放回书架上,坐回到书桌前喝了口开水,这里的水不好喝,二婶说碱性太强了。我把杯子放下的时候,听到他们又开始断断续续地聊了起来,不过话题似乎已经变了。我走到门边去,想听得清楚些,却看见电脑屏幕一闪,进入了屏保程序。
我听到二叔说,是啊,他刚刚考上大学。
陈德厚说,你看看你们家族都是能读书的娃,昱倩也读得那么好。
二叔说,昱倩这还没个头绪呢。
陈德厚说,跑不了。
二叔说,朋逸不是也读得不错。
陈德厚说,他啊开学高三了,现在放假一点样子都没有,书也不读,没什么出息。
二叔说,他有他的打算,你当爹的急什么。
陈德厚说,他小子能有什么打算,哈哈,就知道玩。
我没有再听下去,坐回到电脑前,开了邮箱看了看那些广告邮件,又随便看了会儿新闻,书房里开始变得熏蒸,风扇已经不起作用了,我才发现自己已经流了这么多汗,起身找空调遥控器却始终找不到,出门去客厅,才发现陈德厚已经走了,我看到二叔自己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泡茶,那个黑色的袋子还在地上没有解开。
二叔看见我笑了笑,要喝茶么?我说好,便坐在他边上,他一边给我弄了杯茶一边感叹道,这年头选票真值钱。我也笑了,二叔拿起地上那个黑色的袋子,利落地打开来,看了一眼,说,又是这些东西。我下意识地从他手里接过,看到袋子里有好几条烟和几瓶酒,我说,还真是烟酒啊,这么俗。二叔说,不俗就奇怪了,底下还有红包呢。我听罢一阵翻腾,还真给我找出了一个精致的红包。撕开黏住的口子,取出里面的钱数了数,八百。二叔问,多少?我看了一眼撕开的口子,说,八百。二叔吸了口气,呀了一声,道,比沈利还多一百啊,看来陈德厚是挺难过的。
我说,这个村长就这么能吸引人,两个人都这么想当。
二叔说,陈德厚当上瘾了,今年来了个沈利大家就叫他别和年轻人争了,他就是不甘心。
我说,沈利这个人怎么突然想当村长了?
二叔说,有钱就想捞点官做啊,他这几年包养殖场大赚了一笔。我点点头没有接下话茬,喝了口茶,二叔继续说,沈利的红包是前些日子就送出去了,一个人三百,看来陈德厚下了不小的决心。我问,是你和二婶两张票?二叔答,是啊,一人一张,红包收下来至于投给谁那就是我们自己知道了。二叔狡黠地笑了,接着说,鹬蚌相争,这村长的位置啊,就是那颗珍珠。片刻,我问二叔找到了遥控器,便又进书房去了。
晚上十点钟左右,二婶把庭院的大门锁上了。每天这个时刻往后,就基本没有什么病人了,夜里气温凉快,我们都搬了椅子坐在庭院里,今晚满天都是灰色的云,连成一大片一直蔓延到山的那边去了,海边的山都低,充其量只能叫丘陵。二婶从屋里端出水果来,是葡萄和水蜜桃,我拿了个水蜜桃吃起来,二叔正在看手机里的新闻,偶尔有车从外面驶过,轰隆隆地响,大多是高出围墙许多的大货车。暗夜行路,恐怕都是超载的车子。
十一点钟一过,连车子都少了下来,我们把桌椅搬进屋里,二叔锁上门打算休息了。我上楼去洗完澡从浴室里出来的时候,昱倩已经和二婶去睡觉了,二叔把电话的听筒拿下来,看见我疑惑,解释道,半夜经常会有病人打电话说是突发情况需要出诊,接了不去又说不过去,干脆把电话拿下来。不过以前我们都会跟他们说去卫生所,那里晚上也有医生。现在也没什么人会在夜里找我们了。我喝了杯水,便准备回房间睡觉了。二叔突然说,今晚可能会下雨,记得把窗户关上再睡。我点头,他进屋睡觉去了。
夜里被声响吵醒的时候,我摸索着拿过手机看了一眼,是凌晨三点十五分左右。我听到楼下有声响,楼梯口的灯打开了,光照进我房间里。我心里一沉,有种不好的预感袭来,便连忙翻身起床,却听见楼下二叔的声音,还有人在不舒服地哼哼。走到楼下看见二婶和二叔都在,二叔戴着口罩从注射的小隔间走出来看见我有点吃惊,说,被吵醒了?我点点头,二叔接着说,不要进去。我知道应该是突发情况半夜来敲门,二婶示意我上楼去,我知道没事便上楼了,躺在床上听着楼下变得细微的声响,翻来覆去却怎么也睡不着了。
风变得大起来,呼啸着从窗口过去,夹着细微的啪啪声,下雨了。
我迷迷糊糊就又睡过去了。
三
今天二叔轮休,我起床下楼的时候他正在前厅里给病人拿药,看见我便叫我赶紧吃早饭,这几天在二叔家睡,清晨都听不到闹钟响,反倒是被太阳光给照醒了。吃到一半的时候,二叔走到餐厅里坐下,盛了粥也吃起来,撕下半条油条放到我碗里,又过了一会儿二叔道,寒阳,待会儿去新房子那边帮帮忙。我愣了几秒钟才想起来临出发来霞美镇之前,母亲跟我说过二叔的新房子已经开始装修了。我点点了头说,吃完就过去吧。二叔说,好,今天让你当苦工。我也笑了,听见前厅有声响,是二婶出诊回来了。
父亲有三个兄弟,还有最小的一个妹妹。二叔是医生,我父亲和三叔还有小姑都是教师,当年爷爷一介贫民可谓相当有远见,苦日子过着也下了决心要让四个孩子都读上书,父亲到我高中时谈及当年的生活还是慨叹不已,爷爷担着米翻山越岭送去学校,父亲讲到这里总是难过起来。幼年时家贫,连花生都是奢侈品,每每过年团圆之时,奶奶还会说起当年父亲偷花生米的故事,说是那时奶奶把晒干的花生用编织袋装好,系上绳子绕过房梁挂得老高,父亲和叔叔们年纪还小够不着,垂涎不已,后来父亲想出法子,便取来一根竹竿,往那个袋子一捅,每回都能从窟窿里掉下几个花生来,不料几次之后终于东窗事发,三兄弟站成一排挨了一顿打,兄妹早已各自成家,十几口人听完哈哈大笑,喝杯酒唏嘘着苦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实话讲,兄妹四人感情很好。来往频繁,早些年日子还不好过的时候相扶相持倒是谁也没有落下,伯叔姑侄之间没有什么隔阂,倒也是一件好事。加之公认的三个好媳妇,奶奶总是说自己上辈子积德才有这么些乖媳妇,听话不顶嘴还孝顺。
天伦之乐,我想大概也就是如此。
吃罢早餐,二叔骑上摩托车载着我去了新宅,和二叔现在住的房子一样,新宅也在马路边上,只是没有庭院,门口是个不大的水泥空地,我从摩托车上下来站在水泥地上抬头看了一眼,新宅一共四层,一楼的玻璃大门和楼上的玻璃窗亮堂堂的泛着光芒,二叔锁好了摩托车和我一起走进了一楼的大厅里。他说,过几天就有领导过来检查了,所以这两天要提前打扫。我不解,领导?二叔说,是啊,你看看这一层的格局。刚入门的右手侧用毛玻璃隔出一个大概长宽各两米的小单间,二叔说,这是注射室,以后这栋楼的一层全部都将医用。往里面走就是两个巨大的药柜,这里是取药区,在大厅最里面的左手侧,是个卫生间,卫生间出来的边上也有个小隔间,是用来给需要点滴的病人躺着休息的地方。
大厅其他的地方都空荡荡的,满地的白灰和塑料袋,二叔递给我一把匕首一般的东西,走到墙壁说,着墙上贴了瓷砖,抹天花板的时候滴到不少墙漆,你就这个把它们弄下来。我明白了,搬了把椅子就开始弄了起来。
二叔自己到另一边也忙了起来,从我身后传来他的声音,啊对了,医用的只有第一层所以到时候检查的也只是第一层,楼上有师傅在铺砖,我上去打个招呼。说完从里面的楼梯上楼去了。我不停地重复着把瓷砖上的墙漆弄下来,不时从椅子上下来挪个位置再爬上去,等到把进门左手侧的整面墙都弄干净的时候,二叔下楼来了,一同下来的还有两个师傅,穿着迷彩服不过沾满了水泥和土灰,其中一个师傅看见我连忙给我递烟,我摆摆手说我不抽烟,自己有点不好意思。二叔说,寒阳,辛苦了,过来喝点饮料。他们坐在那个当注射室的小隔间里抽起烟喝起饮料来,里面有风扇,正呼呼地响着,我进去拿了瓶橙汁也坐在边上。
他们又开始聊起选举来,这几天我似乎在什么时候都能听到这个话题,这一回他们似乎在讲更久之前的事情,我从他们口里听到了一个没有听过的人物。两个铺砖师傅有一位看上去年纪大些,话也少些。年轻的那位师傅喝掉一大瓶橙汁,和二叔随便聊了起来,他说,听说陈德厚给了陈金鸣十五万。
二叔笑笑说,这兄弟都要打起来了,不过我听说没那么多。
师傅说,屁话,没听过这么当兄弟的,十五万!这不是光天化日抢劫么?
二叔点上一根烟,说,人家说啊就是拿个样子,私底下都还给陈德厚了。
这回拿个师傅笑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就陈金鸣那种货色,十五万银子摆在他面前他死都不会撒手的,要想他还给陈德厚,陈德厚只能做梦了。
二叔说,毕竟是兄弟。哎哎,这下可好,陈金鸣真拿着那十五万退出候选人了,结果沈利这个人可不吃陈德厚这一套,坚持要和陈德厚竞争到底。
师傅抽着烟,沈利势头可是相当猛啊,年轻人真有胆量。
二叔只是点点头,沉默着抽烟。我身上的汗干了些,拿起饮料瓶走出小隔间,走到大厅最里边的窗户边去,站在窗边看出去,原来新宅后边二十来米开外的地方有条小溪,溪水看上去甚是清澈,岸边杂草丛生,绿色在两岸蔓延,让人觉得生气盎然。夏天的太阳明晃晃的,投在水面上都是反光,亮斑闪闪烁烁,迎面而来一股燥热的气息。
中午将近十二点的时候,我和二叔把四面墙上所有的墙漆都弄了下来,用干抹布擦过一遍,听到门外有声响,回过头去看见二婶正走进来,寒阳肚子饿了吧?我没来得及说话,二婶对着二叔道,你自己不饿以为人家都不饿啊,都十二点啦!我以为你们早回去了,没想到还在这边。二叔咧咧嘴笑了,我这不是想着下午不来了嘛,干脆弄晚点,我还真把寒阳给忘了。二叔哈哈笑着,把东西整理好我们便出门回家了。
这天午后出了件大事。
两点钟一过,庭院里被毒辣的太阳光笼罩着,二叔把玻璃大门关上,打开空调,大厅里的凉空气里弥漫着一股中草药的味道,二婶在塑料椅上躺下眯着眼稍微休息,二叔正在一边按着遥控器换台,昱倩在楼上午睡,我无所事事地翻着放在药柜上的报纸杂志,四下里静悄悄的。差不多将近一刻钟的时候,二叔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二婶在塑料椅上翻了个身醒过来了,二叔结果电话,停了几秒钟之后神色有些紧张。我察觉出异样,盯着二叔的脸看,片刻后他挂掉电话对着二婶说,陈德厚的儿子在南塘溺水了,可能出事了。
二婶腾地站起来,说,你赶紧去看看,啊……是谁给你打的电话?
二叔从柜台上拿起钥匙,是朋逸他叔。说罢,拉开玻璃门大跨步走了出去,消失在庭院的大门外了。我转头看着二婶,问她,南塘在什么地方?二叔怎么没骑摩托车?二婶道,就在马路对面的那片田地里,那个水塘就是南塘。言罢神色凝重地走到茶几边倒了杯水咕隆几声喝下去,突然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了句,真是祸不单行!我没有理解二婶的话,但也不好插嘴,只好在一边沉默,突然我想起了昨天在楼顶的阳台看见的那个水塘,这才明白二婶所说的南塘原来就在这么近的地方。
二婶又喝了杯水,对我说,昨晚喝酒摔伤大半夜送来的是朋逸的另一个叔叔,今天怎么朋逸就溺水了……我恍然。
我原本打算也走到水塘边去的,但是二婶不同意,她说有些东西不要看的好,从她的语气里我听出了凶多吉少的意味,只是我和这个陈朋逸素未相识,不知为何此刻却有莫名的心神不宁,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出于恐惧抑或惊吓,只是好像有些无力感。这个午后的病人零零星星,来的人反反复复地跟二婶提起陈朋逸溺水的事情,长叹短叹,从谈话中我们还是知道那个陈朋逸终究没有逃过一劫,几个妇女感叹了几句离开了,二婶也沉默不语。
有个略显富态的中年妇女买了两瓶正气水,似乎和二婶是相识,便坐在长凳上和二婶谈起话来,她说,我刚刚也去了南塘。停了些许时间接着道,唉……我都不忍心看下去了,那么大个孩子就这么没了,乾婷都不知道晕过去几次了,都快二十岁了……几声嘘唏,二婶的茶泡得缓慢,茶香飘散在空气里,和草药味混杂着,变得不易察觉。
正午还是毒辣的阳光,到了傍晚,二叔还没有回来,天却变色了,庭院里没有了风,那股海边小镇特有的咸湿味道像是凝固了一样浸透在空气里,我浑身燥热,汗水细细密密地冒着,从远处的丘陵连绵而来的乌云翻涌着从头顶上呼啸而过,看样子今晚要下起大雨来了,二婶也看了看天轻声道,台风要来了。我听罢才想起,这几日天气预报说是台风已经成型,正向着这个方向而来,如果没有正面袭击,恐怕台风尾扫过也有足够的降雨。昱倩在看电视,专心致志旁若无人,她倒是完全没有理会溺水事件的好奇心,其实也是,这与她……与我,都是无关的。
二叔回来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那个时候有个五十几岁的男子正在打点滴,二叔走进前厅,坐在了长条椅上,二婶问,情况怎么样了?二叔摇摇头,似乎有点无可奈何,我还以为去了做做心肺复苏能不能有点效果,结果我到那里一看,瞳孔都放大了。
二叔说罢和那个打点滴的男子说起话来,钱叔,不舒服?
那个被二叔称作钱叔的人答道,这几天有点头晕。
二叔说,你都要六十的人了,不要那么拼命。
钱叔笑了,黑黑的脸庞上沟壑纵横,还能做就做呗,等哪天不动了再麻烦人家。
二叔说,说的也是,唉。
钱叔说,陈德厚现在怎么样?
二叔似乎不是很能理解,说,我刚刚从他家回来,现在乱作一团了。
钱叔点点头,若有所思,过了许久才说,后天就要选举了,这下出了这么个事情……
二婶在一旁突然说,估计也是选不成了,哪有心思再选。
二叔接下话茬,他们家今年流年不利啊。那个南塘上个月刚刚入夏的时候就淹死了一个小学生,过来家家户户都不许自家孩子靠近,怎么偏偏陈朋逸这都要二十的人了还去那游泳……据说朋逸啊,水性很好哇!
钱叔摇摇头,轻声感叹,生死有命……
吃晚饭的时候,二叔和二婶面色平静地聊着下午发生的事情,二婶只是同情乾婷,也就是朋逸的母亲,但除了一阵感慨也做不了什么,昱倩丝毫没有理会发生了什么,二叔转过头开始教育昱倩不能到处乱跑,更不能靠近南塘,昱倩满口答应,只顾吃饭都不夹菜,急匆匆地吃完就上楼玩电脑去了。
夜里晚些时候,开始下起雨来。
四
雨还在下,漫天阴霾,站在书房窗前可以看见很远的丘陵那边闪电不时闪过,但是却没有雷声传来,我搞不清楚这究竟是台风带来的雨还是夏季的雷阵雨,风呼呼地响着,劈头盖脸地朝着我扑过来,我静静地站了一会儿,脸上有些水珠,便关上窗户坐到那把藤条摇椅上,昱倩正在书桌前玩电脑,忙着给她那个宠物各种折腾,由于下雨她得到了这难得的一天的假期。看了一会儿书,我起身去客厅喝水,却看见有客人来了。二叔看见我走出来,和我说道,寒阳我给你介绍下,他就是沈利叔叔,和我是同学。我开口道,沈利叔叔。他点点头笑了,你好,马上要去上大学了对吧,我经常听你二叔夸你。我连忙说,谢谢。打过招呼,我倒了水便又进了书房。
我坐在摇椅上,一边看书一边断断续续地和几个同学发着短信,有些同学的录取通知书寄到了,约好了时间去学校领档案、转出团员关系,这一类的零散事务好像还有好多,我答应他们后天一起去学校,班长告诉我有几个同学要去班主任家里拜访,提醒我不要缺席,我打过电话回去确定了时间,这个早上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过去了。
雨点打在窗上啪啪地响,我听不到客厅里的声音,待到我再出去的时候,沈利叔叔已经走了,二叔也不在,估计是下楼去了。我坐在沙发上吃起果冻来,昨晚二叔跟我说如果今天天气适合的话就带我去海边的养殖场,去看看那些大个头的鲍鱼养在什么地方,二婶昨晚显得有些忧心忡忡,台风临近,养殖场就像是暴露在风暴中,毫无抵抗的能力,只能祈祷风浪不那么猛烈,倒是二叔淡然地说,要是台风真的来了,谁也逃不了,别自己给自己添堵了。二婶有点不高兴,每次台风暴雨你什么时候担心过了?都不是我一个人在操心!二叔点点头,我知道你操心,放心吧……这几年哪个台风哪场暴雨让你家赔钱了?我们那是风水宝地,不怕台风!二婶不屑地看了二叔一眼,净说胡话。
我觉得自己在霞美镇的生活就是睡觉、吃饭、上楼、下楼、洗澡……一点实质性的内容也没有,倒是看着昱倩天天上补习班,回来作业一份接着一份,心里竟然羡慕起来,高考结束到现在我不知道把十二年来学的东西扔掉了多少,好像是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一般,如释重负。我还记得高三最后那段时间,凡是高考不考的无论题目简单还是困难,一律不管;至于那些要考的,每天几十遍地重复着,到了晚上闭上眼睛,那些公式数字会排着队从你脑海里唱着歌跳着舞走来走去……然而就在一瞬间,烦躁、不安、抑郁、甚至是疯狂,都突然不见了,那种以前没有将来不知道还有没有的激情就这样离我而去,离开的时候还告诉我,你被无罪释放了。但是那一刻才突然觉得,我要的不是这样,就像布鲁斯在肖申克监狱被关了四十年,等到走出监狱外时才赫然发现,自己的世界早就不复存在了。
我是怎么了?回过神来,我问了自己一句,或许是刚刚和同学的聊天勾起了我的回忆,那些我原本以为自己所憎恨的,原来早就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怀念那些六点钟起床的日子,我怀念有那么大一群人在教室里打闹的日子……但我无能为力。
下楼吃午饭的时候我可能看上去郁郁寡欢,二婶问我是不是不舒服,我搪塞道,天气阴沉沉的有些闷。她说她也不喜欢这种天气,给我盛了饭,昱倩还在楼上舍不得下来,二婶说不用理她,等她饿了再训她,我笑着叫二叔进来吃饭,他说看个新闻。二婶就笑了,说,父女一个德行。
二叔吃饭的时候说,陈德厚没打算退出选举。
二婶夹了菜,许久才说,真想不到。
昱倩这才刚刚下楼来,二叔说,你不是不吃了么?昱倩哼了一声自己盛饭去了,二叔接着对二婶说,我也觉得夸张,刚刚沈利说的时候我还以为听错了。
二婶说,出了这种事你说还有几个人会选他,他哪里来的心思。
二叔说,你别出门到处发表见解。
二婶不屑地说,我才不是那种人!我说你还是少寻思人家的家务事,这天气……你跟养殖场那边打过电话没有?
二叔不紧不慢地说,打了,没什么影响。
二婶说,你就这个性子,什么都不担心。
二叔笑了,没影响我担心什么?这不是没事自找烦恼嘛。过了会儿他对着我说,寒阳,看来这天气去不了养殖场了,今天早上渔船都被通知回港避风了。我点点头说,没关系。二婶问我,寒阳你说你明天就要回去了?我说,是啊,后天得会学校领档案。二婶说,这才住了几天,开学还有那么久时间怎么急着去领档案?我说,领档案有时间限制,而且同学说要聚会……二叔说,同学聚会得去,没关系,反正领完档案你再来。我点点头。
天色阴沉,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我在前厅里看电视,昱倩又在楼上,二叔在整理药柜,时不时停下来看看电视,看上去很是悠闲,下午的时候两个中年妇女撑着伞走进了庭院,二婶从塑料椅上站起来去开玻璃门,告诉我是邻居。
二婶说,你们今天怎么有空呀,没有去挖蚵呀?
稍微胖点的那个阿姨说,今天下雨了,蚵场闷得慌,干脆就停工了。
二婶说,坐吧我给你们洗点水果,这个是我侄子。
我叫道,阿姨。
两个人都坐了下来,我放下手里的遥控器给她们泡了茶,二叔说,你们家的养殖场怎么样,应该没什么大碍吧?
那个稍瘦的阿姨说,今早去看过了,这个风浪没那么猛应该没什么事。
胖点的阿姨说,这个台风来得真不是时候,我刚刚给鲍鱼喂了菜,鲍鱼都还来得及没吃呢。啊……嘉义啊,今天早上你去陈德厚家里了么?听说乾婷晕过去了好几次。
二叔说,没有,他们没有叫我去,我不好去,怕给添乱。
二婶端着水果出来了,瘦阿姨说,是够乱的……我说啊,真惨啊。
胖阿姨接下话茬,我就想不明白,陈德厚怎么就还想着当村长。
瘦阿姨和二婶同时说道,我也不明白。说罢二婶摇摇头,问二叔道,这日子难过了,朋逸是独生子对吧?二叔点点头,是啊,而且我昨天听陈德厚他弟媳说了,乾婷已经结扎了。
二婶说,就算没有结扎,这个年纪了还怎么生。
胖阿姨说,你们说陈德厚是不是舍不得那些砸下去的钱啊,而且陈金鸣真的拿了十五万吗?这也太不厚道了,这下可好,乱成一锅粥了。
瘦阿姨说,哎哎不管说什么,我可亲耳听沈利说了他要是选上了村长,海场那边要专门有人管理,要降低台风对养殖场的影响,还说了给全村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每个月发生活费,我说啊,年轻人就是有干劲……她突然压低嗓门说,你看看陈德厚当了几届的村长了,净给自己家捞好处,连条路都修不起来,搞什么办厂,都给外面的商家赚了去。
二婶笑了,说,丽姐你就是这样,这话可不能在外边说。
胖阿姨说,在你家说有什么关系,哈哈!
二叔把所有的药柜整理好了,从柜子后边走了出来,坐在另一把塑料椅上喝起茶来。
二婶说,幸亏这个雨不是很大,小风小浪的没什么大碍,不然养殖场那边就有得忙的了。
胖阿姨说,嘿我说你怎么净爱瞎操心,我老寻思着沈利说要建海坝防风浪,还有换新的养殖网给大家降低损失……听着真是让人心痒痒,年轻人有文化就是好。
瘦阿姨说,怎么听着像你没文化似的。
二婶哈哈笑起来,胖阿姨说,我啊,你看看我长得这么粗智商肯定不高。这下大家都哈哈笑起来,二叔都笑出声来了。我在一旁听着,看庭院里雨还在下,天色阴沉,阴沉得看不出才四五点钟。
不知道怎么的,我心里突然冒出一句“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苦情”,瞬间感慨不已。
五
早晨吃完饭的时候,班长又给我打了电话,我站在一楼的前厅里把电话接了起来,她说,方老大你人在哪里?我笑了笑,不敢当,洪大人您有什么吩咐?她说,我告诉你哦,时间改了,明天大清早我们和苏老师去爬山,应广大群众要求,我现在邀请您参加。
我说,苏老师有这个闲情啊……我在遥远的海边小镇呢,明早几点?
她说,六点钟就再云岩山下出发啦,不然该热死在半山腰上。
我说,行……我下午回去,明早六点钟之前一定到云岩山脚下,南门对吧?
她说,对,南门,挂了啊。随后耳边只剩一片忙音,不知道家里那边是不是放着晴,这台风天的怎么会安排去爬山呢,我回过头去看了一眼长椅上病人的挂瓶,还有大半,据说这瓶氨基酸是补充营养的,二婶交代我看着那点滴瓶,要是见底了记得叫二叔给换下来。二婶出诊去了,二叔正在注射室里给一个小孩打针,刚刚还寂静得很,现在那孩子开始哭闹起来,孩子的母亲正在找各种借口让孩子安静下来,反倒是二叔,一声不吭。昱倩今天还是没去上课,台风的架势愈发猛烈,今早吃早饭的时候,二婶满面愁容,看来是担心养殖场那边的情况,二叔说他待会儿要去一趟,眼下没有功夫抽身。
庭院里到处都是积水,这场雨从昨天下起来就没有停过,到了今天反而有越下越大的趋势,沿海一带的风都大,这下刮得呼啦啦地响,雨点都是斜着的。
我看了一眼挂在电视上边的时钟,九点半钟,二叔从注射室里走了出来,那孩子正在嚎啕大哭,脸都憋红了。泪水还挂在脸颊上,他母亲给了他一颗糖,紧紧拽在手里,瘪着嘴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
二叔和那打点滴的男子说,十点钟选举,这雨怎么越下越大了。
男子说,点滴十点钟前能打完吧?
二叔道,马上就打完了。
男子说,今天选举,陈德厚少了他那个快嘴巴的老婆,估计连话都说不出来。
二叔说,这不刚刚遇事了,大家都能体谅。
男子说,人家都说啊,陈德厚不要命!儿子没了还想着当村长。
给那个孩子包了药,看着母子两人在雨里撑着伞走了,二叔回过头说,也不知道陈德厚他是什么想法,要是想拉同情票就太夸张了。说话的间隙,二婶回来了,在门廊上从身上拿下雨披走了进来,看了看点滴瓶说,差不多可以拿下来了。男子点点头,二叔对二婶说,待会儿怎么去?二婶答道,是在村委会……我看着也不远,干脆就走过去吧。二叔回过头来对着我说,你要不要去玩一趟?我想了想答应了,过了一会儿,我和昱倩撑着一把伞跟着二叔走在马路上,去了村委会大楼。
村委会楼前是片大空地,放着两个简易篮球架,地上都是积水,二楼的栏杆上拉着红布条,写着“霞美镇美南村选举投票点”,走廊上庭院里站满了人,吵吵闹闹的,大家看见我们走过来,纷纷和二叔打招呼,有个和二叔一般年纪的人告诉我们,投票间在一楼的最右侧的房间里,十点钟准时开始,昱倩说要去上厕所,要我和她去,绕过村委会大楼走到了楼后,几个不大的洗手间并排在一起,待我们回到前面的空地上,投票已经开始了,我和昱倩走到走廊上进了一个门口贴着“休息室”红纸的大厅,几个妇女看见昱倩就招呼我们过去,有个妇女问昱倩,你妈妈怎么没来?昱倩说,等我们回去了她才来,她在看店。
这房间的地板是灰白色的瓷砖,下雨的缘故,现在混着泥水到处肮脏不已,水渍斑斑。房间里弥漫着浓浓的烟味,熏得我的眼睛很不舒服。找了个位置坐下,环视了下房间里的人,却看见好像是陈德厚正坐在角落里抽着烟,边上坐着几个人正跟他说话,我眯着眼睛辨认了下,应该没有看错。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心理作用,这猛的一看,让人觉得和前两日在二叔家里看见的陈德厚相去甚远,头发似乎都没有打理,乱蓬蓬地。显瘦的身材坐在角楼里,透着一股苍老的味道,他身边的人讲着话他似乎没有怎么开口,只顾着吸烟,我收回视线,不好意思这么一直盯着那个方向看。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二叔很快就投完票过来找我和昱倩,他看见了我们,便找了个座位坐下来,和边上几个人聊了起来,房间里说话声汇成一片,热闹极了。雨大了起来,我听见旁边的几个人就开始把话题转到养殖场上去了。
言语之中透出担忧的味道,面色沉重地交谈着。有个老头说,看来这台风不管来不来,都要造成不小的损失了。旋即一片附和声,又有人说,养殖场这个时候的风浪恐怕已经很大了,还有些渔船没有回港。马上有人接下话,不是昨天就通知回港了吗?眼看着今天早上风小了些,几个人又冒着雨出海去加固渔网了,这不是台风尾嘛,不打紧。估计也该回来了,今天投票都是知道的……
十点半光景,二叔站起身,示意我们要回去了。
我们一回到家里,二婶就撑着伞去投票。我上楼去整理东西,二婶告诉我霞美镇只有两班车,一班早上九点钟从门口经过,另一班下午四点钟经过。我把衣服都塞进登山包里,用个塑料袋子把几本书装起来也放进去,整理完了,才从外层的口子里拿出雨伞来,整理妥当便下楼去了,这会儿二婶已经投完票回来了,正在做午饭,昱倩没在楼下,应该在书房里玩电脑。早上没几个病人,现在却都是人,长椅上坐满了人,男女老少都有,我小心翼翼地穿过去,坐在了靠门的那张凳子上。
有人在和二叔说话,那人说,两点钟结束投票。
二叔说,那什么时候开票?
那人说,刚刚我回来的时候来了几个领导,今年说是要把票送到镇上去开。
二叔没有说话,顾着包药,许久才开口,今年这么特别啊……那估计得傍晚才出结果了。
那人说,估计是,领导刚刚去吃饭来了,吃完都不知道几点了。一共多少钱?
二叔答,十块。那人付了钱,说了句走了,便出门去了。直到将近一点钟,病人才陆陆续续地走了,二叔进餐厅吃午饭的时候,二婶把汤又热了一遍,我慢悠悠地吃着,二叔说,今年估计是沈利当上了。二婶在厨房里答道,八九不离十,我就说陈德厚真不知道怎么想的。二叔边吃饭边说,陈朋逸溺水这件事情怎么这么快就过去了。
二婶走出来说,还没过去呢,人家都说陈德厚想当村长想疯了,因果报应的,他儿子才去南塘……
二叔突然呵道,别胡说!
二婶板着脸,又不是我说的。转身进了厨房,过了会儿把汤端了出来,坐到了二叔对面说,我告诉你啊,这回南塘出人命上面都知道了,本来村子里打算给陈德厚一笔钱,说什么精神抚慰金,结果镇里不同意。二叔抬起头问,抚慰金?谁说的?
二婶说,谁说的不重要!我是要说,有人说是沈利去镇里说了什么才不发抚慰金的。
突然一阵良久的沉默,二叔才开口道,沈利没事说这个干什么。二婶不说话,给自己盛了碗汤,过了会儿对我说,寒阳你真下午就走啊?我点点头。她说,这才住了几天时间,车子四点钟才来,你回到家里估计天都黑了,要不明早再走。我说,明早和同学约好了去老师家里,估计没办法了。二叔说,约好了就没办法了,你东西都整理好了么?我说都整理好了。
吃完饭我去前厅里看电视,这种天气没有开空调,前厅里的气温还是明显地降了下来。
将近四点钟的时候,我上楼去取下了登山包,手里拿着雨伞。
二婶在柜台的抽屉里一阵翻找,拿出了几张零钱来,说,零钱当车票省得找钱。我说不用,她硬是塞到我手里。二叔还在厨房里,过了小会儿,他提着个黑色的袋子走出来,说,这里面是几条鱼,还有一些其他的海鲜,带回去。我点点头接过袋子,二婶问二叔道,你放冰块了没?二叔说,放了,这天气没那么快化掉。
车子来了。
四点钟一过,我和二婶就站在庭院的大门外边等车,片刻后,一辆灰白色的客车从笔直马路的斜坡后边冒出头来,二婶说,来了来了。东西都拿齐了吗?我说都拿了,心里却有没有底,好像漏了什么东西似的。二婶挥挥手,车子在我面前停了下来,我走到车上,二婶和二叔在下边说,过几天再来,我点点头示意,车子便开动了。
车子启动的时候,我转过头去看了一眼左边,透过房子间的间隙,我看见了大片的稻田,才几日的光景,来时看见的那些零零星星的绿色似乎都消失不见了,大片的金黄色在阴霾的天空下,隔着雨水像是隔着层雾,安静得让人心慌,我努力地望了望稻田,看见了那棵扭着枝干的大树,却看不见水塘。
等我回过神来转过头去看二叔家的方向时,早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雨还在下,我关上车窗的时候看到玻璃车窗上都是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