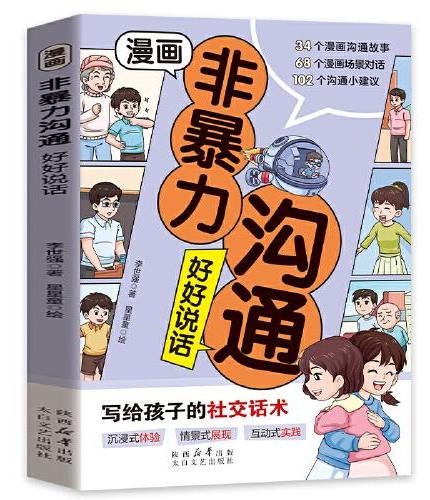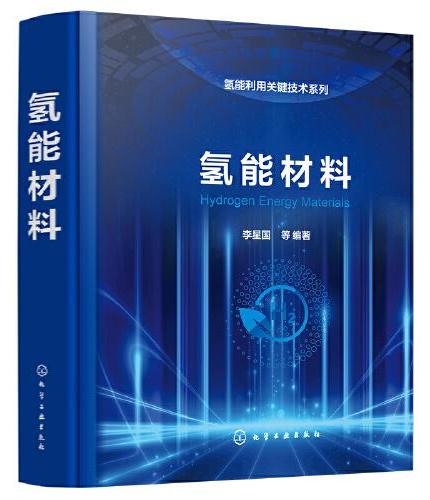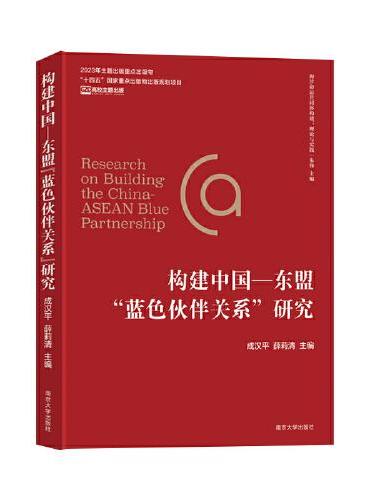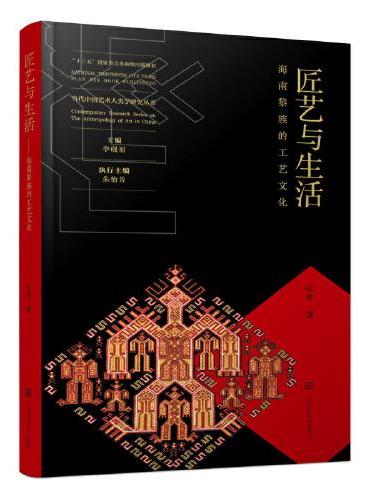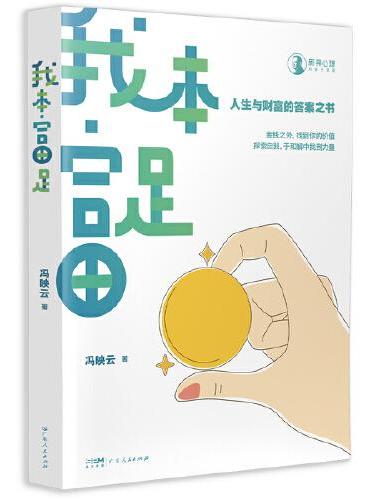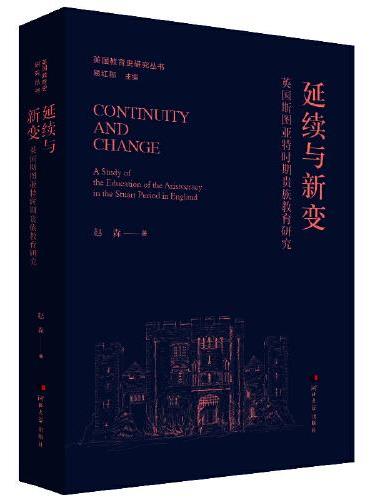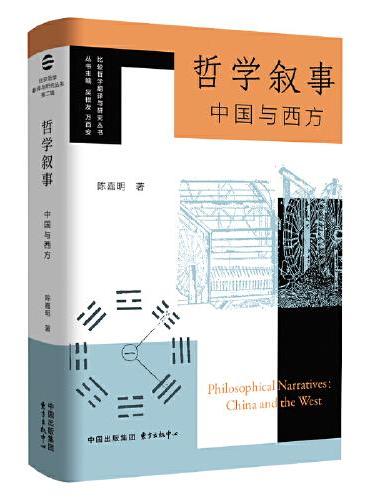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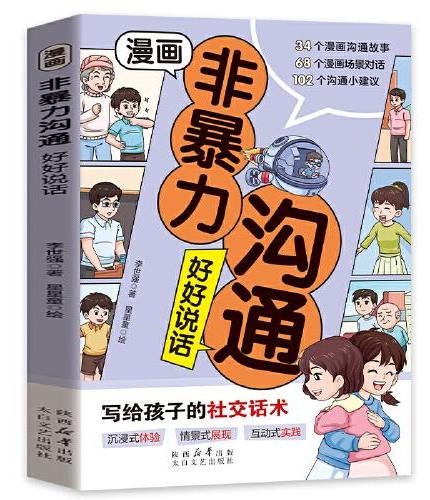
《
漫画非暴力沟通 好好说话写给孩子的社交话术让你的学习和生活会更加快乐正面管教的方式方法 教会父母如何正确教育叛逆期孩子 用引导性语言教育青少年男孩女孩 帮助孩子拥有健康心理的沟通方法
》
售價:HK$
5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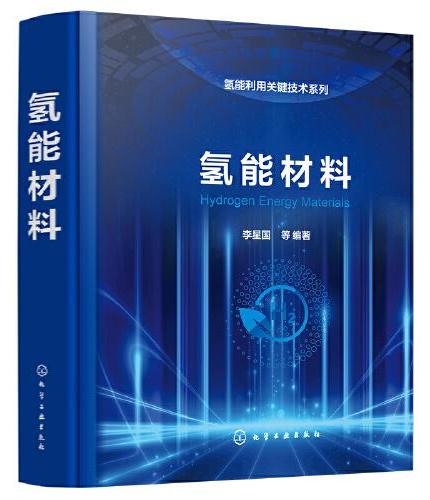
《
氢能利用关键技术系列--氢能材料
》
售價:HK$
39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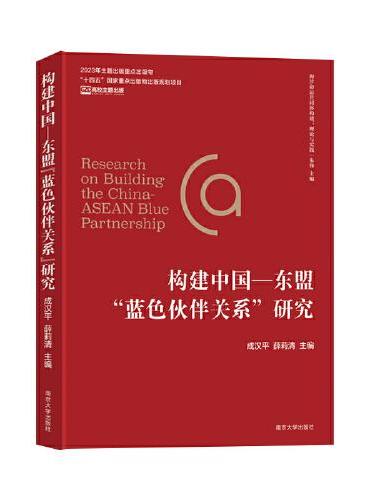
《
(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 理论与实践)构建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研究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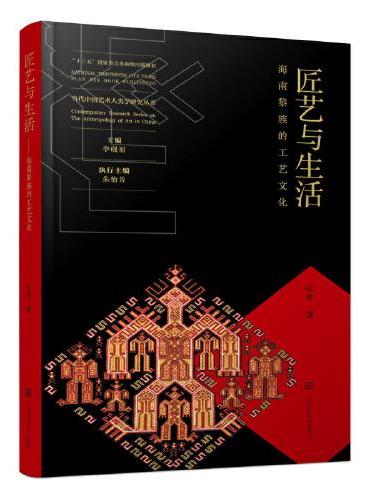
《
匠艺与生活:海南黎族的工艺文化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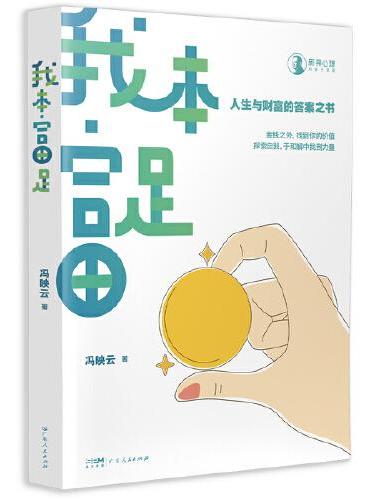
《
我本富足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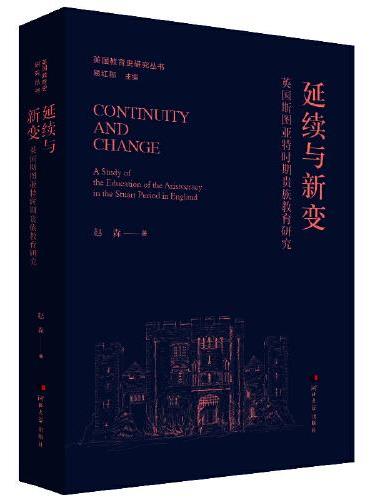
《
英国教育史研究丛书——延续与新变:英国斯图亚特时期贵族教育研究
》
售價:HK$
108.9

《
更易上手!钢琴弹唱经典老歌(五线谱版)
》
售價:HK$
5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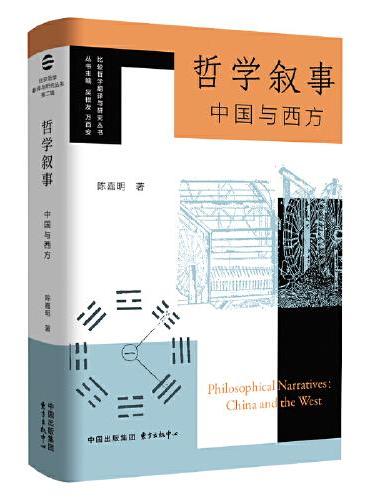
《
哲学叙事:中国与西方
》
售價:HK$
107.8
|
| 內容簡介: |
|
王安忆的长篇小说《启蒙时代》是一部关注和审视成长的小说,确切地说,是“老三届”的精神成长史。本书是对其的精彩讨论,既有作者王安忆和张旭东的长篇对谈,也有张旭东对文本和启蒙问题的深入分析,更有王安忆对小说“虚构”功能的畅谈。本书对理解小说、理解王安忆的创作理念会有相当大的助益。
|
| 關於作者: |
|
张旭东,1965年生,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95年获美国杜克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为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研究系教授。主要中文著作有:《批评的踪迹: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通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等。英文著作有:《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后社会主义与文化政治》等。
|
| 目錄:
|
成长·启蒙·革命
关于《启蒙时代》的对话王安忆张旭东
“启蒙”的精神现象学
谈谈《启蒙时代》里的虚无与实在
张旭东
“谁”启“谁”的蒙?
关于《启蒙时代》的讨论
罗 岗 倪文尖 张旭东等
虚构与非虚构
王安忆在纽约大学东亚系的座谈
|
| 內容試閱:
|
成长•启蒙•革命
关于《启蒙时代》的对话
王安忆 张旭东
“有写大东西的欲望”
张旭东:从《长恨歌》、《富萍》,经过《桃之天天》、《遍地枭雄》,《启蒙时代》你又转回到写60年代的上海。为什么会挑这样一群人物,写他们的成长、自我教育和“启蒙”?从题材上来说,最早说你是知青作家,有上山下乡的背景,但《启蒙时代》完全是在城市里面。从《长恨歌》之后你就被人认为是上海的代言人,但那个上海包括了49年前的上海。《启蒙时代》背景却是“文革”初期,只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你是怎么决定写这样一部作品的?
王安忆:怎么想起来写这样一个故事?《长恨歌》之后,《富萍》《桃之天天》都是一些小长篇,十几万字。我非常重视的,不是你有一个大的故事要写,或者说你有一大段时间供你写,而是你有一大的欲望。写大的东西是需要有一个大的欲望。前面几个篇幅都不是很长,故事都是比较轻盈的,到了这一个——2005年夏天开始动笔,这时候觉得有一种欲望,想写一个大的东西。有的时候事情是从外部来决定的,想写一个大的东西,先是规定了它的体量和内涵。于是,找到这样一个大时代的故事。
这个年代的故事,我还没碰过。有些评论家,如陈思和说的,这是一个好现象,我又回到原初写作状态,写和自己经验有关的东西。像《长恨歌》也好《富萍》也罢,和自己的经验是有距离的,是比较客观地写一个别人的故事。而我写作的开端是与自己经验离得比较近的。很可惜的是,当自己还不怎么会写的时候,消耗了很多材料,经验性的材料。比如说《六九届初中生》,那就是和自己的经验贴得很近的,里面的人物和我同年龄,经历的事件也差不多,但这种感性的经验在长期的写作里面被消耗得差不多了。
《启蒙时代》的故事一方面是和经验有关,那个时代是我已经有认知能力的时代;另外一方面,又和我有点距离,因为小说中人物的经验是我不曾有过的,就我们所见,他们好像是那个时代的主流,而我是旁观者。 张旭东:我想问的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六九届初中生》是在一个很个人的意义上展开的,是基于个人经验,熟悉的生活……但是你现在经过这么多年,再回到这样的年代、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环境,这就不完全是一个纯粹个人的东西了,而是不可能不带有一种意识、表达的欲望,一种历史判断。有没有这一层因素?
王安忆:有时候我们受到暗示,所以就很难断言欲望一定是自然发生,其中有自觉,也有不自觉。自觉的是说想写大东西,从《长恨歌》以来都是写小的东西,就想着应该写大的东西了;不自觉的,就是那些受到暗示的结果。比如说,青春、文化大革命、激进政治,总是以重大意义体现在意识里。这些年里的价值观的变化,推动了现实批判的诉求,也是重大的。于是,你的欲望便扩大了。
张旭东:这次回国之后,跟一些人谈起过这部作品。我告诉他们我非常喜欢它,但有些读者觉得,你在写一个你并不熟悉的东西。他们中有人会说,王安忆对“文革”、上海红卫兵到底有多少了解,是不是真正了解?
王安忆:我承认是弱项。但是对他们理解的也不是完全认同的。这个小说里,我对自己有几个挑战:第一,我其实是不适合写历史事件的,从来不适合写大的事件;第二,我也不大擅长写男性。你们可以看到在我的小说里,凡是男性都很类型化,比如说《叔叔的故事》,不像写女性那么生动具体。这也是我一个不擅长的地方;再一个挑战是经验上的隔离。我确实没参加过红卫兵,你要说对红卫兵运动,我确实没有亲历的体验。但是对人们的质疑,我有两个回答:一个是在这场运动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在自己的位置上都有所见所闻。每个人完全可能会有自己的描绘;还有一个回答是我和他们参加过红卫兵运动的人,也许有不同的想法。我不认为这场革命有多少思想的含量。当然我不能说我自己做过很多调查,只能说我做过思考。这一个评价也许是不让亲历者满意的。
2007年“五一”长假在大连开《启蒙时代》研讨会,薛毅有一个对我的批评的发言。他对我非常不满意,觉得我的启蒙里面不包含毛泽东主义的启蒙。怎么讲,我觉得他是有点要重新塑造这场革命。薛毅是70年代生人,离“文革”更远,他难免会想象这场革命企图汲取某种思想资源。我个人不以为这场文化大革命有多少思想含量。我对当时的事情或者不了解,但是从以后来看,它并没有留给我们什么思想果实,甚至,我觉得我们今天很多的问题都是在当时那些没有品质的政治事件中遗留下来的。我并不是政治性非常强的一个人,也不太敢发表这种言论,完全可能有人运用更多的材料、概念来说明这场革命的意义。对于这场革命,每个人都有太多的意见要发表。我也没有企图正面去表达这场革命,我没有身经其中。但是至少在上山下乡运动上,我汇入了文化大革命。
张旭东:我感觉这篇小说本不是要以现实主义手法去再现“文革”……更不是历史题材的小说……
王安忆:对,不是现实主义题材的。这场革命我觉得也轮不到我去发言。
《启蒙时代》写作和阅读有时候会有差异,这部长篇最早是在《收获》上发表的,所以我和《收获》的编辑是最早交流意见的。她就问我一个问题:“对你来说,哪些方面是你不够满意的?”我说我总觉得不满意的地方是第三章,舒拉、舒娅姐妹,珠珠、丁宜男,一串小女儿。可是很奇怪大家都觉得那一章是我写得最自如的一段,认为这一段最有趣味,这其实就是一个生和熟的问题。我为什么觉得不满意,可能是太熟了。没有新鲜劲,熟极而腻的感觉。但是又跨越不过去,我这个人发力比较晚,一般都是后发的,我一定要让南昌和这些女孩当中的某一个发生肉体关系,可是是谁,一直没有选择定,或者说这个人一直没有产生。我特别需要事实的合理性,不肯迁就,准备过程难免冗长,先写的是舒拉,又写了珠珠,然后丁宜男,最后是嘉宝。就想把那个过程快点过完。
张旭东:对,写的像是一个梗概。就好像对课上的学生说,反正你们已经知道我在说什么,给几个词交代一下,有很多类似梗概和提示这一类,另有一些是新鲜的东西,客观造成什么效果呢?我给你写过E-mail,说《启蒙时代》跟《长恨歌》相比,是个大东西,而《长恨歌》是个相对比较小的东西。在形式的那个最基本的意义上,《启蒙时代》有点儿像你所有小说的一个总汇,提要,index,索引,目录,从中可以引发出去,找到你其他小说内容的原点和原型。它也好像在告诉读者,这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进一步发挥出来,如果你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感到了什么,你想再多读一些的话,你可以去读王安忆的其他的作品,比如《长恨歌》、比如《“文革”轶事》、《桃之天天》等。我们再回到你前面所说的要写一个大东西的欲望的问题。为什么这个欲望指向了“文革”和启蒙这个问题上,不是落在自己相对更熟悉的问题上?《启蒙时代》在技巧上、素材上,都是一个综合的、全景图的写法,在人物上尤其是群像和画廊式的笔触,但是这个综合的东西,又落在这样的一年,这样一群中学生身上。在上海和“文革”的大背景下,你的选择好像是经典现实主义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不过这不是通过一个长时段来构造叙事矛盾,而是在一个瞬间,即一年之内的“空间”里描写和安置这样一群人、这样的故事,用来做你写作的阶段性总结。
王安忆:这里面其实是有着极大的局限性的。我们所以这么写,不那么写,很多时候是出于无奈。小说里的时间你们要仔细打量其实是可以打量出来的,红卫兵过去了,上山下乡还没有来临,正好是两次大规模青年学生运动中的一年间歇。这一年间歇暗合了我的个人经验。当时我是个小学生,前面的红卫兵运动我参与不进,后面的参与,上山下乡已经是另外一个话题了。这一段时间却是我可以参与到这个时代里去的,红卫兵落潮,青年们闲散到社会上,正与我的处境相符。这是一个无奈,人的写作都是这样,只能在自己的写作局限性里开拓可能性。我就给了这段时间很多的意义,我倒是真觉得,这平静的一段,正好是供给思想活动的。有很多人质疑,为什么叫启蒙时代,想不通。因为人们公认这段时间是最苍白的,最混乱的,根本不可能给人启蒙的,尤其是陈思和,极不同意给这时代“启蒙”的命名。这的确是一个奇异的时代,世界大战期间都没有这样,学校全面停止教育。这对教条主义意识形态来说,说不定是福音呢,给一个机会和时间去自己感受生活。我写这些孩子——主要是写南昌,我就是让他自己的感性和这个世界接触。
南昌的任务最沉重,他这个教条主义,处境恰恰最复杂,他的身份最可疑,认同身份的过程,就是他认同这场革命的过程,或者反过来说,认同这场革命就是认同他的身份。刚才你问我,为什么这个故事里的主角是男性,把男生作为写作对象。好像那个时代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些有思想的、高年级的男生的身影,他们是这个时代的主角。我们都是边缘上的,只能看他们。也不排除,和青春期的前兆有关,对异性生出模糊的向往,就像小说中的舒拉。这么多年,我从《长恨歌》过来,好像在外面兜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个人经验。从《纪实与虚构》之后,我基本就和我自己的个人经验保持距离了。
张旭东:因为一些朋友知道我最近在读《启蒙时代》,一直追问我感觉怎么样。我对他们说,我觉得王安忆现在是在写她真正该写的东西了。这当然是一个不准确的说法,但其实我们知道,人虽可以把一些事情做得不错,但并不一定就找到了自己真正应该做的事情。在一个大语境里,在文学史的意义上,甚至在世界文学生产的意义上,当代中国作家到底在哪些方向上是不可替代的,哪些东西他们不写就没有人能写了,再具体到个人,每个人写作在内容和形式上真正不可替代的东西,或者说是使命,还是需要在批评的意义上考虑的。我觉得《启蒙时代》已经指向一种你不得不写、非你来写不可、不写就辜负了自己的使命的东西。
王安忆:说实话,在刚开始写的时候还茫茫然的,但是写出来之后,很多人跟我说,我又回到自己的内心。和自己的内心生活有关系的写作,对我倒是个提醒,自己写的时候,人在事中是看不清楚的,我当时就是想写一个大的东西。但是也能感觉到这个故事是和自己的经验、感情有关的。
张旭东:刚才提到的那个“深”,你说你要写一个大的东西,深的东西,但是你刚才又说,这个《启蒙时
代》中的革命本身是没有品质、没有内涵的,在思想上是非常空洞苍白的,这帮小孩说到底是闹着玩的,一场闹剧。那这个很深的东西和很浅的东西、很大的东西和很小的东西、很激烈很有内涵与理想的东西和空洞、苍白、不明就里的东西是怎么糅合在一起的呢?
王安忆:这又和我的局限有关。我没有正面参加这场革命,我不知道人物在这场革命里应该做什么。
张旭东:因为革命是个太大、太抽象的东西。
王安忆:在个人其实又是具体的,但这种具体的性质,又常常被从革命中剔除,不被当作革命的属性。我们这些人,虽然没有开宗明义说要表达“文革”,我们对“文革”不敢说有什么认识,可是我们都是被“文革”塑造出来的,整个成长时期是在“文革”里面度过的,我们就是在乱世中长大。所以这场革命对于我们来讲,它几乎不是客观的,它跟你的日常生活经验连接在一起。所以非常矛盾,一方面,我完全不了解这场革命里面的事件,对外的路线斗争,对内的派系斗争究竟是针对什么人,什么事,我始终没有搞清楚,也终于放弃搞清楚的企图。而另二方面,作为一个历史时期,我也是亲历者,我也看见了,看见的是什么?革命时期的生活。
倘若努力思考这场革命,我觉得有两点强烈的印象,是许多年以后慢慢回过头去的时候显现的:一个是激进政治,一个是教条主义。这两点越来越鲜明。我在想他们,南昌为首的他们这帮人,首先是要治疗这种病。这个小说,因为不是自己特别熟悉的,不能够得心应手地,随时可以生发出细节、人物,我非常挑战自己,给自己出了一个大难题,就是放到一个空白里面去构造故事,计划性很强。
张旭东:能感觉到,很用力。而且,因为是在一个“空白”里面来写,作家就必须把自己所有的积累、能量、想象和技巧调动起来,最终把自己的“政治无意识”调动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而不是在简单的题材、主题意义上,我说我觉得你在写一个大东西、一个真正应该写的东西。
王安忆:努力在调动,一直在想,想我应该怎么安置我的人物,他们都应做什么,他面临的任务我很清楚,可是怎么完成他的任务,怎么达到他的目的,又很模糊。
张旭东:还有一个很表面的感觉,读《启蒙时代》的经验让我想起少年时代读19世纪俄国小说的经验,它里面大段大段地有类似俄国小说的东西,我是说阅读经验上的相似性,比如有的地方情节进展很慢,几乎陷于停滞,取而代之的是那种思想和内心矛盾的空间,行为的世界难以展开,但心灵世界里的悸动和骚动变成了时间的单纯内容。这让人想起我们读俄国文学的经验,《罗亭》、《前夜》、《父与子》;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在这些作品里,主人公可以一夜不睡,就谈理想,谈爱情,谈改造社会,谈革命,最后当然什么结果也没有。但对年轻人来说,甚至对一个时代来说,这一夜的空谈,有过和没有过是大不一样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