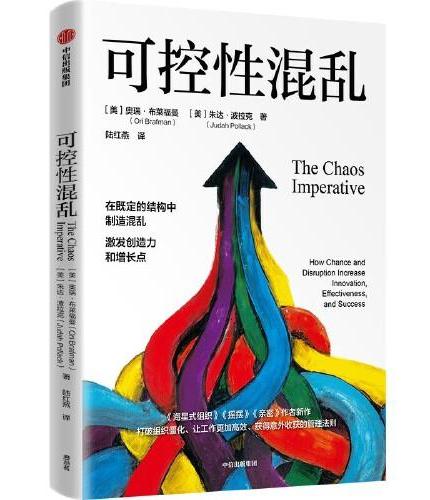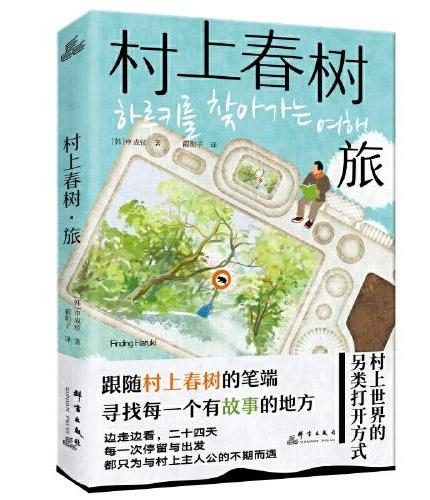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小时光 油画棒慢绘零基础教程
》
售價:HK$
8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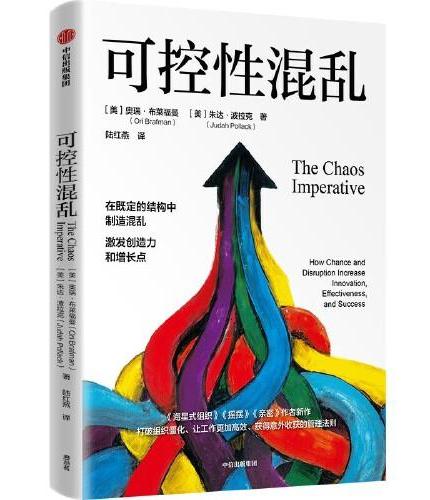
《
可控性混乱
》
售價:HK$
66.1

《
篡魏:司马懿和他的夺权同盟
》
售價:HK$
65.0

《
狂飙年代:18世纪俄国的新文化和旧文化(第三卷)
》
售價:HK$
177.0

《
协和专家大医说:医话肿瘤
》
售價:HK$
109.8

《
潜水指南 全彩图解第4版
》
售價:HK$
132.2

《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从工具到实例
》
售價:HK$
8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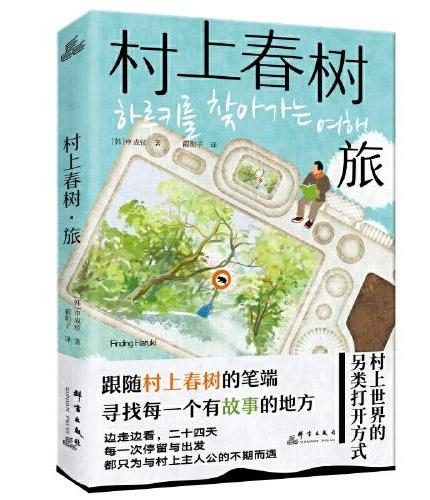
《
村上春树·旅(一本充满村上元素的旅行指南,带你寻访电影《挪威的森林》拍摄地,全彩印刷;200余幅摄影作品)
》
售價:HK$
66.1
|
| 編輯推薦: |
|
《外国中短篇小说藏本果戈理》集中展现了果戈理从早年的活泼幽默到晚期“含泪的微笑”的创作发展过程,值得反复阅读,细细品味。
|
| 內容簡介: |
|
《外国中短篇小说藏本果戈理》分别从《狄康卡近乡夜话》、《密尔格拉得》及《彼得堡故事》中收录了果戈理最具代表性的中短篇小说:《塔拉斯布尔巴》、《涅瓦大街》、《鼻子》、《肖像》、《外套》、《狂人日记》等,这些作品中既有轻松的幽默、乐观的欢笑,也有无情的讥诮和“含泪的笑”,更有因残酷的现实而引起的痛苦而又愤怒的笑。
|
| 關於作者: |
|
果戈理(18191852),俄罗斯作家。出生于乌克兰波尔塔瓦附近的索罗庆采村,祖先是来源于乌克兰的小贵族,具有波兰血统。善于描绘生活,将现实和幻想结合,具有讽刺性的幽默,他最著名的作品是《死魂灵》和《钦差大臣》。
|
| 目錄:
|
狄康卡近乡夜话
序言
圣约翰节前夜
圣诞节前夜
密尔格拉得
旧式地主
塔拉斯布尔巴
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
彼得堡故事
涅瓦大街
鼻子
肖像
外套
马车
狂人日记
|
| 內容試閱:
|
狄康卡近乡夜话
养蜂人鲁得潘柯
印行的故事集
“这是什么奇怪可笑的东西:狄康卡近乡夜话?这算是什么夜话并且是一个养蜂人投到世上来的!老天爷保佑!仿佛把鹅毛拔掉做鹅毛笔,把破布做成纸张还不够尽兴似的!仿佛各种各样的人把墨水涂污手指还涂得不够多似的!居然一个养蜂人也想学起别人的榜样来了!怪不得现在印成的字纸这么多,一时都想不出用它来包什么东西好了。”
我在一个月前早就预感到有人会说出这一番话来!说真的,像我们这些乡下人,要从穷乡僻壤把鼻子伸到上流社会里去嗳呀,老天爷!那就正像有时候走到一位大老爷的府邸里去一样:大家都来围住你,耍弄你。要是上房里的仆人呢,那倒也罢了,不呀,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小鬼头,在后院里打杂的家伙,也要来跟你麻烦;人们从四面八方向你顿脚,问道:“往哪儿走往哪儿走怎么啦乡下人,滚出去……”我跟你们说……可是还有什么说的呢!我情愿每年上密尔格拉得去两次,也不愿意挤进上流社会,密尔格拉得的地方法院审判官和神父已经有五年没有看见我了。可是要是挤进了上流社会呢那么不管怎么着,你总得回答一连串的问话。
在我们这里,亲爱的读者们,不怕玷辱你们的耳朵你们也许要生气,一个养蜂人不应该这么不客气地跟你们聊天,像跟一个亲家或者密友谈心一样,在我们乡下,世世相传有这么一种习惯:等到地里的活一忙完,庄稼人爬到暖炕上去歇冬,干我们这一行的人把蜜蜂藏到漆黑的地窖里去,当天空里看不见一只灰鹤,树梢上看不见一只梨的时候,每当黄昏日落,在街的尽头什么地方一定会亮起灯火来,远远里听见欢笑和歌声,飘来三弦琴,有时候是提琴的声音,人声,喧闹声……这就是我们的夜会啦!瞧,它们很像你们的跳舞会;不过不能说完全一样。你们要是去赴跳舞会,那么,是去活动活动两条腿,用手掩住嘴打呵欠;我们的情形却不同,一群姑娘们聚集在一家人家,根本没打算来跳舞的,她们手里拿着纺锤和梳栉;起初仿佛一心一意干着活:纺锤喧嚷着,歌声荡漾着,大家连眼睛都不往旁边望一下;可是,只要小伙子们带着提琴手闯了进来,立刻就扬起了一片喊声,欢腾起来,跳起舞来,玩出这么许多花样,叫我说也说不尽。
可是最有意思的是,大家挤在一堆,猜谜语或者干脆瞎聊天。我的天!他们讲的是些什么故事啊!打哪儿发掘出这些陈年古话来的啊!他们什么可怕的故事不讲啊!可是别处恐怕再也听不到像在养蜂人鲁得潘柯鲁得潘柯是一个乌克兰语的绰号,意思是“红头发的潘柯”。家里夜会上听到的这么许多奇闻怪谈。村里的人为什么都管我叫鲁得潘柯我可实在说不上来。并且我的头发,看来现在也已经花白,却不是火红色的了。可是,不怕玷辱你们的耳朵,我们这里就有这么一种习惯:给人起了一个绰号,一辈子就脱不掉了。在节日的前夜,乡人们常常光顾养蜂人的茅舍,围着桌子坐下来那时候你们就只管出神地听吧。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些人不是普普通通的人,不是乡下的土佬。即使他们去拜访比养蜂人更高贵些的人物,对方也会引以为荣,觉得蓬荜生辉哩。譬如说,你们知道狄康卡教堂的一个差役福马格里戈里耶维奇么嘿,他真是个有头脑的人呢!他能够讲一些多么有趣的故事啊!有两个故事你们可以在这本书里读到。他从来不穿条纹麻布的宽袍子,像你们看见许多乡村教堂的差役所穿的一样;即使在工作日去找他,他也总是穿着马铃薯冻颜色的细哔叽长褂出来迎接你,这种料子是他在波尔塔瓦几乎花了六卢布一俄尺的代价买来的。至于他的长统靴,整个村子里从来没有听人说过闻到那上面发出焦油的气味;大家知道他用最好的脂油擦靴子,我想,有些庄稼人是高兴把这种油掺混在粥里吃的。从来也不曾听人说过,他曾经像同等身份的人那样地用长褂的前襟擦鼻子;他总是从怀里掏出一块边上绣红丝线的、叠得四四方方的白手帕来,用过之后,照规矩总是把它叠成十二折,重新揣到怀里。还有一个客人……他是这样的一位青年绅士,打扮起来,活像个陪审官或者领地划界公断人。他常常把一只指头伸在鼻子前面,望着手指尖,讲起故事来讲得又斯文又巧妙,就像书本里讲的一样!有时候,你听着,听着,就糊涂了。打死你,你也不明白讲的是怎么一回事。他打哪儿收集了这么一大堆的字汇!福马格里戈里耶维奇有一次给他编了一段有趣的故事,嘲笑他的这种习气:他说,有一个学生跟一个教会秘书读书,等回来见他父亲的时候,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拉丁文学者,连正教的语文都给忘掉了。他碰到随便什么字都在语尾上给加上ус。他管铲子лопата叫лопатус,女人баба叫бабус。有一次他跟父亲到田里去。拉丁文学者看见一把铁耙,问父亲道:“爸爸,你们管这东西叫什么”可是,一不留神脚踩着了钉耙的齿。父亲还没有来得及答话,铁耙的柄反翘起来,一下子打中了他的前额。“可恶的铁耙!”学生一只手捧住脑袋,跳得有一俄尺高,喊道:“这是怎么啦,让鬼把它们的亲爹推到桥底下去吧,打得我好痛啊!”就是这么回事!他把名字记起来了,这小子!文绉绉的说故事人听了这样的故事很不高兴。他一句话也不说,从座位上站起来,双脚叉开,站在房间中央,脑袋稍微往前歪斜些,把手伸到豌豆绿长襟外衣的背后插袋里去,摸出一只圆圆的涂漆的鼻烟匣子,用手指在画得很拙劣的邪教徒将军的脸上弹了一下,倒出一大撮混合着灰烬和独活草的叶子一起磨碎的鼻烟,两只手指弯成一个圆圈,把它送到鼻子跟前,连大拇指都没有碰着鼻子,悬空着就把一大撮鼻烟吸了进去。仍旧一句话也不说。当伸手到另外一只口袋里去,掏出一块方格子的蓝棉纱手帕来的时候,他才自言自语地咕噜了一句几乎像谚语一样的话:明珠勿投给猪有“对牛弹琴”的意思。。“这下子可要吵翻了,”我看见福马格里戈里耶维奇预备把拇指塞给对方看俄俗,把拇指塞在食指和中指的中间,是侮蔑对方的意思。的时候,这样想。幸亏我的老伴儿正在这时候把涂着牛油的、热气腾腾的面包卷端到桌上来了。大家都动起手来。福马格里戈里耶维奇的手也就不去做轻侮的动作,却去拿面包卷去了,于是大家照例夸奖起能干的主妇来了。我们还有一个说故事的人;可是这人夜里不宜提到他有一肚子可怕的故事,说出来时会叫你毛骨悚然。我有意不把这些故事刊载在这本书里。否则的话,老实人会这样地受惊,以后看见我养蜂人,老天爷饶恕我,大家会像看到鬼一样地害怕。要是老天爷开恩让我活过了新年,让我再出另外一本书的话,那时候我可以讲一些亡灵和古时在我们正教国家里发生过的种种怪事来吓唬一下读者。你们在那里面也许还可以找到养蜂人本人讲给他的孙儿们听的一些故事。只要读者有耐心听下去,读下去,只要我的懒脾气不发作,我敢说,写成十来本这样的书是毫不费事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