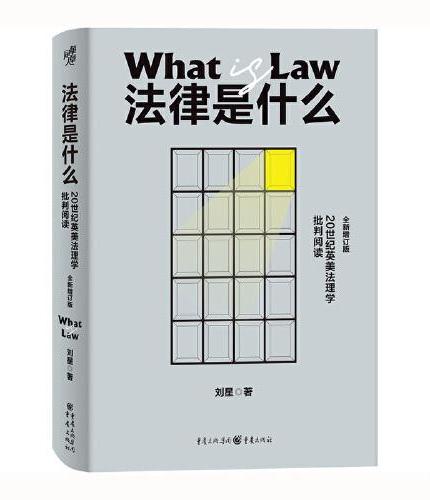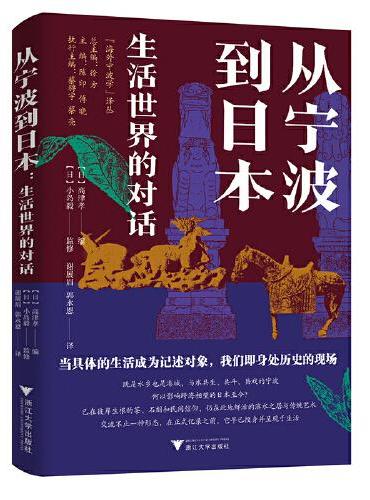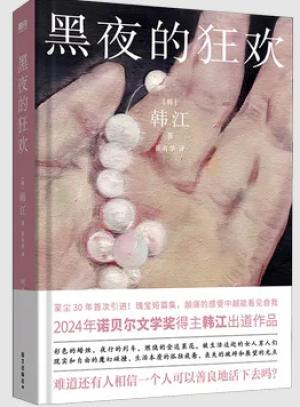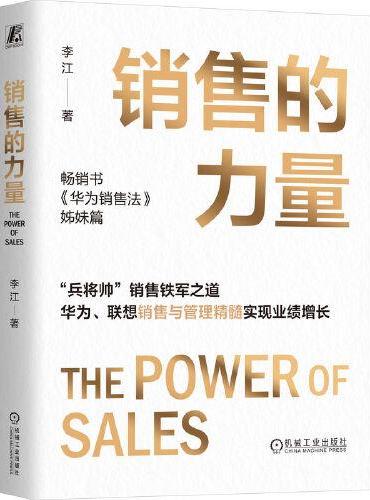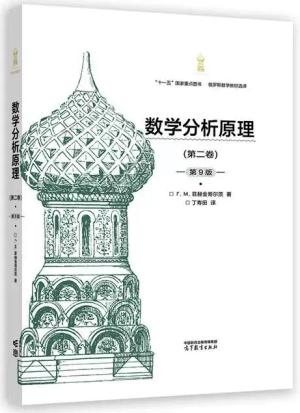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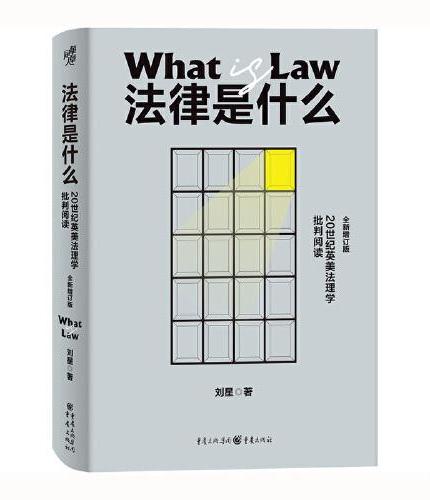
《
法律是什么:20世纪英美法理学批判阅读(全新增订版)
》
售價:HK$
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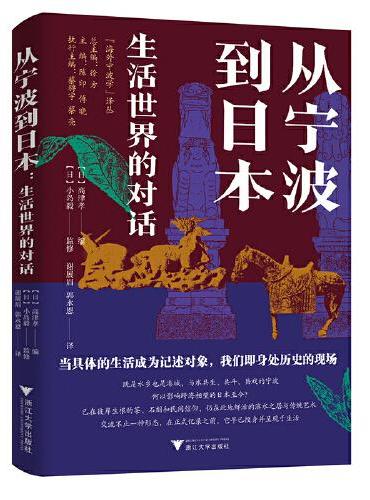
《
从宁波到日本:生活世界的对话
》
售價:HK$
74.8

《
怪谈:一本详知日本怪谈文学发展脉络史!
》
售價:HK$
5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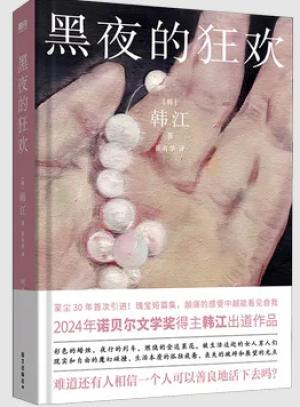
《
韩江黑夜的狂欢: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韩江出道作品
》
售價:HK$
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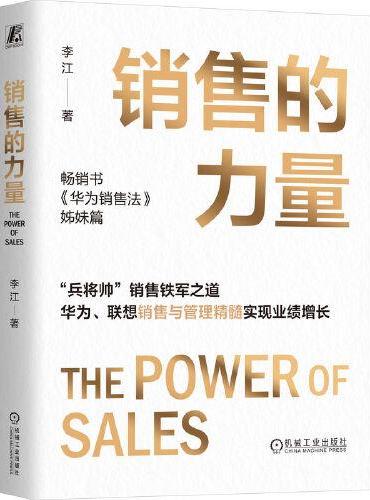
《
销售的力量
》
售價:HK$
97.9

《
我活下来了(直木奖作者西加奈子,纪实性长篇散文佳作 上市不到一年,日本畅销二十九万册)
》
售價:HK$
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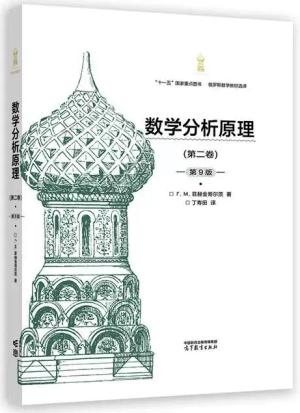
《
数学分析原理(第二卷)(第9版)
》
售價:HK$
86.9

《
陈寅恪四书
》
售價:HK$
316.8
|
| 編輯推薦: |
叶芝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
他一生所写的情诗,都是为了一个女人
全世界都对他青眼有加,她却只肯给他一记白眼
华丽浪漫皆是一位天才赞美令他终生苦涩的缪斯
这个让女人痴迷的王子,那个让女人嫉恨的戏子
叶芝以诗出名。他的散文也处处充满诗意,优美的意象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给。本书精选叶芝散文名篇。
|
| 內容簡介: |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凯尔特的曙光》作者是爱尔兰诗人、剧作家,著名的神秘主义者,是“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领袖,也是艾比剧院(AbbeyTheatre)的创建者之一,被诗人艾略特誉为“当代最伟大的诗人”。叶芝对戏剧也有浓厚的兴趣,先后写过26部剧本。叶芝以诗出名。他的散文也处处充满诗意,优美的意象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给。本书精选叶芝散文名篇。
叶芝早年的创作仍然具有浪漫主义的华丽风格,善于营造梦幻般的氛围,他的散文集《凯尔特曙光》便属于这种风格。
|
| 關於作者: |
|
叶芝,爱尔兰凯尔特复兴运动的领袖。1889年,叶芝结识了热衷于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的茅德?冈小姐。冈小姐非常仰慕叶芝,并主动和叶芝结识。叶芝对她痴心不已,但四次向其求婚都遭到拒绝,尽管如此,他对冈小姐仍然魂牵梦萦,并以她为原型创作了剧本《凯丝琳女伯爵》。1903年,冈小姐嫁给了爱尔兰民族运动政治家约翰?麦克布莱德。十四年后的夏天叶芝和她重逢,并向她的养女求婚,继续遭到了拒绝。同年九月,他改向一位英国女人乔治?海德里斯求婚,两人在当年的十月结婚。
|
| 目錄:
|
凯尔特的曙光目录CONTENTS
青春少年之遐想
四年
帷幕的颤抖
凯尔特的曙光
|
| 內容試閱:
|
一
我最初的记忆纷乱而零碎,没有时间的概念,如同人们对于创世七日之初的模糊印象。这些记忆保留在我脑海中,好像时光不曾存在过一样,因为,一切只与情感和地点有关,与发生的先后并无瓜葛。
我记得曾坐在一个人的膝上向窗外远眺,墙壁表面的灰泥已是四分五裂,不住地脱落。我已经不记得是什么墙了,只是知道有亲戚住过那儿。我曾在伦敦的另一处对着窗外望去,一些小男孩在菲茨罗伊路上玩耍,其中有个孩子身穿制服,也许是个送电报的信童吧。我问他是谁,一位仆人说他每天早上用号子把全镇的人叫醒,然后我惴惴不安地睡下了。
后来是在斯莱戈的记忆,我曾和外公外婆住在那里。我曾坐在地上,看着一条没有桅杆的玩具船,它满是划痕,漆已经被磨得差不多了。我难过地自言自语道:“比原来更长了。”此时,我正盯着船尾的一条长长的划痕,正是这条越来越长的划痕让我说出了那句话。有天吃晚饭时,大舅公威廉?密德尔顿说:“我们不该小看孩子们的烦恼。他们的烦恼比我们的更糟,因为我们能看到烦恼的尽头,而他们看不到。”我很庆幸能察觉自己的烦恼,常常对自己说:“长大了以后,别像大人那样谈论童年的快乐。”我经历过痛苦的夜晚:在连续几天祈祷自己死掉以后,我开始害怕自己真会死去,于是,我又祈祷自己能够活下去。
我没有不开心的理由。没人待我不好,而多年之后我对外婆还是充满了感激和敬意。房子很大,所以我总是能找到躲藏的地方。我有一匹红色的小马,一座可以自由漫步的花园,我的身后跟着两只狗,一只浑身白色,头上顶着黑色的斑点,另一只则披着长长的黑毛。我常常想到上帝,想象着自己是个淘气的小孩。有一天,我在院子里不小心用石头砸折了一只鸭子的翅膀,当大人告诉我会用它做晚餐,而不会惩罚我时,我惊讶极了。
孤独算是种痛苦,对外公威廉?波莱克斯芬的畏惧便占据了其中的一部分。他并不凶,我也不记得他有没有对我吹过胡子瞪过眼,但畏惧和敬仰已经成了我的习惯。他曾经因为救死扶伤而获得几座西班牙城市的荣誉市民称号,但他一直守口如瓶,直到快八十岁时一位老船员过来做客,外婆才知道这事。她问外公这是不是真的,外公说“是”,但对他了解如此之深的外婆并未多问,后来那老船员便走了。外婆对外公同样有习惯性的畏惧。我们知道他去过世界各地,因为,他的手上有一道鲸鱼叉留下的大疤。饭厅的柜橱里有几块从约旦带来的珊瑚、给孩子们施洗的一瓶水、中国宣纸画,还有印度的象牙手杖。外公去世后,手杖传到了我的手里。
外公体魄健壮,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为人称道。他拥有很多帆船,有一次,一名在罗塞斯角抛锚停船的船长报告船舵出了故障,于是让信使传信“派个人来看看哪里出问题了”。回答是“没人愿意”。外公下了命令:“你自己去看看。”被拒绝后,他便自己从主甲板上跳了下去,沿着遍是卵石的海岸一侧游了一圈。他上岸时尽管擦破了皮肤,但对舵的问题已经了如指掌。外公脾气很烈,为了防范盗贼,他在床边备了把榔头,比起诉诸法律,他宁可一锤把人砸昏。我就见过他挥着马鞭追打一群人的样子。外公是独子,所以亲戚很少,孤僻寡言的他也没几个朋友。他和伊斯雷的坎贝尔和韦伯船长保持着通信联系,前者和他的船员在一次海难中和外公相识,而后者则是他的工作同事兼密友。韦伯是第一个横渡英吉利海峡的人,但在尼亚加拉急流游泳时溺水身亡。在我记忆中,外公也只有这些朋友了。但他是个广受拥戴和仰慕的人,当他从巴斯泡温泉回来时,他的手下会沿着铁路燃起绵延几英里的篝火,而他的伙伴、我的大舅公威廉?密德尔顿虽然来来去去,但并不受人注意。威廉?密德尔顿的父亲在大饥荒后的几个星期里照顾病人,有一次,他将一个病人抱回自己家里,却被那人感染了霍乱,后来撒手人寰。他对任何人都是彬彬有礼,为人处世也比我的外公聪明得多。我觉得自己是把祖父和上帝混为一体了。记得有次我在发愁,希望外公能够因为我犯下的错误惩罚我。这时候有个胆大的小表妹在街上的一排树边等着外公(她应该知道外公将近四点去吃晚饭时会经过这里),对他说:“如果我是你,你是个小女孩的话,我会送你个洋娃娃。”我大吃一惊。
尽管对他又爱又怕,但我从来没觉得用智谋打败他的武力抑或是严厉有什么不妥;其他人亦是如此。而且他很少疑心,孤立无助,这让一切变得简单。当我还是个七八岁左右的小孩时,一天,有个舅舅半夜喊我起床,让我骑马赶到五六英里外的罗塞斯角,从一位表亲戚那里借火车通票。外公自己有一张票,但他觉得借给他人用不太好。不过,这位亲戚可要好说话得多。于是,我溜出大门,上了花园旁边一条家里人听不见声音的小道,在月光下欢快地骑着马。午夜时分,我用马鞭打着表哥家的窗户,弄醒了他。凌晨两三点钟我回到了家,发现马夫在小道上等我。外公绝不会想到有人会冒这样的险,因为他相信马厩院子的门都在每晚八点锁上,并且钥匙都得交给他。有些仆人曾在夜里问他要钥匙,于是他吩咐他们要锁好门,但整个家里只有他不知道,门其实从没锁过。
直到今天,当我读到《李尔王》时,眼前总会浮现出他的音容笑貌。我怀疑,我在戏剧和诗歌里描绘的那些有血有肉的人们,他们的喜怒哀乐是不是根据对他的记忆写成的呢?尽管我在童年时并没有看出来,但他一定没啥学问,因为在孩提时代,他常常“从锚链孔钻到海里”——他正是这样描述的。在我印象中他只有两本书,一本是《圣经》,一本是法尔科纳的《海难》,这本绿色封皮的书一直躺在他的桌上。
他是老康沃尔人中一个分支的后代,父亲曾在军中服役,退役后成了几艘帆船的主人。客厅的盾形徽章边挂着一幅版画,外公认为画里的地方是他的老家。他的母亲来自爱尔兰威克斯福德,他的家庭和爱尔兰世代保持联系,一度还染指过西班牙同戈尔韦的贸易。自傲的他很是反感街坊邻居,而他的妻子来自密德尔顿家族,她温柔、耐心,在小小的会客厅里接济过很多穷人。每天晚上外公睡着后,她都会点着蜡烛沿着房子绕一圈,以确信周围没有盗贼会挨上外公的榔头。她热衷于自己的花园,在被家务缠得脱不开身之前,她常会选出几朵最为钟爱的花,然后在纸上画下来。我见过她的手工作品,它们无论从形式还是颜色上,都深深让我折服,而且,这些东西小到只能用放大镜看见。我还记得那些中国画,走廊墙上克里米亚战争的彩图,还有走廊尽头一幅描绘军舰的图画,随着岁月流逝,它比以前愈加黯淡了。
外公膝下儿女众多,这些成年的叔伯姨婶都是和善体贴之人,他们在我的生活中进进出出,言行几乎为我所遗忘。我所记住的,却是一些与他们温和性格大相径庭的“狠话”。我最小的叔叔身材结实,风趣幽默,为了防止漏风,他在大门的锁孔里塞上了皮革质地的鞋舌。还有另外一个小叔叔,他的卧室在石头走廊的尽头处,卧室的玻璃橱里摆放着一只炮舰模型。他很聪明,曾经是斯莱戈码头的设计师,如今却变得疯疯癫癫,在设计一艘“永不沉没”的战舰。他在设计手册上解释道,由坚固木料组成的船体是船不会下沉的原因。六个月前,我的妹妹梦见自己怀抱着一只没有翅膀的海鸟,结果不久就听说了小叔在疯人院去世的消息。海鸟是波莱克斯芬家族有人去世或遇险的预兆。
名叫乔治?波莱克斯芬的舅舅是外婆的掌上明珠,也是我的好朋友,他后来沉迷于占星术,成了神秘主义者。他住在巴利纳,却很少过来。有一次他来参加赛马会,身边还跟着两个穿绿衣服的马车夫。还有,那里也住着借给我火车通票的叔叔。仆人们告诉我,乔治曾经因为用撬棍欺负别人而被学校除名。
印象中,外婆只惩罚过我一次。我在厨房里嬉闹,结果正当外婆进来时,我的衬衫被一位仆人从前裤腰里扯了出来。外婆批评我不知廉耻,把我单独关在一间屋子里吃晚饭。比起外婆来,那些叔父和姑妈们却让我害怕得多。有一天外婆允许我在中午吃饭,但我却被那位拿着撬棍欺负人的小叔发现。他骂了我,让我很是羞愧。我们家九点吃早餐,四点吃晚餐,在两餐之间吃东西会被认为是放纵自己。还有一次,一位姑妈说我在城里骑马时会勒住小马,然后像炫耀似的抽它。她指责我,说我想法不端,为此我难过了一整晚。说到童年,除了痛苦之外我确实不记得什么了。每当一年过去,我都比以前更加开心,好像是在逐渐战胜心里的疙瘩一样。我的痛苦其实怨不得别人,只是我脑袋里的胡思乱想罢了。
二
某一天,有人和我谈到良心的声音这个问题。我思忖再三,得出的结论是我已经失去了灵魂,因为我没有清楚地听见声音。于是我愁眉苦脸地挨过了几天,直到后来和一位姑妈待在一起时,我听见一声低语:“你真可笑啊!”起初我以为是姑妈在说话,但旋即发现她其实什么也没说,我又开心起来:良心的声音出现了!打那以后,这种声音总会在危急关头时浮现在我的两耳中,不过现在,它的出现却如惊雷般突然警醒。它不会告诉我该做什么,而是常常谴责我,比如,“你的想法是不对的。”有一次我抱怨上帝没有听见我的祈祷,它就会告诉我:“上帝已经帮助了你。”
我家的门前立着一根很矮的旗杆,顶上挂着一面红旗,红旗的一角是英国米字旗的图案。每天晚上,我都会收下国旗,叠起来放在卧室的架子上。一天早晨,我在吃饭前发现国旗被打成结系在旗杆的下面,贴在草地上,可我明明记得在前一天夜里就把旗子收下来了。我立刻断定是有仙人下凡,把国旗打成了四个结(一定从前听过仆人们谈论仙人的缘故吧),而且从此以后,我一直相信有隐形人在耳边对我低语。有人说我曾经见到过神鸟,不过我已经没有印象了,也不知道自己看到过几次。还有一次,我和外婆在天黑后乘马车前去斯莱戈五英里之外的海峡。外婆指向一艘闪着红灯、开往外地的蒸汽船,告诉我外公就在船上。这天晚上,我哭号着梦见蒸汽船遇到了海难。第二天早上,感激的乘客为外公找到一匹瞎了眼睛的马,外公便骑着它回来了。在我印象中,外公正在睡觉,此时船长喊醒他,说船要触礁了,外公说:“你们试没试过用那条帆?”从回答来看,船长在接到命令时似乎已是六神无主。在蒸汽船危在旦夕之际,他把船员和乘客转移到了备用的救生小船上。外公自己的船被打翻了,他会水,因此捡了一条命,还救起了几个人;有些妇女靠着裙撑的浮力漂到了岸上。“比起大海,我还是更害怕那个蠢透了的桨手。”一位幸存的校长说。然而,事故中仍然有八个人溺水身亡,这次不堪的记忆也时常折磨着外公的余生。后来每次家庭祷告时,他只会念叨着这场圣保罗的海难。
我对狗的印象仅次于外公外婆。那只毛茸茸的黑狗没有尾巴,如果我没记错,是被一辆火车轧掉的。与其说是狗儿跟着我,倒不如说是我跟着它们,一路走到花园后面的养兔场。它们经常互相厮咬打架,黑毛狗全身的长毛让它屡屡全身而退。在一次残暴至极的打斗中,白毛狗的牙齿嵌进了黑毛狗的皮毛里无法拔出,后来马车夫将它们吊在水桶的里外两侧,一只掉在水里,一只掉在地上,这事才算了结。外婆曾经让马车夫把狗毛剃成狮鬃的形状,车夫和马童讨论了良久,然后将狗的头上和肩膀的毛发统统剃光,只留了下身的毛。于是,狗便消失了一些天,我相信它一定是伤心欲绝。
房子后面的大花园种满了苹果树,中央则是花坛和草地。园子里有两尊船头用的雕像。在被果树挡住的一面墙下,有一片草莓地,其中一尊雕像便藏身于这里,它是一位身着制服的魁梧男子,是外公那艘“俄国”号三桅帆船上的。仆人们都觉得雕像中的男子是沙皇,而且沙皇是亲自将雕像送给外公的。另一尊雕像坐落在花坛里,是一位穿着飘逸长裙的女子。私家车道穿过树丛,从大厅延伸到一座并不显眼的小门,沿路则是一些又脏又破的小屋。我常常觉得应该把这条有着两三百年历史的车道修长些,因为在我的眼里,私人车道的长度是人们社会地位的象征。我的想法也许是来自马僮吧,他是我的好朋友。他有一本《橙之韵律》,我们一起在干草堆里诵读,这让我第一次感觉到押韵的美妙之处。后来有人告诉我,盛传芬尼亚社社员造反,应战的橙带党党员已经分到了枪支。当我憧憬未来的生活时,我觉得自己会在和芬尼亚人的斗争中英勇战死。我会打造出一艘漂亮的快速战舰,手下拥有一批训练有素的年轻人,他们像故事书中的人物一样勇敢而英俊,而罗塞斯附近的海岸将会发生一场激战,我将会在那里血溅沙场。我到处收集小木片,把它们堆积在院子的一角。我经常跑到远处的农田去看一根很老的朽木,因为在我眼里,它对造船会大有帮助。我所有的梦想都和船有关。有一天,一名来我们家和外公共进晚餐的船长用两只手捧起我的脑袋,将我提起来,让我看地图上的非洲是何种模样;还有一个船长曾经指着草坪树丛后面、从码头珀恩磨坊袅袅升起的烟雾,问我圣布尔本山是不是着了火。
每隔几个月,我就去罗塞斯角或是巴利索达尔探访另外一个男孩,他曾经骑着一匹马戏团的花斑小马在广场里溜达,结果忘了路,兜了一个又一个圈子。他便是大舅公威廉?密德尔顿的儿子乔治?密德尔顿。人们那时候认为土地是非常安全的投资,于是老密德尔顿在巴利索达尔和罗塞斯角购置了两处土地,在巴利索达尔过冬,在罗塞斯角度夏。巴利索达尔有密德尔顿和波莱克斯芬家族的磨坊和一座大鱼堰,还有激流和瀑布,但我还是更经常在罗塞斯角见到表亲。我们或是在河口划船,或是乘着慢悠悠的斯库纳帆船出海,或是给轮船上的救生船装上帆具和甲板,然后起航。这里在一百年前曾住着走私贩,所以房子有一间很大的地下室。傍晚,客厅有时会传来三记敲窗户的声音,引得所有的狗都汪汪大叫,据说这是死去的走私贩在发出暗号。有一天晚上我特别清楚地听到了敲窗声,后来表妹也听到了声音,表弟则对它习以为常。有船上的领航员告诉我,他曾三次梦到我叔叔的花园里藏着财宝,然后他半夜翻墙进来开挖,但是一堆又一堆的泥土让他灰心丧气。我把他的话告诉了别人,他们说,领航员没找到财宝是因为一只形似熨斗的精灵守护在这里。巴利索达尔的山岩间有一道裂缝,我每次经过时都会心怀恐惧,因为我相信那里住着一只像蜜蜂一样嗡嗡作响的凶残怪兽。
也许是在密德尔顿家,我对乡村故事产生了兴趣。我听到的第一个故事想必和他们家的农舍有关。密德尔顿一家乐于与近邻交友,经常出入领航员和佃农的屋舍。他们心灵手巧,经常动手做些活,制作船只、喂养鸡鸭,从来不图回报。在我出生前很多年,密德尔顿家里有人设计过一艘蒸汽船。它的发动机早已过了时,所以即便船驶在海峡里,在几英里外的岸边还是能听见像哮喘一样的声音。我长大多年后,还是经常听到它的“喘气”。当年船是在湖边建造的,后来在无数匹马的牵引下穿过城里。那时我母亲在念书,船却在教室的窗外停下了,漆黑一片的学校连续五天都只能点着蜡烛上课。人们相信这艘船能带来好运,所以把它修修补补,一直用了很久。船以建造者的未婚妻“珍尼特”命名,风吹雨打让它的名字锈蚀成了我们更加耳熟能详的“珍尼特”。我很小的时候,这个女人便死去了,那时她八十岁。她是个脾气暴躁的人,她的丈夫因此吃了不少苦头。
还有个大我一两岁的亲戚,为了知道母鸡将要下蛋时是什么感觉,他整天追着它们跑来跑去,把我吓得不轻。他们从来不打理房屋,连温室的窗户玻璃摔下来也置之不理。他们很受人喜爱,但不知何为礼数与矜持,没有那种天生的、卓尔不凡的高贵气质。
外婆有时候带我去拜访住在斯莱戈的贵妇人,她的花园一直延伸到河边,花园的尽头处,一堵矮墙边栽满了桂竹香。我通常会百无聊赖地坐在椅子上,那些哥哥们则边吃油饼边喝雪利酒。相比之下,和仆人们散步要有趣得多。有时候我们会从一个胖胖的小女孩身边走过,这时仆人会说服我给她写一封情书,第二次小女孩路过我们身边的时候,向我吐了吐舌头。仆人的故事更有意思。比如,在某个角落里,一个站在桶里的男人从桶里滚了出来,露出他的瘸腿,便从一名中士教官那里拿到了一个先令。还有,在某座房子里,一位老妇人躲在床下,床上的客人——一名军官和他的老婆在辱骂她,她便操起笤帚打了过去。所有的名门望族都有自己的轶事,要么荒诞不经,要么令人悲恸,要么浪漫温馨。我常常对自己说,如果没有人知道我的故事,就让它们这样消逝的话,那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几年之后,我在大约十岁或者十二岁的时候移居伦敦,那时我常常噙着泪水怀念在斯莱戈的日子。在开始写作之后,我希望用对斯莱戈的记忆来寻觅知音。
我住在梅尔维尔。我家相邻的房子被树木所环绕,在那里我偶尔会看到一个小男孩和他的奶奶待在一起。我已经忘了老奶奶的名字,只记得她对我很和善。我在十三四岁时去过她家,却发现她的疼爱只用在了小男孩身上。客人来的时候,仆人到院子里喊我,可我躲在干草棚里,平躺在高高的干草垛上。
我不记得自己几岁的时候大醉了一场(因为所有的往事看起来都一样遥远)。我同一个叔叔和几位表哥表弟乘快艇出航,但海上的天气并不好。我躺在主桅和斜桅之间的甲板上,一个大浪袭来,碧绿的海水扑向我的头顶。我全身都湿透了,但是很开心。回到罗塞斯角以后,我披上了大孩子的衣服,衣服太松,裤脚拖到了靴子下面,一名领航员递了瓶纯威士忌给我。在和叔叔开车回家的路上,我陶醉在一种奇怪的状态中,因为不管他怎么拉我,我都向每一位路人高喊着:“我喝醉了。”不管是在城里还是别处,我一路都大喊大叫,直到外婆把我推上床,给我灌了点味同黑加仑的液体,我这才沉沉地睡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