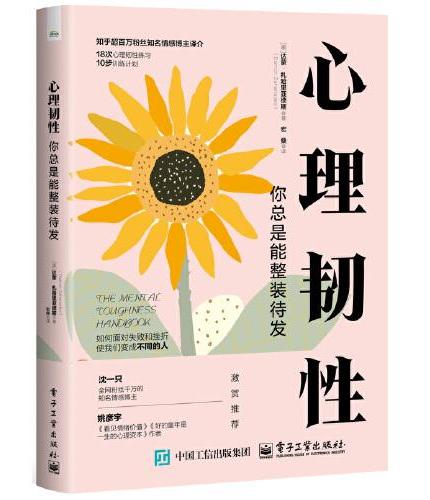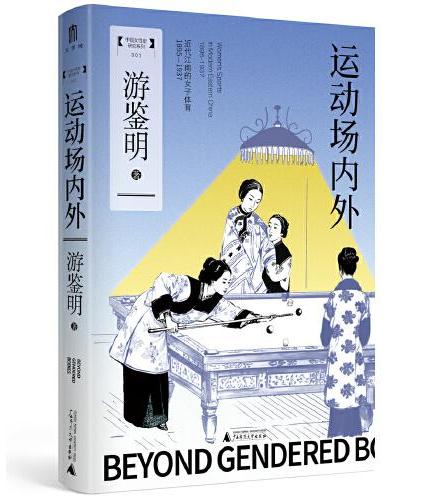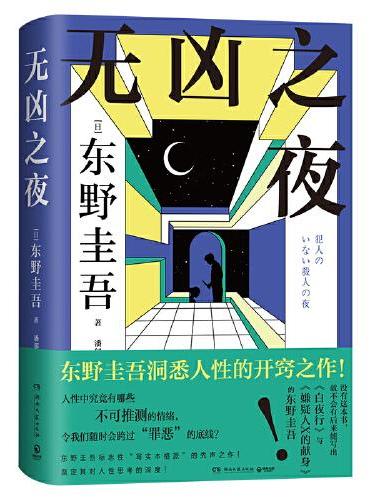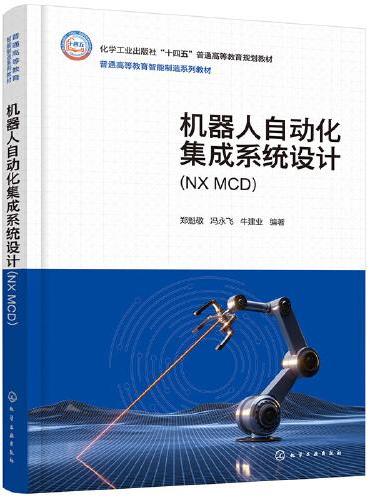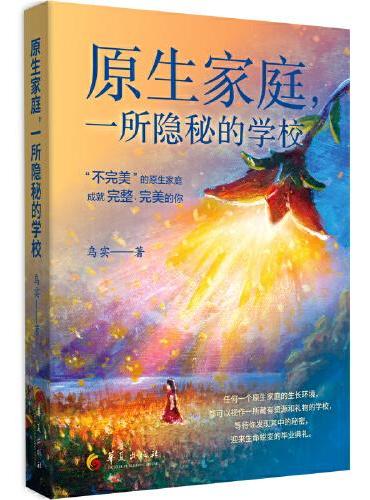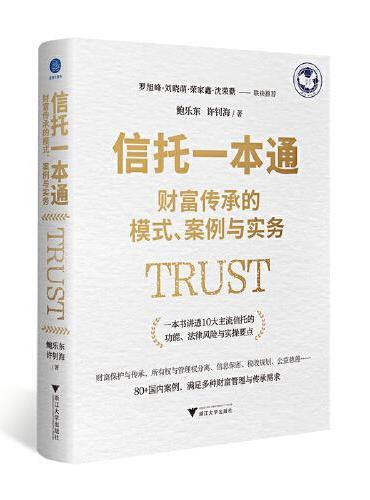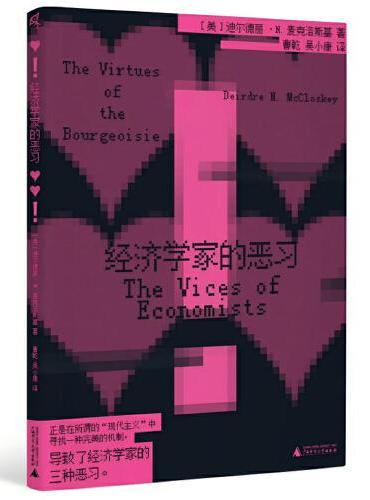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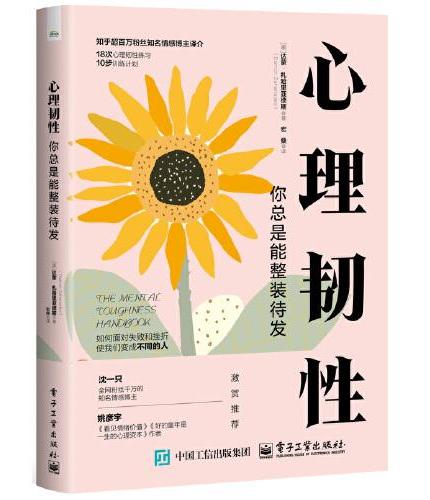
《
心理韧性:你总是能整装待发
》
售價:HK$
6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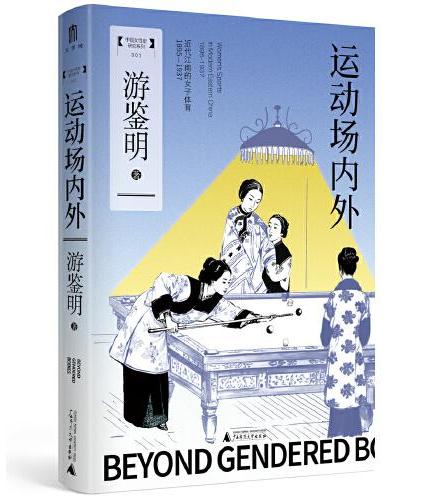
《
大学问·运动场内外:近代江南的女子体育(1895—1937)
》
售價:HK$
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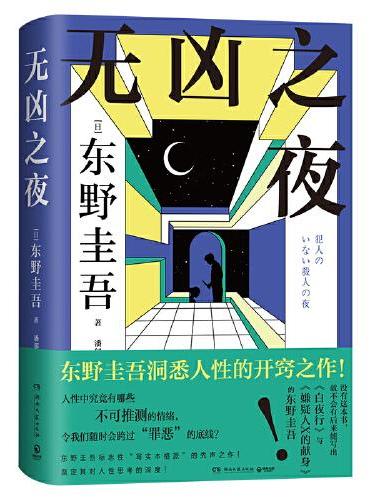
《
无凶之夜
》
售價:HK$
6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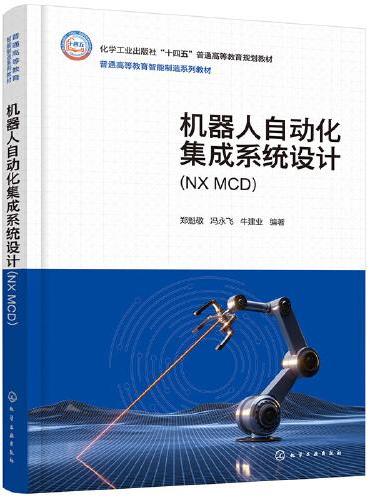
《
机器人自动化集成系统设计(NX MCD)
》
售價:HK$
6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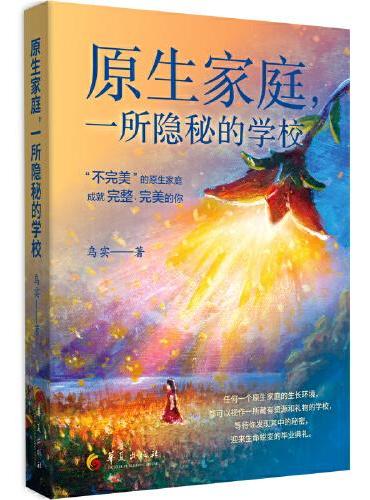
《
原生家庭,一所隐秘的学校
》
售價:HK$
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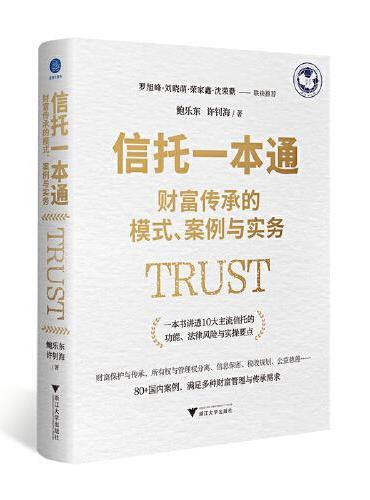
《
信托一本通:财富传承的模式、案例与实务(丰富案例+专业解读,讲透10大信托业务功能、法律风险与实操)
》
售價:HK$
107.8

《
AI绘画:技术、创意与商业应用全解析
》
售價:HK$
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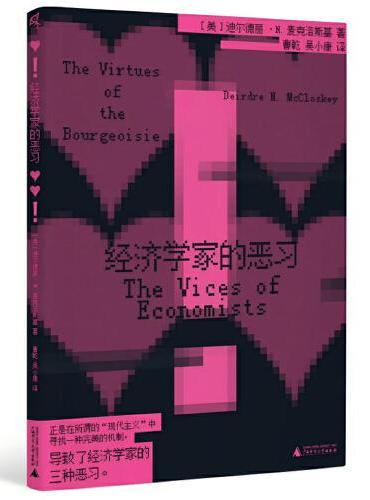
《
新民说·经济学家的恶习
》
售價:HK$
46.2
|
| 編輯推薦: |
|
人生的意义不在于何以有生,而在于自己怎样生活。
|
| 內容簡介: |
|
胡适的散文、随笔、政论、讲演集。自《新青年》起,胡适数十年如一日,反复宣扬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无论国家政治还是个人生活,都以自由的人作为出发点。
|
| 關於作者: |
|
胡适(1891.12.17—1962.2.28),汉族,安徽绩溪人。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改良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与陈独秀同为五四运动的轴心人物,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曾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等职。胡适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
|
| 目錄:
|
问题与主义
杜威先生与中国
新生活
新思潮的意义
人生有何意义
十七年的回顾
《科学与人生观》序
不朽
不老(跋梁漱溟先生致陈独秀书)
归国杂感
易卜生主义
贞操问题
“我的儿子”
我对于丧礼的改革
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
朋友与兄弟(答王子直)
名教
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请大家来照照镜子
漫游的感想
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
我们走哪条路?
惨痛的回忆与反省
信心与反省
再论信心与反省
三论信心与反省
悲观声浪里的乐观
写在也孔子诞辰纪念之后
领袖人才的来源
文学改良刍议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治学的方法与材料
整理国故与“打鬼”(给浩徐先生信)
读书
黄梨洲论学生运动
爱国运动与求学
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
大众语在那儿
|
| 內容試閱:
|
不朽
我的宗教
不朽有种种说法,但是总括看来,只有两种说法是真有区别的。一种是把“不朽”解作灵魂不灭的意思。一种就是《春秋左传》上说的“三不朽”。
(一)神不灭论宗教家往往说灵魂不灭,死后须受末日的裁判:做好事的享受天国天堂的快乐,做恶事的要受地狱的苦痛。这种说法,几千年来不但受了无数愚夫愚妇的迷信,居然还受了许多学者的信仰。但是古今来也有许多学者对于灵魂是否可离形体而存在的问题,不能不发生疑问。最重要的如南北朝人范缜的《神灭论》说:“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刀;形之于用,犹刀之于利。……舍利无刀,舍刀无利。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宋朝的司马光也说:“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剉烧舂磨,亦无所施。”但是司马光说的“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还不免把形与神看作两件事,不如范缜说的更透切。范缜说人的神灵即是形体的作用,形体便是神灵的形质。正如刀子是形质,刀子的利钝是作用;有刀子方才有利钝,没有刀子便没有利钝。人有形体方才有作用:这个作用,我们叫做“灵魂”。若没有形体,便没有作用了,便没有灵魂了。范缜这篇《神灭论》出来的时候,惹起了无数人的反对。梁武帝叫了七十几个名士作论驳他,都没有什么真有价值的论议。其中只有沈约的《难神灭论》说:“利若遍施四方,则利体无处复立;利之为用正存一边毫毛处耳。神之与形,举体若合,又安得同乎?若以此譬为尽耶,则不尽;若谓本不尽耶,则不可以为譬也。”这一段是说刀是无机体,人是有机体,故不能彼此相比。这话固然有理,但终不能推翻“神者形之用”的议论。近世唯物派的学者也说人的灵魂并不是什么无形体,独立存在的物事,不过是神经作用的总名;灵魂的种种作用都即是脑部各部分的机能作用;若有某部被损伤,某种作用即时废止;人年幼时脑部不曾完全发达,神灵作用也不能完全,老年人脑部渐渐衰耗,神灵作用也渐渐衰耗。这种议论的大旨,与范缜所说“神者形之用”正相同。但是有许多人总舍不得把灵魂打消了,所以咬住说灵魂另是一种神秘玄妙的物事,并不是神经的作用。这个“神秘玄妙”的物事究竟是什么,他们也说不出来,只觉得总应该有这么一件物事。既是“神秘玄妙”,自然不能用科学试验来证明他,也不能用科学试验来驳倒他。既然如此,我们只好用实验主义(Pragmatism)的方法,看这种学说的实际效果如何,以为评判的标准。依此标准看来,信神不灭论的固然也有好人,信神灭论的也未必全是坏人。即如司马光、范缜、赫胥黎一类的人,说不信灵魂不灭的话,何尝没有高尚的道德?更进一层说,有些人因为迷信天堂,天国,地狱,末日裁判,方才修德行善,这种修行全是自私自利的,也算不得真正道德。总而言之,灵魂灭不灭的问题,于人生行为上实在没有什么重大影响;既没有实际的影响,检直可说是不成问题了。
(二)三不朽说《左传》说的三种不朽是:(一)立德的不朽,(二)立功的不朽,(三)立言的不朽。“德”便是个人人格的价值,像墨翟、耶稣一类的人,一生刻意孤行,精诚勇猛,使当时的人敬爱信仰,使千百年后的人想念崇拜。这便是立德的不朽。“功”便是事业,像哥仑布发现美洲,像华盛顿造成美洲共和国,替当时的人开一新天地,替历史开一新纪元,替天下后世的人种下无量幸福的种子。这便是立功的不朽。“言”便是语言著作,像那《诗经》三百篇的许多无名诗人,又像陶潜、杜甫、萧士比亚、易卜生一类的文学家,又像柏拉图、卢骚、弥儿一类的文学家,又像牛敦、达尔文一类的科学家,或是做了几首好诗使千百年后的人欢喜感叹;或是做了几本好戏使当时的人鼓舞感动,使后世的人发愤兴起;或是创出一种新哲学,或是发明了一种新学说,或在当时发生思想的革命,或在后世影响无穷。这便是立言的不朽。总而言之,这种不朽说,不问人死后灵魂能不能存在,只问他的人格,他的事业,他的著作有没有永远存在的价值。即如基督教徒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的神灵永永存在,我们正不用驳这种无凭据的神话,只说耶稣的人格,事业,和教训都可以不朽,又何必说那些无谓的神话呢?又如孔教会的人每到了孔丘的生日,一定要举行祭孔的典礼,还有些人学那“朝山进香”的法子,要赶到曲阜孔林去对孔丘的神灵表示敬意!其实孔丘的不朽全在他的人格与教训,不在他那“在天之灵”。大总统多行两次丁祭,孔教会多行两次“朝山进香”,就可以使孔丘格外不朽了吗?更进一步说,像那《三百篇》里的诗人,也没有姓名,也没有事实,但是他们都可说是立言的不朽。为什么呢?因为不朽全靠一个人的真价值,并不靠姓名事实的流传,也不靠灵魂的存在。试看古今来的多少大发明家,那发明火的,发明养蚕的,发明缫丝的,发明织布的,发明水车的,发明舂米的水碓的,发明规矩的,发明秤的,……虽然姓名不传,事实湮没,但他们的功业永远存在,他们也就都不朽了。这种不朽比那个人的小小灵魂的存在,可不是更可宝贵,更可羡慕吗?况且那灵魂的有无还在不可知之中,这三种不朽——德,功,言,——可是实在的。这三种不朽可不是比那灵魂的不灭更靠得住吗?
以上两种不朽论,依我个人看来,不消说得,那“三不朽说”是比那“神不灭说”好得多了。但是那“三不朽说”还有三层缺点,不可不知。第一,照平常的解说看来,那些真能不朽的人只不过那极少数有道德,有功业,有著述的人。还有那无量平常人难道就没有不朽的希望吗?世界上能有几个墨翟、耶稣,几个哥仑布、华盛顿,几个杜甫、陶潜,几个牛敦、达尔文呢?这岂不成了一种“寡头”的不朽论吗?第二,这种不朽论单从积极一方面着想,但没有消极的裁制。那种灵魂的不朽论既说有天国的快乐,又说有地狱的苦楚,是积极消极两方面都顾着的。如今单说立德可以不朽,不立德又怎样呢?立功可以不朽,有罪恶又怎样呢?第三,这种不朽论所说的“德,功,言”三件,范围都很含糊。究竟怎样的人格方才可算是“德”呢?怎样的事业方才可算是“功”呢?怎样的著作方才可算是“言”呢?我且举一个例。哥仑布发现美洲固然可算得立了不朽之功,但是他船上的水手火头又怎样呢?他那只船的造船工人又怎样呢?他船上用的罗盘器械的制造工人又怎样呢?他所读的书的著作者又怎样呢?……举这一条例,已可见“三不朽”的界限含糊不清了。
因为要补足这三层缺点,所以我想提出第三种不朽论来请大家讨论。我一时想不起别的好名字,姑且称他做“社会的不朽论”。
(三)社会的不朽论社会的生命,无论是看纵剖面,是看横截面,都像一种有机的组织。从纵剖面看来,社会的历史是不断的;前人影响后人,后人又影响更后人;没有我们的祖宗和那无数的古人,又那里有今日的我和你?没有今日的我和你,又那里有将来的后人?没有那无量数的个人,便没有历史,但是没有历史,那无数的个人也决不是那个样子的个人:总而言之,个人造成历史,历史造成个人。从横截面看来,社会的生活是交互影响的:个人造成社会,社会造成个人;社会的生活全靠个人分功合作的生活,但个人的生活,无论如何不同,都脱不了社会的影响;若没有那样这样的社会,决不会有这样那样的我和你;若没有无数的我和你,社会也决不是这个样子。来勃尼慈(Leibnitz)说得好:这个世界乃是一片大充实(Plenum,为真空Vacuum之对),其中一切物质都是接连着的。一个大充实里面有一点变动,全部的物质都要受影响,影响的程度与物体距离的远近成正比例。世界也是如此。每一个人不但直接受他身边亲近的人的影响,并且间接又间接的受距离很远的人的影响。所以世间的交互影响,无论距离远近,都受得着的。所以世界上的人,每人受着全世界一切动作的影响。如果他有周知万物的智慧,他可以在每人的身上看出世间一切施为,无论过去未来都可看得出,在这一个现在里面便有无穷时间空间的影子。(见Monadology第六十一节)从这个交互影响的社会观和世界观上面,便生出我所说的“社会的不朽论”来。我这“社会的不朽论”的大旨是:
我这个“小我”不是独立存在的,是和无量数小我有直接或间接的交互关系的;是和社会的全体和世界的全体都有互为影响的关系的;是和社会世界的过去和未来都有因果关系的。种种从前的因,种种现在无数“小我”和无数他种势力所造成的因,都成了我这个“小我”的一部分。我这个“小我”,加上了种种从前的因,又加上了种种现在的因,传递下去,又要造成无数将来的“小我”。这种种过去的“小我”,和种种现在的“小我”,和种种将来无穷的“小我”,一代传一代,一点加一滴;一线相传,连绵不断;一水奔流,滔滔不绝:——这便是一个“大我”。“小我”是会消灭的,“大我”是永远不灭的。“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永远不死,永远不朽的。“小我”虽然会死,但是每一个“小我”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语言行事,无论大小,无论是非,无论善恶,一一都永远留存在那个“大我”之中。那个“大我”,便是古往今来一切“小我”的纪功碑,彰善祠,罪状判决书,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的恶谥法。这个“大我”是永远不朽的,故一切“小我”的事业,人格,一举一动,一言一笑,一个念头,一场功劳,一桩罪过,也都永远不朽。这便是社会的不朽,“大我”的不朽。
那边“一座低低的土墙,遮着一个弹三弦的人”。那三弦的声浪,在空间起了无数波澜;那被冲动的空气质点,直接间接冲动无数旁的空气质点;这种波澜,由近而远,至于无穷空间;由现在而将来,由此刹那以至于无量刹那,至于无穷时间:——这已是不灭不朽了。那时间,那“低低的土墙”外边来了一位诗人,听见那三弦的声音,忽然起了一个念头;由这一个念头,就成了一首好诗;这首好诗传诵了许多人;人读了这诗,各起种种念头;由这种种念头,更发生无量数的念头,更发生无数的动作,以至于无穷。然而那“低低的土墙”里面那个弹三弦的人又如何知道他所发生的影响呢?
一个生肺病的人在路上偶然吐了一口痰。那口痰被太阳晒干了,化为微尘,被风吹起空中,东西飘散,渐吹渐远,至于无穷时间,至于无穷空间。偶然一部分的病菌被体弱的人呼吸进去,便发生肺病,由他一身传染一家,更由一家传染无数人家。如此展转传染,至于无穷空间,至于无穷时间。然而那先前吐痰的人的骨头早已腐烂了,他又如何知道他所种的恶果呢?
一千五六百年前有一个人叫做范缜说了几句话道:“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这几句话在当时受了无数人的攻击。到了宋朝有个司马光把这几句话记在他的《资治通鉴》里。一千五六百年之后,有一个十一岁的小孩子,——就是我,——看《通鉴》到这几句话,心里受了一大感动,后来便影响了他半生的思想行事。然而那说话的范缜早已死了一千五百年了!
二千六七百年前,在印度地方有一个穷人病死了,没人收尸,尸首暴露在路上,已腐烂了。那边来了一辆车,车上坐着一个王太子,看见了这个腐烂发臭的死人,心中起了一念;由这一念,展转发生无数念。后来那位王太子把王位也抛了,富贵也抛了,父母妻子也抛了,独自去寻思一个解脱生老病死的方法。后来这位王子便成了一个教主,创了一种哲学的宗教,感化了无数人。他的影响势力至今还在;将来即使他的宗教全灭了,他的影响势力终久还存在,以至于无穷。这可是那腐烂发臭的路毙所曾梦想到的吗?
以上不过是略举几件事,说明上文说的“社会的不朽”,“大我的不朽”。这种不朽论,总而言之,只是说个人的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言语行事,无论大小好坏,一一都留下一些影响在那个“大我”之中,一一都与这永远不朽的“大我”一同永远不朽。
上文我批评那“三不朽论”的三层缺点:(一)只限于极少数的人,(二)没有消极的裁制,(三)所说“功,德,言”的范围太含糊了。如今所说“社会的不朽”,其实只是把那“三不朽论”的范围更推广了。既然不论事业功德的大小,一切都可不朽,那第一第三两层短处都没有了。冠绝古今的道德功业固可以不朽,那极平常的“庸言庸行”,油盐柴米的琐屑,愚夫愚妇的细事,一言一笑的微细,也都永远不朽。那发现美洲的哥仑布固可以不朽,那些和他同行的水手火头,造船的工人,造罗盘器械的工人,供给他粮食衣服银钱的人,他所读的书的著作家,生他的父母,生他父母的父母祖宗,以及生育训练那些工人商人的父母祖宗,以及他以前和同时的社会,……都永远不朽。社会是有机的组织,那英雄伟人可以不朽,那挑水的,烧饭的,甚至于浴堂里替你擦背的,甚至于每天替你家掏粪倒马桶的,也都永远不朽。至于那第二层缺点,也可免去。如今说立德不朽,行恶也不朽;立功不朽,犯罪也不朽;“流芳百世”不朽,“遗臭万年”也不朽;功德盖世固是不朽的善因,吐一口痰也有不朽的恶果。我的朋友李守常先生说得好:“稍一失脚,必致遗留层层罪恶种子于未来无量的人,——即未来无量的我,——永不能消除,永不能忏悔。”这就是消极的裁制了。
中国儒家的宗教提出一个父母的观念,和一个祖先的观念,来做人生一切行为的裁制力。所以说,“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父母死后,又用丧礼祭礼等等见神见鬼的方法,时刻提醒这种人生行为的裁制力。所以又说,“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又说,“斋三日,则见其所为斋者;祭之日,入室,傻然必有见乎其位;周还出户,肃然必有闻乎其容声;出户而听,忾然必有闻乎其叹息之声”。这都是“神道设教”,见神见鬼的手段。这种宗教的手段在今日是不中用了。还有那种“默示”的宗教,神权的宗教,崇拜偶像的宗教,在我们心里也不能发生效力,不能裁制我们一生的行为。以我个人看来,这种“社会的不朽”观念很可以做我的宗教了。我的宗教的教旨是:
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的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的责任。我须要时时想着,我应该如何努力利用现在的“小我”,方才可以不辜负了那“大我”的无穷过去,方才可以不遗害那“大我”的无穷未来?
(跋)
这篇文章的主意是民国七年年底当我的母亲丧事里想到的。那时只写成一部分,到八年二月十九日方才写定付印。后来俞颂华先生在报纸上指出我论社会是有机体一段很有语病,我觉得他的批评很有理,故九年二月间我用英文发表这篇文章时,我就把那一段完全改过了。十年五月,又改定中文原稿,并记作文与修改的缘起于此。
(原载1919年2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2号)
不老
跋梁漱溟先生致陈独秀书
一 梁先生原信节录
仲甫先生:
方才收到《新青年》六卷一号,看见你同陶孟和先生论我父亲自杀的事各一篇,我很感谢。为什么呢?因为凡是一件惹人注目的事,社会上对于他一定有许多思量感慨。当这用思兴感的时候,必不可无一种明确的议论来指导他们到一条正确的路上去,免得流于错误而不自觉。所以我很感谢你们作这种明确的议论。我今天写这信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我读孟和的论断似乎还欠明晰,要有所申论;一个是凡人的精神状况差不多都与他的思想有关系,要众人留意。……
诸君在今日被一般人指而目之为新思想家,那里知道二十年前我父亲也是受人指而目之为新思想家的呀。那时候人都毁骂郭筠仙(嵩焘)信洋人讲洋务,我父亲同他不相识,独排众论,极以他为然。又常亲近那最老的外交家许静山先生(玨),去访问世界大势,讨论什么亲俄亲英的问题。自己在日记上说:“倘我本身不能出洋留学,一定节省出钱来叫我儿子出洋。万事可省,此事不可不办。”大家总该晓得向来小孩子开蒙念书照规矩是《百家姓》、《千字文》、《四书五经》。我父亲竟不如此,叫那先生拿《地球韵言》来教我。我八岁时候有一位陈先生开了一个“中西小学堂”,便叫我去那里学起abcd来。到现在二十岁了,那人人都会背的《论语》、《孟子》,我不但不会背,还是没有念呢!请看二十年后的今日还在那里压派着小学生读经,稍为革废之论,即为大家所不容。没有过人的精神,能行之于二十年前么?我父亲有兄弟交彭翼仲先生是北京城报界开天辟地的人,创办《启蒙画报》、《京话日报》、《中华报》等等。(《启蒙画报》上边拿些浅近科学知识讲给人听,排斥迷信,恐怕是北京人与赛先生(Science)相遇的第一次呢!)北京人都叫他“洋报”,没人过问,赔累不堪,几次绝望。我父亲典当了钱接济他,前后千余金。在那借钱折子上自己批道:“我们为开化社会,就是把这钱赔干净了也甘心。”我父亲又拿鲁国漆室女倚门而叹的故事编了一出新戏叫作“女子爱国”。其事距今有十四五年了,算是北京新戏的开创头一回。戏里边便是把当时认为新思想的种种改革的主张夹七夹八的去灌输给听戏的人。平日言谈举动,在一般亲戚朋友看去,都有一种生硬新异的感觉,抱一种老大不赞成的意思。当时的事且不再叙,去占《新青年》的篇幅了。然而到了晚年,就是这五六年,除了合于从前自己主张的外,自己常很激烈的表示反对新人物新主张(于政治为尤然)。甚至把从前所主张的,如申张民权排斥迷信之类,有返回去的倾向。不但我父亲如此,我的父执彭先生本是勇往不过的革新家,那一种破釜沉舟的气概,恐怕现在的革新家未必能及,到现在他的思想也是陈旧的很,甚至也有那返回去的倾向。当年我们两家虽都是南方籍贯,因为一连几代作官不曾回南,已经成了北京人。空气是异常腐败的。何以竟能发扬蹈厉去作革新的先锋?到现在的机会,要比起从前,那便利何止百倍,反而不能助成他们的新思想,却墨守条规起来,又何故呢?这便是我说的精神状况的关系了。当四十岁时,人的精神充裕,那一副过人的精神便显起效用来,于甚少的机会中追求出机会,摄取了知识,构成了思想,发动了志气,所以有那一番积极的作为。在那时代便是维新家了。到六十岁时,精神安能如昔?知识的摄取力先减了,思想的构成力也退了,所有的思想都是以前的遗留,没有那方兴未艾的创造,而外界的变迁却一日千里起来,于是乎就落后为旧人物了。因为所差的不过是精神的活泼,不过是创造的智慧,所以虽不是现在的新思想家,却还是从前的新思想家;虽没有今人的思想,却不像寻常人的没思想。况且我父亲虽然到了老年,因为有一种旧式道德家的训练,那颜色还是很好,目光极其有神,肌肉不瘠,步履甚健,样样都比我们年轻人还强。精神纵不如昔,还是过人。那神志的清明,志气的刚强,情感的真挚,真所谓老当益壮的了。对于外界政治上社会上种种不好的现象,他如何肯糊涂过去!便本着那所有的思想终日早起晏息的去作事,并且成了这自杀的举动。其间知识上的错误自是有的。然而不算事。假使拿他早年本有的精神遇着现在新学家同等的机会,那思想举动正未知如何呢!因此我又联想到何以这么大的中国,却只有一个《新青年》杂志?可以验国人的精神状况了!诸君所反复说之不已的,不过是很简单的一点意思,何以一般人就大惊小怪起来,又有一般人就觉得趣味无穷起来?想来这般人的思想构成力太缺了!然则这国民的“精神的养成”恐怕是第一大事了。我说精神状况与思想关系是要留意的一桩事,就是这个。梁漱溟
二 跋
漱溟先生这封信,讨论他父亲巨川先生自杀的事,使人读了都很感动。他前面说的一段,因陶先生已去欧洲,我们且不讨论。后面一段论“精神状况与思想有关系”一个问题,使我们知道巨川先生精神生活的变迁,使我们对于他老先生不能不发生一种诚恳的敬爱心。这段文章,乃是近来传记中有数的文字。若是将来的孝子贤孙替父母祖宗做传时,都能有这种诚恳的态度,写实的文体,解释的见地,中国文学也许发生一些很有文学价值的传记。
我读这一段时,觉得内中有一节很可给我们少年人和壮年人做一种永久的教训,所以我把他提出来抄在下面:当四十岁时,人的精神充裕,那一副过人的精神便显起效用来,于甚少的机会中追求出机会,摄取了知识,构成了思想,发动了志气,所以有那一番积极的作为。在那时代便是维新家了。到六十岁时,精神安能如昔?知识的摄取力先减了,思想的构成力也退了,所有的思想都是以前的遗留,没有那方兴未艾的创造,而外界的变迁却一日千里起来,于是乎就落后成为旧人物了。我们少年人读了这一段,应该问自己道:“我们到了六七十岁时,还能保存那创造的精神,做那时代的新人物吗?”这个问题还不是根本问题。我们应该进一步,问自己道:“我们该用什么法子方才可使我们的精神到老还是进取创造的呢?我们应该怎么预备做一个白头的新人物呢?”
从这个问题上着想,我觉得漱溟先生对于他父亲平生事实的解释还不免有一点“倒果为因”的地方。他说,“到了六十岁时,精神安能如昔?知识的摄取力先减了,思想的构成力也退了”。这似乎是说因为精神先衰了,所以不能摄取新知识,不能构成新思想。但他下文又说巨川先生老年的精神还是过人,“真所谓老当益壮”。这可见巨川先生致死的原因不在精神先衰,乃在知识思想不能调剂补助他的精神。二十年前的知识思想决不够培养他那二十年后“老当益壮”的旧精神,所以有一种内部的冲突,所以竟致自杀。
我们从这个上面可得一个教训:我们应该早点预备下一些“精神不老丹”方才可望做一个白头的新人物。这个“精神不老丹”是什么呢?我说是永远可求得新知识新思想的门径。这种门径不外两条:(一)养成一种欢迎新思想的习惯,使新知识新思潮可以源源进来;(二)极力提倡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养成一种自由的空气,布下新思潮的种子,预备我们到了七八十岁时,也还有许多簇新的知识思想可以收获来做我们的精神培养品。
今日的新青年!请看看二十年前的革命家!民国八年四月
(原载1919年4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4号,附在梁漱溟《致陈独秀书》后)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