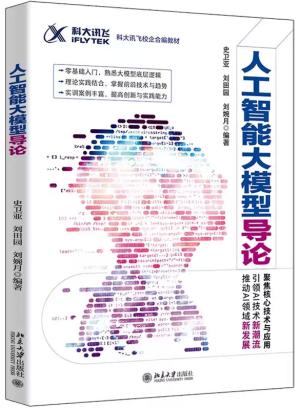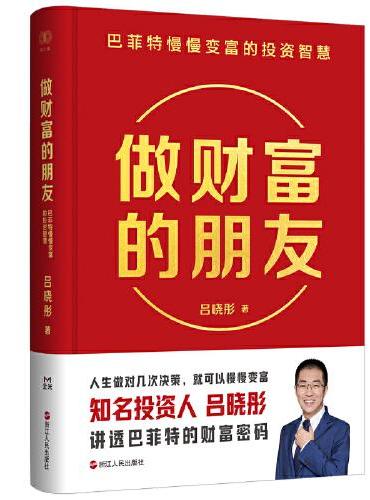新書推薦:

《
软体机器人技术
》
售價:HK$
97.9

《
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
》
售價:HK$
74.8

《
奴隶船:海上奴隶贸易400年
》
售價:HK$
75.9

《
纸上博物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诞生(破译古老文明的密码,法国伽利玛原版引进,150+资料图片)
》
售價:HK$
85.8

《
米塞斯的经济学课:讲座与演讲精选集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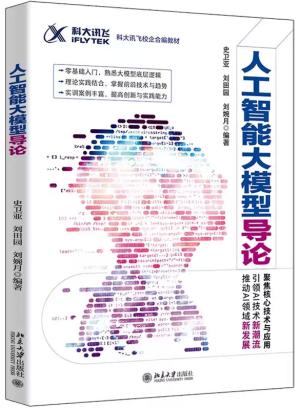
《
人工智能大模型导论 科大讯飞校企合编教材
》
售價:HK$
7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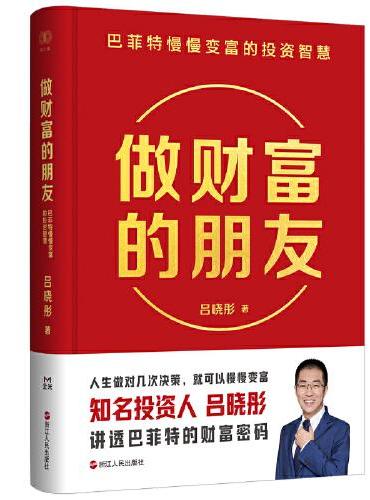
《
做财富的朋友:巴菲特慢慢变富的投资智慧
》
售價:HK$
82.5

《
一群数学家分蛋糕:提升逻辑力的100道谜题
》
售價:HK$
60.5
|
| 編輯推薦: |
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艾丽丝·门罗七部代表作品
国内最全的门罗作品系列 涵盖其创作各个时期代表作
平静生活表面之下风波诡谲……
短篇小说艺术绽放异彩
『她是当代短篇小说大师』——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
随书附赠精美海报!
|
| 內容簡介: |
·《快乐影子之舞》是门罗的成名作和处女作,历时15年写成,一举赢得加拿大最高文学奖项总督奖。《快乐影子之舞》收录的15个短篇故事里,门罗以非凡的视角观照平凡的生活,显示出足以成为经典作家的特质。
《快乐影子之舞》收录的这些故事发生在农场,在河畔沼泽地,在西安大略孤独的小镇和新兴的郊区。女孩跟着父亲上门推销,无意目睹父亲埋藏已久的恋情;两对陌生男女在寂寞小镇里耐着性子相互抚慰,老小姐让智障的孩子们用音乐发出与另一个世界的沟通……作者将注意力投向平常人的欲望及遗憾,爱的欢愉与痛苦,以及逼仄生活中的绝望和负疚,让我们惊觉人心里共同的野心、恐惧和悲哀。
·在《公开的秘密》中这八篇关于“秘密”的故事里,艾丽丝·门罗唤起了旧爱突然重生的毁灭性力量。忘情于书信欢爱的图书管理员、流连在荒野的孤女、破坏邻居家宅的女基督徒……门罗笔下的女子都有一个“秘密”,她们保持着与真相的模糊距离。《公开的秘密》曾获加拿大总督奖提名,被《纽约时报》评为年度好书,并为门罗斩获了WH.史密斯文学奖,自此,门罗作品日益受到国际文坛广泛关注。
·门罗笔下的女人邂逅的真实生活总有些残酷:谋杀、疯狂、死亡、离异,以及形形色色的欺骗。面对这些遭遇,她们总是平静、清醒,甚至有些若无其事。她们在人生中穿行,背负着各自的伤疤,但又当这伤疤不是她们的;她们睿智深邃,但这不能医治她们的柔弱善感。
《幸福过了头》中收录10篇意味深长的故事,太多不能承受的幸福与伤痛,其时罹患癌症的门罗,正欲以此作为她人生的绝唱。《幸福过了头》曾是吉勒奖的夺冠热门,为了给后辈留下机会,门罗主动退出竞争。
·《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由8个篇目组成,由于内容连贯,一度被认作艾丽丝·门罗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里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安大略省的乡间小镇,描绘了一个女性从懵懂青涩成长为一个睿智、聪颖的生活观察者的历程。在目睹情欲和生死之时,她经历了女性所要面对的光明和黑暗面。《女孩和女人的生活》有很强的自传意义,对于门罗的研究者和爱好者来说,阅读《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可以深入了解门罗的生活与创作背景。
·人的一生中能有几回,曾经的伴侣再次相见,尘封的童年记忆忽然惊醒,年迈双亲像婴儿一般被子女照料?《爱的进程》的11个短篇中,门罗将目光投向普通人生活中最为私密的角落,聚焦于恋人、夫妻、手足、亲子之间难解难分的郁结和爱。作家的叙述尖锐而富于同情,记录了生命不同阶段中,人的自我、抉择以及对爱的体验是如何悄悄地转变。
《爱的进程》发表于1986年,令门罗第三次斩获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文学奖。
·《好女人的爱情》中以深邃的洞察力,探索了各种类型的爱,社会礼貌表层之下的冲突和欺骗,以及人心那些奇怪的,每每显得可笑的欲望。时间被屡屡拉伸:男女主人公回顾四十年前初见的那个夏天,人生的真谛都在此时被揭示;时间同时也被置于显微镜下观察:一夜之间,年轻女子发现自己那充满女性魅力的母亲竟已无法依靠……
《好女人的爱情》获得吉勒文学奖和全美书评人协会奖。这部小说集以精彩的细节和坚定的勇气,奠定了艾丽丝·门罗作为当代最出色的小说家之一的地位。
·在《恨,友谊,追求,爱情,婚姻》中,门罗提炼了人一生情感生活几乎所有的主题,用敏锐细腻的语言记述了九个极端接近人生真相的故事。情感没有边界,堕落没有底线,生活没有输赢……无论在哪一个时代,包含在《恨,友谊,追求,爱情,婚姻》中这些故事中的智慧都是应景的,甚至是预言性的,探讨生活的可能性与结果。《恨,友谊,追求,爱情,婚姻》曾入选《时代杂志》年度最佳小说,充满了作家圆熟的人生历练,代表了门罗一生最高的艺术成就。
|
| 關於作者: |
|
艾丽丝·门罗,生于1931年,加拿大女作家,当代短篇小说大师,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少女时代即开始写作,37岁时出版第一部作品。她一生专注于中短篇小说创作,讲述小地方普通人特别是女性隐含悲剧的平常生活,以细腻透彻又波澜不惊的话语,洞见人性的幽微处。
|
| 目錄:
|
《快乐影子之舞》
沃克兄弟的放牛娃
亮丽家园
重重想象
谢谢让我们搭车
办公室
一点儿疗伤药
死亡时刻
有蝴蝶的那一天
男孩和女孩
明信片
红裙子,1946年
周日午后
去海滨
乌德勒支的宁静
快乐影子之舞
《公开的秘密》
忘情
真实的生活
阿尔巴尼亚圣女
公开的秘密
蓝花楹旅馆
荒野小站
宇宙飞船着陆
破坏分子
《幸福过了头》
多维的世界
纯属虚构
温洛岭
深洞
游离基
脸
一些女人
孩子的游戏
森林
幸福过了头
《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
弗莱兹路
活体的继承者
伊达公主
信仰之年
变迁和仪式
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
洗礼
尾声:摄影师
《爱的进程》
爱的进程
苔藓
双帽先生
蒙大拿的迈尔斯城
发作
奥兰治大街溜冰场的月亮
杰斯和美瑞白丝
爱斯基摩人
怪胎
祈祷之圈
白山包
《好女人的爱情》
好女人的爱情
雅加达
库特斯岛
唯余收割者
孩子们留下
富得流油
变化之前
我妈的梦
《恨,友谊,追求,爱情,婚姻》
仇恨,友谊,追求,爱情,婚姻
浮桥
家具
慰藉
荨麻
梁与柱
留存的记忆
奎妮
熊从山那边来
|
| 內容試閱:
|
《蓝花楹旅馆》摘自《公开的秘密》
盖尔是70 年代的一个夏天来到沃利的。她那时的男朋友是个造船工人,她则售卖自己做的衣服——带贴花的斗篷、泡泡袖的衬衫、颜色亮丽的长裙。冬天到来的时候,她在作坊里面找到了活儿。盖尔见识到了进口的斗篷、玻利维亚和危地马拉的厚袜子。她发现当地的女人都在织毛衣。有一天,威尔在路上拦住她,请她帮忙挑选自己在话剧里要穿的戏服——那出话剧叫作《我们牙齿的外壳》。她的男朋友搬去了温哥华。
她把自己以前的一些事情告诉了威尔,以防他看到她身体健康、皮肤粉嫩、额头开阔,会觉得她是组建家庭的合适人选呢。她告诉他,自己曾经有过一个孩子。当时她和男朋友要从桑德贝搬到多伦多,在他们忙着把家具搬进借来的小货车里时,家里发生了煤气泄漏,大人们只是觉得有点不舒服,那却足以杀死只有七周大的婴儿。在那之后,盖尔就病了——得了盆腔炎。她将来很难怀孕,也不想再要孩子,于是做了子宫切除手术。
威尔欣赏她。他是这么说的。他连一句“真悲惨”都没有说,也没有拐弯抹角地暗示孩子的死是盖尔自己的责任。那时他们逐渐熟识。他觉得盖尔勇敢慷慨、机智聪明、充满才华。她为他设计制作的戏服不可思议、无可挑剔。盖尔觉得他对她、对她生活的看法带着一种感人的天真。对她来说,自己根本不是那种自由慷慨的人,反而常常焦虑绝望,很多时候都是在洗衣服、为钱发愁,觉得哪个男人跟自己交往,她就亏欠了他。那时盖尔觉得自己没有爱上威尔,但她喜欢他的样子——他强健的身体那么挺拔,看起来比实际高大;他昂首挺胸,高高的额头闪着亮光;他充满弹性的、泛灰色的头发。盖尔喜欢看他排练,或者看他跟学生说话。他做导演时是那么娴熟无畏,走过学校大厅或者沃利的街道时是那么气宇轩昂。还有他对她所怀有的那种稍显古怪的倾慕之情,他那种爱人般的殷勤礼貌,他家里愉快的异国情调,他和克莉塔的生活——这一切都让盖尔感觉似乎有人在某处受到了特别的欢迎,而那个地方,她可能无权进入。那时,这都不要紧——她占着上风。
那么,她是几时失去上风的呢?从他们同居后、他习惯了和她睡在一起?还是从他们大费力气在河边修建小屋,而她竟然比他还擅长干那些活儿?
她是不是那种觉得总要有人占上风的人?
有一次,散步时盖尔走到了前面。威尔说:“你的鞋带开了。” 就是他说话的那种语调,让她充满了绝望,仿佛是在提醒她:他们已经跨越到了一个昏暗的国度,在那里他对她无比失望、极度蔑视。她最终会绊倒并勃然大怒——他们会度过充满绝望的日日夜夜。接着终于突破困境,甜蜜和好,开开玩笑,稀里糊涂地宽慰起来。于是,他们的日子继续过下去——她并不能真正理解这一切,也不知道别人是否也是如此。但是,平和的日子越来越多,危险都已隐退,她丝毫没有觉察到他早已开始期待去和别人交往——桑迪,在他看来新鲜而又令人愉快,就像当初的盖尔一样。
很可能威尔自己也没有觉察到。
他从没有太多地谈起过桑迪——桑德拉——她是去年参加一个交换项目来到沃利的,来看看加拿大的学校如何教授戏剧。他说过,她是一个年轻的土耳其人,还说,也许她根本不知道对土耳其人的这种叫法。很快,她的名字仿佛带上了电或是某种危险。盖尔从其他地方得到了一些信息。她听说,桑迪在班上当众对威尔提出质疑,说他正在搞的戏剧“毫无意义”,也可能是说“毫无新意”。
“但他喜欢她,”威尔的一个学生说,“哦,是的,他真的非常喜欢她。” 桑迪并没有在此地久留,她要继续到别的学校研究戏剧教学。但是她给威尔写信,而且知道他会回信。因为他们两个相爱了。威尔和桑迪真心爱上了彼此,那个学年结束时,威尔跟着她去了澳大利亚。
真心相爱。威尔这么告诉她的时候,盖尔正在吸食毒品。她重新开始吸毒了,因为和威尔在一起总是让她紧张无比。
“你是说,不是因为我?”盖尔说,“不是因为我讨人厌?”
她安下心来,觉得一阵眩晕,大胆地勾引威尔上了床。
第二天早上,两人都尽量避免待在同一个房间。他们都同意不要联系。也许再过一段时间,威尔说。盖尔说:“随你的便。”
但是有一天,盖尔在克莉塔家看到了信封上威尔的字迹,那信封放在盖尔肯定能看到的地方。是克莉塔放的——对那两个逃走的人,克莉塔向来只字不提。盖尔记下了上面的地址: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布里斯班市图翁区艾尔路16 号。
就在看到威尔字迹的那一刻,她忽然明白,对她来说一切都失去了意义。这座前维多利亚时期的门庭开阔的房子,阳台,酒,克莉塔的后院里她经常注视的那些梓树。沃利所有的树木和街道,湖边开阔的风景,她那惬意的小店。那些没用的图样,那些冒牌货和道具。真正的风景早已不在她的眼前,而在澳大利亚。
这就是为什么她会和那个戴着钻戒的女人一起坐在飞机里。她的手上没有戴戒指,也没涂指甲油——因为一直做针线活,皮肤很干燥。她以前把自己做的衣服称为“手工艺品”,直至威尔对这种称呼冷嘲热讽,不过她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她把店卖掉了——卖给了唐纳达,她老早以前就想买了。然后,她拿着钱登上了飞往澳大利亚的飞机。盖尔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要去哪儿,她撒谎说要去度假,先去英国,再去希腊过冬,接下来,谁知道呢?
出发之前的那个晚上,盖尔改变了自己的形象。她剪短了浓密的灰红色的头发,给剩下的头发抹上了深褐色的染发剂。这颜色的最终效果很奇怪——是种深栗色,看起来很不自然,而且非常暗沉,毫无魅力可言。她从店里挑了一条自己以前从来不会穿的那种裙子——尽管店里的东西已经不再属于她了——深蓝色仿亚麻的涤纶夹克式连衣裙,带着鲜艳的红色和黄色条纹。她个子高屁股大,通常都穿那种宽松优雅的款式。这件衣服显得她又矮又胖,在膝盖上方很不恰当的地方把腿分成了两截。她想把自己打扮成哪种女人?那种会和菲莉丝一起玩桥牌的类型?如果是,那就弄错了。她现在看上去像是那种人——大半辈子穿着制服、做着一份值得尊敬却收入微薄的工作(也许是在医院的餐厅?),现在为了度假花大价钱买了一件既不得体也不舒服的华丽衣服。
没关系,这不过是一种伪装罢了。
在这片陌生大陆的机场洗手间里,盖尔看到昨晚那深色的染发剂没有冲洗干净,现在已经混合着汗水印在了脖子上。
盖尔降落在布里斯班,还没有适应时差,炽热的太阳把她烤得头昏脑涨。她仍然穿着那条糟糕透顶的裙子,但是已经洗过了头发,免得染发剂再次随着汗水淌下来。
她叫了辆出租车。尽管已经非常累,但是不看看他们住的地方,她实在无法让自己平静下来。她早已经买好了地图,找到了艾尔路。那是一条短短的弯曲的马路。她让司机把她放在拐角处,那里有一家小小的杂货店。这很可能就是那两个人买牛奶,以及其他用完的日用品的地方吧,比如清洗剂、阿司匹林、卫生棉条。
盖尔和桑迪从未谋面这一事实显然是个不好的征兆,这可能意味着威尔很快就觉察到了什么。之后再想深挖出什么有用的描述就很难了。高,而不是矮;瘦,而不是胖;浅色头发,而不是深色。盖尔在脑海中描绘了一种形象,就是那种长腿短发、充满活力、带着男孩般魅力的女孩,应该说,女人。但如果与桑迪擦肩而过,盖尔根本就认不出她来。
会有人认出盖尔吗?戴着墨镜,头发大变样,盖尔觉得自己的形象迥异于从前,简直像隐身了一样。身处异国这一事实也让她有所改变,她还没调整好自己。一旦调整好了,她也许再也做不出现在这些大胆的事情。她必须现在就走过马路、去看看那座房子,否则就可能永远也去不了了。
出租车从棕黄色的河边沿着陡峭的公路向上攀爬,艾尔路通向山脊。这是一条布满灰尘的小路,没有人行道,也没有树荫,没有路过的行人,也没有来往的车辆。路边是木板制成的栅栏,或是某种枝条编成的——篱笆?——有时候是高高的树篱,上面开满了花。不,那些其实不是花,而是一些粉紫色或者深红色的叶子。篱笆后面都是盖尔不熟悉的树木,它们的叶子粗糙,上面落满了灰土,树皮呈鳞状或者纤维状,不过是种粗陋的装饰罢了。而且,树上似乎笼罩着一种冷漠而模糊的欲望,盖尔觉得这种欲望跟热带相关。她前面的路上走着两只雌珍珠鸡,一本正经得可笑。
威尔和桑迪的房子掩藏在一排木栅栏后面,漆成了淡绿色。盖尔的心缩成了一小团——看到栅栏,看到淡绿色,她的心疼得缩了起来。
这条路是个死胡同,所以她还得返回来,还要再次走过那座房子。在栅栏中间留着汽车进出的门,那里还有个信箱。她在另一座房子前的栅栏上也看到过这种信箱。她之所以能注意到,是因为插在里面的杂志还露着半截。也就是说,邮箱并不很深,要是伸进去一只手,也许能摸到里面的信——要是屋里的人还没把信取走的话。然后,盖尔真的把手伸了进去,她没办法控制自己。就像之前所想的那样,里面真的有一封信,她把它装进了自己的手袋。
她在街角的商店叫了一辆出租车。“你是美国哪里来的?”商店里的人问她。
“得克萨斯州。”她说。盖尔觉得人们好像总是希望你是得克萨斯来的。果然,那男人抬了抬眉毛,吹了声口哨。
“我早就这么觉得。”他说。
信封上是威尔自己的字。这不是一封写给威尔的信,而是他寄出去的信,写给霍特里街491 号的凯瑟琳?索纳比,也是在布里斯班。还有另一个人的笔迹在上面潦草地写道:“退回寄件人,9 月13 日去世。”有一瞬间,盖尔在混乱的意识中,还以为上面的“去世”指的是威尔的死讯。
她必须冷静下来,好好整理思绪,最好能暂时躲开这暴晒的烈日。但是,她在旅馆里读完了信,梳洗了一下,就立刻又叫了一辆出租车,这次是去霍特里街。就和她所期待的一样,那里的窗户上挂着个牌子,写着:“出租公寓。”
不过,威尔在那封写给霍特里街的凯瑟琳的信中说了些什么呢?
选自艾丽丝·门罗《快乐影子之舞》之《明信片》
(……)
那天下午,我不停地想,我觉得克莱尔会来看看我,至少也会给我打电话。那么,我就可以问他,他以为他在干什么。我自己在心里设想他会给我的几个发疯的理由,比如这个可怜的女人得了癌症,只能再活六个月,她一直穷困潦倒(是他住的酒店里的清洁工),因此他想给她一段安宁时光。或者她因一桩不道德的交易敲诈他妹夫,因此他娶了她,以便让她闭嘴。不过,我没有时间编太多故事,客人川流不息。老太太们气喘吁吁地爬上楼,送给我一个个给孙子买生日礼物的故事,看来朱比利的每一个孙子都是三月过生日。他们应该感谢的是我,我想,难道不是我给他们的生日增添的乐趣吗?就连阿尔玛,看起来也比冬天的气色好了。我想我不是责备她,只不过是个事实。而且,谁知道呢,也许我也一样,如果唐·斯通豪斯像他的威胁那样跑来强奸她,给她从头到脚留一身发紫的伤痕——这是他的话,不是我说的。我肯定会很难过,会尽我所有地帮助她。但是我可能会想,好吧,出事儿都这么可怕,出了事儿,这个冬天真漫长啊。
即使我不想回家吃晚饭也没用,事情要由妈妈来告一段落。她做了大马哈鱼面包、甘蓝和胡萝卜沙拉,里面还放了葡萄干,都是我喜欢吃的,还有苹果布丁。但是,吃了一半,眼泪就流过她脸上的胭脂。“我就是觉得,如果必须有人要哭,应该是我。”
我问:“你有什么倒霉事儿?”
“嗯,我这么喜欢他。”她说,“我那么喜欢他。到了我这把年纪,不会有多少人是我整个星期都会盼望他来的了。”
“嗯哪,我也为你难过。”我说。
“不过,一旦男人对一个女孩失去了尊重,他就会很快厌倦她的。”
“你说这个什么意思,妈妈?”
“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你应该觉得羞愧。”我也开始哭。“对自己的女儿说这样的话。”好了!我一直以为她根本就不知道。不怪克莱尔,当然,怪的是我。
“不会,应该觉得羞愧的不是我。”她抽泣,继续说,“我已经老了,但是我知道。要是男人对女孩不尊重,就不会娶她了。”
“要是真这样,咱们镇大概就没有婚姻了。”
“你自己毁了自己的机会。”
“他来这里的时候,你这种话一句也没有说过。现在,我不想听了。”我说完,转身上楼。她没有跟上来。我坐下来,抽烟,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我没有脱衣服。我听到她上楼,上床。然后,我下了楼,看了一会儿电视,交通事故的新闻。我穿上外套,出了门。
一年前的圣诞节,克莱尔送给我一辆小车,一辆小型莫里斯。我不会开车去上班,两个半街区也开车去,实在太蠢了,就像炫耀似的,尽管我知道有人会这么做。我进了车库,把车倒出来。星期天我开车带妈妈去塔珀镇看住在养老院里的凯姨妈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用过车。夏天的时候,我开车的机会多一些。
我看了看表,吓了一跳。十二点二十分。坐的时间太长了,我虚弱得直哆嗦。这会儿,我想要吃一颗阿尔玛的药了。我有种只想飞起来开出去的念头,但是,我不知道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我绕着朱比利的大街开,一路上,除了我自己的车,没看见别的汽车。所有的房屋都在黑暗笼罩下,街道黑漆漆的,最后一场雪让院子发白了。我似乎觉得,这每一幢房子里住的人,都知道我所不知道的事情。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也许早就知道将会是如此结果,而我是唯一不知情的人。
我开出了格罗夫街,上了明尼街,看见了他家后面。没有灯光。我绕到前头看。他们难道也要蹑手蹑脚上楼,再打开电视机吗?我想知道。屁股像三角钢琴的女人,估计是做不到的吧。我敢肯定他直接带她上楼,进老太太的房间,说:“这位是麦奎恩家的新太太。”
我停了车,摇下车窗。我甚至都没想要做什么,便靠在了喇叭上,让它响,响到我自己不能忍受为止。
这种声音让我如释重负,我可以尖叫了。于是我尖叫。“咳!克莱尔·麦奎恩,我想和你谈一谈。”
没有人回答。“克莱尔·麦奎恩!”我冲着他黑暗的房子大喊大叫,“克莱尔你出来!”我又按响了喇叭,两声,三声,我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少声。不按喇叭的时候,我就嚷嚷。我感觉仿佛就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看着自己。过了一会儿,我握紧拳头,尖叫,按喇叭。我失态地继续胡闹,怎么想就怎么做。某种程度上说,我颇为享受。我甚至都快忘记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了。我有节奏地按喇叭,同时大叫道:“克莱尔,你不打算出来?克莱尔·麦奎恩五月果,要是他不来,我们就离开他① ……”我一边哭,一边叫,就在大街上,也不觉得有什么。
“海伦,你是不是要把全镇人都叫醒?”巴迪·希尔兹说,脑袋贴在我的车窗户上。他是值夜班的巡警,我以前在周日学校教过他。
“我只是为新婚夫妻表演一曲喧闹的庆祝。”我回答说,“有什么问题吗?”
“我不得不告诉你,请不要发出这种噪音。”
“我还不想停下。”
“哦,是的,海伦,你不过是有点心烦而已。”
“我叫了又叫,他还是不出来。”我说,“我只是想叫他出来。”
“嗯,好吧,你得做个好姑娘,不要再按喇叭。”
“我想叫他出来。”
“停。不要再按喇叭,一次也不行。”
“那你能叫他出来?”
“哦,海伦,如果一个人不想走出自己家门,我不能叫他出来。”
“我以为你是法律,巴迪·希尔兹。”
“是,不过,法律能做的也有限。要是你想见他,为什么你不能白天再来,敲开他家的门,这样的做法是不是更适合女士?”
“要是你不知道的话,我告诉你,他结婚了。”
“哦,海伦。他晚上和白天一样,都结婚了。”
“你觉得很好笑吧?”
“哦,不,不太好笑,我想是真的。现在,要么你换个位置,让我开车送你回家?看看这条街的灯,格蕾丝·比彻在看着我们。我看见霍姆斯家的窗户开了。你不会想再给他们添上谈资吧?”
“反正他们除了说话以外,也没别的事儿可做,说我有什么不可以。”
巴迪·希尔兹站直身体,离车窗稍稍远了一点,我看见有个穿黑衣服的人穿过麦奎恩家的草坪。正是克莱尔。他穿的不是睡衣,他穿戴整齐,衬衫、长裤和夹克衫。我坐在那儿等着听,听我自己会说什么。他径直向车子走过来了。他一点也没变,他是个胖胖的,愉快的,神情带有睡意的男人。仅仅是他的外表,和平时一样的随和表情,便让我不再想尖叫,不再想哭泣。我本可以又哭又叫,直到自己的脸变绿。不过,这也不会让他的表情有什么改变,甚至没能让他起床和穿过他家院子的速度快一点点。
“海伦,回家吧。”他说,仿佛我们在一起看了一晚上的电视,现在到我回家上床睡觉的时候了,“转达我对你妈妈的问候。回家吧。”
这就是他想说的话。他看看巴迪说:“你开车送她?”巴迪说是。我看着克莱尔·麦奎恩,想,这是一个一意孤行的男人。当他做了弃我而不顾的事情时,我的感受也不会让他烦恼;即使是他结婚的当时,我在街上大吵大闹,也不会让他烦恼。他是不会解释的那种男人,也许根本没有解释,要是有什么他没法解释的,好吧,他会直接忘掉。现在,他所有的邻居都在看着我们,但是明天,在街上遇见的时候,他会和他们说笑话。那么,我呢?也许某一天,他在街上遇见我,他只会说:“你还好吗,海伦?”然后和我开个玩笑。要是我早想明白他是什么样的人,要是我早点留心克莱尔·麦奎恩,和他的相处开始就会大为不同,也许感受也会不同,尽管老天才知道那样到最后又有什么要紧呢。
“现在,你有没有觉得闹这么大的动静很抱歉?”巴迪说。我滑到旁边的位置上,看着克莱尔回家。我想,是了,我本就应该留心。巴迪说:“现在,你不会再打扰他和他的太太了吧?海伦?”
“什么?”我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