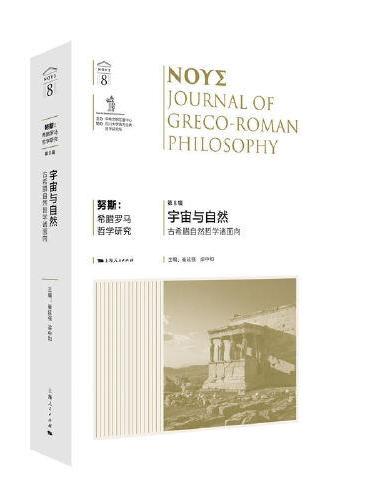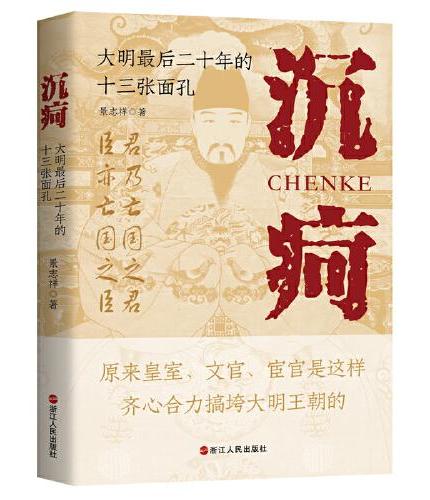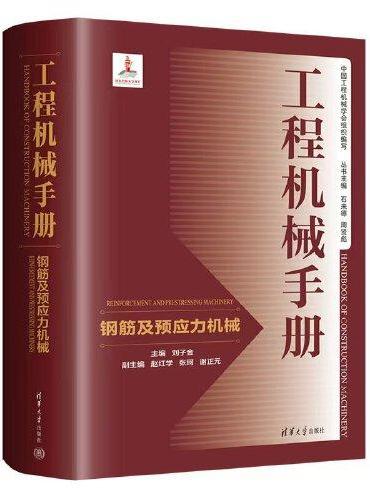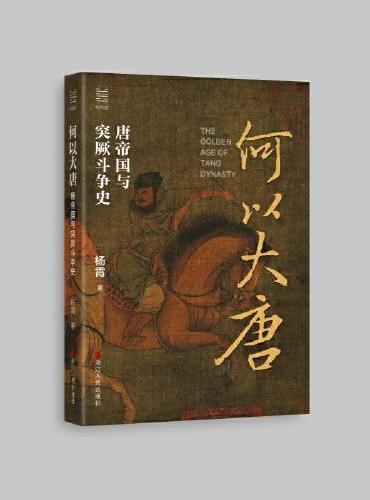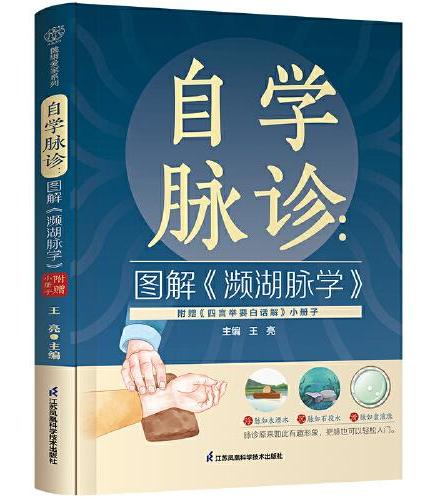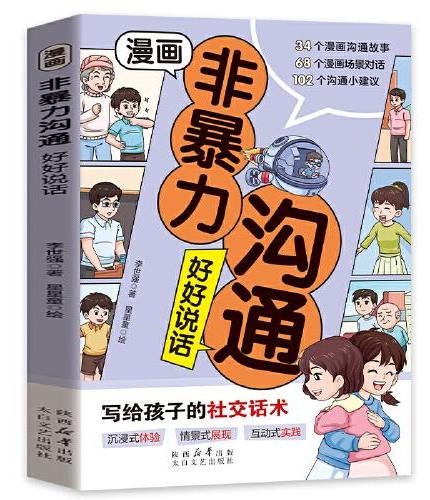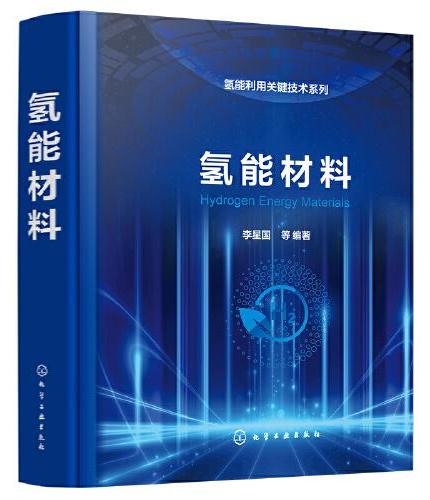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华南主要观赏树木图鉴
》
售價:HK$
17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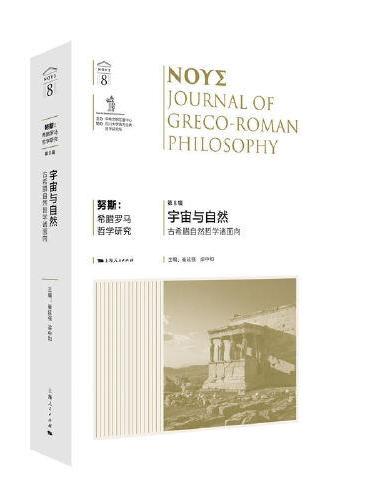
《
努斯:希腊罗马哲学研究(第8辑)--宇宙与自然:古希腊自然哲学诸面向
》
售價:HK$
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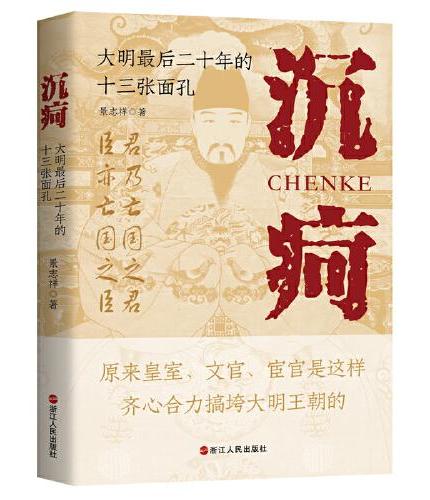
《
沉疴:大明最后二十年的十三张面孔
》
售價:HK$
5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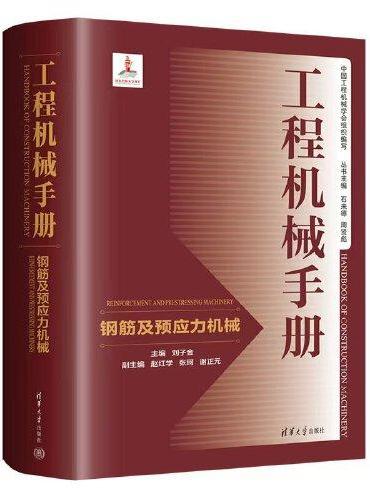
《
工程机械手册——钢筋及预应力机械
》
售價:HK$
36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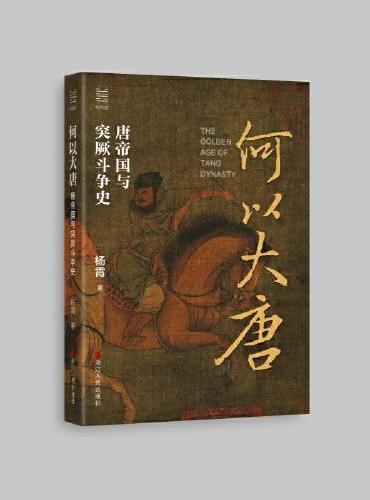
《
何以中国·何以大唐:唐帝国与突厥斗争史
》
售價:HK$
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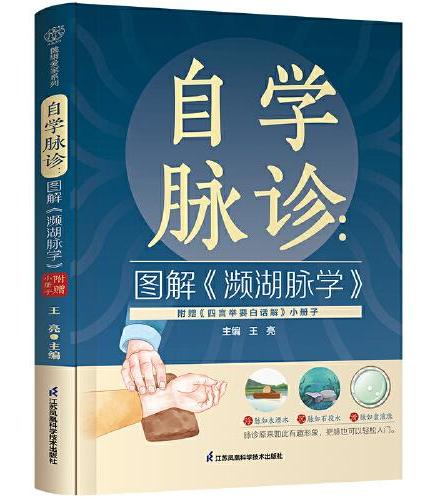
《
自学脉诊:图解《濒湖脉学》
》
售價:HK$
4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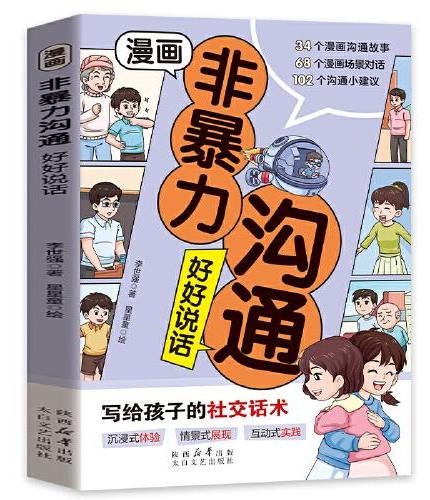
《
漫画非暴力沟通 好好说话写给孩子的社交话术让你的学习和生活会更加快乐正面管教的方式方法 教会父母如何正确教育叛逆期孩子 用引导性语言教育青少年男孩女孩 帮助孩子拥有健康心理的沟通方法
》
售價:HK$
5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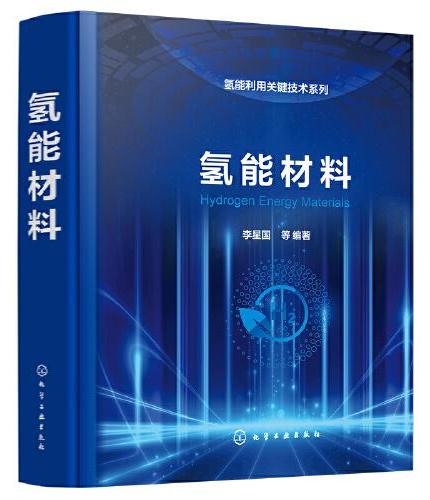
《
氢能利用关键技术系列--氢能材料
》
售價:HK$
393.8
|
| 編輯推薦: |
周作人最详尽最全面的回忆录 根据手稿全新校订
首度全面回顾一生重要经历
祖父科场案 兄弟失和 北大授课 元旦遇刺 敌伪任职 监狱生活
细述亲历之近现代重要史事
辛亥革命 张勋复辟 新文化运动 五卅 三一八 北伐 清党
了解近现代中国历史文化必读之作
|
| 內容簡介: |
|
《知堂回想录》是周作人晚年回顾自己一生重要经历,兼及诗与真实而成之内容丰富的传世巨作。最初只有“北大感旧录”数节,值曹聚仁在香港办《循环日报》,周作人以稿件寄之,在副刊发表,引发关注。后受曹聚仁之邀开始“一生回想”,历时两年多,成文二○七节。手稿总题为“药堂谈往”,出版时改名“知堂回想录”。作为现代文学大家,周作人亲身经历与参与了中国近现代史上诸多重要历史事件,如晚清光复会秋瑾、徐锡麟等的活动、辛亥革命、张勋复辟、新文化运动等,其一生形迹记录即是重要史料。又出之以如面谈之知堂文风,可谓文学性与史料性兼具。难怪促成本书出版的曹聚仁先生说:“这么好的回忆录,如若埋没了不与世人相见,我怎么对得住千百年后的中国文化界?”
|
| 關於作者: |
|
周作人(1885-1967),现代作家、翻译家,原名櫆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绶,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等。浙江绍兴人。青年时代留学日本,与兄树人(鲁迅)一起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五四时期任教北京大学,在《新青年》《语丝》《新潮》等多种刊物上发表文章,论文《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诗《小河》等均为新文学运动振聋发聩之作。首倡美文,《喝茶》《北京的茶食》等创立了中国美文的典范。在外国文学艺术的翻译介绍方面,尤其钟情希腊日本文学,贡献巨大。著有自编集《艺术与生活》《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等三十多种,译有《日本狂言选》《伊索寓言》等。
|
| 目錄:
|
第一卷
一 缘起
二 老人转世
三 风暴的前后上
四 风暴的前后中
五 风暴的前后下
六 避难
七 关于娱园
八 书房
九 三味书屋
一○ 父亲的病上
一一 父亲的病中
一二 父亲的病下
一三 炼度
一四 杭州
一五 花牌楼上
一六 花牌楼中
一七 花牌楼下
一八 四弟
一九 县考
二○ 再是县考
二一 县考的杂碎
二二 县考的杂碎续
二三 义和拳
二四 几乎成为小流氓
二五 风暴的余波
二六 脱逃
二七 夜航船
二八 西兴渡江
二九 拱辰桥
三○ 青莲阁
三一 长江轮船
三二 路上的吃食
三三 南京下关
三四 入学考试
三五 学堂大概情形
三六 管轮堂
三七 上饭厅
三八 讲堂功课
三九 打靶与出操
四○ 点名以后
四一 老师一
四二 老师二
四三 风潮一
四四 风潮二
四五 考先生
四六 生病前
四七 生病后
四八 祖父之丧
四九 东湖学堂
五○ 东湖逸话
五一 我的新书一
五二 我的新书二
五三 我的笔名
五四 秋瑾
五五 大通学堂的号手
五六 武人的总办
五七 京汉道上
五八 在北京一
五九 在北京二
六○ 北京的戏
六一 鱼雷堂
六二 吴一斋
六三 五年间的回顾
六四 家里的改变
第二卷
六五 往日本去
六六 最初的印象
六七 日本的衣食住上
六八 日本的衣食住中
六九 日本的衣食住下
七○ 结论
七一 下宿的情形
七二 学日本语
七三 筹备杂志
七四 徐锡麟事件
七五 法豪事件
七六 中越馆
七七 翻译小说上
七八 翻译小说下
七九 学俄文
八○ 民报社听讲
八一 河南—新生甲编
八二 学希腊文
八三 邬波尼沙陀
八四 域外小说集—新生乙编
八五 蒋抑卮
八六 弱小民族文学
八七 学日本语续
八八 炭画与黄蔷薇
八九 俳谐
九○ 大逆事件
九一 赤羽桥边
九二 辛亥革命一—王金发
九三 辛亥革命二—孙德卿
九四 辛亥革命三—范爱农
九五 望越篇
九六 卧治时代
九七 在教育界里
九八 自己的工作一
九九 自己的工作二
一○○ 自己的工作三
一○一 自己的工作四
一○二 金石小品
一○三 故乡的回顾
第三卷
一○四 去乡的途中一
一○五 去乡的途中二
一○六 从上海到北京
一○七 绍兴县馆一
一○八 绍兴县馆二
一○九 补树书屋的生活
一一○ 北京大学
一一一 往来的路
一一二 复辟前后一
一一三 复辟前后二
一一四 复辟前后三
一一五 蔡孑民一
一一六 蔡孑民二
一一七 蔡孑民三
一一八 林蔡斗争文件一
一一九 林蔡斗争文件二
一二○ 林蔡斗争文件三
一二一 卯字号的名人一
一二二 卯字号的名人二
一二三 卯字号的名人三
一二四 三沈二马上
一二五 三沈二马下
一二六 二马之余
一二七 五四之前
一二八 每周评论上
一二九 每周评论下
一三○ 小河与新村上
一三一 小河与新村中
一三二 小河与新村下
一三三 文学与宗教
一三四 儿童文学与歌谣
一三五 在病院中
一三六 西山养病
一三七 琐屑的因缘
一三八 爱罗先珂上
一三九 爱罗先珂下
一四○ 不辩解说上
一四一 不辩解说下
一四二 吗嘎喇庙
一四三 顺天时报
一四四 顺天时报续
一四五 女师大与东吉祥一
一四六 女师大与东吉祥二
一四七 语丝的成立
一四八 五卅
一四九 三一八
一五○ 中日学院
一五一 东方文学系
一五二 东方文学系的插话
一五三 坚冰至
一五四 清党
第四卷
一五五 北大感旧录一
一五六 北大感旧录二
一五七 北大感旧录三
一五八 北大感旧录四
一五九 北大感旧录五
一六○ 北大感旧录六
一六一 北大感旧录七
一六二 北大感旧录八
一六三 北大感旧录九
一六四 北大感旧录十
一六五 北大感旧录十一
一六六 北大感旧录十二
一六七 道路的记忆一
一六八 道路的记忆二
一六九 女子学院
一七○ 在女子学院被囚记
一七一 北伐成功
一七二 章太炎的北游
一七三 打油诗
一七四 日本管窥
一七五 日本管窥续
一七六 北大的南迁
一七七 元旦的刺客
一七八 从不说话到说话
一七九 反动老作家一
一八○ 反动老作家二
一八一 先母事略
一八二 监狱生活
一八三 在上海迎接解放
一八四 我的工作一
一八五 我的工作二
一八六 我的工作三
一八七 我的工作四
一八八 我的工作五
一八九 我的工作六
一九○ 拾遗甲
一九一 拾遗乙
一九二 拾遗丙
一九三 拾遗丁
一九四 拾遗戊
一九五 拾遗己
一九六 拾遗庚
一九七 拾遗辛
一九八 拾遗壬
一九九 拾遗癸
二○○ 拾遗子
二○一 拾遗丑
二○二 拾遗寅
二○三 拾遗卯
二○四 拾遗辰
二○五 拾遗巳
二○六 拾遗午
二○七 后记
后序
|
| 內容試閱:
|
一 缘起
我的朋友陈思先生前几时写信给我,劝我写自叙传,我听了十分惶恐,连回信都没有写,幸而他下次来信,也并不追及,这才使我放了心。为什么这样的“怕”写自叙传的呢?理由很是简单,第一是自叙传很难写。既然是自叙传了,这总要写得像个东西,因为自叙传是文学里的一品种,照例要有诗人的“诗与真实”掺和在里头,才可以使得人们相信,而这个工作我是干不来的。第二是自叙传没有材料。一年一年的活了这多少年岁,到得如今不但已经称得“古来稀”了,而且又是到了日本人所谓“喜寿”,(喜字草书有如“七十七”三字所合成,)那么这许多年里的事情尽够多了,怎么说是没有呢?其实年纪虽是古稀了,而这古稀的人乃是极其平凡的,从古以来不知道有过多少,毫没有什么足以称道的,况且古人有言,“寿则多辱”,结果是多活一年,便多有一年的耻辱,这有什么值得说的呢。
话虽如此,毕竟我的朋友的意思是很可感谢的。我虽然没有接受他原来的好意,却也不想完全辜负了他,结果是经过了几天考虑之后,我就决意来写若干节的“药堂谈往”,也就是一种感旧录,本来旧事也究竟没甚可感,只是五六十年前的往事,虽是日常琐碎事迹,于今想来也多奇奇怪怪,姑且当作“大头天话”(儿时所说的民间故事)去听,或者可以且作消闲之一助吧。
时光如流水,平常五十年一百年倏忽的流过去,真是如同朝暮一般,而人事和环境依然如故,所以在过去的时候谈谈往事,没有什么难懂的地方,可是现在却迥不相同了。社会情形改变得太多了,有些一二十年前的事情,说起来简直如同隔世,所谓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我想这就因为中间缺少连络的缘故。老年人讲故事多偏于过去,又兼讲话唠叨,有地方又生怕年青的人不懂,更要多说几句,因此不免近于烦琐,近代有教养的青年恐不满意,特在此说明,特别要请原谅为幸。
二 老人转世
我于前清光绪十年甲申十二月诞生,实在已是公元一八八五年的一月里了。照旧例的干支说来,当然仍是甲申,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确是多难的一年,法国正在侵略印度支那,中国战败,柬蒲寨就不保了。不过在那时候,相隔又是几千里,哪里会有什么影响,所以我很是幸运的,在那时天下太平的空气中出世了。
我的诞生是极平凡的,没有什么事先的奇瑞,也没有见恶的朕兆。但是有一种传说,后来便传讹,说是一个老和尚转生的,自然这都是迷信罢了。事实是有一个我的堂房阿叔,和我是共高祖的,那一天里出去夜游,到得半夜里回来,走进内堂的门时,仿佛看见一个白须老人站在那里,但转瞬却是不见了。这可能是他的眼花,所以有此错觉,可是他却信为实有,传扬出去,而我适值恰于这后半夜出生,因为那时大家都相信有投胎转世这一回事,也就信用了他,后来并且以讹传讹的说成是老和尚了。当时我对这种浪漫的传说,颇有点喜欢,一九三一年曾经为人写一单条云:
“一月三十日晨,梦中得一诗云,偃息禅堂中,沐浴禅堂外,动止虽有殊,心闲故无碍。族人或云余前身为一老僧,其信然耶。三月七日下午书此,时杜逢辰君养病北海之滨,便持赠之,聊以慰其寂寞。”本来是想等裱装好了送去,后乃因循未果,杜君旋亦病重谢世了。两三年之后,我做那首打油诗,普通被称为“五十自寿”的七律,其首联云:“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即是用的这个故典,我自信是个“神灭论者”,如今乃用老人转世的故典,其打油的程度为何如,正是可想而知了。
因为我是老头子转世的人,虽然即此可以免于被称作
“头世人”,—谓系初次做人,故不大懂得人世的情理,至于前世是什么东西,虽然未加说明,也总是不大高明的了,—但总之是有点顽梗,其不能讨人们的喜欢,大抵是当然的了。我不想举出事实,也实在没有事实,可以证明这事,现在只想一讲我在四五岁的年头上遇着的一个大灾难,即是出天花,这不但几乎夺去了我的生命,而且即使性命保全了,却变了麻子,一个麻脸的老和尚,这是多么的讨厌的东西呀!说到这里,应当赶紧的声明一句,幸而二者都不,这是对于我的祖母母亲的照顾应该感谢的。
痘为小儿的一大病,凡人都要经过这一难关。但是只要人工的种过痘,无论土法或洋法这便是牛痘,就可保无危险,可怕的痘神给种的“天然痘”,它的死亡率不知百分之几,幸免的也要脸上加上密圈。我所出的便是这种“天花”。据说在那偏僻地方,也有打官话的医官有时出张,施种牛痘,但是在那两三年内大约医官不曾光临,所以也就淡然处之,直待痘儿哥哥或痘儿姐姐来给种上了。那时是我先出天花,不久还把只有周岁左右的妹子也给感染了。妹子名叫端姑,如果也是在北京的祖父给取的名字,那么一定也是得家信的这一天里,有一位姓端的旗籍大员适值来访,所以借用的,不过或者是女孩,不用此例,也未可知。据说这个妹子长得十分可喜,有一回我看她脚上的大拇趾,太是可爱了,便不禁咬了它一口,她大声哭了起来,大人急忙走来,才知道是我的顽劣行为。当天花初起时,我的症状十分险恶,妹子的却很顺当,大家正很放心,把两个孩子放在一间房里睡,有一天两人都在睡觉,忽然听见呀的叫了一声。(不知道是谁在叫,据推测这是天花鬼的叫声,它从我这边出来,钻到妹子那里去了,那么在我也没有叫唤之必要,所以只好存疑了。)大人惊起看时,妹子的痘便都已陷入,我却显是好转了。急忙的去请天花专门的王医师来看,已经来不及挽回,结果妹子终于死去,后来葬在龟山的山后,父亲自己写了“周端姑之墓”五个字,凿一小石碑立于坟前,直到一九一九年鲁迅回去搬家,才把这坟和四弟的坟都迁葬于逍遥溇的。
鲁迅在种牛痘的时候,也只有两三岁光景,但他对于当时情形记得清清楚楚,连医官的墨晶大眼镜和他的官话,都还不曾忘记,我出天花是四五岁了,比他那时要大两三岁,可是什么都不记得了。只是听大人们追述,这才知道一点,据说因为病人发热怕光,一半也因了迷信关系,把房间窗门都用红纸糊封,而且还把眼睛也糊了红纸。这当时不晓得是否玩笑话,但听去又像在讲真话,所以我那眼睛实在有没有被封过,封了又是什么用意,现在已经无法质询,因此无从知道了。在天花结痂的时候,据说很是要紧,因为很痒不免要去搔爬,而这一搔爬可就坏了大事,脸上麻点的有无或多少,就在这里决定了。我是幸亏祖母看得很好,将两只手紧紧的捆住了,不让它动一动,当时虽然很窘,大约哭得很凶吧,然而也因此得免于脸上雕花,这与我的出天花而幸得不死,都是很可庆幸的。
我在十岁以前,生过的病很多,已经都记不得,而且中医的说法都很奇怪,所以更说不清是食裹火或火裹痰了。不过其中顶利害的是因为没有奶吃,所以雇了一个奶妈,而这奶妈原来也是没有什么奶的,为的骗得小孩不闹,便在门口买种种东西给他吃,结果自然是消化不良,瘦弱得要死,可是好像是害了馋痨病似的,看见什么东西又都要吃。为的对症服药,大人便什么都不给吃,只准吃饭和腌鸭蛋,—这是法定的养病的唯一的副食物。这在馋痨病的小孩一定是很苦痛的,但是我也完全不记得了,这是很可感谢的。只记得本家的老辈有时提起说:
“二阿官那时的吃饭是很可怜相的,每回一茶盅的饭,一小牙(四分之一)的腌鸭子,到我们的窗口来吃。”她对我提示这话,我总是要加以感谢的,虽然在她同情的口气后面,可能隐藏着有什么恶意,因为她是挑拨离间的好手,此人非别,即鲁迅在《朝花夕拾》里所写的“衍太太”是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