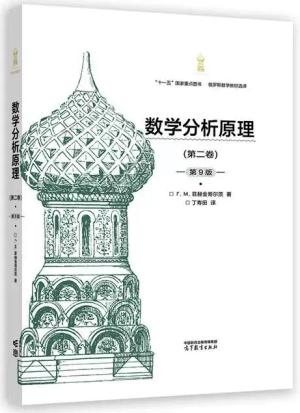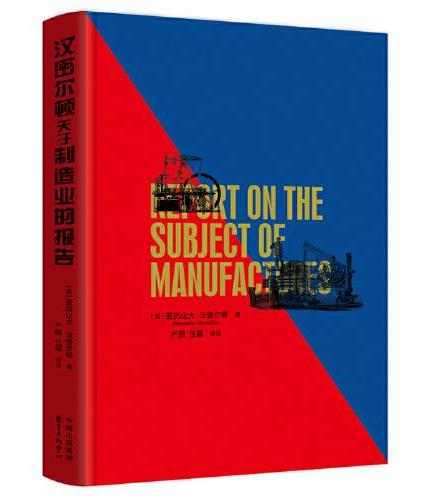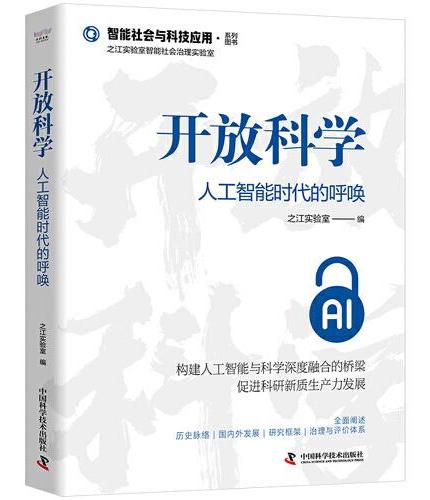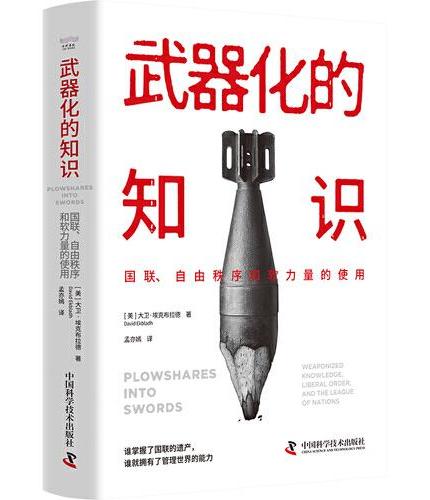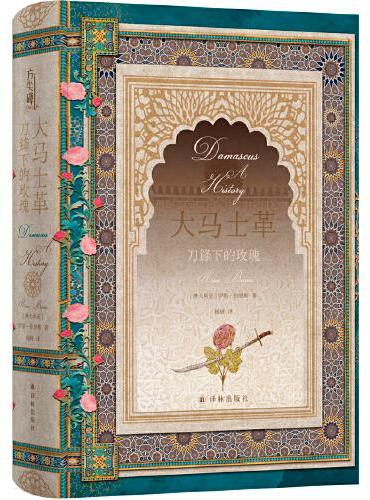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我活下来了(直木奖作者西加奈子,纪实性长篇散文佳作 上市不到一年,日本畅销二十九万册)
》
售價:HK$
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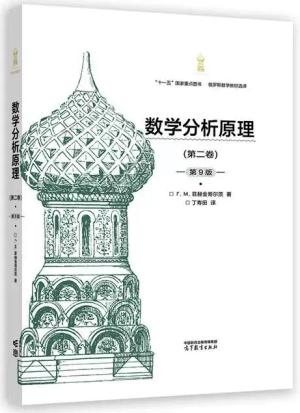
《
数学分析原理(第二卷)(第9版)
》
售價:HK$
86.9

《
陈寅恪四书
》
售價:HK$
31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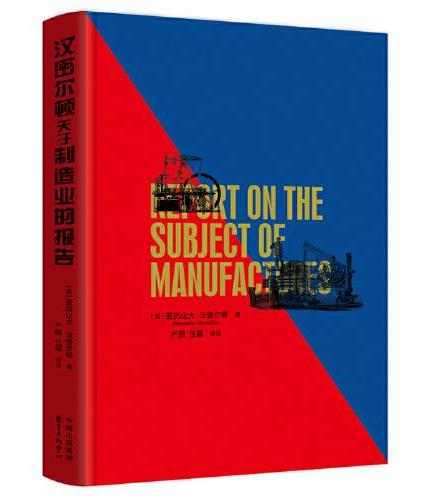
《
汉密尔顿关于制造业的报告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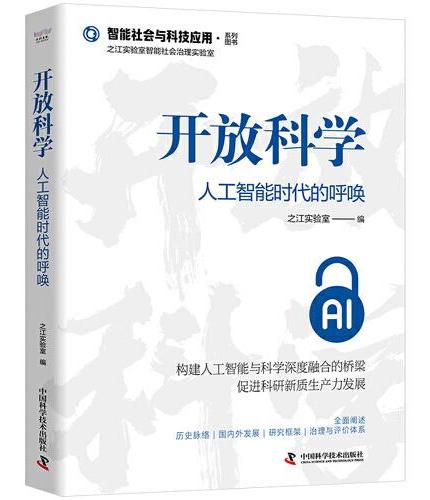
《
开放科学:人工智能时代的呼唤
》
售價:HK$
10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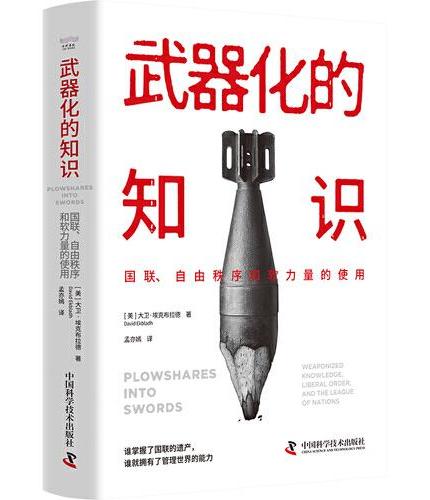
《
武器化的知识:国联、自由秩序和软力量的使用
》
售價:HK$
8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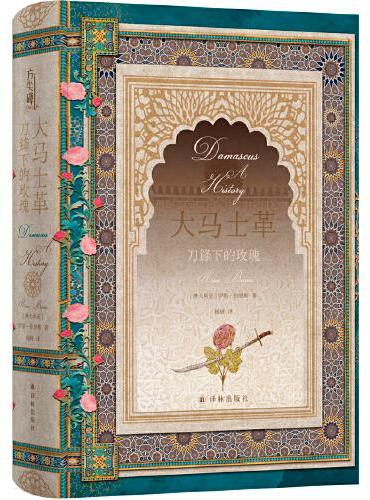
《
大马士革:刀锋下的玫瑰(方尖碑)
》
售價:HK$
130.9

《
造脸:整形外科的兴起(医学人文丛书)
》
售價:HK$
85.8
|
| 編輯推薦: |
|
他被称作一代人的冷峻良知,他一语道破被蒙蔽的事实他是奉了上帝的旨意来目睹现实的寒冷,揭示出最丑陋的灵魂在这个不能自由言说的世界里,他一直在高声呐喊他说:请坚持,并且握紧拳头
|
| 內容簡介: |
|
他贫窘的一生在最后一年得到一劳永逸的改观,他却来不及享受,那享受或许是无法抵抗的沉迷,唯有在痛苦中能保持清醒。他用优雅的句子去揭露谎言,华丽地撕开社会的伤口。韵律跳动的美妙背后,总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留下的所有,都值得一读。
|
| 關於作者: |
|
奥威尔,作家、记者和社会评论家,生于英属印度。他一生短暂,且受到了当局二十几年严密的监视,直到死。45岁时开始创作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1984》,该书于1949年6月出版后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只浅尝了这成功的滋味便因病去世,像是完成了他被赋予的最高使命。1949年10月13日,他和比他小16岁的杂志编辑索尼娅?布朗内尔小姐在病房里举行了婚礼,妻子却并不爱他。婚后一年,正和情人耳鬓厮磨的妻子接到电话,47岁的奥威尔死于肺部大出血。他满身才华,一生落魄,一度流浪度日,他的命运惹人唏嘘,却无法评价。
|
| 目錄:
|
我为什么写作
如此欢乐童年
书店回忆
射象
收容站
绞刑
不小心说漏了西班牙的秘密
回顾西班牙内战
好的蹩脚作品
查尔斯?里德
马拉喀什
唐纳德?麦克吉尔的艺术
英国本色
一杯好茶
诗歌和话筒
苦涩的复仇
一个书评家的自白
体育的精神
普通蟾蜍随想录
英国式谋杀的衰落
甘地沉思录
|
| 內容試閱:
|
我为什么写作
从很小的时候起,大概五六岁的样子,我就知道长大后我要成为一个作家。大约在十七到二十四岁这段时间里,我曾试图打消这个念头,但也意识到这么做是在违背自己的天性,觉得早晚我还是得安分下来著书写作。
三个孩子中我排行老二,老大和老三都与我相差五岁。八岁以前,我很少见到父亲。因为这个以及其他一些原因,那时我有些孤僻,很快我的言谈举止就不招人喜欢,在学校里变得很不合群。像其他孤僻的孩子一样,我总是编造各种故事,同臆想出来的人对话,我想从一开始,我的文学志向就同这种孤独寂寞以及受人冷落的感觉交织在了一起。我自知有驾驭文字的才能,有直面一切令人不快事实的能力,我觉得这为我创造了一片私人天地,每当面对生活中的失败时,我能在这片天地里得到宽慰。然而,我整个童年以及少年时期认认真真的或者说煞有介事的创作,加起来也不过寥寥五六页罢了。大概四五岁的时候,我生平第一次写诗,母亲把它抄录了下来。诗的具体内容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写得是关于一只老虎以及它“椅子般的牙齿”——这个词造得倒还不赖。不过我认为这首诗有抄袭布莱克
的《老虎,老虎》之嫌。十一岁时,一战(1914-1918)爆发,我写了一首爱国诗歌
,登上了当地的报纸。两年后,我另一首悼念基钦纳逝世的诗也在该报上发表。稍大一些后,我便不时用乔治亚风格来写一些蹩脚且通常是没有完成的“自然诗”。我也曾两次尝试写短篇小说,不过最后都以失败告终。这些便是那些年里我一本正经写下来的全部作品。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年间我确实从事过一些文学活动。首先要说的就是那些应付差事的写作,这些东西我写起来毫不费力、得心应手,但却不能汲乐其中。除了学校的功课外,我还写过一些应景诗,现在来看,当时创作这种半喜剧性诗歌的速度连我自己都觉得震惊——十四岁时,大概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就模仿阿里斯多芬
写了一整部押韵诗剧——此外,我还参与校刊的编辑工作,有印刷版的,也有手抄版的。这些校刊上都是你能想象出的最粗浅滑稽的文字,编辑起来毫不费力,就是现在我花在最没有价值报刊上的心思也要比它多。但在从事这些工作的同时,有大约十五年多的时间里,我还一直进行着另一项不同的文学练习:那是一部仅存在于我内心的日记,里面演绎着以我为主角的连续“故事”。我相信一般孩童和青少年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很小的时候,我就常常把自己想象成惊险刺激的冒险故事中的英雄人物,如罗宾逊似的绿林豪杰。但很快,我便不再沉溺于这种纯粹自我陶醉的“故事”中了,转而只是对我所做所见之事作客观的描述。有时候一连好几分钟,我的脑海里会出现诸如这样的句子:“他推门进了房间,一缕金黄色的阳光透过薄纱窗帘斜照在桌面上,上面有一个半开的火柴盒,平躺在墨水瓶旁边。他右手插在口袋里,径直走向了窗边,窗外大街上,一只花斑猫正在追逐一片枯叶”。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我大概二十五岁的时候,正好贯穿了我还未从事文学创作的那几年。尽管我不得不搜肠刮肚,而且也的确费尽心思去推敲斟酌合适的字眼,这种几近刻意的情景描述几乎已是不由自主,仿佛是由于来自外界的压力而导致的。不同时期我曾仰慕过不同的作家,我想我的“故事”一定反映了他们迥然各异的风格,但我记得,它总是秉承了相同的细致描述的特点。
大约十六岁时,我忽然感受到了词语本身的乐趣,即词语音调和连缀所带来的乐趣。《失乐园》 里有这样两句诗:
于是他负难而艰辛地
挺进:他负难而艰辛
现在读起来感觉已不甚稀罕了得,但当时却让我震撼不已,就连以“hee”替代“he”的拼法都让我倍觉欣喜。对于需要描述的事物,我早已了然于胸。因此,如果说当时我有心著书立作的话,我是很清楚自己想要写什么样书的。我想写大部头的自然主义小说,以悲剧结尾,不仅要饱含细致入微的描述和令人称奇的比喻,还要富于辞藻华丽的段落,其用词则一半是出于对词语本身音调的考虑。事实上,我第一部完整的小说《缅甸岁月》
就是这样一类书,虽说它是我而立之年的作品,但对其构思酝酿却是由来已久。
每种成就、每次进步都是源于勇气,源于自我磨砺和自我净化。
我不求驳倒理想,我只是严阵以待。
Nitimur
invetitum——努力破禁锢(奥维德《恋歌》Ⅲ):执此大纛,我的哲学有朝一日必将胜利,因为本质上被禁锢至今的,唯有真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