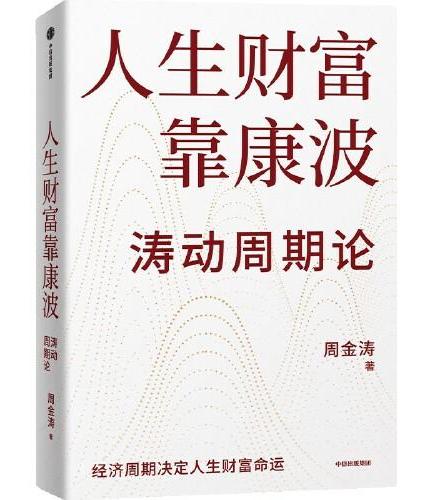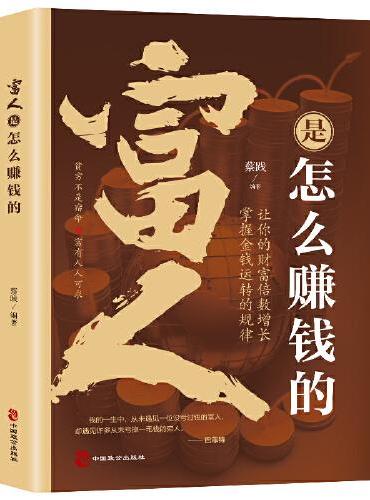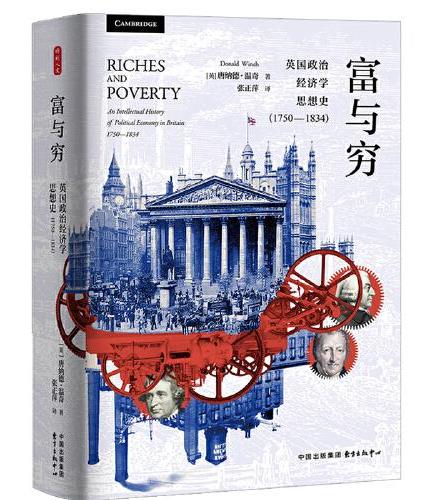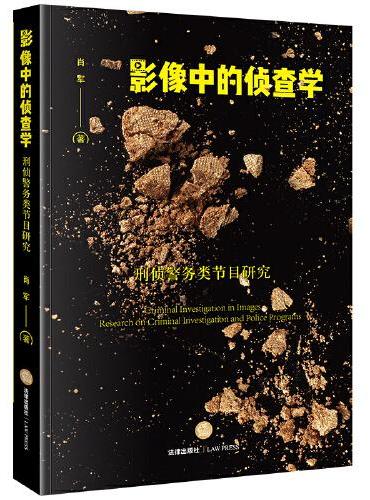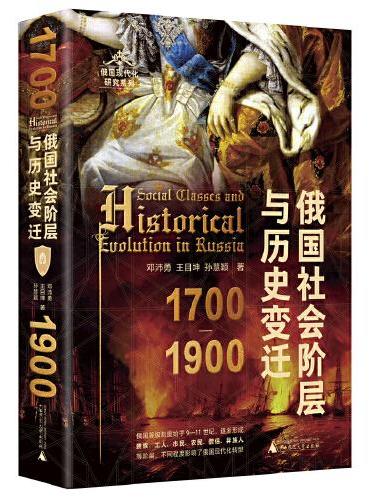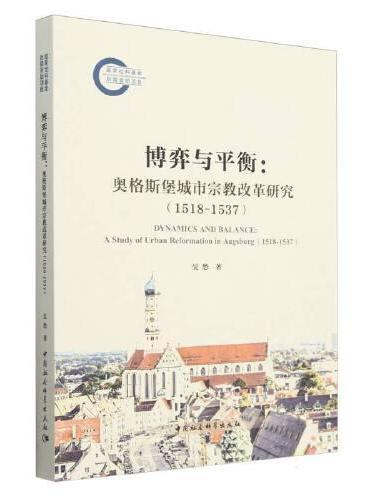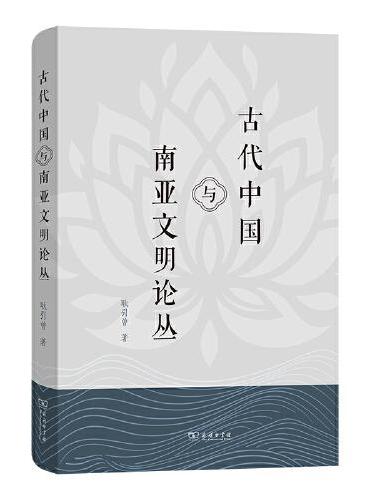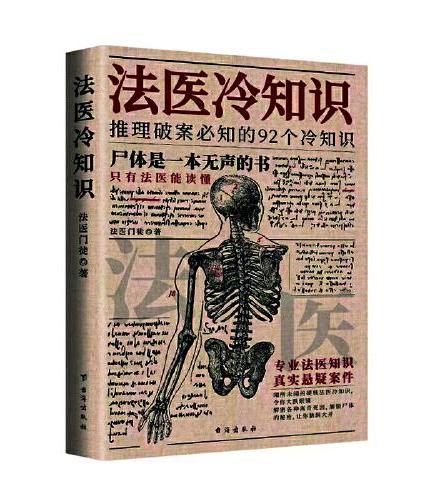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人生财富靠康波
》 售價:HK$
119.9
《
富人是怎么赚钱的
》 售價:HK$
74.8
《
时刻人文·富与穷:英国政治经济学思想史(1750—1834)
》 售價:HK$
107.8
《
影像中的侦查学:刑侦警务类节目研究
》 售價:HK$
52.8
《
俄国社会阶层与历史变迁(1700—1900)
》 售價:HK$
96.8
《
博弈与平衡:奥格斯堡城市宗教改革研究(1518-1537)
》 售價:HK$
118.8
《
古代中国与南亚文明论丛
》 售價:HK$
60.5
《
法医冷知识——尸体是一本无声的书,推理破案必知的92个冷知识 法医门徒 著
》 售價:HK$
65.8
內容簡介:
《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是行为科学奠基人,他的理论主题是人类社会的协调与平衡。书中他开宗明义就强调:工业文明的根本问题,是工业的飞速发展导致产生了社会的反常状态。近代国家都很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却忽视了更为本质的社会和人类问题。
關於作者:
乔治·埃尔顿·梅奥(1880—1949),美国管理学家,原籍澳大利亚,早期的行为科学——人际关系学说的创始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他出生在澳大利亚的阿得雷德,20岁时在澳大利亚阿得雷德大学取得逻辑学和哲学硕士学位,应聘至昆士兰大学讲授逻辑学、伦理学和哲学。后赴苏格兰爱丁堡研究精神病理学,对精神上的不正常现象进行分析,从而成为澳大利亚心理疗法的创始人。代表作有《工业文明的人类问题》《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
目錄
第一篇 科学与社会
內容試閱
第一章 进步的阴暗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