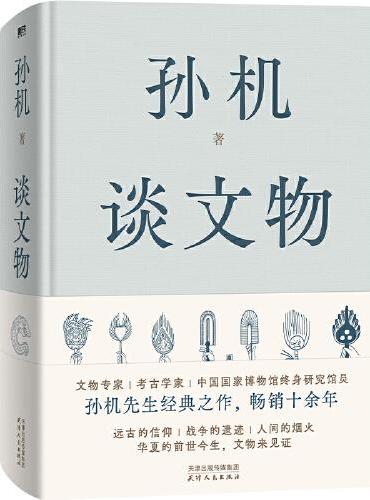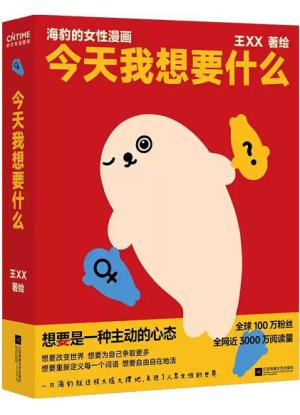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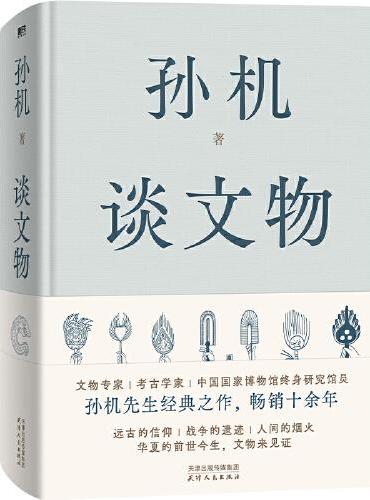
《
孙机谈文物
》
售價:HK$
118.8

《
诡舍(夜来风雨声悬疑幻想震撼之作)
》
售價:HK$
54.8

《
讲给青少年的人工智能
》
售價:HK$
52.8

《
海外中国研究·宋代文人的精神生活(经典收藏版)--重构宋代文人的精神内核
》
售價:HK$
107.8

《
埃勒里·奎因悲剧四部曲
》
售價:HK$
30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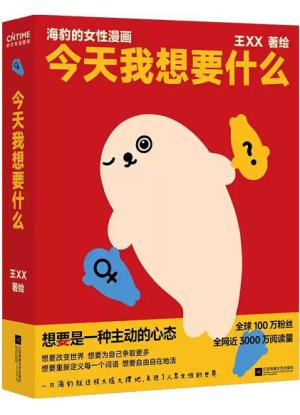
《
今天我想要什么:海豹的女性漫画
》
售價:HK$
74.8

《
日常的金字塔:写诗入门十一阶
》
售價:HK$
74.8

《
税的荒唐与智慧:历史上的税收故事
》
售價:HK$
107.8
|
| 編輯推薦: |
1、活跃在京城文化圈的,凤凰新媒体文化频道副主编、《不周山》系列文集的主编之一于一爽的首部随笔集,收录她两年内与吃饭喝酒有关的博客文章,披露京城文化圈酒桌生活众生相。
2、 解玺璋、张弛、大仙作序,高晓松、高群书、杨黎、狗子、冯唐、王小山、杨葵、大仙、张弛等联袂推荐。
3、 一个自认并不文艺的文艺女青年如何成长为京城酒局信息发布人的第一手饭醉记录。
|
| 內容簡介: |
|
被京城文化圈戏称为以酒成名的于一爽,文风干净利落,有如其酒风,属于愣、直给、二、迷乱、纵向纠结、横向拧巴,然后一烦了,说出一堆直刺人心的大实话。这本书单纯、直接、不掩饰、不做作地记录了她参与的许多酒局和饭局,也记录了这个时代的文化人们相聚、喝大和散场的姿势,拿得起、放得下,读起来很爽。
|
| 關於作者: |
|
于一爽,作家,媒体人。1984年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曾在《北京日报》、文汇出版社、盛大文学任职,现为凤凰新媒体文化频道副主编,在《北京青年报》、《经济观察报》等多家媒体发表过评论文章数十万字。
|
| 目錄:
|
辑一:这一年,没完
神秘树
二〇一一年六月一号,那个当晚
不明之地
二〇一一年六月一号,几天以前
湖边
二〇一一年六月四号,那几天
还是大董
二〇一一年六月五号,前两天
朋友家
二〇一一年六月六号,前两天
特吵一酒吧
二〇一一年六月六号,昨天
一坐一忘
二〇一一年六月九号,几个小时前
还是神秘树
二〇一一年六月九号,今晚
还是猜火车
二〇一一年七月一号,周日
四川仁
二〇一一年七月九号,昨天到今天
798
二〇一一年八月一号,昨天
冯唐家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一号,前些天
旺顺阁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一号,昨天
辑二:这一年,小一半
东局局长
二〇一一年一月一号
西局局长
二〇一一年一月一号
海底捞
二〇一一年一月一号,昨天
草场地
二〇一一年二月五号,上周六的后来,一年前
许仙楼
二〇一一年二月七号,一年前
北京的金山上
二〇一一年二月五号
三个贵州人
二〇一一年二月九号,昨天
渝信
二〇一一年三月一号,前两天
黄楼
二〇一一年三月三号,今天再后来
南锣鼓巷
二〇一一年三月三号,昨天的节前
秀兰小馆
二〇一一年四月一号,前两天的去年
一坐一忘——丹提——纳芳地
二〇一一年四月四号,前天到昨天
大董
二〇一一年四月九号,前两天的后来
秀兰小馆
二〇一一年四月九号,昨天
还是孔乙己
二〇一一年五月五号,前天
南门站
二〇一一年五月五号,周日到周五
纳芳地
二〇一一年五月九号,前两天
乌兰巴托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号,后半夜吧
辑三:上一年,就这点
鼓楼
二〇一〇年七月七号,昨天
孔乙己
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九号,前两天
体育大学
二〇一〇年八月八号,上周一往回退二十多年
猜火车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五号,前天
火星西路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五号,昨天
鼓楼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号,昨天和今天中午
微薄之盐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五号,周日第二天
宋庄——青岛——金鼎轩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一号,上周五的后来
SOHO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一号,昨天下午和晚上
愚公移山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五号,一下午
还是SOHO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九号,昨天和那天
工体西门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二号,前几天到第二天
兄弟川菜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一号,昨天晚上
圣诞节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五号,昨天晚上后来
苹果的店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九号,前两天周六日
总结:这一年
|
| 內容試閱:
|
神秘树
二〇一一年六月一号,那个当晚
事实上很多场景我都不知道还应该怎样去描述。这一个场景不是北京,是北京也没什么的,可不是北京呀……
没爬到二楼就听有人在聊天,或者说仅仅是在制造一些声响,也有音乐。
我上去的时候见了不到十个后脑勺。这间酒吧只有这么一张桌子,我在想这是不是什么阴谋。四周放满了书架,也装腔作势地摆了几本书。杨杨跟我说这是文化人儿才来的地儿。我说哦,倒吸了一口凉气。果然,有个女人在配合着看书。是当地大报的记者,头发像坨烂草,和人的枯干倒是相得益彰。我不知道文艺女青年为什么都这么缺乏营养……这是十几个后脑勺里唯一的女士,如果不算我的话。杨杨介绍的时候,我们互相抬了下眼皮,没有交流。我感觉自己像一个不速之客。这不是我乐于见到的,事实上是杨杨给我从一家饭馆绑架过来的。当然,他没有使用麻绳。
这仅有一张桌子的酒吧,所有人都坐在了一边儿,空出来最舒服的靠墙的沙发。我和杨杨坐过去。他们很多人搬了小板凳都不愿坐在沙发上,这很奇怪,我用手拍着身边的空位招呼一个看上去很“圆”的人。如果给他画像的话,我想需要一把圆规。圆坐在板凳上显然不合情理。他掐了根儿烟,跟我握了握手,没有移动的意思,杨杨给介绍了一下,是什么来着,我忘了,需要回忆一下。也许是个小说家或者编剧?导演?主持人?设计师?
此时挂在墙上的钟表,大针、小针都快走到十二了,城市的多数人已经洗洗睡了,做爱也说不定……而在这个只有一张桌子的酒吧里,我不知道所有人还在等待什么。等待大针、小针走到十二,然后走到一?也许。
很圆那人掐了根儿烟,跟我握了握手,之后又点了一根儿烟,毫无意义地抽着,在那张小板凳上。
他旁边的一位显然比他高了不少,坐在一张酒吧的高脚椅上,刚巧和很圆那人形成神奇的角度,马上就要塌下来了。我很为他们捏了一把汗,高脚椅递给我一根儿烟,甚至也有要握握手的意思,我想就不必了。如果他过来跟我握握手,那个神奇的角度就不美妙了。
高脚椅旁边的男的,我在想应该怎么去形容。清秀?清秀并不重要,对于男的来说。而我,依然对他抱有好感。这种好感可以叫人多喝两杯。
剩下的几个后脑勺我想都可以统统称之为流氓了。有一个流氓很白,我有点儿嫉妒他的皮肤,而我想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护理方法。
当晚还发生了冤家路窄的事件。我欠了一个冒牌艺术家的采访,而他竟然也姗姗来迟,冲到了这间酒吧。要说追杀也不必,和他一块儿冲过来的还有一个大胸的姑娘。我对姑娘充满羡慕嫉妒恨,主要是恨,便也没有招呼她坐过来的意思,我在想一个难题:她能不能在中国买到内衣呢?
大胸姑娘第一时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还有一小撮儿人占用第二时间持续关注这两颗球。有人给大胸姑娘倒了一杯酒,她自己掏出一个棒棒糖,撕开包装,也许是水果味儿的。我觉得有点儿色情可是并没有被诱惑。
现在我大约可以想起来了,沙发上其实还躺着一男的。之前大家一起喝多了,他这会儿还在自言自语,没有一句话不以“你妈逼”结束,看上去非常孤独。
大胸姑娘对“你妈逼”先生很感兴趣,“你妈逼”先生说要跟她睡觉。她开始吃起了第二个棒棒糖,我猜还是水果味儿的。
谁知道什么时候又过来一姑娘,她的样儿我想也是打扮过一番的。姑娘管所有人都叫老师,挨个儿发了名片,一定是不小心,也扔我手里一张,我给整整齐齐压在手机下面。手机在桌子上,桌子上有十二瓶啤酒。在二十五分钟后到来的一场事故中,那张名片变成了喜力味儿。我并没有采取任何救援行动。
我想不起来谁了,肯定是桌上一男的,一直尝试让我们发自内心地笑一下,他耐心讲述了一些段子,我觉得乏味至极,甚至在想,他是不是有口臭。想到这,我去卫生间吐了一会儿。出来的时候,有人起立了。冒牌艺术家要带大胸姑娘走,有人拦着,虚与委蛇了一秒钟之久。
我怕被胸器撞着,避在角落里看热闹。“你妈逼”先生已经打起呼噜了,现场有点儿混乱,我觉得乐不可支。
后来我重新坐进沙发。那天的衣服有点儿低,我一直担心它掉下来,我要提防它可也不想让太多人意识到我很在乎仪容。只是这让我不能专心跟别人干杯。接着我又无所事事地抽了几根烟儿,什么都懒得谈论,开始乐意对段子——黄颜色的——报以两声干笑。
慢慢悠悠的,大针、小针都走到了一,杨杨说咱撤吧。我说我可以自己打车回去,如果他还想待会儿的话。我这么问倒不是出于礼貌,事实上我也看出他有些疲惫了。
接着和很多人再见再见再见……非常清秀的男的,我依然对他抱有好感,可是并不强烈。我有必要往下走一个台阶试试。杨杨比我还要多说几个再见,我跟拐角处等他。司机在楼下等我们。一分钟之后,汽车飞快地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不明之地
二〇一一年六月一号,几天以前
之前在外地晃悠了几天,那是一挺奇怪的酒吧。
最显眼的是,我旁边儿坐一女的,一个劲儿.里八嗦,跟我妈有一拼。我想不出来这种人来酒吧玩儿什么。疑似我妈的这女的旁边儿坐一不出声的,挺孤独挺寂寞那种,好像莫名其妙就精神特痛苦,一看就是老失眠;估计晚上也不爱跟家看电视看书什么的;有没有亲人说不好,男的肯定没有,一个都没有,也有点儿叫人同情。当然也可能这一切一切都不是真实原因。
没一会儿,疑似我妈那个噌地站起来就亮嗓子,还甩胳膊腿都很使劲的样子,胸要是假的安装得不结实就掉啦,我想。她唱得特来劲。我想,可能是,喜欢,唱歌,吧……
其实那是俩中年女作家。中年女作家也算中年妇女这片儿的。看着这些,我就想再过几年我就怎么怎么着了……其实也别过几年,是很快。
一屋子的还有文学批评家啊,说是著名文学批评家都行,跟沙发上躺着朝大家吐舌头,喝多了。事实上一点儿都不色情,从我的角度望过去,他已经变成乌龟。真叫人乐不可支。一想到这些个场景我就是觉得还得活着。谁活着,谁看得见。这帮人什么事儿都不写脸上了,文学啊理想啊都是臭傻逼,看着就是一副醉生梦死的德行。
我和别人一块儿喝芝华士加绿茶,我都一百年不那么喝了。
这会儿,不出声的女的开始跟一男的掷骰子,挺大声地没完没了说几个数字,有人在旁边儿睡觉打呼噜。那男的肚子都起来了,被我一眼识破。没玩儿几把进来一女的,前凸后翘身材怎么着看都还行吧;穿一胸罩一裤衩,她自己跟那儿抻吧抻吧,掷骰子的男的就过去跟她搭讪。女的很配合,我想是职业习惯。俩人也是绿茶加芝华士,我看着他们好像一杯就大了,一见如故跟喝了多少似的。疑似我妈那人唱的声儿突然变大,这俩就开始耳鬓厮磨:耳后、耳垂、脖颈、头发、面颊。一见如故表演得也忒真切了吧……差不多到面颊的时候女的把脸闪开了,她也知道有人在看。后来俩人就那么坐着,男的手一会儿跟女的腰上一会儿跟她腿上。女的从小坤包里拿烟抽,男的没有给她点火的意思,她自己也没火。女的左右翻了翻,打火机火柴什么的,把骰子攥起来看了看,还是没有,又玩儿了会儿烟,烟丝都给捏出来了,干脆给掰折了。二位在角落里看着极其虚晃,说不出来是真情假意。反正真的和假的也没什么区别。后来俩人还提生孩子的事儿。我真想凑过去说点儿废话:别生小孩儿了,反正生命也是短暂的,养条狗算了。我听别人这种争执都难过得要命,完全罔顾虚无的事实,还得让自己特别相信。
一会儿又过来一个人,看那姿势好像是要跟我谈谈工作什么的,还说一二三点。我心想你们丫怎么都还没喝多啊……就一二三开步走去卫生间待了会儿。卫生间我很不喜欢,肯定有女的老家来亲戚了,刚跟那儿换了卫生巾,流了不少血啊……出来的时候我听着他们还说一二三点、工作啊什么的,空头支票。很多显而易见一听就是假的,可我也学会那么点头答应着了,真不知道为什么彼此都没实话,可能是也不需要吧。多亏不需要。
这一屋子其实到处都是我们的人,大家是一块儿过来的,一会儿也一块儿撤,谁跟谁走不知道,但看着还是都特别没关联。这不是任何人的原因。
这会儿文学评论家或者说著名文学评论家不吐舌头了,开始剔牙,目光呆滞地看着显示器,嘴里弄出一些什么玩意儿就啐地上。我相信他在成为一个文艺青年之前,是天天拿锄头那种农民。
时间越来越晚,后来有人还建议再去别地儿玩玩儿,大家都没表态,这大概就是不去了。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出来的时候有出租车飞过来很快就被人拦下了,弄得跟什么似的。这个世界上又不是只剩一辆出租车了,反正有人钻进去,连头都不回一下。唉。
生活中的这些场景太多,缺乏更多合理性。那个疑似我妈的肯定不是我妈。不出声的女的没准有个男人,在一块儿耳鬓厮磨的也许是死灰复燃的情人,老房子着火。文学评论家或者著名文学评论家明天一早就去开会,开会小王子。我和别人聊聊工作,多好。
可是,很快,无论这是什么或者不是什么,它将很快什么都不是。
冯唐家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一号,前些天
那天去冯唐家吃饭,沿途都是平房,一路上,看见好几拨儿老头老太太坐在板凳上,当时已经没有太阳了所以不是晒太阳,他们就那么坐着。怎么说呢,这几乎叫我向往衰老。如果人生也只是弹指一挥间,青春又算得了什么。
与此同时,还有乌鸦在上面啊啊啊叫。
因为我过去得有点儿晚,他们又都大了。艾丹说你先吃先吃,对菜进行一些点评,于是我马上塞嘴里两块儿肥肉。这样我就不用点评了。
彼此之间先喝红的,三四瓶,也可能有五瓶;或者没有五瓶,但是三四瓶总有了。怎么都喝不大,我想还不如直接下药。后来又追加了单麦、蓝方、白的、啤的,以及一网兜橘子。
冯唐的祝酒词永远是:祝你幸福。跟谁都这么说可真够逗的,非常好玩全无用处。每回见面他都说找了男朋友让我们来围观围观。我说好的好的,等我找了一只熊猫就牵过来。李野夫也问我的婚姻状况,于是我只能承认自己结过婚离过婚,反正我也没什么实话。
后来又扑过来一个弄影视的,他非说我的衬衫像八大楼的服务员。他怎么不说八大胡同呀。艾丹也说你衣服是从谁那儿偷的?其实不是偷的是抢的,气死我了。回家我就打算给它扔床底下了,这辈子不穿下辈子再穿。我床底下就是杜十娘百宝箱!
然后无论他们聊什么,做影视的这人都问我:你听得懂吗?我说猜对了,听不懂。因为他们影视行业的普遍认为女的没什么文化,我也不置可否,反正他们自己也没什么文化。
小院里的桌子椅子都是当年“食堂”的,可以想象他们得在这上面吃了多少顿,说了多少人坏话呀……这些人互相看不起,彼此听多了都是树洞。我也骂了一些人傻逼,这无疑证明我就是一傻逼。冯唐说会帮我转达,我说那就好。难道我能因为别人威胁就不说吗?艾丹不愿意听傻逼的事儿,于是他差点儿聊艺术。
四合院三面都是老房子,有一面是未未设计的,草场地风格,可以爬到房顶,于是我爬了上去。从房顶看底下各种小院的万家灯火,非常温馨。我估计灯火里的人在看电视剧或者洗洗睡了,女人将要伺候男人。我想起电影里有人在瓦片上走,好像是马小军。可据说在谁家瓦片上走谁家屋里就漏水,于是我放弃了。我问他们白天能听见鸽哨吗?他们说问也白问,反正你也起不了那么早,我说哦。可我今天起挺早的,才十点钟。
其实院子里再有个猫猫狗狗就好玩儿了,金鱼也行。冯唐只养了两只苍蝇,还被我们失手拍死了一只也说不好。
后来都喝多了开始要这要那要主食。有人去煮面,野夫、毛然一人暴撮一碗,站在正屋左右厢,两尊门神。野夫酒足饭饱摸着自己的肚皮,鼓鼓的,我从房顶望下去,他已经变成了一只袋鼠。
与此同时,艾丹也多了,红色的脸在月光中闪闪发光,身上披了一件大衣,肩膀支得平平的,已经不那么像屠夫了,像个国家干部。
我也爬下来拌了一碗炸酱面。这叫我想起小时候,如果我爸出远门的话,就给我炸一碗酱,这样我再煮些面条就不会饿死了。
吃饱了我把院子里的所有屋子溜达了一圈。他家的浴缸里放满了破烂儿,被我一眼识破。
下半夜越来越凉,感冒又回来了,我都快把肺咳出来了,餐巾纸一张一张又一张,形同出殡。当时小院好像还放了音乐,或者是幻听。榕树下,花开花落,其实没必要这么伤感,伤感容易走入内心,内心充满矛盾和斗争,离精神分裂只差一小步。
又过了很久,彼此越来越安静就散了。临出门我被人强行塞了俩包子,说是他爸擀皮儿,他妈和馅儿,好吃好吃……我坐在车上继续和谁东拉西扯言不及义,都忘了。其间接了一个朋友电话,他说我们好久没见了,我说行,等我哪天喝多了给你打电话……后来下了车,我迅速干掉包子,馅离皮太远,吃了一百米才到。
圣诞节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五号,昨天晚上后来
这个世界上就是有那么些个人老赶上圣诞节过生日。我说的是王小峰。
二十四号晚,满大街都是那首歌儿:Single boy single boy single on the
way……我一个人赶路,奔一个闻所未闻的地儿去给王小峰过生日。那地儿真难找,我一路上问了好几个人怎么走,不过所有人好像都没有停下来的兴致,有个男的猛一挥手差点抽我脸上,说你不要问我不要问我!我心想我问的就是你就是你!我知道你们所有人都很忙,除了我在寒风的街头看见的几个修路工人,他们在一边儿抽烟一边儿刨地。
我很少见王小峰,他也不喝酒。他饭局的最大特色就是姑娘多,男女比例失衡,人员构成复杂。那天又是一长桌跟冷餐会差不多,我看见了能喝酒的奇小怪,于是找他坐,旁边还有伊伟,三个人构成一个小团体,基本和生日无关了。
长桌的最大问题就是吃不着东西,所以当时我很后悔没在门口买个烤白薯。我坐着不动,挨着大门口,老觉得要挨闷棍。本来伊伟也能喝两口,但是他说戒了,我说几天了,他说有三四天了吧。我不清楚这些人为了证明什么?戒也戒不掉。另外,那天好多人串来串去都有点儿眼熟,一年也没见过几回,没话。有的人过来问问我喝酒的事儿,我觉得这完全是妖魔化,他们说没化就是妖魔,我说好吧。
后来任凌云过来,我原来让她设计过几本书,跟她聊了会儿。
她听说我在念书觉得这状态挺舒服的。
我说谢你骂我,其实我主要就是不工作这状态舒服。
她说自己也打算辞了。
我说哦,但是我都不太信。
她说自己也确实下不了这个决心,但是又不满意在现状中磨损。
任凌云移动到别地儿去了,伊伟过来了。他是我见过的最爱讲话的男的。我几年前第一次见他他就直接从九点喷到夜里一点。他从时尚杂志说到健身器材,因为现在杂志绝对是一器材,举起来直接出肱二头肌。
其实那天喝的相当少,因为我是想换地儿——说白了就是回家睡觉。我一到年底就有点儿冬眠的意思。出门的时候曹臻一说不然一块儿去威士忌猫待会儿,我说那就去吧。那个酒吧我一共去过三回,一次跟张悦然,一次大仙诗会,还一次就是马上。但是这地儿我印象极深,因为我一年抽的烟起码一半儿都在这,我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到猫的时候,有人撤了有人还在。最好的时光已经过了,我们属于半截来半截走那种。我看见几个认识的朋友,不过话题也没什么新招其实我觉得本来就不必的;还看见一男的眼熟,没聊,只说了句:我抽根儿你的烟啊。
坐了一会儿,倒的酒没喝,我要回家,曹臻一要去愚公,就撤了。外面很冷,只有一辆出租,于是干脆我俩一块儿回家算了。路上我跟曹说回头给我来一篇《二》的稿子,她说自己懂一三,不懂二,我说反正就是在一和三之间吧。后来语焉不详,就没说这个事儿。然后她说自己前两天看一戏,讲的就是八个字: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我说怎么样,她说可惜了这八个字多好呀。我说是,哪怕就写一个饭桌儿上的吃吃喝喝分分合合都行,不要什么长亭短亭了。或者拍那十四个字也成: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回家我接到短信,一个人问怎么过的,我说一年就今天平安,反正刚吃完,中国所有的节最后就是一顿饭,这是社会主义特色,九九归一。
神秘树
二〇一一年六月一号,那个当晚
事实上很多场景我都不知道还应该怎样去描述。这一个场景不是北京,是北京也没什么的,可不是北京呀……
没爬到二楼就听有人在聊天,或者说仅仅是在制造一些声响,也有音乐。
我上去的时候见了不到十个后脑勺。这间酒吧只有这么一张桌子,我在想这是不是什么阴谋。四周放满了书架,也装腔作势地摆了几本书。杨杨跟我说这是文化人儿才来的地儿。我说哦,倒吸了一口凉气。果然,有个女人在配合着看书。是当地大报的记者,头发像坨烂草,和人的枯干倒是相得益彰。我不知道文艺女青年为什么都这么缺乏营养……这是十几个后脑勺里唯一的女士,如果不算我的话。杨杨介绍的时候,我们互相抬了下眼皮,没有交流。我感觉自己像一个不速之客。这不是我乐于见到的,事实上是杨杨给我从一家饭馆绑架过来的。当然,他没有使用麻绳。
这仅有一张桌子的酒吧,所有人都坐在了一边儿,空出来最舒服的靠墙的沙发。我和杨杨坐过去。他们很多人搬了小板凳都不愿坐在沙发上,这很奇怪,我用手拍着身边的空位招呼一个看上去很“圆”的人。如果给他画像的话,我想需要一把圆规。圆坐在板凳上显然不合情理。他掐了根儿烟,跟我握了握手,没有移动的意思,杨杨给介绍了一下,是什么来着,我忘了,需要回忆一下。也许是个小说家或者编剧?导演?主持人?设计师?
此时挂在墙上的钟表,大针、小针都快走到十二了,城市的多数人已经洗洗睡了,做爱也说不定……而在这个只有一张桌子的酒吧里,我不知道所有人还在等待什么。等待大针、小针走到十二,然后走到一?也许。
很圆那人掐了根儿烟,跟我握了握手,之后又点了一根儿烟,毫无意义地抽着,在那张小板凳上。
他旁边的一位显然比他高了不少,坐在一张酒吧的高脚椅上,刚巧和很圆那人形成神奇的角度,马上就要塌下来了。我很为他们捏了一把汗,高脚椅递给我一根儿烟,甚至也有要握握手的意思,我想就不必了。如果他过来跟我握握手,那个神奇的角度就不美妙了。
高脚椅旁边的男的,我在想应该怎么去形容。清秀?清秀并不重要,对于男的来说。而我,依然对他抱有好感。这种好感可以叫人多喝两杯。
剩下的几个后脑勺我想都可以统统称之为流氓了。有一个流氓很白,我有点儿嫉妒他的皮肤,而我想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护理方法。
当晚还发生了冤家路窄的事件。我欠了一个冒牌艺术家的采访,而他竟然也姗姗来迟,冲到了这间酒吧。要说追杀也不必,和他一块儿冲过来的还有一个大胸的姑娘。我对姑娘充满羡慕嫉妒恨,主要是恨,便也没有招呼她坐过来的意思,我在想一个难题:她能不能在中国买到内衣呢?
大胸姑娘第一时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还有一小撮儿人占用第二时间持续关注这两颗球。有人给大胸姑娘倒了一杯酒,她自己掏出一个棒棒糖,撕开包装,也许是水果味儿的。我觉得有点儿色情可是并没有被诱惑。
现在我大约可以想起来了,沙发上其实还躺着一男的。之前大家一起喝多了,他这会儿还在自言自语,没有一句话不以“你妈逼”结束,看上去非常孤独。
大胸姑娘对“你妈逼”先生很感兴趣,“你妈逼”先生说要跟她睡觉。她开始吃起了第二个棒棒糖,我猜还是水果味儿的。
谁知道什么时候又过来一姑娘,她的样儿我想也是打扮过一番的。姑娘管所有人都叫老师,挨个儿发了名片,一定是不小心,也扔我手里一张,我给整整齐齐压在手机下面。手机在桌子上,桌子上有十二瓶啤酒。在二十五分钟后到来的一场事故中,那张名片变成了喜力味儿。我并没有采取任何救援行动。
我想不起来谁了,肯定是桌上一男的,一直尝试让我们发自内心地笑一下,他耐心讲述了一些段子,我觉得乏味至极,甚至在想,他是不是有口臭。想到这,我去卫生间吐了一会儿。出来的时候,有人起立了。冒牌艺术家要带大胸姑娘走,有人拦着,虚与委蛇了一秒钟之久。
我怕被胸器撞着,避在角落里看热闹。“你妈逼”先生已经打起呼噜了,现场有点儿混乱,我觉得乐不可支。
后来我重新坐进沙发。那天的衣服有点儿低,我一直担心它掉下来,我要提防它可也不想让太多人意识到我很在乎仪容。只是这让我不能专心跟别人干杯。接着我又无所事事地抽了几根烟儿,什么都懒得谈论,开始乐意对段子——黄颜色的——报以两声干笑。
慢慢悠悠的,大针、小针都走到了一,杨杨说咱撤吧。我说我可以自己打车回去,如果他还想待会儿的话。我这么问倒不是出于礼貌,事实上我也看出他有些疲惫了。
接着和很多人再见再见再见……非常清秀的男的,我依然对他抱有好感,可是并不强烈。我有必要往下走一个台阶试试。杨杨比我还要多说几个再见,我跟拐角处等他。司机在楼下等我们。一分钟之后,汽车飞快地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不明之地
二〇一一年六月一号,几天以前
之前在外地晃悠了几天,那是一挺奇怪的酒吧。
最显眼的是,我旁边儿坐一女的,一个劲儿.里八嗦,跟我妈有一拼。我想不出来这种人来酒吧玩儿什么。疑似我妈的这女的旁边儿坐一不出声的,挺孤独挺寂寞那种,好像莫名其妙就精神特痛苦,一看就是老失眠;估计晚上也不爱跟家看电视看书什么的;有没有亲人说不好,男的肯定没有,一个都没有,也有点儿叫人同情。当然也可能这一切一切都不是真实原因。
没一会儿,疑似我妈那个噌地站起来就亮嗓子,还甩胳膊腿都很使劲的样子,胸要是假的安装得不结实就掉啦,我想。她唱得特来劲。我想,可能是,喜欢,唱歌,吧……
其实那是俩中年女作家。中年女作家也算中年妇女这片儿的。看着这些,我就想再过几年我就怎么怎么着了……其实也别过几年,是很快。
一屋子的还有文学批评家啊,说是著名文学批评家都行,跟沙发上躺着朝大家吐舌头,喝多了。事实上一点儿都不色情,从我的角度望过去,他已经变成乌龟。真叫人乐不可支。一想到这些个场景我就是觉得还得活着。谁活着,谁看得见。这帮人什么事儿都不写脸上了,文学啊理想啊都是臭傻逼,看着就是一副醉生梦死的德行。
我和别人一块儿喝芝华士加绿茶,我都一百年不那么喝了。
这会儿,不出声的女的开始跟一男的掷骰子,挺大声地没完没了说几个数字,有人在旁边儿睡觉打呼噜。那男的肚子都起来了,被我一眼识破。没玩儿几把进来一女的,前凸后翘身材怎么着看都还行吧;穿一胸罩一裤衩,她自己跟那儿抻吧抻吧,掷骰子的男的就过去跟她搭讪。女的很配合,我想是职业习惯。俩人也是绿茶加芝华士,我看着他们好像一杯就大了,一见如故跟喝了多少似的。疑似我妈那人唱的声儿突然变大,这俩就开始耳鬓厮磨:耳后、耳垂、脖颈、头发、面颊。一见如故表演得也忒真切了吧……差不多到面颊的时候女的把脸闪开了,她也知道有人在看。后来俩人就那么坐着,男的手一会儿跟女的腰上一会儿跟她腿上。女的从小坤包里拿烟抽,男的没有给她点火的意思,她自己也没火。女的左右翻了翻,打火机火柴什么的,把骰子攥起来看了看,还是没有,又玩儿了会儿烟,烟丝都给捏出来了,干脆给掰折了。二位在角落里看着极其虚晃,说不出来是真情假意。反正真的和假的也没什么区别。后来俩人还提生孩子的事儿。我真想凑过去说点儿废话:别生小孩儿了,反正生命也是短暂的,养条狗算了。我听别人这种争执都难过得要命,完全罔顾虚无的事实,还得让自己特别相信。
一会儿又过来一个人,看那姿势好像是要跟我谈谈工作什么的,还说一二三点。我心想你们丫怎么都还没喝多啊……就一二三开步走去卫生间待了会儿。卫生间我很不喜欢,肯定有女的老家来亲戚了,刚跟那儿换了卫生巾,流了不少血啊……出来的时候我听着他们还说一二三点、工作啊什么的,空头支票。很多显而易见一听就是假的,可我也学会那么点头答应着了,真不知道为什么彼此都没实话,可能是也不需要吧。多亏不需要。
这一屋子其实到处都是我们的人,大家是一块儿过来的,一会儿也一块儿撤,谁跟谁走不知道,但看着还是都特别没关联。这不是任何人的原因。
这会儿文学评论家或者说著名文学评论家不吐舌头了,开始剔牙,目光呆滞地看着显示器,嘴里弄出一些什么玩意儿就啐地上。我相信他在成为一个文艺青年之前,是天天拿锄头那种农民。
时间越来越晚,后来有人还建议再去别地儿玩玩儿,大家都没表态,这大概就是不去了。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出来的时候有出租车飞过来很快就被人拦下了,弄得跟什么似的。这个世界上又不是只剩一辆出租车了,反正有人钻进去,连头都不回一下。唉。
生活中的这些场景太多,缺乏更多合理性。那个疑似我妈的肯定不是我妈。不出声的女的没准有个男人,在一块儿耳鬓厮磨的也许是死灰复燃的情人,老房子着火。文学评论家或者著名文学评论家明天一早就去开会,开会小王子。我和别人聊聊工作,多好。
可是,很快,无论这是什么或者不是什么,它将很快什么都不是。
冯唐家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一号,前些天
那天去冯唐家吃饭,沿途都是平房,一路上,看见好几拨儿老头老太太坐在板凳上,当时已经没有太阳了所以不是晒太阳,他们就那么坐着。怎么说呢,这几乎叫我向往衰老。如果人生也只是弹指一挥间,青春又算得了什么。
与此同时,还有乌鸦在上面啊啊啊叫。
因为我过去得有点儿晚,他们又都大了。艾丹说你先吃先吃,对菜进行一些点评,于是我马上塞嘴里两块儿肥肉。这样我就不用点评了。
彼此之间先喝红的,三四瓶,也可能有五瓶;或者没有五瓶,但是三四瓶总有了。怎么都喝不大,我想还不如直接下药。后来又追加了单麦、蓝方、白的、啤的,以及一网兜橘子。
冯唐的祝酒词永远是:祝你幸福。跟谁都这么说可真够逗的,非常好玩全无用处。每回见面他都说找了男朋友让我们来围观围观。我说好的好的,等我找了一只熊猫就牵过来。李野夫也问我的婚姻状况,于是我只能承认自己结过婚离过婚,反正我也没什么实话。
后来又扑过来一个弄影视的,他非说我的衬衫像八大楼的服务员。他怎么不说八大胡同呀。艾丹也说你衣服是从谁那儿偷的?其实不是偷的是抢的,气死我了。回家我就打算给它扔床底下了,这辈子不穿下辈子再穿。我床底下就是杜十娘百宝箱!
然后无论他们聊什么,做影视的这人都问我:你听得懂吗?我说猜对了,听不懂。因为他们影视行业的普遍认为女的没什么文化,我也不置可否,反正他们自己也没什么文化。
小院里的桌子椅子都是当年“食堂”的,可以想象他们得在这上面吃了多少顿,说了多少人坏话呀……这些人互相看不起,彼此听多了都是树洞。我也骂了一些人傻逼,这无疑证明我就是一傻逼。冯唐说会帮我转达,我说那就好。难道我能因为别人威胁就不说吗?艾丹不愿意听傻逼的事儿,于是他差点儿聊艺术。
四合院三面都是老房子,有一面是未未设计的,草场地风格,可以爬到房顶,于是我爬了上去。从房顶看底下各种小院的万家灯火,非常温馨。我估计灯火里的人在看电视剧或者洗洗睡了,女人将要伺候男人。我想起电影里有人在瓦片上走,好像是马小军。可据说在谁家瓦片上走谁家屋里就漏水,于是我放弃了。我问他们白天能听见鸽哨吗?他们说问也白问,反正你也起不了那么早,我说哦。可我今天起挺早的,才十点钟。
其实院子里再有个猫猫狗狗就好玩儿了,金鱼也行。冯唐只养了两只苍蝇,还被我们失手拍死了一只也说不好。
后来都喝多了开始要这要那要主食。有人去煮面,野夫、毛然一人暴撮一碗,站在正屋左右厢,两尊门神。野夫酒足饭饱摸着自己的肚皮,鼓鼓的,我从房顶望下去,他已经变成了一只袋鼠。
与此同时,艾丹也多了,红色的脸在月光中闪闪发光,身上披了一件大衣,肩膀支得平平的,已经不那么像屠夫了,像个国家干部。
我也爬下来拌了一碗炸酱面。这叫我想起小时候,如果我爸出远门的话,就给我炸一碗酱,这样我再煮些面条就不会饿死了。
吃饱了我把院子里的所有屋子溜达了一圈。他家的浴缸里放满了破烂儿,被我一眼识破。
下半夜越来越凉,感冒又回来了,我都快把肺咳出来了,餐巾纸一张一张又一张,形同出殡。当时小院好像还放了音乐,或者是幻听。榕树下,花开花落,其实没必要这么伤感,伤感容易走入内心,内心充满矛盾和斗争,离精神分裂只差一小步。
又过了很久,彼此越来越安静就散了。临出门我被人强行塞了俩包子,说是他爸擀皮儿,他妈和馅儿,好吃好吃……我坐在车上继续和谁东拉西扯言不及义,都忘了。其间接了一个朋友电话,他说我们好久没见了,我说行,等我哪天喝多了给你打电话……后来下了车,我迅速干掉包子,馅离皮太远,吃了一百米才到。
圣诞节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五号,昨天晚上后来
这个世界上就是有那么些个人老赶上圣诞节过生日。我说的是王小峰。
二十四号晚,满大街都是那首歌儿:Single boy single boy single on the
way……我一个人赶路,奔一个闻所未闻的地儿去给王小峰过生日。那地儿真难找,我一路上问了好几个人怎么走,不过所有人好像都没有停下来的兴致,有个男的猛一挥手差点抽我脸上,说你不要问我不要问我!我心想我问的就是你就是你!我知道你们所有人都很忙,除了我在寒风的街头看见的几个修路工人,他们在一边儿抽烟一边儿刨地。
我很少见王小峰,他也不喝酒。他饭局的最大特色就是姑娘多,男女比例失衡,人员构成复杂。那天又是一长桌跟冷餐会差不多,我看见了能喝酒的奇小怪,于是找他坐,旁边还有伊伟,三个人构成一个小团体,基本和生日无关了。
长桌的最大问题就是吃不着东西,所以当时我很后悔没在门口买个烤白薯。我坐着不动,挨着大门口,老觉得要挨闷棍。本来伊伟也能喝两口,但是他说戒了,我说几天了,他说有三四天了吧。我不清楚这些人为了证明什么?戒也戒不掉。另外,那天好多人串来串去都有点儿眼熟,一年也没见过几回,没话。有的人过来问问我喝酒的事儿,我觉得这完全是妖魔化,他们说没化就是妖魔,我说好吧。
后来任凌云过来,我原来让她设计过几本书,跟她聊了会儿。
她听说我在念书觉得这状态挺舒服的。
我说谢你骂我,其实我主要就是不工作这状态舒服。
她说自己也打算辞了。
我说哦,但是我都不太信。
她说自己也确实下不了这个决心,但是又不满意在现状中磨损。
任凌云移动到别地儿去了,伊伟过来了。他是我见过的最爱讲话的男的。我几年前第一次见他他就直接从九点喷到夜里一点。他从时尚杂志说到健身器材,因为现在杂志绝对是一器材,举起来直接出肱二头肌。
其实那天喝的相当少,因为我是想换地儿——说白了就是回家睡觉。我一到年底就有点儿冬眠的意思。出门的时候曹臻一说不然一块儿去威士忌猫待会儿,我说那就去吧。那个酒吧我一共去过三回,一次跟张悦然,一次大仙诗会,还一次就是马上。但是这地儿我印象极深,因为我一年抽的烟起码一半儿都在这,我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到猫的时候,有人撤了有人还在。最好的时光已经过了,我们属于半截来半截走那种。我看见几个认识的朋友,不过话题也没什么新招其实我觉得本来就不必的;还看见一男的眼熟,没聊,只说了句:我抽根儿你的烟啊。
坐了一会儿,倒的酒没喝,我要回家,曹臻一要去愚公,就撤了。外面很冷,只有一辆出租,于是干脆我俩一块儿回家算了。路上我跟曹说回头给我来一篇《二》的稿子,她说自己懂一三,不懂二,我说反正就是在一和三之间吧。后来语焉不详,就没说这个事儿。然后她说自己前两天看一戏,讲的就是八个字: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我说怎么样,她说可惜了这八个字多好呀。我说是,哪怕就写一个饭桌儿上的吃吃喝喝分分合合都行,不要什么长亭短亭了。或者拍那十四个字也成: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回家我接到短信,一个人问怎么过的,我说一年就今天平安,反正刚吃完,中国所有的节最后就是一顿饭,这是社会主义特色,九九归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