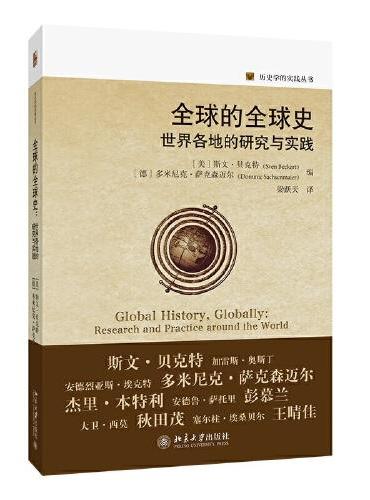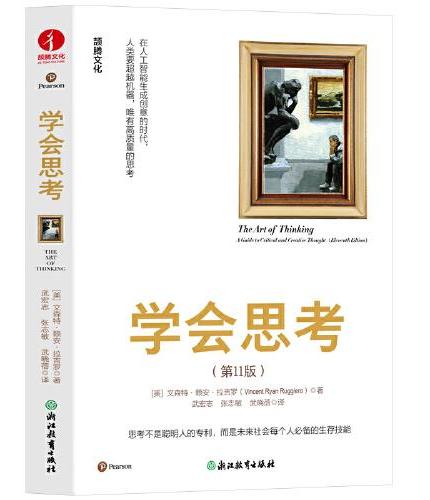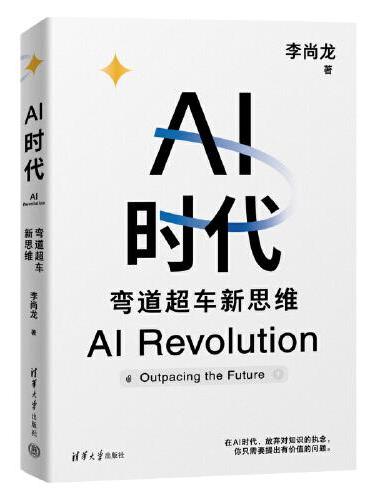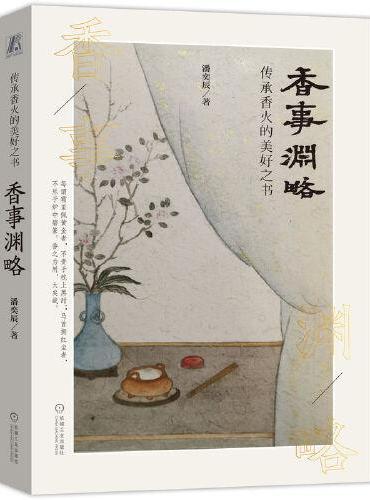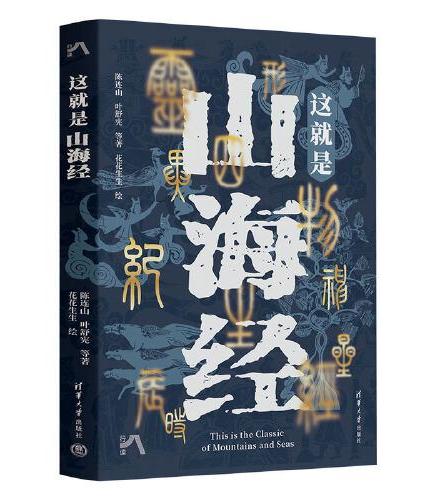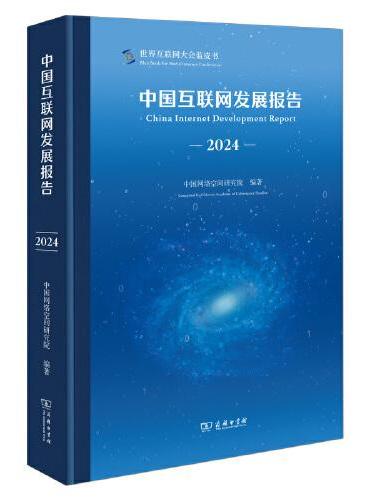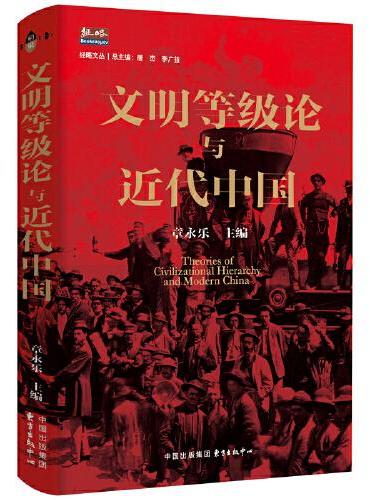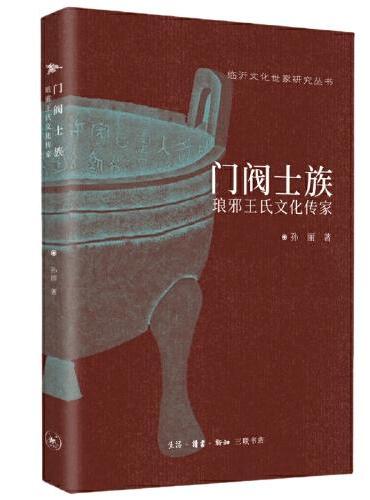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全球的全球史:世界各地的研究与实践 历史学的实践丛书
》 售價:HK$
88.0
《
学会思考 批判性思维 思辨与立场 学会提问
》 售價:HK$
86.9
《
AI时代:弯道超车新思维
》 售價:HK$
76.8
《
香事渊略
》 售價:HK$
108.9
《
这就是山海经
》 售價:HK$
107.8
《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4)
》 售價:HK$
261.8
《
文明等级论与近代中国
》 售價:HK$
76.8
《
门阀士族:琅邪王氏文化传家
》 售價:HK$
86.9
編輯推薦:
美国文化已经堕落成物质与消费
內容簡介:
作者卡勒·拉森和他的“文化干扰者”伙伴们认为“美国不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价值千亿的商标。”作为《广告克星》杂志创建人,卡勒?拉森致力于用改变信息流的方式阻止“美国”的品牌知名度;机构行使权力的方式;电视台运行的方式;事物、时尚、汽车、运动、音乐和文化产业设置的方式;拉森用勇气和强有力的语言表达了解构了广告文化和我们对名牌及偶像的过度关注。他也展示了如何组织对权力的抵抗,如何打破“电视瘾时代”的“媒体瘾”,撕下捆绑在时尚和名流上的标签等……
關於作者:
卡勒·拉森 Kalle Lasn
目錄
引言
內容試閱
引言:文化干扰(Culture Jam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