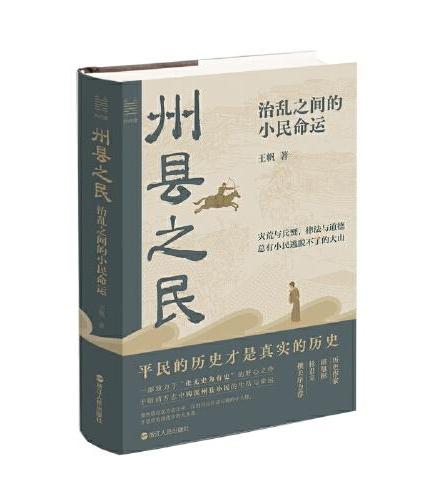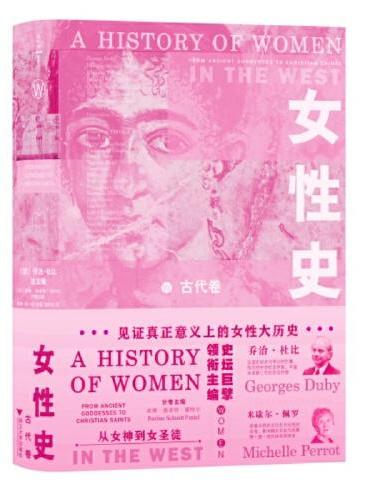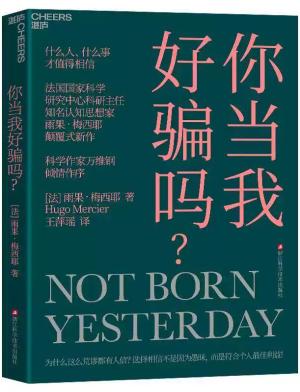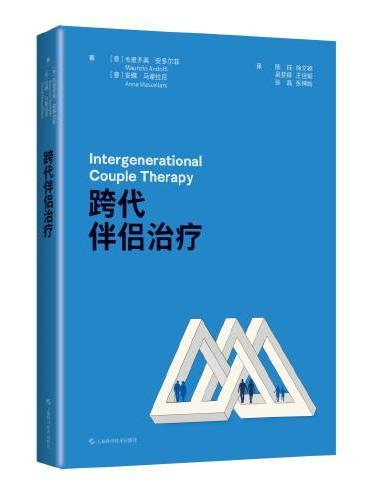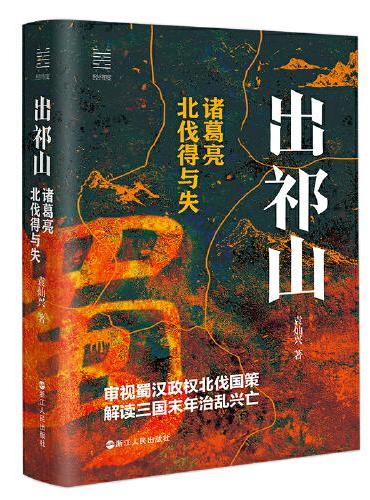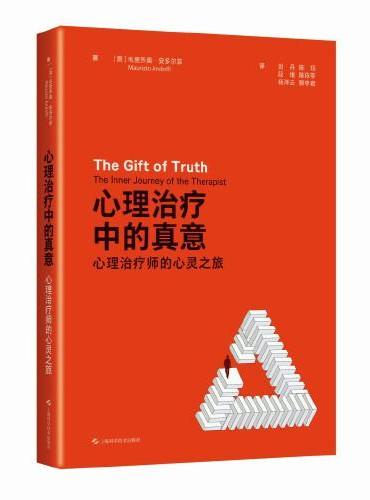新書推薦:

《
自然信息图:一目了然的万物奇观
》
售價:HK$
14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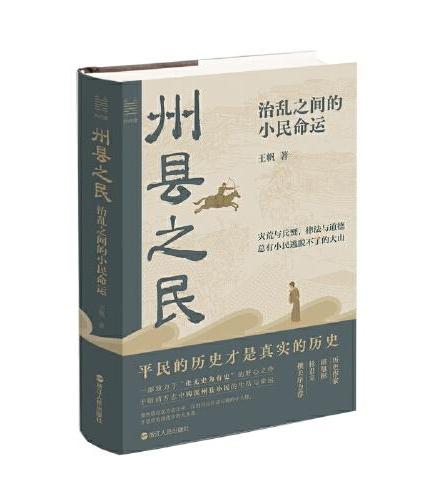
《
经纬度丛书·州县之民:治乱之间的小民命运
》
售價:HK$
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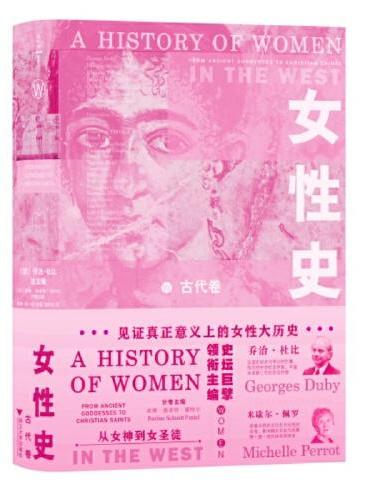
《
女性史:古代卷(真正意义上的女性大历史)
》
售價:HK$
12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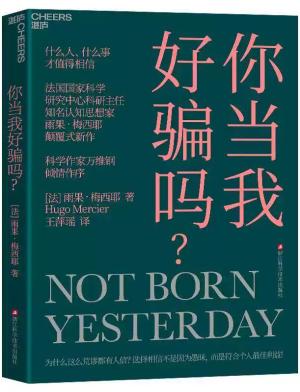
《
你当我好骗吗?
》
售價:HK$
12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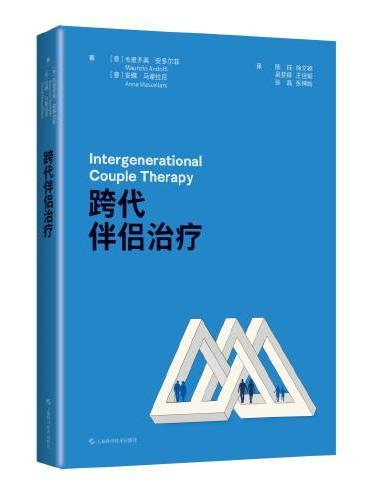
《
跨代伴侣治疗
》
售價:HK$
96.8

《
精华类化妆品配方与制备手册
》
售價:HK$
21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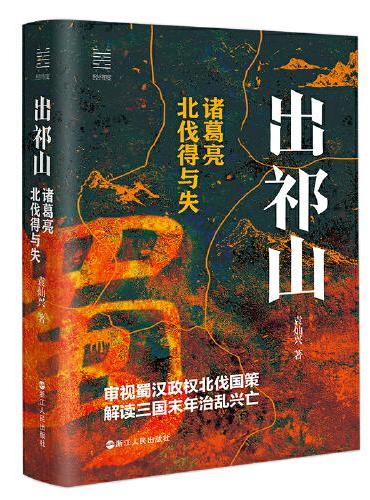
《
经纬度丛书:出祁山:诸葛亮北伐得与失
》
售價:HK$
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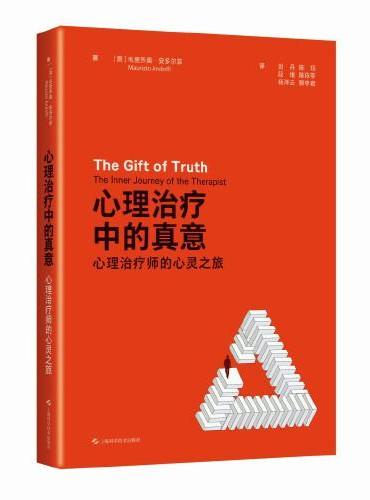
《
心理治疗中的真意:心理治疗师的心灵之旅
》
售價:HK$
96.8
|
| 編輯推薦: |
20世纪最重要的小说,不仅重新界定了文学的定义,也重新界定了美国文化。
向读者展示了一个人间地狱,这里泛滥着色情、毒品与各种可怕的病毒。在这个魔窟里,漂移着活在恶臭污秽中的一群变形的人类。
艾伦·金斯堡说:一本永无穷尽,能使所有人都发疯的小说。
有的批评家将它斥为一堆不知所云的垃圾,精神病态的呓语;另一些人认为,这本书以幽默的形式抨击社会的伪善,探寻人们心灵荒唐的一面,富有深刻的道德内涵,是一部古怪的天才之作。
“垮掉一代”教父经典之作
大卫·柯南伯格同名电影原著小说
《时代周刊》最佳英语百部小说之一
《哈利·波特》中文译者马爱农权威译本
台湾“垮掉一代”研究专家何颖怡精心译作
|
| 內容簡介: |
|
《裸体午餐》被文学史称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小说之一,不仅重新界定了文学的定义,也重新界定了美国文化。本书描述一个毒瘾者漫游纽约等城市的令人胆寒的故事,批判了美国社会的荒诞、堕落和腐朽,向读者展示了一个人间地狱般的美国。作者使用了一种称为“剪裁法”的写作手法,风格新颖独特,并夹杂了大量典故、方言、俚语、黑话、双关语、文字游戏等,给读者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该书被评为《时代周刊》英文百大小说,并于1991年被大卫·柯南伯格翻拍成同名电影。
|
| 關於作者: |
威廉·巴勒斯(1914—1997),美国作家,与艾伦·金斯堡及杰克·凯鲁亚克同为“垮掉的一代”文学运动的创始者。被誉为“垮掉的一代”的精神之父和美国后现代主义创作的先驱之一。晚年涉足演艺界,创作流行歌曲,拍电影,绘画,还为耐克运动鞋在电视上做广告,几乎无所不为。主要作品有《裸体午餐》、《贩毒者》、《软机器》、《爆炸的票》、《新星快车》等。
译者简介:
马爱农,1964年生,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辑,外国文学部主任。译著有《爱伦·坡短篇小说选》、《迷魂谷》、《绿野仙踪》、《黑骏马》,以及《哈利·波特》系列等。
|
| 目錄:
|
序
证词:关于一种疾病
多说几句……您不吗?
开始向西行
义务警员
鲁比
本威
乔斯里托
黑肉
医院
拉撒路回家
哈桑的喧闹房间
地区间的大学校园
A.J.的年度聚会
国际精神病学科技大会
市场
普通男女
伊斯兰股份有限公司与地区间市各方
县书记员
地区间
检查
你见过鸦片玫瑰吗?
可卡因虫
“敌杀死”干得彻底
需求的代数
豪泽与奥布赖恩
萎缩的序言您不吗?
快……
附录
一位多种危险毒品超级上瘾者的信
|
| 內容試閱:
|
开始向西行
我可以感觉到“热浪”渐渐围拢过来,感觉到他们已经开始出动,派出他们那些蠢头蠢脑的暗探,端详着我在华盛顿广场车站丢弃的小匙和滴管,得意地浅吟低唱,跃过一道旋转栅门,奔下两道铁楼梯,赶上一辆开往城外的一线地铁……年轻,英俊,剃着板寸,常春藤名牌大学,显示自己是老派“果子”,打开地铁门让我进去。显然我这样的人正对他的口味。你知道这类家伙总是跟吧台伙计和出租车司机混得很熟,说起麻醉药和海洛因来都很上路子,跟耐迪克商店的店员称兄道弟。一个地道的傻瓜。这个穿白色双排扣男式雨衣的缉毒警察正好出现在站台上(想象一下吧,穿白色雨衣来追人——我猜他是想假装成一个“果子”)。我想,他用左手抓住我的外套,右手放在他的私处时,准会说:“我想你掉东西了,伙计。”
可是地铁开动了。
“再见,雷子!”我喊,表示他的演技只能得B。我直视那“果子”的眼睛,记住他的白牙齿,在佛罗里达晒黑的皮肤,两百美元的鲨鱼皮西服,领尖钉有纽扣的布鲁克兄弟衬衫,和手里拿着当道具的《新闻报》。“我只读小艾布纳。”
一个正经人也想赶时髦……谈起“豆荚”来头头是道,还偶尔抽上两口,随身带着一些,随时给好莱坞的放荡鬼们递过去。
“谢谢,小伙子,”我说,“看得出来,你是我们一伙的。 ”
他的脸像弹球机一样亮起来,泛出蠢兮兮的粉红色。
“他把我给卖了。”我郁闷地说。(注:“卖”是窃贼们的黑话,意思是告密。)我靠近一些,把我跟毒品打交道的脏手放在他鲨鱼皮西服的袖子上。“我们还是共用一根脏针头的割头换颈的弟兄呢。私下里跟你说吧,真该给他一颗好效药吃吃。
”(注:好效药是一种有毒的毒品胶囊,卖给瘾君子,为的是把他们干掉。经常是卖给那些告密者。一般来说,好效药是马钱子碱,它的味道和样子都很像毒品。)
“见过好效药发作吗,小伙子?我在费城看见瘸子挨到一剂。我们在他房间里装了一面仓库用的单面镜子,派一个小东西看着。他都没来得及把针头从胳膊上拔出来。如果针打得合适,一般都来不及拔针头。他们发现他时就那副样子,滴管从发紫的胳膊上耷拉下来,上面满是血迹。毒性发作时他眼睛里的神情——小伙子,真是有趣啊……
“回想一下我跟义务警员一起旅行的时候,他可是这一行里的大哥大。在芝……我们在林肯公园对付男同性恋。一天夜里,义务警员来干活,穿一件黑马甲,上面有一大块锡片,肩膀上挂着一个套索。
“我就说:‘你带的是什么呀?你已经戴假发啦?’
“他只是看着我,说:‘你手里拿点东西,陌生人。’就递过来一把生锈的破六响枪,我就在林肯公园巡视开了,子弹在我周围穿来穿去。他摆平了三个男同性恋,后来警察打中了他。我是说,义务警员的名字可不是白来的……
“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些变态认出同类有多少种说法?比如‘提升’,让人知道你跟他们是一伙的?
“‘抓住她!’
“‘抓住那个卖止痛剂的家伙!’
“‘热心的比弗向他求婚太快了。’
“
鞋店男孩(他在鞋店里搜查拜物狂,所以得到这个外号)说:‘把它给一个有润滑油的蠢蛋,他准会回来求你再给他一些。’男孩看到蠢蛋,便会呼吸加重。他的脸就会涨红,嘴唇发紫,像一个爱斯基摩人热得受不了。然后,他慢慢地、慢慢地向那个蠢蛋献殷勤,揣摩他的感觉,用表皮腐烂的手指触摸他。
“鲁比的模样像个真诚的小男孩,蓝色霓虹灯把他全身照亮。简直是从《星期六晚间邮报》封面上那串蠢蛋中间走下来的,靠毒品保养自己。他的那些傻瓜从来不告密,骗子们甚至还为鲁比带着一个针头。一天,小男孩布鲁开始毒瘾发作,那流出来的东西,准会让救护车上的护理员看了要吐。最后鲁比疯了,在空荡荡的自助餐馆和地铁车站跑来跑去,大喊:
‘回来,伙计!!回来!!’跟着他的伙伴直接进了东河,在那些避孕套、橘子皮、报纸碎片中间,沉入黑色暗流,河水中凝固着大麻烟和敲平了以免色情发射专家染指的手枪。”
那“果子”想:“多有性格!!等我回头跟克拉克餐馆里的兄弟们吹吹这一段。”他是个性格收藏家,乔?古尔德的海鸥表演,也会使他停住脚步。所以我把他当成一个傻帽儿,跟他约了个时间,准备卖给他一些他所说的“豆荚”。我想:“用点樟脑香糊弄一下这个傻瓜。”(注:樟脑香燃烧时的气味像大麻,经常卖给粗心大意或没有经验的人。)
“唉,”我拍着我的胳膊说,“这是份内的事啊。就像一位法官对另一位法官说的:‘要公正,如果做不到公正,就要专制。’”
我闯进自助餐馆,看见比尔
?盖因斯裹着一件别人的大衣,看上去像一九一〇年的一位半身不遂的银行家,年迈的准男爵,衣衫褴褛,模样猥琐,正用脏得发亮的手指抓着重糖重油的蛋糕。
我有几个城外的顾客由比尔负责打理,准男爵认识几个抽鸦片时代的遗老,幽灵般的看门人,像灰烬一样苍白,鬼魅的门房飘过尘封的门厅,缓慢苍老的手,在宿醉未消的黎明,咳嗽,吐痰,隐退的销赃倒爷,住在戏剧旅馆里,还有从皮奥里亚来的贵夫人,鸦片玫瑰,和脸上从不变色的清心寡欲的中国侍者。准男爵迈着老迈昏沉的醉步,耐心、谨慎地把他们一个个慢慢找出来,朝他们没有血色的手里扔进几个小时的温暖。
我为了消遣,跟他打过一次交道。你知道,老人贪吃起来,是什么脸面都可以丢掉的,你在旁边看着简直要吐。老瘾君子对于毒品也是同样的德行。他们一看见毒品,就语无伦次,失声尖叫。烧鸦片时,似乎把身体上体面的外衣都烧化了,口水从下巴上挂下来,肚子里咕噜咕噜,所有的肠子都在蠕动,你觉得随时都会有一大摊口水滴下来,把毒片埋在中间。看着真是恶心。“唉,我那些小伙子有朝一日也会这样,”我感慨地想道,“生活真是古怪。”所以我从谢立丹广场车站回到市中心,生怕那个雷子还潜伏在扫帚间里。
我说过,这种情况维持不了多久。我知道他们都在那里讨论商量,要发挥那些该死的警察的神奇作用,在利文沃斯放出一些我的假人。“在那个上面扎针是没有用的,迈克。”
我听说他们就靠假人抓住了查平。那个被阉过的老雷子就坐在房子的地下室里,一年到头、一天到晚挂着一个假的查平。当查平在康涅狄格州被绞死时,他们发现这个老惯偷的脖子也断了。
“他从楼上摔下来了。”他们说。你知道警察的那套鬼话。
毒品被魔法和禁戒、诅咒和护身符所包围。我可以通过雷达设备找到我在墨西哥城的毒贩子。“不是这条街,下一条,往右……现在往左。现在再往右。”找到他了,一张没牙的老太婆似的脸,两只眼睛都瞎了。
我知道这个毒贩子一边走路一边哼着小曲儿,从他身边经过的每一个人都听得见。他太暗淡灰白,毫无特色,像幽灵一样,他们看不见他,还以为是自己脑子里在哼小曲儿呢。于是,顾客就在《微笑》、《我有恋爱的心情》、《他们说我们年纪太轻难走正路》或当天的另一支歌曲声中走进来。有时,你可以看到大约五十个贼眉鼠眼的吸毒者毒瘾发作,刺耳地尖叫,跟在一个吹口琴的男孩子后面跑,老板就坐在一张藤椅上,扔面包给天鹅吃,一个肥胖的娘娘腔在西五十大街上遛他的阿富汗猎狗,一个老醉鬼靠着路灯柱子撒尿,一个激进的犹太学生在华盛顿广场散发传单,还有一个树木修补专家,一个灭杀害虫的人,一个在耐迪克商店跟店员称兄道弟的假冒的“果子”。世界毒品交易的网络,由腐臭的精液组成的索带来进行调整,龟缩在带家具的房间里,在清晨的宿醉中瑟瑟发抖。(老家伙吸着中国佬洗衣房后面冒出的黑烟,忧郁宝贝死于吸毒时间过长或一口气喘不上来。)在也门、巴黎、新奥尔良、墨西哥城和伊斯坦布尔——在气锤和蒸汽铲下发抖,尖着嗓子互相醉骂——但我们谁也不会听见,老板从一辆驶过的蒸汽压路机里探出身子,我换到一桶柏油。(注:伊斯坦布尔被推倒后重建,是特别破烂的毒品交易场所。伊斯坦布尔的海洛因贩子比纽约城的还多。)活着的,死了的,恶心呕吐的,处于迷醉状态的,上瘾的,戒毒的,重新上瘾的,都直奔毒品而来。毒贩子在墨西哥联邦区的多洛雷斯街上吃炒杂碎,在自助餐馆吃重油重糖蛋糕,遭遇埋伏,被老乡追踪到交易点。(注:新奥尔良的黑话,老乡是指缉毒警察。)
中国老头往一只生锈的锡罐里滴了一些河水,把煤渣般又黑又硬的烟泡洗掉。(注:烟泡是鸦片抽过后的灰烬。)
反正,雷子已经拿到了我的小匙和滴管,我知道他们被那只唤作盘子威利的瞎家雀儿领着,很快就要找到我的交易地盘上来了。威利有一张盘子般的圆嘴巴,周围一圈敏感坚硬的黑毛。他的眼球被子弹打瞎,由于吸海洛因,鼻子和上颚都毁坏了,全身伤痕累累,质地像木头一样又干又硬。他的那张嘴巴,现在只能吃屎了,他摸索着无声的毒品交易,有时嘴里滴答下一条长长的口水。他在全城追随我的足迹,找到我刚刚搬出的房间,雷子还闯进一对来自苏福尔斯城的新婚夫妇的屋子。
“好了,李!!快从那安全带后面出来!我们认识你。”说着,立马就把那男人的阴茎揪掉了。
现在威利干劲十足,总听见他在外面的黑暗中(他只在夜里活动)呜咽,总感觉到他瞎着眼、张着嘴巴四处搜寻时那种可怕的紧迫感。他们闯进来搜查时,威利完全失态,嘴把门咬穿了一个洞。如果不是警察开始搜查存货,控制住了他的情绪,他准会把他找到的所有毒品一股脑儿都吸进去。
我知道,别人也都知道,他们用盘子来对付我。如果我那些小顾客表明态度:“他强迫我做那些可怕的性行为来换毒品。
我就永远不能在街上混了。
于是,我们囤积了一些海洛因,买了一辆二手老爷车,朝西出发。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