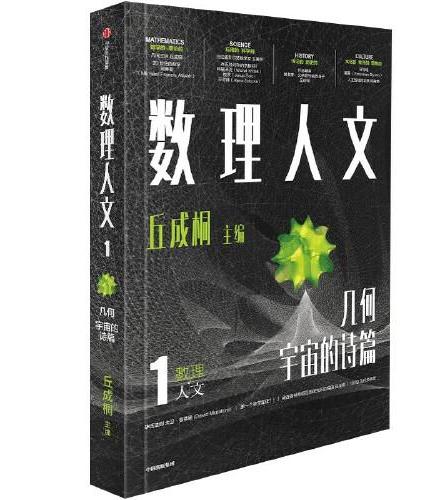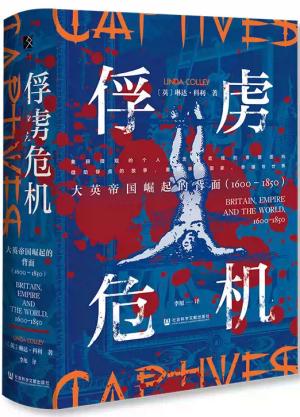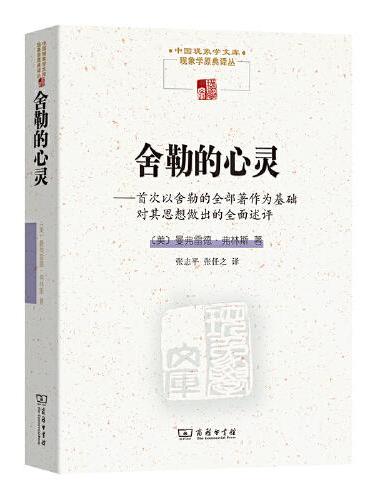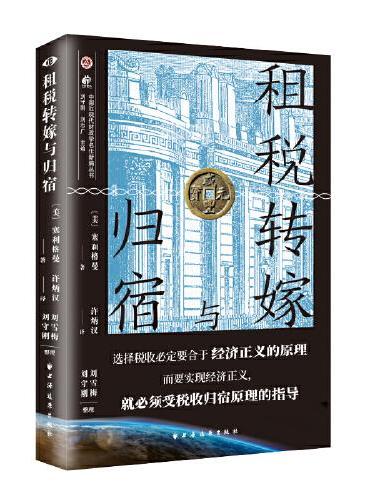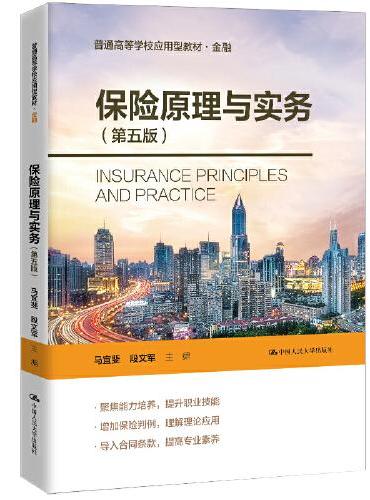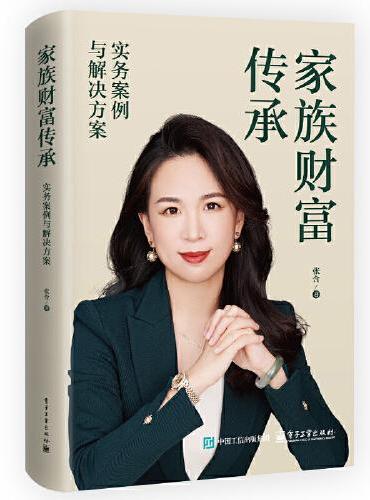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数理人文(第1辑)
》 售價:HK$
107.8
《
俘虏危机:大英帝国崛起的背面(1600~1850)
》 售價:HK$
130.9
《
家庭心理健康指南:孩子一生幸福的基石
》 售價:HK$
65.8
《
舍勒的心灵(中国现象学文库·现象学原典译丛)
》 售價:HK$
79.2
《
租税转嫁与归宿
》 售價:HK$
107.8
《
保险原理与实务(第五版)(普通高等学校应用型教材·金融)
》 售價:HK$
49.5
《
十三邀Ⅱ:行动即答案(全五册)
》 售價:HK$
316.8
《
家族财富传承:实务案例与解决方案
》 售價:HK$
97.9
編輯推薦:
当代中国思想者的研究视域从来没有离开过对中国社会的人文关注。
內容簡介:
全球化研究是199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的一大热点,迄今犹然,牵动着人文社会科学诸多网结,这方面的著述早已汗牛充栋。然而,从哲学角度对全球化进行研究和概括的著作并不多见。本书将“全球性”作为一个扬弃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新的哲学范畴,认为“全球性”将带来“世界文学”的终结,并同时出现一种“全球文化”。但是,全球文化并不是单一文化,而是永远处在一种“对话”的过程中,是为“全球对话主义”。“对话”包含了对自身的超越,因而具有全球性和抽象性,而“对话”也同时假定了参与对话者的不可通约性,“对话”由此得以持续。本书坚信,“全球对话主义”将是一种新的全球意识形态,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需要这样一种理论,一种眼界,一种胸怀,或者,一种态度。
關於作者:
金惠敏,男,汉族,1961年生,河南淅川人,哲学博士。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曲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导、学位委员,英国国际权威期刊Theory,
目錄
序言
內容試閱
就国际范围而言,当然也包括中国,全球化作为一个学术的和社会的话题应该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真正启动起来的。之后,迅即升温,接着是持续了很长时间的大面积的高热、高热、高热……是否会降温,不好贸然断定,但如今的情况则确乎是欲说还休而不说也罢了,因为好像已无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