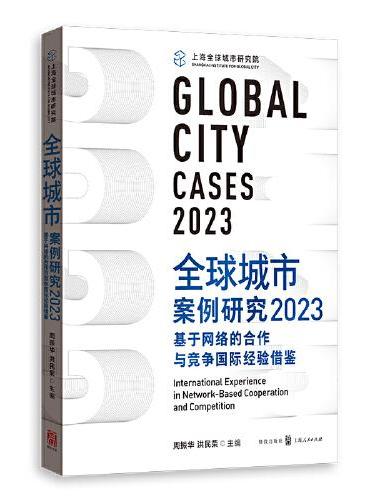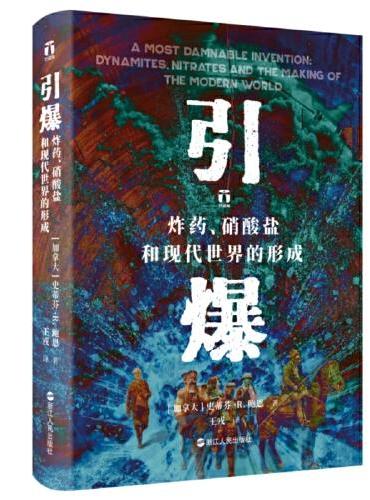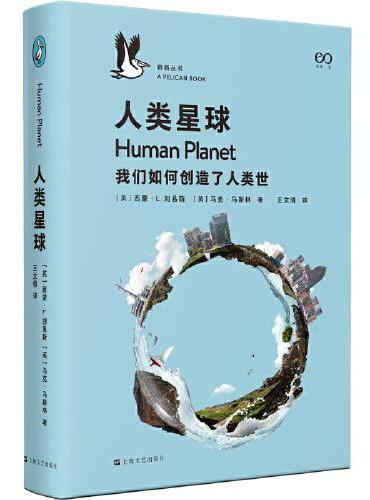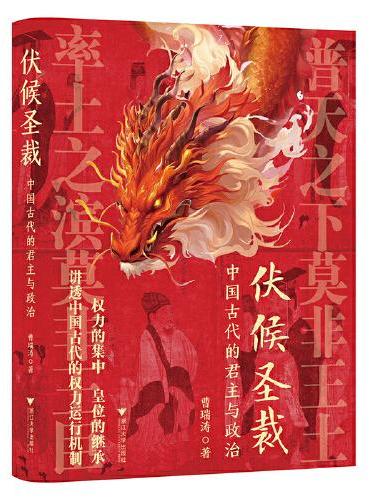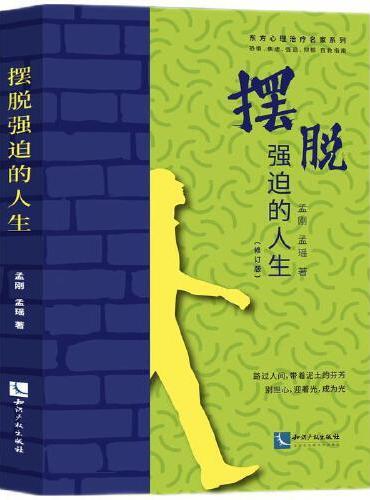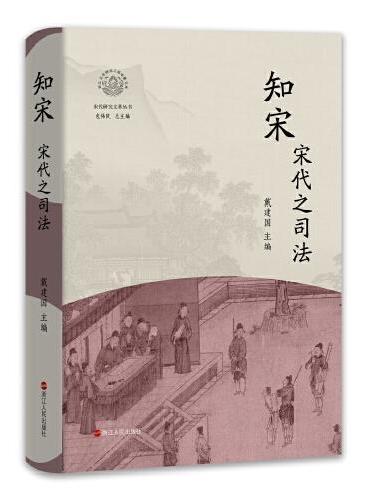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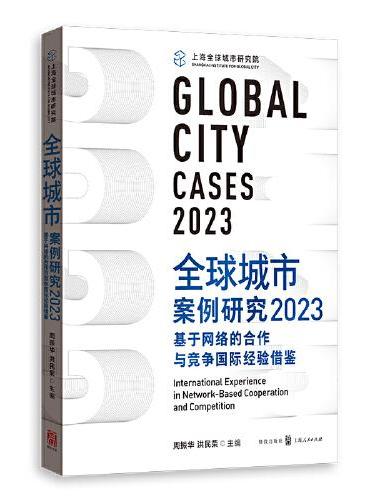
《
全球城市案例研究2023:基于网络的合作与竞争国际经验借鉴
》
售價:HK$
19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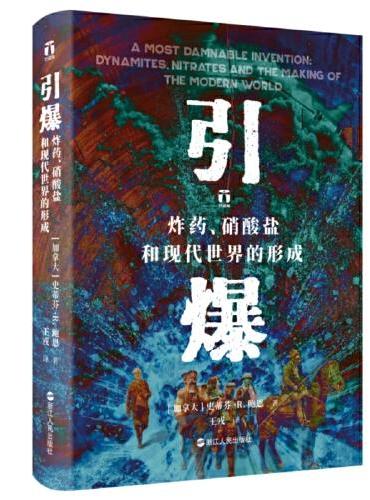
《
引爆:炸药、硝酸盐和现代世界的形成
》
售價:HK$
8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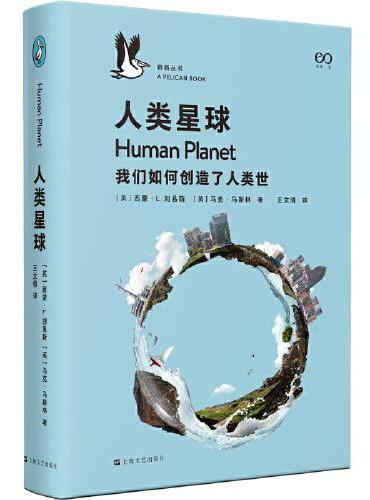
《
人类星球:我们如何创造了人类世(企鹅·鹈鹕丛书013)
》
售價:HK$
9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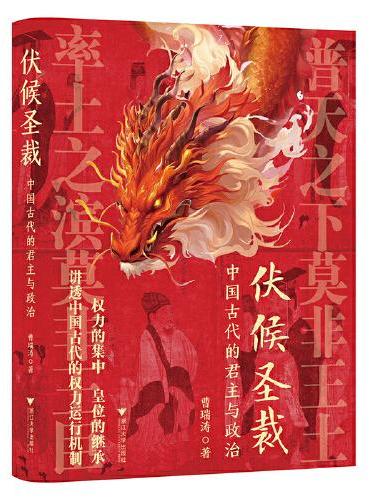
《
伏候圣裁:中国古代的君主与政治
》
售價:HK$
98.6

《
艺术图像学研究(第一辑)
》
售價:HK$
18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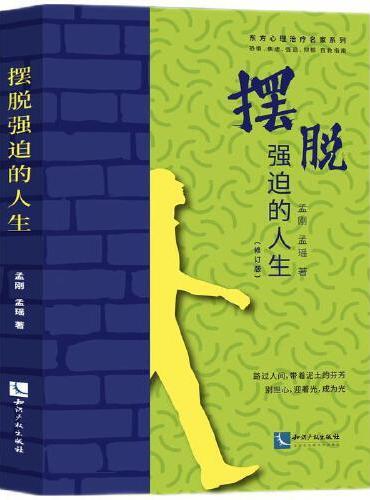
《
摆脱强迫的人生(修订版)
》
售價:HK$
8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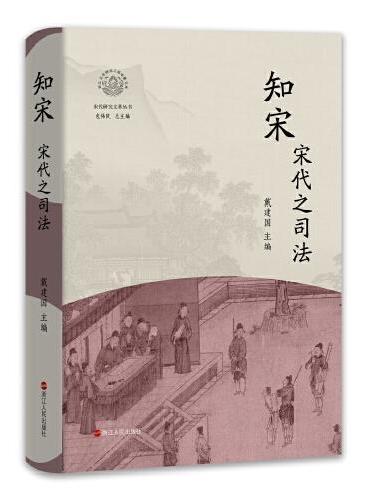
《
知宋·宋代之司法
》
售價:HK$
99.7

《
空间与政治
》
售價:HK$
87.4
|
| 編輯推薦: |
前线硝烟弥漫,后方敌意重重,战争无处不在。
弹火纵横
战友是生死依托
传奇作者亲历“二战”前线,八次被俘,死里逃生!
在欧美文坛,他与荷马、海明威、哈谢克齐名
本书首度披露德国纳粹军队鲜为人知的作战细节全景再现“二战”最前线士兵的惨烈命运
揭秘充满原始兽性的杀戮内幕,直面生存底限的人性罪恶!
解救被战火灼伤的灵魂,解答命令与人性间的困惑!
|
| 內容簡介: |
战争把士兵们彻底变成了动物,充斥他们内心的只有暴力和无孔不入的恐惧。
刑罚团战士斯文、“老大叔”、“小混球”、波尔塔、帝奇因重伤而离开前线,被堆放在破烂不堪的火车车厢里运回后方战地医院,在火车上,没人顾得上他们开裂的伤口,也没人在乎他们吃什么。他们越过了前线的炮火轰炸和旅途的残酷摧残,终于抵达战地医院,但是在那里他们得不到有效地治疗,战争留下的心理创伤也无人理会,他们酗酒、打架、无恶不作,没有人认为他们是为国而战的英雄,都希望他们尽快去死,所以没等伤势痊愈,他们就又被派往了下一处战场。
战争给士兵们带来的折磨。让他们唯能祈愿伤到连站都站不起来或者直接死在战场。
|
| 關於作者: |
斯文·哈塞尔(Sven
Hassel),1917年生于丹麦,14岁加入国家商船队。1936年在丹麦国家军队里服役。退役后,面临失业,随后便加入德国军队,“二战”期间,除了北非战场以外,他几乎在所有战场前线血战过。先后负伤八次,辗转于苏、美、英、丹监狱,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战争的残酷和军营的黑暗,也就是在那时,他开始了这一系列“二战史诗”的创作。
|
| 目錄:
|
第一章 开往战地医院的列车
第二章 生死分界线
第三章 独裁者——“小混球”
第四章 朵拉妈咪
第五章 犹太人
第六章 复仇
第七章 “小混球”订婚
第八章 十一级风酒吧
第九章 夜晚的炸弹
第十章 淫魔
第十一章 即将出发的列车
第十二章 运输线
第十三章 重返前线
第十四章 深入敌后
第十五章 游击队
第十六章 探亲
第十七章 党卫军之夜
第十八章 萍水情缘
|
| 內容試閱:
|
第一章 开往战地医院的列车
我们这帮倒霉蛋被塞进一家急救中心,一个军医冷冷地扫了我们一眼,我们一个个蓬头垢面,臭气熏天,头发、领口依稀可见一群群虱子在蠕动,他便气不打一处来,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世界上最邋遢的猪也比你们干净一万倍!”看来这个军医还是个涉世不深的孩子,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程度知之甚少,在他踏上这片战场之前,顶多闻到过奥地利格拉茨药厂漂浮在空中的一星药味。
“小混球”也不是省油的灯,他把能够想到的最恶毒的谩骂送给了这位军医,说实在的,这些个龌龊的诨名用在“小混球”自己身上最合适。军医气得暴跳如雷,他暗地里记牢了“小混球”的姓名和所在部队的番号,他以刚刚获得部队荣誉的那份热乎劲儿,发誓要让“小混球”受到最严厉的惩罚,除非“小混球”暴尸路途——对军医来说,这当然也是好的结局。
军医把一块块大小不一的碎弹片从“小混球”红肿的肉体里取出来,“小混球”痛得嗷嗷直叫,军医在一旁哈哈大笑。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才过三个星期,军医就被行刑队给枪毙了。原因很简单,一头野猪咬伤了一位将军,那位从野猪口里逃生的将军却很无辜地死在了军医的手术刀下。给将军做手术的那天,军医喝得酩酊大醉,完全不在状态中。集团军军部理所当然要医院交肇事者,医务官毫不犹豫地就把这可怜的家伙呈报了上去。军事法庭裁定,由于军医玩忽职守,业务能力极差造成了事故。
行刑那天,军医被五花大绑在一棵老柳树下。
他两腿瘫软,完全迈不开步,四个行刑队队员拖着他,一人钳住他的头,两人攫住他的腿,还有一人抱着他的上半身,大概是箍得太紧,他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突突突地狂跳。
他一路尖叫,很不体面。
他们对他说:“死也要死得像个男人,男人最羞耻的事就是哭泣。”
他已经是一位拥有两颗星的后备部队医院的军医,要他这样一个人死得从容淡定谈何容易!他才23岁,总认为自己高人一等,年轻有为,前途无量。
据负责行刑的第94团的一个老步兵说,他死得太难看了。第94团的兵个个本事了得,不知道有多少人死在他们手上,若说人的死相,他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整个森林此时一片沉寂,全然不见冰霜扫荡一切死物和活物时的混乱。
机车拉着望不见尾的车厢缓缓前行,汽笛声绵长哀怨。车头喷着白色蒸汽,让以严冬苦寒著称的苏联冬天看上去更加寒冷。火车司机们都戴着毛茸茸的皮帽子,穿着厚厚的棉袄。
顶篷和两侧漆着红十字的车厢里塞满了伤兵。火车前进的冲力,将路基上的雪花扬起、荡开,那泛漫的雪花从结着霜的窗户缝隙钻进来,在车厢中袅袅娜娜地打着旋。
我躺在48号车厢,“小混球”和小个子法国军团大兵也在这里。“小混球”的臀部被迫击弹片炮削掉了一半,只能趴着,小个子法国军团大兵每天都要给他举好几次镜子,因为他想看清战争给他带来的伤。
“你说说看,伊凡(德军对苏军的戏称)撕掉了老子一大块屁股肉,他们会给我发个作战勋章吗?”
小个子法国军团大兵低低地笑了一声:“你真够天真!你还真信!哪个兵不是掉了脑袋后才获得一个勋章的?他们会在你的档案上给你记一次功,接着直接送返前线,好让你把另一半屁股也留在战场上。”
“真他妈的扫兴!到时候老子给你也送一块!”“小混球”愤愤然,哆哆嗦嗦想站起身来,却又不得不骂骂咧咧地躺回草垫子上。
小个子法国军团大兵拍拍“小混球”的肩膀,嘿嘿笑。
“放松点儿,邋遢鬼,要不然你就会去见上帝啦,和其他死鬼一起被卸下车去。”
靠边躺着的胡博不叫唤了。
“他死了吧。”“小混球”说。
小个子法国军团大兵一边擦去胡博额头上的汗,一边低低地说:“他很快就会有伴的。”胡博一直发高烧,血水和脓水浸透了肩上和颈部的衣服,这病号服他才穿上一个星期!
小个子法国军团大兵在外籍军团服役12年,其间受伤14次,这次是他第16次受伤。他自己都认为自己不像德国人,倒更像法国人:1米68的个子,又黑又瘦,一根烟像长在嘴角一样时刻叼着。
“你这个王八蛋,我要水!”肚子豁开的胡安在喊叫。那士官先是威胁、谩骂,再是乞求,最后开始哭了起来。车厢那头传过一阵嘶哑的坏笑,“要是口渴,你也可以像我们一样舔车厢墙壁上的冰嘛!”
我身旁躺着的中士被一挺机枪扫得满身都是窟窿。只见他忍住腹部的剧痛,勉强支起半个身体,伸出一条手臂,像个新兵蛋子似的,行了个僵硬但很标准的纳粹军礼。他开腔唱起来:“高举战旗,排好队!突击队向前向前……”
他跳过一些句子,只拣他最爱唱的唱:“让犹太人的血流吧,也不让社会党分子玷污我们的土地……”唱得精疲力竭了,他就倒回草垫子上。
一阵哄笑撞到被白霜结住的车厢顶篷反弹回来,声音变得更大了。
“‘英雄’撑不住了。”有人清了清嗓子,“阿道夫可不在乎我们,他现在可能正给它的蒙古杂种狗喂食!”
听到这话,那中士歇斯底里地叫了起来:“我要叫你们到军事法庭吃不了兜着走!”
“小混球”将手中一饭盒子的烂白菜朝那面色死灰的中士扔了过去,“小心我把你的猪舌头挖出来!”
那位热爱希特勒的炮兵中士忍不住心里的气和满身窟窿流出的痛,泪流满面地咆哮:“记着!我会修理你这个王八蛋的!”
“呸,老子等着!”“小混球”一边冷笑,一边挥舞着那把他平时藏在靴子里的宽口军刀,“老子要是能站起来,现在就过去,把你那猪脑子剜出来,寄给生养你的纳粹母猪。”
火车一阵急刹车,突然停了下来,造成的颠簸弄得我们车厢里呻吟一片。
严寒像蛇一样游进车厢,越来越深,麻木了我们的脚,冻僵了我们的手。车厢内外的冰霜对着我们狰狞地笑。
有人自娱自乐,用刺刀在车厢内壁霜上画各种动物。他画了一只小老鼠,一只松鼠,还有一条小狗,我们管它叫奥斯卡。其他的动物都被后来结的白霜给覆盖了,只有奥斯卡,那工程陆战队一等兵是画了又画。我们都喜欢奥斯卡,还和他热烈地讨论它。画家说,奥斯卡是一条极美的小狗,满身长着棕色的长毛,头上还有三个小白点儿。我们舔墙的时候都很小心,生怕弄坏了奥斯卡。画家发现我们厌倦了奥斯卡之后,就又画了一只猫,让小狗去追。
“我们这是往哪儿去啊?”一个17岁的小步兵问。他忘了自己两条腿已经被炸得稀烂。
小步兵的同伴是个头部受伤的士官,他轻声对小步兵说:“孩子,我们正回家呢。”
听到他俩的对话,一个黑海水兵全然不顾自己被炸得粉碎的髋骨,哈哈笑了起来:“你们听到了吗?回家!哪里是家?蠢猪!是地狱,是天堂,还是天堂里的绿色山谷?在那绿色山谷里,阿道夫的天使们额头上印着纳粹的‘卍’(万字符),他们在金色竖琴上演奏动听的纳粹党歌!”他大笑之后,抬头呆望着缀满冰晶的车顶,那冰晶也漠然地回望着他。
火车又开动了。这趟附属于战地医院的应急火车共有86节车厢,都是过去用来运牲口的闷罐子。冰冷、肮脏的车厢里塞满了伤兵。这是一群怎样的战士啊?他们为了自己的国家身受重伤。火车的每一次颠簸都会让他们痛得死去活来,咳嗽声、哭泣声、诅咒声充斥着每一个车厢。我们这些垂死的人已被死神吓坏了,这是一出怎样的人间悲剧?这些惨状是从不曾在征兵公告和立功榜上提到的。
“小混球”对着小个子法国军团大兵大声说:“听我说,沙漠浪子!一到那臭烘烘的战地医院,我先去喝他个烂醉,然后就去找三个黑妞大干一场。”他舔了舔冻坏的嘴唇,美滋滋、梦呓般地嘟哝着:“当然是三个一块儿上,我要让她们都舒服得哇哇叫。”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期待的喜悦。这是他第一次进医院,所以他把战地医院想象成了服务周到的妓院。
小个子法国军团大兵笑着说:“兄弟,你很快就会知道,一到医院,你就得忙着担心别的事情,你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里都会渗出弹片来,为了防止你去见上帝,他们会对你全身注射,好让你能继续给他们当炮灰。”
“住口!我不想听。”“小混球”被吓得面色惨白。
几分钟的沉默之后,他警觉地问:“那些医生做手术会很痛吗?”
小个子法国军团大兵慢慢转过头来,直直地盯着大个子,只看到“小混球”那张脸已经被未知的恐惧折磨得变了形。小个子法国军团大兵点了点头:
“兄弟,痛,怎么会不痛呢。他们在你身上撕呀、咬呀,你就痛得喘啊、哼啊!不过,振作一点儿,他们会让你痛得发不出声。”
“噢,圣母啊!”“小混球”喘着粗气说。
我在一旁嘀咕起来,“到了医院,他们一动刀,我就开始对自己说,我要找个情妇,一个很贵气的、迷人的、穿着貂皮大衣的情妇。她很有经验,是个真正的风月高手。”
小个子法国军团大兵点点头,咂咂舌头说:“我知道你的意思,那是好货色。”
“什么是情妇?”“小混球”插嘴。
我们老老实实给他解释了什么是情妇,他的脸上顿时神采飞扬。
“噢,原来情妇是住在家里的妓女,是自由职业者!噢,上帝!要是你能找一个多好啊!”他闭上眼睛,想象着兵营里满是漂亮姑娘,他看着她们扭动高高翘起的丰臀,成群结队地在长长的马路上溜达。
为了不让他的梦中情人跑掉,他只睁开一只眼睛来,问道:“找一个那样的情人一年得花多少钱?”
我也在想着身着貂皮大衣的梦中女郎,忘记了我背上的痛,我感叹道:“一年可得花不少啊!”
小个子法国军团大兵来了兴致,“我在卡萨布兰卡曾有过一个情人。那时我还是第2师第3班的中士。我们师长人很好,可不像其他纳粹烂人。”
“去他妈的师长!我们要听故事!”
小个子法国军团大兵大笑。
“她嫁了个船主,那可是个真正的老色鬼。那钱多得啊,他自己都数不清数字后面的零。那娘们看上的也就是他的钱。他俩倒是真正的一对儿。她的唯一消遣是男人,见一个玩一个,玩厌了就甩。”
“小混球”听得上了心,问:“那你也被甩了吧?”
小个子法国军团大兵没搭理他,自顾自地继续讲他的卡萨布兰卡情人。
“小混球”很是顽固,不断地插嘴,最后居然大声地吼叫,弄得整个车厢都说要把他扔出去。
“我只想知道你是不是也被她甩了。是不是从她厨房楼梯上踢下来的?”
“不,我没有!”小个子法国军团大兵火了,“我找着更好的,就撤了!”
我们都知道他在撒谎。他也知道我们只是不想揭穿他。
“橄榄黄的皮肤,乌黑的头发,花样百出的发式,尤其是那内衣,我的上帝啊,喝一瓶1926年的路易王妃香槟都不如看她的内衣。处男们,你们真该摸摸!”
那头部受伤的士官轻轻笑了起来:“你肯定是个老手,我倒是很想跟你出去走走,看看你找的都是些什么货色。”
小个子法国军团大兵头枕着一个装防毒面具的箱子,闭上眼睛躺着,甚至不屑于朝那士官方向看,只说:“那都是过去的事,女人们再也不会要我啦。”
“沙漠浪子,再讲讲你卡萨布兰卡的情人们吧。卡萨布兰卡的妓院到底在哪儿?”
小个子法国军团大兵干咳了一声:“很显然,你们都认为,这世上只有两件事重要,一是妓院,二是兵营。不错,卡萨布兰卡是妓院,也是非洲西海岸一座极招人爱的城市。在那里,二级小个子法国军团大兵都学会了吃黄沙、喝汗水,还可以叫来整个土耳其军乐队演奏,那些土耳其蠢货还以为我们那些兵懂音乐,没想到我们是猪,猪娘生的……”
“也是猪娘养的。”黑暗中,不知是谁又接了一句。这时,大家才察觉到冰冷的夜幕已经降临。
小个子法国军团大兵说:“没错,他们和你、我一样,都是猪娘生养的!”
有人喊:“猪万岁!”
于是我们嘶哑着嗓子一齐喊:“猪万岁!”“为纳粹卖命的猪万岁!”
“你们这些人渣!恶棍!”希特勒的中士顿时怒火万丈,高声尖叫着,“冯?曼施泰因元帅很快就会跨过洛瓦特河,直逼莫斯科!”
有人讥笑他,“那样的话他一定是坐在一趟开往西伯利亚的囚车上。继续啊!榴弹兵,你就是德意志帝国的救世主!”中士抓狂了,歇斯底里地咆哮起来。
“嘿!激情的‘阿道夫’!既然你说起洛瓦特河时如此温情脉脉,那你参加过韦利奇?鲁基的战斗吗”?”小混球”问道。
“那你呢?”一个一等兵问。他肩上只剩下一条生疽的手臂。
“当然我在!我们仨就待在27师的大本营里。有反对意见是吗?混账东西!”突然,“小混球”对着整个车厢宣布,“我一出医院,就会找一个军需部质管处的军官,把他暴打一顿:抽他,抽得他找不着自己的肘子;削他,削掉他半边下巴,让他下半辈子都咧着嘴,笑不像笑,哭不像哭。”
“你怎么这么恨质管处的人?”手臂生蛆的那人问。
“你脑子有水啊?蠢猪!你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吗?穿着雨披却淋得透湿?那些强盗能从我们用的每一件东西里刮出油水来。那帮混蛋从雨披里肯定是也刮了油水,得了好处的,难不成你愣没看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发给我们的雨披没有一件不漏雨,因为那些雨披件件是次品。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其中的猫腻,只有像你我这样的大傻瓜,才会拿起雨披一件接一件地扔,心里盼着下次别再碰上次货。”
小个子法国军团大兵很是赞同,“大动作!哪天我要是混进了军需部,就把雨披专卖给那群贼人。真主安拉若开了眼,我准能得到那肥差。”
“小混球”这会儿全忘了那该死的质管处,惊呼:“你那卡萨布兰卡情妇怎么办?”
“关你个屁事!”才刚消停了一小会儿,小个子法国军团大兵又自言自语起来,“穆罕默德和众先知啊!我这么爱她,却被她蹬了两次。每次我都想找安拉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混球”幸灾乐祸,“不是你不要她吗?”
“那又怎样?”小个子法国军团大兵不耐烦了,“我才不在乎那些乌龟腿、磨盘屁股,又整天叨叨不停的臭娘们!一大老爷们整天追着她们是够蠢的。还别说,她们早上醒来的时候,丑得让人作呕:口红污得满脸都是,两只眼睛肿得跟鱼泡似的,一张脸肿胀得像夜里发了酵的面团。”
车厢深处传来一个声音,“谢谢。我还当你在夸她们呢!”
黑暗中,又有人搭腔,“是的,有些娘们脚上趿着塌了跟的拖鞋,腿上裹着破了洞的长丝袜,头发里还找得出生了锈的铁发卡子。碰上她们,你会很倒胃口的。”
尽管火车行驶时噪音很大,我们还是分辨出了飞机的轰鸣声。我们屏住声,仔细听,就像野兽们嗅到了猎人和那尾随而来的死亡气味一样。
车厢里,我们在发抖,不是因为寒冷,而是因为轰炸机的到来。一直和我们待在一起的死神随时会带走我们当中的任何人。
轰炸机朝火车俯冲下来,轰鸣声越来越刺耳,然后它绕着火车低空盘旋。飞机上那血红的五角星划过夜空,冷冷地看了看火车每节车厢上的红十字标志。不一会儿它又腾空而起,朝高处攀升。突然,掉转头,猛地向火车扑了过来,像一只老鹰看见了雪地里的野兔子。
“小混球”用他那粗壮的手臂支起身来,朝车门外喊:“来吧,赤佬,把我们碾碎啊,一了百了!”
那飞行员似乎听见了,为了满足我们的心愿,也为了尽力把活干好。只听见子弹嗖嗖地穿过车厢壁,撞到对面又反弹回来,刹那间,车厢内哗啦一片,下起了弹雨,车厢壁上被打出了成排成排的无数小洞。
有些人还在尖叫,有些人惊叫之后,就被死神带走了。
火车拉响了汽笛,我们驶进了一片更深的寒冷。飞行员回家去了,去喝茶吃点心了:点心应该有荷包蛋,是那种只煎了一面的荷包蛋。
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天地间清朗无垠,美丽的大自然尽收眼底,飞行员一定很享受他在天空中看到的这人间美景吧!
小个子法国军团大兵又说话了:“我好想吃香肠,不是普通的,是那种烟熏的猪肉肠,味道浓得像黑胡椒,还带着点儿橡子的味道,因为那猪肉是来自橡树林里放养的猪。”
“吃生蛤会得伤寒,”一个膝盖被炸得粉碎的步兵团护旗兵宣称,“要是每次我一上前线就吃一篮子生蛤,那该多美!”
沉重的车轮碾压着铁轨,缓缓前行,那声音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车厢外的冷空气形成一股强风,不断从轰炸机留下的子弹孔里灌进来。
“阿尔弗雷德。”我叫小个子法国军团大兵。没记错的话,我应该叫过他的名字。不过,是很久没这么叫过他了。
他没反应。
“阿尔弗雷德!”这名字听起来是有点傻。
“阿尔弗雷德,你想过有个家吗?里面会有些家具之类的东西。”
“不,斯文,我早过了那个爱幻想的年龄了。”他答道,眼睛闭着,嘴角挂着自嘲的微笑。我很爱看他那张拉长的脸。
“一转眼,我都30多岁了。”他继续说,“16岁那年,我去投报外籍军团,谎报了2岁。现在我已经做了好多年的猪,猪圈就是我的家,西迪贝勒阿巴斯城的那间破屋就是我最后的归宿。那破屋里头住过成千上万的兵,留下的汗臭,即使烟熏、消毒都没用。”
“你后悔吗?”
“你我不必为任何事情后悔,”小个子法国军团大兵回答,“活着就好!这天气也好啊!”
“阿尔弗雷德,就是他妈的太冷啊!”
“冷也好。只要你鼻子嘴巴还能出气,什么天气都是好天气,哪怕是坐牢,只要活着就好。忘了那些‘如果’……本该过得有多好,就是那些‘如果’让人疯狂,忘了‘如果’,好好活着!”
手臂生了疽的那人问:“伤着脖子,你不难过吗?脖子上戴着个钢箍子支撑脑袋,难受得很吧。”
“不,才不会呢,穿着钢领子的衣服我都能活下去。等一切结束之后,我就回外籍军团驻地去,找个守仓库的活:签上个20年的合同,每晚喝上一瓶维波利切拉葡萄酒,然后拿些仓库里无人认领的东西到黑市上去卖,忘了明天是什么。老子要是喝醉了就踢牧师的屁股,每天去清真寺两次,其他的事都他妈的见鬼去吧。”
“阿道夫下台后,我就去威尼斯住,”那护旗兵插嘴进来,“我,12岁时曾去过那儿,多美的城市啊!有人去过威尼斯吗?”
角落里的草堆上传来一个微弱的声音:“我去过。”
我们循声望去,全被吓傻了,那不是一张脸,他的脸皮已经被热油烧焦了。
护旗兵闭了嘴,不敢看他。然后为了取悦那垂死的飞行员,他用意大利语问:“你去过,是吗?”
接下来是难挨的沉默。每个人都感觉到自己不能说话,因为这个离死神最近的人必须享受优先说话的特权。
“大运河晚上最美,波光粼粼,好像一条镶满珍珠的缎带,河面上的贡朵拉船像嵌在珍珠中的钻石。”飞行员喃喃地说。
“河里涨水时,圣马克广场可好玩啦。”护旗兵说。
“威尼斯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我还想去那儿看看。”垂死的士兵还在说,虽然他知道自己会死在布列斯特-立陶斯克东边这趟拉牲口的火车上。
小个子法国军团大兵开始说:“老兵们总是很快活。他们快活是因为他们还活着,他们知道活着是什么意思。”他一边望着我,一边继续说,“但真正的老兵不多,很多人称自己是老兵,只是因为他们肩上的杠杠多,没有和死神交过手的人都算不上老兵。”
“我到威尼斯定居之后,每天都要去吃意大利肉卷和带壳的蟹。对了,一定还得有鳎目鱼!”
“呸!蠢猪,蛤也好吃呢!”小个子法国军团大兵说。
车厢另一头传来了一个声音:“但是,吃蛤会得伤寒的。”
“我才不管它什么伤寒,阿道夫被绞死了,我们就全会免疫的。”护旗兵信心十足地说。
“不许你这样说我们神圣的最高元首。”那炮兵中士还活着,他尖叫起来,“你们这群叛徒!你们会倒霉的!"
“住嘴!”
火车突然刹车,发出尖厉刺耳的怪叫。接着,继续向前行驶,提速,又是一阵急刹车。
车越开越慢,一阵呜咽般的汽笛声之后,它完全停了下来。
机车头吐出一柱白色蒸汽,开走了,那是司机们给机车作补给去了。
我们知道是到站了,因为车厢外异常嘈杂:靴子的踢踏声和人们的呼喊声、尖叫声混成一片。一阵肆无忌惮的大笑夹杂其间,听着特别刺耳,我们躺在草堆上,怒气在肚肠内翻滚。毫无疑问,只有纳粹猪会笑成那样,忠厚老实人绝不会有那种笑。
“我们这是到哪儿啦?”一等工程兵问。
“苏联。”小个子法国军团大兵的回答很短。
“去死吧,你!我没让你回答!”
“那你还问什么,大头?”
“我想知道到了哪个城市?”
“有意义吗?”
这时,车门被拉开了。一个医疗队的士官脑残似的盯着我们看。
“嘿,哥们!”他嘴里发出马一样的嘶嘶声。
“瞪什么瞪!”“小混球”吼道,又朝那军医的方向啐了一口。
“我要喝水!”污秽的草中有人在呻吟。
“耐心点儿。”那士官回答,“你们马上能喝到水和汤,这儿有需要紧急处理的吗?”
“你脑子有病!我们好得跟刚出生的婴儿似的,我们想和你去踢足球。”护旗兵毫无表情地说。
那士官赶紧转身离开了。
漫长的等待过去了,终于来了个民兵领着两个俘虏出现在车厢门口,他们拖来了一桶汤,开始往我们油渍渍、脏兮兮的饭盒里舀,每人都等到了一勺已经快冷了的汤。我们喝完汤之后,觉得更饿了。民兵答应会给我们再弄点儿来。等了好久,民兵没来,倒是来了个中士,他用枪押着另外两个战俘开始从车厢里往外拖尸体。他们从我们这一节车厢拖出了14具,其中9具是昨天晚上轰炸机的功劳。他们想把飞行员也拖走,刚要动手,他居然动了动,那两个战俘确信他还活着。中士一脸怒容,嘴里嘟囔了几句,但还是让他们把飞行员留在了车厢里。
下午晚些时候,又来了个后备部队医生,他身后跟着两个医疗队士官。他们走到我们当中,把这个瞧瞧,把那个看看,动作很快,对我们每个人都说一句同样的话:“还行,不算太坏。”
他们对飞行员说完那句话后,走到了“小混球”跟前。好戏开场了,不等他们开口,“小混球”就开始发火,“你们这些恶棍!瞧瞧,他们把我弄成了什么?还不算太坏,对吗?你这些江湖郎中,给老子躺下!我把你的屁股也撕掉半边,试试看,然后你告诉我什么才算太坏!”
他一把抓住了那医生的脚脖子,将他拖倒在草堆上。
“当心!当心!”小个子法国军团大兵大叫。
“小混球”旁边手臂流血的伤兵乐了,“好样的,‘小混球’,这就对啦!”说着,他也向医生扑了过去。我们其他人也毫不耽搁,一齐扑向医生。很快,那医生就满身是血,两个助手好不容易才将他拽出人堆。我们一齐喊:“还不算太坏!”
“你们会付出代价的!”受了惊吓的医生威胁我们说。
“你敢吗?再来一次啊。”“小混球”很是得意。
医生和他的助手跳下车,“哗”的一声拉上车门,走了。
火车到第二天早上才开,但是他们忘了我们也要吃早饭。我们这些人除了骂,什么都做不了。
飞行员熬过了漫长的夜晚,但夜里还是死了。一个铁路兵和一个猎骑兵为了得到他那双靴子大打出手。最后,铁路兵一拳击中对手的下巴,让他疼得忘了靴子。这真是一双好靴子:超长的靴筒,筒口的饰毛蓬松柔软,毫无疑问这是那个死去的士兵在上战场之前定做的。
“上帝,多好的靴子!我要穿着它去行军!”铁路兵把靴子举起来,看了又看。他嘴里哼着轻快的小曲儿,开始擦拭。只见他对着靴子不停地哈气,用衣袖子擦了又擦,就像弄到了一件心爱的艺术品似的,宝贝得不行。
“你最好把你自己脚上那双先脱下来,给死鬼穿上,要不然是保不住这靴子的。”有人警告他。
“你是什么意思?”铁路兵张大嘴问,“看谁敢拿!”边说边把靴子往草里藏,那样子和野狗守骨头没什么两样。
“那你就把我的话忘了吧,你会知道是谁要拿走你的靴子。”同一个人在继续说,“宪兵会脱下你那双漂亮靴子,以抢劫罪将你捆了去。抢劫,知道吗?甚至还可以叫劫尸。要知道,我以前一直和那些飞来飞去的军警在一起,我是熟悉那些罪名的。”
“该死!”铁路兵抗议说,“可他已经不需要它们了。”
“你也不需要,兄弟,”那人严肃地说,“你不是有军队派发的那一双吗?”
“那双靴子根本没有用,穿着它们走不得路,更别说行军。”
“去对军警说呀,他们会把你往死里打,直到你签字画押承认你收到的是一双阿道夫发给你的世界上最好的靴子。”说话人面色惨白,双唇也毫无血色。他用一双冷眼瞪着铁路兵,笑着说。铁路兵不再说话,也不再做傻事了。他嘴里骂着,把自己的旧靴子给那死鬼穿上了。
不到一小时,死鬼就认不出自己了,因为身上穿戴的全是些他不熟悉的物件。
腹部受伤的胡安又喊要喝水,小个子法国军团大兵给他撮去了一大块冰。他贪婪地吮吸着冰水。
我的双腿开始剧痛。剧痛慢慢上行,直到穿透我身体的每一个部位,感觉就像烈火在炙烤着我的每一根骨头。我很清楚,这是二度冻伤:腿部的皮肤、皮下、肌肉、骨骼逐层坏死,先是刺痛,然后痛觉消退,再是双腿开始感到烧灼般的痛,这种痛会持续,直到双腿麻木,这就意味着我的腿要废了。疼痛还在一个劲地往上钻,一想到医院里被医生截掉的残肢还会冒热气,我就恐惧万分。上帝啊,怎么都可以呀,就是不能截肢啊!我对小个子法国军团大兵诉说内心的恐惧。他盯着我说:“那你的战争不就结束了,可是腿比脑袋重要。”
是的,如果那样的话,我的战争就会结束。我试图安慰自己,可是刺骨的恐惧封住了我的嗓子;我试图想象要是手的话,情况会更糟,可是恐惧根本不放过我,我看到了我的拐杖。不,我不想失去我的腿!我不要假肢!
“你怎么啦?”小个子法国军团大兵惊讶地问我,他没听到我喊“假肢”。
我睡着了,只是做了个梦!梦里我痛醒了,但我很高兴自己的腿还在,腿痛说明它们还是我的,它们还活着。
火车又停了两次,两次都有医生来看我的腿,每次都被告知“还不算太坏”。“穆罕默德,到底怎样才算真的很糟?”小个子法国军团大兵火气很大,他指着刚刚死去的飞行员问:“难道这也不算太糟吗?”没人搭理他,这趟应急火车还在继续向西行驶。
当火车结束12天的行程,到达克拉科夫时,车上的伤兵只剩下三分之一,其他人已经陆陆续续去了另一个世界。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