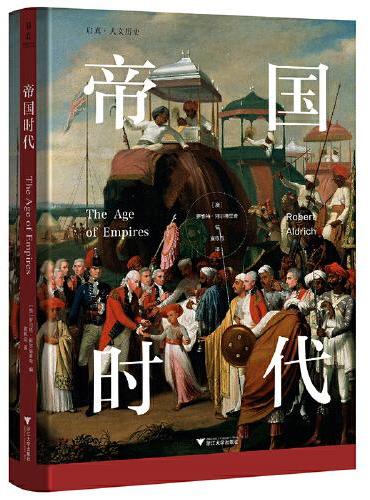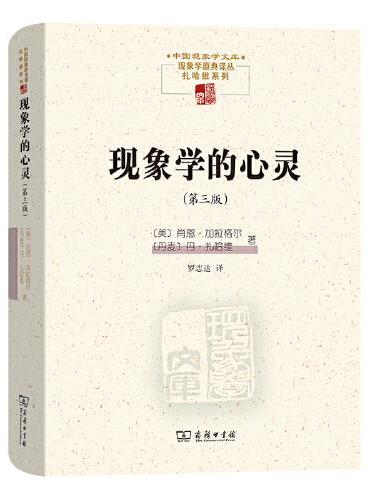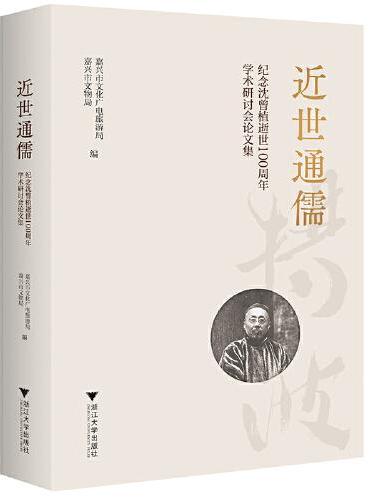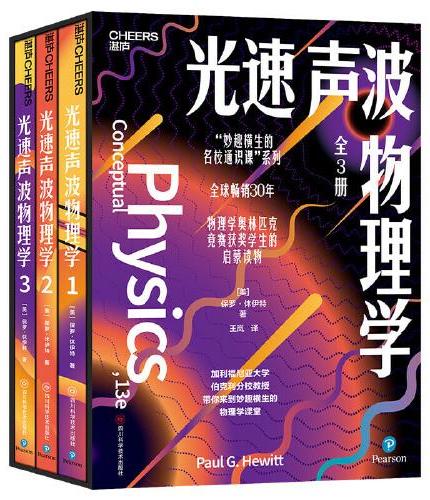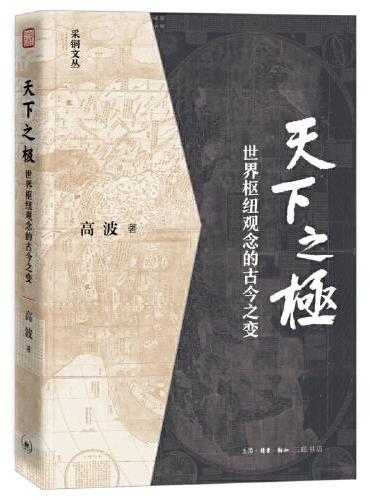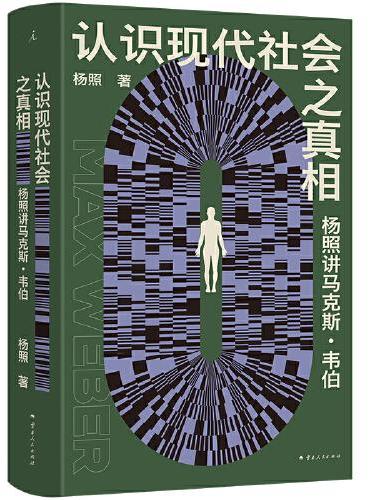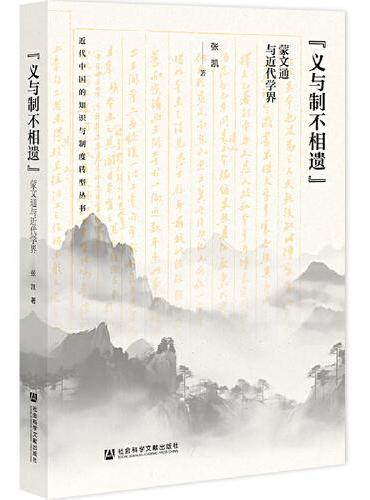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大数据导论(第2版)
》
售價:HK$
7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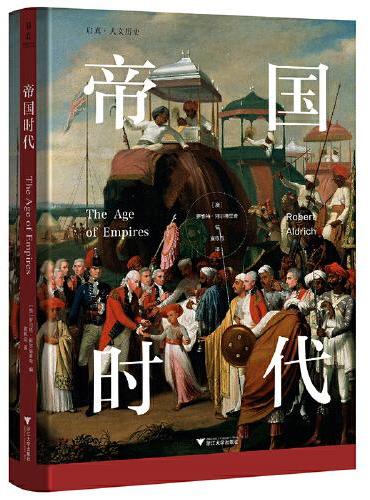
《
帝国时代
》
售價:HK$
20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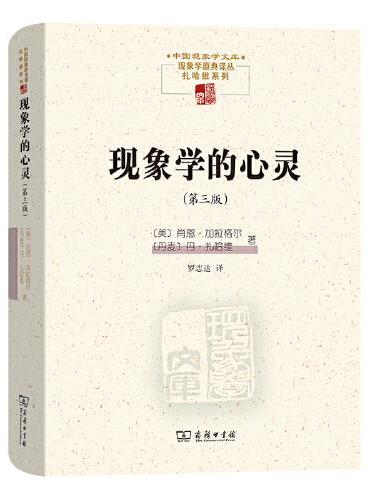
《
现象学的心灵(第三版)(中国现象学文库·现象学原典译丛·扎哈维系列)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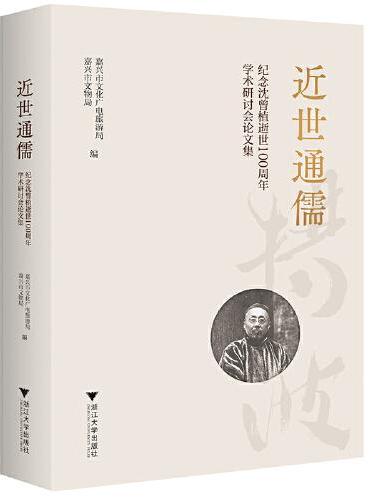
《
近世通儒——纪念沈曾植逝世10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售價:HK$
18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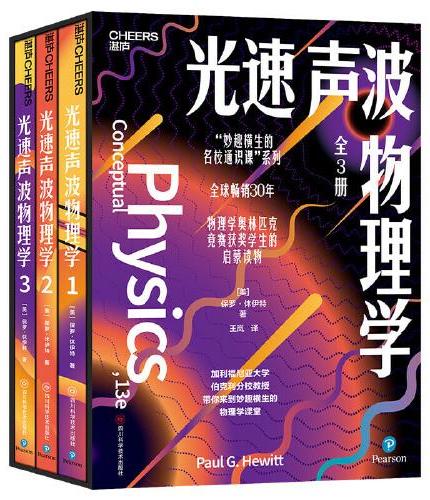
《
光速声波物理学. 1、2、3
》
售價:HK$
49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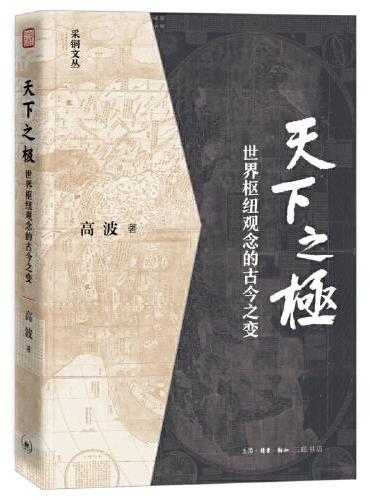
《
天下之极:世界枢纽观念的古今之变
》
售價:HK$
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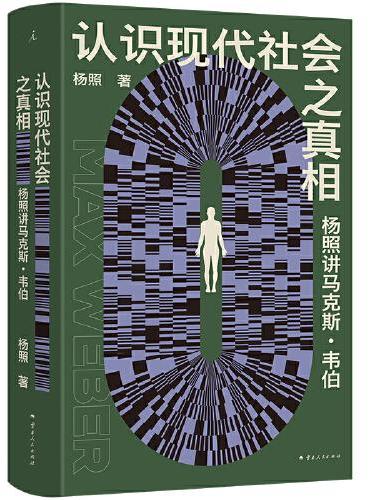
《
认识现代社会之真相:杨照讲马克斯·韦伯
》
售價:HK$
9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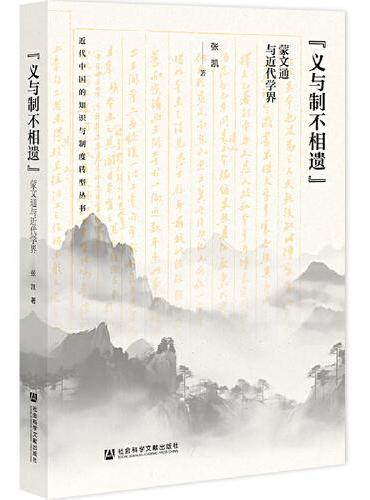
《
“义与制不相遗”:蒙文通与近代学界
》
售價:HK$
107.8
|
| 編輯推薦: |
|
奥兹当今诺贝尔文学奖呼声最高的以色列作家,莫言曾亲面称他为自己的老师。本书《忽至森林深处》是奥兹首部讽喻童话,也是一则精巧奇妙的现代寓言,来源于奥兹母亲所讲述的故事,以优美凄冷的寓言演绎宽容、孤寂、否认与回忆。
|
| 內容簡介: |
|
《忽至森林深处》讲述山村里隐藏着巨大的秘密。动物与飞鸟缘何绝迹?夜晚从窗前闪过的黑影究竟是何物?男孩尼米从森林里回来后,就一直狂叫,又是怎么回事?大人们的讳莫如深,让黑暗的森林恐怖而充满魅惑。玛雅和马提终于鼓起勇气走向森林。在那里他们不仅碰见了尼米,还遇到了传说中的山鬼尼希,看到了动物与飞禽,更在这个王国领悟出许多道理,揭开了多年来一直困扰人们的谜团。可是,当他们开始踏上归途,一切会有所改变吗?
|
| 關於作者: |
|
阿摩司·奥兹是以色列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当今希伯来语作家中诺贝尔文学奖呼声最高的一位。1939年出生于耶路撒冷,12岁那年母亲自杀,直接把他推向了写作道路。父亲懂十几种语言,却只教他希伯来文。奥兹只用希伯来文写作,主要作品有《一样的海》、《我的米海尔》、《爱与黑暗的故事》、《地下室里的黑豹》等。他擅长破解家庭生活之谜,家庭悲剧和夫妻情感其作品常见的主题。他的作品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共鸣,多次获大奖,其中包括1998年以色列建国50周年之际颁发的以色列国家奖、法国的费米娜奖、欧洲颇负盛名的歌德文化奖、西语界最有影响力的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等。此外,奥兹还是一位受人敬重的政治评论家,热情呼吁阿以和平。
|
| 內容試閱:
|
1
伊曼努埃拉老师向班上的同学描述熊长什么样儿,鱼怎么呼吸,猎狗在夜里发出怎样的叫声。她还在班里挂上了动物和鸟类的照片。多数学生都取笑她,因为他们有生以来从未见过动物。多数学生都不相信世上竟有这样的造物。至少我们这里没有。此外,据说这位老师在全村从未找到想要娶她的人,因此,据说她的脑子里装满了狐狸、麻雀,以及单身的人在孤独中胡思乱想的东西。
老师的描述对孩子们的影响微乎其微,只有小尼米是个例外,他开始在夜里梦见动物。早晨到校后,他第一次向大家讲述自己夜晚睡觉前放在床边的一双棕色鞋子在黑暗中变成了两只刺猬,整夜在房间里爬,可一大早,当他睁开眼睛时,刺猬忽然又成了床边的两只鞋。班里的同学几乎全都笑话他。还有一次,他说几只黑蝙蝠深夜来到他的房间,用翅膀驮着他,穿过家里的墙壁,飞到村子的上空,飞过高山和森林,一直把他带到一座迷人的城堡。
尼米是个小迷糊,不住地流鼻涕。两颗凸出的门牙之间还有个豁口儿。孩子们管这个豁口儿叫“垃圾筒”。
每天早晨尼米一来到班里,就给大家讲述他新做的梦;每天早晨他们都说,够了,我们都听腻了,闭上你的垃圾筒吧。他要是不停下来,大家就会取笑他。可尼米并不气恼,与大家一起调笑。他吸吸鼻涕,还把鼻涕咽了下去,突然用孩子们为他取的最伤人的名字来称呼自己:垃圾筒,小迷糊,刺猬鞋。
班上坐在他身后的面包师莉莉娅的女儿玛雅悄悄和他说过好几次:尼米,听我说。你想梦见什么就梦见什么,梦见动物,梦见女孩子,你自己知道就行了。别对任何人说。那样对你不好。
马提对玛雅说:这你就不懂了。尼米做梦就是为了要说给我们听的。不管怎样,他连早晨醒来时都还在做梦呢。
任何事情都会让尼米快乐,任何事情都会让他高兴:厨房里有裂纹的杯子,天空中的满月,伊曼努埃拉老师的项链,还有他自己口中的龅牙,忘记扣上的扣子,森林中的风声。世间万事万物都可以让尼米找到乐趣。一切都可以让他开怀大笑。
直至有一天他跑出课堂,跑出村庄,独自走向森林。大部分的村民都出门寻找他,找了两三天。警察们找了他一周或是十天。在这之后,只有他的父母和姐姐还在寻找他。
大约过了三个星期,他回来了,人又瘦又脏,浑身上下净是擦伤,青一块紫一块的。可他满怀喜悦与激动地狂叫。从那以后,小尼米就叫个不停,再也不说一句话:他从森林回来后一个字也没说过,只是光着脚丫、衣衫褴褛地在村里的街上游荡。他流着鼻涕,龇牙咧嘴,从一个后院跳到另一个后院,爬树攀杆,一直在狂叫。由于过敏,他的右眼流泪不止。
既然得了狂叫症,他就再也不能回学校了。孩子们在回家的路上故意朝他大喊大叫,为的是招他狂叫。他们管他叫猫头鹰尼米。医生说,也许在森林里,他被什么东西吓着或是惊着了,而今他得了狂叫症,过一阵子就会好。
玛雅对马提说:也许我们该做些什么?尽量帮帮他?马提回答说:算了吧,玛雅。他们很快就会腻烦了。他们很快就会把他给忘了。
当孩子们追赶他,取笑他,朝他扔松果和树皮时,小尼米会狂叫着逃之夭夭。他爬上附近的一棵树,待在高高的树杈上,一只眼睛流着泪,龇着龅牙冲他们狂叫。有时甚至在夜半时分,村民们也会觉得听到了远处回荡着他在黑暗中的狂叫。
2
村庄昏暗阴郁。四周只有高山、森林、云翳和阴风。附近没有别的村庄。游客们几乎从未光顾过那个村子,过路人也不会在此驻足。环抱在陡峭高山之中的山谷斜坡上,散落着三四十座小房屋。只有西边在山与山之间有个小山口,那是通往村里的唯一通路,可路并未伸向前方,因为没有前方:这里便是世界尽头。
非常偶然的机会,一个行踪不定的生意人,或者是小贩,有时只是个迷路的乞丐会来到村里。但这些路人顶多待两个夜晚,因为村子遭到了诅咒:这里总是笼罩在可怕的寂静中,听不到奶牛和驴子的叫声,也听不到鸟儿啁啾,没有成群的野鹅穿过空旷的天空,村民之间只谈论最为基本的事情。只听得流水潺潺,夜以继日,因为一条湍急的河流奔腾流过山间森林。它穿过村庄,两岸泛起白沫。它奔涌着,翻腾着,汩汩低吼着,直至消逝在山谷与森林的臂弯处。
3
夜晚,寂静的感觉比白天更加沉郁、厚重:没有狗伸长脖子、竖起耳朵冲着月亮狂吠,没有狐狸在森林中哀号,没有夜鸟悲啼,没有蟋蟀振翅,没有青蛙呱呱作响,没有公鸡在黎明时分打鸣。许多年前,所有的动物——牛、马、羊、鹅、猫、夜莺、狗、蜘蛛和兔子,就全从村庄及其周围消失了。甚至连一只小黄雀都看不到。河里连一条鱼也没留下。松鹤和白鹭在迁徙途中会绕过狭窄的山谷。就连半翅目昆虫和爬虫,蜜蜂—苍蝇—蠕虫—蚊子—飞蛾也多年没见着了。依然记得这些动物的成年人情愿选择沉默。否认。装作遗忘。
多年前,村里居住着七个猎人和四个渔夫。但是自从河里没有了鱼,所有的野生动物迁到远方之后,渔夫和猎人也离开了,去往诅咒影响不到的地方。只有一个名叫阿尔蒙的孤老渔夫一直在村里住到现在。他住在靠近河畔的小木屋里。在给自己烧土豆汤时,他会气哼哼地与自己长谈。直到现在,村民们一直叫他渔夫阿尔蒙,纵然他很久以前便从渔夫变成了农民:白天,阿尔蒙在铺着团块状土壤的苗圃里种植蔬菜和可吃的根茎植物,他在山坡上种了三四十棵树。
他甚至在菜圃里放了一个小稻草人,因为他坚信在他的有生之年所有消失了的飞鸟和动物都可能回来。有时阿尔蒙也会气哼哼地与稻草人进行漫长的争论,恳求他,责骂他,完全不再对他抱有希望。然后,他会拿着一把旧椅子回来,坐在稻草人面前,没完没了地试图说服他,或者劝他至少别那么固执己见。
在晴朗的日子里,渔夫阿尔蒙会在傍晚时分坐在河畔自己的椅子上,戴上一副旧眼镜看书,眼镜从鼻梁滑到他浓密的灰胡子上。不然就是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行字,写写擦擦,冲自己小声嘟囔着各种论据、观点和理由。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学会就着夜晚的油灯,把木块雕刻成许多形状好看的动物和鸟,以及他在想象中或梦境里看到的不知名造物。阿尔蒙把这些木刻生物送给村里的孩子当礼物。马提得到了一只松果猫,还有用胡桃树皮刻成的小动物。阿尔蒙给小尼米刻了一只松鼠,给玛雅刻了两只脖子长长、展翅飞翔的松鹤。
只有从那些小型雕刻和老师伊曼努埃拉画在黑板上的图画中,孩子们才能知道狗的形状,猫的长相,或者蝴蝶、鱼、小鸡、小羚羊和牛犊的模样。伊曼努埃拉教孩子们模仿动物的声音,村民们从孩提时代就已经记住了那些声音,那时动物尚未消失,可孩子们从未听说过。玛雅和马提二人似乎知道了一些严禁他们知晓的事情。他们小心翼翼,不让任何人猜出他们知道或差不多知道了。有时候他们在废弃了的干草棚里悄悄见面,坐在那里低声交谈一刻钟左右,离开时各走各的。村里的所有成年人中,也许只有一位能让他们信赖。也许没有。有几次马提和玛雅差不多决定把秘密告诉修屋顶的达尼尔了,达尼尔晚上有时会和年轻的朋友一起在村中广场大声开着少儿不宜的玩笑。他和朋友们喝酒时,甚至有几次开玩笑说到一匹马、一只山羊、一条狗,他正想着把它们从山谷里的某个村庄弄到这里来。
如果把秘密告诉了修屋顶的达尼尔会怎样?也许他们应该告诉老阿尔蒙?如果有朝一日他们敢走进黑幽幽的森林,哪怕只是几步,试图弄清楚秘密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也许这只是猫头鹰尼米——当然不是他们,做的一个梦,那又会怎样?
与此同时,他们在等待,他们并不知道真正等的是什么。一天傍晚,马提勇敢地问父亲,那些生物为什么会从村里消失。父亲并不忙着回答问题。他从厨房的椅子上站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走了一会儿,然后停住脚步,抓住马提的肩膀。但是,父亲没有看儿子,而是用目光扫视着门上方墙上的一块光秃秃的斑点,那是因潮气渗入石灰使之剥落而留下的印迹。父亲说,马提,你听着。是这样的。村里曾经发生了一些事情,不是令我们骄傲的事情。但并非所有人都有错。肯定不是同样严重的错。除此之外,你是谁呀,你来审判我们?你只是个孩子。不要审判。你没有权利审判大人。无论如何,谁跟你说这里曾经有过动物的?也许有。也许从来就没有。毕竟时间过去那么久了。我们忘记了,马提。我们忘记了,事情就是这样。算了吧。谁还有闲心记这个?现在下去到地窖里拿些土豆来,别没完没了地问下去了。
马提的父亲突然起身离开房间时,又说了一句:你听好了,现在我们,你我之间讲好了——这次谈话只当从未发生过。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这件事?
其他做父母的差不多情愿去否认。要么就是用沉默来逃避这个话题。一个字也不谈。尤其是不在孩子面前谈。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