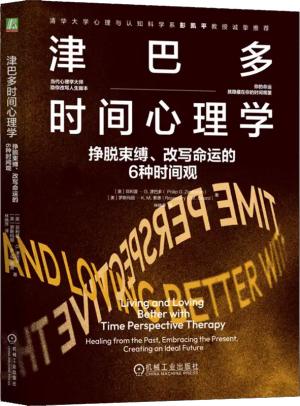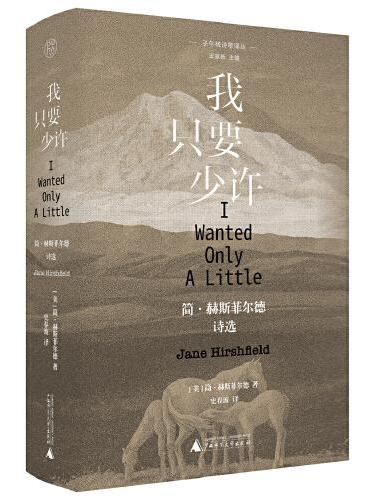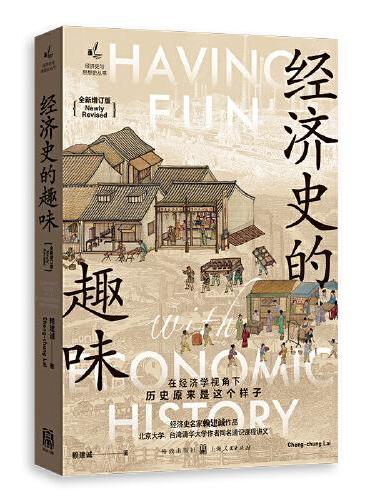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家族财富传承
》 售價:HK$
154.6
《
谁是窃书之人 日本文坛新锐作家深绿野分著 无限流×悬疑×幻想小说
》 售價:HK$
55.8
《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第3版
》 售價:HK$
110.9
《
8秒按压告别疼痛
》 售價:HK$
87.4
《
津巴多时间心理学:挣脱束缚、改写命运的6种时间观
》 售價:HK$
77.3
《
大英博物馆东南亚简史
》 售價:HK$
177.0
《
纯粹·我只要少许
》 售價:HK$
80.6
《
经济史的趣味(全新增订版)(经济史与思想史丛书)
》 售價:HK$
84.0
編輯推薦:
文学大家刘再复对教育的自然情怀
內容簡介:
本书为刘再复先生有关教育文章的合集。作者从跨文化的视野、以哲人的心路历程讨论了教育的本质、内涵、教育的境界、儿童的成长等问题,启人深思。在比较审视的背后,在对故国师长的情思中,是作者对真教育的呼唤和对生命的爱。
關於作者:
刘再复,一九四一年出生于福建南安刘林乡。一九六三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科罗拉多大学、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加拿大卑诗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台湾中央大学、东海大学等院校分别担任过客座教授、讲座教授、名誉教授与访问学者。曾被邀在国内外五十多所高等院校作过学术讲演。著有《性格组合论》、《鲁迅美学思想论稿》、《文学的反思》、《论中国文学》、《放逐诸神》、《传统与中国人》、《罪与文学》(与林岗合著)、《现代文学诸子论》、《共鉴“五四”》、《红楼四书》(《红楼梦悟》、《共悟红楼》、《红楼人三十种解读》、《红楼哲学笔记》)、《李泽厚美学概论》、《双典批判》、《思想者十八题》、《文学十八题》、《读沧海》、《太阳?土地?人》、《人间?慈母?爱》、《人论二十五种》、《漂流手记》十卷、《师友纪事》、《人性诸相》等四十多部学术论著和散文集。作品已翻译成英、日、韩、法等多种文字。
目錄
第一辑 父女教育论语(刘再复、刘剑梅)
內容試閱
关于教育的父女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