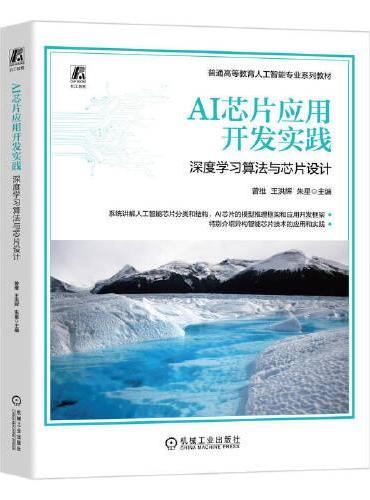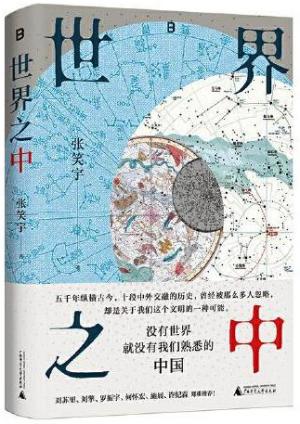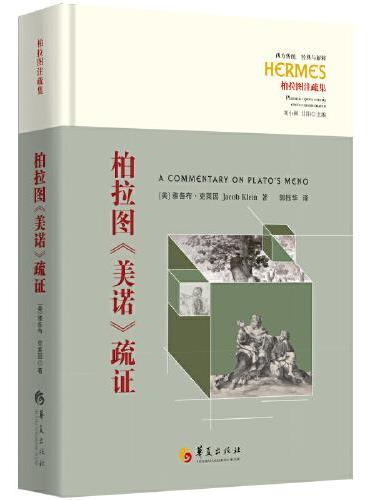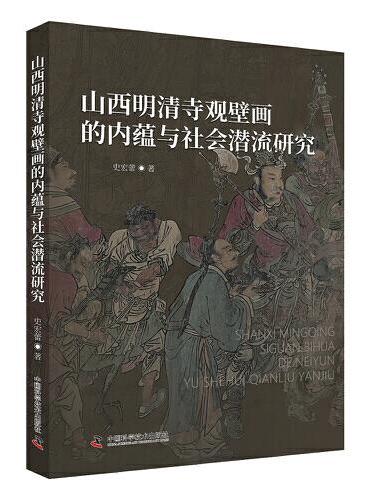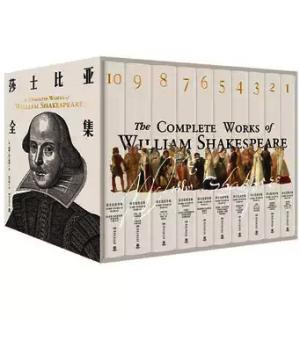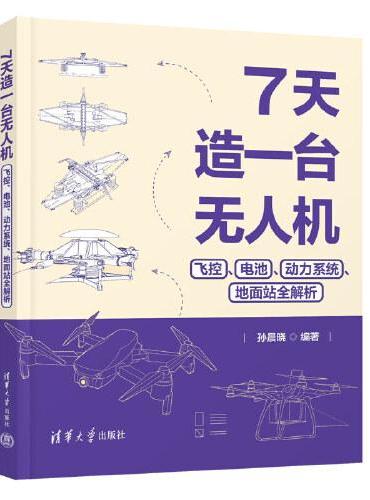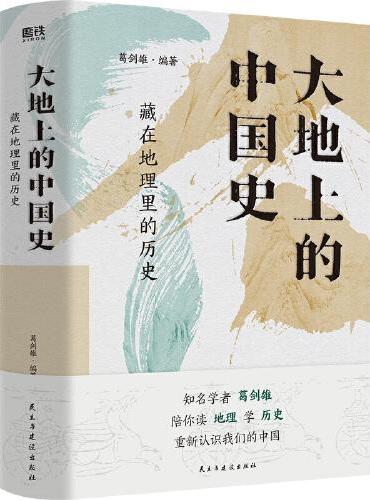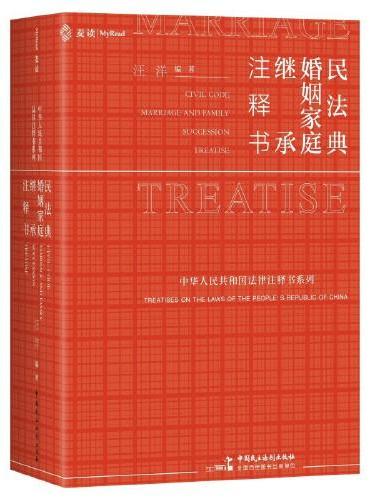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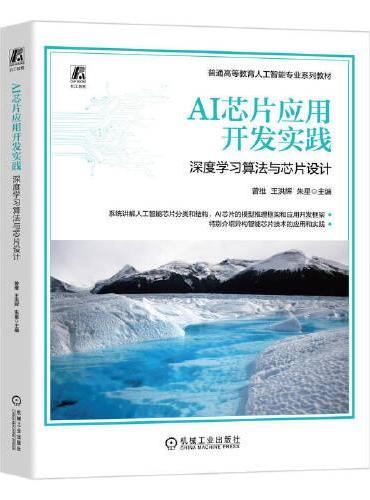
《
AI芯片应用开发实践:深度学习算法与芯片设计
》
售價:HK$
7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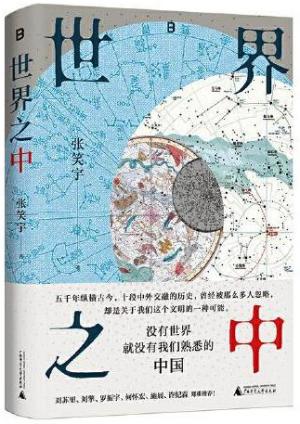
《
世界之中(文明三部曲之后,亚洲图书奖得主张笑宇充满想象力的重磅新作)
》
售價:HK$
8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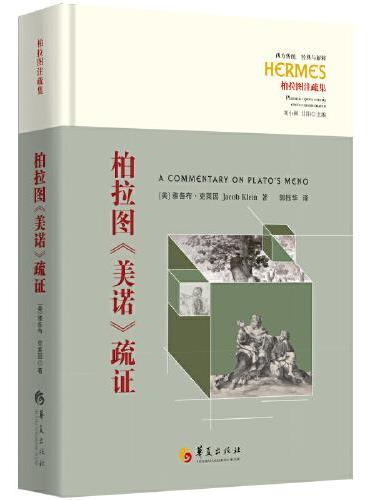
《
柏拉图《美诺》疏证
》
售價:HK$
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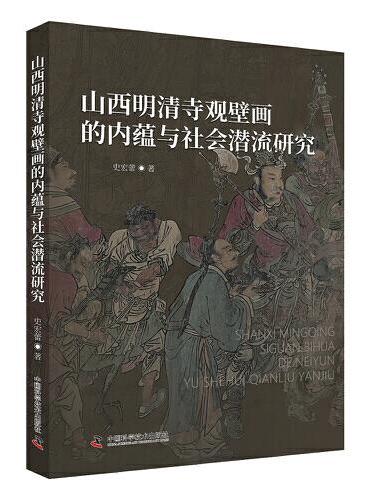
《
山西明清寺观壁画的内蕴与社会潜流研究
》
售價:HK$
14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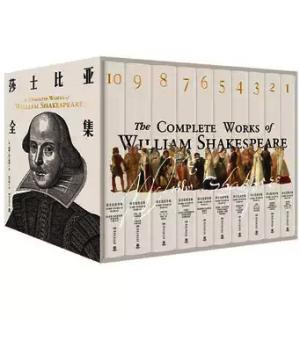
《
莎士比亚全集十卷
》
售價:HK$
59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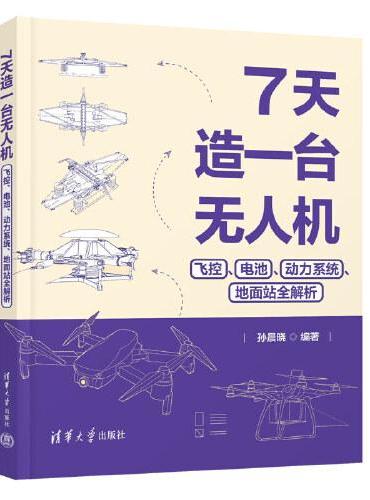
《
7天造一台无人机:飞控、电池、动力系统、地面站全解析
》
售價:HK$
7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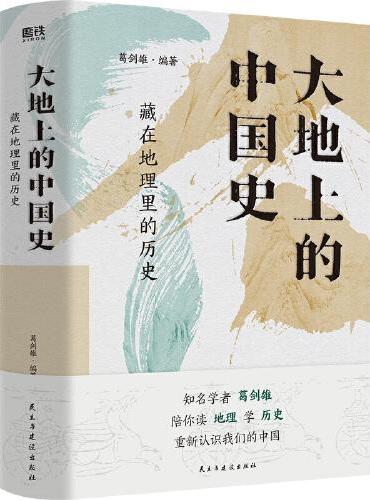
《
大地上的中国史:藏在地理里的历史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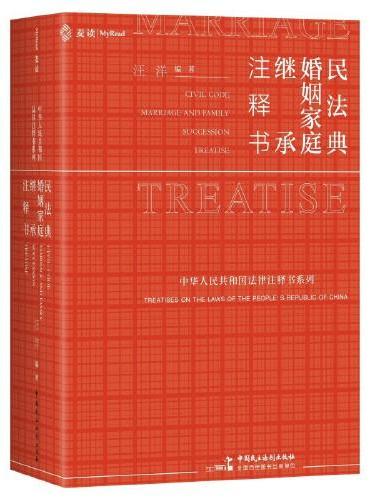
《
《民法典·婚姻家庭继承注释书》(家事法专用小红书,一书尽揽现行有效办案依据:条文释义+相关立法+行政法规+地方立法+司法解释+司法文件+地方法院规范+权威案例,麦读法律54)
》
售價:HK$
130.9
|
| 編輯推薦: |
轰动英国的年度畅销小说,
数十家主流文学媒体蜂拥报道
出版者称其为生平所读过最锥心的作品
亚马逊网站五星推荐
女主人公被欧洲读者网评为“最想要触摸的恋人”第一名
我的灵魂与你相爱,我的身体却未能与你相遇。
这是我们最大的幸运,也是我们最大的不幸。
|
| 內容簡介: |
当一个极度留恋人间、想要重回人间的鬼魂一个自我厌弃、想要结束生命的少年相遇,并一起生活的时候,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阿诗琳能够拯救布莱肯吗?她能否借由这个男孩找回自己离开人间的真相?她能否修补布莱肯一家分崩离析、面临崩溃的关系?她能否寻回属于自己的世界?一切谜底与真相,都在你读完这本书之后。
|
| 關於作者: |
C.K.凯莉·马汀
英国著名畅销作家,目前定居爱尔兰。
著有:《生与死的光辉一面》《大势已去》《一个孤独的学位》等。
|
| 目錄:
|
第一章 阿诗琳
第二章 布莱肯
第三章 阿诗琳
第四章 布莱肯
第五章 阿诗琳
第六章 布莱肯
第七章 阿诗琳
第八章 布莱肯
第九章 阿诗琳
第十章 布莱肯
第十一章 阿诗琳
第十二章 布莱肯
第十三章 阿诗琳
第十四章 布莱肯
第十五章 阿诗琳
第十六章 布莱肯
第十七章 阿诗琳
第十八章 布莱肯
第十九章 阿诗琳
|
| 內容試閱:
|
我知道
一切都已终结
笼罩着一丝淡淡的忧伤
在生与死的另一个洞天
献给
每一个曾经迷茫过的人
愿你们能步入明天
第一章 阿诗琳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永无边际的黑夜,失去了意识的支配,身边空寂无物,所有的一切都不复存在。假如此时此刻,此处存在着另一个你,只是假如,那么这种向过去无限延展的逃离感似乎在预示着什么,仿佛要将你的神智紧紧地束缚在樊笼里。但是,你要知道,这里并不会真正存在另一个你。我一无所有,我一无是处,我就是我,无可替代。我从未在这个世界存在过。除此之外,我没有必要那么做,那样,又会残存怎样的记忆?
莫回首!勿让黑夜蚕食了你灵魂的深处!
假如,我只是说假如,我正在与自己进行一场灵魂的交谈,那么我坚信,这里一定有另外一个我存在。这样通过另一个我的存在就足以自圆其说,证明我确实存在于这个世界。
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片虚无飘渺的景象,而此刻的我,正遨游在卷帙浩繁的星空。星星如磐石般沉寂,却不尽相似,只因它们依旧闪耀着浅淡的微光。我思忖着,思忖着,觉得我能够以一种异于以往洞悉事物的方式,洞察它们的声音。
这声音不是天籁之音,亦非窃窃私语。此刻,我已句尽词穷,不知如何用言语来描述眼前的情形。假如,你有幸聆听过这样的声音,泪珠、眩目的日光以及渊博的知识糅合发出的鸣响,或许这个声音足以阐释徜徉的群星发出的低吟。我并非没有自知之明,我知道自己孤陋寡闻,但我敢发誓,这是唯一可以肯定的事情,亦是初次学习的结晶——群星知悉我们不知的一切,并将永远地高悬在上空。
此时此刻,我的大脑开始被各种各样的问题充斥着:我到底是谁?我在哪里?我现在在做什么?
此刻,我正飞驰在堕落之路,从闪着微光的黑夜里坠落,速度让每个人的心挤到了喉咙。此情此景,身体的本能刺激着我,它不停地劝诫我,伸出你的双手来拯救坠落中的我……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我既没有小腹,也没有双手。
堕落的担忧一直深深地困扰着我,它无孔不入,深深根植在我的潜意识之中。除了静默地等待沉沦的降临,我没有任何办法阻止这一切。当我竭力要魂归故土的时候,身下的这片土地散发着璀璨的光芒,似乎在迎接我的归来。
星星啊,快快挽留我吧,救救我吧,将我揽入你的怀里……
事实最终证明了它们不是星星,那只是一架巨大的喷气式飞机着陆时开启的灯光,此刻,它们的存在使得文明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不知何故,我忍不住想要哭泣,我知道我不能那么做——藏匿了双手,辞别了身体,拭去了眼泪。
当我坠落凡间的时候,又会发生什么呢?
现在的我如此贴近地面,我能清晰地窥探到停靠在路面上的那辆私家车,路边的街灯以及家家户户初上的华灯。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人,在某一个角落,为我擦亮明灯,期待我的归来呢?那么我又该魂归何处?
城郊有一所房子,高耸的屋檐耸入云端,径直地指向我到来的方向。因为我没有躯体,那么也就无所谓粉身碎骨,更不用去担心受到什么损伤。但不知何故,我的意识开始发生动摇,它不断地晃动着,我似乎被一种神秘的力量牵引着,此刻忘却了是谁……不论我曾经做了什么,徒将我的背影留给身下的大地。
这时候,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失败。此刻我已经穿过云层,却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预想的大碰撞没有发生,甚至都不曾着陆。我所做的不过是悬浮在半空,俯瞰着一双双眨动的眼睛。他们离我只有一英尺的距离。你可以想象,当你想去亲吻一个人的时候,你矜持地与他保持的距离亦是如此。可惜我早已忘却了自己的初吻,但幸运的是,我依稀记得吻是何物,正如我记得屋檐与巨型喷气式飞机。我依然能够分清何为浪漫、思念、爱慕与憎恨,当然这一切与我毫无关系。或许,我从未坠入爱河,亦或是在遥远的过去我曾经数百次地沐浴在爱的波流中,只不过是时间太久的缘故,我没有残留丁点的记忆。此时,我不能明辨哪一种意识是更为忧伤的。
当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眼睛不停地眨动着,时睁时闭。那双深邃的眼睛,来自那个身穿白衣的男孩!我清楚地看到他的目光并没有投向我这里,假如我有躯体,我敢说它一定会在那个男孩的头顶徘徊,头脚相偎地窃窃私语。
夜已深,所有人都在黑夜里披上了伪装,包括我们两个。但只有他真真正正地伫立在那里,就是这里,而不是其它地方。
如果我能够活动,我早已离开这里了。我会给他足够宽敞的空间,尽管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空间是多么狭小。我开始为自己的见闻感到局促不安,甚至彷徨。就现在的情形而言,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一直处在被注视的状态。但我又能做些什么呢?什么也做不了。现在的我就像是一架照相机,机械地采撷照片,而不能独立地去控制视角与焦距。
所以我一直注视着男孩上下跳动的睫毛,聆听着他富有韵律的呼吸。他的肺发出的呼吸像一把牛排刀在切割牛排。与其说这是一个哮喘病人的呼吸,不如说这是一个人坠入深渊时绝望的呻吟。但是,他现在还没有坠入绝望的谷底,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假如一个人像他这样生活,那么他又能在这个世界苟延残喘多少时日呢?不可否认,这是一个让人伤心的话题。于是,我艰难地做出一个决定:用我那虚无飘渺的双手堵住我根本不复存在的耳朵。
从外表来看,我的注意力似乎完全转移了。到现在为止,我一直游弋在他的上空,聆听着他那无休止的痛苦发出的类似呻吟的呼吸,就这么一直漫无目的地等待着……
我想,此刻我一定是坠入了梦乡。从星空的坠落以及那个男孩的呼吸声中,我察觉到了伤痛,我知道他们一定都不会是真的。展现在我面前的一幕幕场景不过是一场华丽虚无的梦境罢了,当我明天一觉醒来的时候,唤醒我蠕动的肠胃、我的双手以及那完整无暇的回忆,我想我一定会惊惶失措地摇动我的头颅。在那个时候,我会抓过一支笔,在我的记忆消退之前奋笔疾书,写下所有残存在脑海里的细枝末节的回忆。我甚至幻想过这样一个场景:当我在黎明时分醒来,看到这一切会是多么欣喜若狂……群星用智慧谱写一曲华章,赋予我力量通过呼吸洞穿人类的情感。
仅仅是这样一个梦,就足以让我抓狂。为什么不能梦到那些能够让我流连忘返的东西呢?诸如一对情侣久别重逢后的欣喜或者是高悬在激流飞瀑上的蔚蓝天空?为什么单单让我梦到这样一个让人心生怜悯的小男孩呢?
我仔细地打量着这个男孩,竭尽全力加深镌刻在脑海里的那些细节,这样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等到我醒来的时候,我依然可以清晰地去追忆它们。当我在观察他的时候,我忽然有一个意外的发现:我可以自由地转动相机的视角,当然幅度不是太大,只有那么一点点。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可以在床头或者从他那把偎依在墙角放蓝吉它的地方注视着他。我甚至可以……不,我不能逃离这个房间,我不能无情地将他一个人独自留下。此刻,他在我的梦境里演着独角戏,我注意到,当我将视线从他身上转移到屋子里以便探个究竟时,过不了多久,我的注意力又会情不自禁地转移到他的身上。
这就是我的注意力回到他的身上时,看见的一幕景象:一个约莫十六七岁的少年,棕色有点卷的头发遮掩着脸庞,一双明亮的眼睛,由于身处黑夜的缘故,此时的我无法分辨出它到底是绿色的、蓝色的亦或是深褐色的。他身着一件灰色的T恤,安静地躺在床上,赤裸的胳膊放在被子的表面。此刻的他,端庄而安详,除了偶尔眨动的眼睛能看出还是个活物来,就连那貌似衰竭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吸声在此刻也偃旗息鼓了。当我蓄意地想去倾听他的呼吸时,我发现,如果刻意那么做的话我还是依稀可以听到的。这足以说明,在这个梦境中有些事情我能够支配,显而易见,这个神奇的听觉力现在就在我的掌控之中。
我紧贴着这个男孩的眼睛,打量着他。在他身旁的桌子上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来,就在他飞身冲向电话的时候,我的眼睛不曾离开过他,我甚至开始猜疑这个电话在梦境中到底承载了多大的重量。或许,好戏真的要在此刻开始上演了……
试问,有多少人会在苦难面前袖手旁观、无动于衷呢?既然我已经卷入了这场漩涡,所以我开始祈祷这个梦能够朝着更加有趣的方向发展,哪怕是类似于动作片或者悬疑片之类。难道我喜欢电影里那些硝烟弥漫追逐的场景么?是不是我应该记住那些场面,即使是身处梦乡?
电话声不再响起,男孩拿起手机,似乎要看看到底是谁给他打来的电话,然后又把手机再次放下。突然手机在他的手中再次响起,我敢发誓,这一次声音绝对更响,甚至要和汽笛声平分秋色了。我不得不说,在手机响起的那一刹那,他的反应同手机的声响如出一辙,那是在突发情况下的直觉反应。这一次,在他将手机放回桌子旁的老地方时,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关机。
男孩此时将视线从手机转向身旁的闹钟,指针显示的时刻是十二点二十三分。他平躺在床上,双眼凝视着天花板——那里有我的存在,但是又没有我的踪影。时间在此刻被拉得很长很长:十二点二十四分、十二点二十五分、十二点二十六分……我开始逐渐意识到,我一直苦苦等待的场面的幻化,似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了。
一声轻轻的叩门声打破眼前的魔咒。男孩的双眼似是受到了什么刺激,睁开的眼睛又迅速地闭上。
“布莱肯?”一个梳着大背头的中年男人在微敞的门口左右环顾着,小心翼翼地喊了一声。这个男人的领带歪斜着,他不得不用一只手去试着平整它,然后,他用手将门推开一些,静静地等待着这个男孩——布莱肯——发出什么声响。
然而布莱肯并没有按照他预想的那么做,尽管我心里很清楚他此刻没有入睡。这个男人蹑手蹑脚地走向他,无奈地叹息一声,然后悄无声息地坐在了他的床边。我在心里嘀咕着,这个男人会不会是他的父亲,他是不是希冀着布莱肯能够睁开眼睛同他交谈几句,或者说,他更钟情于此刻的宁静。
如果我愿意的话,布莱肯的呼吸声依旧会刺痛我的心扉,可是我没有这么做。我不得不使出我的看家本领了,使用奇特的音量控制功能来尽量减小声音,仅仅是降低声音而已。他的爸爸,或者随便是他的什么人都可以,似乎没有察觉出什么异常的声音。他先是瞥了一眼被月光笼罩着的墙面,收藏的一串串钥匙链错落有致地悬挂在远处墙边的窗棂上。一副超现实主义的达力版画张贴在门边,床边有一张平克?弗洛伊德的“城墙”宣传海报,还有一张海报是一只足球划破无垠的长空。
达力,我当然记得萨尔瓦多?达力?多明戈。巨型喷气式飞机,还有香吻。萨尔瓦多?达力?多明戈还有平克弗洛伊德乐队。我是多么希望,多么希望你能够出现在这里。我依稀听到动听的旋律在脑海里徘徊,对他们残存的记忆莫名地刺痛了我的心扉。
布莱肯的父亲环抱着双手在床边踱来踱去,他将注意力转移到紧挨在身边的男孩身上,就那么凝视着布莱肯,直到他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现在残留在我脑中的影像不是什么动作片,而是一部类似悲剧的电影,在这一夜之间我看到了太多。此时,我不得不与我的大脑进行一番激烈的斗争。快快醒来吧,睁开你的双眼!与我的理性相比,很明显,我的感性占据了上峰。这一刻,依旧难分伯仲。不管历经了多少次的思想碰撞,我的注意力依旧没有从布莱肯和他老泪纵横的父亲身上转移。天啊,我的苍天!快点让我醒来吧!如行吟般,我不断地尝试着。苍天啊,我的苍天啊!快点让我醒来吧!我就这样不断地吟唱着。怀揣深深的渴望,没有停歇。
但是,无论我多么声嘶力竭地祈祷上苍,依旧无法恢复我的直觉。我身陷囹圄,被这四面墙层层包围。
不经意间,布莱肯的父亲起身,挪动着脚步朝紧挨着他身后的那扇门退去。这使得我成为了布莱肯唯一的见证人,此刻的我显得有些落寞。我依旧注视着他的睡颜,双唇微微张开,呼吸也变得孱弱了。在某种程度上,我敢说他假戏真做了,他的伪装变成了事实,因为他就这样一直持续到黎明第一缕曙光的降临。
当太阳从地平线上崭露头角,鸟儿在布莱肯窗外的枝头上叽叽喳喳地叫唤时,我的意识开始模糊了,我分不清楚自己到底是谁。布莱肯翻了一个身,蜷缩成婴儿的模样。他抬起头,借机带动自己的身躯离开床铺。在明媚阳光的照耀下,他的鼻子有点天蓝色的样子,这个颜色看起来和他宽松运动裤上的条纹很搭配。现在他终于站起来了,我终于可以目睹他的容貌了。他的身材看起来有点瘦削,中等个头,鼻尖有一个明显的肿块,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用受过伤来解释。但是,你千万不要质问我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要知道,我是一个连自己是谁都没有弄清楚的人,你又如何奢求我告诉你我的名字呢。布莱肯将手指深深地埋进头发里,然后奋力地抓挠着。面对着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我开始不停地围着他转,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完全可以围绕着他的身体进行三百六十度的旋转,或是聚焦到他那双赤裸的脚,或是头盖骨的后方。
我可以依附着天花板或者以光速穿越窗户。但是,真正的诀窍在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穿过窗户然后飞跃到户外空旷的场地,但不得不说这真的是一项超越我能力范畴的壮举。与此同时,布莱肯打开卧室的门,向客厅走去。此刻我像是被一股强劲的电流紧紧吸附着,逗留在他的卧室里变得那么不切实际,正如不久之前想要纵身离开他的卧室一样。
突然间,一条比灌木丛稍微高一点的橘黄色夹杂着白色的小狗朝布莱肯狂奔而去,它将前爪搭在布莱肯的左腿上,惬意地休息着,它的眼睛也没有闲着,用恳求的目光盯着他。
“摩西!”布莱肯厉声呵斥。
这是我从他嘴里听到的第一句话,他的嗓音比我预想的要浑厚多了。布莱肯低下身,粗鲁地把狗从他的身边赶跑了。首当其冲遭遇冷眼的是他的父亲,看来这条狗也在劫难逃了。难道这里没有一个人是这个少年愿意倾心交谈的吗?
我又把注意力放在了他的呼吸上,仅仅持续了那么一小会儿,但是相对于降临的疼痛来说,这短暂的时刻已经很奢侈了。对他而言,今天早晨的状况与昨天夜里的情形相比较,似乎没有太大的改观。
摩西在一旁孤独地啜泣着,因为它遭到了主人的冷眼。当一个约莫四十岁上下、身着褪色亚麻布短裤、上身套一件棕色羊毛衫的女人出现在过道里的时候,小狗主动给布莱肯腾出了空,它的眼睛一直在布莱肯的身上游移着。她扎了一袭马尾辫盘在后面,至于她的眼睛,和布莱肯的眼色不分伯仲。因此,要想从他们的眼神判断谁更疲倦一些显得似乎不切实际。
“早上好,”这位妇人打了个招呼。她探身朝向布莱肯,想要把他揽入怀中,他很顺从地接受了。
“早上好。”他从牙缝里咕哝着回了这么一句。
“我正打算下楼去吃早饭呢。”妇人说道,她的一只手搭在他的胳膊上,“有没有什么合你胃口的呢?”
布莱肯抿了抿干涸的嘴唇,耸了一下自己的肩膀。
“那吃点煎蛋怎么样?”她提出这个建议.
“好吧。”他用手挠了挠自己的T恤,顺口说了一句,“谢谢。”
当他们并肩下楼的时候,摩西紧紧跟在身后。我现在开始对我最初的假设——这位妇人就是布莱肯的妈妈——心生疑虑了,但显而易见的是,他对这位妇人还是了如指掌的。有人愿意为他做煎蛋,那么至少说明她是在为他做些什么事的。难道是我对他们的交谈想得太多了吗?至少这点我可以肯定,她对他所经历的痛苦一无所知。
转身来到厨房,布莱肯坐在一把木椅上,眼瞅着妇人从冰箱里取出鸡蛋,从火炉下方的架子上取出煎锅。他清了清嗓子,将一只赤裸的脚架在对面的椅子上。
“是不是苏尼塔已经回家了?”他打破沉默道,“你有没有和她说话?”
“我和她说话了。”妇人转头面向布莱肯。她对他微微一笑,但是她额头上的皱纹似乎暗示着什么,不是出于欢愉的笑纹。“大概一个小时以前,她一直在喋喋不休地抱怨昨晚飞行途中坐在她身边的男人没有间歇地打着喷嚏,除此之外,她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异常。”
布莱肯点头示意了一下,一个哈欠游弋到他的嘴角,这使得他不得不张开下颌。
“你要不要再喝点什么?”她试着问道,“果汁怎么样?”
布莱肯漠不关心地耸了一下肩膀,果汁这个提议在我的心里荡起了一丝涟漪。我当然记得,这当然不能和喷气式飞机或者达力相提并论。我记得我还钟情于什么东西,橙汁,苹果汁也可以,但是橙汁还是我的首选。尽管此刻我还不是那么饥渴,但仅仅提及果汁就让我不能自已了。我对橙汁的渴求可以与酒鬼对伏特加或者威士忌的渴望相匹敌,在这个节骨眼上,似乎没有什么比新鲜榨取的一杯橙汁更吸引我的注意力了。
快点醒醒吧,我不断催促着自己。难道你真的不想尽快逃离这张床,然后给自己斟上一杯真实的橙汁么?
当我正沉浸在情感宣泄的世界时,厨房里神不知鬼不觉地又多了一个女人。不管从哪个方面,她都与先前的那个女人很神似。说实话,要不是第一个女人把自己的头发扎成马尾辫盘在后面,我想我一定会把她们错认成同一个人。
“道恩,”先来的那个妇人喊了一声,伸手轻轻抚摸了一下后者的手臂,“我正打算给布莱肯煎几个鸡蛋呢。要不要我再多煎几个,你也一起吃点?”
道恩不停地摇动着她的下巴,似乎这是一个很棘手的甚至是没有答案的问题。
“那么,坐下吧。”妇人补充了一句,随即又回到刚才的话题,“我可不想再提及煎蛋这个问题了。”
道恩摇着她的脑袋,向桌边缓慢地挪动着脚步,然后停下来研究身后那堵杏黄色的墙面。看起来似乎是不久前拍摄的布莱肯学校的一张照片,紧挨着一个空挂钩,旁边是一幅全家福。我和她一起研读着这幅全家福,终于证实了道恩的身份以及昨天夜里坐在布莱肯床边的那个男人就是他的双亲。但是到现在我没有弄明白做早饭的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在这幅全家福里,还有另外一个女孩,年纪不大,金黄的头发很短,像个假小子。
“啊,天哪!”炉子旁的女人发出这样的呼声,她察觉到道恩的视线落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无力地吐出这个字眼。“我得先去参加葬礼,等我回家后就把这些照片收起来。今天晚些时候我会收拾好的。”
“啊,我的神!”我被她那句话隐含的意义深深刺痛了。我希望我的理解是错误的,这幅全家福里的小姑娘年纪实在是太小了,她不可能就那么飞往天堂的。从这幅照片来看,她的年纪不会超过六岁。但是这个女人所说的参加完葬礼后回家可能会有很多种解释——可能是一位年长的亲戚驾鹤西去了……我不断地提醒自己,不管怎样,那只是我的一个猜想罢了。没有人死去,我不相信那是真的。
布莱肯的母亲坐在他正对面的桌边。他们彼此点头示意,但是都保持缄默不语。整个厨房里唯一的动静来自悬挂在墙上的葵花状的挂钟发出的滴答声,以及那位在炉子边的女人刮擦煎锅锅底发出的声响。
“莉莉?”布莱肯喊了一声,终于打破此刻沉默的僵局。
那个扎着马尾辫的女人转身看着他,“嗯?”
“我想去冲个澡。”他站起身,“能不能等我冲完澡之后再吃这些煎蛋?”
“宝贝,当然没问题了。”莉莉的脸上漫溢着同情之色,“你想什么时候吃都可以,我会一直为你温着它的。”
布莱肯朝他的妈妈瞥了一眼,她的双眸也是一片淡蓝色,但要比他的眼睛明亮。她盯着自己的双脚,摩西蜷缩在瓷砖铺就的地板上,迷惑地盯着她们三个人。道恩的双唇上下颤抖着,略微张开,好像竭力阐述自己的想法。“他已经这样了……”
“我知道,”布莱肯打断她的话,转身径直朝楼梯方向走去。一时间,她们两个人傻了眼,他恨不得扎上翅膀快点从这个厨房消失。
“布莱肯,”他的父亲从楼梯上方喊了他一声。当布莱肯抬头仰望自己的父亲时,他的双肩蜷缩成一团,“刚刚我听到你卧室里的手机铃声,”他的父亲插了一句,顺势把自己的双手插进深蓝色睡衣的口袋里。他的脸上散发着这个屋子里每一个人都深藏不露的不愉快的神色。我注意到,此刻仍旧没有那个金发小姑娘的身影。但是,如果人们下定决心,难道他们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吗?
假如我能够全神贯注,从这幅全家福里去勾勒出她的面孔,使出我的浑身解数让她出现,她是不是就会真的出现在我们面前呢?淡黄色的头发凌乱地贴着她的枕头?我到底能不能在我的梦境里创造出这样一个奇迹呢?
我想,他们一定会说我是在做白日梦,姑且不论我是不是做错了或者根本就是一个谬论,毕竟我幻想的那个小姑娘能和我们一起站在这个过道里的画面没有出现。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知道了。”布莱肯的手指拨弄着卷曲的头发,“我打算洗完澡之后去接收消息的。”
布莱肯走到楼梯口处,与他的父亲擦身而过,穿过二楼大厅的过道,径直走向浴室。我眼瞅着他脱掉T恤和宽松的运动裤,信手把它们丢在地板上。而后,他赤裸着身子走向喷头。他站在水流的下方,低着头,任由水流肆意地从他的脸庞滑落。他闭上双眼,十指抠住了两个腋窝,双肩开始不由自主地颤抖。他把脸埋进自己的胸膛,悄无声息地擦拭着泪水。在潺潺水声的遮掩下,他不住地颤抖、啜泣着。
要是我曾经目睹过有谁这样哭泣,我想我早已将之抛到九霄云外了。但是,在我神志清醒的时候,我敢保证我是不会轻易忘记的。伴随着那个想法是愈积愈多的煎熬,慢慢聚集以至最终我的大脑不得不改变思考的方向,使我得以解脱。
我踏入一片安静、祥和的净土,没有沿着降临时经过的那片星空和屋檐,仅仅是伴随着一片阴影渐至灰色最后变成一个黑色的斑点。布莱肯从我的世界消失了。
有些事情错实在是太离谱了。当我在黑夜漫无目的地游荡时,恐慌不期而至。仅仅是想尝试着脱离自己的躯壳四处游荡,看看到底能把我带往何方。哪怕是沮丧或者恐惧,也没有任何的表现形式。本已模糊的思想此刻更是沦为一片虚无,用双手去攫取本不存在的真实。
没有什么会亘古不变。
无处可藏,除了你想蛰伏的那片热土。但是确有这样的地方,那个男孩,布莱肯啜泣的浴室。尽管我和他身处漫长时光隧道的异端,当我去聆听时,依然能够从遥远的地方听到他的声音。当然我关闭视觉功能,正如此前早些时候调小对他呼吸声的听觉功能,当然我有能力毫不费力地遮盖他的整个世界。
但是现在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是,当我过滤掉那些声音,乎没有什么可以填补眼前的空白,徒留下荒诞怪异的我在黑夜里起舞。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梦。此刻,我本应该被吵醒。我告诫自己:“再去尝试一次!”因此,我更加用力地去鞭策自己。我不禁开始咒骂这无际的黑夜,为了我生命仰仗的知觉奋起反抗。或许,真的见效了。或许,此刻我正昏厥在某个医院的角落。
“尖叫。”我给自己提了这样一个建议。这样我就能让护士和医生知道我在这里,他们就不会对我熟视无睹了。
这个建议听起来似乎是天衣无缝,但是一旦付诸实践,尖叫和鞭策自己一样显得软弱无力。因为我没有使用我的身体,它们的作用也就大同小异了。我能做的一切不过是换着法子去尝试。
此刻我没有醒来又会发生什么呢?我将何去何从呢?
不要再胡思乱想了,我对自己说,你绝不能丧失希望,那样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
我不知道我还有什么可以去挥霍,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谁。此时此刻,我所遴选的那些私人信息在我的心里隐隐做痛,仿佛要昭然若揭,我很清楚,世界不会因为我的离开而停止运转。我不断地奢望,通过布莱肯以及他家人的画面,我一直关注着那些细节。孤孤单单一个人,我钻入自己的内心世界以期能够探寻一些关于我自己的身世,此刻,我的梦想之旅也被暂时搁浅。
沉默并不具有金子那般的价值,却颇似地球上唯一残存的那个人怀有的心态,不管怎样,它能帮我静心思考。下面就是我还能记起的一些信息:
1 毋庸置疑,我喜欢橙汁。
2
我是个女人。(事实上,当我看到布莱肯脱去他的运动裤站到沐浴喷头的下方时,我才唤醒这个沉睡的记忆,但是我对此一点也不感到奇怪)
3
我不得不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因为之前我从来没有亲眼目睹过裸男。(我可以肆意欣赏他身体的任何部分,尽管我是处于隐蔽的状态,但是我还是会感到惴惴不安)
4
布莱肯的小狗是一只博美拉尼亚犬。(当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个品种,但是它牵动了我的记忆——可卡猎犬、猎兔犬、大丹犬、血猎犬、松狮犬……)这不禁让我想起了这样的细节:我是一个喜欢狗的人,而不是钟情于猫的人。
5 我不喜欢蛇或是某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爬行动物,尽管那些个头小的动物不会把我怎么样。
6 我喜欢你能在一旁为我翩翩起舞高歌一曲。
7 我不喜欢曲调忧伤的歌曲,让人撕心裂肺的歌曲除外。
8 我最钟情的颜色是浅绿色。
9 我是个右撇子。(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设想当我去开门的时候,我总是情不自禁地伸出右手)
还有什么呢?谁是我最亲密无间的人?我的朋友还是家人?当他们开口叫我的名字时,他们呼喊的名字是什么呢?当他们盯着我看的时候,他们看的又是谁?
一想起这些事,我的头就变大了。我就像是一部小说,所有的人物描写都被有条不紊地剔除,徒留如“这个、那个、哪里、请讲”等无关痛痒的字眼。
我没有设定什么故事情节,甚至都没有关于我的足够信息来塑造最基本的性格特点。我不得不怀疑,等到我醒来的那一刻,我是否能够自食其力养活自己。要是真的如我所想,到时候又会是谁围绕在我的身边帮我料理这一切呢?
我大脑中硕果仅存的只有那么一些有印象的人,萨尔瓦多?达力、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的成员……还有谁呢?绞尽脑汁去想。音乐团队,画家,那么又能够记起谁呢?里昂纳多?达?芬奇!蒙娜丽莎那神秘叵测的微笑在的我脑海徘徊。文森特?梵高,他毅然割掉了自己的耳朵。米开朗琪罗,绘出西斯廷大教堂的天花板。
披头士乐队高唱着:“我想牵你的手!”马文?盖伊《道听途说》,蒂娜?特纳《山高水长》……但是这些都是历经岁月洗礼的老歌,尽管我不能确定他们到底是哪年哪月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但是直觉告诉我它们就是老歌。那么我最后听到的又是哪一曲呢?最让我魂牵梦绕的又是哪一首歌呢?
地球是圆的,而非方的。地球是围绕着太阳转的。这些都是在学校里学到的教条哲学,我早已经忘记是谁教会我这些知识。
下面还有一些再简单不过的问题——我喜欢太阳吗?
10 当然了,我喜欢太阳。
11
我还喜欢雪。(我在银装素裹的世界里做什么?溜冰?滑雪?没有溜冰鞋,没有滑靴,也没有滑雪板的记忆在我的脑海转瞬即逝)
12 我会溜冰又会滑雪,但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个菜鸟。
13 我会游泳。
14 我能倒立。
除了橙汁,我还喜欢什么呢?
15
冰激凌。(好像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橙子味,还有巧克力、奶油山核桃、泡泡糖、黑樱桃、曲奇奶油和本?杰里的南瓜乳酪蛋糕)
草莓、椰子、薄荷巧克力、覆盆子……在我的意识里流淌。我的手紧紧握着诱人的冰激凌蛋挞,这就是我的手!它的影像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我的手比布莱肯的黑些,像是橄榄的颜色……要是我能够看到的话,一定还会有更多,包括我的身体,我的年龄,我的名字。
我已经察觉到了,尽管我没有那方面的知识,我身体的某些部位依旧保持原来的样子。在无边的黑夜,那些部位搜寻着迷失的自我……如果我用心聆听,在黑夜里独舞,我正一步步揭开神秘的面纱。
我就是我,独一无二的我,我不是任何人。我只爱橙汁和冰激凌,我终究会被某一个来自现实世界的人发掘,然后在某个时候重归现实。我将要睁开我的双眸,在日光下载歌载舞,用尽力气大声呼喊出我的名字,让所有我不认识的与不认识我的人停下脚步,驻足凝望。他们投来的目光会让我兴奋不已,狂笑、欢呼,直到用尽我最后一丝力气——
我就要满十六岁了,我的名字是阿诗琳。
|
|